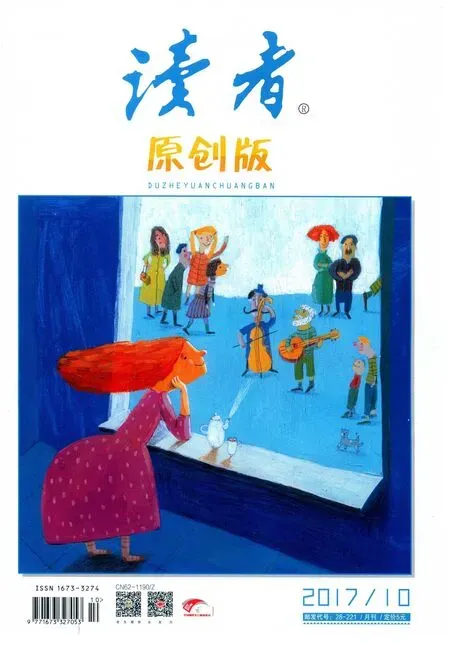时光雕花刀
文|魏 邙
时光雕花刀
文|魏 邙

第一次,在街边小卖部的冷饮摊旁。我买了一根雪糕,给自己解暑;她也买了一根,给她儿子解馋。
我们去附近的麦当劳叙旧。
她聊脚踏实地的生活,聊丈夫,聊孩子,聊婆家;我聊浮在天上的梦想,聊文字,聊音乐,聊情怀。
以致最后,我们无话可说。
静下来,我才发现,她儿子小而圆的脸颊上都是番茄酱,一双眼黑亮黑亮的,水洗过一般,只瞅着我盘子里的汉堡。
我笑着推了过去。
他那双眼睛,和他妈妈的很像,高中时代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女。突然想到些什么,我问她:“你还记得那个‘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事件吗?”
五年来,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密集颁布实施,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制定和修改的法律有十几部之多,其中有六部是新制定和修改幅度较大的;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陆续出台;史上最严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施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对社会公布。为全面推进绿色发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时,经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被放到了同一小组。一系列的顶层设计密集推出,就是要彻底改变发展观念,坚决摒弃错误的发展观,不再以GDP论英雄。由此可见,中国关注经济增长质量,绝不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而是着眼于中长期发展。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开:“怎么会不记得?是‘老班’用来警告那些不规矩、早恋的同学的。”
“我到现在都记得,你当时抢着回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全班同学笑成一片,连班主任都笑了。”
她先是愣住,目光幽幽,仿佛正穿过尘封的岁月;然后嘴角慢慢溢出笑来,接着拍掌大笑,眼角闪着泪花。
周围的人都看了过来,我和她的孩子对视一眼,隐隐有些局促。
离开时,她付了钱,她说:“毕竟你还在读书,好歹让我这个已经工作了的人大方一回。”
服务员找零时,她摆了摆手,没接,想来她现在过得不错。
分别后,母亲打了一通电话,让我去菜市场买几个素包子。那是这一天中的第二次,我遇见她。
正值日落,菜市场里人潮涌动,脚步声、叫卖声、交谈声、剁肉声、捞鱼声混在一处,沙沙地敲击着我的耳膜,有一种令人茫然的宏大感。我只听见这茫然的细部,有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她。她守在一个菜摊前,长白袖罩,灰黑围裙,正拉着个拣菜的阿姨争论:“我们一点儿油水都捞不着的!不是我在乎这两毛钱,那些个菜农见天儿摸黑拉菜过来,也得让喝口水、抽根烟吧!是不是这个理儿?真不是我贪这两毛钱,就两毛钱,我图什么!哎哎哎!您可别掐我这菜根儿……”
我在远处,隐约望见她含糊地笑着。那笑,像是浸过水的红窗花,经日头一照,干巴巴地贴在脸上。
卖素包子的就在她前面两个摊位,我却没有勇气再踏出一步。
日头一闪,沉沉地落了下去。她不经意地往我这边一瞥,我立马蹲下,躲在一个摊子后面,泪水不由地流了出来。
当年那个在要求全校女生都剪短发的学校里,拼死护住自己一头靓丽乌发的小姑娘;当年那个在学习紧张得要命的高中时代,依然能在书堆里架个镜子照好半天的小姑娘;当年那个豪情万丈地说出“只争朝夕”的明媚鲜妍的小姑娘……与眼前这位形容枯槁、斤两必争的妇人,我竭力说服自己,她们是一个人。
原来,之前我一直装作看不见,哪怕刚见过一面,我也一直欺瞒自己说她过得很好。
高中时代,我们一起背李清照,解函数题,拎着饭盒去食堂打饭,去操场看男生打球,在树荫下憧憬未来,连上厕所都要一起。我们本有着最最一致的步调,却在高考过后,分散了。
我一直以为我们都在彼此看不见的地方结识了新的朋友,过着新的生活。我怕我的联系是一种打扰,我一直期待着完美的不期而遇。我固执地以为她和我一样,读大学、读研,或者有一份优裕的工作,我自以为是地想象着这一切。然而,生活总是在背后,出其不意,狭路相逢。
少女那双水灵乌黑的眸,已作麻黄。
我替她觉得委屈,想一把拉过她,拉着她跑过四年的匆匆岁月,回到恣意鲜明的高中时代。可是我没有,我躲在一个菜摊下哭,一堆土豆嘲笑着我。
时光是一把雕花刀,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平凡生长。起初,这把刀很锋利,但我们渴望成长,所以任刀刃刺入骨血,仍能咬牙坚持。我们以为自己已经长成了最好的模样,可是,我们忘了,世上能说结束的事很少,时光推移,岁月的刃越来越钝,当年能承受住刺骨之痛的我们,却挨不了一刀一刀地细磨慢砺,所以我们宁愿推开这把刀,任自己荒凉生长。
或许,她比我更有直面生活的勇气。
而我,却永远地失去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