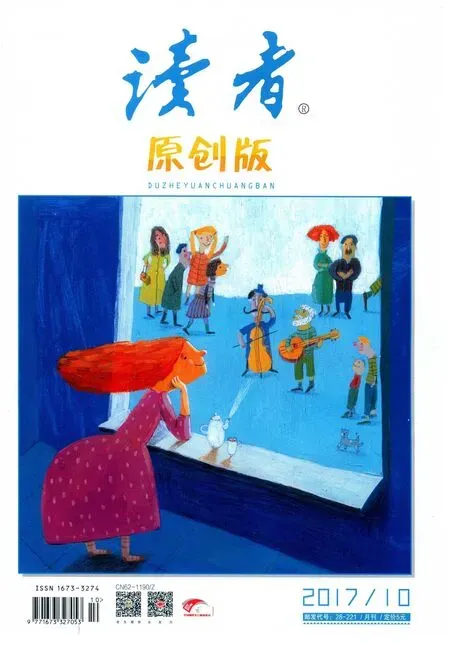一树花落一春尽
文|穿过流水
一树花落一春尽
文|穿过流水

初春的傍晚,想去中学时的校园看看。站在教学楼下,周围是葱郁的树木。从操场的铁门向左、向右各走约15步的地方,曾栽有几棵很大的玉兰树。十几年前,玉兰花开的时候,隔着教室,就能闻到一阵阵的香气。风起的时候,一楼走廊的地面上,会散落很多白色的花瓣,偶尔也会有一两朵被吹到二楼来。说实话,少年时我对玉兰花完全无感,只是觉得花开时整个校园的线条,似乎变得柔和了许多。
十几年前,我读高一,教室在二楼。一楼是高三的教室。每到下课时,高三的同学喜欢在楼下打羽毛球,我和同桌则喜欢趴在栏杆上观战。其中有个女孩很醒目,高挑的身材搭配一头柔顺的长发,头发后常束着漂亮的蝴蝶结。第一次见到她时,学校广播里正放着王菲的歌:“上帝在云端,只眨了一眨眼,最后眉一皱,头一点……”歌的前奏真好听,令人眼前忽然闪过一道晶莹的光。常和她打羽毛球的是个外形清俊的男生,风度翩翩。我一直觉得这种搭配很完美,很有偶像剧的意味。后来我知道,女孩叫晓瑾,男孩叫梁晨。
记得那是高一奥数比赛前,老师安排高三获过奖的人给我做课余辅导。梁晨作为上一届省奥数比赛一等奖的得主,便按照和老师的约定,下课后在一楼的走廊等我。我去找他时,他正低着头在习题集上勾画标注。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来了,准备得怎么样了?”后来我又认识了晓瑾,晓瑾说她以前就知道我,因为学校的宣传橱窗里贴过我的作文。“梁晨上回说你写得真好。”她边说边捋了下头发,柔顺的发丝滑过“天鹅颈”,洒脱而灵动。
我们都很喜欢听CD和打游戏,熟络后,三个人常待在一起。课余时间除了学习,就是混迹于CD店和游戏厅。那时候没有网吧,游戏厅算是紧张学习之余的消遣了。
学校运动会上,晓瑾参加400米接力赛,梁晨中途蹓出去,打车到肯德基买了加冰的橙汁和汉堡。赛前,他抹着一头的汗把东西递给我,说:“你帮我把这个送去更衣室给她。记得跟她说跑完再喝,喝了再跑会吐的,哈哈。另一份是给你的跑路费。”
寒假的时候,我们经常到晓瑾家写作业,彼时,我像一个1000瓦的电灯泡,在她家闪闪发光。晓瑾倒不这么认为,她觉得我的存在反而让家人不用太担心他们早恋的问题。但既然是灯泡,自然还是要有身为灯泡的觉悟,所以多数时间我都在客厅吃桃子、吃虾条、复习令我头疼的化学。偶尔找他们问题目,会看到晓瑾在看梁晨,有那么五六秒,她的目光完全定格在他的脸上。
他们的高考,平静、顺利。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考到同一座城市。临走前,我们来到城里新开的一家咖啡馆吃散伙饭。不擅长面对离别场面的我,使劲吸着冰巧克力,吃下了一半的比萨和薯条。末了,梁晨很笃定地说:“我们会经常见面的,毕竟我们的家都在这里。”晓瑾点点头。我“嗯”了一声,有点儿难过。
我高三时,得知他们分手的消息,是晓瑾写信告诉我的。梁晨觉得晓瑾太贪玩,不思学业,对新事物缺乏兴趣,两个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晓瑾觉得梁晨在新学校太受欢迎,和同系的一个女生走得太近。“他没解释,好像理应分手,可能这几年都是我一厢情愿。”晓瑾在信的末尾写道。五一的时候,她来我家找我,希望我帮她去后勤老师那儿拿学校仓库的钥匙,说要找一个很重要的本子。拿到钥匙后,整整一个上午,我陪着她在那个阴暗的仓库里,从旧书到旧卷子,仔细地翻找那个本子。最后,晓瑾找到了,是一本值日周记,上面有他们以前一起值日时记下的笔记,包括同学的出勤情况、教室的卫生情况。落款是他们两个人的名字。
五一结束,梁晨打电话到我家,提起他们已分手。我说:“我知道。”他说:“她是不是提了我们系的一个女生?我真不喜欢那一型。她想多了,那你……”我想到寻找值日周记的那个上午,无名火起:“我觉得你真是没事找事。”他在电话里稍稍停顿了一下便挂了,之后也很少再联系我。读大学后,梁晨曾打过一个电话到我家,告诉我一个歌手出了新碟。晓瑾去了新加坡,已经很少和中学同学联系,似乎想告别所有会勾起伤感回忆的人和事。渐渐地,我们彻底断了联系。我有很多次想告诉梁晨,晓瑾曾经那么费劲地去找过他们的值日周记,但这话该从何说起,说完又能如何呢?
在我读大一时,玉兰树被学校新任的教导主任勒令全部砍掉,理由是有利于风水。此后,我再也没有遇到过那么好的玉兰树,和弥漫着奇异香气的校园。
十几年过去,我遇到一位与梁晨相熟的中学校友。不久,梁晨让校友转告我,想加我的微信。我回复说不用了,这么多年没有联系过,算了。
很多人,相逢时是什么样的状态,最好相聚时也仍旧如此。我们共同经历过彼此的青春,那是一段充满香气的晴朗旅程,没有多少风雨和坎坷,也没有狗血和叛逆。如果中途有人走散,那么剩下的两人会变得莫名尴尬。看到一个人,就会想到另一个人,虽然她已离开,但在我心中她永远在场。很多年前,我们以为相聚是件简单的事,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很多年后,我们终究没有再聚。
只是这个傍晚,我想回学校看看,即使那里已经没有玉兰树,但我记得就好。眼前的岁月如歌,过往的纯透至空,这就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