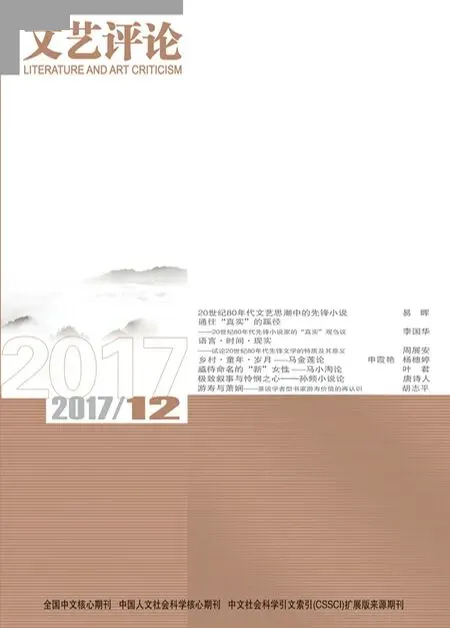回归·救赎·祛魅:网络种田文的流行元素及文学价值
○魏晓彤
回归·救赎·祛魅:网络种田文的流行元素及文学价值
○魏晓彤
自2016年以来,中国网络文学相继走红海外,充分证明了“网络性”和“中国性”的文学结合拥有巨大的读者市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经历了20年的风雨历程,网络文学已从最初被质疑为“垃圾作品”“野蛮生长”而成为当今文学百花园中一朵惊艳绽放的奇葩。每年有数百万网络作者笔耕不辍,数亿网络读者追更阅读。《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3.33亿,占网民总体的45.6%,文学网页日均浏览量超过十五亿次。仅掌阅文学一家,其作品总点击量已超三百亿次,累计拥有6亿用户,日活跃用户超过两千万。这些惊人的数据显示21世纪文学的新寄主诞生在网络。但是与网络文学的如火如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门户俨然的学院派却发声较少,相关理论研究始终处于失衡的状态。而现有的网络文学研究更多地侧重于网络文学的文化消费、IP发展以及产业化功能,忽视了对其本身的文学价值探寻,尤其对多元化的小说类型缺少深入细致地综合研究,从而使一些网络佳作的价值输出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考察,这将制约和影响着网络文学的整体评价。
一、种田文:网络文学世界里的独特风景线
对于种田文,学术界至今还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因为它与网络穿越小说、异能小说、言情小说都有着内在联系。百度百科的词条解释是:“现代‘种田’一词最早出现在SLG(策略类)游戏中,玩家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霸’为宗旨,保护自己的地盘并且大力发展,后期则开始征服其他玩家扩张势力。种田文是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特色小说。”在这类小说中,种田只是一种隐喻。主人公多为超世纪英雄。他们先在自己的领土进行各项制度建设,类似农民种田收获,脚踏实地建立根据地,以此积累资本、积蓄力量,作为未来征服世界的基石。这类小说可以归类为军事谋略类小说。也有学者将种田文定义为:“多指以古代封建社会为背景,描写主人公(一般为普通小人物)及其家人日常衣食住行、鸡毛蒜皮等生活琐事的小说。”①此定义概括了种田文的世俗性特点,但界定内容却和种田关联不大,这类小说归于市井小说更为合适。这里所指的种田文是真正意义上的种田文,以“乡野山村”“布衣生活”“平淡温馨”为基本元素,以书写田园式的生活内容和恬淡从容的处世情怀为本质特征。从叙事风格看,大多数种田文擅长生活细节的刻画以及乡村风情的描绘,具有世情小说风味。也正是因为这些特色,种田文才备受读者推崇和喜爱,才能在网络文学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
2008年起点中文网连续推出扫雪煮酒创作的《明朝五好家庭》第1、2部,以一对夫妻穿越到明朝地主家庭的生活叙述为主线,描写乡里人家的日常琐事以及农村社会风貌,柴米油盐里带着平民生活的悠闲和适意。这在神魔盗墓、仙侠奇幻盛行的网络小说世界里吹进一股清新的田园之风,成为网站年度最佳作品前三甲,点击量共突破五百万的人气巨作。晋江文学城也连载了仟佰禾的《又见炊烟起》,以都市白领辞职回乡养猪种田为主题,在生动真实的乡村记事里充盈着轻松诙谐的生活情趣。淳朴自然的叙述内容,清新恬淡的语言风格,赢得了读者好评和追捧。此后种田文进入了大规模的发展时期,热度高涨、数量激增、佳作频出。如清风暖的《穿越永乐田园》、莲如玉的《小地主》、苏四公子的《种田记》等作品,带人们体验“四季五谷味,山林花香美”的乡野风情,在农时农事和鸡犬相闻间打造了温馨快乐的田园生活。小等娃的《桃家村种田轶事》、名窑的《极品乡村生活》都用淡淡的笔触勾勒出山村生活场景以及洋溢其间的惬意和慵懒。这些种田文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设计,也没有虐心虐恋的恩怨情仇,有的甚至平铺直叙,笔墨淡然,却深受网络读者的关注和青睐。
不同于硝烟弥漫的战争文,种田文描绘的是一种平实世俗的生活画面;不同于阴谋算计的宫斗文,种田文追求的是一种淡定从容的精神境界;不同于天马行空的仙侠文,种田文讲述的是一种贴近现实的人生历程。种田文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成为各大网络原创文学网站的热门小说之一。在国内最大的文学网站——起点中文网,以“种田”为主题的作品近四千部。一些大型社交平台也大量出现种田文的踪迹,如百度贴吧就专设种田文吧,用于种田文爱好者的交流和互动,发帖量有七十五万之多,并且呈现与日增长的态势。这些帖子或是关于经典好看种田文的求书和推荐,或是关于种田文的创作和评论,由此可见种田文的热门程度。
二、回归:寻找精神的栖息之地
卡尔维诺曾说:“文学是一种存在的功能,追求轻松是对生活沉重感的反应。”②身处后工业时代,城市生存的空间不断受到挤压。激烈的职场竞争,快餐式的生活节奏,淡漠的人际关系以及污染遍布的空间环境,都导致了人的生存境域被全面颠倒和异化,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瞬间崩塌。压抑孤独的都市灵魂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精神的栖息场所和诗意的彼岸世界,而种田文所展现的田园情怀和适性生活范式正契合着当代人的精神追寻。
一方面,田园是引领生命从喧哗走向宁静的诗意回归。作为农耕文明发源地,国人对土地和自然的热爱已成为延续千年的人文情怀。农民在自然山水里劳作收获,建设家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种融自然与生产于一体的田园生活方式是一种深烙于骨髓的集体无意识追求,因而中国文化中的田园特质尤为突出,田园情结始终是中国文人书写和表达的重要主题之一。从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开始,“种田”一词便经常出现在后人诗歌里。岑参的“看君尚少年,不第莫凄然。可即疲献赋,山村归种田。”白居易的“金门不可入,琪树何由攀。不如归山下,如法种春田。”都将躬耕生活作为仕途不第的另一种人生选择。于是在田园诗人笔下,有了“孤烟村际起,归雁天边去”“白水明田外,碧峰出山后”的美景描绘,有了“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生活书写。当这种恬淡从容的田园生活方式引入到文学之中,带给身处浮躁社会和城市喧嚣的读者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引领,一剂心灵熨帖,于是“回归田园”也便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热门主题之一。《种田记》里的苏缨和林达夫妻就是田园回归派的代表。普通公务员苏缨被发配到偏远农村挂职锻炼。远离职场纷争的她在农村这片天地里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安详,同时对自然和土地的热爱开始悸动和萌芽。于是夫妻俩尝试种菜种树,养殖鱼虾,在物产丰收的同时也丰盈了内心。最后苏缨辞去了公职,归璞田园,在花香四溢的农家小院里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小说充分表达了“远离城市喧嚣,我种田,我快乐”的人生追求,将田园当作都市人漂泊灵魂和躁动心灵的精神家园与生命归宿。小说还更深层次地阐释了:回归田园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主动的心灵充电。只有懂得回归,才能为心灵寻觅一片澄净的栖息之地。
另一方面,田园代表的是人与自然的生命相依和精神内应。时下全球化语境中涌动着“回归田园”的哲学思潮,从某种程度说,哲学本身就是怀着乡愁去寻找家园的一种精神行为。海德格尔曾说:“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逸,它属于类似于农夫劳作的自然过程。当农家少年将沉重的雪橇拖上山坡,扶稳撬把,堆上高高的山毛榉,沿危险的斜坡运回坡下的家里;当牧人恍无所思漫步缓行赶着他的牛群上山;当农夫在自己的棚屋里将数不清的盖屋顶用的木板整理就绪:这类情景和我的工作是一样的。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③由此可见,广阔的山野世界和丰富的乡村生活提供了人们进行精神思考的巨大空间,同时乡村田园也正体现了人对自然依存与适应、亲近与融合的理想格式。“在这个田园的生活世界中,人显得和谐而不混沌,宁静而不死寂,淡泊而不冷漠,自然而不蛮野,适意而有憧憬,简朴而有韵致,温情而有理性,诗意而有智慧。”④而大多种田文以穿越重生的方式使主人公逃离身心俱疲的现代都市,回归到“青山绿水无污染、恬静温馨有家园”的乡野世界,实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诗性追寻。这种文本建构足以吸引那些渴望放松心灵、悠然生活的城市人们。这方面较为经典的作品有《小地主》,该书历时4年完本,文笔清新,内蕴丰富。城市“四无”青年胖子意外得到月光宝盒而穿越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处小山村。这里没有经济发展所孕育的人性异化,也没有都市文明所熏染的生存困境,只有淳朴善良的乡亲,奇异珍贵的动植物。在这里,人与自然相伴而生、息息相融。山野的澄静荡涤了城市的喧嚣,淳朴的乡情滋润着荒芜的心灵,由此胖子从心底发出呐喊:发誓要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小说所展现的具有精神抚慰和人性矫正的田园般生活画面在现代社会无疑具有着强烈的暗示和参照意义,为人生价值思考提供了一种复归自然的文化能量。
三、救赎:受挫欲望的想象性补偿
在当代,文学的意义并不总是把载道教化放在首要位置,而是要切入人们的内心,关注人心需求,让读者能够在文学世界里收获一份快乐。而人类共同心理模式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人性不可以真正被压抑,即使是弱者都有表达自己欲望的本能需求。弱者往往会利用想象中的强者为自己制造一个领域,一个能够突破现实桎梏而永远自由行动与自我决定的空间。文学正是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把生活中不敢做、做不到的事情在作品里面做到了。而且往往是现实生活中越是懦弱、无用的人,越可以在文学作品里表现得特有本事。这就是人类最精深的心灵之殇的疗愈办法——文学的精神救赎之法。相比于传统精英文学强调的严肃沉重的历史和社会话题,网络文学以张扬人的各种欲望而介入读者精神生活,以脱离宏大主题而转投于大众怀抱,由此彻底释放了现实的束缚,回归自由本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现实中各种社会规则、环境因素以及自身能力的限制,很多欲望被挤压和封闭。受挫的欲望并未消失,而是潜伏于无意识的某个角落,等待理性监控松懈之际乘隙逸出。逸出的欲望时常乔装打扮,借助各种符号和意象从事象征性表演。⑤弗洛伊德就曾将文学比喻为“白日梦”:现实中无法满足的欲望成为文学想象的催化剂。种田文便是充分提供给人们一个世俗欲望得以补偿和实现的想象性文本,把读者从压抑束缚的现实中解放出来,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这种“草根逆袭”的主打模式具有相当的普适性,能够满足不同人群共通的心理需求。
1.穿越与重生:想象性文本建构的主要途径。穿越行为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当代生存困境的一种超越。身处钢筋水泥的都市,面对各种污染的侵蚀,人的内心充满了压抑和惶恐。因而远离城市纷杂,享受悠闲人生,便成了当代人最简单却又最遥不可及的梦想。“人类的本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意味着自由,是主体对自由的向往。禁锢与自由、疆界与穿越之间的矛盾成为人类生存永恒的动力。”⑥在种田文的文本建构中,作者往往设计主角穿越或重生于过去或历史的某一语境中。他们适应和遵循陌生环境的规则,逐步累积、努力奋斗,实现了惬意自由的田园之梦。《农门妇》《农家媳妇的古代日常》都建构了现代女穿越到古代并且重生为孩童的故事。前者重生为被卖入农家冲喜的童养媳,后者重生为在后娘手下讨生活的小白菜。一方面她们带着前世的记忆开始了重新成长和发展之路,利用对现代农作物、生产技术、经营理念的认知,自力更生而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她们抓住重生机会,重新审视人生的情愫,珍惜前世所缺失的家庭亲情。在平凡简单的农家生活享受相濡以沫的夫妻情谊。因穿越重生而弥补现实缺憾成为种田文的主要情节元素,也正满足人们“如果人生能够重来”的心理和梦想。
2.异能与空间:想象性文本的另一种构建方式。对于现实中的平凡人物而言,拥有奇异特殊能力以及随身异度空间是一种超人式梦想。超人思想不仅是尼采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凡人心中的普遍情结。但是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并没有运用这些神奇能力和空间去开疆拓土,而是转向农村开荒种地,发展各类副业,关注个人环境的改善和悠闲生活的经营。这类小说往往架构在当代背景下,结合农村现实,颇具乡土韵味。《山村桃源记》:厌倦都市生活的白领因一枚种田戒指而获得了促进动植物奇特生长的加成功能,从此过上了闲适安康的小农生活;《随身带着两亩地》:失业大学生依靠家传玉佩的特殊能力回到村中种田,获得丰收,也收获爱情;《极品乡村生活》:北漂青年意外得到神秘灵异的生长空间而重返家乡,发家致富,成了有房有地有存款的小农民。主人公们充分利用自身异能和奇特空间获得了现实中无法企及的成功快感,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而其中所展现的自由精神和适意生活方式让小说拥有了大量的读者。
莫言谈及文学时曾说,小说是亦真亦假的文学世界。在种田文里,时空交错的背后隐藏着现代叙述内核,其现实人生和虚拟人生构成了绝妙的互文关系。虚拟世界的得意和满足正反映出现实生活的失意和匮乏,神采飞扬的抒写渗透了世俗理想的失落和情感荒漠的苦涩。而现实人生的个体消弭和凡俗欲望通过虚拟文本得到了充分的补偿,成就了普通人的精神救赎之路。因此,不论在现实意义和文学意义方面,种田文都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
四、祛魅:普罗大众的世俗化书写
自从马克斯·韦伯的《世界的祛魅:西方宗教精神》一书问世以来,“祛魅”一词便迅速席卷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在韦伯看来,世界对于人类来说不再是充满迷魅的神秘存在,而是人的理性能够完全把控和掌握的机制。现代社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以理智合理的态度和方法对之前所形成的“魅”进行祛除和清理的基础之上,对形而上意义和价值进行理性化的重建。虽然“祛魅”产生于西方国家从宗教神权社会向世俗社会的现代型转型中,但是“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的思想理念正契合了当下网络文学反叛传统和经典的精神实质。以个性、自由、娱乐为倡导的网络文学迫使传统文学的权威性和经典性受到不断撞击。“网络文学一开始就呈现出消解权利话语、欲望化表达、多元化、大众化价值取向的后现代审美观照,成就了文学的祛魅。”⑦但是从网络文学的产生发展来看,“祛魅”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型延伸过程,而是包含了一定的辩证发展关系。一是网络文学以“自由”和“解构”为本质的游戏性审美书写祛除了传统文学建立起来的“魅”。二是在祛“魅”过程中因其文学模式被不断复制和使用而不自觉地建构了自己的文学图景,这便成为后来者所要祛除的“魅”。而种田文正体现了对传统穿越小说经典模式和主流风格的消解和背离,具有一定的文学祛魅价值,也因此更贴近当代读者的接受心理。
1.颠覆英雄女神化塑造模式。早期穿越小说往往体现了一定的现实缺席性,其主角多为高大完美形象。男主天纵英才,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或品质。在历史语境里指点江山,成就丰功伟业,甚至改变历史走向(如《新宋》《窃明》《寻秦记》)。女主大多为宫中贵女、名门闺秀,博古通今,容貌与智慧并存,成为人们仰视的女神。她们甚至参与宫廷权力斗争,推动朝代更迭。(如《梦回大清》《独步天下》《末世红颜》)。大多数种田文也走穿越之路,但不同的却是以理性的精神祛除主角头上的神秘光环,让穿越者走下了神坛,还人物真实的生活面貌。主角穿越前是平凡小人物,面临各种不幸,穿越后依然是村夫农妇、丫环童养媳等普罗大众。穿越者不再试图去征服前人、改造世界,也不再叙写他们匪夷所思的传奇经历,而是将现代理念和经验转变为现实中的实用技能,在架空历史中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用心经营属于自己的田园生活。2012年弱颜的《重生小地主》便是此类代表,该书因一千三百多万的点击量跻身起点女生网热门小说前列。主人公连蔓儿前世被小三暗算而香消玉殒,却意外穿越重生为古代农家女童。在成长的过程中连蔓儿始终以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生活困难,用乐观坚韧的意志建造起小康之家。小说将重生作为人生转折的一个契机,在世事如浮云的感叹和人生可重来的机遇下,连蔓儿选择了家庭生活的温情营造,而不是个人事业的辉煌成功。从关注“我”到关注“我的生活”这一转变的文学意义重大,这说明穿越小说已由先前的娱乐游戏而转向对社会现实和当下人生的探寻。网络小说开始打破虚幻,逐渐和现实取得了一定的联系。
2014年以后的种田文更具突破性,穿越主角往往处境困顿、生活艰涩。《山民锦绣》中的锦绣在逃难中被卖给了无田无房的山民,成为终日为生计所迫的农家妇。《农家有女初长成》中的苏婧面对的则是家徒四壁,上有病母、下有弟妹的艰难困境。《花香满园巧种田》中的林玉岫更是穿越为经常遭受虐待的养女,后由族里长老做主而自立门户。她们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知,对陌生环境充满警惕,自觉用规则约束个体行为。“低调做人、小心做事”成为这些小人物们的处事准则。在坚韧意志的支配下,她们凭着勤劳智慧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发家致富,打造起田园生活乐园。由此可见,种田文将叙述视角从光环围绕下的个人崛起转向静默个体的精神存在。以平民视角关注小人物命运,描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揭示大众精神世界。从这点来看,种田文从回避现实的“减压式”人生中逃离出来,书写直面困难的“抗压式”现实体验,体现了文学的进步性。而种田文中的小人物命运与当代生存困境之间所构成的互文关系也说明穿越小说开始进行“为人生”的思考,消解了网络文学广为诟病的游戏意味,为读者开启了另一扇审视现实和人性的窗户,因而具有潜在性的文化建构功能。
2.摈弃宏大史诗性叙事风格。传统男穿主角往往凭借时空优势和思维优势在古代历史语境中进行技术创造和思想占领,并自觉承担启蒙民智、复兴民族、建构国家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小说里充满了金戈铁马的壮阔场景,以及轰轰烈烈的历史改革。即使女穿主角也展现了高屋建瓴的历史优势,对时光风尘下的人物和故事进行波澜起伏、壮志悲情的描绘。而种田文却以世俗语境中的日常生活为叙事架构,注重生活细节刻画和社会风情渲染,擅长美食、服饰、礼仪、器物的描写,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幅世俗生活的画卷。乡野间的柴米油盐、鸡飞狗跳,生活里的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看似平淡如水的琐碎片段被演绎成温情脉脉、滋滋有味的叙述内容,满足感和幸福感洋溢其间。《桃家村种田轶事》以恬淡平实的笔调叙写桃三爷一家的生活场景。田间的精耕细作,家庭的上慈下孝,邻里的和睦相处。一字一句缓缓道来,一点一滴全是生活。写作者努力发掘具体而丰富的日常生活的积极面,让主人公在尘嚣间达到诗意的栖居。
种田文的作者大多为女性,作品内容也较多反映了情爱问题,因此不少文学网站给种田文另贴了“言情”标签。但是和传统言情小说相比,种田文摈弃了浪漫虚幻的情感渲染,以理性从容的态度看待婚姻家庭生活。女主角们所嫁的皆非高富帅,而是老实忠厚的普通农夫,但是却在平凡琐碎的生活中收获了永恒的真爱。《穿越永乐田园》里出身书香之家的姚瑾因受辱而被退婚,自愿嫁进丧妻的农户家庭当后妈。但她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礼待丈夫,孝敬公婆,爱护幼女,夫妻感情也在相互扶持的细水长流中日渐浓郁。在《农门妇》《农家媳妇的古代日常》里,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和曲折动人的恋情,只有男女主人公在日常生活细节中体现的有商有量和彼此尊重,充分诠释了“平淡是真”的人生哲理。在一定程度上,种田文的走红也说明了读者对于当代婚姻家庭的认知日趋成熟。以金钱、地位、外貌为主导的择偶观念逐渐淡化,对简单真实而又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怀有期待。马克斯·韦伯认为,“‘世界的祛魅’过程,实质上是世界从神圣化走向世俗化,从神秘主义走向理性主义的过程”。⑧种田文正是这种文学祛魅的体现,它代表了网络文学开始将理性的笔触延伸到大众生活领域和平凡世俗世界,让人性得到了充分肯定,让凡俗欲望受到关注和认同。
结语
21世纪的文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变革的时代。文学创作由精英视角转向大众视野,文学主题由深刻宏大变为日常通俗。网络种田文的兴起和流行正符合这一文学发展趋势。虽然种田文在发展的十年间,和其他网络小说一样摆脱不了快餐式文学的桎梏,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一些作品的情节类型化,内容平庸粗糙,语言缺少艺术性,但不可否认,种田文所体现的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对成功欲望的诉求以及对温暖亲情的渴望,正折射了当代人的普遍社会心理,而世俗语境下的审美化生活书写,恰好符合后工业时代的文化消费需求。正是承载了与众不同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种田文对于当代网络文学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影响力。
①李昊《新世情小说的复兴——浅谈种田文的走红》[J],《当代文坛》,2013年第5期,第64页。
②[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③[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语要:人,诗意地安居》[M],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④李庆明《哲学回归田园:一个现象学的透视》[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16页。
⑤南帆《文学批评拿什么对“网络文学+”发声?》[N],《文艺报》,2016年10月28日,第2版。
⑥李盛涛《网络穿越小说:当代文化镜像的反讽性文本》[J],《东方论坛》,2013年第 4期,第 87页。
⑦严军《后现代媒介下的“祛魅”文学——网络文学的游戏性审美观》[J],《社科纵横》,2012第5期,第82页。
⑧释智文《祛魅与复魅:中国佛教当代发展的路径探索》[J],《法音》,2015年第 1期,第 25页。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