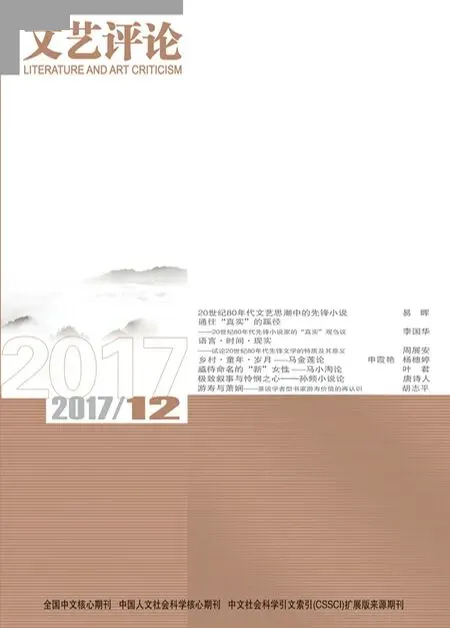极致叙事与怜悯之心
——孙频小说论
○唐诗人
极致叙事与怜悯之心
——孙频小说论
○唐诗人
一
在我阅读孙频小说集《盐》的那天,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曼德勒海湾赌场附近发生枪击案。小说很极端,处处有惊骇情节;惨案极为恐怖,一名白人男子在高处用机枪向正在观看音乐会的民众扫射,导致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我一边读着小说,被孙频小说中的极端故事震撼,感动于作家对这些悲惨人物内心世界的关照;同时,另一边,我拿手机关注着这个惨案,看着视频中那些在枪声下叫喊着逃奔的人,看到一些被击中倒地的血腥图片,心痛无比。我愤怒于那些恐怖分子,同情于那些无辜的受害人,尽管他们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残忍事件总会让人为之震动、沉痛。那一刻,我在想,极端的小说叙事与极端的恐怖行为之间,在这个时代,到底是种怎样的关系?
还值得一起分析的是,在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一向安检很随意的广州地铁,宣布开始全面严格化,宣称以后乘客乘坐地铁,必须做到“人过安检门、物过安检机”。面对这种全面的安检升级,公民意识向来比较强烈的广州市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面对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增多的极端化恐怖活动,人们对于有着提供更多安全保障理由的各种措施,不再持怀疑态度,只将默默接受。
这两种现象,看似跟文学无关,跟我们要探讨的孙频小说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我要追问的是面对这些事件、面对这类故事时,我们内心深处因着什么而被触碰、被感动?孙频小说中,那些极端凄苦、极端残酷的现实人生、人性,为什么能够如此打动我们?这种感动在这个恐怖事件频发的世界又有何意义?我们总是说这是个平庸的时代,但我们所看到所见识到的,却是无数的极端化、极致化的痛苦与灾难。难道是这些极端事件、极致故事已经锻炼了我们的内心?导致我们无能于鉴别那些细微的温暖和宁静的生活世界?极致、极端,总是牵动着我们内心的软肋。可是,当我们经常性地被极致、极端触碰的时候,我们的软肋会更为柔软还是逐渐坚硬?我很怀疑,软肋变得不软时,人会变成什么?正如如今我们对身边的、生活世界里愈来愈多的拘束都不再有感觉、不再能提出异议了,这时候我们变成了什么?
每当我在阅读极致叙事和听闻到各种极端恐怖事件时,我都在担忧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我们适应着极端、适应着恐怖,同时,我们本来柔软的内心变得愈来愈坚硬;我们的内心在极致化的故事熏染下变得越来越波澜不惊,我们的性格也在无数恐怖新闻的摧击下变得越来越怯弱温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伊格尔顿,面对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这个刚刚开始的喧嚣世纪,已经被无止境的鲜血所玷污,已经被数以万计不必要的牺牲所标记。我们已经习惯将政治生活视为暴力、腐败与压迫。对这些阴魂不散的现象,我们甚至早就司空见惯了。难道我们就不希望在人类历史的编年册中,能有更多一些甜蜜和光亮么?”①我们当然希望,可是我们该怎样做才能有更多的甜蜜和光亮?
必然,要寻甜蜜和光亮,并不是去忽视黑暗,更不是屏蔽掉那些极端的恐怖消息。查尔斯·泰勒帮我们指出过:
消极的、自卫的反应是将它的大部分阻挡在外面;甚至不去瞄一眼晚间新闻,而是专注于其他东西。更具腐蚀性的是,贯穿整个历史,我们总是善于告诉自己这些人实际上和我们并不相像,以此来消除那种恐惧;也许他们不像我们这样在意贫困和肮脏;也许他们是坏的,是邪恶的,他们应受这种苦难;也许他们由于自身的懒惰和软弱才遭受苦难。或者我们可以画一幅关于事物的更亮丽的图画,在其中苦难被隐藏了;例如,通过对那些生活在意义厚重的文化中的土著人采取一种外在的审美想象力,我们使自己与他们远离。②
回避、远离是一种消极的反应,泰勒接着分析了一些“修复世界”式的积极反应。所谓修复,也就是做出积极行动。可是怎样的修复行动才能对付这个世界的苦难?我们个体听闻这些恐怖灾难,同情和愤怒是允许的,但我们肯定不会允许自己也成为受害者,不会允许邪恶靠近我们。这是一种现代的漠然立场,给予同情,看见问题,但肯定不允许这些问题与自己有关。内在于这种立场的,是一种恐惧心理。出于这种恐惧,我们会乐于采取防范和改善措施,以消灭、抹除灾难可能性。或许,这就是拉斯维加斯恐怖事件和广州地铁安检升级的关系,两个国家,地球的两面,就这样被人心勾连起来,这也是全球化、媒介化时代的一种历史实践。
出于恐惧的防范实践,我们当然愿意看到这类善意修复和保卫世界的行动。但同时,我们其实也恐惧于防范行动升级为强大的控制力量,以致于行动之外的一切都纳入了需要牺牲的代价。为了避免苦难与邪恶事件发生,我们付出行动强大自己,同时也顺理成章、轻而易举地要斩断与灾难受害者、犯恶者之间的关系,甚至为了防患于未然,对于风吹草动也大动干戈。最终,我们原本柔软的同情转换为了坚固的堡垒,堡垒之外的一切都可以毫无例外地消灭。无疑,这也是我们不敢想象、不愿抵达的另一个极端的邪恶状态。
面对这两个极端的可能性,我们需要防范的,除开可见的邪恶势力,还有我们自己内心深处不可见的恐惧所能反弹出来的对抗力量。修复世界的行动,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隔着的其实就是人心,是人对他人的同情和怜悯能力。失去了这份柔软的内心,两个极端就变得通畅无阻。我们需要珍视这份柔软之心,重视这动不动就让我们泪水盈眶的软肋,它会是挽救人类的最后一份力量,当然也是我们最可信赖的希望之光。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上,我感受到孙频小说的特殊价值。孙频擅长极致叙事,她的极致叙事与其他作家的极致叙事有何不同?孙频这种极致化的苦难和人性描绘,对于这个极端事件频发的当代世界而言,有何种意义关联?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以为,孙频叙述出极致状况下的人性状态,让我们看到卑微处境下的人如何生活如何思考、苦难中的个人如何卑琐又怎样值得同情,甚至挖掘出变态中的悲悯所在。孙频这种写作,是对受难者和作恶者内心世界体贴入微的观照,根本而言又是对我们同情心的珍视,她帮助我们发现自己原来还有一颗可以去同情和怜悯那些卑微的、变态人物的柔软内心。
二
所谓极致化叙事,就是将平常的事物极端化处理,一般是说作家将一种性格、一种情感、一种精神书写到绝对状态,这是孙频小说最为明显的叙事特征。对于极致叙事,洪治纲曾在论述20世纪80年代先锋叙事时有过很好的论述:
这就是带着超验特征的极致性审美法则,也是先锋文学中最为活跃和最具表现力的一种表达手段。一方面,它注重话语表达过程的极致性审美目标,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情节结构,都不断地走向某种极端,完全摆脱了客观现实的庸常状态,使文本在许多臆想不到的情境中显示出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另一方面,它又极力强调话语表达的超验性品质,在艺术传达过程中鄙弃一切通常的经验逻辑,抛却那些具有集体倾向和公众意趣的审美感受,使人们的一切理性预设手段都失去作用,话语呈现出大量非理性、颠覆性、独创性的成分。总而言之,它是一种超验性和极致性的高度融合,是先锋作家对自身超验性审美感受的极端表达,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反抗既定的文学观念和话语秩序的同时,确保文本全面地展示作家自我艺术理想的完整性和深刻性。③
这虽是针对先锋叙事,但洪治纲讲到的两个方面,都很适合用来评说孙频小说。人物性格和情节结构,都走向极端,而且它们的极致化是相辅相成的。长篇小说《绣楼里的女人》,将每个人的性格都极致化处理,但每个人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极端化的性格,都与他们各自的生活遭遇相关。贺红雨的决绝、冷酷性格,她自作主张嫁给穷人,后来对女儿孙女的残忍态度等,都与她自己小时候受到的歧视、漠视相关,与她的生活中总是遭遇各种悲剧灾难相关。这种性格、情绪的极致书写,可以生成一种富有冲击力的审美感受。《东山宴》里的采采也是极致化的性格形象。采采性子烈,母亲改嫁后,父亲新娶,父母都觉得她是累赘,被赶来赶去,后来她通过到处诉苦大声喊可怜来获得同情,她将诉苦喊疼变成了让自己活下去的方式。《无相》里的于国琴,家庭极端贫困,靠母亲的拉偏套(地方上的变相卖淫)维持生计。于国琴考入大学后,得到一位老教授的慈善资助。于国琴内心特别脆弱、敏感,她每动用一下饭卡里老教授资助的钱都觉得有人看着自己,每周去帮老教授打扫卫生做家务时也都满怀自卑与恐惧。老教授给钱她更觉得受辱。于国琴一直担忧这种被资助终究会被要求偿还。果然,后来老教授想看于国琴的裸体,这种观看让于国琴彻底撕下之前的自卑和愧疚之心,她变得决绝,将老教授的要求看做偿还他对她资助的要求,她将脱衣服变成了偿还和报复的方式。脱下了衣服,也就是脱下了羞耻之心。《因父之名》中的田小会,父亲离家出走之后,被所有人嘲笑无父,十来岁即受到六位男老师的强暴。一次被班主任强暴时,被学校门房李段撞见。此后,李段因为帮助田小会堕胎、不告诉别人等缘由,做了田小会的干爸,其实是捆绑了她作为泄欲对象。十年后,田小会的生父回到家里,但经历过那么多磨难的田小会,内心已死,不再回到他身边。这里面的极致,是田小会的不认生父,她以认一个老流氓为“父”来抵抗家庭的孱弱和世人的邪恶。还有《无极之痛》,写一个青年教师的妻子如何低贱、死皮赖脸地求校长潜规则自己以获得分房机会,小说对这种贱卖自己求帮助而不能的心理叙述得特别精细,可以说是把当前青年的求助心理极致化了。还比如《隐形的女人》里的郑小茉,为了一个男人甘愿沦为妓女。这些小说的人物性格,极端到了非理性程度,正常逻辑下无法理解,也很少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但这种极致处理最能体现艺术特征所在,它放大一种情绪、性格,使得这些看似平常的性格变得锐利可怖,如此也就展示了内在于这些性格特征的恐怖潜能,同时也使读者感受到作家深刻的现实批判旨意。
尽管洪治纲所论述的先锋小说极致叙事特征对于理解孙频很适用,但孙频的极致叙事与先锋小说的极致叙事又有着极大的不同。先锋小说的极致叙事是叙事艺术上的探索,孙频的极致叙事是人物情感方面的深刻挖掘。孙频的极致不是为极致而极致的艺术考究,而是因为她感受到了当下现实的残酷所在,为此她需要使用极致笔法才能更真实也更刺目地表达出自己的精神判断。就像《东山宴》《无相》《无极之痛》等现实感极强的小说,比起极致化的人物性格来,更为醒目的其实是血淋淋的残恶现实,极致性格也都是现实生活的绝望而逼致的。同时,走向极端、变得恐怖的人物,也因为有着令人绝望的现实处境而变得可以怜悯、值得同情。人物的极端不是一种无厘头的恐怖表演,而是为追求一种有尊严的生活而必然导致的极端走向;人物最后的毁灭式付出,是性格原因,更是现实逼迫。就如《无极之痛》的储南红,她这样低贱地想把自己卖出去,让校长潜规则自己然后获得分房可能,但现实是早在她知道有房可分之前房子就已经分完了。在如此绝望的现实处境下,像储南红这样的年轻人越是自我贱化,就越是让人感到悲痛、越能激起我们的怜悯之情。
三
对现实苦难的深切体悟,或许又能使我们将孙频的小说界定为底层叙事。孙频小说叙述的的确是底层卑微人物,但她与王十月、曹征路、陈应松等人代表的底层叙事有很大不同,甚至不能化为同类。这里面的缘由,即在于极致叙事艺术的突出,让孙频的小说不现实、但很现代。这种现代感,是为孙频不热衷于书写残酷现实本身,而是叙述出被残酷现实摧残为鬼、逼迫成狗之后的人物心理,为此也能理解她笔下人物的性格、心理为何都是夸张的、扭曲的、荒诞的。当人被苦难摧残成非人之后,非理性的行为和极端化的情绪就会主导他们的生活,人物可以迅速从脆弱变为决绝、从卑贱跨越到恐怖。这种非理性、极端化的决绝和恐怖,在前已述及的《无极之痛》《无相》《绣楼里的女人》等小说人物中已有表现,我们继续探讨另外一种极致状态,即《乩身》所代表的那种人被苦难摧残为“鬼”之后如何进入了“享虐”的可怖状态。
《乩身》是孙频近些年很受欢迎的一个中篇,这篇小说最为典型地展示了孙频极致叙事所具备的多维度魅力。小说讲述一个小县城女瞎子常勇的生平故事。常勇一岁半之前叫常英,高烧导致眼瞎了,遭到父母的丢弃,被五金厂老工人收养。老工人知道他们生活的小县城有着无数老光棍恶棍,他们专肆摧残女性弱者,他深知将一个女盲人抚养长大后,她的未来会有多么悲惨。为了让常英长大后不被恶棍们盯上,老人把常英改名成了常勇,强迫性地完全以男性标准培育她长大成人。老人去世后,常勇开始独立生活。因为年轻没经验,无法靠老人教给她的算命方式赚钱,她不得不去垃圾堆里摸拣事物活着。一次捡垃圾回来途中,被同为底层最受人歧视被吓得阳痿的流浪汉杨德清发现。杨德清为弄清楚常勇到底是男还是女,跟随并偷窥了常勇,发现了常勇的女身。杨德清有欲强暴但无能为力,躺在常勇窗外一整夜。杨德清对常勇的身世遭遇产生了同病相怜之情,逐渐将常勇视作自己的同类人,给予帮助,一起生活,并带着常勇去参加一场需要用铁棍穿透脸颊的自残祭祀表演。常勇在自残后变成了乩身,开始表演神灵附体。杨德清继续从事着自残的工作,后来脓肿而死。常勇则被奉为神人,最后自焚以帮助村人抵挡拆迁。
《乩身》这种故事,如果仅仅是惨烈,必然不会出奇,重要的是孙频叙述出惨烈背后人心的决绝,并将决绝化作了柔情和希望。常勇虽是瞎子,被要求以男人自立,但原本就是女人的她,女性意识越被压抑,也就反抗得越激烈。她知道有男人跟踪她窥视她,她虽害怕得发抖,但又故意露出了自己的女性特征,有意让人发现自己的女身,甚至有着一种渴望被强暴的欲望。生活的虐、肉身的虐,各种强势的力量压迫在常勇和杨德清身上,这些力量虐打他们,以致于他们必须要在这些虐中寻找生活的快乐、活下去的勇气。常勇渴望成为荡妇,如此才证明自己是个人、是个女人;杨德清迷恋上钢筋刺脸的自残表演,只有在舞台上他才被尊敬、被当作人。常勇迷恋上的通灵表演以及最后的自焚,都是在享受一种受崇拜、被观看的快感。他们被生活所虐,于是倒置过来成了享虐。所谓享虐,即是将痛感转化为快感,将卑贱上升为神圣。小说明确叙述出了常勇和杨德清的享虐心理:
众人的围观给了常勇一种剧烈而新鲜的刺激,就像在她身体里种了一只鱼钩一样,人们期望着能从她身体里钓出更血腥、更刺激、更神秘的东西来,她也不负众望,必须把戏演到底,演到骨头里,演出自己所有的可怕潜质,才能在这巨大的无边无际的黑暗中站住脚,活下去。她成了人、神临界处的一个优伶,在灯火辉煌处供众生赏玩。④
不错,他们都是怪物,可是明白,更需要这样一个怪物的其实不是县城里的人们,而是他自己。从前的种种羞辱与种种罪恶感在他身上留下了巨大的缺口,不如此自虐他便不足以填补自己身上的那些缺口。他正在把一种暴力正当化,而把暴力正当化的过程就是他正面接受自己耻辱的过程,接受了这耻辱他才觉得自己强大了。⑤
这两段很明白地写出了常勇和杨德清由受虐到享虐的心理。陈曦(陈希我)曾经专研过文学中的享虐现象,他的结论中,认为享虐现象并非恶魔并非怪物身上才会出现,它反映着一种文化现实,有着我们独特的文化土壤。⑥孙频《乩身》里的常勇和杨德清现象,有着我们特殊的现实土壤。这两个最底层的人物,他们的享虐心理,不同于宗教上的赎罪式自我鞭笞,也不同于弗洛伊德等人心理学上的性受虐心理,甚至不同于福柯思想中的权力机制缘由,而是生活现实的苦难、残酷导致的,是周身世界的残恶人性逼致的。
或许,在很多人眼中,常勇和杨德清都成了恶魔、成了怪物。但其实,他们都是最普通的人,只不过孙频用了极致化的叙事方式,将一种非常普遍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极端化了。她把人心真实和社会现实结合得惊悚化,以实现震惊的审美效果。孙频的叙述展示了众多的震惊场面,包括自虐表演,也包括常勇和杨德清的一场“性爱”,都到了令人恐怖的巅峰状态。人物投入一种惊悚化的销魂状态里,以痛为乐,实质上是以此来超越现实的痛苦、残酷与不堪,完成的是享虐式精神升华。这种精神升华作为审美图景,我们感受到震惊、感受到骇人的崇高。此崇高不是说小说人物多么伟大,而是文本本身拥有了崇高的美学特征。康德在论述崇高美时,特意强调了一种令人畏惧、使人惊愕的崇高美。⑦伯克也曾指出:“凡是能以某种方式适宜于能引起苦痛或危险观念的事物,即凡是能以某种方式令人恐怖的,涉及可恐怖对象的,或是类似恐怖那样发挥作用的事物,就是崇高的一个来源。”⑧恐怖、惊愕之所以具备崇高美,在于它超越了经验的有限性,抵达了一种完全属于精神世界的无限性。常勇和杨德清享受的不是肉体的痛,而是因这种痛而具备的精神光环,他们享受的是超脱丑陋肉身之外的幻觉世界的快乐,我们阅读观看到的也是超离了常规经验的纯粹精神性的图景。从感官到心灵,我们都受到震惊,受到感动。震惊于他们如此凄惨、卑微、可怜,震惊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如此残酷、凶恶;同时,我们又感动于生活在此等恶劣环境下的如此卑微人物,还能够结成同伴相互抚慰,还能够在痛苦凄惨中维护起自己作为人、作为女人的生活勇气和人格尊严。有这两方面的感受作为心理基础,无论小说人物多么不道德、非理性,都能够激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
对于同情、怜悯,孙频在小说后记中直接言明:“我写的每一个人物,不管他丑陋还是让人怜惜,我都对他付出了绝大的深情还有真正的同情。人对人最高的同情是什么?就是怜悯。”⑨创作论上的这种认知,与她小说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特征有着一致性,这更加说明,孙频的极致写作从叙事意旨到叙事效果,都不是为极致而极致,而是为表达出真正的同情、为激起我们最深刻的怜悯。这种极致叙事,伴随作家的叙述过程,我们能够进入到受难者的内心世界,能感知到这样一种极致化的精神性格是如何生成如何演绎又为何是无法避免的,如此也就对受难者、对那些被苦难折磨成非人的人物性格和内心状况有了理解和体悟。有了理解,也就有了同情和怜悯。
四
谢有顺论述阎连科的极致叙事特征时指出:
极致叙事创造了这种震惊性的经验,而正是这些震惊性的经验,促使阅读者真实地面对生命的困境、死亡的强大以及人身上那坚不可摧的生存信念。在这个层面上,阎连科为自己的写作建立起了一种有效的叙事说服力。他写的往往不是生命的常态景象,而是把生命放在非常态的世界里观察,逼视,追问,最后使之显露出极端的面貌。阎连科是想在世界的另一端在生命的绝境里,测量人承受压力的限度,以及书写出人在生活面前的可能有的勇气。”⑩
从这一论述可以察觉,孙频的极致叙事与阎连科的极致叙事有着共同的美学逻辑。但是在伦理反应机制层面,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孙频的极致叙事是为引起我们对其笔下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在此基础上再去规避和抵抗残酷现实对人性的异化;而阎连科的极致叙事,尤其后期的一些小说,其伦理意义不是通过激发怜悯之情,而是通过压迫性的黑暗来实现。阎连科曾借用盲人用电筒的故事来解释这种伦理反应机制。
盲人打电筒,目的不是自己看,而是给别人看,是盲人自身感受到黑暗,于是努力为别人提供光明。“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地闪开和躲避。”⑪阎连科这里的意思是,作家书写恶和黑暗,其伦理意义就在于让我们清晰地感受到内心阴暗面的卑琐以及人性之恶的恐怖,也警觉到“恶”所能造成的毁灭性,进而避开它、防止它。但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个故事,比如这里所谓的照亮黑暗,其光来自盲人的电筒还是盲人的内心?在我接触孙频小说之前,我更相信是阎连科所言的电筒,而在我思考孙频的极致叙事时,我开始觉得,盲人的内心和电筒,都是光芒所在。理解到盲人还要打电筒的内心,就如体悟孙频笔下那些被非人化的人物还要努力让自己活得像个人一样。盲人打电筒未必是有心去照亮别人的路,更可能是强调自己是盲人也是人的那种尊严感,要表现出自己同正常人一样能感受到黑暗与光明。同时,也正因为他照亮了自身,所以他才照亮了别人。
盲人手里的电筒,盲人打电筒的内心,这里其实涉及两种关于黑暗写作、极致叙事的理解方式。对于阎连科极致化的小说,我们更可能是感受到无限量的黑暗、罪恶,那是一种荒诞的、超现实或者说神实化的恐怖,自然有它的伦理价值。而对于孙频的小说,尽管叙事出很多内心狠辣的人物,但在那种极端艰难的环境下,给予我们更深感受的,不是个体的邪恶,也不止于整体的黑暗,而是在黑暗、困苦环境底下还能活着、还会柔软的人心。孙频用来照亮整个故事和点燃我们内心希望之灯的,不止于她写出了什么罪恶或何种黑暗,更重要的是写出了黑暗环境下的、内在于阴狠、猥琐、残暴等极致化性格背后的艰难生活和柔弱人心。因为有艰苦的环境作为叙事背景,小说中的人物,为了最起码的生活,一切所谓的阴狠也就变得不再可怕。他们为生存希望而做出的行为选择,尽管都是非道德的,也总能携带些引人怜悯的因素,即便是走向了罪恶行径,依旧有值得悲悯的空间。
或许因为孙频是女性作家,她的叙事就更能拨动我们内心的软肋。她的极致叙事,并不是为叙事艺术而来,而是为人物的内心情感而来,是为实现人与人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理解而来。“文学、小说给了我们理解冉·阿让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机会,因为小说全面地描述了他们的生存状况、主体性及其情感。”⑫这是埃德加·莫兰对文学、小说功能的看法。实现人与人之间最内在的相互理解,文学、小说具有其他沟通方式难以比拟的效果。
莫兰说“我们仍处于互不理解普遍化的时代”,世界布满了互不理解的黑洞,“不理解”生长出冷漠、愤恨、厌恶、仇恨和蔑视;“不理解”往往携带着心灵谋杀,容易对他人进行恶意的贬低、丑化。孙频小说中的人物,如果作家没能叙述出他们内心世界的艰辛与绝望,如若读者看不到内在于他们极端性格的软弱和温暖一面,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贴上变态、疯狂、恐怖等恶魔化标签,如此对他们的忽视和扼杀就变得理所当然。反过来说,孙频能够将这些被残酷现实摧残得非人化的人物内心描述出来,也就使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非常态人物有着怎样的经历、情感、内在动机、痛苦与不幸。
理解孙频的小说,就是更全面更内在地去理解一些平常状态下无法理解的极端性格与变态内心。而且,如果根据一种复杂人类学知识,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着“智人/疯人”双重本性,都有可能走向极端、变成变态。根据美国神经进化科学家麦克林的研究,认为今人的大脑中包含三重性质的头脑:古生代脑、中脑、新皮层。它们分别意味着冲动、情感、理智。不同个体、不同时刻,这三个部分会有不同的主导关系。这种生物、神经结构,意味着理性的脆弱,意味着走向极端、成为变态是潜伏在每个头脑内部的可能选项。孙频小说所叙述的那些极致化性格、心理,之所以能够被尚属正常态的我们理解,或许也与这种共通的大脑结构有关。由此,我们理解孙频,也就不再只是理解这些虚构的人物,更是理解我们自身,帮助我们看到一些潜伏在自己头脑深处的冲动情绪和极端倾向。
对他人极致化性格状况的理解、对自我极能性的认知,这是一体两面。理解他人,所以能同情、可怜悯;认知自身,为此要规避极端、需谨慎行动。理解他人,不是放弃对变态人物极端行为的审判,不是面对这个世界愈来愈多的极端事件无所作为,而是去体察那些有罪的、卑微的、无耻的人格状况,认识到他们也是人;认知自身,也即检省我们对于他人的态度是否同样陷入了极端化。莫兰论述人类性意义上的“理解伦理”时,最后指认说:“要走出全球铁器时代,不同个体、文化、民族之间需要增进彼此间的理解。理解意味着兄弟化的可能,理解之后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都是‘地球祖国’的孩子。”⑬要修复世界,要走出这个残酷、恐怖事件愈来愈普遍的铁器时代,理解他人的痛苦和检省自身的极端可能,是我们每个人最紧迫的修为。
①[英]特里·伊格尔顿《论邪恶·译者序》[M],林雅华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②[加]查尔斯·泰勒《世俗时代》[M],张容南等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7年版,第779页。
③洪治纲《守望先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12~113页。
④⑤⑨孙频《盐》[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版,第39页,第43页,第367页。
⑥陈曦《文学中享虐现象之考察》[D],福建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35页。
⑦[德]康德《论优美感和崇高感》[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页。
⑧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374页。
⑩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86页。
⑪阎连科《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J],《语文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1期,第75页。
⑫⑬[法]埃德加·莫兰《伦理》[M],于硕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17年版,第169页,第185页。
暨南大学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