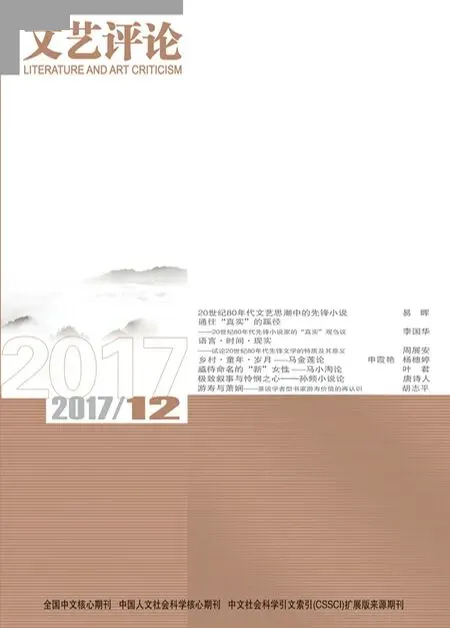亟待命名的“新”女性 ──马小淘论
○叶 君
亟待命名的“新”女性 ──马小淘论
○叶 君
在“80后”作家中,马小淘算不上多产,却极具辨识度。从近年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如长篇小说《慢慢爱》和中短篇小说集《章某某》来看,其高辨识度或许并不在于,她那为众多论者所津津乐道的脆蹦鲜活、泼辣俏皮的语言;而在于她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女性群体──她们正处于从“女孩”成长为“女人”的过程中。具体而言是那些大学毕业刚入职场,年近三十,在寻觅情感归宿,或刚刚走进婚姻,少女梦没有褪尽,却又不得不习染妇人心态的“年轻妇女”们。这是一个亟待命名的“新”女性群体。与上世纪90年代林白、陈染等作家基于女性主义的立场,呈现女性从女孩到女人的精神蜕变不同,马小淘笔下的“新”女性成长于这个充分物质化年代,在生存的挤压以及日常琐屑的锻炼中不断丧失自我,当然,也有她们的坚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此前几个时代的女作家们大多以诸如“她用一个晚上走完了女人一生的路”之类的表述一笔带过的女性成长过程,被马小淘絮絮道出个中那不足为外人道的心理婉曲,并深深打上当下这个世代的烙印。
一、匿名抑或退避
短篇小说《章某某》是马小淘迄今最为成熟的作品,甫一问世便引起较大反响,作品结集时,仍以“章某某”作为书名,亦可看出作者自己对这部作品的认可。
“我”的广播学院女同学章海妍由于频繁更名,众人索性以“章某某”称之。主人公这一不断自我命名到被匿名的过程,折射出一个外省青年在北京的遭遇。她怀抱主持春晚的“远大理想”,一番拼搏与挫败,最终“庞大的理想终于撑破了命运的胶囊”,让她出校门后成了一个精神病人,在毕业十周年同学聚会之际,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一个奋发向上的女生始于著名高等学府而终于精神病院,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像喻。而“章某某”如同一个可以无穷代入的符码,是一个群体的代指。《章某某》取材于作家极其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物,自身经历的代入,处处显示她与笔底人物的无间性,对同龄人命运的关切与省思,蕴含于作者那不动声色,甚至带有几分戏谑的叙述中,精致且不失力度。
章海妍自然并非只是个“青年失败者”那么简单。伴随她那追求“宏大理想”过程中的频繁更名,实则是一个外省女生面对排山倒海般的社会挤压与频遭挫败时的自我本能防御,“仿佛无奈地一次次放弃失败的自己”。“章艺囡”“章熹婉”“章晅姝”等等,这些出现于主人公不同人生阶段,笔画繁复、读音诡异的名字,是她无力面对失败时一厢情愿的自我隐匿。繁复之极归于简单,“章某某”这一来自周围同学的命名,反倒促成了章海妍自我隐匿心愿的最终实现──周围人似乎忘了那个自我认定的失败者到底是谁。从处心积虑的自我命名,到名字成了一个模糊的能指,这一切都源于一个来自三线小城带有巨大优越感的小女生,身处大都市那难以超越的自卑。然而,怪异的新名字到底不是可以让她安然蜷缩其中的甲壳,这掩耳盗铃的障眼法自然成了笑谈。
毕业十年,精神病院成了女主人公更其彻底的退避之所。那么,从“章某某同学”到精神病人章海妍,到底经历了什么?除了自感“远大理想”愈发渺茫,她还经历了全然忽视内质只在乎皮囊的初恋,结果痴心错付,被无情抛弃。只是小女孩心态不改,毕业后再次遭遇“恋上美少年”的失败。情感轮番遇挫,她自诉“信主”终于让自己找到了内心的安宁,其后再次恋爱,却又因她那保守的贞操观念而告吹。始终不合时宜的章某某,最终以对物质的靠拢──嫁给有钱人而变得“靠谱”,出嫁前夕改回了那个最初的名字。名字的回归,意味着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然而人终究无法回到起点。章海妍由怀抱理想到嫁作商人妇,向上力量的消失,换来的自然是不可救药的沉坠。而原本并不强烈的物欲的满足,到底不能泯灭其心底的少女梦,深深遗憾于“没有梦想的人生不是人生”。可见,其致疯之疾,在于“商人妇”与“少女梦”的纠缠;在于从女孩到女人,身份角色的无法顺利转换。精神病院里的章海妍是一个疯女孩,抑或疯女人。
面对生存的挤压,作为女性,身体是章海妍最后的资本。细思她那精神病院的终极退避,却是可能潜藏于当下任何一个“年轻妇女”身上的悲剧。从女孩到女人的挣扎与锻造,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时间或许有长有短,但在一个普遍丧失崇高精神指向的社会里,章海妍的悲剧在于,她仅靠自身无力完成这一蜕变。正如更名与匿名无法规避失败,名字的恢复,亦并不代表这一成长过程的真正完成。
马小淘的讲述,不免令人追问:世间还有多少无奈退避的年轻求生者?《章某某》是马小淘最近的作品之一,主人公的命运最为惨烈,稍稍回溯,《毛坯夫妻》是另一篇广受好评的中篇。这是一篇打上了“80后”戳记的“新写实”小说。
小夫妻雷烈温小暖是广播学院播音专业前后届同学,住在位于北京城最东端的一套毛坯房里,丈夫雷烈每天往返奔波六十多里,上班下班,每月所得大部分用来还房贷,余下的应付自己和妻子温小暖,还有四只流浪猫的开销,梦话都是“不行……我还要赚钱!”温小暖虽然专业优异,毕业后却在一家公司干着录彩铃、搞笑段子、鬼故事的工作,因天性懒散,不合意公司的考勤制度,一气之下炒了老板“成了新时期的待业青年”。都市远郊的这套只付了首付,装修了厨房和卫生间的毛坯房,从此成了她的退避之所,乐此不疲地过着黑白颠倒的日子。夜里在网络世界通宵漫游,白天睡到下午才起,如是日复一日。她就这样惯性地“宅”着,或曰“懒”下去。退避无需理由,只是对毛坯房外世界的本能排斥。这又是一个外省女生的故事。章某某是太有理想却屡遭失败,温小暖则压根儿就没有关于人生和职业的任何规划甚至物欲,只需要一个能供自己蜷缩其中的处所。毛坯房还有宽容的丈夫,成就了她的现状。相貌出众,拥有令人眼羡、就业率百分之百的播音专业出身,温小暖却宁愿退避一隅,过着一份常人看来不着四六的生活。百年前,一代新女性以勇敢地走出家庭为时尚,以“我是我自己的”相标榜;百年后的“新”女性却主动放弃唾手可得的经济独立退回家庭。温小暖并非个案,退避、彷徨、渴望庇护,几乎是马小淘笔下女主人公共通的心理,近乎一代“新”女性的时代病。
究其原因,同样源于从女孩到女人那被自我阻遏的成长。温小暖跟雷烈在一起已然六年多,即便早已离校,结婚成家,还是习惯叫丈夫“师哥”。这生成于青春校园里的称呼一直延续到婚后,即便青葱岁月不再,不得不面对挣钱还贷、柴米油盐,但一声“师哥”似乎能让她始终停驻于“女孩”阶段。而“女孩”所需要的,最好是一个能富养她的父亲,而不是丈夫。雷烈一觉醒来,看着彻夜奋战于淘宝,关注那些廉价服装的妻子,不禁自问:“这个人就是所谓的妻子吗?恐怕她更像他的女儿,可爱的、纯真的、任性的、让人恨铁不成钢的、心头一紧气不打一处来的女儿。”
所以,《毛坯夫妻》实则讲述了一个拒绝成长的故事。被人为悬停的人生,生生扭曲了温小暖的身份角色定位与转换──从恋人转向妻子;从被养的女儿到独立养活自己的妇人。当替代的“父”忍无可忍,“父女”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面对丈夫的控诉,温小暖完全是一副被宠坏了的女儿的骄蛮:“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是没有斗志,我就是没有欲望,我就是懒,我宁肯不吃,也不想出去觅食。”
然而,人到底还是要成长,人为的阻遏只是一时的任性。温小暖那被自我阻遏的成长,最终完成于跟丈夫前女友沙雪婷的见面。沙雪婷完全是“新”女性在另一极端上的行走──一个装腔作势完全被物化的女人。对于有身体资本的“新”女性来说,这是一条更易走上的“坦途”。当所有念想被物欲挤兑得一干二净,只余下华丽的空洞,正如沙雪婷那装修豪华的别墅,还有荒芜不堪的心灵。一个被物欲彻底掏空、压扁的女人与一个固执保持天真不愿意成长的女孩,在雷烈的内心自然有了自己的判断。即便是毛坯房里的夫妻,也自有其安然、平凡与实在的幸福。而从温小暖对沙雪婷那一大段感慨与“痛扁”里,让雷烈亦让读者看到了她那虽然任性、骄蛮却并不贫瘠的内心。
二、慢慢爱与乌托邦
相对于职场困境,马小淘更多文字聚焦于“新”女性的情感世界,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富有特色的情爱故事。
因为初恋的失败,冷然(《慢慢爱》)对爱情再难生出尝试的兴趣。分手后与高铭断断续续七年间的交往,让她对貌似精彩的男性有了更其深切的了解,不再被他们的皮囊魅惑。同时,她也亲见中学同学潘俏雪靠大手笔整容“脱胎换骨”,并成了高铭夸炫人前的资本。一个矫饰、虚荣的男人,匹配一个面容虚假的女人,这带有反讽的戏剧性设计,亦是当下这个虚浮社会的表征。而大学时一直扮演着安慰天使角色的金凝,最终发现自己不过被一个已婚男人玩弄。小说里三个女性各具特色,而又彼此缠绕的情感经历,不过印证了“真爱难寻”,这稍稍老套的话题。
对男性的冷淡,并不表明冷然没有爱的渴望。她只是在等待真爱的出现,但经不起等待的并不是她自己,而是其父母。女性三十,似乎是她们彻底告别女孩成为女人的关口,临界点的逼近,让“二老”早已无法淡定。冷然遭遇着所有大龄女的共同困境,父母逼婚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小说里太多精彩的段落,再现了冷然与父母之间,关于催逼与延宕的斗智斗勇。在一次仅为满足父母愿望的相亲活动中,她偶然与更名为钱熙源的小学同学钱源相遇。一对大龄男女间貌似不太可能出现的爱情戏码随之展开。自身条件优越的冷然,一开始压根儿就没有把刻板、木讷的钱熙源放在眼里,及至自己主持的节目被裁,遭遇职场挫败的她,想退避却发现没有一个可供自己安妥身心的所在。给自己放假的那一周,她出没于公园、菜市场、超市,还有钱熙源的家,在失落与惶恐中享受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快意。钱熙源的用心追逐,让她开始接纳,感情逐渐升温。
一番职场与情感的历练,或许让冷然意识到自己此前关于男人,关于爱情的种种看法,正如那一周的自我放空,只是小小的任性而已。从此,对人与人的遇合,她有了全然有别于女孩阶段的理性认知:世间原本就没有童话和传说,精彩十分有限,有的只是平凡而现实的生活,而一个人的世界其实很小,不过跟几个熟悉的人在“打连连”,没有什么迫在眉睫,亦无需想得太清楚。因而,与其等待,与其寻寻觅觅,不如慢慢爱。
然而,在马小淘看来,“慢慢爱”是一种境界,能慢慢爱是一种幸运。《两次别离》就讲述了一个想慢慢爱而不得的故事。主人公谢点点是北京土著,在四环内拥有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而在同学婚礼上认识的外省男生朱洋,各个方面乏善可陈,自然不是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两人之所以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并即将走入一场没有悬念的婚礼,对于谢点点来说,显然并非基于物质的考量,而是父母和周围人对其个人问题的“关心”早已超出了她的心理承受能力,逼着她与一个妇女的惯常人生轨道合辙──她只是需要一个让自己完成从女孩到女人蜕变的“同谋”。“有了自己的房子”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相反,谢点点“在朝着三十岁疾驰而去的人生里,早已明白了得过且过的道理”,她清楚自己并非有多爱对方,“只不过保险起见,安全第一,奔着细水长流来的……”
“细水长流”是“慢慢爱”的别种表达,没想到,准夫妻俩跟随旅游团的东京之旅,却彻底粉碎了谢点点的这一愿景。朱洋在东京的诡异失踪,好像是一场对于爱的考验,只是,这原本实属无奈的“细水长流”自然经不起考验,亦无需考验。对于只为满足世俗想象而找人结婚的女性来说,男性更多具有的是象征意义,正如朱洋即将成为谢点点作为女人的象征;而他的消失,则让后者在无边的焦虑、恐怖与尴尬中,对爱情、婚姻以及自身与社会有了一番痛切的审视。其结果,谢点点不想再迁就任何人或观念,再次做回了自己。一年后跟朱洋再见面,果断离开了对方,从一种世俗认定的“正常”生活轨道里走出。只是,分手前的抢白貌似强悍,却也难掩苍凉:“你不知道吗?我不是原来的我了。拜你所赐,你把我的人生搞得如此悲凉而别致,我已不好意思再装天真耍鲜嫩,我历经沧桑,必须凶猛。”而一旦卸下无形的桎梏,谢点点身上那原属于女孩的骄蛮随即显形:“必须坦诚地告诉你,我没有多么爱你,被你的消失折磨得死去活来,跟爱也没有多大关系,更多的是面子问题。”但这强势的告白,到底难敌话一出口那回光返照般的脆弱。一年前所经历的种种,或许让她意识到女性到底有多弱势。我想说的是,只要男性中心主义的生存处境不变,谢点点们所面临的成长抑或蜕变困境便始终存在,告白与发泄的快意以及分手后的平静,又能持续多久?
事实上,马小淘似乎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新”女性的自我妥协与慰安。小说《春夕》再次呈现了一个准妻子的心灵世界。江小诺偶然发现同居男友钟泽钱包里夹着一张钢笔画女性图像,于是展开了一场费尽周折的调查。那个名叫“春夕”的女人似有若无,成了她──一个语言泼辣、内心强大,貌似满不在乎的都市女性的心狱,甚至梦中都念念不忘。很显然,江小诺在意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钟泽的过去。她自己可以有初恋,并可以跟前男友保持亲密的“哥们”关系,但钟泽的情感世界,过去应该一片空白,现在则只能属于自己。这霸气十足的女孩心态,最终令她筋疲力尽。“春夕”成了一个诡异的装置,在推动故事发展的同时,也推着她一步步向女孩告别。小说结尾,她终于有了顿悟,决定放过春夕,“也放自己一马”。她自我安慰,无论钟泽和春夕有着什么样的过去,但那一页终究已然翻过;她更大度地想到,在三十岁的男人里,找一个没有过去的也不可能,自己既然没有孤独终老的胆量,“那么,结婚吧”。江小诺似乎一个早晨完成了这最后的蜕变。值得注意的是,始于延宕终于无奈,是马小淘笔下“新”女性成长的共同模式,从《慢慢爱》的结语“语焉不详也是好的”,到此篇结尾的“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莫不如此。
如果说冷然、谢点点、江小诺多少表现出即将进入婚姻围城的被动,那么,中篇《不是我说你》《你让我难过》,则呈现了“80后”“新”女性主动追求爱情时的别样遭遇。爱情的复杂之处,往往体现为对伦理的冲犯。在这一点上,两部作品明显带有互文性。这或许也是作者让两篇主人公共用一个名字的原因所在。表现婚姻与伦理的悖谬,从自上世纪80年代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及后来风靡世界的电影《廊桥遗梦》《失乐园》来看,所呈现的不过是中年人的情感危机。时代的变迁,这本属中年的困境,貌似在低龄化。
出校门后的同居生活,让电台主持人林翩翩(《不是我说你》),对男友的新鲜感丧失殆尽,欧阳雷那外露的优秀稳重,以及曾经能够满足她虚荣心的复姓,都了无新意。脆弱的爱情变成了惯性的亲情,想离开,却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台长叶庚是她大学时代的偶像,小说细腻呈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爱情”,在一个女孩身上那不可理喻的发生机制。当离异后的叶庚再次出现在林翩翩的生活里,一段恋情的展开似乎不可阻挡。年龄不是问题,欧阳雷的存在也不是问题,只是当初那小女孩的纯情早已褪尽,两个成年男女之间的爱恋与情欲,附带权力与利益的纠葛,欲罢不能。林翩翩小心翼翼地守着“香艳的秘密”,在公共空间里与叶庚装作是毫无瓜葛的上下级。她的辛苦还在于,面对欧阳雷,她还有脚踏两只船的自责。偶然获悉欧阳雷的不忠,似乎给了她一个顺势作出了断的理由,但问题没那么简单,叶庚看重的不过是她的美貌与身体。面对一个情场老手,林翩翩自然不是对手,只有交出身体、守住秘密的义务。她那企图走进婚姻的试探,被对方以冠冕的理由轻轻挡开。“你为什么不能娶我”,这溜到嘴边的话,到底还是被自尊挡住。爱情乌托邦的破灭,让林翩翩重又回到了现实,答应了欧阳雷的求婚,戴上戒指,擦去泪痕,醒悟到“完美是个圈套,相安无事就好,别要求太高,别委屈就好。太阳底下,并无新事”。
比较而言,《你让我难过》中的林翩翩对有妇之夫钟泽的爱恋更显纯粹。父亲的婚内出轨与早亡,成了她难以言说的伤痛,促成了她的早熟。她对婚姻没有兴趣,实则是对婚姻没有信心。她爱着钟泽,又不愿伤害他的妻子,她要的不多,可着对方的方便,仅仅是短暂的相处,便有了灵与肉的满足。他们不存在权力关系,她也压根儿就不要求钟泽给自己一个名分,只是与另一个女人共享一个男人,相安无事,不求结果。然而,在剧院里,当钟泽和妻子恩爱地出现在她眼前,林翩翩那独自建造的爱的乌托邦便轰然瓦解:“演了好多年的超脱和大气,忽然就有点演不下去了。”而且,她发现钟泽亲近自己的原因,亦不过因自己与他妻子在外形、气质上的相近。
“怕做错,怕承担沮丧,所以不作为”,但不作为到底不能规避这狭路相逢的沮丧。泼辣、尖刻的语言,让林翩翩显得强大凶猛,成了她掩饰沮丧的唯一方式。而“脆弱的凶猛”与其说是钟泽对林翩翩的洞穿,不如说是马小淘笔下一系列“新”女性的共同标识。马小淘式情爱故事的特出之处在于,往往以对爱情乌托邦的想象开始,以反乌托邦叙事终结,在描写爱情的同时,以一种苍凉的心态消解了爱情。
三、代入与自诉
“80后”、广播学院、才美外现、语言冷峭而内心柔软,熟悉马小淘的人,从其笔下“新”女性身上可以清晰看见作者的影子。一个作家所能呈现的,其实是其所处社会有限的层面,以及个体自身有限的经验,写熟悉的生活、熟悉的人,某种意义上是诚意的体现。不过,马小淘似乎做得比较极端,其创作几乎是自身经历、情感、经验的代入,是她面对社会与自我内心世界的自诉。有论者认为“80后”创作的通病,在于“主观陈述干扰了客观呈现,个人表达溢出了故事内容本身”①。主观陈述与客观呈现的调和,受制于不同写作者的趣味与偏好,所谓“通病”或许言过其实,但自诉性或许是这代作家共有的特征。
在我看来,一个作家值得关注,无非在于是否具有直面时代与自我的勇气与诚实。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创作的虚弱,很大程度上源于写作者的畏怯与虚饰。因而,文学边缘化某种意义上是个伪命题,关键是又有多少作家、作品值得关注?马小淘的可贵之处在于,她以有限的作品,写出了一代人特别是“80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与成长困境。高房价的压迫、价值的失落、职场的迷惘、情感的困惑,还有无尽的日常琐屑,造就了她们新的“烦恼人生”。马小淘自觉承续了上世纪80年代“新写实”的余绪,传达出她对当下社会的思考与对同龄人命运的关切。每个写作者都存在自身的局限,也多少带有自己的风格,但写作立场与价值取向,却始源性地规定了其文字生命的长短与价值的大小。在当下这个喧嚣浮躁,时刻求新求变的社会语境里,马小淘的创作取法乎上,立于写作的正道,叙事中规中矩,简单而不失力度,不媚俗,有自觉。即便看取一隅,却能让人窥见社会的全貌。
这是一个人人都渴望被关注的时代,苦难、身体、经验等等都可以成为写作者进行自我炒作的资源。一如其它行业,其结果对文学之外因素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而出身“作家二代”的优越环境,开始写作以来,自认为一路坦途的马小淘,却始终关注着周围同龄人的苦难,代入的是自己,言说的是“她们”。站在弱者的立场,替沉默者发声,让她的文字葆有尊严。与其笔下一个个性格鲜明的80后“新”女性相反,男性几乎都面目模糊。对男性的虚化,彰显了马小淘那毫不含糊的性别立场。其女性意识自觉投射在林翩翩、谢点点们对男性那别无所求的爱恋与果断决绝的分离上。然而,她们追求人格独立,却不得不面对诸多掣肘;她们渴望真爱,却都以无奈的自我妥协告终;她们外表凶猛,却内心脆弱。马小淘的文字呈现了“80后”“新”女性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她们在男权社会里的各色遭遇。她们身上的女性意识已然苏醒,唯其如此,她们对现实的妥协才更显悲壮——源于时代的造就,她们早已跟姐姐、母亲们不同。
前文论及,马小淘笔下的“新”女性几乎都处于“成长为女人”的过程中。而从写作本身来看,马小淘的文字同样处于逐渐脱掉青春写作印记的过程中。具体表现为小说里始终存在两种绝然不同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女孩的语言;另一种,我姑且称之为“女人的语言”。前者多半用于描写、对话,尖刻俏皮,活泛跳脱,大凡流行歌词、诗词警句、网络熟语,都被信手拈来,或戏仿,或跨语境植入,大多熨帖生动,风格戏谑,读来不时令人莞尔。女主人公们的“凶猛”,大多有赖于此。或许,这原本就是“80后”一代的话语方式,出于对笔底人物的熟稔、无间,马小淘几乎能做到张口就来。只是,话语方式的代际隔膜,有时候亦让人多少觉得有些“贫”,甚至是带有学生腔的呈才使气。“女人的语言”则是小说叙述人的语言,用以传达人生感慨与情感体悟,深沉而苍凉。可以看出,马小淘在将自己代入到笔下人物身上的同时,亦随时跟她们拉开距离,站在其身后加以审视。这两种话语方式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岁月渐长,从《飞走的是树,留下的是鸟》(2005年)到眼下的创作,大致可以看出“女人的语言”在增多,以至二者平分秋色。只是前者给读者留下的印象过于深刻,以致形成了对马小淘的认知惯性,而对后者有所忽略。我认为,充分彰显作者才情的“金句”恰恰是后者。尖刻、俏皮似乎不难;平易深沉却殊难达至。不妨略举几例:
江小诺认为那嗓子神了,落叶听完狂飞舞,河蚌听了乖乖吐珍珠,玉兔听完不捣蒜,熊猫听了想染黄毛,牛魔王听完撕了芭蕉扇,关云长听完丢了赤兔马,她江小诺听着听着就听上瘾了,恨不得幻听里都是那声音。
(《春夕》,《章某某》第 99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无论他们是恩断义绝还是心魂相守,不管之前的故事是多宏大的叙事还是多香艳的野史,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春夕再厉害,她的王朝也已经覆灭了。甭管现在登基的是世袭贵族还是农民起义,反正天下在手,甭管钟泽是不是前朝忠民。他还是要识时务地活在新时代。
(《春夕》,《章某某》第14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爱情走家串户,很少在哪长久驻扎。婚姻太容易半途而废了,她不想忍辱负重,也怕不小心伤了那同床共枕的人。婚姻的赌局,她的赌注不敢轻易下。怕扑向海市蜃楼,撞个头破血流。如若不结,便不怕看走眼。在局外,才可永不遭受出局的苦涩。
(《你让我难过》,《章某某》第220页,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以上三段屡被论者征引,以说明马小淘的文字风格。窥斑见豹,它们分明体现了马小淘小说语言的三种状态:从极力铺陈的戏谑、夸张,到新奇类比与婉曲内心的杂糅,再到平易沉郁。三者相较,最能进入读者内心的自然是最后那段。语言的快感其实多种多样,固然可以生成于纵情铺张,亦可源于约束内敛;新奇有快意,平淡亦然。从马小淘近作来看,文字的内敛性在明显增强,一些散见于作品中的貌似平常之语却常常直抵人心。而在一个太过看重创作数量的年代,马小淘对作品同质化的警惕,显然是一个作家对创作行为有自觉性的体现,亦是趋于成熟的表征。在“80后”作家中,她自然值得期待。
①行超《自信勇敢的“80后”世界——马小淘论》[J],《创作与评论》,2014年2月号(上半月刊)。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2BZW113)]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