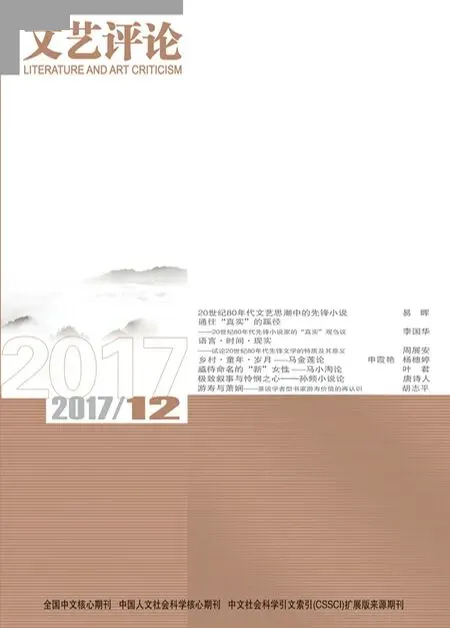乡村·童年·岁月
——马金莲论
○申霞艳 杨穗婷
乡村·童年·岁月
——马金莲论
○申霞艳 杨穗婷
随着资源分配方式的高度集中,活跃在当代文坛的“80后”作家,多数生活在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及省会城市,他们书写城市,乡村在他们的作品中悄然沉默。他们刻画自我和欲望,或多或少带有消费主义色彩,给人以当代生活云蒸霞蔚、热气腾腾的一面。马金莲是颇为特殊的一位,她是回民,成长于西海固,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早已是一位勤劳、能干而隐忍的小媳妇,曾当过乡村民办教师,夜晚在批改作业、安置好娃娃之后她提起笔,写下隐秘的心事和无法磨灭的记忆。
在“乡土文学终结”如雷贯耳之际,马金莲依然执着地书写她的干旱的小小的故乡。雷蒙·威廉斯在《乡村和城市》中分析了英国现代转型时期的文学,他认为:“现在乡村的一般意象是一个有关过去的意象,而城市的一般意象是有关一个未来的形象,这一点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将这些形象孤立来看,就会发现一个未被定义的现在。关于乡村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以往的方式、人性的方式和自然的方式。关于城市的观点产生的拉力朝向进步、现代化和发展。”①他接着阐释:“乡村的观点往往是一种关于童年的观点:不仅仅是关于当地的回忆,或是理想化的共有的回忆,还有对童年的感觉:对全心全意沉浸于自己世界中那种快乐的感觉——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最终疏远了自己的这个世界并与之分离,结果这种感觉和那个童年世界一起变成了我们观察的对象。”②也许纯属巧合,马金莲凭直觉写下她对乡村和童年的深情,写出了个体成长所带来的分离感、分裂感和痛感,以及在城市化刺激下农业文明根部的细微而深刻的变化。
马金莲的文风缓慢、沉着、悠长,那片亘古如斯的土地像静物画一样唤醒我们,吐故纳新,死亡转化为新生,催生出缓缓流动的风景。阅读她的作品常常让我们产生恍惚感,静水深流,似曾相识又宛然若新。故乡、大地、亲人、孩童的稚气、小媳妇的辛酸、母亲的眼泪,老人的沧桑与沉默的岁月犹如星光闪烁,地老天荒的寂静之感迎面扑来。马金莲的遥远的“扇子湾”,犹如史铁生的清平湾一样让人梦牵魂系,在文学地图上执着地占据一湾之地。
一、向死而生
西海固缺水,被认为是不宜人居之处,生存条件十分恶劣,物质极其匮乏,大家对食物保持罕见的虔敬之心,马金莲就是在如此贫瘠的地方长大。她的故乡充斥着疾病、早夭、饿死、冻死等非正常死亡。饥饿与“死亡”像噩梦一样缠绕着马金莲的写作之夜。
“非知生,焉知死。”这个句式常常被反过来,的确,生死联系着生命的两端,可以从任何一端来展开、透视。生命如此深邃、如此神秘、如此无常,有着难以窥破的秘密与经久不衰的惑魅。就像凋谢呈现花的笑靥一样,我们常常能从残酷的死中看到高贵的生,从艰难的生中看到仁慈的死。死亡终结生命同时凸显生命的意义,一代代生死轮回中往往承载了全部人类历史的重量。
在《长河》中,马金莲聚焦审视“死亡”这一命题。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死亡的帷幕从一位十岁左右小女孩的视野中徐徐展开。儿童视角是马金莲最为常用的一种,具有陌生化的优势。儿童的智力刚刚开始发展,但他们对事物的习得更多地依赖毛茸茸的感受和经验的累积,他们的全部感官对世界是敞开的,对一切都不加辨析,新鲜如初见。他们尚未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要到少年之后,人才慢慢建立成年逻辑,能够将符号与它指代的对象分离开来进行所谓的理性思考,拥有所谓意、言分离的能力。《长河》的核心是四次送埋体的过程:能干而勤快的伊哈被匆忙而寒酸地送进坟墓;我的小伙伴在山上摘花时突发心脏病后睡进了小土包;瘫痪多年的母亲在大雪里躺进了冰冷的黄土地;热心助人的穆萨老汉被拥进了村庄的怀抱。四次生离死别的经历,记录了“我”艰难的成长过程,“我”看到了死亡的出其不意,也看到了死亡对苦难的解脱和对恩怨善恶的超越;“我”体验到母女阴阳两隔的孤独和悲伤,也体验到落叶回归大地的安详与宁静。
随着不断亲眼见证他人的死亡,与死亡不断对话,“我”对生命真谛的认识渐渐加深,并逐步在内心与世界讲和。对伊哈的死“我”一无所知,让“我”难过的是伊哈家没有发“海底耶”,导致“我”无法享用美食,他人的死在孩子看来具有节日喜庆的色彩,只是一个满足口腹之欲的大好时机。他者的生命还未曾进入“我”的情感世界,或者说孩子单纯的心中尚未建立起死亡意识,这就是孩童时代对死亡最初的认识。当“我”的好朋友素福叶在如花的年纪猝死,死亡的残酷与真实一下子被拉近、被具体化了,痛苦感油然而生。而当母亲被疾病夺走了生命,那种剧烈的悲伤和不可逆转的分裂乃至恐惧感阵阵袭来,孩童圆融的生命裂开了口,看到了生命尽头屹立着死亡的倒影。
当“我”在目睹母亲和素福叶的坟墓时,心里涌上奇异的感受:
母亲在前,素福叶在后,一大一小两个坟堆离得很近,真的就像是一对儿母女呢。
我忽然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发现自己在羡慕素福叶,甚至是嫉妒的,我痴痴地想,为什么睡在那里的不是我呢?
真的,只要能陪伴着母亲,我愿意睡到冰冷的黄土里面去。③
母亲的去世让“我”明白了生命的另一种真实,那是死亡带来的永远的别离和旷日持久的思念。为了与最爱的母亲重逢,“我”甚至不再害怕死亡,内心急切地渴望它的到来,死亡似乎也不再可怕。当“我”看到母亲与“我”最亲密的朋友的墓紧挨着,忽然感觉到她们像是人世间的母女。这种瞬间降临的念头让“我”对生命有了重新的认识。
老阿訇是回民中知识与智慧的象征,常常被回民拥戴。当老阿訇穆萨在大雪中辞世,“我”已经能够感受到“死亡是洁净的,崇高的”④。“我”心平气和地接受人的最终结局和死亡的超越性,因为“我”深深地领悟到“从前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太过片面,存在着误解,死亡内容不仅仅是疼痛和恐惧,一定包含了更多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内容,比如高贵、美好,还有宁静。”⑤老阿訇的辞世让“我”对死亡产生了顿悟,生命本身是短暂的、无常的,但是一个人可以凭着人格魅力永久地活在另一个人的心中。每个生命的消逝都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老阿訇将他的知识、智慧与信仰传递给了整个村庄,于是个体的生死轮回也具有了民族代际交替的意味。回民的信仰使“我”更加坚信死亡的洁净与生命的美好,重新审视世世代代的回民在艰苦的环境中生活的意义以及隐忍生辉的民族精神。
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由此可以看到生命与河流的相似性,川流不息,人类生生不息。水滋养着生命,生命汇入时间的长河。每个人的生命就像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河,百川归海,永不止息,这似乎也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流传的过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整个民族对生命的态度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对生命的尊重也体现在对死亡的理解上,死亡是对生命的另一种馈赠,苦难会对人的肉体进行磨练甚至侵蚀,而坚韧的生命的死亡并不是溃败,而是汇入奔流的时间长河,获得崇高。
民族精神的延续具体体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代又一代人的延续。“家”以血缘为纽带,是依赖婚嫁与繁衍来维持的。“成家”是一个家庭故事的开端,《诗经》开篇《关雎》就在讲述古老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故事,讲述家庭人伦。在中国古老的智慧中,结婚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父母不仅要抚养儿子长大,还得为儿子娶媳妇,父母的使命才正式完成。为了孩子的幸福和家族的延续而倾尽所有,这让苦难中奋斗的父母获得前行的动力,默默地承受、坚持又包含着新的人生希冀。这与西方的家庭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西方崇尚的是个人主义,所以父母从小鼓励孩子独立,而东方文化是家国同构,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细胞,家庭内部是一个整体,父慈子孝、天伦之乐乃中国人的追求。理解这种文化的特性才能理解当代小说的中国性。马金莲的《项链》与莫泊桑的《项链》有相似的核心情节,却有完全不同的结局。莫泊桑的是喜剧写法,通过丢失项链歌颂了契约精神以及劳动对人精神世界的深度影响。而马金莲写的是一个现实的悲剧,“项链”的丢失带来整个家庭希望的落空。小说中,马万山为了凑钱给儿子娶媳妇,几乎是穷尽一切可能,作者罗列了他家中的所有积蓄:“把家中十九只羊卖了,一万多斤洋芋卖了,四千斤麦子卖了,三头牛卖了,加上这几年存在箱底的积蓄,算是凑够了钱。”⑥这是非常及物的列举,乡村生活的皱褶被细细打开,羊、洋芋、麦子、牛……哪一样东西不是凝聚着全家人的汗水和希望、劳作和笑容。当未来儿媳突然追加要一条金项链时,马万山依依不舍地牵着家中唯一的牛到集市上卖了,“捏着对方硬撅撅的指头,心头颤抖着,看看天色实在不早了,就答应了”⑦。但忍痛卖牛的钱却被人抢了去,“一夜工夫老汉的头发白了,前额两鬓霜染了一样”⑧,马万山重复了“白毛女”愁白头的故事。“白毛女”是旧中国的阶级悲剧,马万山的白头是当代乡村家庭脆弱的经济生活的写照,聘礼再度成为压迫农民的一座大山,横亘在男孩的父母面前,实质上这也侧面指认女性物化的变本加厉。当然后者不是马金莲的关注重点,她始终关心的是个体和家庭生存之艰。在西海固,马万山这样的家庭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他们经不起风吹雨打,任何一个计划都需要全家含辛茹苦地劳作,一次意外就可能摧毁他们全部的期望。
如果说结婚是个难题,那么生子同样是个难题,尤其是对母亲而言。在回民家庭内部依然信奉着男尊女卑的观念。《赛麦的院子》以三女儿赛麦的视点展示整个家庭的一波三折。身为女性,马金莲对母亲的痛苦更是感同身受。随着“赛麦”从拖着鼻涕脏兮兮的小女孩变成了拖着长辫子的曼妙少女,她更能近距离地感受到母亲连生七个女儿所承担的精神重负。母亲白天为一大家子忙得团团转,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着赛麦姐妹们在春风吹拂、秋月照耀下长大才能获得些许的安慰,但思念离家远行的父亲让她“整夜行走在一个人的忧愁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女性连绵不断的忧愁。后来终于盼来了弟弟,那是全家人的节日。毕飞宇的中篇《玉米》也写到过同样的故事情节,玉米扬眉吐气地抱着“小八子”去父亲(村长)好过的女人面前示威。可是欢愉易逝,好景不长,赛麦的弟弟得了肾病,不断地在家和城市大医院中奔波治疗:“她望着天边慢慢变幻色彩的云朵,第一次觉得人世真是难以说清,一场突然降临的大病,让她家转眼间什么也没有了。所有的家产全变卖成钱,拿到医院去了。医院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口,黑乎乎地张着,它吞进去的全是钱,赛麦家所有的家产变卖而来的血汗钱。”⑨疾病夺走了弟弟幼小的生命,击倒了母亲的精神支柱,也拖垮了这个普通的家庭。唯一的变化是曾经浪荡的父亲经历中年丧子的打击之后成熟了,他背起行囊去赚钱,劫难、债务和责任让父亲游离的心回到母亲身边。赛麦在成长的拔节声中也饱尝了人生的凄怆。女儿总是从母亲的命运中窥见自己并不遥远的未来。
《摘星星的人》中还是写到中年丧子对家庭的摧毁性打击,作者将更宽广的时代内容融进来了。儿子马丹的淹死是病死,但这个意外与计划生育结扎的奖励政策及危房指标联系起来。村干部的权力也随之浮现出来。随着作者的成熟,马金莲关注的社会更深广了,她对权力的毛细血管作用有自己的认识,但她的表达十分节制,比如写主任的女人“这几年就很爱像男人一样说大话”,主任他妈“话大了,气壮了,腰杆子硬了”。又如,马丹母亲因伤心情绪失控去主任家吵,作者用了间接引语使语气委婉平缓,如“主任半夜里给男人出去打工的年轻媳妇做伴”。在城市小说遍布滚床单、一夜情的今天,马金莲仍然小心翼翼地拿捏感情和表述的分寸。
在家庭内部,马金莲更为关注女性和弱者的处境,她们是女儿、小媳妇、母亲、妯娌、祖母、外奶奶乃至寡妇。这些女性的境遇让人想起萧红笔下那些受到夫家虐待的童养媳和妇女们,还有那些被父母贱卖的女孩们,她们比男性更为凄苦而且无处倾诉,除了生活本身的困厄之外,女性还要忍受家庭内部男性的统治。在农村,男性从事农业、手工业或者商业,他们是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也是家庭生活的主宰,他们决定整个家庭如何分配金钱、如何享用食物。爷爷、父亲总是率先坐上桌,其他人才能落座,而女性往往依然在厨房忙碌。如果我们看过动物的纪录片,很容易想到狮子王对食物的优先权。在家庭内部的食物链上,爷爷、父亲是优先享用者。
在马金莲讲述的故事里,两性平等仍然是个遥远的梦,受制于极端匮乏的经济条件。女性没有话语权,她们不仅要干农活,还要生儿育女,煮饭浆洗,更为可怕的是不幸者要忍受家族的流言、夫家的歧视甚至丈夫的暴力和冷漠,这使得女性处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压迫之下。“家”是女性全部的活动空间,陈旧的灶台、繁琐的家务、吵闹的孩子,困住了女性的身心;而男性的身影很少出现在厨房,他们不是在外做农活就是凑在一起找乐子,后来他们离开农村外出打工,极少停留在家里。因此,女性成了“家庭”的支撑,经受着外部和家庭内部的风暴。男人大抵是沉默的,女性很少能够从他们的言语中获得些许情感安慰。只有孩子的欢笑能够疏解她们的郁积,只有延续血脉的孩子们能够给她们生命提供意义和支持,突如其来的疾病往往会摧毁她们幸福建立的基础。
母亲一直是马金莲近距离的观察对象,母亲身上呈现了生命的来处。《利刃》中的寡母,《梨花雪》中的“她”,《鲜花与蛇》的阿舍……她们是现实苦难和不公命运的承担者,她们以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重担和人生的希望。她们以惊人的耐力与生命的韧性将民族精神传递下去。母亲是支撑整个家庭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越是物质匮乏的时代,母亲生命内部所蕴藏的柔韧与坚毅越发珍贵,就像时间长河中的粼粼波光让人惊奇、让人唏嘘。
二、村庄与时代对话
如果一个作家眼中只有逝去的村庄和童年,那么她必定会枯萎、衰败。只有带着今天来审视昨天,这种书写才能不断生长,不断呈现新的面貌和新的意义。过去并不是凝固的,童年和村庄同样是流动的,其意义在每个今天的建构中不断丰满。和当代“进城”故事关注一个个个体如何离开乡村进城的书写重点不一样,马金莲更为关注村庄与时代的对话,像穿梭巴士一样,她的笔始终在乡村和城市中往返,她的书写重心更多是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乡村。乡村作为主体如何被城市化碰撞、激活、创造和再生。
马金莲细致入微地展现了农村的自然景观:细雨中的梨花、风吹过的田野、天空隐没时的山峦,雪压过后的麦子……土地、农民、庄稼的事情她无不知晓,她深谙农民与四时的关系。她的写作之根深植于她生长的村庄,她似乎总是要将过去深深回味。她时刻关注着村庄的风吹草动,关注村庄在时代的变迁下的微细变化。
近年来,马金莲的一批小说标题上集中出现了具体的时间,我以为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作家自身历史意识的反映。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他的时代犹如走不出他的皮肤。丹纳认为艺术受制于种族、环境、时代几种要素。边地的“小村庄”与喧闹的“大时代”,个人与其置身的环境之间的切磋磨合,这是马金莲在小说中试图回答的问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我们整个国家的确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大时代,但落实到扇子湾的家中,依然是过日子的那些细小的事情:借单车相亲、夫妻拌嘴、走亲戚、小孩嘴馋、重男轻女、失去儿子的父母、日渐衰老的村庄……伴随着“物”的变化,借由对空白的想象我们可以拼贴出一个村庄完整的往昔和迎面而来的变化。村庄被安放在历史的逻辑链条中呈现,城市化的意义不仅在日新月异地改变城市,也催生出乡村的新貌。
《1986年的自行车》和《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两个标题相仿,自行车将家庭与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浆水和酸菜”集中书写家庭内部的饮食,两者都通向生活方式。两篇小说都引入了民谣,前者是“头九温,二九冷,三九四九冻破脸”;后者是“羞脸鬼,羞脸鬼,端个瓦盘要浆水”。民谣具有高度精练的概括力,最能够反映一方水土的风土民情。《1986年的自行车》这个标题突出了物,自行车进入家庭具有身份认同的特殊意义,就像《人生》中巧珍学着刷牙的细节一样具有启蒙的意义。当民办老师的父亲有一辆自行车,他对这辆自行车珍爱有加。自行车将他和村民区分开来,当老师的父亲是流动的,而其他村民被牢牢地固定在田野上。为了增加身份的分量,舒尔布费尽心机借父亲的自行车去相亲,结果车被摔坏了。在这条主线之外,是父亲用车载女同事上班的插曲。《1990年的亲戚》和《1992年的春乏》以孩子明亮的双眼发现了生活的新鲜、纤细,远方总是这样,既让人向往又让人不适。亲戚家的青墙让“我”感到新奇,座钟尤其让“我”移不开眼睛,时间意识由此传递过来。我们可能还记得《倾城之恋》白公馆的钟总是比外面晚一个小时,这是一种隐喻;而《围城》中方老爷送给方鸿渐的钟则每个小时慢6分钟,非常地具有讽刺意味。新妈家物质的富足使幼小的“我”意识到巨大的贫富等级,作者对贫富悬殊的批判被有效地束缚在人情人心的范围内。
《一抹晚霞》以舍尔巴奶奶的衰老隐喻村庄的精神离散过程。展示衰老的细节显示了马金莲非同一般的洞察力,三个儿子都离开老人到外面谋生去了,大儿子去新疆前为父母种了一棵树,“今已亭亭如盖耳”;两个小儿子也都去镇上做买卖,即使回家来也是双眼盯着手机,没有同老人交流的兴趣。机器正在奴役我们,牢牢地参与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削弱人与人交流的愿望。城镇化的脚步越来越快,舍尔巴奶奶和村子一起衰老。儿孙离家赚钱、谋生、求学、革命,堪称现代小说的必经之途。对未来充满欣喜的青少年和落寞的老人构成鲜明的对比,时代就在老人和少年之间涌动变化。
对于那些离乡者来说,他们怀着古老的村庄上路。家乡的温情与美好幻化成他们梦中的月亮,依稀在他们心灵深处发出幽微的光,发出故乡对游子的召唤。乡村生活的岁月在他们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迹,淳朴自然的他们信奉着内心的道德律令抵挡来自陌生环境里的风暴,在凉薄的城市里无依无靠,独自疗伤,砥砺前行。
在近作《梅花桩》《平安夜的苹果》《贴着城市的地皮》中,村庄的变化加剧了。扇子湾不再是闭塞、落后的农村,而是在不断接受现代和消费的刺激推陈出新。村民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念也在与时代和应起舞,稳固的大地似乎开始漂移。一批从扇子湾走出去的离乡者在城市底层艰难谋生。他们没受过多少教育,只好干繁重体力活甚至行乞,还得忍受城市人的白眼和歧视,如《贴着城市的地皮》中的“我”进城后万般无奈当起了“哑巴”乞丐,《梅花桩》里的妹妹是酒店的保洁员……他们的劳作十分卑微,但他们就是城市的一部分,城市的清洁、便捷建立在他们努力工作的基础之上。城市化的浪潮席卷了乡村,将村子里的中青年都吸引走了,城市既给离乡者以现代文明的洗礼,同时他们所接受的城市启蒙又含有被动性,他们努力为“获得一份工作改变农民身份”,却最终成为了城市里的漂泊者,“失去了家”⑩。马金莲饱含同情地刻画出离乡者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的痛苦与挣扎,呈现了他们在城市和乡村均无根的漂泊状态。《人生》中土地所具有的慰藉人的精神力量正在逐步减弱甚至丧失。村庄的精神生活面临着惊人的挑战,马金莲的心魂念兹在兹。
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金钱前所未有地重要起来。金钱引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宰制人们的头脑。人们开始以金钱衡量人的社会地位、人生价值,金钱成为成功的头号判断依据,这致使乡村的传统以及人伦关系的改变,直接表现为年轻的一代开始对土地的厌倦、对教礼的简化与疏离。“阿訇”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也起了变化,阿訇在回民的精神空间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是传道者、启蒙者,是知识与信仰的象征。《金花大姐》一文中刻画了知识分子“我”、阿訇与体力劳动者(金花)三种不同身份的社会地位的颠倒。勤劳而能干的金花姐姐嫁给在远方念经将来要回村子当阿訇的穆萨,整个村子的人都明里暗里地羡慕,母亲高兴得直夸姐姐的命好。可惜好景不长,社会风气剧变,阿訇的地位急剧下降,穆萨这只“潜力股”惨遭贬值,外出打工者赚的钱比阿訇更多。为养家糊口,目不识丁的姐姐和穆萨只好做最低贱的工作。被金花姐姐曾经瞧不起的“我”,如今却因“知识分子”身份而反被她羡慕。现代化使“知识”转化为最有价值的“财富”;而作为信仰符号的阿訇却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险遭淘汰。道德与金钱较量,知识与信仰博弈,一切固有的价值观均受到挑衅、质疑和重建。作为回民,马金莲的写作总是要直面宗教信仰问题,而这一神性的维度恰恰与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大呼人文精神失落相呼应。消费社会的精神建构如何可能?人心如何妥善地安放?马金莲的追问由此抵达了时代的核心。
马金莲的写作联系着另一种层次的中国,那是渐行渐远的“乡土中国”,是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静默的乡村,乡村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有我们祖辈的劳作、叹息和沉醉,有我们醇厚的童年和素朴的风情民俗。那些早被遗忘的简朴、纯粹、美好和安宁,让我们忍不住仰望久违的星空,想去探究永恒的秘密。阿伦特肯定思索过去的积极意义,她说:“对于人类来说,思考过去的事就意味着在世界上深耕、扎根,并因此安身立世,以防被发生的事情——时代精神、历史或简单的诱惑——卷走。”⑪安身立命不仅是写作的出发点,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目标。马金莲的作品中保存着古往今来人类生存的艰辛、苦难与欢乐,存有岁月长河中最为沉静而耐人咀嚼的部分。通过对一系列平凡的小人物的生命瞬间和命运漩涡的凝视,马金莲描绘出大历史演进过程中回民生活的时代变迁。
①②雷蒙·威廉斯《乡村和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01页,第402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马金莲《长河》[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第44页,第42页,第178页,第181页,第183页,第65页。
⑩马金莲《绣鸳鸯》[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年版,第194页。
⑪[美]汉娜·阿伦特《反抗“平庸之恶”》[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0页。
国家社科基金“当代家族叙事中的自我意识与国族想象研究”(16BZW142)阶段性成果]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