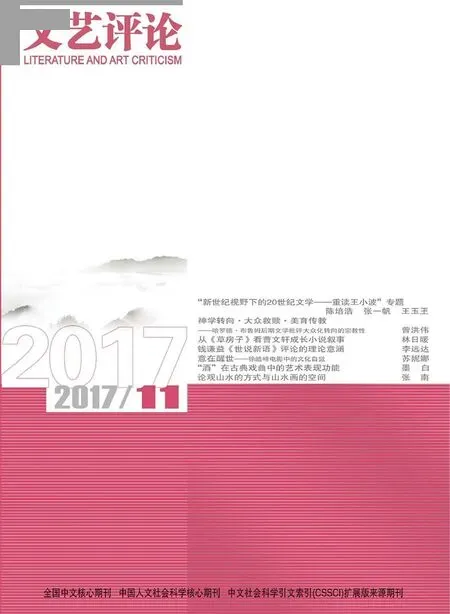神学转向·大众救赎·美育传教
——哈罗德·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的宗教性
○曾洪伟
神学转向·大众救赎·美育传教
——哈罗德·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的宗教性
○曾洪伟
一
“凡对西方学术及思想稍有研究者都会发现,除非我们知道了某位作者的神学见解,否则即难以窥知其学术见解的堂奥。”①这是因为大多数西方学者往往都会有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其学术研究与思想及产品又受其信仰的影响,两者紧密关联,难以分割和剥离。因此,要深度、准确把握一位学者的学术思想,就必须深入剖析、考察其“神学见解”。而哈罗德·布鲁姆就是一位具有虔诚宗教信仰和明确、坚定宗教立场并且其文学批评宗教色彩浓厚的批评家。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如国内学者大多无宗教信仰,学术研究的宗教敏感性与宗教意识不强;布氏学识渊博,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与批评家,其著作的宗教涉猎广泛、驳杂,涉及犹太神秘主义(Kabbalah)、诺斯替教(Gnosticism)、伊斯兰教苏菲信仰(Sufism)、基督教、摩门教(Mormonism)、南方浸礼教(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等多个教派以及大量宗教术语与词汇等等,要快速厘清其宗教知识谱系具有很大的难度;布氏论涉的许多宗教内容对于异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学者而言十分陌生,并且由于缺乏切身的宗教信仰体验与氛围,这些宗教对他们来说显得十分晦涩难解;布氏对这些宗教往往具有自己个性化的、与众不同的解读与诠释,要跟上布氏的理解(思路)也殊为不易;对其宗教批评的研究必须具有丰富、广博、精深的相关宗教背景了解与宗教知识储备等等,这些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而言都具有极大的挑战性,因此,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哈罗德·布鲁姆的研究大多忽视或回避了其思想、认识上的宗教意识形态的一面,从而对其文学批评的研究往往缺乏深度把握与开掘,在许多问题上未能探知其原委与真貌。因此,要深入研究其文学批评,就不能绕开其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鉴于此,本文即主要从哈罗德·布鲁姆的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入手,探赜、寻绎、审视其后期的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
二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布鲁姆的学术批评即陆续赋上鲜明的大众化色彩。其文学批评大众化的转向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世俗原因之外,还有着更为深层、不易为人觉察的宗教动因,即在表面的经典普及和大众美育目的之外,布鲁姆还拟以文学(阅读)救赎大众。何以见得?
在其《西方正典》《如何读,为什么读》《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中,在论及经典阅读、文学批评的目的和功用之时,布鲁姆说道:“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②“传统告诉我们,自由和孤独的自我从事写作是为了克服死亡。我认为自我在寻求自由和孤独时最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去阅读:去面对伟大。这种面对难以遮蔽加入伟大行列的欲望,而这一欲望正是我们称为崇高的审美体验的基础,即超越极限的渴求。”③“仍然存在着孤独的读者,老的少的,哪里都有,甚至在大学里。如果批评在当前还有一个功能,那就必须是针对这个孤独的读者,她为自己而读,而不是为那种被假定为超越自我的利益而读。”④“我们可经由自身的孤独认识自我,或者我们可以——尤其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认识代表自我的人物,或者我们可以在自我中认识上帝,但那必得真是我们自己的自我才行。”⑤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其中反复出现的三个关键词:“孤独”“自由”“自我”(不仅如此,在这些书的其它地方以及布鲁姆的其它著作中,我们也可频繁遇见这三个语词:它们不仅被布鲁姆用来论述文学的功用,而且被用于分析文本、评价人物,如在《西方正典》中,他认为“莎氏独特的伟大在于对人物和个性及其变化多端的表现能力”⑥,他创造出了以伊阿古、福斯塔夫和哈姆莱特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自由的自我艺术家”形象;哈姆莱特能够成为经典的中心,就在于他突出的“自由反思的内省意识”),它们是典型的诺斯替教宗教话语;而且文学/审美阅读对于个体/主体的心灵作用方式与诺斯替教对信徒的精神救赎方式具有异质同构性:“在美国(本土)宗教语境中,自由就意味着与上帝或耶稣独处,与美国式上帝或美国式基督独处。而在社会现实中,至少在最深层的意义上,这(指自由——译者注)可以译作孤独。当灵魂(soul)离群索居(即孤独、独在)之时,比灵魂更深层次的真我(Real Me)或自我(self)或活力(spark)由此也会自由地与同样离群索居的上帝(即处于自由境界或状态中的上帝)完全独处。这种美国式自我本身已具有了上帝性(神性),这使得它与上帝进行自由的交流感应成为可能……如果一个美国人不是处于独在(alone)的状态,那么她就不会真正地感到自由,而且没有美国人最终会承认她是自然的一部分。”⑦可以看出,美国(本土)宗教(在布鲁姆看来,它们在本质上是诺斯替教)的三个关键词也是“孤独”“自由”“自我”,与前述的文学(阅读)功用论中的三个关键词完全重合;而且,文学阅读与诺斯替教在心灵救赎的作用机制与思路程式上也内在一致,都遵循“孤独—自由—自我—救赎”这样一个方略和路径,亦即:(阅读/宗教)个体孤独(独在)→心灵/精神自由→(内在/深层)自我与上帝交流感应相通→获得救赎→超越死亡,获得永恒/永生(这反过来也说明了为什么布鲁姆的批评著作中会出现如此多的“孤独”“自由”“自我”等关键词:这并非空穴来风或偶然巧合,这充分体现出诺斯替教对其文学批评的影响与建构,也暗示了其中所蕴涵的宗教救世思想)。因此,根据它们之间存在的这种深度互文关系,或者说批评/美学话语与宗教话语之间的高度一致性,我们可以断定,布鲁姆的文学经典普及不仅仅是一种审美教育、大众美育,更是一种以审美(的名义)对大众实施和践行的宗教救赎,或者说其大众化转向具有内在的、深层的宗教拯救动机。
那么布鲁姆为什么要借大众美育对社会文化大众进行宗教救赎呢?这就涉及到其宗教信仰、宗教批评观与文学观。首先,众所周知,布鲁姆是一位虔诚的诺斯替教信徒。“我不是荣格的信徒,不会去相信什么集体潜意识的原型象征。但我是文学与宗教评论者,是古今灵知(即诺斯——引者注)的忠实学徒,对重复出现的属灵意象怀有绝大的敬意,不管这些意象是如何流转传布的”⑧,“我自己的宗教经验与信念属于灵知信仰。”⑨(即诺斯替教——引者注)而诺斯替教作为基督教历史上最大的异端教派之一(其它的异端教派还包括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苏菲派、犹太神秘主义等),其关于上帝、世界、人、救赎等核心宗教观点与“正统”宗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上帝观的问题上,诺斯替教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认为他内在于人,并与“自我”同一(也就是说,“自我”即上帝,上帝即“自我”;它并非普通世俗意义上的“自我”,而是一个充满神性光辉的“自我”),内化于自我之中,与现实世界疏离,从而无法拯救世界。而且,在诺斯替教看来,基督教的上帝也无力拯救这个日益走向毁灭的世界。“宇宙就像一个巨大的监狱,最里面的地牢是地球,它就是人类生活的场景”,而“人类成为一个充斥着挫败、沮丧和欺骗的世界的囚徒”,“诺斯替努力的目标就是将‘内在的人’(inner man)从世界的监禁中解救出来,使其返回到他原先的光明王国之中”⑩。在这样一个充满灾难的世界中,人的获救只能依靠人类自身,即通过内在自我寻求上帝,与(内在的)上帝交流沟通,从而实现自我救赎:“它(诺斯替教)不能接受一个外化而至善的神与邪恶灾难世界的并存,因而将一切归向于人的自身,内向化的思考乃是它最主要的特性。人必须在自己里面会见神,那是一个更原初、也更真切的生命与信仰状态。人只有透过对自我的不断的询问,才能知道自己,也才能知道神。”⑪“它(诺斯替教)的上帝是个受苦的上帝,而世界则正陷入错误中,而人则是其中的异乡客,天堂才应是他们的家乡,而人内在的自我则和上帝拥有同样的性质。”⑫因此,综上所述,自然而然,在布鲁姆看来,现世、此在世界中的人类个体都是需要拯救的,而其获救的方式,则是通过内倾转向“内在自我”——“上帝”,而非传统宗教信仰向外寻求一个外在于人的万能上帝。
其次,诺斯替教的这种自我心灵/精神/灵魂拯救方式有效吗?或者说为什么布鲁姆会毕生信仰并研究诺斯替教呢?在《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Omens of Millennium:The Gnosis of Angels,Dreams,and Resurrection,1996)一书中,布鲁姆自述在35岁时,“经历了一段悲惨的时光”,“原本坚实的自我已被掏空”⑬,心灵处于崩溃的边缘。而在此时,对布鲁姆实施精神救赎的就是诺斯替主义思想:他在诺斯替教信条、教义和爱默生“自我/自助”哲性思想(爱默生本人也是诺斯替教信徒)的引导和启蒙下,摆脱了精神困境,实现了自我救赎,重建了自我。而由此,他也确立了自己终身的宗教信仰,并完成了个性化的文学观的初步建构。因此,正是诺斯替教的成功救赎,使布鲁姆皈依并成为诺斯替教的忠实信徒。
再次,如何实施心灵拯救呢?“诺斯替教的教义认为邪恶、痛苦、不幸的根源在于物质创造的环境上。要获得拯救就必须克服无知,通过发现内在的神性,逃避这些外在的环境。”⑭在布鲁姆看来,文学/审美就可以帮助实现这种宗教救赎功能。因为在他看来,阅读文学(尤其是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可以使主体进入“孤独”“自由”的境界、状态,进而使其能够“认识自己”“增强自我”,通过“潜在的自我”唤醒、激活深层、内在的自我,并最终实现与其神性“内在自我”感应相通,获得拯救。“你年轻时若爱上伟大的诗篇,便是和潜在的自我相逢,当时大都是不自觉的。潜在的自我有一股力量,与自我的永生有关,这并非时间的延续,而是醒悟自我内在那未曾出生、因此也不会死去的部份”,“布雷克、哈特·柯瑞恩、马娄、莎士比亚、米尔顿的作品除了高超的语言表现以外,更激起了狂放的想象与思想的乐趣,改变了一个人的认知,使得外在自然为之改观,内在自我随之浮显,那是自我中的自我,之前不曾知晓,不曾改变”⑮。不仅如此,布鲁姆还主动介绍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切身体验,以证明这种“文学阅读”救赎的有效性与可信性:“我个人所坚持的自我倚恃必然与深层自我有所关联,而且我的超越感受始于阅读好诗的惊奇,因此我不得不来做个见证:文学作品可以创造超越的体验。”⑯“心灵自传必定是一曲自我之歌。我65岁了,仍然不确定我的自我是何时诞生的。它在我最早的童年记忆里无处搜寻,却在我9岁或10岁的阅读记忆里显现踪影,尤其是阅读威廉·布雷克和哈特·柯瑞恩的记忆。至少就个人的情形而言,阅读想象诗作为自我接生;自我的诞生姗姗来迟,或者可以说是二度诞生,而前述之阅读似乎可以比拟为:认识我内心之中我先前不认识的东西。”⑰在这里,“自我内在那未曾出生、因此也不会死去的部分”“自我中的自我”“深层自我”“我内心之中我先前不认识的东西”异曲同工,都共同指向一个内植于自我的“上帝”。在《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一书中,布鲁姆曾“提醒人们要在呼唤自己中,去面对自己内在的那个上帝与自我永恒的生命”⑱,而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布鲁姆的心目中,文学(阅读)是能够唤醒“麻木、沉睡”的自我,并使之萌芽、显形的灵验良方与有力武器,它是个体实施宗教救赎的有效切入点和正确进路。因此,宗教救赎与文学/审美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铆合点——即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它犹如人类灵魂黑暗中的灯塔,照亮、开启、指引着个体的心灵/精神救赎之路。
另外,在布鲁姆看来,至少在美国本土的范围之内,这种心灵救赎的实施和实现有着广泛而坚实的信众人群与潜在读者基础。因为经过研究,他发现在宗教信仰层面,大多数美国人信仰的其实是诺斯替教(这是他个人的独到发现与惊人结论)。因为他们的信仰都受到美国(本土)宗教的潜在影响,并涉及到美国人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早已构成美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只不过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察觉或不愿意承认而已。“到现在少说也有两个世纪了,美国人寻找的大都是内在的上帝,而不是欧洲基督教的上帝”⑲,“如果我们是美国人,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共有美国(本土)宗教的因素,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愿意”⑳,“本书(指《美国(本土)宗教》—引者注)提出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但我们并不是。这不是美国宗教(religion in America)的问题,而是我称作美国(本土)宗教(the American Religion)的问题……在美国确实有成百上千万的基督徒,但大多数自认为是基督徒的人其实是别的什么人,他们具有极高的宗教热情,但实际上笃信的却是美国(本土)宗教——它在我们之中存在的历史已很悠久,并饰以多种伪装,它决定和支配着我们大多数的民族生活”㉑。
而在他看来,美国(本土)宗教在实质上又是诺斯替教性质的,而并不是基督教性质的。“摩门教教徒和南方浸礼教教徒自称是基督徒,但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更接近于古代诺斯替教徒而不是早期的基督教徒”,“美国(本土)宗教是普遍存在且其影响是压倒性的,甚至我们的非宗教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在他们最终的预言上与其说是人本主义者,倒不如说是诺斯替教徒”㉒。这样,数量庞大的潜在诺斯替教信徒人群为布鲁姆诺斯替教救赎性质的审美批评文本的传播、接受、认同奠定了坚实的受众基础,而这又必然有利于其大众化心灵救赎计划与愿望的展开与实现。
因此,鉴于以上原因,布鲁姆以文学经典对文化大众进行潜在、深层的宗教救赎(其本质是诺斯替救赎、“自我”救赎)也就顺理成章、不足为奇了。
三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布鲁姆后期的文学批评实际上具有较强的宗教色彩和救赎指/旨向——虽然其宗教性、宗教意识、宗教话语隐藏在文学批评话语和审美话语之中,其痕迹不太容易寻觅、追踪与识别;而综观其前、后期文学批评形态的动态发展与演变,不难发现,其后期的文学批评与前期世俗性质与形态的批评相比,具有深层的宗教转向倾向,而不仅仅是表层的由学院、精英向民间、大众的转向:这就彰显了其文学批评大众化转向的神学转向本质与特征。而这一转向的发生,也标志着生成并扎根于布氏头脑与意识、贯穿布氏一生且若隐若现的宗教情怀(如前期批评理论建构的宗教基础性,中期的宗教批评,后期的宗教救赎意识)犹如地下暗河一般终于由心底、“地底”浮出“地表”,得到释放和实现(即救赎大众)。如果说其前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为生活、为稻梁谋,是为生存于学术体制之内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或者是为学术兴趣而作),那么其中、后期的宗教批评、文学批评则是为救世、为救赎大众而作。而其文学批评神学转向的深层原因,除了上述所析,一方面是因为诺斯替教信仰对其思想、认知影响深刻,从而他认为人类个体都是生活于充满灾难的现世之中,处境悲苦,都需要获得拯救的神学内因之外,另一方面,当代西方“后现代之后”文学理论宗教转向的时代语境,也是促成其宗教转向的重要世俗性、现实性、时代性外因。
本世纪初,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理论之后》中指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文学理论已进入了崭新的“后理论时代”。那么,这一时代的文学理论有何总体发展趋向或显明特征呢?实际上,无论是伊格尔顿还是其他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如德里达),其诗学著作在此一时期(后现代之后)都不约而同地呈现出“神学转向”的倾向。这是因为,“伊格尔顿意义上‘理论之后’的理论,必须转向对人类现世生活中人性基本欲望问题的探寻,而今日广泛流行的科学客观主义观念,显然难以对诸如宗教、传统、爱、终极关怀等普遍性问题作出完满的回答,因而有必要进行思想与理论的‘宗教转向’”㉓。而“后现代固然摧毁了关于理性与压抑的总体性观念,但也抽空了人性尊严与道德共同感的普遍根基”,因此,“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内在困境与人性尊严及共同本质存有的基本设定,促使西方当代文学理论发生‘宗教转向’”㉔,以期在后现代主义“解构一切”的“疯狂”之后所留下的思想、认知、价值幻灭废墟之上,实现超验思想和诗学/审美理论的铆合、嫁接与融合、统一,并张扬和凸显前者,其目的是在文学/审美之中为自我主体重建永恒的信仰根基,而在宗教之中为自我觅得主体栖身和灵魂安顿之所,从而实现对后现代之后社会语境中自我主体的救赎。
从学术生产的实际状况来看,西方理论界(含哲学、神学、文学、艺术等多个意识形态、学科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推出了多部论涉、探讨宗教与其它人文社科/知识领域关联的作品,往往“以断裂与整体、差异与普遍、短暂与永恒、世俗与神圣为主题”,并蔚为壮观,“成为一种时代性的超强音”㉕,最终在事实上形成了一股理论(含文学理论)的宗教转向热潮。这些作品包括德里达的《自我的束缚》(1996),《宗教行动》(2002),威利斯的《哲学及其宗教转向》(1999),理查德·科尔尼的《隐在的上帝:宗教解释学》(2001),齐泽克的《木偶与侏儒:基督教的倒错核心》(2003),齐默曼的《回归神学解释学:具象化的三位一体理论阐释》(2004),卡普托、史坎伦的《奥古斯丁与后现代主义:告白与复告白》(2005),尼尔森、萨博、齐默曼等的《犹在镜中:圣灵的受难与文学及理论的崇高》(2010),㉖等等。
而从种种迹象与表征来看,这股强劲的、横扫西方学界的宗教转向热潮对于布鲁姆的文学批评也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与推动,并促成了其批评生涯的神学转向:因为布氏中、后期的批评在诸多方面与西方理论界的这股转向潮流对接、融通、洽合。首先,转向发生的时间相同。与西方理论界宗教转向的时间几乎同步,也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J之书》(1990)和《美国(本土)宗教》(1992)的出版为主要标志,布氏开始转向和涉足宗教批评,或者说探讨文学(批评)与宗教(批评)的关联;而在其后期,有关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批评论著也不断问世(如《托马斯福音:耶稣的隐秘话语》(1992),《千年预兆:天使,梦想和复活的诺斯》(1996),《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2002),《耶稣和耶和华:神圣的名字》(2005)等),而诸多表面归属文学批评的大众化美育论著,如前所述,在其深层意旨上实际上蕴涵着“自我”救赎、大众救赎的宗教意图,即借文学美育之名,行宗教救赎之实。其次,聚焦“自我”。在其批评生涯中、后期,作为“自我”宗教(即诺斯替教,它本质上是崇拜人类个体“内在自我”的宗教,即通过“内在自我”而实现对“自我”拯救的宗教)和“自我”美学(布鲁姆的美学观实际上受“自我”宗教观的深刻影响,并建基于其上,二者异质同构)的虔诚信徒,作为“自我”美学家、艺术家,布鲁姆无论在宗教还是在美学层面都十分看重与强调“自我”(从起源来看,其美学“自我”源于宗教“自我”,二者具有同一性),它已成为其批评论著的核心关键词:因为在他看来,“自我”是实施和实现个体救赎的唯一、有效路径。而这与后现代之后西方文学理论“宗教转向”中对“自我”的关注与重视也是高度合一的。再次,转向的意旨相同。西方文学理论“宗教转向”的旨意在于“使文学与思想面向人的生存现实敞开,将生活中的某一瞬间铆于文学的永恒节点,将生命中的偶然化为生存的普遍叙事,重新探寻蕴藏在文学与人之生存中的神圣追求与现世关怀,在文学特殊性的多样化叙事中,凸显文学的普遍性与神圣关怀”㉗,即以文学、以宗教促进人的现实/世关怀、精神关怀和终极关怀;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的目的在于推动文学经典的大众化、普及化,而在推行文学的审美教育之外,受其宗教信仰的影响,他更着意于挖掘、彰显、张扬文学的神性光辉与神圣救赎,从而将文学对读者/受众的世俗关怀与神圣关爱巧妙、深度结合起来。因此,布鲁姆后期文学批评的神学转向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宗教转向在转向的目的与意图上也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布鲁姆中、后期批评在转向的时间、对“自我”的关注、转向的目的等多方面与西方文学理论的宗教转向不谋而合,这无疑不是一种巧合,而是其文学批评神学转向深受西方文学理论宗教转向时代大潮影响的一个明证。
与此同时,为切实推动文学批评的神学转向,以文学实现“自我”救赎,布鲁姆苦心孤诣地通过系统的文学批评建构起了他的神学谱系和救赎机制(或者说他通过文学的宗教化而建立起了一种文学“宗教”,其本质是诺斯替教性质的)。具体而言,则是以《西方正典》和《莎士比亚:人类的创造者》的写就、出版为标志,布鲁姆建构起了以莎士比亚为最高神(“上帝”——“莎士比亚在我心中是唯一的上帝,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的上帝”㉘)、以其他经典作家为次级神、以莎士比亚和其他经典作家(本质上都为“自我艺术家”)作品为文学的圣经或正统经文、以其他非经典作家的作品为伪经的神学体系;两本书中的关键词“创造”(invention)和“正典”(canon)分别是“(上帝)创世”和“(《圣经》)正经”的神学隐喻,二者都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和神学意蕴。而若更深入地分析,我们可以说他的文学批评是一个遴选作品、确立真经、淘汰伪经的文学圣经文本甄别过程,他通过文学批评向大众推广、普及文学经典的活动可视作是其传布宗教(即文学宗教、诺斯替教、“自我”宗教)的隐喻,其倡扬经典、反对非经典的行为则可看作是其宣扬正统宗教、排斥异己宗教的一种宗教活动隐喻,其对经典文本的讲解与阐释是对“自我”宗教教义的宣讲与布道,而其文学与其宗教信仰统一于“自我”之中并由之彰显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与其说布鲁姆是一位文学美育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宗教传教士。
因而,布鲁姆后期的文学批评实质上是一个巨大的神学隐喻系统,它包含了一个完整的、自成体系的新宗教(或自创宗教,即其文学“宗教”)建构与运行过程,而其最终目的则与其它宗教一样,都是为了实现信众的心灵救赎和精神拯救,只不过它是通过文学这一特殊的媒介和渠道来展开和实施的。
四
布鲁姆既是诺斯替教徒,又是批评家;同时他既是文学批评家,又是宗教批评家(其批评身份是文学与宗教的统一与整合),而且他深信:“文学即是宗教,宗教也是文学。”㉙这集中体现出他心目中文学与宗教间的亲密关系:在他看来,文学与宗教是二位一体的,两者互不排斥,互洽共生,甚至能够相互转化,兼具对方的形和神、特质与色彩,亦即文学宗教化,文学可以具有宗教的神圣性(“Bardolatry,即莎士比亚崇拜,应该在已有宗教形态的基础上更成为一种世俗宗教”㉚),同时也可以具有宗教的救赎性(“认识自己,认识莎士比亚,认识上帝”㉛);宗教文学化,宗教文本也可具备文学的审美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圣经》乃是复杂的正典化过程的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其评判标准居然是美学的,或者说至少是与美学相一致的。《雅歌》之所以被收进《圣经》中,就因为它已经令伟大的犹太拉比阿基巴(Akiba)心醉神迷,并且这种迷醉与我们对雅歌的着迷,如瓦尔特·惠特曼所说的‘当丁香花在门前庭院绽放的时候’,并没有根本的差别”㉜),宗教具有文学的本质性(“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是在崇拜上帝,但实际上他们崇拜的是三位主要文学人物:J作者的耶和华,《马可福音》的耶稣以及《古兰经》的安拉”㉝),两者在倡扬“想象”(imaginative)、“创造”(creative)、强调深层内在自我(inmost self)等方面具有内在的相通性和不谋而合的一致性。“从瓦伦提努到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再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奈瓦尔和英国作家威廉·布莱克,诺斯替教一直与想象性天才难以区分。在对诺斯替教作了一辈子的思考之后,我大胆地提出这样一个判断,即诺斯替教实际上就是文学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literature)”,“诺斯替教,[是]作为文学天才的宗教(thereligionofliterarygenius)……”㉞在诺斯替教的研究权威汉斯·琼那(Hans Jonas)看来,强力诗人(即文学天才)始终不渝地追求的是“创造性自我的自由”(freedom for the creative self),“自我精神意识的扩张”,而布鲁姆认为,诺斯替教就是一种知识,它使创造性心灵摆脱神学、历史化和一切“与自我之中最具想象力的部分完全不同的”神灵的束缚与羁绊,而且它也特别强调和捍卫深层内在自我的存在,因此,诺斯替教与文学具有深层的统一性。另外,布鲁姆认为,在西方文学史上,许多杰出的作家都是诺斯替教徒,他们的信仰就源自于他们的审美创作。“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中最具雄心、最具抱负的诗人,从雪莱、维克多·雨果到威廉·巴特勒·叶芝,再到雷勒·玛莉亚·里尔克均为诺斯替教徒,他们在自己的诗歌基础之上创构了一种宗教。”㉟而且,在《天才:创造性心灵的一百位典范》中,布鲁姆还以卡巴拉宗教描述上帝的内在本质特点(即Sefirot或“赛斐若”,代表了上帝“神圣品性的秘密”,它们是卡巴拉宗教的核心内容)来构架全书体系,认为一百位天才作家(布鲁姆将其分为十组,每组十个)及其作品充分体现了“上帝的天才”(God’s genius)的十个方面属性,即“至高冠冕”(Keter),“慧”(Hokmah),“智”(Binah),“爱”(Hesed),“大能”(Gevurah),“美”(Tiferet),“ 永 恒 ”(Nezah),“ 荣 光 ”(Hod),“ 基 盘 ”(Yesod)以及“王国”(Malkhut)。㊱这样,经典作家、文学作品就被蒙上了浓郁的宗教色彩。而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布鲁姆所进行的文学宗教化批评的努力与实践。因此,总的来看,在布鲁姆的批评视阈与世界里,文学与宗教之间具有难解难分、互渗互融、水乳交融的关系特性。
而从精神、心灵救赎的层面来讲,其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这具体体现为“美育”与“宗教”之间的亲密关系。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尼采曾经悲观地宣称“上帝死了”,宗教的精神柱石、救赎功能轰然坍塌、崩溃,代之而起的则是“以美育代宗教”的审美救赎思潮;在20世纪中后期,随着后工业、后现代、消费社会的兴起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潮流的泛滥,审美也日渐式微,美育的救赎作用与效力又广受质疑与诟病;然而,在布鲁姆看来,宗教的救赎功能并未失效,文学、美育对人的心灵净化、美化与拯救作用也依然不减,因此,他依然笃信自己的宗教信仰,依旧钟情自己的美学理想,并积极整合、利用自己长期以来进行宗教与文学(审美)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巨大影响与丰富资源,充分激活与发挥宗教、文学的力量与功能,为大众救赎服务。在他看来,美育与宗教并不矛盾、冲突,二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结合,相得益彰。最终,他不是“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美育传宗教”,即通过大众美育活动,促进宗教的传播,并使其充分发挥救世功能。这彰显出其大众救赎的世俗性与宗教性、审美性与神性的二元性复合与构型:其救赎框架、总体思路、最终目的是诺斯替教性质的,而其切入口、进路却是文学/审美的,其大众救赎是文学与宗教、经典美育功能与宗教救赎功能的紧密结合、整合与统一。㊲
①⑤⑧⑨⑪⑫⑬⑮⑯⑰⑱㉛哈洛·卜伦(Harold Bloom)《千禧之兆:天使·梦境·复活·灵知》[M],高志仁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序”第15页,第15页,第11-12页,第1页,第16-17页,第 18页,第 25页,第 18页,第 20页,第 16页,“序”第18页,“序”第13页。
②③⑥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1页,第414页,第46页。
④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M],黄灿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⑦ ⑲ ⑳ ㉑ ㉒ Harold Bloom.The American Religion[M],New York:Simonamp;Schuster Press,1992,P.15,P.28,P.37,P.22.P.26.
⑩⑭R.V.Young,“Harold Bloom:The Critic as Gnostic”[J],Modern Age,Vol.47,Issue 1,Winter 2005.
㉓㉔㉕㉖㉗谷鹏飞、关莉丽《“后现代之后”西方文学理论的宗教转向》[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5日。
㉘㉙郑丽《文学是生命最美的形态——哈罗德·布鲁姆教授访谈录》[J],《外国文学》,2014年第2期。
㉚㉝Harold Bloom.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M],New York:Riverhead Press,1998,P.17,P.18-19.
㉜哈罗德·布鲁姆《批评、正典结构与预言》[M],吴琼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㉞㉟㊱Harold Bloom.Genius: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M].New York:Warner Books,2002,P.18,P.19,P.11-14.
㊲这二者的结合不仅仅体现在其批评作品的文字(如批评话语)上,而且还体现在其部分批评作品的封面图像中,如布氏后期的文学批评著作《如何读,为什么读》(How to Read and Why)英文版(2000年版)封面页就引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早期绘画杰作《天使报喜》(Annunciation)的局部,《写给各年龄段聪明绝顶儿童的故事与诗歌》(Stories and Poems for Extremely Intelligent Children of All Ages)英文版(2001年版),封面引用了威廉·布莱克的作品《教这些灵魂飞》(Teach These Souls to Fly)。这两幅作品都是富有宗教意蕴的画作,它们在赋予审美大众以充分的美感(即美育)和传递出布鲁姆的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同时,也分明透射和漫溢出其神性的光晕与宗教的韵味(关于这两幅封面画作的详细分析,请见曾洪伟、曾洪军《西方文论著作封面图像研究》[J],《编辑之友》,2015年第5期)。而相较于文字,图像的直观性、形象性更使其内蕴的宗教性彰显和突出。
四川省社科规划外语项目“哈罗德·布鲁姆宗教批评观研究”(SC12WY00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公共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