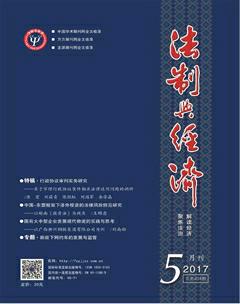“买卖型担保”的定性与效力
韩仪
【摘要】双方当事人以买卖合同为借贷合同提供担保的新型担保方式称为“买卖型担保”。学界集中围绕“买卖型担保”的法律性质、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等问题争论不断,文章收集整理相关文献比对后,认为“买卖型担保”应该划归为“非典型性担保”一类,而买卖合同除了要符合《合同法》的要求之外,还要遵守流质契约的规定才能发挥担保作用。
【关键词】买卖型担保;非典型性担保;合同效力;流质契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刊登的“朱俊芳与山西嘉和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朱俊芳案”)中,最高院认为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一种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而在另一例最高院审理的“杨伟鹏诉嘉美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一案中,法院则认可了双方的借贷关系,认定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为借款合同提供担保,且应视为一种非典型性担保,受到流质条款的制约。
对比这两个相似的案件,我们可以发现最高院在对这种“买卖型担保”的法律关系、法律性质以及合同效力上的认定有所不同。鉴于目前的《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已经对“买卖型担保”的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了规定,既统一为民间借贷关系,因此无需对法律关系的争议再做讨论。而关于“买卖型担保”的法律性质以及合同效力问题现阶段我们依然无法找到有力的法律依据。那么,究竟这种“买卖型担保”的法律性质是什么,这种买卖合同的效力又该如何认定呢?
二、“买卖型担保”的定性
(一)观点展示
1.让与担保说
有学者以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此种担保虽以不动产为标的,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其约定也不符合担保法规定的担保方式,故成立一种非典型的担保。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办理备案登记的行为,是以所有权转移为手段实现债权担保之目的,符合让与担保这一权利移转型担保的要件,构成让与担保。
2.后让与担保说
杨立新教授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买卖型担保”与让与担保的对比说明两者只是在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时间上有所不同,因此“买卖型担保”应当称为后让与担保。
3.抵押权泛化说
这种观点认为随着担保制度的发展,传统的担保物权也发生了一些泛化,“买卖性担保”应该被涵盖在泛化的抵押权之内。
4.以物抵债说
持该观点学者认为这样的行为模式实际是一种以物抵债协议。他们认为以物抵债合同涉及让与担保、流质合同、债之变更和代物清偿等多种法律概念,是故买卖合同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合同内容的不同样态予以区别对待。
(二)观点评析
针对以上几种学说,笔者提出一些自己的见解,首先,这里的买卖合同显然是有担保功能的,以物抵债的观点主要就是模糊了此处买卖合同的担保作用。《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的第一句话就提到了“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显然是肯定了买卖合同在“买卖型担保”中的确可以起到担保作用,明确了买卖合同在这样的案例中应当作为借贷合同的担保来处理。无论是以物抵债还是设定担保其实都是保证债权实现的手段,但是以物抵债合同明显是一种对现在状态的救济方式,往往是在债务人已经确定届期无法偿还借款的情况下双方达成的合意;而设定担保则是体现出对债务人未来的偿债能力的一种预测式救济,是在债务还未届期时就已经事先约定好的。而我们所讨论的“买卖型担保”明显更为符合担保的特征。
最高院在“朱俊芳案”中认为借贷合同实际上是为商品房买卖合同附加了解除条件,也就是说当“债务在期限内被偿还”这个条件成就的时候,买卖合同自动失效。反过来说,当债务还未被偿还时,买卖合同应该是有效的。既然买卖合同真实有效,双方就应该履行该合同,即转移标的物所有权,这跟“买卖型担保”的情形并不相符。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把这种买卖合同和借贷合同割裂开来单纯看做一个合同,它就具有了履行的要求,而“买卖型担保”应该是在债务届期无法偿还时双方才有履行合同的义务,这也印证了这种买卖合同在借贷关系中起到担保作用的解释显然更为妥当。
笔者认为把这种“买卖型担保”归为一种非典型性担保更为妥当。第一,“买卖型担保”不是后让与担保。让与担保的行为模式是确定且完整的,而“买卖性担保”明显不符合这个行为模式,而且让与担保的担保权人是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而这种“买卖型担保”并没有公示的要求,难以保证借款合同的债权人享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的权利。第二,抵押权泛化的说法也略显牵强。现阶段的传统担保物权已经有着自己明确的概念特征和基本行为规则,例如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必须公示。无论社会怎样发展,一个制度的泛化也不应该超越其本身最基本的行为规则。而“买卖型担保”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征,这种担保并非都需要公示,有些标的物只要双方达成合意就可以设立,因此也就不符合传统担保物权的特征。第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担保的形式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实务中也有许多法院对各种不同的新型担保方式予以了认可。“买卖型担保”以订立买卖合同做担保自然也是新型担保的一种,理所当然地可以被称为“非典型性担保”的一种。
三、“买卖型担保”的买卖合同效力
对于这种买卖合同效力的问题,首先,单看这个合同,本身这个合同的效力应该根据《合同法》来判断,只要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事由,就应该被认定为有效合同。其次,从整体来看,买卖合同是借贷合同的担保,那就涉及到了流质契约的适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流质契约仅仅适用于抵押质押这样债权人有优先购买权的情形,而“买卖型担保”的债权人并没有优先于其他债权人优先受偿的权利,因此不适用流质契约;还有学者认为流质条款要禁止的就是不经清算直接抵债的行为,这种担保正是以买卖合同掩盖其不经清算直接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行为,显然违反了流质契约的规定,应该无效。有学者则认为“买卖型担保”的担保人也面临着与法定担保物权人相同的交易风险,自然可以适用流质条款。
笔者认为:第一,这里的买卖合同本质上仍然是合同,只要不存在《合同法》规定的无效情形,就应该被认定为有效,而担保是一种保障债权实现的债法制度,应受到流质条款的制约。前面已经论证过这里的买卖合同实际上就是为主债务合同设立的担保,因此必然受到流质契约的约束。第二,有学者认为流质契约约束的担保仅指传统的抵押质押担保物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狭隘的,我们应该对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做目的性解释,探究法条背后想要保护的法益,而不是局限于对形式要件的要求。流质条款的一个目的是为了维护债务人的利益,而以买卖合同设定担保是否可以适用流质契约,我们就要看在这种环境下,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是否也会面临相同的风险。以商品房买卖合同作担保为例,当商品房的价值较订立合同时出现增长时,能督促借款人及时还款,而借款人或者第三人自然面臨着利益风险。此外,实现债权不经清算程序也是设立流质契约的目的之一,“买卖型担保”这种形式正是不经清算直接转移所有权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买卖合同约定当债务不能届期清偿时,债权人可以直接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那么买卖合同就会因为违反流质条款而无效。
《民间借贷规定》第24条第二款规定了债权人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受偿,隐含的意思就是不能直接获得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这就跟流质契约所禁止的不经清算受偿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认为这就应当是认可了买卖合同的效力实际上受到流质契约的约束,这样的理解与之前承认担保作用的理解也可以相互应证。
综上,“买卖型担保”作为一种新型的担保方式,应当将其归为非典型性担保。在效力的判断上要先讨论合同本身的效力,然后再考虑是否违反了流质契约的规定。
四、非典型性担保在民法典物权分编中的方案构想
在未来民法典物权分编的编纂中,笔者认为要对这种非传统的担保形式作出规定,规定的方式要么就是把实务中常见的一些非典型性担保列举出来,要么就是改变严格的物权法定主义。对比这两个方案,笔者认为第二种更为妥当。一但列举就意味着限制了一定的范围,这样的规则只能照顾到当今最常见的几类非典型性担保,显然无法做到准确全面,且不具有前瞻性。而传统的严格物权法定主义缺少法律必要的弹性,无法应对现实中出现的新型物权,适当地缓和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样的规则就具有一定前瞻性。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