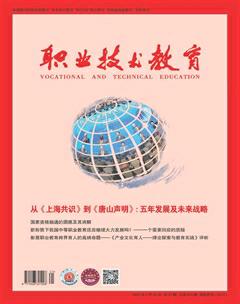国家资格融通的困惑及其消解
肖凤翔+安培
摘 要 国家资格框架构建需要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实现等值互认。身份文化的负面社会心理效应,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配套制度缺乏,国家资格开发课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国家资格融通的困惑,提出塑构职业资格证书理性、开发国家资格融通课程、完善国家资格框架支持系统,以打破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双轨制”,促进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帕累托最优实现。
关键词 国家资格框架;教育资格;职业资格;融通困惑;消解之策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21-0029-05
国家资格是个体胜任专业活动的条件与身份,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资格,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是国家资格框架的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等值互认是国家资格融通的逻辑前提,是国家资格框架构建的关键基础。我国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已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但国家资格框架构建仍面临一定的资格融通困惑。深入探究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融通存在的障碍,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对加快我国国家资格框架实施进程,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推进人力资源高质量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国家资格融通的基础
(一)等值互认是国家资格融通的逻辑前提
等值互认是国家资格框架构建的应有之义与逻辑前提。国家资格框架是特定国家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的基本规范及其制度体系,它规范着人力资源的合理分层和有序流动。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及其相关制度是构成国家资格框架的核心要件[1]。职业资格证书是反映劳动者具备某种职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和技能的证明,是劳动者求职、任职、开业的资格凭证,是用人单位招聘、录用劳动者的主要依据,也是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办理技能公证的有效证件[2]。教育资格证书是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授予接受各种形式教育并达到一定标准的受教育者的教育凭证,我国实施学业证书制度和学位证书制度,学历、学位证书是教育资格证书的主体。职业资格证书指向工作世界,以职业标准为依据,强调对从业者职业能力考核,其设置目标在于提高劳动者的职业能力,促进更广范围内人力资源开发,增加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存量和增量。教育资格证书获得者最终也走向劳动力市场,以实现促进学生知识、技能、素养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统一为目标。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同属于特定的专业领域,在目标价值、考核内容等方面具有一致性,通过对资格证书学习时间、学分、课程量以及学习成果等进行考核以表征价值,等值互认是其融通转换的逻辑前提。
(二)国家资格框架蕴含多重实施价值
国家资格框架是国家資格表征、认定与转化制度体系,关涉教育、培训与劳动力市场等多领域,具有多重价值。国家资格框架融合职业资格与教育资格,实现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自由转换,增强教育系统的灵活性。职业资格证书获得者通过学分转换等方式参加学历教育,获取更高层次的教育资格证书,增扩教育容量,刺激教育消费,拉动教育经济,增强教育积累,构建学习型社会。培训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以国家资格框架构建为契机,加大对培训市场的开发力度,加强对培训市场规划指导,规范培训市场行为,提高培训市场份额与地位。国家资格框架通过教育与培训将更多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改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质量与结构,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生产发展。完善与国家资格相配套的劳动准入与社会保障制度,可促进和谐劳动关系建立,促进更公平的社会保障实施,使国家资格获得者有更多获得感,国家资格框架蕴含的多重价值是国家资格框架构建的实施动力。
(三)国家资格框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先验参考
经济全球化和产业国际化促进人力资源全球或国际配置,推动国家资格框架的国际化。截至2012年,已有15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国家资格框架,其中欧盟36个国家、东盟10国和32个英联邦国家实现了国家资格的对接和资格课程学分互认[3],为成员国人才流动互通提供参考。发达国家国家资格框架将教育、培训以及劳动力市场有机融合,成为我国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参照系。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制定国家资历框架,加快推进人才发展体制和政策创新,为我国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提供政策保障。2002年,湖北省在《关于开展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文凭证书相互沟通试点工作的意见》指导下开展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互换试点工作。2007年出版的《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转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一书,对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转换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入研究,为我国国家资格框架构建提供先验参考。
二、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困惑之审视
(一)“身份文化”的负面社会心理效应
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都是资本的物化形态,具有身份赋权功能。由于“二元结构”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差异、重“劳心者”的白领职业偏好、重学历轻实践的价值偏向使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可获得性不同、对资源支配与占有的先赋能力不同,两者表征差别化的“身份文化”,成为阻碍国家资格融通的社会心理阻碍。
惯于“二元结构”的社会资源配置。资源是社会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与财力的总和,资源配置即在一定的范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分配。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分属教育部门、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管理,形成了“二元结构”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提供教育资格证书服务的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获得国家、地方政府、社会捐赠、自筹学费等多样化资源支持,并拥有一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教师为学生提供专业化服务,充足的财力、物力与人力资源保障使教育资格证书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职业资格证书主要由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以及行业部门管理,虽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与政策保障,但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产生的培训费用、鉴定费用多为个体自筹,容易产生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机构“利益寻租”现象,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教师质量参差不齐,降低职业资格证书的通货价值。“二元结构”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使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处于不平衡的市场状态,职业资格证书的劣势地位加大两种国家资格的融通难度。
重“劳心者”的白领职业偏好。职业偏好是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及生理的种种原因形成的偏爱特定职业的心理倾向。职业偏好对劳动者的择业决策、就业倾向和待遇要求有重要影响[4]。在我国,教育资格证书是公务员、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等白领职业的硬性必要准入条件,职业资格证书以及工作经验要求多为辅助性附属条件。就业准入标准存在对教育与培训选择的心理导向效应,职业资格证书相较教育资格证书的各类资源交换能力较弱,在国家资格框架建构过程中处于“非主流”的式微地位。职业资格证书的“式微身份”影响对职业资格证书的价值评判,偏重“劳心者”的白领职业偏好心理强化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割据。
重学历、轻实践的价值偏向。学历证书是教育资格证书的典型代表,学历证书是本体性价值与工具性价值的统一体。学历证书的本体价值在于其能够表征个体人力资本存量、质量与可能增量,具有标识个体知识、技能、能力等测度指标的功能;学历证书的工具性价值表现为学历作为国家信用承诺下的“一般等价物”能够实现与职业、职业收入、权力、社会地位或社会身份等社会资源的有效交换[5],也即高学历能够为获得者赢取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经济收益、更广泛的权力范畴和更具威望的社会地位。与此相对,职业资格证书指向工作世界,注重对个体实践能力等职业胜任力的考核。重礼崇文尚经的古代文化视技术为“奇巧淫技”、现代唯分数是举的“应试教育”缺乏对实践能力的重视与培养,实践很难实现与高职位、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等值交换,实践的“枝末地位”导致价值判断偏差,迷失国家资格等值前提。重学历轻实践的价值偏向使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资格证书具有明显的“身份差异”与“价值鸿沟”,不利于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有效衔接融通。
(二)缺乏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配套制度
国家资格认证制度保障国家资格证书的“含金量”,顶层设计的就业准入制度促进职业资格证书与劳动力市场规范运行,健全的社会保障配套制度能够减少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但我国现阶段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配套制度缺乏,增加了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的融通障碍。
国家资格认证制度未真正体现国家意志。国家资格认证由教育资格认证与职业资格认证两部分内容组成,教育资格认证在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下,由国家批准的学校等教育机构鉴定实施。职业资格认证由国务院劳动、人事行政部门通过学历认定、资格考试、专家评定、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进行评定认证,进行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认证的目的在于通过认证提高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供给质量。但现阶段我国国家资格认证尤其是职业资格认证存在认证利益化、认证监督机制缺位、背离国家需求等问题。2015年末全国共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12156个,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关系”特性,很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鉴定程序不规范、职业技能鉴定考评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职业技能鉴定质量不过关,甚至存在职业资格证书培训机构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通过“关系”进行“合谋”,引发职业资格证书“利益买卖”等市场乱象,认证的利益化倾向明显,加之實质性的职业资格认证监督机制缺位,职业资格认证存在明显的背离国家需求倾向,导致职业资格证书认证质量欠佳,不利于职业资格证书社会认可的形成,不利于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关系的建立。
尚未实行顶层设计的就业准入制度。根据《劳动法》要求,对从事技术复杂,通用性广,关系国家财产、人民生命安全、消费者权益的职业实施就业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是就业准入的基本条件。从现象视角审视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准入,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和家庭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都是关键影响要素,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体制内优势单位均将教育资格作为必审核项,通过公务员、事业单位考试录用制度选拔人才。对国家规定必须实施就业准入控制的职业,部分地区单位为减少用工成本存在准入执行控制不严格状况。就业形势严峻情况下,为满足求职者增加就业准入筹码心理,各类组织团体推出五花八门的职业资格证书,对劳动力就业准入产生的实际成效不得而知,相反近年来我国每年因各类考评创收带来的“证书经济”总额超过3000亿元[6],职业资格证书市场有序不足,这与尚未实行顶层设计的就业准入制度不无关系。以国务院治理职业资格证书为起点,完善就业准入制度顶层设计,规范实施就业准入,为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创造条件。
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未形成合力。国家资格框架建成需要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协同支持,教育制度服务于劳动制度,劳动制度是联接教育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中间媒介。劳动制度一般包括职工录用、劳动关系、劳动报酬等内容,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住房保障等。个体社会保障可获得水平与教育水平、劳动制度关系密切。教育资格证书增加正式劳动关系建立的可能概率,与之相对应可获得更优厚的社会保障。职业资格证书获得者在求职就业、劳动关系建立过程中处于尴尬的弱势地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机会较少,薪酬与社会保障都处于低位水平,形成由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引起的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增加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的外生性障碍。另外,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多头管理,教育部门和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就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缺乏有效的内部沟通协调机制,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制度未形成合力,国家资格融通面临的困境内外交加。
(三)国家资格开发课程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资格框架是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合意表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国家资格框架的存在要义。课程是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的中介,现阶段国家资格开发课程内容不适合社会发展,课程目标落后于产业标准,未体现新兴产业需求,这成为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障碍。
教育和培训课程内容不适应社会发展。教育与培训是培养人的活动,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载体,课程来源于学科,是从学科知识中选择一部分“最有价值的知识”组成教学内容[7],学科课程是普通教育最经典、实施最持久的课程模式。近年来我国职业院校积极引入“双元制课程”“MES课程”“CBE课程”,开创具有我国职业教育特色的“项目课程”“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等,但由于受职业院校组织惰性影响,学科课程在职业院校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职业教育课程难逃学科课程窠臼,不利于职业院校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而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多以应试为主要目标,课程内容以应试内容为主,或出于降低课程实施成本的考虑,偏重理论课程,不注重实习实训。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内容以职业标准为依据,针对性强,课程内容覆盖面相对教育资格证书更窄,可选择性不高,且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多为碎片化课程,课程内容系统性较差,很多培训机构课程实施不规范,存在“偷工减料”行为,职业资格证书培训质量得不到有效保障。普通教育资格证书、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内容各具特色,但都未能很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寻找各类课程的有机融合点,补缺差异课程内容,为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合奠定基础。
教育和培训课程目标落后于产业标准。联合国统计署2008年8月11日正式公布第四版《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产业标准统筹范围广泛,对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均有适用性,可作为国家资格开发课程的统一参考规范,以促进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衔接转化。课程目标是人才培养目标在课程领域的延伸,是课程实施的预期结果。“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是我国普通教育典型的三维课程目标,普通本科院校以学科课程体系为主,遵循学科知识渐进逻辑,其课程实施具有较强的校本属性,课程设计主要由任课教师主导,对产业标准的关注不尽相同。职业院校课程以培养生产建设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课程目标存在落后于产业标准的情况。职业资格证书课程以培养学生胜任职业所必须的知识、技能、能力为主,课程设计主要以职业标准为依据,课程目标主要培养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因此,无论是教育资格证书还是职业资格证书课程目标设计都对产业标准关注不够,不利于提升教育与培训的产业服务能力。
教育和培训课程未体现新兴产业需要。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正式提出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7大新兴产业23个重点方向,新兴产业发展需要对口专业人才支撑,对比《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我国教育资格证书教育的专业设置未能充分覆盖新兴产业,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受历史惯性与组织定型影响,课程更新速度较慢。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以产业发展状况为依据,以服務新兴产业发展为导向,但因职业院校位于教育招生的最底层,课程以实践为导向,理论深度有待提升,课程对新兴产业服务能力有待强化。职业资格证书课程参差不齐,课程的基础特性明显,以胜任职业所必须的基础知识为多,对新兴产业需要的新兴课程涉及不够深入。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课程服务新兴产业路径不明晰,未能很好的满足跨产业需求,未能高效对接新兴产业特殊领域,教师服务新兴产业能力不强,其差异性也成为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融通互换的障碍。
三、国家资格融通困惑的消解路径
(一)塑构职业资格证书理性,实现国家资格的最大通约
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实现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融通,需重构职业资格证书理性。匡正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认知偏颇,职业资格证书不是学历文凭附属品,不是金钱交易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同样具有表征人力资本的就业准入价值,是与学历证书等同的市场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证书类型。增强职业资格证书的市场含金量,依据职业、产业标准开设职业资格证书课程,规范职业资格培训,严格职业资格证书鉴定过程,实行强有力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公信力。并强化政府与社会的统筹监督效用,加大对职业资格证书不规范行为的打击力度,引入职业资格培训机构信用体系,规范职业资格培训机构行为,全面提高职业资格证书质量,以塑构职业资格证书理性,为两证融通奠定基础。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资格证书融通转化需探寻国家资格的最大通约性,即实现两者的等值互认。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资格证书在理念、知识、技能、能力等契合点方面相互吸收、相互漂移、相互补充,通过学习成果等可计量标准实现双证书的价值量化,促进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由分离走向融合。
(二)打破国家资格“双轨制”,寻求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的帕累托最优
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在职业获得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二元路径”的劳动力市场进入、薪酬待遇、社会保障、社会地位与职业流动方式,形成由教育资格与职业资格引起的劳动力市场“双轨制”。充分发挥国家意志的主导作用,将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明确纳入政府工作议程,出台相关政策,强效促进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等值实现,减少教育资格证书获得者再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额外成本,降低职业资格证书获得者为获取学历证书进行的教育投资,实现教育与培训的有机融合。加强教育和人社部门协同,克服部门壁垒,顶层设计并强制实施就业准入制度,将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获得者在就业准入过程中同等看待,平等建立劳动关系,实施同等薪酬待遇,公平享有社会保障权益,助推教育、劳动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帕累托最优实现。
(三)开发融通性课程,完善国家资格框架支持系统
国家资格框架建设的相关支持条件包括资格标准系统、资格认证系统、课程建设系统、学分转换系统、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结果认定系统、质量保障系统、技术支持系统等内容[8],其建设是复杂性系统工程,需要专业化组织统筹指导,建立国家资格框架的管理机构[9]。可选择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等职业教育发达地区先行试点,保障资金、技术、人员等方面,以点扩面,逐步推广。其中,课程是国家资格融通的基础,课程开发质量直接关系教育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授予质量。学校、行业企业、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加强协同,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为目标,以产业标准为依据,体现新兴产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开发适用性强,融通转化度高的符合学习者认知规律特点的国家资格课程。
(四)加强制度建设,以法律规范国家资格框架的权威
国家资格框架建设是大势所趋,国家资格框架的系统性要求有完善的法律法规等制度作保障。相较嵌入法规,独立法规更能有效规范国家资格框架运行,如南非《国家资格框架法》等。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国家资格框架法》,通过立法明确我国国家资格框架实施的指导思想、相关利益主体权责、支持系统、运行机制等内容,以法律权威强力规范国家资格框架高效施行。约束国家资格框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不端行为,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应加大对职业资格考试不端行为的处罚力度,以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加强对教育资格证书授予过程的监督,加强对学位授权点的评估,以保证教育资格证书质量。以《国家资格框架法》为依据,形成国家资格标准制度、国家资格认证制度、国家资格课程制度、国家资格学分累计转换制度、质量保障制度等制度体系,促进国家资格高效实施,保证国家资格框架权威。
参 考 文 献
[1]肖凤翔.国家资格框架中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等值[J].教育发展研究,2015(5):1.
[2]黄尧.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转换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5.
[3]张伟远,段承贵,傅璇卿.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国际的发展和比较[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4:3.
[4]苑茜,周冰,沈士仓.现代劳动关系辞典[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210.
[5]彭正文.文凭与社会资源交换的社会学分析[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5:22-43.
[6]李长安.将更多职业资格认定交给市场[N].深圳特区报,2016-06-07(A02).
[7]周光礼.“双一流”建设中的学术突破—论大学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建设[J].教育研究,2016(5):72-76.
[8]肖凤翔,黄晓玲.国家资格框架发展的世界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职教论坛,2014(16):79-83.
[9]姜大源.現代职业教育与国家资格框架构建[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21):23-34.
On Perplexity of Accommodation N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its Resolution Strategy
Xiao Fengxiang, Anpe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requires the equivalence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Negative social psychological effect of identity culture, lack of supporting system of education,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cours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 lagging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re the perplexity of accommodation of national qualific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construct the logos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 develop national qualification accommodating course, consummate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support system, to break the dual track system of educational qualification and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so as to promote realization of Pareto optimal of education, labor and social security.
Key words 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perplexity of accommodation; resolution strategy
Author Xiao Fengxiang,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duc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 An Pei, PhD student of School of Education of Tianjin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