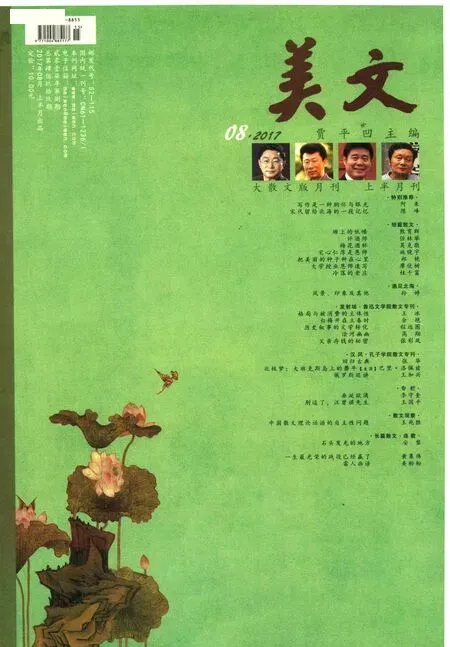梅花酒杯
——写给我的老师蒙万夫
◎ 吴克敬
梅花酒杯——写给我的老师蒙万夫
◎ 吴克敬

吴克敬 1954年生于陕西扶风县,西安市作协主席、陕西省作协副主席,西北大学客座教授。曾荣获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散文奖、柳青文学奖等奖项。2010年10月,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
酒浆扯成了线,叮叮当当地跌入一只彩绘了梅花的酒杯。我有太多的泪水,像这晶莹的酒浆一样,在眼的湖海里涌动、流出,清清亮亮的一滴,竟溅进了我面前的那杯酒液里,溅出一声惊心动魄的声响。我睁开婆娑的泪眼,看见了捏在手中的酒杯,奇迹般地壮大起来,特别是酒杯上的那朵梅花,突兀在风雪漫卷的冬天,灿烂着满目的亮红。我看见敬爱的蒙万夫老师,从荡荡的酒液中走来,顶着风,顶着雪,来到枝摇花开的梅花树下。我晓得,他只能从酒液中走来,他的灵魂和精神,都闪耀着纯而又纯、粹而又粹的酒光。我还晓得,他将永远与梅花为伴,圣洁高雅的梅花,不求助绿叶的呵护陪衬,不需要春雨的滋润营养,全凭着抗风雪斗严寒的质本,在白雪皑皑的世界里,独自展现他自在的壮美与活力。
我独自坐在这个初春的夜里,手捏着这只梅花酒杯,一口又一口地喝着辣得喉咙发疼的酒水。十分普通的一只陶瓷酒杯,因为上面烧制了一株凌霜傲雪的梅花,便深得蒙万夫老师喜爱,他把它送给了我,亦成为我珍爱的宝物,清冽的酒液从细圆的酒杯滑进我的口中,缓缓地流过舌面,再从喉咙透进肺腑,直达每一根血管,仿佛要经历十年百年的跋涉。
一个人的初春的夜晚,一杯烧酒,一盏昏灯,我静静地回味纯粮酿制的佳酿,浓烈如火的酒液,勾起我不尽的回忆。
到西北大学读书,对于我这个农家青年,已经是个破碎的梦。虽然我一边做着沉重的木匠活,一边还写着被叫小说的文章,最使我扬眉吐气的,是我创作的中篇处女作《渭河五女》被《当代》选中,刊发在1985年第三期的头题位置,这使我更渴望能有一次深造的机会。这个机会就在蒙万夫老师的一封信中,寄给了还在乡下的我。当我读着信中那简约的几句话时,心里的激动,像长了翅膀的雁雀,伴随着蓝天白云,呼呼飞往西北大学。我把使在手中的那把木匠斧,顺势斫在一块木板上,站起来,抖掉一身的木屑,毅然踏上了报考西大作家班的路程。
作为柳青研究专家的蒙万夫老师,那时是西大中文系的一名副教授。我在花团锦簇的西大校园里打听着他,想不到一下子打听到他的当面。
我小心地问:“知道蒙万夫老师在哪?”
他笑了,说:“你认识他吗?”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他还是笑着,说:“找他有事?”
我把他写给我的信掏出来,交给了他。这时候,我已敏感到他就是我要找的蒙万夫老师了。可是我不敢十分的肯定,因为他的衣着,和他对人毫不拘礼的言笑,怎么和一位很有建树的大学教授也联系不起来。
只看了一眼信封,一种他所独有的慈祥,取代了他脸上的浅笑。他说:“才来。”
紧接着又说:“还没吃饭吧。”
接下来的一切,都在蒙老师的安排下进行。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简简单单的几个小菜,一瓶红西凤酒,两人便吃喝得很开心,而且十分地投缘,好像我们早就是一对相交很厚的师生,相隔数年,今天又喜获重逢。因此,菜吃得不多,酒喝得不少,你一杯,我一杯的,转眼就腾出了一个空酒瓶。考试、录取,让我害头疼的两件事,一下子变得也简单了。五日后,我便幸运地拿到了西大作家班首期学员通知书。
去学校报到,交上两千六百元的学费和一千二百元的宿费,便囊中空空,平日的生活用度立即成了问题。与我境遇相同的,还有几位同学,几乎清一色农家儿女,我们既得不到公助,亦得不到私助,愁情困态只有自己来解决。
蒙老师从饮食上发现了我们的潦倒,他为之担心起来,因我有一手自觉不错的木匠手艺,他便出主意,让我把家伙(木匠工具)带来,由他出面在学校找个地方,课余和星期天揽活儿做。蒙老师的主意差不多已打动了我的心,决定回乡下取家伙时,渭南人李康美和我胡诌,言下之意企业有钱,我们有笔,何不到企业去给他们写点什么,说不定能换回几个子儿。此言一出,我甚欢喜,当下与李君找到蒙老师,讲了我们的设想,他大为支持,电话要通了未央区一位掌握实权的他的学生,三五句话,就谈妥了一本宣传企业的报告文学集写作合同。这一合同交给了李康美去完成,而我则孤身去了宝鸡,与当地的经委谈成了又一本报告文学的写作出版合同。于是我们几位农家子弟的学员各得其所,便大干了起来。
我领衔宝鸡那本书的操作。其间,蒙老师放心不下,偕同系上的李成芳老师到宝鸡来给我们助阵。来的那天,好像是个芒种日,放眼宝鸡塬坡的小麦,已是熟得一片金黄,空气中,浮动着新麦诱人的馨香。在宝铁招待所我迎接来蒙老师一行。当晚,即由厂家做东,在招待所备了一桌酒宴,为蒙老师他们接风。作陪的除了我和厂方的几位头儿,余下的都是分配到宝鸡工作的西大学友,且都聆听过蒙老师的教诲。于是,一桌饭吃得十分愉快,所有的人都敬了蒙老师的酒,他也有敬必喝,一点儿也不含糊。大家敬了一巡,他又过来敬大家,三敬两不敬,蒙老师的话多了起来,滔滔不绝,一桌人就他一个声音,预订好的一桌菜,还没上齐,他已醉得不能自已。及至客人走散,我把蒙老师扶到下榻的房间,他依旧大唱独角戏,言语既出,有对他新老学生的希望要求,有对社会的认识见解,还有对人生的辨析探微,说来不磕绊,洋洋洒洒,好不痛快,仿佛要在这一夜,把他心中的块垒全都吐露出来。这么倾泻着,大约到深夜11时半,两行浊泪从他朦胧的醉眼中喷涌而出,随即大吼一声:“人还活个什么劲?”同时跃身而起,直奔窗口,就要从三楼高的地方跳下去。
蒙老师的这一举动,大出我们的意料,在场的我和李成芳老师及另外一位同学都大吃一惊。毕竟我还年轻,手脚敏捷,先于蒙老师几秒钟,把他拦腰抱起,从悬悬的三楼窗口拖回房间。此后一个时辰,刚刚强强的一个大学教授,虚弱得如一个久病的大孩子,蜷缩在床铺上,嘤嘤地哭泣起来。他向我要了一支笔,一页纸,埋头写起什么来,黄豆大的泪滴,仿佛串串珍珠,纷纷坠落笔端,在雪白雪白的一页纸上,绽开重重叠叠的酒泪之花。
终于,蒙老师睡去了。我从他手里取出满纸未写完的酒话,细细品读时,心灵不能不为之而震颤。字字皆珠玑,行行为肺腑,满篇忧国忧民情。他太热爱自己的祖国了,在诅咒那场动乱的同时,殷切希望我们的祖国强大起来,兴盛起来;他还希望人能爱人,以赤诚的心,对待生养自己的土地,对待这土地上生活着的自己的同胞。
匆匆三月时光,我主持的那本书稿业已编辑出来,交由出版社审读。几日无事,与蒙老师敞开胸膛拉了几回家常,彼此心意相契,很是谈得投味。那一日晚饭已用,我正要出门闲溜,蒙老师又来了,他从怀里摸出一个瓷瓶的汾酒,并那只梅花酒杯。我原想他是又要和我喝一场了。可蒙老师并未久留,只说他过几日要和路遥诸君去一趟铜川,酒先放在你处,回来咱把它干了。
过了一日,我因出版费还待落实,就去了宝鸡,谁知就在他和路遥相约去铜川的那日清早,竟急病弃绝人寰。消息传来,我痴呆呆坐了很长时间,只觉苦涩的泪水,如决堤的洪涛,从翕动的鼻翼上滚滚而下。
我不相信蒙老师会离开我们而去。
火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已不再铿锵,沉闷得像一头呜咽的老牛,驮着我从宝鸡往西安赶。还是这班火车,我与蒙老师有过一次同行,车行途中,蒙老师从他的怀里摸出一瓶存放得有些年头的红西凤。我惊讶蒙老师带了酒旅行,高兴得鼓起了掌,因为我知晓53°的红西凤酒,存放的年头越久越有滋味,启开盖,香了一节车厢。没有酒杯,我们对着瓶嘴吹,那一分豪气,那一分张扬,让人真有点忘乎所以了。
没有下酒菜,相互的言语便成了必不可少的佐料,以至于酒喝完了,话还说个没完。下了火车,出了站台,也不急着回家,两个人漫无目的地走进了古城墙边的环城公园,其时太阳已经落尽,半轮月亮昏昏暗暗地挂在远处的西城门楼上。
不知高低、不晓深浅的我,向蒙老师海聊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追求,兴之所至,还会一个蹦儿跳起来,好一番手舞足蹈。说着,还说起我对一个女孩的暗恋,这个女孩现在已是又一个女孩的母亲和我相濡以沫的爱人。我不知该怎么感激我敬爱的蒙万夫老师,正是有了这一次掏心窝的倾谈,蒙老师便不遗余力地促成了我们的相恋相爱,而组成我们幸福美满的家。
蒙老师也说了他自己。分明有着长期压抑的情感,像垒积起来的一座山,让年届50岁的蒙老师要喷发了。当我听到他喉咙里一声低吼才起,便有火山般挟雷裹电的岩浆喷薄而出,整个人颤抖得像是一场地震,他顺势抱住身边的一棵大树,那是一棵榆树,有碗口粗的样子,正是榆钱儿闹枝的季节,在蒙老师剧烈的摇撼中,榆钱儿像是星光洒下的雨珠,失魂落魄地坠落下来,落了蒙老师一头一身。
是什么让蒙老师如此痛伤?
我无助地盯着蒙老师,没有一句安慰的话,任由蒙老师自由地发泄。我也没有多问什么,从他断断续续毫不连贯的述说中,仿佛晓得了根由,日后回想,又仿佛什么都不晓得。
在城墙公园抱着树摇,在蒙老师的生活里究竟发生过多少次?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还有一次,是与陈忠实先生一起摇了的。西北大学临近西安城墙,城墙公园自然成了蒙老师与友人散心聊天的好地方。陈忠实先生写出了《白鹿原》的初稿,他们两人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陈忠实把初稿那给蒙老师看,蒙老师认真地读了。读了后,他把陈忠实约在城墙公园谈感受,说体会,两人谈得投机,说得投缘,竟然绕着城墙公园走了一个晚上。他们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在来日初夜时分,蒙老师穿着件单衫子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我弄了几样小菜,我们喝酒了。我们喝的还是红西凤,几杯酒下肚,蒙老师说话了。他说陈忠实咥了个大活。他说我要有机会看一下,对我是会有大启发、大帮助的。蒙老师没有用“写”,他用了个陕西乡间人好说的“咥”字。咥即是吃,蒙老师的意思我懂,阅读《白鹿原》要有吃的态度,仔细地咀嚼,认真地吞咽,踏实地消化才好。我记下了他的话,后在《白鹿原》出版出来,确如他指导的那样细嚼慢咽踏实消化了。当然,这都是后话,我与蒙老师是夜喝着酒,喝着喝热了,蒙老师习惯地解开单衫子上的扣子,敞开了他的胸怀,这使我吃惊地看见,他的胸膛上是一片擦伤后结出的痂,层层叠叠,仿佛鱼的鳞甲!我问他了,他立即拉着衫襟,把胸膛上的伤痂掩饰起来。不过他给我说了,是他和陈忠实在城墙边转,转了一夜,两人转着说着,到了不可抑制处……蒙老师还要往下说的,我端起一杯酒,把蒙老师的话堵回了他的嘴里。我想象得出来,他会像与我那次一样,在城墙公园里抱住一棵树摇了。树皮的表面都是粗糙的,粗糙的树皮被他紧紧地抱着,一摇一摇的,怎能不擦伤他的胸膛。
噩耗传来,我知世上没有还魂药,无力让蒙老师和我再说什么。回到西大校园,我突然感到原来热热闹闹的地方,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我记下了那个日子,1988年10月2日。我欲哭无泪,痛感除我父母之外,生命中又失去了一个亲人。
来读作家班的同学,在西大或多或少都得到过蒙老师的帮助和关照。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的心中激起的哀伤,犹如山倾海覆,大家或作诗,或写文章,写出来就找地方贴,一时间,竖起在校园喷水池两侧的布告栏,重重叠叠都是哀悼蒙老师的文章,实在没地方贴了,有同学就贴到教学楼的墙上,你贴我也贴,一下子把教学楼用纯白的纸张裱糊了一遍。仅此,还不能表达我们的哀伤,便扯了一条丈六白绫,手书“痛悼我师蒙万夫”几个大字,直直地悬挂在作家班同学住宿的大楼上。
1988—2016,掐指算来,蒙老师已和我们分别二十九年。这二十九年,蒙老师给我的那瓶汾酒还在,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记着你的话,等你回来,咱们一起干了它。你给我的梅花酒杯还在,它已成了我所有珍藏中最牵肠挂肚的一个。每临寒食节,我必取出梅花酒杯,斟上酒,恭恭敬敬地洒了,祭奠我酒泪迷茫的蒙老师。
今夜又寒食,我无客无朋,家人也出游去了,只我一个人在客厅里孤独地喝着酒,窗外是孤傲游走的风声,室内却是凝然静止的景物,只有我的思绪像窗外的风,飘散得细细碎碎。我不能自已地又往梅花酒杯斟酒,酒液叮叮当当注入酒杯里,却怎么也把小小的酒杯灌不满。这个发现让我吃了一惊,仔细看时,才发现这只梅花酒杯原来残了一个小小的缺口,酒液默无声息地从缺口溢出去了。
十数年前,我即写了怀念蒙老师的文章,这次再写,做了很多修改,也添加一些内容,我是想我该有这样的态度,当然也有这个机会,把我心里的蒙老师尽可能真地写出来。修改到最后,我把那只梅花酒杯拿在手里,仔细地端详着,我在想,蒙老师为什么送给我一只缺口的梅花酒杯?他是在他多个酒杯里随便取了一只送给我呢?还是有意选择了一只残了一个小小缺口的送给了我?我不得而知,只是固执地并且是徒劳地往酒杯里注酒。我多想把酒注满酒杯,但无论怎么努力,却都不能满杯……晶晶莹莹的酒光在我心头明亮着,我忽然明白了,这难道不是蒙老师对我的鞭策吗:
再有学问的人,也有自己的缺失,难有一杯满酒;
再完美的人生,也有自己的缺失,难有一杯满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