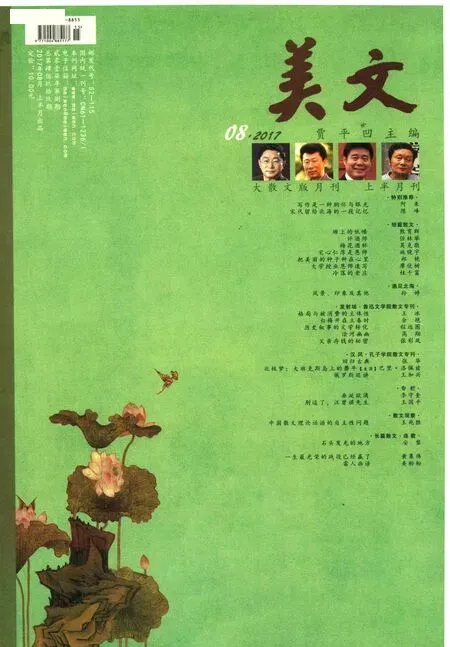塬上的纸幡
◎ 熊育群
·短篇散文·
塬上的纸幡
◎ 熊育群

熊育群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文学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散文委员会委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中国作家》郭沫若散文奖、第十三届冰心文学奖等,获评广东省文学领军人才、德艺双馨作家等。出版有诗集 《三只眼睛》,长篇小说 《连尔居》《己卯年雨雪》,散文集及长篇纪实作品《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西藏的感动》等19部作品。
周陵
一种莫名的情绪,夏日黄昏,一座巨大的坟墓上,幽远如旷古的气息,笼罩、弥漫,像田野上的烟岚,模糊了远近的树木与房屋。
我站在坟顶,有点猝不及防,仅仅一个时辰前,我还在飞行中,奇特的地貌“塬”在机翼下出现,渭河平原的村落、玉米地、苹果园、道路,随着飞机高度的降落变得清晰……一对隆起的土堆那么突兀,像大地上的双乳,相连的小径露出腥黄的泥土。我注目着它,想象着、判断着……
一种想法,驱使我终止转机了,突然又轻率地决定——去那两个土堆。在咸阳机场联系酒店,很快,一辆面包车把我接出了航站楼。
车往北开,高空鸟瞰的玉米地、杨树,带着渭河平原的气息把人裹挟进去。一堵猩红的围墙,里面露出墨绿色两座山头。想不到酒店就在围墙后面。两座山头就是那两个土堆?是不是太巧合了?我冲动着,放下行李便出了门。
围墙铁门早早落了锁。沿着墙根讪讪而行,我从一个破落的院子冒冒失失闯了进去,里面是坍废的墙垣,一条青石板的老路伸向田野。几棵老槐树落日下橙与绿交融成一爿光亮,濯亮了青石条的路。路边又是一道围墙,围着一座古庙,古庙后面一座小山出现了。
寂寂无人。山下一股荒凉之气,让人想到侠客隐身之地。青砖青瓦砌筑的亭塔立于山脚,说它亭塔,是样子像亭,其实是塔。近了,看到中间凹墙里嵌了一块黑色石碑,上书黄色隶书大字:“周文王陵”。
周文王?三千多年前的坟墓?细看题款,乃乾隆年间咸阳知县孙景燧所立。
都说周朝墓而不坟,有茔无冢。春秋孔子父亲死时还没有坟,他长大后寻找埋葬父亲的地方还颇费了一番周折,于是破古制,为父母立起了坟堆。这块土地上最早立坟的是秦国王公墓葬。由坟称陵,则从秦惠文王始。这是不是秦王的陵墓?周文王何以筑陵?难道周朝已有坟了?
阶梯升向天空,陵的顶端平如直线,这是一座覆斗形方陵。走在平坦的陵顶,稀疏的柏树立如人形。北面的一座陵墓,泥土的小径隐没在荒草丛中,恰似颈脖上围了一个项链。夕阳正从它的一侧坠落。那是周武王的安寝之地。
想起小镇的名字周陵,周朝的开创者就在这里安息?这是否是后人假托?丰京、镐京,两个词突然生出了一种气场,哪怕隔着三千年,它好像就藏在我的身旁。今夜就睡在陵墓兆域之内,我陷入了一种深沉的梦幻:灰色、模糊而虚幻,但却如此真实!
橘红的夕阳,天鹅绒蓝的穹庐,如水的晚飔,北方与南方阳光如此不同,哪怕正值盛夏,夕阳亦有深秋金箔般的色泽,光芒笼盖四野,一如垄上烟火,洪荒世界并未远去,苍茫岁月浸满了虚妄的况味。
一架一架飞机低低越过,白银闪耀,轰鸣声风一样四散。想起上午的那扇舷窗,我从嘉峪关飞西安,久久地眺望——起飞时满窗钢蓝色,祁连山如伏地的冷兵器。钢蓝色曾困住我,爬七一冰川时,山上下雪,山下落雨。雨水引发了落石,落石阻断了铁路。六月雪把我留在了镜铁山的黄昏里。矿区桦树沟食堂,与刚出矿井的年轻矿工一起排队打饭,他们看我的眼神充满了疑惑,但内心的热情却毫不掩饰——我这位不速之客打破了他们寂寞单调的生活。
入夜,月出峭岩,山高月小,等待出山的矿区火车犹如荒古遗物,被峡谷阒静深埋。我吟哦起匈奴的悲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感觉一条山谷古近而今远,匈奴的幢幢幻影正在靠近……卫青、霍去病的军队打到了山下。山下的酒泉正在庆贺胜利……两千年的岁月在巉峻岩壁上像神思一恍惚,它这么一晃荡就没了。
仅仅一夜之隔,我就站到了渭河平原。
周陵恰如一次奇袭。我遭遇了历史时空的重叠。
三千年的睡眠是如此安详,像田畴上的庄稼潮汐似的交复,王朝更替,演绎着天地间的宿命。脚下堆砌的巨大工程让死亡恒在,这是一次至今还在进行的死亡。兆民的膜拜把它比喻成了高山,巍峨、壮阔。王的威严在大地上亘古不易。
这一刻,触及的历史如此真切,时空穿梭的感受是如此强烈,风一样行走的影子,便是暮霭似的王的殿宇楼阁,氤氲气象……
远处的村落,传来了鸡鸣犬吠。
周陵周围是否有周文王的后裔?或者人群里留下某种传承的行为、习俗、语言,基因一样遗传?哪怕只鳞片爪都是令人兴奋的。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偏执,时间久远漫漶,我明白两位王者早已失去了与世间的关联,土著们不过是来历不明的移民,但内心里却不愿两座陵墓孤悬于世。
一种冲动,为着印证,为着世间零落的奇迹。
一座大牌坊,红底黄字写着崔家村,逆光中的村庄像浮在光里。走村串户,我的眼里早把三千年与现在连成一体了。
新农村建设,水泥的村道,瓷砖的墙,院落围在屋子里面,由老人们守着。一个个老人询问下去,他们不是姓崔便是姓李,并无姬姓。经打听,清明节周陵隆重的祭祀,村里人都是去陵墓祭拜的。
三个老年妇女在宽敞的水泥路上收拾麦子,我跟她们一样蹲下来,淡淡的阳光浮在周围,仿佛自己也参与到这千百年重复的劳作中,老人慈爱的笑给了我回家一样的感受。
一位老人指给我费家村的方向,说那个村里有姬姓人家。
崔家村与费家村之间隔着大片田地,地里枯黄一片,都是收割后的麦茬。青青的玉米苗从麦茬里蹿出半尺高了。费家村村口废弃的小学叫崔费李小学,三个姓氏里独不见姬姓。
见到姬三建、姬辉的时候,欣喜的情绪难以掩饰,感觉讶异,就像他们是我的远亲似的。盲目的行为竟然有了结果!问起族谱,他们的祖先就是周文王姬昌。以前村里建有祠堂,可惜毁了。现在村庄因城镇化要搬迁,他们舍不得离开。除了故土难离,还有他们世代对周陵的守望。
血缘是这样奇妙,这一对堂兄弟长相并不相同,我却试图从他们的脸上寻找某些特征,去想象陵墓里的人。这样偏激的想象直到离开也没有停止。交谈、留影、观察,在他们宽大而空荡的房间穿过,直到夜幕降临,依依惜别。走在黑暗中的乡土路上,突然觉得时空从来就没有流动过。有个身影开始弥漫,仿佛正在靠近……
康陵
站在周文王陵上,发现西南方烟蓝色的山影,疑窦顿生:平原何来孤峰?若是陵墓,何以如此巨大?第二天,租了一辆三轮电动车,我往西南方向而去,一种预感,我在赴一个古老时空之约。它的朝代古老到了哪一个年代?一种呛人的岁月烟尘渗满了现代汽车尾气。
开电动三轮车的老人,是从三岔路口三轮车堆里挑的,他掉了一半的牙齿让人心生怜悯。谁能想到他与我同龄呢。称呼他大爷他连连说“不敢不敢”。他的方言是一株植物,看不明,认不清,风中哗啦啦翻响着。模糊中,明白了他的疑惑,他不知道我去哪一座。难道有很多座山?
当然是去最近的。“去大寨村?”“大寨村?”听不明白。任由他往前开吧,有山我自然看得到。
康陵就这样向我扑面而来,西汉最后一位短命国君要向我诉说他的亡国之恨了。
一块简陋的牌立在铁栏上,记载了汉平帝刘衎的死期:公元6年2月4日。这是一个寒冷的日子,绿色褪尽,泥土冻得生硬。葬礼一定是隆重的。汉代的厚葬之风炽盛,皇帝的葬礼全都极尽奢华。
铁栏内欹斜的踩踏出的泥径,像一条倒挂的河流,急泻的地方坡陡,漫流的地方则缓,庞大的伸向天空的山体如此巨大,与一个十四岁少年的死太不相称了。一步一步攀登,平原低低地退缩、臣伏,双层覆斗形陵墓,半山上有一圈平台,在此驻足、眺望、沉思。埋葬如此之深,就像秘密的冤屈一样深。少年是心脏病复发还是被椒酒毒死?专权的王莽已经握紧了帝王的权杖。公元前206年由刘邦开创的巍巍汉代江山走到了尽头。这一个中华民族星河璀璨锦绣斑斓万世景仰的王朝,一个确立了汉人、汉族、汉语、汉礼、汉服的朝代,翩翩少年再也扛不住它了,未央宫里曾经照耀五服蛮荒的光芒渐渐熄灭,阴谋家露出了得意的笑脸。
山上来了一群人,一条五彩风向标迎风飘荡,一把巨大的滑翔伞意欲挣脱绳索飞去。有人架起相机,向着烟云浩渺的渭河平原取景。咸阳城的高楼矗立于地平线上。帝王的陵墓一座座在远处浮现出来,高高的陵墓一共九座,沿渭河北岸展开,让平原生出了一种气势。
康陵脚下闪闪发光的全是墓碑,坟墓密密麻麻,死亡是如此浩大,他们都愿意长眠在帝王周围。
一队披麻戴孝的人出现在田间小道上,向着康陵走来。走在前面的人举着白色的招魂幡。他们头戴丧冠,身穿孝服,手执竹杖。队伍静默地行走着,不知是为新亡人前来祭悼还是办理什么丧事。
与汉代一样,杖依然竹制,那时长与胸高,现在短如戒尺;汉时苴绖用麻,现在用白布;那时最重的斩衰服不加缝缉,现在孝家穿的是白大褂;女子依然不用丧冠,汉代女人麻布条束发成髻,现在白布裹头;汉代孝服以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服来区分与死者的亲疏远近,持斩衰之服的男子穿斩衰裳,系苴绖、绞带,执杖,冠绳缨,着菅屦,服丧三年。现在以白黄红三色的冠绳缨和杖做简单的区分……死亡没有变,对待死亡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这是对待生命的态度,是人心人伦温度的变化。
茂陵
出租车司机姓陈,他不知道茂陵往哪里走。他没关心过陵墓。他在一家工厂当保安,下班后开了自己的车来马路边拉客。对我坚持要去茂陵他感到奇怪,知道我来自广州后就更加不能理解了,一个外乡人跑这么远来看一座土坷垃?他一连说着“坟有什么好看的!坟有什么好看的”。
昨晚去路边的一家烤鱼餐馆,那是从康陵去咸阳的路上,暮色田垄里的一长排红灯笼,暖暖红光后面一座高大的坟墓。我拐到了坟前,天已黑,周围同样坟茔遍布。向人打听,谁也不清楚坟里埋的什么人。世代与陵墓相守的人,陵墓对他们不过寻常之物吧,已经视而不见。
司机一路打听去茂陵的路,聊起了他去广州北京打工的经历,说自己是一个喜欢结交四方朋友的人。
水泥的公路,铺在玉米、苹果树与西瓜秧的平原上,铺在夏天的阳光里。路边砖混的农屋,零星散布在地里。靠近茂陵时沿路出现两排房屋,似街又不似街,粗糙的房屋,红砖外露,有的贴着劣质的瓷砖,有的水泥粉刷。想着汉代皇帝陵墓边的陵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这些因供奉山园而修建的城邑,李白当年的想象与玉宇琼楼的陵邑仍不能相比,豪强大贾如挚纲、原涉、郭解都搬迁来了,虽然是强迫,但后来就连司马迁、董仲舒、司马相如也相继迁居。住在陵邑成了身份的象征。
路边这些狼犺的砖房,显出现代人的生活是多么简陋原始,对待生活的态度是如此的不经心、随便,得过且过。
茂陵出现了,除了一堵围墙,四面都是玉米地和苹果树。往东,陵邑一点踪迹也寻觅不到了。绕着茂陵围墙走的时候,注目东方,遥远的烟火气息似乎在我的鼻腔里弥漫。刺目的太阳光下,如毯的庄稼地,玉米与苹果树的绿四面延伸。陵邑数万人家仿佛一夜间蒸发。旷野里岑静无人,懒洋洋的热风把土地的腥气带向空中。
茂陵邑奢华喧闹的时候,陵墓还在修建,每年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投入修陵。汉武帝在长安城的未央宫临朝听政,他的大将霍去病、卫青先后离他而去,作为陪葬者,他们的陵墓在东方高高垒筑起来。卫青的陵墓形如庐山,霍去病的则状如祁连山。他们当年攻打匈奴,一路打到祁连山下的酒泉,霍去病把汉武帝奖赏的一坛酒倒入泉水中,与将士们共饮,酒泉由此得名。
茂陵修了53年后迎来了它的主人。他口含蝉玉,身穿金缕玉衣,安放五棺二椁的梓宫,随黄肠题凑、便房、堂坛、墓道、羡门、甬道一起埋入地下。茂陵修成了汉代最气派的王陵。陵墓的随葬品充塞,多得再也放不进去了。“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生禽,凡百九十物”。
随后,他五柞宫临终托孤的大臣金日碑、霍光也埋到了茂陵之东,为汉武帝陪葬。
一座座巨大的封土堆穿越岁月的风雨,高高耸立在今天的庄稼地里。茂陵的阙门、寝殿、便殿、昭灵馆、承恩馆、陵庙……不见了踪影,荒草地上仿佛晃荡着一个巨大的谎言。一个农人经过,偶尔一声咳嗽,发出了最真实的响声。
进茂陵不锈钢的大门,门外突然响起了鼓乐声。一辆卡车坐满了打鼓吹号的人。车在大门外停下,鼓乐也停了。三台白色面包车和一辆大巴开了过来,车内坐的全是穿白衣服的人,他们满脸哀戚的神情。
空调大巴下来一个男人,他头戴白色绳缨,身穿白大褂,拿着一把缠满白纸的竹杖。接踵而下的人抓着矿泉水瓶,三三两两朝前走。偶尔有人小声说话,有人热得解开了衣扣直裸着胸膛,女人有的相互搀扶,他们慢慢走成了一个队形,男人在左,女人在右。人群朝西走进了玉米地。
这是一支送葬的队伍?没有灵轿,没有长绋,更无哭泣。我看不到死者。如若火化,那个小小的骨灰盒呢?它也在空调车上,或者面包车当了灵车?
我在草丛间追到了队伍前面。走在最前面的人双手端着外金内银锡纸包的脸盆,里面盛着金银色锡纸包的元宝,肩上扛着红白两色纸幡,头戴黄色的绳缨,身穿白大褂。他很年轻,圆脸阔大,浓眉微蹙。人在悲痛时眼睛总是低低看着路面的,仿佛有无尽的路要走。
走在他旁边的老年妇女,哀戚是沉甸甸的东西,拽着她的脸。她的头一直低着,眼皮也没有抬一下。他们都沉湎于自己内心的悲苦,也许正在冥想着死亡,困惑于生与死,也许在回忆着往事,独独忘了一个外人把镜头对着他们。
看到红绸包裹的骨灰盒,绸上印着黄色的“奠”字,心里一沉。她就是今天要安葬的人了。捧骨灰盒的人走在小伙子后面,他头戴黄色绳缨,年岁稍长。从黄色绳缨知道他们是同辈人。他的后面是一位长者,捧着黑白遗像,这是一位八十多岁老人的像。再后面是捧灵牌的人。灵牌白纸上用毛笔写着“魂帛”二字。他们都头戴白色绳缨。
南来的风吹动着纸幡,灼热的阳光照得尘土虚白。如此寂静的葬礼,不闻哀乐、炮竹,没有哀号,只有脚步踩踏尘土的声音。那座汉武帝的巨坟慢慢后退着,青青的树木渐渐变得灰绿,它屹立在天地间,见证了两千年的死亡,见证了葬礼、葬俗的变迁与人间的哀乐。它自己也成了死亡的昭示。大地上死亡的绵绵不绝、无处不在,拓开了茫茫时空。历史在所有的死亡之上得以完成。
疯长的荒草,成片的墓碑露出石头的青白。黄土隆起,南北低陷,形如微缩的塬。这塬上全是坟墓。鼓乐又在上面响起来了。
这是一个村庄的墓地还是一个家族的墓地?他们为何埋得如此之远?水泥砖砌好的穴,骨灰盒安放后,纸扎的金童玉女放进去了。陪葬的人偶着色彩艳丽的华服,让人想起世间的繁华亦如纸薄。
不闻哭声。一个人沿来路返回的时候,只有阳光里的风声,大地亘古的宁静。
李夫人
抬头看到一座陵墓,来时只注意了送葬的队伍,我竟然没有看到它。
陵墓似乎是秀丽的,一种孤独的秀丽。陵分两层,虽然高大,但比茂陵要低。陵上青草稀疏,没有一棵树木,掩不住的黄土,一条灰白的土路蛇行而上,老远就看得清晰。
从一片片苹果树与玉米交织的庄稼地走近墓碑,阳光越来越猛烈,我靠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想不到李延年的《丽人曲》与这堆黄土有关!他所唱的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就埋在这座陵墓中,这座陵墓就是英陵。
一个人如此靠拢,独自面对,一种迫近的压力,感觉到她的灵魂、她的气息在荒冢之上氤氲,灵魂的秘语在飘荡,我听到了自己的呼吸,听到丝丝风声拂过旷野,天地间的大寂静、大寂寞凝结在冰冷的天穹,汇聚在铁幕似的蓝色里,脑海里杂念全无,身心浸满了这万古沉寂。
李夫人是李延年的妹妹。李延年为汉武帝献艺,一首《丽人曲》深深拨动君王的心。她眉如柳叶,脸似桃花,何等的绝世芳华!汉武帝对李夫人一见钟情。当一对情侣生离死别时,汉武帝哀求她转过脸来,见上最后一面。她却执拗不肯,直至红颜委蜕,玉骨销香。她想要汉武帝记住的是自己最美的容颜。
《牡丹亭》里的爱情在长安城里发生。汉武帝命画师在甘泉宫画上李夫人的像,又邀方士祈仙求神,作赋唱曲。思念如同烈焰把他吞噬,汉武帝求助方士法术,他要去鬼神的世界与李夫人相见。
那天夜里,方士作法,看着自己心爱女人的衣服被抱进帷帐,生前的种种回忆一定汹涌而至。烛光摇曳,酒案飘香,方士东喷水、西念咒。汉武帝独坐帐前,痴望着帐内的灯光,数个时辰后,李夫人的身影帐内出现了,恍兮惚兮。他忘记了阴阳两隔,站起来就往帷帐内冲,悲伤与喜悦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方士一把拦住了他。那一刻,他心内一定如同刀剜。看着女子转瞬逝去,“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情到深处,文字带泪。汉武帝这首短诗被收入了乐府诗,千古流传。
入葬英陵,汉武帝又写《李夫人赋》。这首赋写得痛彻肺腑:“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
“芜秽”写英陵上的杂草,而“隐处幽”写泥土深处的幽冥。面对同样的一堆黄土,爱她的人伤心欲绝,凭吊者如我则只有唏嘘。
站在英陵之上,脚下便是“隐处幽而怀伤”。远处的墓地,送葬的人群开始回家。寥廓的田野,苹果树、玉米一行行排列得整整齐齐,如列队的兵士。这些来自美洲大陆的玉米李夫人是陌生的,坟边张里村人李夫人是陌生的,红砖坡屋顶的小楼杂乱不堪,远处的荒冢死者不知来自何方,如果灵魂飞扬,东南方的茂陵一定是她向往的地方,那里有她的君王在思念着她,等待着她,与她茕茕相吊,遥相呼应。他们相守了两千年。
走下陵墓像有人把我往下拽,山坡有些陡。正午的阳光闻得到焦糊味,土地被太阳烤得灼热。我轻抬脚步,担心这样厚的黄土压痛了她,疑惑着这堆泥土怎么收拾得了这样的绝代佳人和千古风流?鼠洞、蚂蚁、蚂蚱与庄稼地一样的黄泥,热风、蓝天,阒静同样寂寞笼罩,汗水湿透了T恤,泥土便是脂粉,敷了皮鞋厚厚的一层粉尘……
汉长安城
秋天来了,从广阔的天空吹来了凉意,几片枫叶飞下枝头。抬头望一眼虚空中的蓝,感知着更深的节律。秋天,我又来到了渭河平原,来到了汉长安城,来到了汉武帝与李夫人一起生活的地方。
这个秋天,在天津滨海新区客居、写作,我纠缠于芦花与荻花的区别,月光下细细观察芦花,希望它有银狐一样的光芒,仿佛这是一段借来的时光——我在过另一个人的生活。
汉代长安城遗址就在这个时候清理出来了。邀我去的电话来自北京,奇怪,又是汉朝,令人好不愕然——
这年,从春天开始,就跟汉代结了缘似的。四月徐州丰县之行,无意间我到了中阳里刘邦的故里。在汉皇祖陵看汉代开国皇帝的祖坟,青岩的墓碑,还有引出筑巢引凤成语的古木。一场突然而至的清明雨,庄稼地上哗啦啦响成一片。我在雨中鞠躬行礼,闻到了一股墓地泥土的气息。
那么,周陵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周、汉两个朝代之间是春秋战国漫长的分裂时期,秦统一后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就灭亡了。隔着一条宽阔的时光峡谷,汉代一定遥望过周的背影。它从诸子百家中吸收了众多的思想与智慧,但如何治理一个大国,周朝是唯一的榜样。正如我从周陵望见汉陵,历史的延伸需要传承。周陵给予我的是某种历史的象征,从中可以品味,可以思索。
汉长安城的遗址就在西安未央区龙首塬上。正是张衡《西京赋》中的“疏龙首以抗殿”。那里有绵延的黄土城墙,残碎的瓦当青石,巨大的础石,宫殿宫署的地基。未央宫周围的村庄搬迁走后,一个荒凉却真实的遗址裸露了出来,它面积达36平方公里,城墙长50多里。迅速扩张的西安城早已把它包围了。
一座大都市,如此广阔的土地可以任凭荒草生长,这是多么奢华的举动!谁有这样的魄力?汉代是如此强悍地存在着,两千年了遗迹犹存,特别是长安城的城郭竟然如此完整无缺!伟大的朝代获得了后人的礼遇,这是我们向文明的致敬!它带给了子孙古老的文明气息和深刻的历史启迪。千年之后,今天的举动也将为后人赞叹。
汉长安城的古老堪比意大利庞贝古城,其神秘则可比秘鲁的马丘比丘,它的规模之大人类任何古老遗址都无可比拟。西方石头的建筑保存并不难,东方的土木建筑历经岁月与战火鲜有保存下来的,长安城会有怎样的模样?
飞机降落咸阳机场已是入夜时分,望着舷窗外沉入夜色的渭河平原,心里默想着文王、武王的陵墓,它们就在我的脚下,飞机的引擎声已经惊动了封土堆上的秋虫。
未央宫出现在我的面前,在一片市声远去后,它那开阔的视域,高高升起的台阶,当年的时空就凝固在今天的秋阳下,笼罩了悠远的静谧。一条几十米宽的中央大道彰显着一个东方帝国的气势,出入未央宫的人就走在这条大道上。
大道通向西安门。
西安门是汉长安城12座城门中的一座。城墙东南西北各有三座,西安门是南城墙最西边的大门,有东、中、西三个门道。除西门道遭破坏,东、中门道仍清晰可辨,它们宽8米,进深20米,门道间的夯土隔墙厚达14米。门道两侧排列着巨大的础石。地面由不规则的石头拼成,钢化玻璃下面它们呈现着一种淡青与泥黄的色泽。
两面的城墙早已坍塌,但气势依然不凡,高耸的泥土墙向着东西伸展,在淡蓝色秋霭里看不到尽头。与它平行的城壕,宽如小河,低低凹陷,野草如毯铺满了河床。壕中水由南向北,注入渭河。北城墙东段和东城墙的城壕至今仍在使用,那是一个湖——汉城湖。
城墙上的杂树绿得凝重,墙土斑斑驳驳起了一层灰白的皮壳,有砖砌一样笔直的线痕。这是一层层夯实时留下的印迹。裸露的一个个小洞,也许是竹筋,它们早已朽烂。城墙的夯土据说炒过,草籽和虫都被烧死了,又加糯米汤,这样既长不了杂草又坚固。十几万人修筑城墙,历时5年才完成。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墙。也许,世上历时最久的土城墙也只有它了,两千年的岁月仍然不倒。
从前有人在城墙下埋人掘墓,挖几下手就起泡了。住在城墙边的农民,砌房不用打地基,就在城墙上直接砌。李下壕村人清末战乱时还在城墙下挖过窑洞,那时森林茂密,时有豺狼出没。
当地人把城墙神化了,南城墙被称为公龙,北城墙称为母龙。卢家口村人传说,北宋以前村里的城墙很完整,一天夜里,只闻车响马鸣,第二天一早,发现城墙都倒了,家家骡马大汗淋漓,一夜之间城墙的“脉气”飞去了汴梁。
四野空旷,阳光下草木的气息浓烈。我向着远处的高台走去,未央宫前殿虚幻的影子似有若无,默想着《三辅黄图》中的记载:“前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它让这片荒地即使荒芜也难以堕入荒野之列。《水经注·渭水》写到未央宫前殿“斩龙首山而营之”“山即基阙,不假筑”。眼前的土地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南向北分成了三级,一级高过一级,这是前殿的台基,脚下的草地便是被削平的龙首山。曾经四座庭院梁柱雕花,瓦当悬空,在此经风沥雨。
长安城最密集的建筑群就在这里,班固的《西都赋》也在这里展开了。它崇方择中、左祖右社,《长安志》所列殿、台、观、阁70余座,温室殿能驱寒保暖,清凉殿伏天可清暑生凉,未央宫面积达到现今故宫的6倍。
当年萧何监造未央宫,刘邦进攻匈奴回到长安,看到一座极尽壮丽的宫殿,他为如此靡费财物而生气:“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却理直气壮回答:“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刘邦听后露出了笑容。的确后世再没有比它更加雄伟的宫殿了。这是《汉书·高帝纪》记载的情景。
想象着汉武帝接受群臣朝拜的情景,我穿行在宽大的汉服丛中。从这里发出的诏书传到了最遥远的地方。帝国的疆域如此辽阔,北方现今俄罗斯的贝加尔湖变成了它的内湖,西边到了哈萨克斯坦的巴尔喀什湖,东面鞑靼海峡是它的内海。汉武帝开疆拓土,达到了中华疆域的顶点,罗马帝国也无法与之相比。霍去病曾在此发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张骞从这里两度出使西域,打通了一条丝绸之路。他们都表现了汉代人开阔的胸襟。大汉雄风不仅在于宫殿与疆域之大,还在于人们的胸怀之大。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视野开阔,面对苍茫壮阔的世界,人们为森然磅礴的气势所吸引而投入创造。他们想象奇丽,诡思放浪,随物赋形,不泥于实,形神妙趣,婉若天成,这正是汉人九天揽月气魄的真实写照,中华民族的奔放和世界的壮阔在此融为一体。这样的精神气象波及黄海之滨,当年孔子乘槎登山望海的地方,现今连云港孔望山发现的东汉大象石雕,椭圆形巨石通体雕琢,与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如出一辙!
帝国的心脏就在这里跳动。汉武帝接见西域使节,受理西域纳贡,回馈礼物。皇帝登基、天子大婚、寿诞、皇帝入殡,都在这里举行。重大的决策在此做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此出台,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直至今天。“实事求是”的思想也在这里发源。确立“二十四节气”,传统节日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七夕节、重阳节也从这里开始进入百姓的生活。司马相如的煌煌大赋在这里传颂。当年司马迁走过未央宫,前往天禄阁、石渠阁翻阅图书典籍和档案,构思他的历史巨著《史记》。天禄阁至今弦歌未断,天禄阁小学就建在它的遗址之上。
登上前殿台基,城市的高楼退得远远的,阡陌之上,村落、耕地、树林,一如茂陵所见,大荒之野,仿佛历史从没发生过。而高台下发掘出的遗址十分醒目,皇后居住的椒房殿、皇室官署少府、中央官署、天禄阁、石渠阁,露出地面的础基,巨大的础墩……都像梦境似的呈现。
注目于高台下的槐树、大皂角树。槐树分两种,洋槐四五月开白花,可以吃,国槐七八月开黄花,结槐米,可以入药。汉长安城曾遍植青槐。
台基上站着一位王姓中年男子,他天天来这里,告诉来人这里发生过的故事。譬如他以前锄地,经常有西汉时期的钱币从地里蹦出来,地里瓦碴也多,从前村里有人用汉砖、瓦当垒过猪圈、厕所。他们村里的人把舅家叫尉家,因为西汉皇帝把皇后娘家人封为太尉。他在台基上出了一个上联,求来人对下联。
男子是大刘寨人。大刘寨就在台基的东北方,村庄搬走不到两年。槐树、大皂角树就是大刘寨的树。这片土地属于未央宫,还是属于大刘寨人呢?这是他们的故土,他们迁到北三环以外的地方去了,每户村民迁走前都拍了照片留念。他们还写下村史,编纂成《汉宫九村寨》出版。属于汉长安城的地名需要确定空间,需要考古,而属于一个个村庄的地名一目了然。
村名与汉长安城有什么关联?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已经水乳交融,城如书,村如字。譬如高庙村,因为村庄所在地段的城墙上曾建有庙,被称作高庙;吴高墙村因为有姓吴的人居住,建村的地方城墙高大,故称吴高墙村;夹城堡村因为村庄的西面是汉长安城的西城墙,东面是桂宫的城墙,因此称作夹城堡村;天禄阁遗址边的小刘寨和柯家寨合成一个大队,取名天禄阁大队;樊疙瘩村建在高地上,因为村南卵石铺的路疙里疙瘩而得名,卵石是汉代铺的,后来挖出陶水道、汉砖和写有“长乐无极”的瓦当,才知道这里是长乐宫的前殿。樊疙瘩村的老人说,当年举行岁首朝仪大典,刘邦对着瑰丽的长乐宫发出“知皇帝之贵也”,这慨叹就是站在他们村南说的。
去茂陵时阳光那么灼热,眼前的太阳却失去了热度,蝉也喑哑了,黄昏时凉意开始渗骨。想起英陵和茂陵,汉武帝与李夫人在这里有过怎样甜蜜的时光?那个病重不肯转过身来的女子,对一代君王有过怎样的期望?临死也要把病魔夺去的美留在他心里。那座甘泉宫呢?那些画像呢?那些方士画师曾经陪伴安抚过的心呢?一种痛彻仿佛还在空中不去不散。
在未央宫前殿台基上北望,我希望再一次看见他们的陵墓。田野上,庄稼、树木和村落由近及远,直至虚如紫烟。茂陵一点踪迹也看不见。想起班固《西都赋》中写长安城“北眺五陵”的文字,他指的五陵是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和平陵,那不是他远眺能看到的情景。李白“南登杜陵上,北望五陵间”,他能看到的也只能是田垄村舍。而汉武帝当年写《李夫人赋》时一定也向英陵长久地眺望过。
茂陵与汉长安城并不遥远,当年霍去病举殡,一路旌旗蔽日,边境五郡将士身穿黑铠甲,排列两旁,浩浩荡荡自长安城一直布列至茂陵。李夫人举殡的情形并不知晓,四十里的路,阴阳两隔。汉武帝生前看到自己陵墓东西两端都埋下了自己最心爱的人,他的心该多么痛。怅然北望,目光里掠过的忧伤无人懂得。懂得他的人已经身在“隐处幽”了。一座未央宫已盛不下他的一腔情思,他的忧伤已随文字洞穿了苍茫岁月。
一个王朝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途已经匿迹。当最后一位皇帝刘衎的灵柩抬过渭河时,巍峨的王城就不再有西汉之魂了。虽然它作为国都又延续了一百多年,新莽、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都以它为都,东汉献帝、西晋惠帝和愍帝也在此建都,但王城再无汉代豁达闳大之风了。
平民百姓大约从元代开始住了进来,现在居住在遗址上的人大多是明朝华县大地震迁徙过来的人。又一次迁移开始,未央宫遗址上的9个村庄已经搬走,还有更多村庄等着搬迁。甲午年夏天,重新面世的未央宫遗址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想起飞机上看到的塬,一种参差错落的奇异地貌,它由雨水切割而出,一块块平原因河谷而悬空,一面面的崖,陡而直,河谷直直地下落。这样的地貌你站在谷地,高处的平原只有一堵墙,背影一样平整地伸展,不像山更似岸。譬如一个朝代,我们落在了时间的悬崖之下,你看得到岁月的高墙,却看不到高处的平原,你只能仰望,无法攀登。这就是岁月,是历史,是王的土地的奇观。那一片看不见的塬,早已升到了我们的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