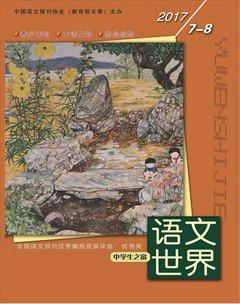你一定要读王鼎钧
李昕
三联书店要推出王鼎钧作品系列了,想起这事,内心就止不住有些激动。我关注鼎公二十年了,阴差阳错,一直未能如愿出版他的作品。这一次,经过相当激烈的版权竞争,鼎公欣然同意将他的回忆录和散文作品版权委托给三联。
编辑中,鼎公曾经两次嘱我作序。作为晚辈,自知才疏学浅,力有不逮,未敢应命,悬疣书前。但对鼎公的书,我一向推崇,想说的其实很多。
大陆读者对鼎公或许并不熟悉。但是王鼎钧这个名字,在台湾却是家喻户晓。这里甚至用得上那句话:“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我一直想不清楚,台湾作家如柏杨、李敖、白先勇、龙应台、陈映真等,大陆读者早已耳熟能详,但为何鼎公却独独被严重忽视?其实,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我开始关注台湾文学时,最早希望介绍给大陆读者的,一位是李敖,另一位就是王鼎钧。但鼎公的被忽视,或许与他本人的低调和超拔脱俗的性格有关。鼎公其人,似乎并不在意他的书多出一本还是少出一本,也不在意读者对他的评价,并不急于为自己做“推销”。
鼎公的作品,用他本人的解释,广义上都是散文,狭义上又分两类,即回忆录和随笔类的散文。鼎公的回忆录四部曲,洋洋一百万言,博大而丰富,厚重而深沉。他现已九十高龄,一生经历丰富坎坷,抗日时跟着父亲打过游击,后来做过国民党的宪兵,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去台湾后,先在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国广播公司做编辑,后来又担任过多家报刊的编辑和主编,晚年定居美国。进入晚年以后,他觉得自己阅尽人间沧桑,万语千言郁积心头,不吐不快。然而他写完回忆录前两册《昨天的云》和《怒目少年》之后,忽又搁笔停止写作。为什么?因为他感到自己还没能超越过去长期接受的狭隘的政治观念和党派立场,他不想使自己对于历史和人生的观察和思考带有任何偏见。于是他在静静地等待,等待自己的心灵归于平静,等待自己的灵魂进入超然的境界。所以他说自己是用“等了一辈子的自由”,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回忆中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居乎其上,一览众山小”。
从另一方面说,许多人写回忆录,是因为人们总是最关心自己,最忘不了自己;而大部分读者并不爱读别人的自传,也是因为别人的自传与自己无关。但鼎公的回忆录不同。他作为20世纪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并不是为自己写作。他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他的回忆录可以说是20世纪一代中国人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的缩影。
台湾作家杨照说:“王鼎钧写出的,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后,留在身体里的,永远的疤痕和恐惧。”中国近代史专家高华去世以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推荐鼎公的《文学江湖》,说“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至于鼎公的随笔类散文,大陆一些读者或许知道他非常著名的“人生三书”和“作文四书”,那是伴随着一代台湾读者成长的经典性作品,想起它们,就如同我们想起当年在中学课本里时常出现的散文名篇一样。鼎公的散文,文笔极佳。抒真情,写真意,妙语连珠,信手拈来。有诗情,有哲理,篇篇美文,章章精品。我以为,这样的散文不是刻意写出来的,而是从心底里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来自于一种人生境界。古人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鼎公的功力,首先来自于他对于世事和人情的大彻大悟。同时,他也曾说过:“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所以他的作品,是一位文學大家的人格与才华的双重见证。仅就这些散文作品文字上所显示出的才华来说,我以为,那种圆熟、老到,那种融会贯通,那种炉火纯青的功力,不仅在台湾,在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恐怕也不多。
二十年前,当董桥先生的作品被介绍到大陆的时候,香港作家柳苏写过文章,大陆作家陈子善更是编书推荐董桥,两人用的题目都是“你一定要读董桥”。于是董桥的作品在国内大红大紫。我觉得,董桥确实值得一读。他的作品小巧而圆通,遣词造句讲究,布局谋篇精致,富于文人雅趣,实属当今少见的美文。但相形之下,鼎公的作品,则以格局和气象见长。喜欢散文的读者,若想领略举重若轻的大家气象和行云流水的大家风范,我想对他们说:“你一定要读王鼎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