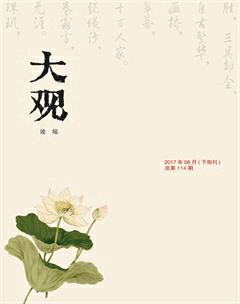温情书写下的人性精神家园
刘晓梅
摘要:作家迟子建以女性特有的敏锐、温情、宽容的胸怀关注并书写着北国的原始风景和淳朴敦厚的民俗风情。她熟悉世间的悲欢离合,坚定地守护着人类善良的秉性,看似朴素的文字下却蕴含着脉脉温情,这种温情来源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理想的憧憬。在小说《白银那》中,作者用全知视角和日记体交互呼应的方式叙事,温情书写的同时用细节来刻画人物形象,加之朴素的生活化语言,使小说呈现了独特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迟子建;白银那;温情主义
小说陈述了在我国北部边远一个叫白银那的小村子,遇到千载难逢的特大鱼汛,渔汛给村民带来了希冀的同时,也带来了邻里间的抵牾、轇轕和灵魂的纷争。 黑龙江中的冰排消逝的第二天便来了鱼汛,白银那这个村庄的人们开始拿出了许久不用的渔具,不辞辛苦夜以继日的捕鱼,这些鱼给他们平淡的生活带去了惊喜。他们在渔汛中取得丰收后却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马占军夫妇私抬盐价,引起了大家的公愤。面对突如其来的渔汛,白银那没能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以至于鱼贩子没能及时来收购。盐价的大肆提高,让大家的心里充满了担忧,因为捕来的鱼既没有鱼贩子来收购又没有盐来腌制很容易就会腐烂,那么他们在渔汛中的辛苦和希望都会付之东流。就在白银那的村民坚决抵制购买高价盐的时候,乡长的妻子卡佳为了不讓鱼腐烂独自一人上山采冰块,途中遭到熊的攻击而丧命,这便将小说的发展推向了高潮,更是由此展开了人性的善与恶、欲望与良知的较量。
一、多种写作视角的交互运用
迟子建的小说地点多发生在她熟悉的东北黑土地上,《白银那》中的白银那就是座落在黑龙江上游的一个小村子,小说的故事情节内容也是由此展开,其叙述的手法也多样化,充实了小说的可读性。这篇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有两种视角,一是全知全能的视角,多角度,全方位的介绍白银那以及发生在那里的事;一是外来访问者古修竹的视角,古修竹以日记的形式用第一人称描述了在白银那短暂居住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两种视角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印证,使小说叙述故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切入,同时以旁观者局外人的身份对这里发生的一切,进行切身的感受与评述,使作品情感得到升华。
全知视角的应用表现在叙述者的视野覆盖着白银那人,如同一架摄像机可以自由进去白银那的家家户户,进去他们的内心世界。采用这样一种俯视的视角来观察着白银那的动态,能很好的记录每天发生的事件,使故事情节更加连贯有序。迟子建在构思这篇小说的时候目光不仅局限于一种叙述视角,全知视角固然可以全方位的叙述,但是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内心世界还是很难表现出来的,所以作者又巧妙的融入了另一种日记体的叙述视角。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能更加全面的勾勒出小说的整体框架。在小说中全知视角和古修竹的日记相得益彰,客观之中夹带着主观,能将白银那这里发生的种种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
除了采用全知视角和日记体的叙述视角,作者还精巧地利用顺叙和插叙的交替互补及时间横面的跨度,有效地控制了作品的节奏。从白银那发生渔汛到马占军夫妇抬高盐价间接使卡佳遇难,这些作者都是采用顺序的手法来写,而对于卡佳为什么来到白银那这段描写则是采用了插叙手法,就好比一条平静向前的小何中突然激起一朵浪花,使从容徐缓的的文风节奏更加具有跳跃感。
二、充满温情主义的书写
迟子建的小说立足民间生活,着眼于富有活力的大自然,一贯散透露着温情的光辉。她曾说温情的气力就是批判的力量。温情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两个方向,一个是乡土社会内部打乱人性温情的因素,另一个是从根本上威胁着乡土社会的外来现代城市文明。前一个因素,迟子建在小说《白银那》中有充分的展示,马占军夫妇想通过暴利谋财的欲望试图挣脱乡土温情的制约,便严重威胁乡土社会的温情世界。马占军夫妇破坏了白银那固有的温情,在人们享受渔汛带来快乐之际故意抬高盐价欲谋取暴利。迟子建笔下的白银那是美丽的,永远带着好客的风俗。一些在多年以前曾经到过白银那的人想要故地重游时都不免对着地图发呆:白银那哪儿去了?这时候熟悉那一带渔民生活的人会爽朗地告诉你:“白银那还在,快去吃那儿的开江鱼吧,那里的牙各答酒美极了!”[1]白银那的人们是善良的,他们的生活仰仗着大自然的恩赐,邻里间相处和睦。
对于马家夫妇迟子建主要着重他们”恶化——善化“的过程,以前马占军夫妇遇到邻里左右出了红白喜事也乐于出钱出物,但是由于马占军得了病,乡亲不愿意借钱才致使他们往”恶“的方向发展。对于马占军夫妇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恶“,作家还是采用充满温情主义的书写去消解和感化人性中的”恶“,正如作者所说:对心酸生活的温情表达却是永远都不会放弃的。
迟子建的小说写作在满怀温情关怀的文字书写中既不躲避现代文明对古典的充斥和人性阴暗面的揭露,又始终坚持积极、强健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白银那这个村庄可以看做是原始风景的一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善良淳朴,但是能引起这个村庄丝丝涟漪的竟是与外界的隔绝。小说中的最大的矛盾就是人们打捞的鱼却无法把它们卖出去,最大的原因就是在于没能向外界传达消息。小说也有写道;虽说白银那通上了电,一些人家还拥有家用电器,一家乡办企业正要从闺中出门,但老人们仍觉得生活正在可怕的倒退。马占军夫妇设计使白银那与外界失去联系,让他们卖不出去鱼从而故意抬高盐价,间接性的致使乡长的妻子卡佳丧命。乡长由最初对马占军夫妇的恨转变为释怀的谅解,这里面正是融入了作者的温情主义书写。这种温情主义的书写可以在《畅饮“天河之水“——迟子建访谈录(代序)》中可以得以印证:如果说我没有感受到生活中的“恶”,那绝对不是事实,我也曾在一篇随笔中写道:”我从来没见过狰狞的鬼,却遇见狰狞的人”,可我更信奉温情的力量同时也就是批判的力量,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我特别喜欢让“恶人“心灵发现”,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底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2]
三、细节塑造人物
白银那是侧卧在黑龙江畔的偏僻、深远、落后、美丽的小镇,黑龙江养育着一代又代辛勤、仁慈、淳厚、朴实的乡民,这个在地图上没有立足之地的小镇,却有很大的魅力,冰排、鱼汛、牙各答酒、独特的生活方式。然而,悠悠的江水、茂密的深山、神奇自然,并没有给立足在那里的农民带来福音,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他们仍然贫穷落后,和外界很少联系的他们独自承担生活的艰难、不幸、屈辱。在小说的叙述中,马占军、马川立、王德贵、卡佳、陈林月都是个性鲜明的人物,马占军的固执、“残忍”、精明;马川立的善良、执着、可爱;王德贵的大度、温和、负责;卡佳的风情、温柔、真诚;陈林月的纯真、无邪、大方等,这些人物无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者很是注重剪裁取舍和谋篇布局,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高质量的,从而保证了人物的生动、情节的缜密或意绪的流贯与意境的浑成。就拿作者写马川立和陈林月在黑夜中约会的甜蜜就充分利用了细节描写,马川立因为把河水里的冰排比作冰棺材而被陈林月搡了一把,他趔趄着一脚伸进冰冷的水里,被凉气逼人的江水激得打了一个冷战,就势抱住陈林月让她赔他身上的热气。当然那热气很快就在拥抱中回到他身上。这段逼真的细节描写充分将两人爱情中的甜蜜表现出来,同时也勾勒出了马川立的可爱之处。
在塑造人物时,事件是最直接、最直观体现人物性格的要素,作者在描叙这些事件很是细致,细节之中就将人物生动的塑造出来。对于卡佳的丧礼准备,乡长的一系列表现都充分的体现了他对妻子的留恋和不舍。乡长坚持要为卡佳打造一口新的棺材,因为她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这些乡长都记得并为她坚守着,这件细微之处就将二人间爱情的矢志不渝表现出来。
四、朴素的生活化语言
迟子建认为小说最终的好是朴素——语言、意境、用词、生活态度,乃至人格,朴素是最高境界,朴素还是生活化的反映。《白银那》的语言风格淳朴大方,精练流畅,语气轻缓,饱含诗意美。发生在白银那一桩桩难以忘却的苦难记事,没有对与错正与邪善与恶的二元对立,在作者诗意的笔触、语调中更多的是悲悯与同情,是对生命、人生的真诚的感受、体悟。作品寓苦难失意于诗情画意中,在充分享受作者细腻、朴素、自然、诗意的描写的同时,让人心情逐渐的沉重起来,最终又脱离文本,引起对生命的思考。白银那村庄里的那些人,那些事,在作者朴素的语言表述中是如此的凄迷,如此的萦绕心怀,如此充满魅力,如此的挥之不去。
小说生活化的语言中蕴含着强大的温情力量,在乡长的儿子准备给母亲卡佳报仇时反问父亲难道不恨马家,乡长一句朴素的话语:我这辈子最不喜欢听“恨”这个字……虽然简短的几字却将所有的仇恨化解,这句话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但从乡长口中说出来,使人物形象笼罩着人性的温情之光,在繁琐、庸常的生活中安慰人心,给人带去希冀。
五、人文关怀的流露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创作精神不断变化着,小说创作逐渐的从一种“共同的话语”空间中剥离出来,向普通化、世俗化、商业化靠拢时,迟子健仍然坚守着作家的艺术良知,不媚俗、不惑众,在创作中始终保持着高品位的审美追求,不忘初心的追求着自己灵魂精神的归宿。在迟子建的作品中,有着对乡村世界中人与人相互眷注的深入窥探。在中篇小说《白银那》中,迟子建以直接的生活事件、艺术形象和环境描写,通过人性和物欲的激烈冲突,抒发了对理想化的人际关系,对良善、饶恕、和谐向往的祈望。
在这篇近乎寓言的故事内容,既有对乡民寝露品德的剖析,更有含有遲子建温和的宽宥和悲悯,从而高高举起了人文关怀的旌旗。迟子建曾这样解释她对乡民生活的认识:“中国老百姓大多数都是处在这么一种尴尬状态中:既不是大恶也不是大善,他们都是有缺点的好人,生活得有喜有忧,他们没有权也没有势,彻底没有资本,他不能做一个完全的善人或恶人,只能用小聪明小心眼小把戏,以不正当手段为自己谋取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他会左右为难备受良心折磨,处在非常尴尬的状态中。[3]迟子建对人性有着很高的期望,她”要把一个沾满陋习的人身上那仅有的人性美发掘出来,以求溶化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人与人之间应该多一些眷注和体解,少一些狐疑和痛恨,这样才能让生活中多点幸福感与和谐美,才能实现在互相尊重个性和精神个性的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包容、将心比心和认可。
六、结语
小说的开头作者就交代白银那村庄坐落在黑龙江的上游,这里的白银那表征着传统与现代碰撞中的人性美的回归,河流的出现使得迟子建小说中的白银那具有了亘古不变的沧桑感,它承载着对漂浮魂灵的安慰和塑造精神家园的重担。在主题内涵上,作品中处处弥漫着真、善、美的情怀和温润的忧愁,展示了作家对自然的属意、对生命的感悟和对爱的追随。全知视角和日记体的相得益彰使小说的叙事更加富有张力,满含人文关怀的温情书写,朴素生活化的语言和各色各样的人物形象在《白银那》中得以充分体现,这些无疑是作家卓越的创作特色的展现。
在当代文坛中,迟子建的创作风格是极具特色的,通过小说展现出的那朴实而原始的北国风采、那苍凉而温情的叙述风格,我们能切身地体会到来自作家灵魂深处的伤怀之美,给小说抹上一层温情而忧伤的背景色,具体体现为有灵性的自然、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及对死亡平淡的叙述,这些都试迟子建的小说创作更加具有深度和可读性。
【参考文献】
[1]迟子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6.
[2]迟子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53.
[3]迟子建,阿成,张英.温情的力量——迟子建访谈录[J].作家,1999,(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