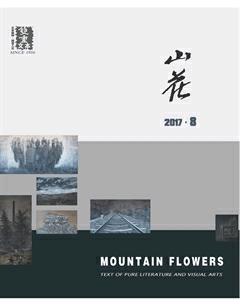“阳光明媚时这里令人忧郁”
行超
在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笼罩之下,整个大不列颠岛向来都是阴晴不定、雾雨绵绵。爱尔兰著名的小红莓乐队(The Cranberries)有首歌叫做Dying in the Sun,对于生活在这两个相邻岛屿上的人们来说,“在阳光下死去”也许是他们所能想象的最美好的死法了。细细想来,《呼啸山庄》《简·爱》《德伯家的苔丝》……多少英国文学作品中,男女主角的爱情故事都是以一声惊雷抑或是一阵疾风骤雨为背景的。或许只有这样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才能塑造出如此多面的作家与作品:晴时是简·奥斯汀的活泼与浪漫,阴时是勃朗特姐妹的低沉与忧郁,风雨交加之时,则是所有爱恨情欲一触即发的那个瞬间。
一
约克人称他们“和上帝住在同一个地方”,这话其实并非完全是笑谈。拜大自然所赐,面积不足六千平方英里的约克郡(Yorkshire),却时常给人一种国家般的辽阔感。今天的约克郡分为南约克郡、西约克郡、北约克郡和东约克郡四个行政区。北约克郡面积最大,首府约克(York)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北英格兰的首府,因而拥有举世瞩目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置身今天的约克,在现代化的建筑和设施中,举目可见中世纪的街道、13世纪的城墙和大不列颠岛上最大的中世纪大教堂,古老与现代、历史与当下就这样令人着迷地不时碰撞着。
在约克安静而潮湿的清晨早早醒来,不由得庆幸时差作祟,让自己不到六点便出门闲晃。初秋的凉风中,这座还未苏醒的城市显得无比安宁,沿着通向市中心广场的主干道一路走去,两边是高低错落、形色各异的小屋,有的年代久远,墙壁已经有些斑驳,却因为爬满了青苔和藤蔓而陡增生机,更多的是砖红色的乔治亚风格建筑,每道门廊后面仿佛都深藏着一个故事。几乎每家都有私人花圃,种满了各色植物,玫瑰、蔷薇、雏菊或海棠,开得饱满繁盛却没有争奇斗艳的俗气,四下无人中,反而流露出一种温柔的坚毅。城市仿佛一个巨大的带有体温的臂弯,怀里揽着尚在安睡中的人们。路上偶尔看到一两个沿途晨跑的人,彼此笑笑,算是新一天的第一声问候。
一片雾色中,太阳缓缓升起,城市的色调从清冷寂寥逐渐变得温暖起来。路边便是树林,影影绰绰之间,晨曦微微透出光芒,眼前的画面被切割成三个层次:抬眼处是正在升起的朝阳,穿过厚重的云彩,与湛蓝的天空彼此交融;身前是一片氤氲的雾气,从地面一点点升腾起来,似有一汪湖水在密林深处;四周则是横无际涯的、包容万象的绿,它可以与所有颜色在一起,有时是背景,有时是主角,永远和谐而安适。在色彩的怀抱中,我不由得拨开树林,踏着青草与露水,循着光亮向远方探去,走近才发现,远处缥缈着的雾气并非来自湖水,而是赛马场的草地上升腾起来的晨雾。温暖的晨光下是一望无际的绿草如茵,太阳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势,四周的世界越来越明亮,每一秒钟都是新的颜色、新的风景——万籁俱静中,新的一天正在来临。此刻的我,仿佛置身于《霍比特人》中那个生活着各种奇妙生灵的山丘之间,随时随地都充满了神奇。脑海中盘旋了许多年的文字世界,就这样与脚下这片土地完整地重合——所谓的身心贯通,大抵就是这样吧。
下午的约克却是完全不同的样子。英国有民谣说:“钟敲四下,一切为下午茶停止”。英国人对于下午茶的执着举世闻名,而在下午茶刚刚开始兴盛的维多利亚时期,约克因为其自身特有的文化背景和赛马活动,一度成为英国贵族的社交和时尚活动的中心。因此,在约克的下午找一个街角的位置,享受一段美好的下午茶时光,几乎成了每个游客的梦想。穿过约克大学、火车站和约克大教堂,不远处就是著名的Bettys Tea Room。坐落在市中心的这家老店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它并不现代,更不奢华,而是始终保持着最传统的样子。迎面走来的那个服务生酷似《唐顿庄园》中的女佣安娜,一丝不苟的盘发、略带羞涩的目光、迷人的英式英语,精致优雅和复古怀旧随着她的脚步扑面而来。一杯伯爵茶,一套完整的三层茶点,看着窗外淅淅瀝沥的小雨,脑中不时闪出简·奥斯汀小说中那些琐碎的下午茶时光。
曾经有那么几年,我是拒绝再读简·奥斯汀的,这拒绝中有轻视、不屑,甚至还有一点愤恨的味道。不屑的是,奥斯汀的小说永远那么一地鸡毛,谁家的小姐看上某处的阔少啦,多事的母亲和恨嫁的女儿啦,以及没完没了的餐桌、舞厅,再特别的少女,如果不能嫁给一个富有的绅士,那她一定是不幸的——这显然与我们所追求的现代都市独立女性的生活背道而驰。愤恨的是,如同所有青春期的懵懂少女一样,我亦想象过一个属于自己的达西先生和布兰登上校,永远义无反顾地在远方守护着自己。然而现实生活哪有那样圆满,奥斯汀笔下的男女主人公放在今天,几乎就是玛丽苏与杰克苏的典型,而现实,永恒的、坚硬的、日复一日的现实,让我们对这样的人设、对这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越来越心怀警惕。
我们无法确知,奥斯汀的一生是否真的始终孑然一身,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一生都在书写爱情的作家,一定是用自己毕生的梦想去憧憬着爱情,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一次次地回望着自己年轻时代那段刻骨铭心却不了了之的爱情。奥斯汀的小说中,主人公的爱情故事都是在步入婚姻的前一刻戛然而止,因此,她的作品所提供的始终是一个关于完美爱情的幻想。这幻想中虽然也有误解与背叛,但其中的轰轰烈烈、一往无前却对渴望爱情的人们有着无限诱惑。因而,虽然奥斯汀笔下都是平凡男女的爱情故事和生活琐事,但她的作品在风格与倾向上却始终充斥着一种迷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几乎是同一时代的,同样终生未嫁却写出了惊心动魄的爱情的艾米莉·勃朗特,她笔下的文学世界却是完全迥异的另一番样貌。我至今记得第一次打开《呼啸山庄》时的那种震颤:“这儿可真是一个美丽的乡间!在整个英格兰境内,我不相信我竟能找到这样一个能与尘世的喧嚣完全隔绝的地方,一个厌世者的理想的天堂”——艾米莉·勃朗特写作《呼啸山庄》的时候,与简·奥斯汀创作的高峰期不过相差三四十年,但两者在精神风貌和审美取向上却大相径庭。奥斯汀拉拉杂杂、絮絮叨叨,却始终透着一股举重若轻的、乐观而调皮的机灵劲儿,而艾米莉的小说却充满了压抑和深沉,更似阴云密布、狂风暴雨。
很难说清楚,上帝对于勃朗特家族究竟是垂爱还是不公。勃朗特姐妹生活在西约克郡一个叫做霍沃斯(Haworth)的小村子,如今这里以勃朗特一家而闻名,然而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这里几乎人迹罕至。幼年丧母的勃朗特姐妹一直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在宽松而封闭的家中阅读、学习、写作。1847年,勃朗特三姐妹奇迹般地同时发表了自己的作品《简爱》、《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然而在接下来的一年中,艾米莉和安妮相继辞世。不久之后,已怀有身孕的夏洛蒂同样英年早逝。在短短几年时间内,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家族为英国文学留下了不朽的精神遗产,然而对于身在其中的家人来说,留给他们的也许只是难以为外人道的伤痛与绝望。
现在的霍沃斯遍布着勃朗特姐妹的足迹:小镇的最高处是勃朗特家族博物馆,也就是勃朗特家族的故居。故居外紧邻的教堂,是勃朗特姐妹的父亲担任牧师的地方,夏洛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是葬在这个教堂里。教堂外几步路就是当地最古老的黑牛酒吧(BLACK BULL),沿着石墙夹道的绿茵小路再走不远,可以看到一所废弃在山顶的房屋,那就是呼啸山庄的原型。用最耐心而细致的步伐走过这些地点,也不过是一两个钟头的时间——而这,竟然就是勃朗特姐妹生活的全部内容。霍沃斯的山水和荒原上呼啸的疾风培养了三姐妹坚毅的个性,让她们的骨子里有一种刚硬。走在霍沃斯的小路上,我的耳旁时常回想着安妮·勃朗特在《艾格尼斯·格雷》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那句话,“他们可以把我碾碎,但不能使我屈服”。
伍尔夫的读书笔记中,在评价夏洛蒂·勃朗特时曾将她与哈代视为拥有“个性的力量”和“狭窄的眼界”的那类作家,“凡是以自我为中心、受自我所限制的作家都有一种为那些气量宽宏、胸怀阔达的作家所不具备的力量。他们所感受到的印象都是在他们那狭窄的四堵墙里稠密地累积起来,并牢牢地打上了戳记的。他们的心灵所产生的一切无不带着他们自己的特征。他们很少从别的作家那里学习什么,即使采取一点儿什么,也消化不了”。的确,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有一种简单而直接的力量,她們作品的力量更多地来自于那种充满抒情色彩的诗意和敏锐,而非其思想洞见的深刻性、独特性。挣扎、自闭、多思充斥在她们的生命中,于是便溢满了她们笔下的故事。
二
沿着约克一路向北,经过以酒吧文化和足球流氓而著称的纽卡斯尔,便到达了苏格兰境内。首府爱丁堡依山而建,到处都是起伏的道路、厚重的岩石和高耸入云的建筑。巨石般的坚硬与温暖的人文情怀、暗黑奇崛与阳光普照,在这里以惊人的和谐共处着。威廉·华兹华斯在苏格兰游历时曾说的“阳光明媚时这里令人忧郁”,恰好可以概括这个充满了矛盾却永葆生机的地方:有明亮又有黑暗,有欢欣又有压抑,有奇幻又有沉重。
老城以建立于14世纪的爱丁堡城堡为中心,它居高临下地盘踞在一个黑色的死火山之上,一眼望去,有一种雄伟强悍而不容置喙的压迫感。城堡正对的是爱丁堡最重要的商业街:王子大街,街道将城市分为新旧两城,南面为旧城,北面为新城。新城建立于18世纪,错落有致的乔治风格建筑与老城形成鲜明对比。王子大街的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商店,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从早到晚在这里穿梭,穿着苏格兰裙、吹着风笛的街头艺术家们是这条路上最引人注目的风景。悠扬的风笛声在爱丁堡老城高高低低的街头回响着,或欢愉轻快,或悲壮嘹亮,无一不在努力诉说着属于这个城市的过往和故事。
王子街的尽头是著名的王子街公园,里面屹立着苏格兰人的骄傲——欧洲“历史小说之父”瓦尔特·司各特的纪念碑。走在老城的任何一个角落,几乎都可以看到这座巨大的,造型奇特、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建筑。1836年,在司各特去世仅仅四年之后,爱丁堡便建起了这座如今已成为地标的建筑。一百五十多级台阶本身就是一次旅途,苏格兰人把对文学的热情都放在这里了。高处的塔楼又分三层,第一层有一个彩色玻璃纪念馆,记述了司各特的生平和故事。大理石制成的司各特雕塑,一百八十多年来,就这样淡泊而骄傲地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也见证着苏格兰人对于文化的热爱与敬重。
司各特家族是苏格兰、英格兰边界地区(Scottish Borders)的望族,瓦尔特·司各特在仅仅十八个月时便患上了小儿麻痹,从此终身残疾。虽然身体不便,但他却游历过苏格兰各地,在他晚年生活的阿博茨福德庄园内,收藏着七千余册、十七种语言的民间传说、历史、旅行、巫术等书籍。司各特一度是19世纪收入最高的英国作家,所有与他交往的人都称他随和、好客、善于交际;而当他因受金融危机的波及而债台高筑时,他拒绝了所有朋友的帮助,坚持独立还清债务,最终在夜以继日的写作中告别了人世。
司各特并不是生而具有巨大才情的作家,站在今天的角度评价司各特的小说,多少有点“理念先行”的味道——他的小说往往以某个具体的政治斗争或社会变革为背景,在塑造典型人物的同时揭露问题、针砭时弊,表达自己的政见。这样的写作其实并未完全摆脱中世纪欧洲传奇小说的俗套,缺乏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关怀,多少显得有些陈腐和苍白。在《人间喜剧》的序言中,巴尔扎克曾这样评价司各特小说中的人物:“他们差不多总是必须作为反映时代的一个伟大形象才活得下去。这些人物是他们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全部人类感情都在他们的皮囊底下颤动着,正面往往掩藏着一套完整的哲学。”
但不得不承认,司各特的勤勉、博学强记和人格力量支撑起了他的作品。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曾说过,“一个为留下好名声而勤奋做事的人,毫无疑问可以称之为绅士”。司各特毕生都在追求“宝贵的信用”和“战胜生活的勇气”,苏格兰高地的冷风和多姿多彩的文化塑造了这个英雄般的、不断向命运发起挑战的文学巨匠。从这个角度看,司各特无疑是大不列颠民族所推崇的“绅士精神”的代表。
20世纪以来,受到资本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冲击,传统的“绅士精神”渐渐由具体而微的行为准则转化成了一种深层的精神信仰。那日驱车在爱丁堡新城,一个喧闹的十字路口前,一位苏格兰老人正要穿行,却被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阻挡了去路。车内的我们赶紧刹车放行,老人随即一面摘下帽子,对车内微微颔首,一面加快了脚步,迅速穿过马路。阳光下这个画面无限美好,一位穿着三件套西装的老者,一顶哈里斯花呢的帽子,一个标准的绅士动作,仿佛裹挟着传统与高贵从遥远的19世纪穿越而来,然而又确乎发生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当下,几百年过去了,周围的一切都变了,但似乎又什么都没有变。
但愛丁堡绝不是一个沉迷于传统和旧日辉煌的老派贵族。世界上所有最前卫、最潮流的文化,都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里生根发芽、野蛮生长。历史悠久和贵族气息只是多元而复杂的英国的一角,它也有狂热粗鄙的足球流氓,也有激进亢奋的摇滚青年,同所有大众文化盛行的地方一样,它茅茨不翦、泥沙俱下。这也是英国之所以成为英国的原因——它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宽容度,所有人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同类,所有你所热爱的生活细节都在这里,时不时以某种不经意的方式出现,在措手不及间触动你的灵魂。
也许正是这样的宽容,让这个城市和这个民族长久地享受着做梦的权利。20多年前,在充满了奇迹与神迹的爱丁堡,刚刚从一场失败的婚姻中逃脱出来的单身母亲J.K.罗琳辗转于几家咖啡馆之间,用一部老旧的打字机,一字字敲下了《哈利·波特》的整个故事。罗琳出生在距爱丁堡老城很近的古老村子Merchiston,这是个盛产巫师的地方。巫术文化在欧洲尤其是在苏格兰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罗琳的写作当然根植于这样的文化。一个在此时此地的困窘中艰难度日的单身母亲,选择了用写作让自己“飞”一次,她动用自己的才华、想象以及骨子里的神秘主义因子,在自己亲手创造的另一个世界中幻想另一种生活,就此创造了一个凤凰涅槃与“麻瓜”逆袭的奇迹。
而罗琳的幻想并不仅仅是天马行空,更不是简单的穿越或者玄幻,它有太多扎实的细节、联动的线索、复杂的背景知识,因此成为了一个逻辑自洽、内容饱满丰盛的想象世界。英国文化极大地滋养了罗琳笔下的故事,霍格沃兹的学院制源自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教育模式,魁地奇由英式足球发展变形而来,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坐落在伦敦开往爱丁堡的国王十字车站中……罗琳笔下的幻想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关联性,甚至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真实的可能性,因而对于时刻渴望改变又生活在现实的泥淖中的读者来说更具有诱惑力。
伏尔泰《哲学辞典》里曾有这样一段哀叹:“今天再也没有中魔的人,没有魔法师,没有星相师,没有精灵,这真令人遗憾。一百年以前从哪儿来那么多神秘,实在难以想象。那时候贵族们还生活在城堡里,冬天长夜漫漫,若是没有这些高贵的娱乐,人们会无聊至死。任何一座城堡在某一天总会出现一位仙子,每座村庄都有它的男巫或女巫,每位亲王都有他的星相师,每位夫人都有人给她算命,中魔的人在田野狂奔,人人都争着说自己看过鬼,或者以后会看到鬼。”在知识、理性、科学和现代法律等观念统摄下的今天,人们对于神秘主义的迷恋或许正是基于一种现实生活的精神补偿。拜《哈利波特》所赐,托尔金、C.S.刘易斯等魔幻文学的老前辈们近年来被屡屡拿出来反刍,大洋的另一边,丹·布朗已成为美国畅销书的代表,方兴未艾的中国网络文学更是充斥着玄幻、穿越……似乎全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对幻想的迷恋,在这样的氛围之中,未来文学的样子或未可期。
三
从爱丁堡出发,向西南方向行驶大约三个小时,当四周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明亮饱和,两边的植物越来越葱茏、道路越来越蜿蜒曲折,车子被环抱在一片碧水之中时,便到达了英国最有名的度假胜地——湖区(The Lake District)。
湖区之美不仅在于这里波光粼粼的湖水和层峦叠嶂的山谷,更在于它的多元性与戏剧性。在英国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湖区还有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塑造了以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为代表的湖畔派诗人。将近两百年前,威廉·华兹华斯与他的妹妹多萝西·华兹华斯、妻子玛丽·郝金生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就生活在格拉斯米尔(Grasmere)郊外的一座小农庄中。
这个名为鸽屋(Dove Cottage)的小农庄自1890年起被辟为华兹华斯故居,马路对面是狭小而精致的华兹华斯纪念馆。鸽屋的外表非常平凡,略显斑驳的灰顶白墙上零星地爬着各种形态的藤蔓,外面是一道石砌的围墙,覆满了青苔。一位双颊泛着可爱的小雀斑的英国姑娘是我们的志愿讲解员,当她问起有多少人知道这间房屋的主人时,只有两三位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举手。内心当然不免失落,在我心目中,这个英国文学史上的“桂冠诗人”理应是世人皆知的。然而事实却是,这座平凡的小屋与湖区其他的景点并无二致,大抵只是游人由此经过,顺路游览的一个地方。转念想想,与广阔的生活相比,文学的确是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落。文学从来都是寂寞的行当,华兹华斯一开始便深谙这一点,他看遍了革命的激情,也学习了现代知识,却最终选择回到故乡、远离尘嚣,守住内心的宁静,执着于深耕自己文学的疆土。
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一起俯身走进小屋,屋里只有很小的两三个窗户,在常年雾蒙蒙、阴沉沉的英国,恼人的昏暗和阴冷可想而知。不到十人的观光团队已将这座房子挤得水泄不通,屋内零星陈列着的也只是一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即使是在两百多年前,对于一个已经享有盛誉的诗人来说,这样的质朴和清简也是令人吃惊的。唯有一些简单的写作工具和华兹华斯生前的手稿,让屋子多少显得热闹丰满些。二楼有一间很小的阅读室,屋顶和四周的墙壁上密密麻麻地贴满了泛黄的报纸,就是在这间逼仄的小屋里,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骚塞等人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了联系,他们在这里讨论文学艺术问题,有时争论,更多的应该是志同道合者的惺惺相惜。
后院是一座半开放式的花园,如今这里种满了玫瑰、蔷薇,与一个普通的英格兰家庭并无二致。不过在华兹华斯兄妹生活的时代,这里不仅是观赏的花园,也是他们收获食物的苗圃。根据多萝西日记的记载,在斜坡上,他们种了蕨类、块茎植物和在散步过程中采集的或者当地人送给他们的野花。他们修葺了台阶,种了些能够食用的蔬菜,沿着围墙种了金银花和玫瑰。多萝西终生未婚,始终陪伴在哥哥的身旁,不仅照顾威廉的饮食起居,更与他一起漫游,相互倾诉。无数次,兄妹俩就从小屋后面的碎石小路出发,走进广阔的旷野和湖畔。多萝西的日记事无巨细地记载了他们沿途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和事,她的文字饱含着赤子般的敏锐、好奇和爱,很多时候,威廉诗歌写作的灵感正是从妹妹的日记中得来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华兹华斯的艺术主张和诗歌语言也是一样的洗尽铅华,平白自然。在鸽屋生活的十年(1799-1808),也是华兹华斯个人创作的高产期和高峰期。正是在这里,在与同道者柯勒律治、骚塞的不断切磋中,湖畔派诗人最终形成了共同的文学主张。1800年版的《抒情歌谣集》中,华兹华斯所作的序言被后世当“浪漫主义的宣言”,在这篇长文中,他开宗明义地表达了自己的写作主张:“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我们的各种基本情感共同存在于一种更单纯的状态之下,因此能让我们更确切地对它们加以思考,更有力地把它们表达出来;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丽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在英国文学史上,华兹华斯的文学成就和贡献必然是属于湖区的,这里有他生命的根和底色,有他思想和审美变化的足迹,这里的一草一木给予了他强大的内心力量和情感寄托。湖区,或者说是大自然成就了华兹华斯,成就了湖畔派,然而与此同时,正是这些在大自然中成长的文学家、艺术家们发现并进一步赋予了大自然另一层的深意,让这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更具有人文主义色彩。
離开鸽屋,几公里外便是英格兰最大的内陆湖——温德米尔(Windermere)——也是整个湖区最热闹繁华的地方。白天,熙熙攘攘的游客挤满了码头附近的商店、餐馆、咖啡屋,大大小小的船只在湖面来往穿行。在一片现代化的喧嚣中,人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湖区的自然之美,碧水、青山、蓝天是那样的浩大无边,容不得别的什么去喧宾夺主。在大自然丰饶而深邃的身体中,所有的人与物都不过是点缀,然而缺了这点缀却也不行——我们正是这幅画本身,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是大自然的注脚。还有什么比生活在画中更令人向往的呢?
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与码头一街之隔的山丘上,最幸福的莫过于在房间里静静地看太阳一点点沉下山来,看湖水的颜色逐渐晦暗下来,看人潮散尽,一切回归平静。从铺满绿草的山坡上拾级而下,走到湖畔的长椅上安静地坐一会,想着不久之前,这里还是避之不及的人声鼎沸,此刻却显得那样空旷孤独。码头零星的灯光下有几只微微晃动的船舶,岸边的水鸟不时发出几声低鸣,时有时无的自然之声反而将这夜色衬托得更加安静。生活在都市中的人啊,多么希望这一刻久一些,再久一些——就让这墨蓝色的天空和波光粼粼的水面覆盖着、吞噬着,忘记一切,专注而投入地贪恋这一时安宁。
温德米尔湖旁边便是小镇鲍内斯(Bowness),密密麻麻的商铺之中,深藏着一座童心的世界——“碧雅翠丝·波特的世界”(World of Beatrix Potter)。碧雅翠丝·波特是著名的“彼得兔”的创造者,她1866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孩提时期,父母几乎每年夏天都会带她来湖区度假,这里的青山绿水成为日后她创作的重要灵感。在“彼得兔”系列故事出版并备受瞩目之后,因为未婚夫的突然辞世,波特女士选择了远离城市,定居乡间。如今,在温德米尔湖不远处的一个小山丘上,依然伫立着波特女士生前居住的小农庄。
与在湖区土生土长的华兹华斯不同,碧雅翠丝·波特是地地道道的外来者。如果说大自然的精神力量已经内化于华兹华斯的生命当中,那么波特则更像是一个经历了现代化的纷扰而最终回到自然怀抱的皈依者。该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让一个正在上升期的女作家放弃了伦敦的一切,来到这个人烟稀少、安静得让人寂寞的地方,将自己的余生全然奉献给了动物、植物和泥土?
还是在彼得兔的世界里,波特给了我们答案。湖区的风光和这里的生活从童年时代开始就在波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小兔彼得、松鼠纳特金、小兔本杰明、小猪鲁宾逊等等,都是波特在大自然中发现的生灵,更是她一生最好的朋友。波特的创作是一种天性的流露,对于大自然的感情灌注在她的作品中,万物有灵与众生平等是她骨子里的信仰,也是她创作的所有底色。一个多世纪以来,彼得兔和它的朋友们陪伴着世界各地一代代孩子们的成长,它们不仅让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看到了大自然的美和生趣,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拟人化的小动物身上,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成长中的自己。
在今天,高傲的英国人无不以这位女士为荣,不仅在于她曾创造出一个举世闻名的卡通形象,更是感谢她为湖区和英国自然保护作出的贡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工业化的触角伸向湖区时,波特将自己几乎所有的收入都用于购置湖区的农场和地产。1930年起,她停止了创作,全心投入到保护英国乡村生态的事业中去。1943年,波特女士在辞世前,曾把自己名下湖区的四千英亩土地、十五座农场以及若干小湖都捐给了国家信托组织(National Trust),并且在遗嘱中说,“希望森林不被砍伐,农夫可以按照原有的习惯生活和劳作,湖区能鲜活地保存下来”。正是因为这样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波特才写出了最纯粹美好的童话。从城市到乡野,波特女士对于英国和整个人类的贡献不仅在笔下、在纸上,更在于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于她对于大自然和一切原初起点的坚守。而在盛名之下从容地转过身去,对自己内心的一方小小天地温柔以待,也许正是大自然给予波特的人生启示。
在伦敦市中心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内,有一个朴素但却引人驻足的角落。这里安葬着莎士比亚、狄更斯、乔叟、弥尔顿、哈代、华兹华斯、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等120多位英国文学史上的荣耀作家,这一隅被称作诗人之角(PoetsCorner)。与教堂内那些已故王室们的奢华与堂皇不同,这里更像一座座安静的纪念碑,记载着几个世纪以来英国文学的变迁,更记载着大不列颠民族的文化传承与精神遗产。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王室的专属教堂,然而英国人却将其最中心的位置留给了这些文学家,也留给了达尔文、牛顿等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贡献的人。一个极度看重阶级、出身和血统的国家,对于知识和文化却始终葆有如此的尊重和敬意,他们当是确知,曾经的“日不落”王国当然有着令人艳羡的历史和文化,它是所有英国人的母亲,滋养了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塑造了所有这些名垂史册的作家。但同时,如果没有作家们的创作,没有他们对于人和世界的思考,大英帝国不会呈现出现在的样子,也不会如今天这样厚重,这样让人倾心。
夕阳下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岿然不动,一片静穆之中,死亡也变得不再那样令人生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