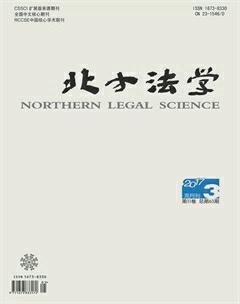共同饮酒法律责任实证研究
胡岩
摘要:通过对我国涉及共同饮酒的142个侵权案件的判决理由进行类型化分析发现,根据法院判决对注意义务的认定,可以区分为“危险防范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法定附随义务”、“一般注意义务”等。通过在法理上对这些注意义务的来源进行辨析,其均存在一定问题。在与此相关的侵权案件审理中,法官通过扩大注意义务范围对社会交往规则进行调整,以司法政策为导向的过错认定有一定弊端,应当在侵权案件审理中坚持司法克制。
关键词:共同饮酒 侵权 注意义务 救助义务
中图分类号:DF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7)03-0046-11
一、导论
作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过错的认定是侵权案件审理的核心问题,而认定过错有赖于行为人注意义务的确定,但这个问题一直是我国侵权案件审判的短板之一。以共同饮酒案例为例,共同饮酒者对醉酒者有无救助义务?各地法院给出了不同的判决结果、不同的判决理由。面对“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我们需要首先探讨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存在侵权法上的救助义务;如果没有,法官能否在司法政策的引导下确定救助义务的范围。
本文共有三个部分,首先通过对国内共同饮酒责任案件判决的分析,山以共同饮酒者的救助义务为切入点,逐一解析判决中法官对共同饮酒者的义务认定的诸多问题。其次在此基础上探讨侵权法上救助义务规则,此类案例困难在于,我国并无一般的救助义务规则,而从比较法的角度论,救助义务规则也处于发展中,并无统一认识。最后探讨欠缺相应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能否在司法政策的引导下通过解释“过错”来扩张注意义务的范围,建立救助义务规则,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设置法律规则。
二、共同饮酒者的法律义务来源评析
自2001年首度出现要求“共同饮酒者”对因醉酒死亡的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以来,这类案件已蔚为大观。基本相同的案情,但各地法院做出了不同判决。笔者搜集了142个相关案例的判决,其中一审判决87例,二审判决52例,再审判决3例。判决结果有三种:驳回原告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按照公平原则承担补偿责任、认定被告有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其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11例,占案件总数的7.8%;判决承认被告无过错,但要求被告按照公平原则承担补偿责任的有34例,占案件总数的23.9%;更多判决认为共同饮酒者在酒后负有注意义务,应承担赔偿責任,此类判决有97例,占案件总数的68.3%,而判决理由各异,彻底的“同案不同判”。
在认定共同饮酒者应承担责任的判决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探讨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的来源,各地法院给出完全不同的判决理由,总结如下:
(一)共同饮酒者对共同危险行为的防范义务
关于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的来源,获得最多支持的观点认为饮酒本身是一种危险性活动,共同饮酒开启了这个活动的危险,因此共同饮酒者应对共同危险行为承担防范的义务。如有判决指出:“共同饮酒是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各共同饮酒人之间并不必然产生法律上的权力义务关系,但当共同饮酒行为可能使他人发生特定的危险时,其他共同饮酒人则产生相互提醒、照顾的义务。”更有判决将共同饮酒行为作为开启危险源的先行行为,由此要求被告承担相应的注意义务。如“公民的生命权受法律保护。宴请与接受宴请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宴请中举杯敬酒是社交活动的常识,是人们之间合法的、正常的交往活动之一,但是请客者及同饮者与受害人一同饮酒,应当相互节制并互相照顾。开启或维持危险之人,必须以一个合理人应有的注意去防范危险可能带给他人的损害”。有判决更做出详尽的分析认为:“共同饮酒人承担注意责任的前提是共同饮酒行为,且这种行为已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处于危险状态,如醉酒、饮酒人神志不清等危险状态。如果仅是少量饮酒,酒后行为正常却引起其他意外事件发生,如心脏病突发难以预见等情况,则共同饮酒行为只是一个诱因,不能造成注意义务责任的产生。共同饮酒人承担注意义务的判定标准应为通常情况下普通人能够预见到损害结果发生的注意。普通人能够预见的醉酒易引发的损害承担责任,如酒精中毒造成身体的伤害、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的损害、酒后从事高度危险作业造成的损害等。对普通人通常情况下不能预见的损害后果不负侵权的责任,如共同喝酒的其他人酒后犯罪、殴打他人,饮用假酒造成身体伤害,酒后自毁财物等等,则共同饮酒人不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义务的内容,有判决认为:“两被告是否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取决于其在饮酒阶段有无劝酒和强迫饮酒的行为以及在酒后送人阶段是否尽到救护、救助醉酒者的义务(共同饮酒这一先行行为产生的注意义务)。”还有“一起饮酒者因共同实施了喝酒这个在先的行为,就会产生一种在后的对醉酒者的注意、照顾、救护等保护义务即法律规定的先行行为引起的法定救助保护义务”,并认为这一义务属于“道德上安全保护的善良义务,也是法定的义务”。
必须指出的是:风险的存在并非是注意义务的来源。如果我们承认:饮酒行为本身属于制造危险的行为,那制造这一危险并能够有效控制这一危险的是饮酒者本人,而非参与的共同饮酒者。如果饮酒者自愿饮酒且无强制劝酒的行为,则饮酒者的行为属于“自甘风险”的行为。自罗马法以降,自甘风险属于被告的抗辩事由,被告无需对原告自甘风险的行为承担赔偿责任。罗马法格言“对自愿者不构成伤害(Volenti non fit injuria)”,如果一个人自愿从事危险性的工作,那他不应由这个危险所产生的损害请求赔偿。在近代民法中确定自甘风险原则的“Priestley v.Fowler”案,赫舍尔法官就明确指出:“某种行为是在一个人邀请或同意下发生,当他因此受伤时,他就不能以侵权为由起诉。”而美国的《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496条更是明确规定:“原告就被告的过失或者不计后果行为而导致的危险自愿承担的,不得就该伤害请求赔偿。”因此,即使饮酒属于危险行为,由于这是饮酒者自愿实施的行为,即使因此陷入其中的危险,也应自甘危险。而共同饮酒者即使参与制造这一危险,也不是控制这一危险的最佳人选(最佳人选是其本人),因此对于醉酒负有注意义务的是本人,而非其他参与饮酒的人。
更进一步分析:即使我们承认本人是控制醉酒危险的最佳人选,能否免除其他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换而言之,如果危险性的存在与可预见相结合,能否导致共同饮酒者注意义务的产生?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判断本人与其他共同饮酒者之间的关系?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第315条曾经规定:“被告没有义务控制危险行为人的行为以避免给他人造成人身伤害。除非被告和危险行为人之间有某种特殊关系,使被告承担了控制行为人的危险行为的义务,或者被告和处于危险之下的可预见的受害人有特殊关系存在。”但单纯的共同饮酒行为是情谊行为,彼此之间并无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不构成能够产生注意义务的特殊关系。
(二)共同饮酒者的安全保障义务
对于注意义务的来源,还有判决认为共同饮酒者承担的是安全保障义务。这一观点也获得较多判决的支持。有判决径直认为,“原、被告共同饮酒,相互之间都有安全保障的义务”。还有判决扩张安全保障义务主体的认定,共同参与群众性活动的人也对其他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属于该条规定的在其他社会活动中的自然人,在和杨子金共同饮酒时,未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受害人醉酒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我国最早确定安全保障义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嗣后又在《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中明确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但是将安全保障义务纳入共同饮酒者的法律义务考量,会存在一个问题:适用主体是否合法?《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主体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和“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并未要求一般主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要求共同饮酒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无疑于法不合。
(三)共同饮酒者的法定附随义务
有判决认为,共同饮酒者对于同席饮酒的人负有一种“法定附随义务”。如“共同饮酒行为虽然不具有产生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的效力,但共同饮酒过程中仍会产生相应的附随义务,也即饮酒过程中和之后的注意义务,具体是指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相互承擔的劝阻、通知、协助、照顾和帮助等义务,履行这种义务的表现方式,应当是明示的作为义务。如果饮酒后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其他共同饮酒人均构成民法上的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所谓附随义务,是指债之当事人为使债权能圆满实现或保护债权人其他法益债务人除给付义务之外还应负的义务。该义务是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并非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债的关系变化而发生的义务。故附随义务的产生需以在先的债的法律关系存在为前提。而共同饮酒的行为,“作为一项社交性的邀请,虽然貌似合同,但无论是邀请人或被邀请人,通常其赴约的行为并不具有财产价值,甚至发生财产的减损,即时间或金钱的付出。而且共同饮酒的邀请,仅仅出于增进情谊的目的,邀请本身并不能形成某种法律关系”。情谊行为本身不可能产生附随义务,只有情谊行为产生债的义务后(如好意同乘发生交通事故后产生损害赔偿之债),方讨论附随义务的有无,因此共同饮酒行为不可能产生所谓的“法定附随义务”。
(四)共同饮酒者的一般注意义务
部分判决径直认为:共同饮酒者对于同席醉酒的人具有一般注意义务,其理由是:
1.基于合理的预见性而产生注意义务。有判决认为:“我国法律虽不禁止成年人饮酒,但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对饮酒后会导致人的意识、行为控制能力下降的情况是明知的。故在共同饮酒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合理地预见到共同饮酒期间和饮酒后因醉酒造成他人或自身损害的可能,也都有不使他人受到损害的注意义务。”
可预见性确是注意义务存在与否的判断规则。但是单纯地预见到危险则不是注意义务产生的依据。即使当事人能够预见到他人可能遭遇某种危险,并不自动赋予这个人救助的义务,比如在游泳池中游泳,即使他人发现有人不会游泳而下水,这个发现的人并无救助之义务,除非他自愿参与救助,或者他是游泳池的救生员。
2.客观形成的注意义务。有判决认为:“被告与受害人共同饮酒,在受害人饮酒之后,客观上形成相互保护的安全注意义务……因为喝酒能使人的神智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清醒,动作也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易于控制,这是正常人都知道的社会常识,共同饮酒的每个人都应当预见到喝酒就会有不安全性、有造成损害的可能,所以共同饮酒人之间应当互相照顾,阻止饮酒的人单独外出,或者将其送至安全地点或通知其家属。”
客观情形能否导致注意义务的产生,确实需要讨论。自学理而论,客观情形导致注意义务的产生,需要看其情形为何?是否符合产生法律义务的规定?如有职业上的要求(如警察),或者有法律上的规定(如《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的医师急救义务),或者存在先行行为。客观情形本身并不能自动产生注意义务。
3.注意义务属于法定的义务。有判决认为:“本案中,共同饮酒应具有一定的注意义务,即饮酒人之间应当承担的互相提醒、劝阻、照顾和帮助等义务,该义务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也是一种法定义务。因不履行该义务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还有判决提出:“按照相关规定,共同饮酒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各人均应合理预见共同饮酒期间或饮酒后有可能出现的不安全因素会造成他人或自身损害的可能性,各人均负有避免他人受到损害的注意义务,相互之间应当予以提醒、劝阻或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来保障共同饮酒者的人身财产安全。”但问题也就在这里。狭义的法定义务是指法律法规中的强制性规范明确规定当事人特定的注意义务,如《侵权责任法》第37条所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但是国内并无法律法规规定共同饮酒者之间存在注意义务的强制性规范。所谓“按照有关规定”,应在判决中予以明示,如未明示,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4.基于情谊行为而产生的注意义务。有判决认为:“亲朋之间宴请聚会饮酒本属一种情谊行为,每个饮酒者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有最高的注意义务,对其他饮酒者不能恶意劝酒,要有善意的提醒、劝诫甚至照顾的义务。……而与受害人同桌饮酒的被告,虽无证据证明其存在恶意劝酒行为,但作为共饮者在栗林饮酒后应尽到互相扶助、注意、提醒的义务,因此,同桌饮酒的被告对受害人的死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如前所述:我们同意共同饮酒属于情谊行为。但是情谊行为并不自动产生法律义务,因为情谊行为本身就表明行为人之间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不应受法律的约束,故要求其在酒后产生法律义务,显然欠缺足够的理据。
5.注意义务源于善良风俗。如有判决认为:“被告未能将不听其劝导坚持酒后自行驾驶摩托车回家的受害人护送回家,未能尽到符合善良风俗的相互照顾、保护义务,但对应承担这种义务的人应否承担连带责任,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规定,故一审法院判决受害人在各自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后相互承担连带责任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予纠正。”
善良风俗能否导致注意义务的产生?首先,判决需要论证存在酒后救助的善良风俗;其次,更重要的是,善良风俗所产生的是道德义务还是法定义务?只有证明这一善良风俗已经让普通百姓产生法律上的信赖,成为习惯法的义务,否则我们不能用道德替代法律。同时,如果认定共同饮酒行为属于以“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实施的侵权,则可以从比较法的角度思考。《德国民法典》第826条规范“违反公序良俗”的侵权行为,但该条规定要求行为人是“故意”侵权。就共同饮酒致损而言,共同饮酒者即使存在过错也肯定不是故意(除非存在强迫饮酒、知其不能饮酒而强劝等),其过错要件不符合该条规范的要件要求。
6.基于邻人原则产生的注意义务。有的判决认为:“同饮者基于特殊亲密关系而聚会喝酒,或者通过聚会喝酒建立、维持乃至增进情谊亲密关系,同饮之人具有感情上的彼此信赖。根据邻人规则理论,‘一个人作为或者不作为时应该考虑受自己行为直接、紧密影响之人的利益,同饮者也能合理预见自己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可能会导致对其他同饮者的损害。同饮者之间未履行注意义务,这是其承担侵权民事责任的过错所在”。
邻人原则是英美法中判断注意义务有无的重要原则,在著名的Donoghue v.Stevenson案中,阿特金(Atkin)勋爵指出:“你应当爱护你的邻居,这一规则已经成为了法律上的规则,你不应当损害你的邻居。而律师们提出的问题是,谁是我的邻居?该问题应当作限制性的回答。你应当承担合理的注意以避免那些你可以合理预见到有可能损害你的邻舍的作为或不作为。那么在法律上谁是我的邻居?答案似乎是,当我在采取引起争议的作为或不作为时,我应当预见到的会受到我的行为影响的、同我有密切关系并会直接受到我的行为影响的人即是我的邻居。”这一规则相继为Anns v.Merton LondonBorough council,Murphy v.Brentwood DC等判例所调整,成为英国侵权法中认定注意义务的重要规则。但是这一规则解释我国的判决却存在问题。首先我国法律中有无邻人原则适用之余地有待探讨;其次即使按照邻人原则,判决也需要进一步论证两个问题:(1)共同饮酒者与受害人之间能够通过共同饮酒的行为建立了法律上认可的特殊关系;(2)加诸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是“公平、公正和合理的”。这两个检验在审判中均值得商榷。在共同饮酒案例中,如前所述,共同饮酒行为是情谊行为,双方没有建立法律上认可的特殊关系;同时对于饮酒造成的风险,受害人自身更具有控制能力,而如果将这一控制风险的义务转嫁给共同饮酒者,显然有失公平。
7.其他理由。还有判决径直认定注意义务的存在,而不讨论其来源。如有判决认为:“饮酒过量会导致人体健康受损乃至死亡应是一般人的常识,在一起共同饮酒的人应当负有合理注意义务。”还有判决认为:“被告在与受害人高某同桌共饮后,负有将其妥善安排的义务,但上述被告因未履行此义务,以致此次事故的发生,故上述被告均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
对于共同饮酒的法律责任,学界也有讨论。如有学者总结认为:“在我国,涉及共饮人不作为侵权行为的相关判例相互间并无统一的思路,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受法律保护,同饮人应当对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承担过错责任。既然同饮人与受害人一同饮酒,就应当相互节制,并相互照顾。受害人在饮酒后造成自身的伤害,此种伤害与饮酒具有因果关系,由于共饮人在主观上对饮酒后损害结果的发生没有起到照顾和阻止的责任,故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受害人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应当知晓饮酒的后果(包含过量饮酒的后果),因此受害人对自己饮酒行为和酒后的行为都应当负责;如果法院认定共饮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将会导致认定自然人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泛化,其判决結果必将与社会的正常交往活动相抵触。宴请与接受宴请在社会交往中普遍存在,这是一种正常的、普通的社会交往活动,而在宴请中共同饮酒,特别是敬酒,也是社会交往活动的常识。如果社会交往中,相互之间无论关系如何,也无论是否相识等因素,只要因各种原因聚集在一起,只要坐在饭桌上,只要端起酒杯喝酒,不特定的相互人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责任和义务,这是显然有悖社会常识的,也违背了侵权责任法责任自负的精神。”
这一研究值得思考。讨论赋予共同饮酒者的救助义务,我们需要讨论赋予这一义务的理据为何?其正当性为何?
三、侵权法上的救助义务规则
对于共同饮酒者在酒后对醉酒者的救助义务,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因此在法律上存在一个真空地带,就是人们对于处于并非由自己造成的危险中的人有无救助义务?自传统民法的角度,自有“无救助义务规则”,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我们才能够要求不作为的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即违反作为义务的人。自学理上讨论,作为义务的来源,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是随着社会危险的日益扩大,人们必须寻找法律的平衡,在救助处于危险的人和赋予人们行为自由间获得平衡,注意义务的扩张成为必要。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英国法的“邻人原则”、美国法的“注意义务”与德国法的“交往安全义务”具有同一的功能,即在于填补界定疏忽的侵害行为(careless interference)所保护的关系的范围,也就是要确定可能对特定的加害结果承担责任的人的范围(它比充分因果关系能更有效地实现这一要求),特别是确定特定情况下救助义务产生的范围。
在我国审判实践中如何认定救助义务需要进一步检讨,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共同饮酒的案件中:
案例一:女顾客在银行办理业务后走出银行(取钱时并无异常),坐在银行门口达数小时,后路人发现其异常,似发病。该女顾客发病后爬到银行,银行将其劝离银行业务大厅,后路人报警送医,然女顾客送医抢救无效死亡。问:银行有无救助之义务?
案例二:两个朋友相约在郊区河堤钓鱼。不知何故,其中一人跌进2米深的河沟,此时,就在河堤边与其同行的朋友,眼看着其在水中挣扎,却未进行施救。闻声赶到的群众虽跳入河中进行救助,但掉到河沟的人最终仍溺水身亡。问:其朋友有无救助义务?
案例三:2007年11月怀孕7月的李丽云在同居者肖志军的陪同下赴北京某医院检查就医。经医生检查发现,李丽云有生命危险,必须剖腹产,让肖志军以家属身份签字同意进行手术,但是由于肖某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医护人员束手无策。医生只好动用急救药物和措施,不敢擅自进行剖腹产手术。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最终孕妇李丽云和体内胎儿不治双双身亡。问:医院有无救助之义务?
案例四: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震惊全国。2011年10月出生仅2岁的小姑娘王悦,在广东佛山遭遇了车祸。在小悦悦遭遇车祸后的七分钟内,前后共有18位路人从事故现场经过,然而竟无一人提供救助,最后王悦被一位长期在附近捡垃圾的阿姨发现并送至医院抢救,但终因伤势过重而命丧黄泉。问:路人有无救助义务?
现代侵权法仍然建立在个人主义的道德基础上。从比较法的角度看,对于不作为而言,本无需承担法律责任,故在英美法系国家长期坚持“无救助义务规则”,直到1908年,美国人詹姆士.巴尔。艾姆斯(James Barr Ames)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和道德》的经典论文,其中提及了一般救助义务问题。而最初救助义务的规定,也是出现在海商法,如共同海损制度,同时《布鲁塞尔公约》第11条规定:“每个船长都有义务对任何海上损失危险中的人,即使敌人也不例外,提供救助,但以不给其船舶、其船员和乘客带来严重危险者为限。船舶所有人不因违反上述规定承担任何责任。”进入现代,英美法有限地将救助义务纳入考量,以影响巨大的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版)》为例,第314条明确了“无救助义务规则”[《侵权法重述(第三版)》第37条仍然坚持这一规则,但同时在第315条规定了产生救助义务的特殊情形,包括:(1)原告与被告之间或被告与危险制造者之间存在特殊关系;(2)被告的行为或手段(有过错或无过错)地导致了损害;(3)被告自愿救助受害人或开始救助但救助不当;(4)被告干涉或阻止他人实施救助。同时在重述第323、324条做了进一步的规定。而在美国法院的实践中,也越来越多地将这些例外规定纳入审判的考量,以扩大传统责任的范围。
在大陆法系中,近代民法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确立了“自己责任原则”,包含了四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二,每个人只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无行为无责任;第四,无过失无责任。这一原则内容成为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的核心内容。作为义务的来源在德国法的传统学说中仅仅存在于有法律规定、契约约定或有在先的危险行为时才产生,这一学说为《德国民法典》所接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德国逐步通过判例创造出“交往安全义务理论”,这一理论表明“法律秩序不再要求社会成员透过放弃对该危险源之利用,避免损害之发生以保护法益。侵权行为法不再禁止(具有危险性之活动)行为本身,转而要求行为人应尽交易上必要之注意避免危险实现发生损害。即对一定危险源之存在为基础之过失责任,危险源之创造者或维持者,应尽之行为义务并非结果避免义务,而为适正处理该危险之义务”。同时,部分大陆法系国家通过立法规定救助义务。如在1867年《葡萄牙民法典》中首度规定救助义务,该法第2368条规定了见危不救者的民事责任:“遭受暴力攻击且有权自卫的人可以向当时在场的人要求民事救助,但这种救助以不会使救助人自己暴露在危險之中为限;不愿意并且没有救助的旁观者应对损失承担补充责任。”1966年《葡萄牙民法典》第486条修正这一规定,该条规定:“基于法律或法律行为有义务实施一项行为而未实施的,如果还符合其他法定要件,单纯的不作为也导致赔偿损害的债”。同时该条也为其同源的《澳门民法典》第479条所继承。而《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415、416条和《魁北克民法典》第1471条均有类似的规定。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对于救助义务的规定仅限于合同关系或者身份关系中,如《合同法》第301条规定的“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而《婚姻法》第20条规定的“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以及第21条规定的“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但并无一般意义上的救助义务规则。
回到共同饮酒的案件,首先我们需要承认并无法律规定在共同饮酒的情况下,同饮者对于醉酒的人负有救助义务,其次我们应该承认:除非同饮者恶意灌酒,导致饮酒者陷入危险境地,同饮者负有救助义务,如果饮酒者自己醉酒,不能要求同饮者承担法律上的救助义务;第三饮酒者与同饮者之间仅仅是情谊关系,彼此之间没有法律关系,不能产生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故没有救助义务。
那么,我们需要追问:法官能否以司法政策为考量,为共同饮酒者设定法律上的救助义务?
四、司法政策导向下的注意义务的认定
在现实案例中,笔者经常遇到法官通过扩大注意义务的解释来确定救助义务。值得我们思考与检讨的问题是:法官能否基于司法政策的考量扩张注意义务特别是救助义务的范围?笔者认为,我们当前不应基于司法政策的考量扩张注意义务的范围。
侵权责任法是一部弹性的法律。在现实生活中,随着司法政策的变化,法官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调整注意义务的内涵,各国司法实践莫不如是。与危险扩大化相适应,社会的发展也使得侵权责任处于膨胀之中,在英美法上有侵权法危机之论,大陆法系国家同样存在着侵权行为责任扩大化的倾向,大体包括:(1)从过失责任到无过失责任的倾向;(2)邻人诉讼类型的出现;(3)不作为责任的扩大;(4)侵权行为的契约责任化;(5)说明义务的扩张。上述变化均涉及当事人注意义务的扩张。而注意义务的扩张往往会涉及到司法政策的判断。众所周知,侵权法涉及到两种利益的平衡:行为人的行为自由和受害人的权利保护。在侵权疑难案件中,特别是涉及到过错认定的疑难案件中,往往是法官通过司法政策的考量决定过错的有无。在《荷兰民法典》中,甚至公开承认司法政策对于责任承担的意义,该法第6:162条规定:“……(3)加害人因自己的过错造成损害或者依据法律或社会观点对损害负有责任时,加害人对加害行为承担责任。”
以共同饮酒者案例为例,导致多数法官支持共同饮酒者承担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基于司法政策意图遏制恶性饮酒的行为,笔者与参与审理类似案件的一位法官讨论该案时,该法官言简意赅地指出:“没办法,本地区酗酒闹事的太多。”同时,对法官而言,同情弱者也是判决被告承担责任的理据之一。我国《侵权责任法》在颁布伊始,更多地强调该法保护受害人权益的内容,而较少提到行为人自由的利益保护,加之近年和谐司法的理念,让法院判决具有强烈的“司法父爱主义”色彩,因此,对于被告的过错认定,也具有了司法政策的考量。
但这种司法政策的考量也是侵权法中注意义务扩张的风险之所在,与明确规定的法律不同,司法政策存在的弹性和个人认知的差异,不同的法官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司法政策认知导致法官不同的判决,进而出现“同案不同判”,损害了法院判决的权威性。
回到共同饮酒案例,对于赋予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在司法政策上可能导致三个问题:一是有违责任自负的原则,如前所述,如果饮酒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则控制这一风险最有力的人是受害者本人,而将这一义务转嫁无疑有违责任自负的原则,故法谚云“任何人对他人行为的结果不负责任(Non ex alterius facto praegravari debet)”;二是对于共同饮酒者而言,几乎无法控制受害者的行为,换言之,如果受害者坚持饮酒,则共同饮酒者无法控制并要求其不再饮酒,因为每个人是独立个体,彼此间并无干涉的权力,所谓“法律不能强人为难(Lex non cogit ad inpossi-bilia)”,赋予共同饮酒者注意义务,则无疑赋予其无法承担的义务;第三,对于共同饮酒者而言,酒后具有照顾、保护能力的人应是未醉酒的人,才能够承担救助义务。那对参与宴会的人而言,避免承担责任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灌醉,否则就要承担责任,在这一规则的指引下,醉酒成为人们最好的保护,这样的行为指引则无疑有违这一规则的初衷。故赋予共同饮酒者的注意义务,并非最佳选择,笔者不赞同这一规则。
法官在解释《侵权责任法》第6条第1款的“过错”时,应谨守司法的分际,唯有在获得现行规范支持的情况下方可认定,避免法律责任随意的扩张与缩小,特别是在价值多元化的转型社会,除非社会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否则不宜扩张注意义务的范围,肆意修订在社会交往中多年形成的交往规则。在这方面英国的教训值得我们吸取,英国的阿特金(Atkin)勋爵在Donoghuev.Stevenson案中创制了邻人原则,完善了英国过失侵权的制度设计,进而英国在Anns v.MertonLondon Borough council案对邻人原则确定了“两步法”的检验方法,从而为侵权诉讼大开方便之门,导致英国侵权法进入所谓的“滥诉”时期,上议院不得不在Murphy v.Brentwood DC案中确定“三步法”来约束对注意义务的认定。
从这个意义上讲,笔者赞成在我国的侵权案件审理中,坚持“司法克制(Judicial Restraint)”。所谓司法克制,是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严谨地执行现行法律的意志,尽可能地不渗入法官个人的信仰与倾向。而法官对注意义务的认定,应该认识到自己的权力边界,应当将尊重方法论作为法官创制规则的必要前提,其权力的行使必须是慎重且抑制的,同时应有辅助原则(如优先考虑法律的條文解释,立法者的意思以及现行法律构成,造法必要者负有对其主张的证明责任等),尊重根据程序法上的规定而产生的界限等方面来对这种解释进行必要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