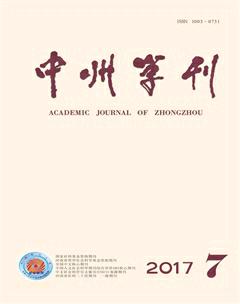略论中国近代史之开端
摘要:鸦片战争前的中西方坚守着各自的“天下秩序”。中方继续坚守“天朝体制”,西方却要求整个世界接受“对等”的世界秩序。两者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最终爆发了鸦片战争并以中国被迫接受西方的世界秩序而告终。即此可见,鸦片战争充其量只是中西方冲突后的一个拐点,在此之前相互间的体制冲突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为此“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并非始于鸦片战争,必要的“前推”,不仅可以对“中国近代史”之开端进行“长时段”的“解读”,而且可以恢复“世界史”视域下的“中国近代史”的本来面目。
关键词: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中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K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7-0115-06
有学者曾称:“研究近代中国制度变迁史,不能仅仅局限于对1840年以后的考察,需要打破近代史与古代史之间的隔阂,尽可能地往前追溯历史渊源,了解近代中国制度变迁的源头。”①不仅近代中国制度史之研究需要如此,更为宏观的中国近代史之研究也应注意此点。几乎自16世纪以来,世界的一体化格局就日渐形成。但无论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还是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却有各自的“体制”与“秩序”。因鸦片问题而引起的西方各国对中国的殖民,充其量只是16世纪以来中西方冲突的一种表象和爆发途径,相互间的体制与秩序冲突才是真正的症结所在。为此,中国近代史之真正开端并非始于鸦片战争,而应追溯到前辈学者所倡导的“近世史”②之源头,放弃学界一直以来的近代史时段之划分。这样做不仅可以兼顾到各阶段历史的连续性,而且尽可能地保全中国近代史的“长时段”特点与“中国近代史”属于“世界史”之重要内容的本来面目。以此立论,本文将围绕鸦片战争前的中西体制冲突及演变,讨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是否恰当,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鸦片战争前清朝的统治体系
1.对传统体制的坚守
中国历代皇帝在构建自己的天下体系时,其“天下”范围通过“自内而外”与“自上而下”的两种方式表达。
“自内而外”,“中国本域”圈层是该体系的“中心”,构成了该体系的第一个圈层。“中国本域”圈层又由“内”“外”两部分构成。内部为十八行省,紧邻其外的为各边部。清代的“中国本域”就是由内地各行省和藩部构成,藩部主要包括蒙古、西藏、回疆等。逐次向外的第二圈层为属国圈层,清代多指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诸属国。这些属国在多数场合下均被清朝视为其统治范围,如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在给缅甸国王的召谕时就称:“中国抚有函夏,东自高丽琉球及东洋诸大国,南则交趾以南诸国,北则准噶尔全部,西则回部数百城,并入版图。”③
“中国本域”和属国圈层外,第三个圈层即朝贡国圈层。朝贡国包括英法等国,如乾隆年间的《皇朝职贡图》中列举的朝贡国就有“合勒未祭亚、翁加
收稿日期:2017-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外蒙古草原上的内地商民人研究”(2016BZS104);河南大学校级教改项目“高校中国史教改初探——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中心”。
作者简介:柳岳武,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开封475001)。
里亚、波罗泥亚、英吉利、法兰西、瑞士、马辰、汶莱、柔佛、荷兰”④等。与属国不同,清廷对朝贡国不进行册封,只要求朝贡国来华时向它进贡、对其表示恭顺;反过来,清廷则要对这些朝贡国实行赏赐,作为他们前来朝贡的一种回报。第四个圈层是互市国圈层。互市国主要指只同清廷进行贸易,而不向清廷进贡的那些国家。清代的俄罗斯通常意义上被清廷视为互市国,另外还有葡萄牙、西班牙以及那些偶尔来到中国沿海、同中国从事贸易的其他国家。互市国圈层之外,就是所谓的化外之域了。化外之域之外就是蛮荒之地,时人主要通过想象来构建这些地方。通过这样的一个由内向外的结构可以看出:整个“天下体系”就是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向外不断辐射、扩散的过程。⑤
除了“内外”的圈层结构外,清代皇帝同整个“天下”的关系还可通过上下的纵向结构表达。皇帝自称天子,统治范围包括本国、属国、朝贡国。本国下面则为省、府、厅、州、县。省、府、厅、州、县下面是家族,家族下面又是一個个家庭,家庭下面又为普通家庭成员,即天子的庶民。天子之庶民既包括中国的庶民,也包括属国、朝贡国的子民。总之,这样一个纵向关系是一个由上向下不断扩大的结构。⑥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坚守的就是这样一套体制,如此“坚守”更为具体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坚守“中心到外围”式的防御体制。以上描述表明:由内地十八行省和藩部构成的“内中国”与属国、朝贡国、互市国等圈层结构,体现的正是清代“中心到外围”的防御体系,清朝皇帝企图用这个体系来实现“守在四夷”的目标,其途径就是在“最中心的中国内地”的外面设置藩部,保护内部的十八行省。以属国圈层构成外一层的藩篱,拱卫“内地十八行省”与藩部的“内中国”这一中心。属国圈层之外的朝贡国,也是用来拱卫中心、确保天朝安全,并尽量避免天朝受到朝贡国之外的化外之域的冲击的。⑦鸦片战争以前,清廷仍坚持它同各“外围”的关系。如清廷在册封朝鲜、安南、缅甸等国王时,要么要求它们“屏翰东方、藩屏攸赖”⑧,要么要求它们“恪遵侯度、屏藩南服”⑨。
其二,坚守传统的通商体制。清廷建立起来的天下结构,除本域之外,无论是属国还是朝贡国,他们同清廷的关系都是不对等的,让这种不对等关系长久持续的主要手段就是通商。只要各国接受中国的“上国”地位,并对皇帝俯首称臣,就能取得来华通商的特权。否则即拒绝。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马戛尔尼访华被逐事件⑩。正是如此,鸦片战争前,朝贡贸易充其量只是一个制约机制,只是协调中心与外围关系的一种工具。如清代同准噶尔部的关系,康雍时期,清廷常使用“边市”和“朝贡贸易”的机会,对其进行牵制。如果准噶尔部按期到清廷进行朝贡,不对西藏、蒙古等地方骚扰,清廷就会给予它贸易机会;否则,即失去此待遇。再如当中越关系缓和的时候,清廷就允许越南朝贡,中越之间关系紧张时,清廷就不允许它来朝贡。又如康雍乾时期的中俄关系也体现了此点,当俄方侵扰清朝北部疆域时,清廷就断绝恰克图边市,直到俄方接受清廷提出的要求后,才以恩赉的方式重开边市。总之,清廷总是通过是否允许对方同中方通商开市的措施迫使对方就范,对自己表示臣服。传统的通商体制中,商业只是协调政治关系尤其是内外关系的一个辅助工具。这说明农业型国家主要重视农业而轻视商业,就像乾隆在马戛尔尼访华时所强调的那样:“天朝”“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言外之意,对外商贸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并非中方必须,只是体恤外夷的一种途径而已。
其三,坚守传统的文化体制。中国实现“天下一统”,除上述方式外,所依靠的最重要的手段应属文化、礼仪,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以德化夷”“化天下”。如《中庸》就称:“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望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其中的“厚望而薄来”“嘉善而矜不能”“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都是天朝“德政”的主要体现,也是天朝能够使各国主动来朝的重要推动力。如康雍乾三帝为对朝鲜、越南、琉球等实行德化,就从朝贡贸易方面对它们实行“厚望薄来”,如康熙五年,清廷将顺治时期的“减礼条例”再次酌减。雍正元年,雍正帝再减朝鲜贡物。乾隆帝也命令减朝鲜国馈送诏使仪物。另一方面则是赐品的日增。如顺治十八年,清廷赏朝鲜国王各锻共50匹。康熙年间,又加赏朝鲜国王和使臣。雍正帝要求“外藩人等来朝”“务使得沾实惠”。“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的“德政”在清朝时期也得到体现,如乾隆帝对安南陈氏王朝的兴灭继绝就是例证。
除“王化政治”的“德政”外,天朝又通过“书同文、车同轨”的方式进行影响。如乾隆四十八年(正宗七年)朝鲜大司宪洪良浩就向国王提出学习汉语,“汉人之语,即中华之正音也”,“挽近以来,汉字之讲,便成文具,能通句读者绝少,数使臣之与彼相对也,耳褎而口噤,片言单辞,专仗象胥”。
“书同文,车同轨”更为深层的内涵为学习中国的典章体制,这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东亚范围内也体现得很明显。如朝鲜、琉球等在天朝体制崩溃以前均追随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清代朝鲜的读书人要求自己比中国的士子更要遵守传统的儒家经典,坚守宋明理学,遵守华夏礼制。清代琉球政治制度也多仿效中国。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就称:“先王之制,凡属国止封其君,而其臣之爵秩不与闻焉。琉球爵秩,亦分为九品如中国例。”
总之,近代以前东亚各国,大到国家典章制度、法令律例,小到民间契约、碑刻祭文、书信文章,不仅文字上采用汉字,而且规制、格式方面也严格遵循中国的“范式”,深刻反映出中国文化对各国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传统的东亚“天下”的影响之大。
2.清廷的挣扎与无奈
导致清朝统治衰弱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清廷统治效能的相对下降。1764年时中国总人口为20560万,到了1812年增至33300万余人,再至1835年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已经增至近4亿人。与乾隆中期相比,人口总数净增近1倍。人口的增长的同时,对国家安定产生至关影响的地方行政机关的州县,设置数量并无太大变化,大约1200—1300个。如果说乾隆中期以前全国近1300个县令负责处理全国2亿人口的大小事务,每县平均15万—16万人,还能保持农耕社会基本平稳。至嘉道后,每县平均增至30万—32万人口,其办事效率可想而知,整个基层统治混乱、滞后,行政效率底下。
除了这一因素外,清代中期疆域的进一步扩大也超出了农业型帝国的有效管辖范围。在主要以马匹、帆船等作为交通手段、依靠驿道传递军情、依赖骑射守卫边陲的年代里,农业型帝国实际有效控制的范围是有限的。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因维系如此广阔版图而要极大消耗自身实力的状况,导致统治秩序出现危机。如晚清时期的蒙古,传统的保护蒙古的政策即开始废弛。西藏也一样,内部危机日重,接连爆发了萨玛第巴克什危机和热振呼图克图被逐危机。这些地区相继爆发的问题,虽有外来侵略导致的内部压力,但清朝内部积累起来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封建统治或阶级压迫。为此,清代中后期清廷统治的败坏,不单是清廷自身统治不良的恶果,更与乾隆中后期没有与庞大帝国相匹配的新兴科技有关。正是由于科技未能发展、技术没有长进,清廷主要仍依赖22万八旗和66万绿营为主体的正规军去维系统治秩序,而军队的腐败废弛也加剧了这一恶劣形势。
二、文艺复兴后的西方世界
鸦片战争前清廷还想竭力坚守自己的传统体制,但是西方世界的变化已经不再允许它那么做。同时期,西方殖民帝国对东方世界的冲击实已开始,它正试图颠覆东方的传统秩序。如此的颠覆活动与16世纪以来全球一体化格局的到来密切相关。西方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其二是西方变化后对东方以及世界各地的巨大影响。
1.西方自身体制的变化
西方自身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政治、外交体制的变化。在文艺复兴后,西方王权还开始了对教皇的挑战,并最终夺取了对本国人民的神权和政权的控制,从而为西方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了条件。不仅如此,“三十年战争”后《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签订(1648)意义更为重大。它不仅促使国家主权观念进一步产生;而且还导致了西方近世以来的外交理论即国际法观念之出现。从此“国际法代替基督教原则,成为处理国际纠纷和维持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同时在追求个性、追求创新思维的引导下,西方的科学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它不仅为欧洲各国反对教皇、追求国家独立提供了保证,而且也为资本主义今后的全球扩张提供了最好的武器。如“1450年加农炮的发明,使战术发生了有利于国家发展”的转变。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日后扩张,这一技术革命为它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因此,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后,“造成了欧洲列国制度的兴起及外交制度的应用”。不仅如此,还引发了西方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对东方的扩张,他们从此向东方推行“扩张有理”论。
2.西方对东方的扩张
近代西方国家在自由、探险、殖民等思想的引导下,开始向东方扩张。不断对清朝属国进行殖民扩张。如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后,随即派遣它的舰队来到暹罗,“拉玛提波底二世应允葡萄牙人可以在泰国安居和通商,以作为交换他们的武器和弹药的条件”。1600年后,葡萄牙人开始在缅甸发展自己的殖民地。1752年后,葡萄牙人、法国人、英国人在自己的公司的掩护下纷纷来到缅甸,开始了对缅甸的殖民掠夺。1511年葡萄牙在越南的岘港附近建立商埠。1672年,英国人驾驶“桑特号”商船前来越南,请求贸易。1680年,法国人商船也开进了越南,请求设立商埠,從此开始了法国人对越南的殖民活动。
明末清初西方殖民者不仅对中国周边的属邦进行经济渗透,而且还对中国本土进行殖民渗透。1557年葡萄牙人使用贿赂的手段,获得了在中国澳门的居留权,这是中国澳门被殖民的开端。英国人则于1637年开始了同中国的第一次贸易。法国人于1660年来到广州,美国人于1785年来到广州。俄国人由于与中国边界接壤的原因,则在1567年就来到了北京。道咸同时期,西方对东方殖民更为加速。据统计,1800年至1875年期间,殖民帝国每年平均获得殖民地为83000平方英里。这一侵略速度在18世纪是十分快速的。此举表明,文艺复兴后,殖民主义全球扩张愈演愈烈,同时,它也表明中国传统藩属体系所面临的威胁日益严峻。
以上历史表明,明末清初之际,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巨变;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已经开始向全球扩张,并迫使全球成为一个整体。自此之后,西方要用资本主义的手段、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资本主义制度来规划全球;并使用精神的、宗教的、武力的手段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全球推行。明末清初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不再是中国的历史,而是全球范围的历史。
三、“西力东渐”下“天朝”体制的崩溃
1.西力东渐下属国体系的崩溃
在被西方各国“开国”之前,整个东亚范围的各个国家多奉行同中国一样的天下格局观念。如日本,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也参照中国“中心到外围”式结构去构建它的宗属体制。其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明代后期日本迫使琉球臣属于自己,又想占领朝鲜,“入主中国”,清代时将琉球纳为其属国。越南也有自己的属国体系,越南就曾把它周边的一些部落变成其保护对象,它曾经一度想迫使本属中国边地的土司等臣服于己。再如廓尔喀,它于乾隆中后期,不仅兼并了周边的各小国,而且甚至迫使本属于清廷属国且同西藏有着密切关系的锡金、不丹等臣服于它。所以在近代之前整个东亚体系内,各个国家都认可中国式“天下”结构,接受类似的天下观,并对西方为代表的外夷均持抵制态度,把它们视为不文明、不开化的对象。但是整个东方坚守的如此秩序、格局、价值观念,至19世纪后却遭到西方的破坏。自16世纪以来,不仅中国的外围,如印度、缅甸、泰国等开始遭受西方各国的冲击,中国本身也开始遭受外来冲击。如1793年马戛尔尼访华,1832年阿美士德访华,都是代表。所有的这些都是对东方式秩序和价值规则的冲击。虽对各自的冲击程度,先后顺序有所不同,但总趋势一致,均代表西方社会对东方所坚守的传统体制的破坏。
2.鸦片战争后西方对“清朝本域”的冲击与影响
鸦片战争对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破坏更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冲击了传统的朝贡体制,导致该体制对西方社会不再适用,中外位置被倒置过来。鸦片战争前,在清廷看来中国同英法美等国的关系是宗主国与朝贡国的关系,后者须向前者进贡,须臣服于中国皇帝,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与中国从事朝贡贸易的机会,否则,将被驱逐。马戛尔尼访华时,马戛尔尼就想同中国结成一种对等的关系,但是乾隆皇帝坚决不同意。为何反对,因为在传统的体制里面不存在如此模式。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国迫使清廷签订《北京条约》,清廷不仅同意英法美等国在京驻公使,而且给予英法美等国对等的国家关系。这样一来,传统的天朝上国地位开始丧失。传统天朝上国同英法美等国之间的旧有的尊卑屈从关系取而代之以所谓的平等关系。不仅如此,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通商口岸的开辟等,都开始迫使清廷屈从于西方。至此旧有的中外交往模式,已经被倒置过来。过去西方屈从“天朝”,现在是“天朝”不得不屈从于西方。
其次,冲击了传统的属国体系,导致该体系的瓦解。几乎与鸦片战争相伴随,清廷传统的属国体系也在崩溃。如苏禄早在乾隆中期就停止向清朝进贡。暹罗于咸丰二年(1852)最后一次进贡后,即不再进贡。暹罗为什么不向清廷进贡?因为暹罗已经遭到英国的“开国”。被“开国”后,暹罗变成了英国的势力范围,接受近代西方的秩序,向英法开辟通商口岸。英法在暹罗驻领事,暹罗也尝试学习西方外交规则,向西方派留学生、公使等,开始了暹罗的近代改良。不仅如此,渐渐地,暹罗对中国传统的那一套体系不再认同。如光绪十年(1884)郑观应前往暹罗,遭到暹罗拒绝,实则表明暹罗已不再承认这一传统关系。再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方史料亦无布鲁特、浩罕等中亚小国向中方进贡的记载,这些“属国”都不再向“天朝”进贡,它们同清廷的宗属关系也基本终结。
最后,鸦片战争后,传统的藩部体系也开始瓦解或转型。晚清以来的藩部体系也在发生变化。与属国不同,清代的藩部都属中国,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清廷对传统藩部地区施行的却是与内部十八个行省不同的治理政策,多采取因俗而治、因地制宜的治理方略。清廷主要让各个部的王公领主代表皇帝实行直接管理。如此格局为晚清以来的西方各国染指各藩部提供了极大便利。英国曾两次进攻西藏,西北各蒙古地区、天山南北的回疆地区也遭到俄国的入侵。除一些传统藩部土地遭受殖民帝国的直接侵占外,至光绪后大部分藩部也开始发生转型。这种转型既有内部自我生成的因素,也有外来压力的结果。当新疆难保的时候,清廷就派左宗棠收复新疆,将新疆改设成省。当东北地区遭受到日俄侵犯时,清廷就将东北地区改设为三个行省。除此之外,当外蒙古、西藏等地区遭受侵略即将难保的时候,清末朝廷又试图在这些地区推行新政,试图将这些地区由传统的藩部逐渐变成清廷统治下的地方行政区域,变成地方上的省、府、州、县,设立流官,实行直接管理。这些努力虽终因某些殖民帝国的反对和部分王公贵族的抵制,在清末时段内未能真正完成。但从长时段上看,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果。
四、“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重新构建与“书写”尝试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近二三百年的时间内中西方的冲突就已发生,此种冲突的背后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天下秩序”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之间的碰撞,这种碰撞实则代表了两种不同体制、秩序之间的撞击。一方是以农业文明为核心的东方的“天下体制”,另一方是以工业文明为核心的西方的“世界秩序”,虽不能从价值尺度上武断地判断谁优谁劣,但却代表了两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和社会形态。碰撞的最终结果是清朝的“天下秩序”不得不徹底屈从于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秩序。
但这一冲突背后凸显的却又是另一种的不对等,即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秩序与国际规则虽不乏包含人类文明进步之内容,但亦暗藏诸多开化、殖民、弱肉强食之实质,实则有用一种新的不对等的“世界秩序”去取代以中国为代表的旧的“天下秩序”。随之而来的是变“天朝为中心”为“西方为中心”,变西方各国匍匐来朝为中国对西方各国新规则、新秩序的全盘接受。
如此的转变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已基本完成,但中西之间的博弈与冲突并非始于当前学界所认为的近代史之肇端的“鸦片战争”这一拐点。为此真正的“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实应早于鸦片战争,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必要“前推”,不仅可以方便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长时段”的“解读”,而且可以恢复“世界史”视域下的“中国近代史”的本来面目。为此,学界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相关内容时,必要的“前推”是很必要的,否则无法解决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不能忽略1840年以前的中外格局而单强调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变化。
因此,笔者中国近代史之开端定于16世纪初较为稳妥,这一时期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法制、内外关系等内容呈现出了中国传统体制之本质。与16世纪后西方世界的变化以及西方世界新秩序的生成产生碰撞,这其实是两者之间本质的冲突,两种体制与秩序之间的碰撞结果是鸦片战争的爆发,最终使“中国近代史”进入一个新的拐点: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逐渐让位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因此客观的“中国近代史”不仅存在中外空间上的互动问题,同时也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解释1840年后中国传统体制、思想为何由传统向“近代”发生转变,以及如何最终实现了此等转变。否则,我们无法解释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框架中发生的诸多重大历史问题。
注释
①朱英:《如何研究制度史》,《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4期。②郑鹤声:《中国近世史·自序》,中央政治学校印,1930年,第1页。③《清高宗实录》卷八四五,乾隆三十五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436页。④王有力主编:《中华文史丛书》之十一,《皇朝职贡图》,台湾华文书局,1968—1969年,第36—42页。⑤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6页。⑥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300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c1984. p.25, p.16.⑦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⑧《清世祖实录》卷四五,六年八月丁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363页。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乾隆五十五年三月乙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90页。⑩故宫博物院文献馆:《英使马戛尔尼来聘案》,《掌故丛编》第1辑,和济印刷局,1930年,第70页。李元度纂:《清朝先正事略》(一),卷五《名臣费扬古》,明文书局,1985年,第184页。黄鸿寿编:《清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240页。《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一〇,乾隆五十三年八月癸巳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662页。《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82页。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9页。孔子等:《四书》《四书·中庸》,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4页。《清圣祖实录》卷康熙五年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291页。托津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三,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第7797—7798页。《清高宗实录》卷九,雍正十三年十月辛未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212页。托津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二一七,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第857页。、《显宗改修实录》十年三月甲辰条,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1957),第3958页。托津纂:《大清会典事例》卷五〇六,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第862页。张登桂纂修:《大南实录》正编卷三九年黎昭统二年冬十月戌申条,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80年,第284页。《正宗实录》七年七月丁未条,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昭和32年(1957),第431页。朴齐家:《北学议·序》,《贞蕤集》,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61年,第3页。《清代琉球纪录集辑》,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239页。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另可参阅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43页。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清代中国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9页。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一六·户丁·稽查种地民人》《理藩院》卷九七八,清会典馆,光绪二十五年(1899)石印本,第1128页。《清宣宗实录》卷四〇六,道光二十四年六月初七日条,中华书局,1986年,第82页。《西藏研究》编辑部编:《清代藏事辑要》(一),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99—500页。何新华:《夷夏之间,对1842—1856年清政府西方外交的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8页。王明星:《朝鲜近代外交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第14页。Richard Bean. War and the Birth of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march 1973, p.208.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37、36页。王曾才:《中国对西方外交制度的反应》《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七编,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1页。广东省文史研究馆译:《鸦片战争史史料选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30页。田禾、周方冶:《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6页。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03页。《越南》,维斯特编,台湾英文杂志社有限公司,1994年。马士:《中華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1960年,第45—60页。斯塔夫亚诺斯:《全球分裂》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70页。《琉球往来》抄本,转引自殷梦霞编:《国家图书馆藏琉球资料续编》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639页。《清高宗实录》卷三九三,十六年六月辛酉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63页。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1984年,第234页。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1997年,第225—226页。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1995年,第19页。赵尔巽撰:《清史稿》卷三一五,《属国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4697—14698页。田禾、周方冶:《泰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01—102页。沈云龙主编,俞樾辑编:《彭刚直公奏稿》,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150页。《清德宗实录》卷二五五,光绪十四年五月庚申条,中华书局,1987年,第435页。《左宗棠全集》,上海书店,1986年,第8801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科给事中左绍佐奏为西北空虚边备重要请设行省事》(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5618-019;缩微号:432-2508。
责任编辑:王轲
"Conflict" and "Collision": A Brief Discussion on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Liu Yuewu
Abstract:Before the Opium War both the East and the West insisted to their "world order". China w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celestial system", the west was asking the whole world to accept the "equivalence" of the world order.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s inevitable, finally broke out the Opium War. China was forced to accept the western world order. Therefore, the Opium War was at best an inflection point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efore this, the institutional conflict with each other was the real sticking point. Therefore,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did not begin with the Opium War, necessary "forward push" not only interpre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for a long time, but also restore the true features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 in the sight of "world history".
Key words:Opium War;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中州學刊2017年第7期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2017年7月中 州 学 刊July,2017
第7期(总第247期)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No.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