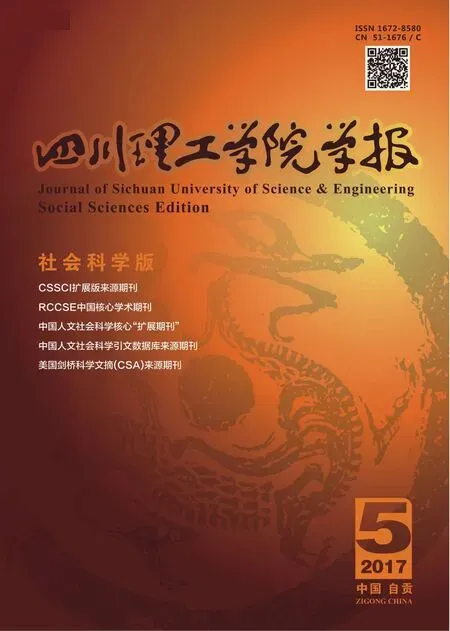应对灵活性对大学生压力适应的作用机制
雷 鸣,位东涛
(1.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成都611756;2.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重庆,400715;3.西南大学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应对灵活性对大学生压力适应的作用机制
雷 鸣1,位东涛2,3
(1.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成都611756;2.西南大学 心理学部 重庆,400715;3.西南大学认知与人格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重庆400715)
应对灵活性是指个体能够根据压力情境有效选择压力应对策略的能力。尽管已经开展了二十多年的研究,但是应对灵活性受到的关注还是不够。当前研究着重探讨应对灵活性在压力应对和促进个体社会适应方面的作用及其机制。鉴于当前的研究现状,本研究揭示在大学生群体中应对灵活性的积极作用。研究一对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进行中文版修订。该量表从压力应对者感知的角度评估自身具有的应对灵活性,是评估应对灵活性的有效工具之一。量表中文版的修订为探讨压力情境中个体的应对灵活性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先后三次随机抽取了2190名大学生参与修订工作。结果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中文版由11个题项组成,包括“事件聚焦”和“未来聚焦”两个维度;在信度方面,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8,分半系数为0.656,间隔3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741,2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714、0.685;在效度方面,主要拟合指数支持修订后量表的结构模型 (χ2=206.303,df=43,RMSEA=0.065,IFI=0.901,CFI=0.920,GFI=0.960,p=0.000)。同时,应对灵活性及其事件聚焦、未来聚焦两个维度与压力感、消极情感呈负相关,而与应对效能、认知重评、积极情感、心理复原力、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呈正相关,在汶川地震灾区大学生中,PTSD自评高分组在事件聚焦和应对灵活性上显著低于低分组大学生。这表明,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此基础上,研究二在大学生群体中考察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随机抽取1138名大学生,以积极心理健康(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作为社会部适应的观测指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体验与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之间起到有调节的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压力体验与社会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应对灵活性对大学生的压力适应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这项研究表明,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可以用于评估中国大学生的应对灵活性;应对灵活性对大学生的压力适应起到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应对灵活性;积极心理健康;心理复原力;大学生;适应;幸福感
一、问题提出
人在其一生中难免会遭受压力事件,甚至有时会是暴力、自杀、自然灾害等潜在可能的创伤事件(potentially traumatic events,PTEs)。不少学者关注压力亲历者采取的应对(coping)过程、方式及其可用的资源,以有效地抵抗、降低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学者们从应对的过程,聚焦压力应对的核心因素——控制感。Lazarus和Folkman的压力认知评价模型认为,感知到的对情境的可控性会影响个体应对行为的选择。如果个体感知到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改变外界环境(可控性),那么他就会采取聚焦问题解决的策略。相反,在控制感较低的情境中,个体就倾向于选择聚焦情绪调节的策略,缓解情绪反应的强度。从社会适应的角度来看,聚焦问题解决的应对策略更有利于减缓压力的反应,而聚焦情绪调节的应对策略则不利于促进个体适应。但是一些在不同的情境中的后续研究并没有得到与之一致的结果。聚焦情绪调节的策略也能促进个体积极地适应。不少学者认为,个体可能会在不同的情境中灵活地选择不同的应对策略[1]。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压力情境下的积极适应与其说是特定应对方式产生的效果,不如说是个体根据应激的性质而灵活选用应对方式的结果[1]。应对灵活性成为了应对研究的重点。
灵活性(flexibility)也称为变通性,一般是指人们在认知过程、行为调整、情绪反应等心理活动中展现出来的自动调整程度。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对灵活性的研究主要涉及认知、应对和情绪三个方面,形成了认知灵活性(cognitive flexibility)、应对灵活性(coping flexibility)、情绪灵活性(emotional flexibility)、情绪调节灵活性(emotion regulation flexibility)等主题鲜明的研究领域。在压力应对领域,应对灵活性和情绪灵活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前者侧重于描述个体应对方式、策略调整的变通性,后者则突出个体在情绪反应过程中调节的自由程度。不少学者将情绪灵活性或情绪调节灵活性视为应对灵活性在情绪调节方面的具体表现。虽然应对灵活性的相关文献还相对比较少,灵活性在增进个体心理健康中起到重要的作用[2]。最近一篇整理过去40年研究的元分析结果明确显示,应对灵活性有利于增强个体在变化的生活压力情境中的心理适应状况[3]。
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的研究,学者们对“应对灵活性”概念的理解存在五种视角:一是应对策略数量的取向(the repertoire approach),将应对灵活性理解为个体在应对过程中选用的应对策略的种类及其使用频次。在这种研究取向中,一个人的应对灵活性体现在其使用的应对策略种类和使用频次都超过所在群体的平均水平[4]。如果个体持有的应对策略的种类越多,使用频率越高,那么他的应对灵活性自然很强。当然,也可以从应对策略的应用范围来评估。应对策略被应用的范围越广,一个人就越容易表现出灵活性。二是策略使用频次的平衡程度(the balanced profile)。一个具有灵活性的个体在应对压力的时候,不会过度地依赖某一种应对策略,而是比较均衡地使用一系列地应对策略,各种策略在使用频率上大致相当。比如,Gan等人[5]的研究和Kaluza的研究[6]。三是变化过程的取向(the variation approach),应对灵活性表现为个体是否能够根据压力事件或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原有的应对策略。在这一类研究中,应对灵活性取决于一个人在不同的压力情境或时间范围内选用的应对策略的数量总和[7]。四是应对策略与环境匹配的取向(the fitness approach)。这种取向将应对灵活性视为个体能否在评估压力情境之后选择一种恰当的应对策略,达到应对方式与环境的互相匹配(goodness-of-fit hypothesis)。个体能够选择恰当的应对策略被视为具有应对灵活性的表现。这可以从客观的应对结果中应对模式和压力可控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来考察[8-9]。五是能力感知的视角(the perceived ability)。主要从压力亲历者的角度评估自己在不断变化的压力情境中使用各种不同应对策略的能力。这类研究主要从应对的过程考察个体根据环境而灵活调整目标、选择策略以及调整应对策略的能力。实际上关注个体感知到自我调整的能力及其应对压力的胜任能力。
在这五种研究取向中,前四种取向都是基于研究者的视角,忽视了压力应对的主体。一个人个体能否成功地适应不断变化而复杂的环境,需要个体快速地评估压力情境,并据此选择恰当的应对方式以达到压力反应与情境的最佳匹配。这一内部的心理过程,压力应对主体的自我评价才是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同时,由于成长经历的不同,即便在相同压力情境中选择了相同应对策略的两个人,他们做出选择的原因是不尽相同的。因此,需要从压力应对主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应对灵活性及其相关研究,并编制了一些符合心理测量学要求的自评量表,比如,Brandtsta咬dter 等人编制 的灵活目标调整量 表 (the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 Scale,FGAS)、Bonanno等人编制的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 (the Perceived Ability to Cope with Trauma Scale,PACT)以及 Kato 编制的应对灵活性量表(the Coping Flexibility Scale,CFS)[3]。
灵活目标调整量表和耐力目标追求量表(the Tenacious Goal Pursuit Scale)是Brandtsta咬dter等人根据应对双加工模型(the dual-process coping model)的同化耐性应对策略(the assimilative tenacity coping)和适应灵活的应对策略(the accommodative flexibility coping)两大类应对策略而编制的。其中,灵活目标调整量表是评估个体在面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困境时灵活调整目标的行为,比如,目标下调,降低预期,自我提升等。从这些行为反应中评价个体的应对灵活性。Kato编制的应对灵活性量表则基于压力应对的交互理论(transactional theory),在这个理论看来,任何一个经受压力的个体都会试图解决问题,但是应对策略并不是总能带来预期的结果。如果当前的应对策略不能带来预期结果的时候,就需要采取评价性应对(evaluation coping),比如,重新理解压力环境、检测或评估应对的结果、放弃没有效果的应对方式等;当个体需要放弃没有效果的应对方法而选择另外的应对策略时,就需要进行适应性应对(adaptive coping),比如,选择可替代的应对策略,实施新的应对策略。这两种策略交互作用直至压力被解决。这个量表就是从这两个方面评价受测者的应对灵活性,聚焦应对策略的可变通性。
相对于其他两份量表,Bonanno等人更关注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甚至潜在可能的创伤事件时的行为反应。他们认为,应对灵活性就是当面对极端压力事件或潜在的创伤事件,个体能够使用不同类型的应对方式以达到良好适应的能力[10]。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经历了重大压力事件但仍然适应良好的个体更为灵活地选择了一些诸如转移注意、回避、展望未来、改变对事件的看法、解决问题等应对策略,促进自己实现心理复原,达到良好的适应状态。通过因素分析发现,Bonanno等人编制的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在315名可能暴露于恐怖暴力事件的以色列大学生中探索出两大类应对策略:事件聚焦和未来聚焦[10]。量表的二因子结构在另外106名美国大学生中也得到验证。通过比较个体在这两大应对策略的总平均值和差异值,可以评估其应对灵活性的水平和程度。国外已有多篇研究报告了这份量表的信效度以及应用情况,但是国内尚未见到有研究报告介绍此量表的中文版。鉴于此,有必要探讨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在评估大学生应对灵活性的适用性,检测其心理测量学的信度、效度指标。
既往的研究着重考察应对灵活性对个体社会适应以及心理健康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在特殊经历人群中探讨应对灵活性在促进个体心理健康或适应方面的积极作用。比如,Park等人在经历创伤暴露的韩国成人中调查发现,应对灵活性有助于缓解这些被试的PTSD和抑郁症状[11]。Cheng等人发现,应对灵活性有助于提升贫困人群的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12]。Kota在1770名日本大学生中发现,应对灵活性有助于缓解大学生自评的抑郁症状[13]。但是深入地考察应对灵活性作用机制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也就是说,应对灵活性如何促进个体提升心理健康水平,积极适应环境变化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明。鉴于此,在修订量表中文版的基础上,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考察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适应之间的作用机制。
二、量表中文版的修订
(一)量表中文版题项的翻译与定稿
原始问卷源于Bonanno等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量表中文版题项的翻译和定稿过程如下:(1)先请三名心理学专业的博士或副教授分别翻译原量表的项目,对比这三份译稿,形成量表中文版的初稿;(2)之后再分别邀请英语翻译专业的教师和留学归国的心理学专业老师进行回译;(3)对照英文版原稿和回译稿的差别,重新调整中文版译稿。最终形成20个题项的中文版定稿,并随机安排原版题项的顺序。
在测验题目的翻译方面,考虑到Bonanno等人在编制这份测验的时候,重点考察个体在面对潜在的创伤性事件时采取的应对策略及其调整的灵活性,且在编制过程中也没有选择经历创伤性事件的个体。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为避免修订过程中出现歧义,课题组认为翻译为压力事件更为妥当。因而将测验名称翻译为“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
(二)研究被试
为修订量表的中文版工作,先后三次对四川省部分在校大学生进行萃集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2190份。受测大学生的年龄介于18—24岁。其中部分被试来自汶川地震灾区。
第一次调查的样本(样本一)用于对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有效问卷有821份,其中,男生486人,女生335名。
第二次调查的样本(样本二)用于对心理复原力量表的结构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效度检验。有效问卷1309份,其中,男生600人,女生709人;非灾区大学生889人,灾区大学生420人。其中,有35位同学在3个月后重新接受问卷调查,以考察量表中文版的再测信度。
第三次调查的样本(样本三)有60名亲历汶川地震的灾区大学生中。使用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进行调查,以检验量表在高分组和低分组被试中的区分度。其中,高分组、低分组各30人。
(三)研究工具
1.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
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由Bonanno,Pat-Horenczyk和Noll编制[10],共计20个项目。受测者根据自己在面对可能的潜在创伤事件的行为反应和使用的应对策略,从“根本不符合”到“完全符合”(采用7点量表计分,分别计1—7分),选择贴切自己行为反应的选项。英文原版量表主要是有两个维度构成:未来聚焦(forward focus)和创伤聚焦(trauma focus)。在这个量表中,需要先统计未来聚焦和创伤聚焦分量表的平均分数,之后将两个分量表的平均分数相加,得到量表的总分(应对能力),再将未来聚焦分量表的平均分减去创伤聚焦分量表的平均分,差值取绝对值,得到应对极端化分数(coping polarity),最后再将总分减去应对极端化分数,便得到应对灵活性的分数。
2.心理复原力量表
采用Wagnild和Young编制的心理复原力量表(RS)[14]。该量表罗列了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过程中正面、积极的行为反应,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情况,使用7点评分方式进行评定,从1到7表示从“极不符合”到“完全符合”。该量表包括25个项目。量表总分介于25到175之间,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复原力越高。有研究表明,心理复原力量表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中各年龄段人群的心理复原力[15]。国内学者Lei等人曾在汶川地震灾区大学生中获得了该量表中文版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并提取出控制性、坚持性、效能感、独立性四个维度[16]。在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a系数为0.900。
3.大学生压力量表
该量表由李虹、梅锦荣等编制[17],用于测量大学生在校园里面的压力类型与程度水平,共有30个题目组成,包括学习压力(学习及考试烦扰,16个题项)、个人压力(个人的日常烦扰,10个题项)和消极生活事件(负性消极影响的应激性事件,4个题项)三个维度。量表采用四级记分(0=没有压力;1=轻度压力;2=中度压力;3=严重压力),理论分数范围是0—90分。分数越高,表明受测大学生的压力越大。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a系数为0.934。
4.应对效能量表
应对效能量表是由童辉杰编制[18],主要考察大学生在面对挫折或打击的时候自己的主观感受,共计17个项目。采用4点量表计分,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4分。该测验包括三个维度:胜任力、自信程度和认知水平。分值越高,表示成功应对困难或挫折的信心越足。在本研究中,总量表的Cronbacha系数为0.818。
5.情绪调节问卷
情绪调节问卷(ERS)是由国内学者王力等人根据情绪调节过程模型编制[19]。该量表考察受测者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两种策略对厌恶、愤怒、悲伤、恐惧和快乐5种基本情绪的调节情况。该量表共有14个项目,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各有7个项目。采用7点计分方式,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在表达抑制和认知重评策略上的分值越高,表示被试越常使用该调节策略。在本研究中,情绪调节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17。
6.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
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是由Watson等人根据情绪愉悦度维度编制的,郑雪等人在大学生中进行修订,测量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20]。修订后,最终确定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中文词语各9个,共18个题项。采用5点计分方式评定相应情绪体验的强度,1表示“非常轻微或根本没有”,5表示“非常强烈”。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总分范围介于9—45。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回答最近一周体验到相应情绪的程度。在本研究中,情绪调节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2。
7.积极心理健康量表
选用“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HC-SF)(成人版)”测评大学生的积极心理健康状况。该量表主要通过让受测者评价在过去两周到一个月之内自己出现所述行为的大体频次,以评估受测者在情绪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三个方面的积极心理健康状况[21]。共14个条目,采用6点计分方式,1代表从来没有,2代表每周1次或2次,3代表每周1次,4代表每周2次或3次,5代表几乎每天,6代表每天。本研究中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8。
8.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
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PTSD-SS)是由刘贤臣等人根据DSM-IV和CCMD-Ⅱ-R中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而编制的[22]。该问卷以自我报告的方式,考察PTSD的反复重现创伤体验、持续性警觉、回避与情感麻等症状,以及个体的主观评定和社会功能受损情况。量表共包括24道题,采用5点计分方式。在本研究中,要求被试回答从地震发生到现在的持续行为表现。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8。
(四)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PACT量表中文版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原版20个题项的因子结构;第二阶段是考察量表中文版的信度、效度;第三阶段则选择来自汶川地震灾区的部分大学生进行效度分析。
每一个阶段的问卷发放都是通过被调查学校的心理健康机构联系到所有的被试。在调查之前,告知所有的被试本研究的目的以及对他们的帮助。在征得他们本人的同意后,才开始在课堂上填写问卷。在自愿填写完毕之后,给予所有的被试适当的报酬。
使用SPSS 16.0和AMOS 21.0对数据进行因素分析、相关分析以及量表结构模型的验证。
(五)量表中文版的修订结果
1.英文原版中文版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根据Bonanno,Pat-Horenczyk和Noll[10]的研究结果,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在美国人群中获得两个因素:未来聚焦和创伤聚焦。在样本一中,按照原版量表的因子结构进行结构模型的验证, 各项拟合指数如下:χ2/df=7.554,RMSEA=0.089,NNFI=0.617,GFI=0.646,GFI=0.832,CFI为0.94,AIC=1389.661。结果表明,原英文版20个题项的量表并不适用于中国大学生人群,需要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进行修订。
2.中文版题项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采用主成分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的方法探讨量表中文版在一般大学生中的因子结构。首先,KOM统计量为0.833,说明各变量间信息的重叠程度较高;其次,球形Bartlett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3281.446(df=190,p<0.001),这表明相关矩阵并不是一个单位矩阵。KMO和Bartlett检验结果显示,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从原版的20个题项中可以提取出5个因子,共解释差异量的51.374%,结果表1。每个项目的因子负荷均大于0.4,项目负荷在0.418—0.750之间。但因为第2题和第13题出现了跨因子负荷的情况,且有两个因子的项目数量少于3个,因此,删除第 2、5、6、7、13、15题。 同时,为保持与原版量表的因子结构一致,删除第10、11、12 题。
从表1可知,第一个因子由1,3,4,9,14,18共6个项目组成,这些项目都描述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的行为表现,命名为“事件聚焦”。第二个因子由8,16,17,19,20共5个项目组成,这些项目描述的是个体在应对压力性事件过程中展望未来而进行积极调整的行为,命名为“未来聚焦”。
3.信度检验
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58(p<0.01),分半系数为 0.656(p<0.01)。 两个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714,0.685(p s<0.01)。
35名大学生参加两次时间间隔为3个月的测验,两次测验的数据相关系数为0.741(p<0.001)。这表明,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的测试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4.效度检验
在效度检验上,从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两个方面对量表中文版的效度进行检验。在结构效度上,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在一般中国大学生(n=889)和汶川地震灾区大学生(n=420)人群中对修订后11个题项的二因素模型进行检验。
在评价模型的适合性时,对模型的拟合度指标有所选择[23]。具体说来,本研究采用绝对拟合指数(χ2,RMSEA,GFI,AIC,BIC,ECVI),相对拟合指数(CFI,IFI)来评估模型的拟合程度。一般来说,RMSEA在0.08以下,GFI,IFI,GFI在0.9以上,拟合的模型便可以接受。量表(中文版)的各项拟合指数见表2。修订后11个题项的二因素模型在一般中国大学生和汶川地震灾区大学生人群中都可以接受,只是在一般大学生人群中的拟合指数要优于地震灾区的大学生。11个题项在一般大学生人群中的因子负荷结果,见图1。

表1 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n=821)

表2 量表中文版在一般大学生和灾区大学生样本中的效度检验

图1 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
在效标效度方面,参照既往编制和修订PACT量表的研究文献[10][24-25],在样本二中检验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的校标效度。结果表明,应对灵活性及其事件聚焦、未来聚焦两个因子与压力感、消极情感呈负相关,与应对效能、认知重评、积极情感、心理复原力、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呈正相关,结果见表3。

表3 应对灵活性与应对效能、压力、积极与消极情感以及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研究随机调查了部分经历汶川地震创伤暴露的大学生,选用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评估他们受到地震的影响,检查高分组和低分组在量表上得分的差异。结果如表4所示,高分组与低分组大学生在聚焦事件以及应对灵活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4 PTSD-SS高分组和低分组在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的差异分析
(六)分析与讨论
当一个良好的测量工具被应用于一个新的研究群体时,需要使用因素分析的方法考察在这个人群中的潜在结构的稳定性[26]。同时,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已广泛地应用于多个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但是国内尚未有研究报告该量表的中文版修订情况。另外,在样本一中进行的因子结构验证结果,也表明有必要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探讨该量表的适用性。
以往有的文献表明,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中,该量表的二因结构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比如,Pinciotti等人在322个美国大学生中发现,20个题项组成的二因子结构具有良好的模型拟合度[27],Park等人在韩国经历创伤事件的成年人中也进行同样的验证性分析,结果也发现量表的二因子结构具有良好的拟合度[28]。但是因子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Pinciotti等人在进行量表的验证性因素分析之后发现,尽管组成因子的题项不变,但是却形成了一个二阶因子结构[27]。这可能因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相同题项却属于不同的心理结构。比如,国内学者Lei等人在对心理复原力量表原版20个题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的时候就发现,在美国人群中形成的二因子结构却在中国大学生人群中转换成四个因子[16]。样本一的因素分析的结果也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类似。同样的题项却构成不同的因子。比如,第三个因子(“安慰他人”,“我会开怀大笑”,“让自己注意到或在意别人的需要”)反映了个体在应对压力困境过程中关注周围人的行为表现。这是典型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压力应对。中国人在面对压力事件的时候,会有“面子压力”,即个体会顾及因处理任何事件而可能对声望的影响[29]。虽然这种顾及“面子”的考虑并不是应对行为的目标,但却是一套应对的行为法则。不过为保持与原版量表的理论假设一致,最后只保留11个题项。很多量表在被修订中为了保持与原版量表因子结构相同而出现删减题项的情况,比如,郑雪等人在修订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的过程中,删除了2个题项[17]。从信、效度的检验结果来看,删除原版9个题项是可以接受的。
研究对这11个题项组成的量表效度进行考察。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11个题项构成的二因素结构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主要的拟合指数都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在校标效度方面,参考了既往研究结果,比如,Bonanno等人选用认知情绪调节、自我复原力作为校标之一[10],Knowles等人选用领悟压力感、积极与消极情感作为校标[24]。在研究中也采用了这些量表。同时,Hanssen等人研究就发现,应对灵活性能够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25]。从已有的研究来看,认知重评策略是积极情绪调节的一种方式,必然能够促进个体的应对灵活性;表现出应对灵活性的个体势必会增强自身的自我效能。基于上述结果,研究将应对效能、压力、心理复原力、积极与消极情感、幸福感作为效标。检验结果显示,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大体一致。另外,研究也选择了经历汶川地震的大学生来检验量表的区分效度。结果显示,PTSD自评量表高分组和低分组大学生在聚焦事件以及应对灵活性上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两组大学生在应对灵活性上的差别主要集中在聚焦事件方面。与Bartholomew等人[30]在PTSD组和非PTSD组人群中的结果是大体相同。
研究也检验了量表的信度。结果显示,作为团体施测的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半信度系数以及再测稳定性系数都是在0.7以上。这些数据大致与Bartholomew等人[30]报告结果是一样的。这表明该量表测量大学生的应对灵活性具有良好的稳定性。
三、应对灵活性的作用:中介变量,还是调节变量
(一)研究被试
1204人接受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138份。男生512人,女生626人;文科大学生413人,理科大学生490人,工科大学生235人。
(二)研究工具
1.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见第二部分“量表中文版修订”部分的工具介绍。
2.大学生压力量表。见第二部分“量表中文版修订”部分的工具介绍。
3.积极心理健康量表。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社会适应的含义有所不同,比如,重大灾害之后民众的社会适应就不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适应[31]。社会适应是青少年社会化的重要目标,也是衡量个体发展的重要指标[32]。一般将个体的心理健康作为社会适应的观测指标[33]。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趣,心理健康不再仅仅是指没有心理疾病,而是应该追求积极的心理健康状态,即积极心理健康[34]。本研究选用Keyes等人编制的“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HC-SF)(成人版)”测量大学生社会适应状况。量表的具体介绍见“量表中文版修订”部分的工具介绍。
(三)研究程序与数据分析
研究考察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大学生社会适应之间的作用。调查的方式也与第二部分的研究程序基本一致。所有被试也都获得了适当的报酬。
使用SPSS 16.0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调节效应的检验。
(四)研究结果
1.大学生压力感、应对灵活性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将大学生压力量表、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中文版)、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MHC-SF)(成人版)的各维度与总分进行Pearson积差相关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5可知,个人压力、学业压力、消极生活事件以及压力总分与应对灵活性、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呈负相关,相关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应对灵活性及其事件聚焦、未来聚焦维度与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呈正相关,相关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

表5 大学生压力感、应对灵活性与社会适应的相关分析
2.应对灵活性在压力和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
在理论上,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既可以起到调节作用,也可以起到中介作用。采用温忠麟等人对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程序[35],首先将数据进行去中心化处理,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年龄、性别、生源地、专业类别)的条件下进行层次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应对灵活性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
为检验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参考温忠麟等人的调节效应检验程序[35],采用分层回归分析,在对数据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生成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与应对灵活性的交互项。分别以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一步同时引入压力感和应对灵活性两个变量,第二步再引入交互项,通过新增解释量(△R2)或者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是否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来判断调节效应是否成立。

表6 应对灵活性在大学生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调节效应检验
结果见表6,在以情绪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交互作用项(情绪幸福感*应对灵活性)的回归系数达到显著性水平(β=-0.144,t=-5.177,p<0.001),且引入交互作用项新增解释量(△R2)也达到显著水平(p<0.001),表明应对灵活性能够调节压力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同样,在以心理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应对灵活性能够调节压力与心理幸福感的关系。但是在以社会幸福感为因变量的回归方程中,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社会幸福感之间没有调节效应。
在考察应对灵活性的调节变量之后,按照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26],考察应对灵活性是否在大学生压力感与社会适应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结果见表7。
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大学生的压力体验对积极心理健康的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但是应对灵活性变量纳入后,压力体验对积极心理健康的预测下降,但仍然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同时,应对灵活性显著预测了积极心理健康的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三项观测指标。应对灵活性在宽恕在压力体验和社会适应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应对灵活性的中介效应分别解释了因变量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社会幸福感方差变异的16.50%、16.43%、13.33%。

表7 应对灵活性在大学生压力与社会适应之间的中介效应
(五)讨论与分析
综合研究对应对灵活性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的检验结果,应对灵活性在大学生压力体验和社会适应三项观测指标之间的作用各有不同。具体来说,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体验与情绪幸福感、心理幸福感之间起到有调节的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压力体验与社会幸福感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与Park等人的研究结果[35]相似,应对灵活性在创伤亲历者创伤暴露程度与PTSD、抑郁症状之间起到中介作用,降低创伤对个体的负面影响。同时,Cecilia Cheng等人的一项针对应对灵活性的元分析结果显示,应对灵活性直接调节着个体的适应状况[3]。总的来看,应对灵活性能够影响并调节个体对压力的反应,甚至是在经历创伤的情况下。因此,在增强个体压力应对能力的同时,应该注重培养个体的应对灵活性。
但无论从元分析的结果,还是这项研究的结果来看,应对灵活性的调节效应量和中介效应量在数值上都属于中等强度。对于这一结果,Cecilia Cheng等人在系统进行元分析之后,认为与研究者对应对灵活性概念的认识有关[3]。从不同角度对应对灵活性的理解,得到的效应量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从效应量本身的意义来看,应对灵活性只是个体成功应对压力情境的其中一个因素。应对灵活性还可能与其它变量(如心理复原力)存在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在今后的研究中,综合考察具体背景因素,更为精细地考察应对灵活性的作用和效应。
四、总讨论
潜在可能的创伤性事件强调了压力事件的性质,即有可能但不必然会给个体带来创伤的压力事件。从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这样的事实,由于个体成长经历的差异,有些压力事件可能并不是创伤事件,但也有可能会给个体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在编制这个量表的过程中所选用的受测者选择直接暴露或间接暴露于恐怖暴力事件的亲历者,而不是表现出创伤应激反应的经历者。这实际上表明该量表可以评估个体在面对一般意义的压力事件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可以是面对创伤事件而表现出来的灵活性。因此,潜在创伤事件应对能力感知量表适用的压力事件范围更为宽泛。
压力应对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调节过程,涉及到的人格因素、应对技能、应对经历、社会支持等。从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应对灵活性在不同研究背景下或起到调节作用,或起到中介作用。这就意味着应对灵活性在压力与适应之间有不同的作用机制,需要结合具体的研究背景进行分析。今后的研究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应对灵活性与其他应对资源(比如,心理复原力、压力后自我成长、获得意义感等)的互相作用机制,为临床提供有效的干预方案。
另外,应对灵活性是近二十年来压力与应对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但是相比较而言,应对灵活性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学者们都看到应对灵活性的重要作用,但是对这一概念的理论理解和操作定义却不甚一致。虽然学者都是从应对过程的角度探讨应对灵活性,认同应对灵活性表现在两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但是哪两个应对过程,目前学者们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分歧。Cheng以及Kato就很清楚地说明,当前对应对灵活性的研究呈现多视角化的倾向[3][13]。今后的研究可以在理论层面上对应对灵活性概念的内涵做进一步的探讨和整合,也可以借助现代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探明应对灵活性的本质。
[1]Cheng,C.Assessing coping flexibility in real-life and laboratory settings:a multimethod approach[J].Journal of Personality&Social Psychology,2001(5):814-833.
[2]Kashdan,T.B.,& Rottenberg,J.Psychological flexibility a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health[J].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2010(7):865-878.
[3]Cheng,C.,Lau,H.P.,&Chan,M.P.Coping flexibility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changes:A meta-analytic review[J].Psychological Bulletin,2014(6):1582-1607.
[4]Roussi,P.,Krikeli,V.,Hatzidimitriou,C.,&Koutri,I.Patterns of coping,flexibility in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women diagnosed with breast cancer[J].Cognitive Therapy&Research,2007(1):97-109.
[5]Gan,Y.,Liu,Y.,&Zhang,Y.Flexible coping responses to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related and daily life stressful events[J].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004(1):55-66.
[6]Kaluza,G.Changing unbalanced coping profiles:A prospective controlled intervention trial in worksite health promotion[J].Psychology and Health,2000(15):423-433.
[7]Compas,B.E.,Forsythe,C.J.,&Wagner,B.M.Consistency and variability in causal attributions and coping with stress[J].Cognitive Therapy&Research,1988(3):305-320.
[8]Park,C.L.,Folkman,S.,&Bostrom,A.Appraisals of controllability and coping in caregivers and hiv+men:Testing the goodness-of-fit hypothesis[J].Journal of Consulting&Clinical Psychology,2001(3):481-488.
[9]Zakowski,S.G.,Hall,M.H.,Klein,L.C.,&Baum,A.Appraised control,coping,and stress in a community sample:a test of the goodness-of-fit hypothesis[J].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A Publication of the Society of Behavioral Medicine,2001(3):158-165.
[10]Bonanno,G.A.,Pathorenczyk,R.,&Noll,J.Coping flexibility and trauma:The perceived ability to cope with trauma(PACT)scale[J].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Policy,2011(2):117-129.
[11]Park,M.,Chang,E.R.,You,S.Protectiv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PTS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llowing trauma[J].Personality&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5,82:102-106.
[12]Atal,S.,Cheng,C.Socioeconomic health disparities revisited:coping flexibility enhances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for individuals low in socioeconomic status[J].Health&Quality of Life Outcomes,2016,14(1):7.
[13]Kato,T.The Impact of Coping Flexibility on the Risk of Depressive Symptoms[J].Plos One,2015,10(5):e0128307.
[14]Wagnild,G.M.,&Young,H.M.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testing of the resilience scale[J].Journal of Nursing Measurement,1993(2):165-178.
[15]Wagnild,G.A review of the resilience scale[J].Journal of Nursing Measurement,2009(2):105-113.
[16]Lei,M.,Li,C.,Xiao,X.,Qiu,J.,Dai,Y.,&Zhang Q.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resilience scale in wenchuan earthquake survivors[J].Comprehensive Psychiatry,2012(5):616-622.
[17]李虹,梅锦荣.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J].应用心理学,2002(1):27-32.
[18]童辉杰.应对效能:问卷的编制及理论模型的建构[J].心理学报,2005(3):413-419.
[19]王力,陆一萍,李中权.情绪调节量表在青少年人群中的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7(3):236-238.
[20]邱林,郑雪,王雁飞.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PANAS)的修订[J].应用心理学,2008(3):249-254.
[21]尹可丽,何嘉梅.简版心理健康连续体量表(成人版)的信效度[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5):388-392.
[22]刘贤臣,马登岱,刘连启,等.心理创伤后应激障碍自评量表的编制和信度效度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1998(2):93-96.
[23]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J].心理学报,2004(2):186-194.
[24]Knowles,L.M.,O'Connor,M.F.Coping flexibility,forward focus and trauma focus in older widows and widowers[J].Bereavement Care,2015(1):17-23.
[25]Hanssen,M.M.,Vancleef,L.M.G.,Vlaeyen,J.W.S.,Hayes,A.F.,Schouten,E.G.W.,& Peters,M.L.Optimism,motivational coping and well-being:evidence supporting the importance of flexible goal adjustment[J].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2015(6):1525-1537.
[26]Loewenthal K M.An introduction to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scales[M].Psychology Press,2001.
[27]Pinciotti,C.M.,Seligowski,A.V.,Orcutt,H.K.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PACT scale and relations with symptoms of PTSD[J].Psychological Trauma Theory Research Practice&Policy,2017(3):362-369.
[28]Park,M.,Chang,E.,&You,S.Protectiv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PTSD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following trauma[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15(82):102-106.
[29]朱瑞玲.“面子”压力及其因应行为[C]//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61-185.
[30]Bartholomew,T.T.,Badura-Brack,A.S.,Leak,G.K.,Hearley,A.R.,&Mcdermott,T.J.Perceived ability to cope with trauma among u.s.combat veterans[J].Military Psychology,2017(3):165-176.
[31]周炎炎,杨世箐.灾后移民社会适应状况评价——基于北川等地的调查[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81-86.
[32]李冬梅,雷雳,邹泓.青少年社会适应行为的特征及影响因素[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50-156.
[33]陈建文,王滔.社会适应与心理健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34-39.
[34]Keyes,C.L.The mental health continuum:from languishing to flourishing in life[J].Journal of Health&Social Behavior,2002(2):207-222.
[35]温忠麟,侯杰泰,张雷.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的比较和应用[J].心理学报,2005(2):268-274.
责任编校:万东升
Th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Undergraduates'Stress Adaptation
LEI Ming1,WEI Dongtao2,3
(1.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ounseling Center,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1756,China;2.School of Psychology,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3.Key Laboratory of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SWU),Ministr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Coping flexibility refers to one’s ability to effectively modify coping behaviors in the face of stressful situation or potentially traumatic life events.Although the research of coping flexibility started 20 years ago,little attention was attracted from scholars.The current researches focued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stress adjustment.In view of the current literature,the study revealed the positiv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college students groups in the face of stress.In Study One,the factor structure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PACT were investigated among undergraduates.The Perceived Ability to Cope with Trauma(PACT)Scale has two subscales that measure the perceived ability to focus on processing the trauma and to focus on moving beyond the trauma.The coping flexibility score represented the ability to use both types of coping.The 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scale provided a good basis for discussing the coping flexi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stressful situations.Totally,2190 Chinese undergraduates completed a set of scales,including the PACT,the Resilience Scale,the Stress Scale for College Students,the Coping Efficacy Questionnaire,the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the Positive Affect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and the Mental Health Continuum Short Form in Adults.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and concurrent validity were investigated.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2-factor model with 20 item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Americans was not replicated,and 2-factor structure including 11 items was suitable in the present study (χ2=206.303,df=43,RMSEA=0.065,IFI=0.901,CFI=0.920,GFI=0.960,p=0.000).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was 0.758(p<0.01),split-half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was 0.656(p<0.01),and the test-retest reliability coefficient is 0.741 (p<0.01),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 of two subscales was 0.714,0.685 (p s<0.01).The coping flexibility score,events focus score,and forward focus score were correlated negatively with Stress,Negative Affect,positively with Coping efficacy,Cognitive reappraise,Positive Affect,Resilience,Emotional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Social Well-being.Another 60 undergraduates,living in the earthquake areas,were recruited to complete the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elf-rating scale(PTSD-SS).Participants showed higher total PTSD-SS score,reported higher level of Event Focus and Coping Flexibility than those of low PTSD-SS score.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ACT was demonstrated to be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ment in assessing coping flexibility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Based on these studies,the positive role of coping flexibility in college students between stress and social adaptation was discussed in Study Two.Another 1138 participants attended.Results indicated that coping flexibility played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stress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well-being,psychological well-being,and partial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tress experience and social well-being.Research showed that coping with flexibility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ollege Students'stress adaptation.
coping flexibility;positive mental health;psychological resilience;college students;adaptation;well-being
G40;B849
:A
:1672-8580(2017)05-0071-16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2YJC190014)
雷鸣,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E-mail:jdleiming@swjtu.edu.cn)
DOl:10.11965/xbew2017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