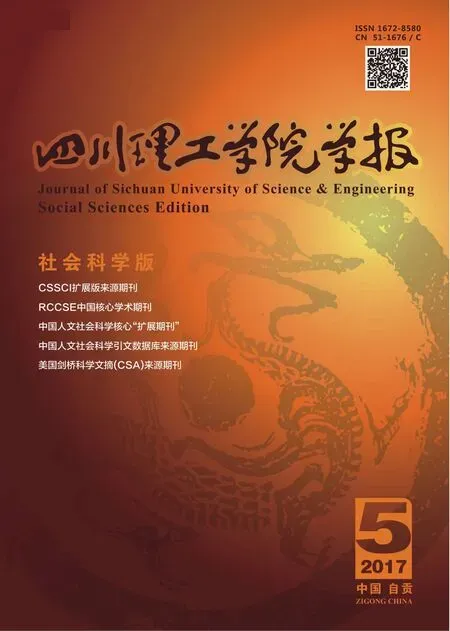法治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及其构建
——中国法治建设人力资源问题初探
李小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南京210004)
法治职业共同体的内涵及其构建
——中国法治建设人力资源问题初探
李小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南京210004)
推动法治建设,人的因素是关键因素。当前我国的法治工作从业者数量巨大、类型多样、素质良莠不齐。为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政策,需对中国法治建设人力资源实行分类管理、精细化培养,而开展此项工作的前提是对这一职业共同体的内在结构与群体价值有充分的把握。有机互动的职业共同体可有效实现社会整合。法治职业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法治的核心人力资源。基于对“中国特色”,“统一战线”等的考量及法治社会整合的需要,应加强法治职业共同体的构建。与“法律职业共同体”标准法定,成员特定的封闭结构不同,“法治职业共同体”更是抽象开放的精神共同体。前者关注“法律职业”功能发挥,树立法律权威,后者关注法治价值社会整合,促成法治信仰。内嵌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治职业共同体”,呈现出“团体格局为内核的差序格局”构造。构建法治职业共同体应秉持“法学院——用人单位”共构理念,坚持职业素养的持续提升,呈现理智仁爱的群体气质,追求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融通整合。应围绕综合性推进、知识理念一体化、阶段相衔接等关键环节,以法学教育为源动力,职业资格考试为风向标,职业培训为跟踪器,打造互洽协同的中国特色法治人力资源建构模型。中国法治职业共同体对内应关注各职业群体的素质提升、互动协调,对外应致力于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外渗融合。
法律职业;共同体;社会整合;人力资源;法治人才;法学教育
一、问题提出
推动法治建设,人的因素是关键因素。为高效发掘各类法治人才的智识、能力、个人价值,推进中国法治事业,各相关用人单位应借鉴公司企业对人力资源管理开发的先进理念,充分关注、科学规划法治人才的招录、培训、使用、流动、升迁、退休等职业发展流程;党和政府、法学院所、行业组织等则应从法治工作队伍职业共同体建构视角加强对从业者的价值、信念、思维、技能等的养成与整合;法治人才个人则应从个体兴趣、职业、志向等角度进行规划和行动,以不忘初心、追求卓越。
梳理过往,《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先后颁行,并于2001年全部修订,法官、检察官、律师的职业资格考试,统一为司法考试;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下称“法律职业资格意见”),将司法考试升格为“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这些为我国法律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价值引领。法律职业从业者从“行政化、地方化和大众化”,“泛政治化和多元化”,逐渐走向“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几乎与司法考试开启同步,法学界有学者发出“法律人共同体宣言”[1]3-30,点燃了学术群体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研究热情,霍宪丹、孙笑侠、贺卫方、何美欢、范愉等均著文讨论。2002年“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者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范围、性质、形成条件,法律职业共同体与法治之间的关联,发展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现实障碍、宏观思路、微观对策等展开深入探讨,形成一定的共识[2]。之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趋淡,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2010年的两本著作,即刘小吾的《走向职业共同体的中国法律人:徘徊在商人、牧师和官僚政客之间》和卢学英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引论》。近年来,伴随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以及前述“法律职业资格意见”的顶层部署,渐又有学者开展了对该专题的研究,如刘作翔、葛洪义、何勤华、程金华等均对法治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本文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展的对中国法治建设人力资源问题的初步思考。
“人力资源是指人所具有的对价值创造起贡献作用,并且能够被组织所利用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3]3,当前参与法治建设的人力资源数量巨大、类型多样、素质良莠不齐,而国家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针对不同职业类型,提出不同要求,一类是必须拥有资格,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一类是鼓励取得资格,如立法工作者、法科教研人员等。对这两类不同的法治职业从业者的管理要求和培养模式应有区别,各职业的职业规划路径也有差异,先前关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学术研究在很多时候无法涵盖研究对象,学术研究的张力不足;从职能部门和用人单位的角度来看,也无法很好地展开政策部署,并对人力资源实行分类管理、精细化培养。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一个新的共同体术语,即“法治职业共同体”,并将具体阐述提出此概念的内在意旨,分析其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联系与区别,在此基础上对“法治职业共同体”构建的相关理念和基本模型展开初步探讨。
二、“职业共同体”与“中国法治”
(一)“职业”“职业群体”与“职业共同体”
职业,按传统解释是指一个人在社会中所从事的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称之为“职业”的工作一般应区别于没有技术含量或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一个“职业”从业者应是有较强专业性的。职业在传统社会往往是与生存紧密相连的一种行为,当下在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的基础上,职业流动现象大为增多,职业与生存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但与个体兴趣爱好等的联系在加强。当然获取生活来源依然是职业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正因为此,才有学者概括道,一定意义上“凡以法律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都应该属法律职业”[4]。如此,当今的职业与人们的生活保持关联,具有专业性,与个人的兴趣爱好联系度增强,个体对职业有了规划意识,这种职业状态为职业共同体的建构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为了本文的论述,“职业”、“职业群体”与“职业共同体”等概念需要廓清。以下两点应予明确:第一,并不是每一群体都是职业群体。在讨论共同体问题时,不少学者喜欢讨论“农民工”,事实上这一群体各主体之间只是从业状态相似,并不存在一种确定的职业类种。这类主体即使是一个共同体,也是阶级、阶层意义上的共同体,而不是职业共同体。第二,并不是每一职业群体都可以或有必要组成职业共同体。“职业群体强调的是共同特性静态的简单聚合,而职业共同体强调的是共同特性动态的有机互动”[5]3,如果一个职业群体的工作技术含量和专业要求较低,或者从业者相互之间只是简单的劳动交流与协作,劳动内容分散且相对简单、独立等,那么该职业则不具备形成共同体的客观基础。职业共同体中从业个体的劳动技能和劳动规则“需要系统的理性知识的积累”,“劳动责任可能相同,也可能相悖,不管怎样,都不可能不发生联系”,从业者针对相同的工作目标,以大体相同的职业技能、职业规则进行交流、协作或对抗,相互之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常态性的有机互动。这种“常态有机互动”是指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存在有规律的制度性的互动必要,同时这种互动关系“已经如同生物有机体内部的生理组织那样相互依存,难分难舍”[5]3。如在狭义的法律行业中,侦查者、审查起诉者、裁判者、代理辩护者相互之间是不可或缺、牵制联动的工作共同体;在广义法治事业中,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释法者之间必须话语一致、理念互通,否则法治工作根本无法形成合力。
(二)职业共同体是实现社会整合的人力因素
对从事各种职业的社会主体进行职业类别划分,相同、相近或相关联的职业群体,基于专业、志业、职业目标等的一致性可以析出“职业共同体”。同时如严强教授所说的,这种研究“目的不是要简单地、平面地描述职业群体的类别与分布,而要探讨从职业群体走向职业共同体的逻辑与现实之路,并探讨职业共同体的构建对于改造社会主体结构的重大价值”[5]3。针对职业共同体之于改造社会的价值,李强教授认为职业共同体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他指出杜尔克姆“强调的就是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职业群体”,实际上是提出了“分工基础上的职业共同体”。而职业共同体,“内部具有实质的社会互动,是有真实意义的社会群体”,所以“当一个社会由于社会转型、社会规范巨变而变得分崩离析,人与人之间连基本的社会信任关系都失去了的时候。依靠什么能够重建社会整合呢?职业显然是最有利的渠道”[6]。个中原理,杜尔克姆的观点主要有:人们自我选择职业的力量会使相似心态的从业者进入相似的职业;职业所致的频繁互动会使人们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互动工作又使相同职业者之间产生合作和共享的价值观;基于职业的专业化培训和实践中的工作互动,从业者之间会产生同质化效果;相同或相似职责、义务可以使从业者形成共同追求的利益;职业群体内的行为范式,不断固化和明确,成为职业规范。同时他认为职业群体内分工越明确,各部分功能越细化,从业者相互之间越难以分割,人们越需要有机团结[6]。
(三)“法治职业共同体”是实现“中国法治”的人力因素
当前,中国法治已经离开了绝对工具主义的发展模式,向价值理念主义的方向发展。我国在法治建设的各方面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这些成就包括“把依法治国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确定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等[7]33-53。
在法治总目标不变的前提下,就法治事业,当前社会全力要做的是在已有成就基础上,继续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以公平正义为旨归的法治社会。然而公正正义是人类永恒辨析的价值命题,没有自然科学般绝对精确的答案,其“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背后有无数种解释,让人们“深感迷惑”[8]252。所以法治建设是没有终点的旅途,是需要法律职业从业者永远在场,不断诠释论证的人类交互的和谐状态。从国家和社会治理角度考量,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但这些都是实现法治的物力因素,良法需人制定、实施、遵守,正如海瑞在《治黎策》中分析的,惟有人法兼资,天下之治才可成。有学者指出,建设中国法治,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是重要任务,其中“建设宏大的法治工作队伍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组织和人才保障”[9]。这支“宏大的法治工作队伍”,首先包括法治专门队伍,即立法、行政执法、司法队伍;其次包括法律服务队伍,即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队伍;再次还包括建构法学理论、培养法治人才的法学科研教学人员等。
经过多年的制度构建和学术界不断呼吁,传统的法律职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如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制正在全面推进,律师行业则在市场的刺激下,数量、质量都产生了巨大变化,但对法治职业共同体建设无论理论研究,还是自主式推动都远未展开。比如对立法、行政执法从业者,对人民调解员、法学教研人员的主体性研究均不到位,特别是对党政机关内部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很少关注,而事实上很多地方性的法治建设统筹规划,这部分从业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的法治职业共同体初具模型,初显价值,但各方主体对职业共同体的主体扩大、价值优化,以及对职业共同体之于社会的整合功能是忽视的,对中国特色法治工作队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联等关注不够。
法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模式,是实现社会和谐有序的路径,也是一种价值追求和文化样态。当一种事业已经向文化价值的角度发展时,推动事业发展的主体一定是一个从知识、技术,到理念、价值、思维等高度统一的文化共同体。而如果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高度契合的共同体,我们必须努力使之成为这样的共同体,唯此才可能积淀和弘扬法治文化,有效地推动法治事业。
也就是说,实现“中国法治”的重要力量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法治职业共同体”。并且这一特殊职业共同体的价值还可挖掘更深。从社会学学者提出“共同体”概念之日起,所强调的就是其聚合、整合的功能,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很多基于兴趣、爱好、血缘等因素而聚合的群体,比如传统社会的宗族、家族、士绅等,日常我们经常所说的关系圈,如校友、老乡等,甚至自媒体时代所形成的“朋友圈”、网友、“粉丝”等这些都彰显着共同体研究者所述的聚合功能。特别是自费孝通先生始诸多学者深入研究过的中国乡绅群体,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对“国泰民安”的超稳定社会状态发挥着巨大的整合作用[10]91-98。以致到今天不断有学者还在寻找着替代乡绅群体的“新乡绅”群体,以继续发挥群体连接国家政权与基层民众的整合价值。在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背景下,众多职业共同体中,法治职业共同体无疑将发挥更大的整合价值,原因在于法治职业共同体在推进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是全方位、多角度介入社会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
三、“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
(一)“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联系
“为数不少的学者通过撰写学术论文的方式,讨论了法律人或者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相关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多将法律人的范围大致圈定为,包括法学学者在内的所有以从事法律事务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职业群体。”[11]9但各个研究者对具体的法律人范围以及各类法律人在共同体中所处的地位观点不一,有的认为法律人主要指“专门以研究法或法律为职业的”,从事“专门化的法律活动”的“职业化的法官、检察官和律师”[12]12;有的认为法律职业者是指直接从事与法律有关的各种涉法工作的人,通常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立法者、公证员和法学教授等,但法律职业的主体或核心成员仅指法官和律师,认为法官、律师、检察官占据着法律职业体系的核心区域,而法律顾问、立法者、法学学者等职业则屈居法律职业的核心区域所投射的阴影之中[13]。总体上学者们“对于法官、检察官、律师属于典型的法律职业、并构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核心成份并无异议”[2]。
也有学者依中国法律人“差序格局”结构为前见,认为“法律人共同体纯粹形态”下“法学者”是法律人共同体中的核心成员[5]70-109。其以费孝通先生分析中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概念为背景,描绘出了中西方法律人共同体的结构图。他认为西方法律人共同体的结构是由“律师、法官、检察官、法学者”构成的一个“捆柴火式”的“团体格局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四类职业者关系清晰,不会出现职责模糊不清的情形;而中国法律人共同体则是“涟漪式”的“差序格局式”共同体,即“把因引进西方法治文明的事实而被改变或受影响的人群比作石头所激起的波浪”,则这个共同体中最中心的涟漪是律师、法官、检察官,之后依次是具备法律职业资格身份的公证员、商事仲裁员、劳动或人事仲裁员,以及有职业资格不从事上述职业但对公共权力承担职责的人群,如直接组织、参与或影响立法的工作人员,对法官、检察官负责考核的执政党机关的公务人员,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人员等,此外还有法学教育工作者、法学者,在和法律有紧密联系的媒体谋职的工作人员,如法律编辑,政法记者,转播政法新闻的主持人,播音员等,最外圈是“对法治文明不拒绝、不排斥的人”[5]52-58。这种格局描述非常形象,但应进一步修正,原因一方面在于从我国当前的法治推进状况来看,有两个背景条件的出现,影响上述法律人架构:一是“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要“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建设对象涵盖立法工作者、行政执法者、法官、检察官,各类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法学科研教学人员等;二是“法律职业资格意见”中明确规定“法律职业人员是指具有共同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职业伦理和从业资格要求,专门从事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和法律教育研究等工作的职业群体。”要求“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公证员、法律顾问、仲裁员(法律类)及政府部门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应当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国家鼓励从事法律法规起草的立法工作者、其他行政执法人员、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参加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取得职业资格。”另一方面其未注意到现代意义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本土自发生成的理念,而是中华文明在一定的历史节点,主动或被动的对其他文明的接受、移植,即使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并且该类法治“是人类法治文明中独树一帜的奇葩,是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和实践体系”[7]10,但本质上必须是法治,中国法治必须保有人类法治文明的共识、基本的价值内核和制度内容。我们确实可以自信于此种类型的法治,因为我国法治确实不同于其他任一国家,但却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发挥着效用。因此中国法律人的共同体格局不可能也不应当是纯粹的“差序格局”,而应当是“团体格局为内核的差序格局”结构。
至此,本文所要讨论的中国语境下的“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联系就一目了然了,即“法治职业共同体”是以法治价值和理念为基本指引,建构并实践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和制度规范,以职业化为表征,以专业化为内质的职业共同体。“法律职业共同体”则是法治职业共同体中,由国家法律规定了严格的任职资格、清晰的职责内容,相互之间围绕法的运行存在法定的互动制衡功能的职业从业群体,这些职业群体自成一个独立的共同体,是法治职业共同体的内核。
(二)“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区别
首先,“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成群体不同。尽管说“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治职业共同体”的内核,但笔者并不主张将二者关系定位为绝对的属种关系,因为二者的群体构成标准不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群体构成标准参照“法律职业资格意见”的规定可概括为:依法应当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方可入职的,专门从事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服务等工作的职业群体。此处的“依法”应是依狭义之法,因为对法律职业从业者进行资格控制,本质上是行政许可,依《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应由法律设定,目前《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公证法》等法律中对相应的从业者的入职资格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是无可争议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除此外“法律职业资格意见”中规定的“法律顾问、仲裁员(法律类)及政府部门中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人员”,也应当取得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的政策要求,则应通过全国人大修改《仲裁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或通过专项决定的形式进行落实。一旦立法确定,这部分从业者也即成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法治职业共同体”的群体构成标准借鉴“法律职业资格意见”的规定可概括为:接受过系统的法学专业教育和法律职业培训,具有从事法治推进工作的专业技能、职业伦理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以及从事法律法规起草的立法工作者、行政执法人员、法学教育研究工作者等涉法类职业从业者。该共同体的基本标志是:法学专业、法治思维、法律职业伦理、涉法类工作等,依此一般来说除上述已列出的成员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人民调解员、党政机关内部专门从事法律事务的工作人员等均可视为共同体成员。
有学者提出“依法治国者”这一概念,其将治国者定义为“手中有权力‘治国’,并且直接处理国家法律事务或者影响国家法律事务处理的人……外延上既包括国家的立法者、执法者和司法者,也包括在领导岗位上行使公共权力并影响国家法律事务处理的党政干部”,其文章关注的主要是俗称“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14],这部分人是否是共同体成员,应以职业内容和专业背景作为判断因素。总得来说,法治职业共同体的主体范围不宜过于宽泛,如“对法治文明向往、追求的人”,“对法治文明不拒绝、不排斥的人”[5]58,“依存于法律(包括人对法律的期待与遵守)……受制于法律的人”[15],等等,不宜作为职业共同体成员的判定标准。
其次,“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客观形态不同。“共同体”是一个“常态性”的“有机互动”群体,组成共同体的每个个体作为个性化的自然人存在差异,同时共同体内部各职业群体的职责分工同中有异,各自以相对独立的职业模式协同服务于共同体整体的价值追求。所以不同的职业共同体,所呈现的客观形态亦不尽相同。根据如上的成员标准,“法律职业共同体”是一个边界清晰、成员特定的封闭式共同体,其成员是必须具备国家认可的法律职业任职资格才可入职的特定从业者。这一职业共同体中的个体在推动法治建设工作时,相互之间的互动行为模式是法定的,其法治参与行为有明确的制度性约束。“法治职业共同体”则是一个开放式的群体,一定意义上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虽然有职业、伦理、专业等识别标签,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内核,但法治职业共同体本身没有统一的制度性文件或共同体论纲等,群体无法有绝对明晰的边界。
第三,“法治职业共同体”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价值关注不同。对“法治职业共同体”我们应当关注其“共同体”价值,对“法律职业共同体”我们应当关注其“法律职业”价值。因为“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理念模式、交往范式,需要不特定多数人去创设、倡导、践行并最终形成合力,而这正是作为“共同体”的法治职业群体价值所在;又因为法治具有工具价值,也是一种客观实在,需要具体的“法律职业”从业者按照法律科学所设计的最优架构各司其职、相互协作。在“差序格局”法律人共同体格局下,如果激起涟漪的是某个具体案件,本不应混乱的法律人涟漪圈,因为团体界限不明晰,处于外圈的官僚政客、法学学者等往里圈挤压,核心圈的法官、律师等往外圈靠,这极有可能扭曲法治的公开正义追求[5]56。而在法治职业共同体中则可以最大化地避免这种可能的扭曲,因为尽管有些共同体成员的行为依然会突破其本身的职业界域,给共同体的整合价值带来不利,但作为“团体格局”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与“团体格局为内核的差序格局”的“法治职业共同体”因构造不同,个案式的突破很难对团体的格局带来根本性或制度性的不利后果。
(三)提出“法治职业共同体”概念的价值
长期以来,不但学界一直关注着“法律人共同体”、“法律人之治”等问题,执政者也一直重视政法队伍建设,但在社会转型关键期,仅仅关注政法队伍建设,对法治工作的推动已经远远不够。治理语境下的依法治国,强调多元主体的多元参与,因此“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即“法治工作队伍”。学术界在这一背景下,有必要跟进探讨法治工作队伍如何培育、整合等问题,但在展开进一步探讨前,首先应解决的是术语问题。
与“法治职业共同体”相关联的学术术语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为什么在学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已经到了一定层次,甚至如学者所说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构建已经是“一步之遥”的最后或关键时刻[16],又提出“法治职业共同体”这一概念呢?
首要的考量是“中国特色”。我国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人力资源状态与其他各国的状况就有较大的差别。比如在中国推动法治事业良性发展的最关键的人员可能并不是立法者或司法者,而是“依法治国者”或者“关键少数”[14]。又比如中国的法律职业从业者有独特的国别特征,即要有“共同的政治素养”。按“四中全会”的指示,不但针对传统语境中的“体制内”共同体成员,要求“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体制外”的律师等法律服务职业群体,也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法治作为律师从业的基本要求,增强广大律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还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全方位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阵地”,致力于“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法学教研人员。在中国推行法治建设,一般是中央首先完成顶层设计,发出倡导指示,之后由立法机关进行制度确定。故从法治工作的组织架构角度来看,各级党委政法委、各地的依法治省(市、县、区)领导小组等法治工作的组织、协调、核查等职业群体,也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人力资源。“党委政法委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组织形式,必须长期坚持”,领导小组等高规格的“非常设机构”要负责各地法治工作的“部署、指导和检查,推动工作落实”[17]302,324,如果我们在研究中国法治建设人力资源时忽略这类职业群体,那么我们的法治职业群体的聚合功能就会减损。
次之的考量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之价值,在中国语境下是耳熟能详的,任何一项工作,如果有了“统一战线”,那么就有了“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共同体的存在之义即为整合力量,那么即使是为了法治事业扩大同盟的需要,也应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具有共同专业背景的相关职业从业者纳入共同体中。在这一构想下,法知识权力拥有者主要负责“创造并生产法学知识”,释明法治困惑,评价司法现象、参与立法进程[18];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主要负责互相制约、协同推进法治实践,力保在行政执法、刑事侦查、起诉、裁判,诉讼和非诉纠纷解决程序中都能树立法的权威;其他分散在各种涉法岗位上从事法治工作的人员亦各司其职。所有职业者结合成一个共同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过程中,才能形成合力,协同推动事业的发展。此外,随着科技进步,一些新类型涉法职业在渐次出现,理查德·萨斯坎德教授就乐观地为受过法律训练的年轻人展示了各种新涉法职业选择,如“法律知识工程师”、“法律流程分析师”、“在线纠纷解决师”、“法律风险管理师”等[19]129,而且这已经不是未来,“未来已来,只是尚未铺开”[20]3。作为一个开放性的职业共同体,未来更多的涉法职业类型出现,只要符合共同体的特征,成为共同体成员均无障碍,这既有利于共同体的创新发展,亦可为新型职业提供专业的支撑,以利于我国法治事业的现代化转型。
再次的考量是学术研究的理顺。过往学界基于“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术语开展研究,一方面目光较多聚集在“法律”这一专业角度,而在职业共同体的研究视域内,专业当然需要关注,但同时更要关注“共同体”的价值,在强调相同的思维方式、职业技能、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要关注法治事业推动的功能性,环节的完整性,特别是法治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互相配合与协调问题。另一方面较多进行“内向”式研究,围绕着法官、检察官、律师三者展开,当试图进行“外向”式研究时,鉴于术语的涵盖能力不足,很多时候分析论证无法理顺,研读有关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学术文献时,可以发现研究者在对“法学家”、“立法者”等群体进行讨论时,往往或蜻蜓点水或欲说还休,研究的腿脚无法伸展。
基于如上考量,加之中国式法律人职业共同体形成的根本性机制或“超常规体制”[16],决定了推动共同体价值发挥的力量不能仅仅是来自当前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那么就需要对传统意义上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主体范围进行合理扩容。扩容之后共同体以何种术语代称,笔者斟酌可取的词汇即“法治职业共同体”。其原因,一是通过多年的学术论辩和实践摸索,我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完成了从工具主义向价值主义的提升,动态的“法治”更能代表法治追求的本质,“法律”一词的内涵相对狭窄,也应当特定化。二是“法律职业共同体”过往的研究所指多为法官、检察官和律师这一狭义的法律职业范畴,并且已取得较好的研究共识,如果职业主体范围扩大时,继续沿用“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概念并进行广义解释,则会导致原有的研究成果出现涵盖能力不足的问题。选择“法治职业共同体”这一术语,“法律职业共同体”可特指过去学者习惯指称的共同体特征更为明显的几类法律职业,“法治职业共同体”则指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参与法治建设工作的职业群体。三是便于通过宣传推动共同体聚合。在我国口号、标语具有极强的宣传价值,对力量整合具有特殊作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必须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工作队伍”,称之为“法治职业共同体”,是极具感召效应的术语。
“如果主客观条件暂时无法保证法律职业者做到内心对法律的确信与尊重,或者,现实不允许他们忠实执行法律,他们之间又无法找到妥协的方式”,那么,依法办事的矛盾就是不可弥合的,法律人“也就不可能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共同体”[16]。亦即建设法治社会狭义法律职业共同体根本无法自顾,必须在更大范围内有更多职业同行支持、协助才能实现在狭义范围内的“法律的统治”。所以“法治职业共同体”既是一个理论上可以存在的概念,也是对法治建设具有功利价值的概念。
四、“法治职业共同体”构建的理念校正
(一)摒弃法学院全能观,建立“法学院——用人单位”共构理念
有学者指出中国法学教育的“问题”有“准入门槛过低”,“与职业技能教育完全脱节”,“欠缺通识教育”,“欠缺职业伦理教育”等等,认为“法学教育必须以职业为导向,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法律知识教育、职业技能教育和职业伦理教育的三位一体”[21]2-4。各法学院为了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纷纷增设了模拟法庭、诊所式教育等教学内容,积极推进和实践部门人员互聘计划等。在笔者看来,这种努力可以为之,但无须过度,法学教育与实践的连接,能起到了解实务场景,明确法律职业分工及工作效能的判断标准,熟知法律专题的相关法理与法律规定即可。在此过程中给学生建立起法学专业实践性基本理念,其核心的实务素养要在实践中由任职单位负责。
换言之,法学院并不一定要将法律人的全部素养养成,法学院应专注于法治职业所需要的核心素养的培养。“核心素养”是一种胜任力,是一种经过大量专业知识熏陶之后而沉淀在受教育者身上的解决复杂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综合性能力,而不只是专业技能的娴熟。当然核心素养的养成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应该是基础,但何种知识和技能是养成核心素养的关键,是法学教育者应研究并做出取舍的。对学生来说,是滚瓜烂熟于更新极快的各种法条重要,还是具备法治思维理念,学会在具体的做事做人、交往互动中融汇贯通这种法治思维重要,是不言自明的。正因为此,尽管笔者赞成法学教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职业培训互动对接,但对“一个从事法学教育的老师,从来没参加过司法考试,怎么能确保教学内容跟学生未来的法律职业产生紧密联系?”的质疑不以为然[22]71。对此何美欢教授的观点值得借鉴,她认为“真正的专业法学教育并不教授实务技能,并不仅教授法条”,而是“学术性的”、“博雅的”,“学院里的教育任务不应是将一切现存内容传授给学生,而是装备他日后终身自学”[23]1,8。
当然,笔者并不是二元思维,主张非此即彼开展法治人才培养,而是说要有取舍侧重,毕竟分工已经成为社会常态,并且与职业实践相关的知识、规范、经验和技巧“往往是具体化的、情境化的、甚至个人化的知识,因而是难以言之于书,授之于课堂的。正所谓,怎么讲也讲不明白,一做起来就全明白。学习者必须亲身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请教、领悟、体会。因此,法律职业训练不宜于在学校的课堂上、乃至于模拟的环境(如模拟法庭)中进行,而必须在法律实践这个活生生的课堂上进行。”[24]最理想的状态是法学教育与法治人才用人单位的职业训练犬牙交错、和谐对接、各司其职,共构共同体。为此,法学教育的各类实习环节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是连接法学教育与法治工作的关键环节,但当前法学院教育中对该模块的教学安排并不尽如人意,无论是日常教学中的实践教学,还是毕业前的实习环节,形式化现象都较严重。
(二)剔除“完人”情节,坚持职业素养的持续提升
法律是平衡社会主体权益的技术,法治是追求公平正义的价值体系,人们天然地认为受过法学教育,熟知法律规范的法治职业从业者应当道德高尚、公正严明,对共同体成员存在技术与道德上的高标准要求。事实上因为评价体系和标准的多元,世界上很难有“完人”,同时知识可以型塑人格,但知识的价值追求与人的品格并不必然对称,掌握平衡利益之术者并不必然就能公平正义,熟知法律知识者也不能保证不触犯法律。社会主体对法律人不宜做“完人”苛求,惟此才能给法律人适度宽容,不因某些法律人出现问题而否定共同体,也不因某一时段法律人的群体性不振而对法治失去信心。同时法律人亦不应以“完人”自居,在处理法律事务时刚愎自用,忽视证据、程序、规律,以及其他共同体成员的意见和建议等。事实上,法治职业从业者的知识技能获得与职业伦理道德养成模式与其他社会主体并无差异,其需在长期的职业发展过程中,不断提升修炼,在此过程中,良好的共同体有机互动是核心推动力。
(三)淡化“精英”想象,呈现理智仁爱的群体气质
托克维尔在讨论美国的法律人时,谈到他们“在研究法律当中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独辟一个行业,在知识界中形成一个特权阶级。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或缺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的习惯,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除此而外,他们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团体”[25]303,“他们的法学知识,早已保证他们可以在同胞中出人头地。他们的政治权力,可以把他们推上高人一等的地位,并使养成特权阶级的习性”[25]309。在我国则有不少学者将法律人的职业化、专业化理解为精英化,认为法律职业可通过垄断性促进精英化,进而提升法律服务的质量[24],或者认为法律人通过法学教育获得了“职业语言,职业知识,职业思维,职业技术”之“才”,“职业信仰和职业道德”之“德”,法律人之治就不会走向人治[12]54。在笔者看来,这种推理并不周延,因为“才”养成与否是一个变量问题,“德”具备与否是一个超验的问题。
法治职业共同体是社会大架构中一个特别重要但并无特权的协作团队,“法律职业卡特尔”[26]54在我国既不可能,也并不值得推崇,反而应警惕。法治的追求是高尚的,法治的推进则是具体的,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等也决定了精英化的定位,并不适合中国特色法治工作者,构建法治职业共同体应淡化从业者的精英化色彩。中国的法治职业共同体成员宜向社会呈现理性、智慧、仁爱的群体气质。“法律和法院在国家中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智和道德功能在个人身上的延伸,个人凭理智和道德将其经历转化为行为准则。做什么是对的,什么事又是最该做的,完全由他个人决定;如果他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他会坚持这些原则,抵抗感情和激情的欲望。”[27]145理智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会目标明确,精准导航,拨开蒙蔽的法治天空中的身分、地位、人情、面子等各类影响因素,毫不动摇地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权威。仁爱的法治职业共同体,会关怀终极人权,呵护实质自由,承受被误解被放逐的委屈,在各种法律实践场域,将公平正义的法治价值理念客观化,促成法治的信仰。
(四)改变“机械独立”的共同体思维,追求与其他社会主体的融通整合
“机械独立”的共同体观念中,一是追求共同体的纯粹,认为“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公证员”是“正规化的法律工作者”,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人,主张“大学法学教育的目标可以瞄准”这部分人[28]1-4;二是要求每个成员的共同体属性要纯粹,比如法学教研人员,是教育职业共同体或知识分子群体中人,所以就不宜归属于法律人职业共同体中。
构建法治职业共同体,应拓宽视野,向内专注于共同体的专业性,向外致力于共同体的整合性。对任何一个从业者或职业群体来说,其角色定位不外乎横向关注社会分工,纵向关注社会分层,在社会群体纵横交互的模型中,一定数量和类别的人可共处于某一界域,虽然个体的归属界域可能并不唯一,但当我们讨论某一职业内容时,这个主体的界域是可特定化的,比如讨论法学家的法学观点我们一定是将其视作法治职业共同体成员,而讨论教育教学技术时,则是将其视作教育职业共同体成员的。我们应当明确,人的角色定位是一个抽象的型构,是一个基于概念的演绎,不是客观模型,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唯一的点。
按滕尼斯的说法,精神共同体是“真正属于人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29]65,精神的养成靠强调和认同,前者必须宣讲、灌输,需要外力强加,后者需要共同体成员内省为之,所以建构法治职业共同体重要的是加强法治职业共同体的研究,达成共识,并且不断宣传和使用“法治职业共同体”这一号召性、宣示性的概念,在整个社会,特别是相关职业共同体群体内形成情感共识。一旦诸多个体拥有共同体的“观念和利益,情感和职业”,他们“就会带有某些相似性,就像有一种力在推动他们一样”,“彼此相互吸引,相互追求,相互联系,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一般社会中的一个有限的群体,而且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旦这种群体形成了,任何事物都阻挡不了这种恰如其分的道德生活演化下去,同时,这种生活也成了促进它产生的特定条件的标志。”[30]21简言之,内在情感认同促成共同体形成并实现群体对社会整合浸融,这种状态又反哺共同体完构。
五、“法治职业共同体”构建的基本模型
各法域基于不同的权力架构和文明传统,法治职业共同体的构建模型也不同,比如英、美等国是典型的一体化模式,德、日等国则是“同训同考”基础的上二元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各国都对从业者设置了严格的入职条件,对法律人提出了较高的职业道德要求,其法律人的培养都是由“学科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共同组成并完成的,大多采用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分阶段、相衔接的教育培训制度”,即素质教育、专业教育、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一体化模式[31]。
这种模式的关键问题是综合性推进、知识理念一体化、阶段相衔接,我国的法治职业共同体构建也需要重点围绕这几个问题下功夫。在客观条件上,虽然我国没有类似美国律师协会(ABA)那样高效的行业管理主体,但我国综合性推进某项政策的效率远大于行业组织。目前来看,“四中全会”对“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作出了部署,为综合性推进法治职业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只要这种支持有可持续性,那么关键问题就是保证政策落实的专业性。在笔者看来,应该从“知识理念一体化”角度着手,我国的法治建设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实践体系等如何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下不背离“法治”的基本规律,这是需要法学研究者、法治工作推动者去协力解决的问题,法治职业共同体必须形成基本共识,并且在这些共识基础上加强互动、不断商讨,将共识制度化,进而从共同体共识向社会共识演化。“阶段相衔接”则是一个共同体建设综合性推进的技术性问题,难度最小。
从实践性角度来研究,建构法治职业共同体,目前可以考虑的手段不外法学教育、职业资格考试、职业培训,这三者中法学教育是共同体构建的源动力,职业资格考试是风向标,职业培训是跟踪器。源动力、风向标、跟踪器三者“三位一体”,互洽协同培养法律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法治职业共同体的基本建构模型。对此较早已经有研究者意识到了法学教育、司法考试、职业培训是三位一体的,指出三者之间应相互适应、配合、促进、协调发展,但其并未对三者之间如何协同培养法治人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32]。后续有较多学者探讨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之间的互动问题,但较少有将职业培训加入研究视域中者。也有学者注意到了霍宪丹的前期研究,但却将三者关系理解为线性、链条式关系[33]。
事实上,三者对法治人才的型塑并不总是线性展开,而是互洽协同的。法学专业教育要保证供给法律资格考试合格、足量的应试人才,也要支持职业群体的学历学位类培训。职业资格考试引导法学教育的内容、形式,同时为法律职业进行入职把关,储备法治人力资源。职业培训则应针对法治职业在职人员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培训要求,通过分立合并等多元组合方式开展培训。进言之,法学专业教育以综合开展学科知识教育为主,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是选择和储备法律职业人才的手段,职业培训重在管控法治从业者的职业伦理并提升其职业技能,三者协同、互促才能成就法治从业者的专业化、正规化、职业化以及一体化。三者发生作用的方式和机理各不相同,法学专业教育应保持其基本的自主自治,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作为“法学”教育,法律语言、基本法理和法律解释、推理等法律技能是基本内容和当然重心。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本质上具有行政许可意义,意在考核把关,国家应通过对考核内容的设置筛选出有利于推动和实施国家法治政策和理念的,具有法律专业技能的人才。入职和职业发展培训则是为确保法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而强制开展的提升行为。对法学专业教育国家权力应较少介入,以促进学术繁荣;在资格考试中宜通过对考试内容的控制,实现理念与知识的权力引导;在职业培训中则可对从业者职业素养提出强制要求。
这一模型的打造,重点是专业教育、职业资格考试、职业培训在共同体培养过程中的互洽协同。法学专业教育规模、布局、结构等问题重重,各界均有共识[34],因此如何破除现实格局,按理想的一体化架构开展专业教育是首要问题。其次法律职业资格考试需要解决新旧制度的衔接,立法、行政执法等从业者的资格考试引导,职业伦理、职业道德以可见的形式考查等一系列问题;再次,应推动职业入职培训和职业发展培训的衔接,建立以培训考核登记为支撑的涉法职业从业者全方位动态管理机制。
这一模型的打造,难点为“一体”实践的体制困境。当下法学专业教育、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法治职业培训的主管机关各不相同,由哪个主体统筹推动协同机制运行是一个体制困境。学者曾提出“建立非政府的全国法律教育专家委员会”[35],司法部恢复设立“法学教育司”[34]等设想,但至今法治职业的职业发展类培训推进主体依然是各行业主管部门、行业自治组织或各用人单位。法学专业教育则是“教育部门宏观管理、司法部门行业指导、教育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法学院自主管理”的“四位一体”模式[36]。同时从法治职业群体的身分来看,有体制内外、公务员与事业编制人员等不同类型,在我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机制没有完成一体化之前,综合推动法治职业共同体构建,在很多方面需要突破。
六、结 语
综上,一个以职业化为表征,以专业化为内质,有相同的价值理念指引的开放的“法治职业共同体”,既解决了学术研究术语混乱、涵盖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为中国特色的法治建设事业构设了一个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未来,中国法治建设人才队伍,对内应关注共同体内各职业群体的素质提升、互动协调,对外应致力于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外渗融合,推动法治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的交汇,一步步地将中国的法治向前推动,保证不走偏不走样,以与世界法治文明同步契合。这个共同体的构建,既要集中精力主抓“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以“法律职业资格意见”为指引,通过对法学教育内容和资格考试内容的综合设计,培养、遴选出职业能力与职业道德最优的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推动国家的司法进步,树立法律权威;也要兼顾主体范围更大的“法治职业共同体”建设,加强对共同体成员的价值理念整合,以法律人“共同体”价值发挥为追求,通过法学理论供给、法学教育托底、法治文化传播、法治政策部署,法律规范制定、法律实践推动等,服务于“中国法治”这个共同体的本质旨归。
[1]强世功.法律共同体宣言[M]//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
[2]强昌文,颜毅艺,卢学英,等.呼唤中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国法治之路与法律职业共同体学术研讨会综述[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5):151-156.
[3]邹华,修桂华.人力资源管理原理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4]刘作翔,刘振宇.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认识和理解——兼论中国式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角色隐喻及其现状[J].法学杂志,2013(4):95-104.
[5]刘小吾.走向职业共同体的中国法律人:徘徊在商人、牧师和官僚政客之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6]李强.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学术界,2006(3):36-53.
[7]李林.中国的法治道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8]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9]张文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纲领——对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认知与解读[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1):5-19.
[10]费孝通.论绅士[M]//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
[11]李小红.法学学者的法治参与[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2]孙笑侠,等.法律人之治[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13]公丕潜,杜宴林.法治中国视域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J].北方论丛,2015(6):144-148.
[14]程金华.依法治国者及其培育机制[J].中国法律评论,2015(2):107-119.
[15]胡玉鸿.法律人建构论纲[J].中国法学,2006(5):31-46.
[16]葛洪义.一步之遥:面朝共同体的我国法律职业[J].法学,2016(5):3-12.
[17]侍鹏.法治建设指标体系解读[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8]李小红.法学学者的知识权力问题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16(12):85-91.
[19]理查德·萨斯坎德.法律人的明天会怎样?——法律职业的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0]严青,等.遇见法律知识工程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21]郝艳兵.法治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22]何勤华,唐波,戴莹,等.法治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3]何美欢,等.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
[24]黄文艺.法律职业的特征解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3):44-49.
[25]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6]理查德.A.波斯纳.超越法律[M].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27]罗伯特·N.威尔金.法律职业的精神[M].王俊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8]刘坤轮.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衔接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9]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0]爱弥尔·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M].渠东,付德根,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1]霍宪丹,刘亚.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上)[J].中国律师,2000(12):67-70.
[32]霍宪丹.法律职业的特征与法学教育的二元结构[J].法律适用,2002(4):9-11.
[33]李红海.统一司法考试与合格法律人才的培养及选拔[J].中国法学,2012(4):54-72.
[34]王健.构建以法律职业为目标导向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法律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J].法学家,2010(5):138-155.
[35]霍宪丹,刘亚.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二)[J].中国律师,2001(1):48-49.
[36]袁贵仁.创新法治人才培养机制[N].人民日报,2014-12-12.
责任编校:万东升
The Connot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the Rule of Law——A preliminary study on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Li Xiaohong
(Institute of Law,Jiangsu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Nanjing,210013,China)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the human factor is a key one.At present,the number of professional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is huge but they are varied and different in quality.To implement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policy,it is necessary to classify,manage and refine the legal talents,and the premise of this work is to fully grasp the inner structure and the group value of the professional community.Interactive professional community can achieve social integration effectively.Professional of the rule of law is the core human resource to realiz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For the purpose of integration of a society by law and due to the need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united front”,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be constructed.Different from “leg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 which has a distinct boundary and exclusive structure with specific members,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the rule of law is abstract,open,and ideological.The former focuses on the function of “legal profession” and establishes a legal authority,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value of social integration and fosters the faith in the rule of law.Embedded with legal professional community,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the rule of law is featured with the structure of“pattern of difference sequence with group sequence as the kernel”.In order to construct professional community of the rule of law,law schools and employing units are supposed to collaborate to achiev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rofessionalism,cultivate social morals of reason and benevolence,and pursue integration with other social subjects.Besides,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such key steps as comprehensive promotion,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ideas,connection by steps,to the source power of legal education,to the signpost of vocational qualification examination,and to the tracker of vocational training,all of which aims to facilitate the model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for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manner of negotiation and collaboration.Professional of the rule of law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quality promotion,interac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all professional groups,and shoul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 influence of community values.
legal profession;community;social integration;human resources;talents for the rule of law;legal education
D901;D902
:A
:1672-8580(2017)05-0042-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4BFX006)
李小红,博士,博士后,副研究员(E-mail:lixiaohong@jsass.org.cn)
DOl:10.11965/xbew20170503
- 四川轻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习近平高等教育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