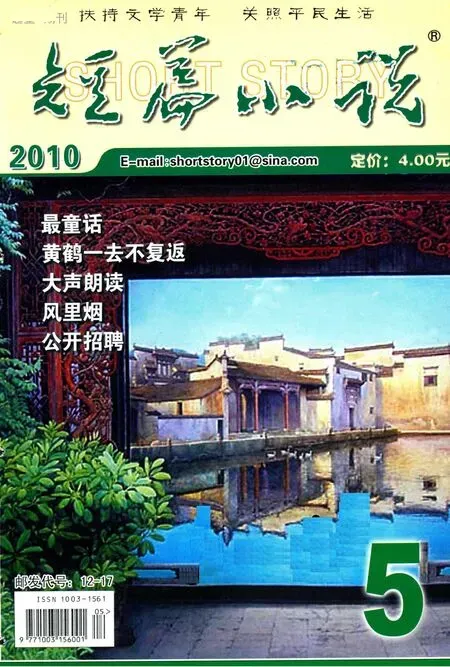寻找时光深处的鱼
◎钱 静
寻找时光深处的鱼
◎钱 静
钱静,男,生于1976年,云南省作协会员,现居云南武定。主要从事小说创作,曾在 《滇池》、《安徽文学》、《山东文学》等杂志发表小说多篇。

1
徐贵打电话给弟弟徐强说,回来,我活不过两天了。他说得平静,波澜不惊。不过,刚说完,他就感觉不自在,像一根树枝在胸口上撑着,但自己说的话又确实是事实。
徐强说,你生病了,还是咋样。徐贵说,没生病,总之活不过两天,你只有一个哥,回不回来你看着办。徐强纳闷,哥哥咋说这要死要活的话,明显是神经被什么紧要事扯住了。

事情本可以在电话里说清楚,但徐贵知道,电话这东西,方便是方便,可有些事,在电话里办不了。徐贵想让徐强回来,再好好跟他说清楚。他的话,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把徐强震回来,事情确实关乎人命,徐强应该回来处理。
打完电话,徐贵往东边的巷子走,到了村头,站在一棵乌桕树下。近两个月来,他常来这里。前面五十米处是正在建盖的两幢楼房,每幢有六七个人砌砖,搅拌水泥,清亮的叮叮声敲打着四周的寂静,这寂静像是支援似的,从四处围拢来。在钢筋水泥之间的空地上堆放着被烧得漆黑的房梁。房梁旁是两堆灰烬,那里原来是两丛高大茂密的竹林。楼房后是三棵烧尽叶片的银杏树,只留下黑漆漆的光枝条。他还是孩子时候,常和同伴在银杏树下游戏,现在,一把火,记忆的凭据没有了。没有凭据,记忆哪里落脚呢,只能像鬼魂一样了,最后屁一样消失掉,他暗想。
他想到那个小女孩,清澈明净的大眼睛,粉嘟嘟的小脸,小嘴一碰,敲出一串柔嫩的乐音。一次在巷子里,一条小白狗,撕扯她的裤脚,她被吓得惊叫,徐贵赶忙过去,把白狗赶走,小女孩哭起来。他说,回家去。小女孩抹着眼泪说不敢回去,他便带着她在巷子里走。女孩把手悄悄伸进他的手心,他轻轻握着凉凉的小手,心立刻软软的,一时觉得,她就像是自己的女儿。他只有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第二个儿子还没出生的时候,他希望是个女儿,可最后还是失望。后来,小女孩只要遇到他,都会脆脆地喊一声阿叔,或递给他两三颗彩色纸包裹的糖,小脸向他仰着,露出让石头也能融化的笑。
现在,清澈明净不在了,粉嘟嘟不在了,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就像她从来没到过这个世界上。在徐贵心里,小女孩来过,而且将会停留很长很长时间。小女孩是她母亲第一个发现的。她卷曲在衣柜后面的地上,衣服成了灰烬,全身漆黑,肚子鼓鼓的,行将爆裂,右手指烧成短短的炭条,手心里是一摊将化尽的糖。纵火的是她父亲王定国,徐强厂里的一个工人。他向父母要钱,没要到,打算用火烧了他们的房屋,没想到,两家紧邻,自家也烧了,连女儿也赔进去。
就在王定国和他父母房屋被烧的夜晚,几条黑影在夜色的掩护下,飘进残垣断壁间闪来闪去,几分钟后,各挟所得飘然而逝,不一会儿,又有几条黑影随风而来,那里似乎成了鬼魅乱窜的墓地。
太阳向西微微偏一些,徐强回来还要一个多小时。他折身进巷子,刚走几步,迎面走来那条撕扯小女孩的白狗。它长高了,也老了许多,可那副穷凶相依然不老,还勃勃有生气。当它走过身边时,他警惕地盯着,白狗扭头看他一眼,走了。
徐贵停在一个巷子口,付军家的院门就在这个巷子里,院门外是一棵三围粗的橡树。树冠膨大,枝叶茂密,遮盖了半条巷子,还覆盖了两间房顶的上空。每年冬天,小孩子们从橡树下捡来橡子,用一根细棍从中间穿过,手指用力搓细棍,橡子在地上旋转,看谁的橡子转的时间长。他小的时候,很多时光就在这棵橡树下度过。几十年来,橡树还是他小孩时候的样子,好像时间在它身旁划过,不曾在上面停留片刻。他父亲曾说,这棵橡树,这里开始有人居住,它就在着了。这样说来,它已走过两百多年的漫长岁月。
橡树下的这些屋檐,相互交错,挨挨挤挤,有的墙面在风吹雨淋中斑驳,下陷,瓦缝间伸出绒绒茅草,在微风里轻轻摇曳,瓦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褐色苔藓。这些老屋和橡树两三天后就不在了,将被一场大火吞没。付军和与他房屋紧邻的两个男人悄悄决定,要一把火烧了它们。付军老婆昨夜在门外听到丈夫和两个男人的密谋,早上来家里叫他打电话给徐强,让徐强出面阻止。这女人受了付军不少气,挨骂是常有的事,一次徐强和徐贵到付军家吃年猪饭,付军让女人去买个什么,女人忙着打扫饭桌、收碗,好像忘了那事,付军骂开了,说了一句要操女人妈的话,他父亲在堂屋里跟客人聊天,听到后,骂他短命儿子,徐强在一旁说,你太过分了,付军呵呵笑起来。
付军老婆走后,徐贵在村外的玉米地里找到付军。劝他不要干那事。付军说,哪个跟你说的。徐贵没有告诉他。
房子那么密,会烧了全村。徐贵说。
你不要多管闲事。
付军最后警告他,如说出去,不要怪我不给你兄弟面子,我是不客气的。付军呼呼喘粗气,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下。
徐贵只好让徐强回来。
2
付军身体粗实,力气大,能扳倒一头大牯牛,喘声呼呼,人称大气筒,十七八岁时是村里一帮年轻后生的领头。一次,他的同伴在镇上被一个年轻人打了,他带着弟兄在那人回家的路上设伏,待他走近,用麻袋将他迎头套下,一阵拳打脚踢后,付军又抽来一根木棒,将那人的腿打断。结果,人打错了。付军蹲监狱后,他的团伙也风流云散。从监狱回来,付军身体越发壮实。去年,村里的二狗惹上他,他提着十多斤的铡刀把二狗撵得满村跑。
徐强初中毕业回来,成为付军团伙中的一员。父亲让他别跟付军混在一起,他没有听进去。那次打人,他也参与,被拘留两个月后出来,父亲让他滚远点,少回这个家,他便进城去。在城里,他也没有安分,和三个同伴劫一个深夜到银行取款的女人,他在银行对面的人行道树里望风,警察查看监控,没看到他,三个同伙被抓,没供出他。他用分来的六百元买一辆二手三轮车,给夜市的大排档运啤酒,三年后,他租下一间房,开起打折火锅店。火锅店生意兴盛,赚了不少钱。一天下午,一个锌矿老板的女儿来吃饭,说要见见老板,想看看这个有创意的老板是什么样。见到他,笑了,说,你的长相就很有创意。她说的是他的下巴,他下巴膨大茁壮,嘴却很小,笑起来才修改了一些不协调。徐强与她相识后,渐渐来往甚密,一年后结婚。徐强转让了火锅店进到岳丈厂里。他开始在办公室,岳丈看他颇具胆识,提他为公司副经理,四年后,岳丈买到一座矿山,让他出任原厂的分厂厂长,他也不负厚望,把厂子打理得有模有样。
几年下来,徐强的分厂向县财政每年缴纳四五百万的税款,占了总公司的一半。逢年过节,县领导都要买些礼物拜望他。他回到家,镇上的领导闻风而动,成为相聚时的座上宾,与派出所也混得透熟,觥筹交错间,称兄道弟。
村里人要让大学或中专毕业的孩子到徐强厂里,他没有答应。只收留了王定国一人,后来王定国出了事。付军跟他说过想进去,被他拒绝,他说,干你的村长吧。徐贵不知道徐强为什么拒绝付军,又为什么让王定国在厂里,他没问,他不是喜欢问的人。
徐强让哥哥进厂,徐贵没有去。徐强是什么人,没有谁比他更清楚,自从徐强少年时跟付军在一起混,他就觉得这个弟弟游走在生活的悬崖边上,内心里一直没有接纳徐强。父亲以为,他已走上正途。三年前,父亲到徐强厂里住了一段时间。一天,父亲回家,敲门后两三秒,屋里传来啪的一声,好像一个玻璃杯掉到地上。半天,徐强才开门,父亲咕噜一句,搞什么。徐强脸上显出难得一见的笑,王定国握着扫帚扫地上的碎玻璃,举头向他微笑,那笑分明是硬扯出来的。客厅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父亲用鼻子仔细辨认,是一股酸涩味,以前没有这个味。父亲目光在茶几上搜寻,上面还是摆着茶杯、果盘,三个香蕉在果盘里正在变黑。他的目光移向垃圾桶里,一张锡纸躺在一块香蕉皮旁,他用手指捏起凑到鼻子前闻,酸味更浓烈,满屋子的味道就是从这儿来的了。父亲举着锡纸问徐强这是什么,徐强说,就一张纸啊,会是什么。父亲移开沙发垫,伸手在靠背下的缝隙里探,抓出一个插着塑料管的玻璃瓶,里面有半瓶水,他又把瓶子举到徐强面前问是干什么用的,徐强说,晓不得是哪一个塞进去的。父亲常看报纸,把锡纸和水瓶联系起来,知道徐强在干什么了。
父亲从厂里回来,把徐强吸毒的事告诉他,嘱咐徐贵不要告诉任何人。自从徐贵知道那件事后,再也没有进厂的念头。徐强曾对他说,两个儿子以后找不到好的工作就进他的厂,徐贵说,到那时候再看吧。
3
巷子尽头是一方大水塘。徐贵走向坝堤,广阔的水塘,水色青蓝,静静地铺展着,像一块厚厚的绒布。坝堤可容两辆货车停放,这里也是人们休闲的娱乐场。坝堤往南延伸成一条公路,与从镇上到县城的公路相会。这个娱乐场的西边是一间土坯房,山墙面对水塘,墙上有一块黑板,黑板右边是付军让徐贵用丙烯颜料写的村规民约,第一条就写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安达村,学法知法,遵纪守法,发现违法违规的人和事,敢于制止并及时向村长和村委会报告。“告”字的“口”不知被谁擦去最后一横,擦痕像一道破皮的伤口,他觉得那伤口就像在自己身上,一股不舒适感缓缓流淌出来,随即如氤氲般弥散开,布满全身。
水塘边一只公鸡伸着脖子喔喔长鸣,然后慢慢踱步,偶尔低头啄一下。离公鸡四五米的水塘边,是二十多米长的围栏,把水塘与地面隔开。原来水少的时候,那里是一块深厚的沙土,村人就近取材,把沙土挖走,留下近三米深的大坑,水漫上来,就成了危险之地。三年前筑起的围栏,现在已遭到破坏,几块木板歪斜,两块已拔出漂浮在水边,留下近两米宽的缺口,还站立的木板只有警示的作用。如果乐而忘形的孩子靠近围栏,大人看见要训斥一番。
徐贵又走进巷子,迎面走来付军,付军微笑着,得闲啊?他嗯地应一声。付军说,如果徐强回来,让他给我打电话,我两个要好好喝一回,好久没见着他了。徐贵知道,如果自己不是徐强的哥哥,付军不会有这样的笑脸。
这些年来,徐强和付军的关系一直很好,自己的话,付军听不进,只有徐强的话才管用。被付军撵得满村跑的二狗打断母亲的大腿,因为徐强一句话,付军就给了他困难户的名额。
4
徐贵回到家的时候,太阳已经很偏了,阳光累了似的软下来。院子里空空的,一只鸟从院墙边的桃树上扑地飞走,像桃树吐出的一口痰。他打电话给梅香,告诉她徐强要回来。梅香问他徐强咋要回来,他说回来看看我们。梅香感觉这话有些奇怪,看我们,有什么可看的。父亲两年前死了,两口子没关照过徐强,徐贵没给过他好脸色。父亲本来身体好好的,从徐强厂里回来后,身体像被抽走骨头,慢慢软下来。临死前跟他说,徐强这辈子,没救了。
梅香到家开始做饭,叫徐贵杀一只鸡,徐贵犹豫了几秒,捉鸡去了。
刚把鸡煮上,徐强走进院子。徐强比哥哥稍高一点,原来身体壮实,这一年来瘦了许多,凸起的肚子不见了,神情也显得黯淡。
他说,哥,咋了,我下午一个重要的会都没法参加。徐贵在屋檐下用毛巾抹着手上的水,说,等会儿再说,先喝口水。梅香听到徐强说话声,从厨房走出来,打过招呼,她说去屋里喝水,说完上前推开堂屋门。徐强跟在嫂子后面进去,坐在沙发上,眼睛在屋里游来荡去。梅香给徐强倒一杯茶后回厨房去了。徐贵在沙发的一端坐下,离徐强远远的。徐强先开口,问他为什么不进他的厂,他说我在家也过得好,几十年在家,习惯了。哥你没说真话,是因为爹以前告诉你的那件事,我真的没做。我认真问你,你改了没有?没有的事,是他瞎想,我咋会做那样的事,我以前就跟你解释过了,你就是不相信。改了就好。不是改了,本来就没有。
两人没再说话。徐强端起茶杯喝一口,嘴里发出吸水时噗噜的声音。徐贵的目光移到门外,院墙的影子一点点往上蔓延。
哥,到底咋了?
走,到楼上说。徐强又喝一口水,跟在哥哥后面。徐贵走进隔壁房间,墙角一把木板楼梯直通楼上。哥俩走上楼,楼梯咯吱响。楼上没有隔墙,四根光裸的方形柱子笔直地撑着房顶,南边靠墙是一排砖砌的粮仓,中间隔着矮墙,堆放着稻谷、玉米。徐强的目光四处巡游。徐贵走到粮仓旁停住脚,转身对着徐强。
付军要烧他的房子,旁边的两家也跟着,你跟他们说说不要这样搞,如果三家烧起来,全村完了。徐贵的语调平静,轻缓,他不想让楼下的梅香听到。他注视着徐强的眼睛,徐强把巡游的目光收回来,眼皮倏地向上提起,看着哥哥。
徐强问付军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说,王定国不是因为房被烧得了钱么,他们也想得到政府的六万补助款。
烧了,每家都得补助款,这是好事;除了政府补助你六万,我再给你十万,你可以好好盖一幢楼房了。徐强看看房顶的屋瓦。徐强会说这样的话,徐贵是想到的,自己只是争取说服他。徐贵看到徐强的右手指微微颤抖着,神色凝重起来,嘴动了动,最后还是没说。
那火不一定烧到你这儿,离你远着呢;付军做事,我相信他,他们会控制火不会烧到别家。徐强说。
控制,你能控制你的手指不抖么?
我的手指咋会抖。徐强抬起右手,眼睛瞟一眼手指。
他们那一块,房子挨挨挤挤,火一烧起来,除非老天下雨才救得了。徐贵依然轻声说。
又不光烧你一家,怕什么。
那些人呢,树呢,你忍心看着他们死。
你管得太多了,真追究下来,跟你屁关系没有。徐强提高嗓音。
徐贵觉得没有再说下去的必要,转身往楼下走,徐强默然跟在后面。
5
徐强回到堂屋,端起茶杯喝了两口,嘴唇上衔着一片褐色茶叶,到屋檐下噗的一声吐掉,一只闲逛的母鸡看见,以为是他吐出一只虫子,赶忙奔过去,低头一看,失望地走了。徐强对哥哥说,他出去走走。徐贵让他过一会儿回来吃饭。
太阳已经变得浅红,像一张酗酒的脸,脑袋慢慢垂下,快靠到西边的山顶。
徐贵没有给梅香帮忙的兴致,在沙发上呆坐一会儿,走出屋,在院子里来回踱步。他好像想到什么,又回到堂屋里,在电视旁的茶盘里抄起待客的云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茶盘里找不到打火机,供桌上也没有。他拉开抽屉,找到一盒火柴,盒子凹下去,不过里面还有几根。当火柴点燃的时候,他没有了抽一口的欲望。他呆望着火苗。它很规矩,静静地燃烧,几秒钟后烧尽火柴棍。
将烧起的那场火不会这样规矩,它会在那三户房屋之外蔓延,所到之处,噼里啪啦,烧掉所有的房屋、上百年的老树,还有牲畜,甚至是人,留下一片焦黑。一把火,把过去全抹掉了。也许,村庄永远成为废墟,成为一块巨大的伤口。也许会矗立起一幢幢崭新的楼房。但即使整个村庄焕然一新,身披锦绣,也没有给他带来兴奋。他喜欢变化,但这变化应该是平静的,如溪流在山间潺潺流动,它清洌、婉转、曲线般流畅、自然。他对瀑布没有众人那般喜爱,如果站在瀑布旁,他感受更多的是恐惧。他不喜欢这样的突然转变。现在,村庄成了一个橡皮泥,握在付军的手心里,他想使劲拧,造出另外的样子。徐贵不知道最后的结果会怎样,不管怎么说,他都感到疼痛,他受不了这一拧。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做呢。父亲从徐强的厂里回来后,到镇上派出所去过两次,两次都没出现一点泡影,他们说,要有证据,再说了,他是我们县的财神爷,咋会做那事,回家好好待着。父亲说,可以验他的尿啊。他们说,万一验不出来呢,那影响,你想想吧。父亲没有办法,只能独自叹气。
太阳显出血红,像个发出红光的血盘子立在山顶上。徐强还没有回来,徐贵掏出手机,刚要打过去,徐强来了电话,他说在付军家里,吃饭不要等他。
吃饭的时候,梅香问徐贵,他和徐强在楼上说些什么。他说,我向他借点钱,买些砖和水泥砌楼上的隔墙,我带他看看要多少砖和水泥合适。他不想把付军烧房的事告诉她。他知道梅香的脑子像个浅水槽,一到她耳朵里,不管如何交代,没过一天就流出去了。然而,这件事是绝不能向外张扬的。父亲去派出所的事,是他再三催问,父亲才告诉他,而且父亲要他把那件事烂在肚子里,永不外说,包括梅香。
6
吃完饭,天已经黑了,东边的天空升起半个月亮,在几片薄云间快速穿梭。梅香喂猪,喂牛水,徐贵在厨房里洗碗。
徐强现在会对付军说些什么呢,也许把自己跟他说的那番话告诉付军。徐强应该不会那样傻。他会阻止付军的行为么?不会的,在楼上,他的拒绝没有一点犹豫,而且对付军的行为还很赞许。他们此时也许边喝酒边闲聊。徐强虽然喝点酒,可他没见徐强酒醉过,最多说话密一点,声音响一些,言语清楚,走路稳当。一旦他觉得自己很醉,他就要在屋外吹凉风,他说,吹凉风能让酒醒得快一点,身体会更舒服些。
现在事情没有解决,付军会继续他的计划。可能一把火就将村庄的命运扭到另一个方向上去,那些树,那些房屋和人将成为遥远的记忆,而此时,他们还沉睡在时时可能引爆的炸药桶上,浑然不觉。他觉得,所有那些人们嘴里莫测的命运,都是人造成的,不是什么神。他想到那个小女孩,粉嘟嘟的脸,清亮的眼睛,脆嫩的嗓音。
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会怎么办呢,他不知道。
他想再跟徐强谈谈。如果谈不好,去派出所说一下,他们会理会没发生的事么,他觉得很难。父亲不是去过了么,结果人家不理睬。
叮的一声,手里的白瓷碗碰在盆边沿,碗边上缺了半个指甲大的一块,他想到那个“口”缺的最后一横。徐贵把碗收进碗柜,回到堂屋,打开电视,几个影视演员跟一个穿着花里胡哨的男主持在舞台上无聊地嘻嘻哈哈逗乐,台下的观众发出风吹树林的哗啦声,喧闹声灌满整个屋子,这热闹声让他烦躁起来,他上前啪的一声关了电视。喧闹声闪电般蹿进电视机里,屋子空下来,他的心平静一些。
他来到院子里,半个月亮搁在房脊上,几片薄云在远处,一时还缠不到它身上,远山在月光里显出青灰。他看看手机上的时间,已经九点半。徐强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梅香走出厨房,进堂屋打开电视,喧闹声从门口蹿出来,播撒在院子里。徐贵走进耳房一楼的睡屋,床头的书桌右上角,摆着一叠父亲留下的报纸,有《新华文摘》、《信息报》、《云南日报》,那些报纸他曾看过。无聊时,他会练习毛笔字,但他不舍得用这些报纸来写毛笔字。抽屉里还有厚厚的两摞,作为父亲的遗物,他要永远留下来。报纸旁是一个罐头瓶做的笔筒,一支狼毫毛笔高高立于几只钢笔之上。他又想到那个“告”字。徐贵抽出毛笔,揣进内衣上兜,从书桌脚拿起半瓶丙烯颜料放进夹克的外兜,抓起一只手电走出睡屋。
他对正看电视剧的梅香说,他去看看徐强,喝醉了没有。
巷子里没有人影,初冬的夜晚流动着冷风,这样的天气人们早回家了。刚到巷子口,听到水塘边有踉跄的说话声,他关了手电,仔细听,是付军和徐强,徐强要在水边吹冷风,付军说不能吹风,吹后更受不了。
徐贵摁亮手电,向他们走去。
7
徐贵走进堂屋的时候,梅香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微低着头,脸上没有动静,他素来就是这样,喜忧不放在脸上,全藏在肚子里。梅香问徐强咋不回来,他说,我没到付军家,只在外面走一阵,他可能在付军家睡了。
他最后说,我睡了。
梅香直直的眼神看着他走出屋的背影,像要看清他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第二天早上,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看到黑板上那个“口”字的最后一横已经添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徐贵在田里背着喷雾器打农药,他的手机响了,梅香的电话。她说,付军老婆问付军一夜不归,是不是在她家里,她说不在,她还以为徐强在付军家睡呢。
你说他两个昨晚上会去哪儿?梅香问。
我咋晓得,他说。他收起手机,放下喷雾器,坐在田埂上,看着两百米外的村庄。那棵橡树庞大的树冠像蘑菇一样长出屋脊,在旭日之下,枝叶光彩熠熠。也许是风,让它微微晃动,他感觉,那是一张充满阳光的脸在向他遥遥点头。他露出浅浅的笑,算是对它的回应。他看着村里起伏的屋脊和边上的绿树,渐渐地,那鱼鳞似的屋脊游动起来,树冠也浮起来了,许许多多顶着绿冠的鱼迎着阳光游去,游向远处,一直到时光的深处,再回头。
中午饭的时候,二狗在坝堤上看到水面飘着一只皮鞋,走近看,是付军的。他还记得,付军抬着铡刀撵他的那天,就是穿一双宽大的皮鞋才没追上他。
傍晚时候,付军和徐强被人们从围栏下的水塘里捞上来,两具尸体平躺在沙地上,都闭着眼睛,表情严肃,像两个孩子比赛谁能不动不移睡得更长久。坝堤上的人群外,一只红公鸡,不合时宜地伸长脖子喔喔叫。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