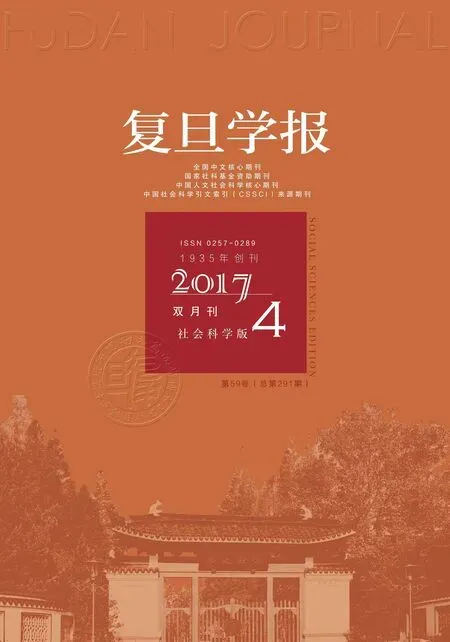威权之域与首善之区
——两汉散体赋都邑理念的差异
侯文学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威权之域与首善之区
——两汉散体赋都邑理念的差异
侯文学
(吉林大学 文学院, 长春 130012)
两汉散体赋对于都邑的赋写,实质上是赋家基于时代诉求而产生的都邑理念的艺术再现。此类题材的赋作,大体呈现出两种倾向: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赋家以表现天子威权为主,突出西都长安的壮丽饶富;以班固、张衡为代表的赋家以表现天子德治为主,赋文打破了历史发生顺序,重新组合东汉帝王的礼制活动,或按照由内而外的德化顺序,或按照礼书所载一年四季的礼仪安排,表现永平之政,突出东都洛阳首善之区的地位。由扬雄发端的关于司马相如赋二元对立的讽谏结构的解读,以及班固、张衡赋作对于颂今、讽谏立场的强调,使其赋文中西都壮丽背后的树威意识被淡化乃至被忽略,代之以淫侈之私欲的表达。
汉赋 都邑理念 威权之域 首善之区
都邑是古代帝王政治权力的空间表达,也是古代文人士子趋骛与关注的所在。对于两汉涉及都邑题材的散体赋,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其讽谏的创作动机,抑或聚焦于其对汉代都邑制度的反映,而对于以赋家为代表的汉人都邑理念的探讨则很是薄弱。
一、 威权之域:汉代散体赋中的西都形象
(一) 长安的壮丽饶富与统治者的威权诉求
汉高祖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得天下,需要解决诸多方面的问题,天子威权的树立是其中之一。据《汉书·叔孙通传》记载,刘邦已并天下,诸侯于定陶共尊刘邦为皇帝,但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刘邦深以为患,叔孙通趁机劝说刘邦“起朝仪”。于是叔孙通获命与鲁诸生三十人,“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采古礼与秦仪杂就而成汉朝仪。叔孙通的朝仪集中体现了朝堂的等级之别,也确实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所以高祖慨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叔孙通制礼,对于草莽出身的刘邦集团确是必要的努力。礼的实质是等级制度,是维护统治、树立威权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但朝仪对于庞大帝国机构的秩序建构而言仍然有鞭长莫及之憾。因此,经过吕后之乱而即位的文帝,其节俭与优容的施政方针固然对经济的发展有利,但其优容无为政策也给中央集权政治带来一系列后患,彼时诸侯王“等齐”(贾谊《新书·等齐》)于天子的现象十分严重,景帝时吴楚七国之乱的爆发,可以说是文帝政策的直接后果。天子的威严,自高帝至景帝时时受到挑战,真正收回天子至上威权并成功高踞天下人之上的是汉武帝。他一方面通过众建诸侯的方式削弱地方诸侯的权力,使其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汉书·诸侯王表》),一方面征伐四夷,同时也在富厚的经济环境中大兴土木,扩建上林禁苑,修建建章宫、甘泉宫,在帝王宫室苑囿方面,真正达到了萧何所说的“且亡令后世有以加”(《汉书·高帝纪》)的程度。大汉天子的威权,也因为上述诸种举措的成功而得到保障。
帝王威权的回收与巩固在武帝时完成,这里面固然有其个人的施政品格在起作用,但前人及时人的言说建议也不可忽视。儒学在武帝威权于物质形式方面的落实中起到重要作用。前人论及儒学,往往与尚俭联系起来,而对其于华美富丽一面的强调,则关注不足。对此,我们有必要略作申说。文帝时期,贾谊注意到诸侯王“等齐”于天子的现象,并以此为重要议题,深以为忧:“衣服疑者,是谓争先;厚泽疑者,是谓争赏;权力疑者,是谓争强;等级无限,是谓争尊。” (《新书·服疑》)面对天子威权受到的挑战,贾谊建议“贵贱有级,服位有等”,使天下之人“见其服而知贵贱,望其章而知其势”。具体而言,就是:“制服之道,取至适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进之帝。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 (《新书·服疑》)贾谊显然是倾向以宫室、车服等器物用度的华美富丽来显示天子之威严的,他曾有这样的比喻:“人主之尊,辟无异堂。阶陛九级者,堂高大几六尺矣。若堂无陛级者,堂高殆不过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 (《新书·阶级》)贾谊并不反对高屋广厦,只是主张它与等级制度相应。依贾谊之意,天子之尊高不可及,其用物之华美必须无以复加。
贾谊提出的用服物的华美体现天子的威权,是有儒家礼学文献作为依据的。先秦礼学文献已经提示:在社会生活场域,礼以多、大、高、文为贵(《礼记·礼器》)。简单来说,就是等级秩序(“礼”)需要借助于外在方式(“器”)来表达,而资源分配多寡则是其外在方式之一。等级愈高,所享有的资源愈丰富。这样选择是有理由的,所谓“礼之以多为贵者,以其外心者也。德发扬,诩万物,大理物博,如此则得不以多为贵乎?故君子乐其发也”(《礼记·礼器》)。即便是主张“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的一代儒宗董仲舒,对此也表示赞同。其《贤良对策》有云:“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宫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汉书·董仲舒传》)此说与其借助于宗教神学强调君权至高无上的天人理论,一并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契时代之需,也应和着武帝“玄黄旌旗之饰”(《汉书·董仲舒传》)的兴趣,故一经提出,即受到武帝的重视。
宣帝时的治政多“循武帝故事”(《汉书·刘向传》),使武帝确立的汉家制度得以稳定。西汉帝王的树威工程以甘露二年(前52)呼韩邪单于的归附为标志而达到顶点。宣帝诏“其以客礼待之,位在诸侯王上”的待遇对待呼韩邪单于,以显示安抚之意,但在双方相见的程序中,史家特意强调宣帝召见呼韩邪单于的地点与节目,是“置酒建章宫,飨赐单于,观以珍宝”(《汉书·宣帝纪》)。建章宫以高邃华丽著称,宣帝选在此地飨赐呼韩邪与下面的“观以珍宝”目的一致,即以物质的宏富来显示汉家天子的威严,以达到震慑蛮夷的目的。
(二) 两汉散体赋的文学表现
从汉初以来帝王所焦虑的树立威权问题,至武帝方真正解决。在文学上较早予以回应的是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此赋虽然名为《天子游猎赋》,实则是班固、张衡等人《两都》《二京》等都邑赋的雏形,对此认识,学界并无异议,而对于此赋的创作时间则存在争议。*具体争议可以参阅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刘跃进题之以《子虚上林赋》,并据《上林赋》提及的异域名物入上林苑的时间、赋文结尾部分,以及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兴儒的关系等三条理由,将之系于元光元年(前134)*参见刘跃进:《〈子虚赋〉〈上林赋〉的分篇、创作时间及意义》,《文史》2008年第二辑。。此说理据充分,颇可信从。
宫馆、苑囿是帝王生活环境的主要构成,也是天子之威可以落实的物质形式。因此,司马相如此赋之下篇即《文选》目为《上林赋》者,其第一部分主要是展示帝王苑囿之美及田猎之乐,在物质层面压倒齐、楚两国;第二部分则叙写天子的勤政措施与礼乐建设,在精神层面压倒诸侯,以全面彰显天子的威权。需要申说的是,相如赋将两部分内容设为天子依时之先后而行的两种举措,固然后者是其称颂的对象,前者也未必受到赋家的否定。由物质上升到精神,这是自枚乘《七发》以来即已形成的赋文本的内在结构。至于两者被视为正反对立的行为,以为前者彰显帝王奢侈荒淫之意,后者乃是赋家期待的内容,是对前者的反拨,则无疑是受到儒家经学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确立以后尤其是扬雄以后赋论家的影响。
司马迁较早站在儒家诗教立场上看待相如之赋,谓“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迁对于相如赋的华丽辞藻及夸张手法颇不以为然,但重视其归于节俭的思想立意,而司马相如本人却未必持有这样的立场。其《大人赋》在西汉后期传播中的遭遇可以作为辅助的说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他作《大人赋》,是鉴于“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据此,司马相如先有了《大人赋》的未完成稿,并且颇为得意其“靡”,故愿意完成奏上以满足武帝的仙趣。司马迁也有附带的说明:“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司马相如将“大人”最终达成的境界描述为“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视眩眠而无见兮,听惝恍而无闻。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这是一个“天地与我并生”的独立无偶的境界,引人无限遐想。赋奏,“天子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可以说司马相如奏《大人赋》的目的达成了。但相如奏《大人赋》的目的,在西汉后期扬雄那里,却遭到误读。《汉书·扬雄传》录扬雄《自序》:“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在《法言·吾子》中,扬雄对于靡丽之赋的“讽”“劝”矛盾问题也有类似申说。这一观点得到班固的推扬,并将之拿来作为对于司马相如赋的评价。《汉书·司马相如传》:“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风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至此,散体赋劝讽二元对立的文本结构形态的理论才得到普遍认同。

上述文字立意在与齐楚二国的猎苑争胜,落笔主要在两个方面:天子上林苑猎区的广大与财富的众多。笔法夸张,颇遭后人诡滥不实的诟病。但作为赋体文学,它首先是“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的呈现,也是天子纳天下万物于一苑的情实所致,其表象背后更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的帝王观念的落实。苑囿宛然是帝国版图的缩影,天子纵猎其中,其“万物在我脚下,河山在我手中”的恢弘气势得以展示。


武帝的声威为东汉前期的定都之争增添了历史文化内涵,在都长一派的赋写中成为铺陈的重点。杜笃《论都赋》以追忆的方式再现西汉长安的帝京之美,建议东汉帝王都之。赋文先概述高祖创业、文帝守文的历史,继之以武帝功业的铺陈,重点在对外用兵的一面。写其钩深图远,北击匈奴,开通西域,又“立候隅北,建护西羌。捶驱氐、僰,寥狼邛莋。东攠乌桓,蹂辚濊貊。南羁钩町,水剑强越。残夷文身,海波沫血。郡县日南,漂概朱崖。部尉东南,兼有黄支。连缓耳,琐雕题”,凡此种种,用以说明廱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的所在,是“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后汉书·杜笃传》),亦即西汉盛世的凭借。
西汉的帝都以壮丽威严取胜,并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在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西不如东的赋写中,西都壮丽的美仍是不可否认的存在。对于西汉宫室的壮丽,东汉赋家倾注了较多笔墨,从三个方面予以铺陈:首先表现在上与天象紫宫相合,其次表现为基址的隆高,再次,表现为宫馆数量众多。当然,班、张等东汉赋家赋写西都颇多贬抑之言,奢靡享乐是他们赋予西都的新意蕴,穿插于宫室、田猎中的女性描写就是为此立意服务。班、张这样写的目的是反衬东都之盛德,讽谏东汉帝王,这是古今论者的常识。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并不必然排除班、张等赋家对于西都在树威方面的肯定。西都之奢华与树威的关系在关于西都的赋写中同样构成一个主旋律,如写宫室部分,“惟帝王之神丽,惧尊卑之不殊”(《西京赋》)一语是关键,其他铺叙都是依此展开,反映着西汉帝王宫室修筑“重威”思想。至于游猎方面,班、张等也不否认西汉帝王“奋大武乎上囿”,乃是基于“威戎夸狄”(《西都赋》)的耀威目的,只是西都之树威不如东都之建德层次更高罢了。
二、 首善之区:汉代散体赋中的东都形象
(一) 洛阳的礼制建设与统治者的德治意趣
西汉立国二百年后,王莽篡汉,仅十八年之后,新莽政权即被推翻。人心思汉是当时的情势。民间甚至传言:“刘氏真人,当更受命。”(《后汉书·刘玄传》)西汉帝王的统绪,成为各路义军的旗帜。如刘林“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立王郎为天子。(《后汉书·光武帝纪》)光武帝本人也是高祖九世孙,“出自景帝生长沙定王发” (《后汉书·光武帝纪》);更始帝刘玄则是光武帝族兄,也是刘姓子孙;赤眉立城阳景王之后刘盆子为帝,也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当求刘氏共尊立之。”(《后汉书·刘盆子传》)而刘秀之所以能够从众多刘姓子孙中脱颖而出,除了军事上的胜利之外,还有民心的支持,而后者的获得则是通过对于前汉典章的维持。《后汉书·光武帝纪》载,王莽死后,更始将北都洛阳,以刘秀行司隶校尉,使前整修宫府,“于是置僚属,作文移,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刘秀此举受到三辅吏士的称赞,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民心因此归附,“由是识者皆属心焉”。
由此看来,经过西汉二百年的统治,刘姓帝业的传承已经深入人心,刘秀甫建帝业,政治血统的自信已经不是问题。困扰西汉前期诸帝的问题,在光武帝这里已经不复存在。《东观汉记》载,建武七年(31)杜林上疏,以为“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8页。就是这种血统自信的最好说明。加之以刘秀对于西汉哀平之际兴起的谶纬的利用,造成“受命中兴”的舆论效果,刘秀即真的合理性从而在天命层面获得保障。
与汉代政权稳固相一致的,是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如果说武帝时期的儒学主要是解决权力分散,以及与此相关的树立帝王政治威权的问题,并且此一问题在武帝时已经获得解决,此后刘姓的统治基础得以稳固,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教化开始提上日程,依礼治国成为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但武帝的举措与他所提倡的儒学却存在较大差距。功成治定之后,汉家制度与儒学(古礼)之间的矛盾开始彰显。比如武帝确立的甘泉泰畤之礼,虽然对于一统政权的威权树立起到较大作用,但它来源于方士的建议,与儒家礼学文献的记载颇有差距,因而在西汉后期受到儒者的攻击。自元、成二帝起,汉制与古礼之间的冲突日益激烈,直到汉平帝时王莽主政,此一矛盾才最终解决。这表现在都邑建设上,便是依托先秦礼学文献规划都邑建筑。先秦礼学文献记载先王于都邑南郊祀天、北郊祀地,天子有明堂、灵台、辟雍等礼制建筑,而据《汉书·平帝纪》、《王莽传》、《后汉书·张纯传》等文献记载,平帝元始(1~5)年间,王莽依据《周礼》等文献,对于礼制作出一系列改革,起明堂、辟雍、灵台,恢复南北郊祭祀天地制度,使武帝以来颇杂方术的礼仪向古礼靠拢。新莽时期,这一制度得以延续并强化。
光武帝本人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后汉书·光武帝纪》叙光武帝少年时代的经历,特别点出:“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所以“爱好经术”的刘秀即位后,往往“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效果也是显著的。先时逃遁林薮的儒者们,“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光武帝定都洛阳以后,延续并落实西汉后期的都邑设想,即所谓“元始中故事”。据《后汉书·祭祀志》,建武元年(25)光武帝即位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就依礼“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第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洛阳城南七里,依鄗,采元始中故事”。三十三年(57)正月,又立北郊,“别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如元始中故事”。《白虎通》是章帝时期官方经学的记录,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其时朝廷礼制的解释说明。可以说,到章帝时期朝廷礼制建设已经洋洋乎大观了。
礼治的思想原则是德治。在儒家看来,德在礼中,因礼而显。《礼记·曲礼上》如是阐明德、礼的关系及明礼的重要性:“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要求治国的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东汉诸帝十分注重德政。光武帝标榜自己治理天下是行“柔道”(《后汉书·光武帝纪》),又说“柔者,德也”(《后汉书·臧宫传》)。这也成为东汉的开国纲领。此德政落实于都邑建制,则是在洛阳修筑诸多礼仪建筑,而以“三雍”最为醒目。东汉官方经学文献对于“三雍”的解释,莫不以“德”为意。《白虎通·辟雍》:“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圆,以法天也。雍者,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言积也,积天下之道德。”“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天子所以有灵台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阴阳之会,揆星辰之证验,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陈立《疏证》引古微书《援神契》:“灵台考符,居高显神,圣王所以宣德察微。”*班固撰,陈立疏证:《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65页。

(二) 东汉散体赋的艺术表现
由于历史的诸多引领,东汉前期帝王致力于德政建设,并在都邑规划、个人行为方面做出比较全面的落实。作为一代文学的散体赋必然要对此有所表现,这类作品以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为代表。在赋家的艺术再现中,不但有东汉历史的真实面影,更寄托着赋家关于都邑(政治)的理想。
班固《东都赋》*按本文所引《两都赋》,均出自《后汉书·班固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结尾部分借东都主人之口,批评通过西都宾传递出来的巨丽侈靡的都邑理念,责其“但知诵虞夏之《书》,咏殷周之诗,讲羲文之《易》,论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浊,究汉德之所由”,强调东汉帝王的“德政”。所谓“汉德”就是赋文前面所称颂的建武之治、永平之政。《东都赋》称颂光武帝的政治,说他“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伦寔始”,“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车,造器械”,“龚行天罚,应天顺人”,“迁都改邑”,“克己复礼,以奉终始”,“宪章稽古,封岱勒成”,“案《六经》而校德,妙古昔而论功”,每一项举措都与某位前代明王相类,意在说明光武帝集前代圣王之功业于一身,所为皆是“仁圣之事”、“帝王之道”。核诸史书,我们知道,除了迁都改邑、封岱勒成二事,其他几项很难落到实处,从手法上来看,以虚写为主。
赋文称颂明帝,先是强调其在光武帝奠定的基业基础上,“重熙而累洽”,继写明帝的一系列礼仪活动,每一项礼仪活动铺陈之前,大多有表示因果、递进、承接关系的连词引领:先是“盛三雍之上仪,修衮龙之法服,洪鸿藻,信景铄,扬世庙,正予乐”,接下来是“乃动大路,遵皇衢,省方巡狩”,继以“然后增周旧,修洛邑”,“外则因原野以作苑”,目的是“顺时节而蒐狩”,狩猎之后,“于是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觐明堂,临辟雍,扬缉熙,宣皇风,登灵台,考休徵”,结果是四方“自孝武所不能征,孝宣所不能臣,莫不陆詟水慄,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秩序井然。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对于永平之政的赋写并没有按照明帝举措的实际顺序来构思,而是按照他对于帝王德治的理想重新组合了明帝的行为。比如,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明帝“服冠冕衣裳”以行三雍之礼(“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升灵台”、“幸辟雍”)集中在永平二年(59),“正予乐”(即“改大乐为大予乐”)在永平三年(60);明帝的省方巡狩,计有三次,依次是永平二年(59)的西巡、永平十年(67)的南巡、永平十五年(72)的东巡;增修宫殿(即北宫)的举措在永平三年(60)至永平八年(65);绥哀牢、开永昌事发生在永平十二年(69);校猎事则发生在永平十五年(72)。但班固的行文顺序却将明帝的“正予乐”提到第一次省方巡狩之前,将绥哀牢事置于校猎蒐狩之后,这就构成了一个新的因果序列:明帝先依礼治京师朝廷,然后才巡狩“散皇明以烛幽”;“中夏”布德之后乃有增修宫室苑囿的行为;文治大备,乃继之以“蒐狩”“讲武”,而蒐狩活动因为西汉赋家的铺陈,最容易给人以奢靡纵欲的印象,故作者间以《诗》《礼》之语穿插,所谓“临之以《王制》,考之以《风》《雅》,历《驺虞》,览《四驖》,嘉《车攻》,采《吉日》”云云,都提示此举与前代明王的礼制相合,复又收之以“荐三牺,效五牲,礼神祇,怀百灵”的祭祀活动,表明东都帝王的田猎乃是服务于礼仪目的,非耽于逸乐。文武兼修之后,天子乃向四裔宣布神威,所谓“瞰四裔而抗棱”,结果自然是周边方国部族前来归附,于是天子顺势“绥哀牢,开永昌”。
《东都赋》接下来便写天子因万方归附而在云龙门盛礼兴乐,行春日万国朝会的大典。我们看其中的酒宴规模与场面描写:“乃盛礼乐,供帐置乎云龙之庭,陈百僚而赞群后,究皇仪而展帝容。于是庭实千品,旨酒万钟。列金罍,班玉觞,嘉珍御,大牢飨。尔乃食举雍彻,太师奏乐,陈金石,布丝竹,钟鼓铿鎗,管弦晔煜。抗五声,极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备,太古毕。四夷间奏,德广所及,仱佅兜离,罔不具集。”这段文字以虚写为主:天子赐予的礼物是“庭实”,食物是“太牢”,所奏之乐舞则是《韶》《武》之类的上古雅乐。文字以《诗》《左传》《论语》等经典之语为多。即便是奏起四夷之乐,也是“德广所及”的范围。赋家始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经学理性,借助经典之语,为这个盛大场面罩上儒家礼乐文化的光辉。
班固对于永平之政的铺陈,无论是祭祀、巡狩,还是服制、田猎,莫不以礼为据,所奏音乐也都是雅颂之声。这就给我们造成一个印象:明帝所行完全是理性的安排——其治政遵循由内及外的顺序,没有个人的欲望。这固然如前所言得力于赋文对于帝王举措的重新安排,也有赋家虚语的作用。比如明帝时的宫室修造,就并非如班固所云“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完全符合礼制的规定。班固《东都赋》所表彰的明帝“增周旧”的工程,主要是指包括德阳殿在内的洛阳北宫的建造,这项工程也因设计的崇高弘丽而受到当时朝臣的反对。《元河南志·后汉城阙宫殿古迹》:“《东观汉记》曰:明帝欲起北宫,尚书仆射钟离意上书谏,出为鲁相。后起德阳殿,殿成,百官大会。上谓公卿曰:‘钟离尚书若在,不得成此殿。’殿前有东阁,《汉官典职》曰:‘德阳殿画屋朱梁,柱皆金镂,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周旋容万人。激洛水于殿下。’”*徐松:《河南志》,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48页。班固的叙述,显然带有他个人的理想化色彩。而班固犹以为未足,赋文接着写明帝躬自节俭以化天下:“乃申旧章,下明诏,命有司,班宪度,昭节俭,示大素。去后宫之丽饰,损乘舆之服御,除工商之淫业,兴农桑之上务。”效果是惊人的夸张:海内之人尽皆“弃末而反本,背伪而归真,女脩织紝,男务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耻纤靡而不服,贱奇丽而不珍,捐金于山,沈珠于渊”。而史书对于明帝节俭的记载,仅见于永平十二年(69)五月颁布的一份禁奢的诏书:“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后汉书·明帝纪》)主要还是在责令臣民方面,未及诏书下达后的效果。相对于史书可以落实的记载,赋文显然是在夸大其词。赋文继言明帝德化天下的效果,也颇多《诗》《书》等经典陈辞构织的虚语,如写百姓“嗜欲之原灭,廉正之心生,莫不优游而自得,玉润而金声”,学校的士子们“献酬交错,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咏仁”,“相与嗟叹玄德”。赋文与其说是明帝朝政的实况,倒不如说是先秦礼学文献所载典礼的汇集,与作者对礼典场面及其效果的憧憬。
张衡《东京赋》*按本文所引《二京赋》,均出自《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规模更大。此赋与《东都赋》的异同,前人论说已多,这里着重指出两点:首先,张衡在整体框架上按照时间顺序由光武帝写到明帝,但到明帝时期,就不再遵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而是依据《礼记·月令》等文献,按春、夏、秋、冬的框架叙写帝王举行的各种礼仪活动:先是“孟春元日”的群臣朝贺之礼、天子燕飨群臣之礼,接下来是郊祀天地之礼、正月宗祀五帝于明堂之礼、立春之日(“农祥晨正”)的籍田礼、三月(“春日载阳”)的大射礼,之后是十月(“日月会于龙狵”)的养老礼,接着是“三农之隙”的校猎之礼、岁末大傩之礼,最后收之以五年一次的巡狩之礼,表示德治的一终。其次,张衡《东京赋》所揭东京诸仪,比班固《东都赋》更为完备,描写也更为详尽,如三雍之仪,在班固那里是概写,张衡则充实以宗祀上帝、大射、养老等具体的礼仪内容。至如春日籍田礼、岁末大傩之礼,则为班固《东都赋》所未及。至如班固着重铺写的“蒐狩”和春正朝贺之礼,张衡也是毫不逊色。与班固《东都赋》一样,张衡《东京赋》中,每一项礼仪活动都有相应的声教布濩、民心和畅、万邦归附之类的效果缀其后。另外,班、张二赋往往使用《诗》《书》之语,经典用语与礼仪活动相得益彰,文字上呈现出典雅之美。
傅毅《洛都赋》今存残文,内容较班、张之作简略,其对于洛都的叙写,不外是光武定都于洛阳的历史追溯、洛阳的地理形势、都城的建筑布局、帝王田猎。赋文以礼为节的特点仍然十分明显:言布局则挈入“面朝后市”的礼家言语,言建筑则提点“明堂、辟雍、灵台之列,宗祀扬化,云物是察”*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03、1103页。。李尤《辟雍赋》《德阳殿赋》《平乐观赋》《东观赋》,可作为《洛都赋》的补充。这些作品对于东汉宫室描写呈现出两个特点:第一,关注礼制建筑;第二,如西汉一般,崇尚巨丽繁华。所不同者,东汉赋对于本朝宫室巨丽繁华的铺陈中,往往间以《诗》《书》等经典之语,使我们在领略了赋家铺陈的才情之后,又回归于礼制的场圃。
三、 余 论
在一般的汉代文化探讨中,论西汉,则以为崇尚巨丽繁华;论东汉,则以为崇尚礼法。在都邑赋的讨论中,这种意识尤为明显。这是根据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得出的结论,但班、张二人赋作,一是为颂扬当代,一是为讽谏朝政,在对东都的叙写中,更多传递的是二人的政治理想。二人尤其是班固在东都的赋写中,有意弱化了帝都巨丽繁华的一面。似乎东汉洛都就是纯粹的礼仪之地、廉俭之区。如果我们将史书记载与东汉都邑题材的赋作置于一处,就会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
两汉散体赋对于都邑的表现有共同之处,如都侧重于展示帝都物质饶富、宫室建筑、帝王活动,反映出汉代赋家对于都邑的共同认知:帝王之城。帝王是都邑中活跃的主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都邑的华丽是两汉赋家的共同印象。班、张二人均未将宫室的壮丽落墨于洛都,这并不能说明赋家缺乏现实的模板,也不能说东汉赋家对于壮丽之美普遍失去了兴趣。傅毅《洛都赋》已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趣味:“览正殿之体制,承日月之皓精。骋流星于突陋,追归雁于轩軨。带螭龙之疏镂,垂菡萏之敷荣。顾濯龙之台观,望永安之园薮。”*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103、1103页。概言之,西汉的宫室壮丽体现的是皇家的威严,东汉宫室崔嵬则与不逾制(合乎礼制)结合在一起。
两汉帝王宫室建制与帝王生活内容,多有相同之处,如前所说,东汉洛阳修筑的部分礼仪建筑在西汉后期的长安已经出现。东汉帝王固然有礼仪建设之功,但西汉诸帝在这方面的举止也不是空白。《后汉书·陈忠传》载陈忠上疏安帝即云:“藉田之耕,起于孝文;孝廉之贡,发于孝武;郊祀之礼,定于元成。”东汉诸帝固然多躬履节俭,惠于鳏寡,西汉诸帝也未尝无此举。元帝初元二年(前47),“诏罢黄门乘舆狗马,水衡禁囿、宜春下苑、少府佽飞外池、严籞池田假与贫民”(《汉书·元帝纪》)。据东汉马廖的上疏,西汉还有“元帝罢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乐府”(《后汉书·马援传》)的举措。西汉的宫室固然崇丽华美,东汉的宫室也未尝不壮丽。袁宏《后汉纪·章帝纪》就有“是时承平久,宫室台榭渐为壮丽”*袁宏:《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17页。的记载。但在班、张等赋家的构思中,上述内容却被割裂开来:游乐内容置于西都(京)赋的表现范围,礼乐内容置于东都(京)赋的表现范围。我们以平乐观为例。汉代东、西两都均有平乐观之设,西京平乐观是上林的宫观之一,是西汉帝王娱乐及向匈奴等异域君主宣示汉威之所。《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三年(前108)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观”;元封六年(前105)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是与民同乐的记载。《汉书·西域传》载,元康二年(前64),“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东汉承之,于洛阳设平乐观。据华峤《后汉书·灵帝纪》,灵帝时也于此“设秘戏以示远人”*汪文台:《七家后汉书》,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18页。。所谓“示远人”,就是展示给外国君长,起到威慑与交好的作用。《汉书·西域传》说,汉武帝“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渝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然张衡《西京赋》写到上林平乐观,则侧重于西汉帝王的独乐之乐:在铺陈各种娱乐活动之前,先行用“攒珠玉之玩好,纷瑰丽以侈靡”一类文字,暗示此活动的奢靡基调。根据张衡的描述,西汉平乐馆的秘戏包括了杂技、歌舞、武艺、角力等。这些都可以在东汉李尤《平乐观赋》中找到踪迹,如“方曲既设,秘戏连叙”、“戏车高橦,驰骋百马”、“乌获扛鼎,千钧若羽”等等。而由赋文前面之“南切洛滨,北陵仓山”*欧阳询:《艺文类聚》,第1134页。的交代可知,李尤赋写的对象正是东汉平乐观。由此赋来看,东都平乐观活动与西京并无二致。而张衡《东京赋》写东都平乐观,则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规遵王度,动中得趣。”文字的简省与“规遵王度,动中得趣”的交代,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东都帝王并不以平乐观为满足游乐私欲的场所。
由此来看,汉代散体赋中的都邑意象,诸如宫殿、街衢、市场、游侠、礼制建筑等,都是经过精心汰选,是赋体文本中的都邑,与都邑的实际情形有差异。换言之,无论是威权之域还是首善之区,赋家在赋写中都采用了“推类而言”、“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汉书·扬雄传》)的夸张手法,使之达到无以复加的艺术效果。班固《东都赋》、张衡《东京赋》,是赋家对东汉治国思想的文学解释,其中渗入了赋家本人的都邑理念;而后人对于相如赋的讽谏结构的确认,又遮蔽了其赋文对于武帝树威的积极回应的一面;班固《两都赋》序、《后汉书·张衡传》所强调的“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因以讽谏”云云,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我们在阅读时,对东汉赋家夸叙西都壮丽与帝王树威意图的关联之把握,而将西都的壮丽饶富置于帝王的淫侈之欲下观照,对其主题作出单一化的解读。
[责任编辑 罗剑波]
Authority Area and the Most Philanthropic and Benevolent Community: the Capital Concept Differences in the Poetic Proses of the Han Dynasty
HOU Wen-xue
(College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The description and narrative of the capital in the poetic proses in the Han Dynasty is an artistic reproduction of the capital concept. The works of such subject were roughly presented in two tendencies: the writers that were represented by Sima Xiangru focused themselves on the emperor authority and the magnificence of Chang’an. The writers represented by Ban Gu and Zhang Heng focused themselves on the benevolent rule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rosperity of Luoyang. Later interpretations on the binary structure of Sima’s works and the emphasis on the standpoint of euphemistic criticism and the praise of contemporary in the works of Ban Gu and Zhang Heng, played down the consciousness of authority setting-up underlying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capitals.
poetical prose in the Han Dynasty; capital; emperor authority; benevolent community
侯文学,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汉代文学与都邑文化”(项目批准号:11YJC75103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