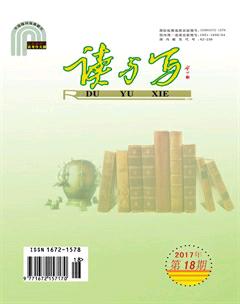从《撒哈拉的故事》的翻译中谈归化与异化
田原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6-0006-01
简析: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在翻译上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即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
因为本文是对文学作品片段的翻译,在译的过程中,为了让读者更容易理解文章内容,多使用了归化。归化与异化之争的靶心则是处在意义和形式得失漩涡中的文化身份,文学性乃至话语权利的得失问题。[1]
三毛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她的文字里总是流露着女性的柔美和细腻,让人沉浸。
三毛的文字并不華丽,却用简单的勾勒细致地描绘出了当时的情景。三毛的丈夫荷西是西班牙人,他们平时的交流也多用西班牙语,所以三毛在写他们的对话的时候,就已经是把对话从西语翻译成了汉语,而在本文中,又把三毛翻译的汉语翻译成了英语,多重翻译,必然会丢失很多原汁原味。但从另一角度看,三毛在描写他们的对话时,必然有她自己的用意,写成任何意思都是她的原作,所以,此时翻译成英文,也只是一重翻译,只要英语读者能感受到三毛的原意,就是合格了。
且看译文,第一句中,“闲话不说”, 如果按原文直译,则可译为"Not to make more rubbish talk", 但闲话一词如译为"rubbish talk", 则与原文基调不符,毕竟原作者是一个笔尖灵活的女作家。此时反说正译,译为"To cut directly to the topic", 则符合英语习惯,让人一看即懂。
“母亲在台湾”,汉语为主系表结构做主语从句,而译为英语时,以插入语的形式修饰主语结构中的主语成分,即"My mother, who is living in Taiwan"。这是因为,汉语是主题显著的语言,很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而英语为主语显著的语言,如果说"My mother lives in Taiwan"是心痛的主语,是讲不通的,因为"心痛"的施动人为"母亲"。所以,在译此处时,采用了归化的方法。
"知道我婚姻后因为荷西工作的关系,要到大荒漠地区的非洲去,十二分的心痛",汉语语序习惯先写因后写果,而英语语序习惯先写果后写因,在译此处时,采用归化的方法,先写果"felt so heartbroken",再写因"that I was moving to the African desert with my newly married husband Jose"。
"饭票" 凭以买饭的票券,这里引申指能够负担得起日常生活消费、提供"长期饭票"功能的男人。在译文中,选用了对等意义的短语"the source of income of this family"。此处采用的即异化的方法。
"食客只有一个不付钱的",其中"食客"为去"饭店"吃饭的人,如译为"the people who eat in the restaurant", 既罗嗦又显得生硬,直接用"customer",与前文"restaurant"想联系,"食客"一意自然就出来了。而"不付钱的"译为对等短语"eating gratis",即"吃白饭的"。
"荷西下班回来总是大叫:'快开饭啊,要饿死啦!'"根据小说的描述,可知荷西并不是一个文雅精细的人,猜想当时荷西所说的可能是"Dónde está la comida?",即"饭呢?"此口语也恰好符合他的人物性格,说话直接简练,一语中的。此处采用归化的方法,译为"Where's dinner! I'm starving!"原文仍是主题显著的句子,突出了"饿",而译文均采用了增补法,把主语补全。
"我这'黄脸婆'倒是做得放心。""黄脸婆"一词为中文特有的词汇,在英文中并没有对等的词汇,这也许与以这两种语言为母语的人群的人种有关。比如,如果一个白肤色的英国妇女消瘦疲惫,可能其肤色会倾向于苍白而非黯黄吧。但,这里原作者用引号将"黄脸婆"一词进行标注,稍有自嘲的情趣,大概指她快成了家庭主妇。即"rest assured as a simple 'housewife'."
"'这个啊,是春天下的第一场雨,下在高山上,被一根一根冻住了,山胞札好了背到山下来一束一束卖了换米酒喝,不容易买到哦!'"异化也指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异域性,故意打破目标语言常规的翻译。它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丰富目的语文化和目的语的语言表达方式。[2]这一长句的整体采用了异化法,这些人文风情及原文作者所添加的虚构情节,对于英语读者是较难理解的。类似的直译名词还有,如"蚂蚁上树",译为"ants on the tree","很贵的鱼翅膀",译为"dear fish wing"。此处之所以用"dear"而不用"expensive", 是因为这是荷西所说的话,所以选择了发音较短较为顺畅的"dear"。
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曾指出,翻译有两种情况,"译者或者尽量尊重原著,让读者适应作者;或者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3]尽管他倾向于异化,即保留作者的异域情调,让读者去适应译者,但在文学作品中,有很多语言习惯在源语和目标语中是十分不同的,如果大量异化并不做足够的注释,容易让读者觉得匪夷所思,而且也失去了文学作品的可读性。而适度的异化会一方面保留源语的异域情调,而且其归化的译文会让读者真正享受其间。
"翻译的任务在于发现翻译语言中的意向,并从这种意向出发唤醒原作发出的回声。"[4]本译文一方面尽量保留了原文作者的语言风格,轻畅明快,用语简练,又带有风趣的情调。这也应属于语体的异化。
参考文献:
[1] 韩青.2011博文
[2] 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2001.《译者的隐形》(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3] 施莱尔马赫《论翻译的不同方法》
[4] 《施莱尔马赫和本雅明的翻译理论》 君行齐修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