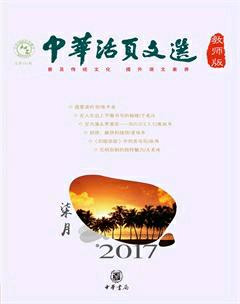元明杂剧的独特魅力
王星琦
我们通常所说的“元明杂剧”,乃是一个偏意词组,主要指的是元代北曲杂剧,或径直称之为“元曲”。当然,“元曲”这个称谓,又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元曲,还包括散曲,而狭义的元曲,则专指元代的北曲杂剧。之所以又习惯上称“元明杂剧”,是因为除却《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之外,明人编的杂剧选本往往杂入明初人的作品(包括由元入明作家的作品),如最为通行的《元曲选》,即是如此。尽管明人的作品数量有限,它却是元杂剧创作的余绪,其中确有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如果我们着眼于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线索和规律,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封建王朝的陵替而断限,我们是不难发现明初北杂剧创作与元人杂剧在精神上是有相通之处的。有的学者将元明杂剧的下限延至嘉靖间,显然是取较为宽泛的意义。将北曲杂剧称作“元明杂剧”,实始于明人,约定俗成,沿用不废。如明人息机子所编《古今杂剧》,其中“今”字,就意味着有明人的作品;另一种明代选本“继志斋本”,索性就叫《元明杂剧》。
近年来又有“金人杂剧”“金元杂剧”之说。早在60年代,戴不凡先生曾写过一篇《王实甫年代新探》(后收入《戴不凡戏曲研究论文集》),提出“我们通常所说的杂剧,根本不是元朝一统中国以后从天而降的”,认为“金代确有杂剧”。但没有具体的文献佐证,只是从现存杂剧作品中寻找了一些内证,故未曾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1990年,徐朔方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第46辑发表了《金元杂剧的再认识》一文,沿着戴不凡先生的思路,做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认为“元曲一词应当更正为金元杂剧,或更谨慎地说,金(宋)元杂剧”。徐先生虽然仍是采取内证的方法,但例证更多,并结合内证作了审慎而又细微的推测和判断,不仅为戴说张目,同时也使得“金元杂剧”的称谓成为一家之说。
本文取“元明杂剧”的称谓,盖因其普通和习惯,并非未曾注意到各家不同的看法。
元明杂剧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产物,也是宋元时期市民文化的丰硕的果实,它在中国戏曲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与古希腊戏剧或者说欧洲传统戏剧相比较而言,中国戏曲的确是晚出的,个中原因,极为复杂。然而,唯因这种晚出,则所积弥厚,使得我国各门类传统的文学艺术和表演技艺在经历了长期的、高度的发展之后,又随机性地在勾栏瓦肆中互相汲取与溶汇,终于使以综合性为其主要特征的中国戏曲艺术的诞生成为必然趋势。毫无疑问,宋元时期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戏曲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因为戏曲艺术的基本观众是市民阶层,故而市民阶层的审美心态、欣赏习惯,甚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自然也就成为我们阅读欣赏、并进而探讨杂剧艺术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在杂剧产生以前,正统的诗文一直占据着文坛的统治地位,而宋元时期戏曲小说的逐渐勃兴,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状态。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才将宋元时期看作是文学史、艺术史上一个大转折的时期。元曲与唐诗,宋词的鼎足而立,便是大转折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读元明杂剧,既要看到它与我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联系,更要注重它的特殊性。
说到联系,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古老的诗歌传统对元明杂剧的深刻影响,它首先是诗的戏剧,是“美文舞蹈的、诗韵兼全的”一种艺术形式。元明杂剧不仅汲取了诗词歌赋的韵律之美、意境之美,还熔铸了诗的灵魂和精神。只要认真读一读《西厢记》《汉宫秋》等杰作中优美的曲词,就不难领略到这一点。如明人何良俊评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之[圣药王]曲曰:“清丽流便,语入本色;然殊不浓郁,宜不谐于俗耳也。”(《曲论》)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评李好古《张生煮海》一、二折,称其“陆续铺陈的叙海洋风景的曲辞,更是壮丽眩目,可以作为一篇《海赋》来看”(《元人杂剧概说》)。尽管不同作家的作品风格不同,前贤对元剧作家有“本色”“文采”两派之分,但元明杂剧中抒情写景的曲辞追求诗韵和意境之美,却是相通的。这个特点比较显然,兹不赘述。总之,诗魂铸就曲的灵透与流利,影响到了后世戏曲,以致形成了民族戏曲突出特色之一。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在文学史的联系中看清流变与发展。然而,元明杂剧毕竟是完全不同于诗歌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是属于更高级的形态——戏剧诗时代的东西。它的曲词必须与情境、矛盾冲突以及人物形象塑造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必须与表演艺术水乳交融,因此,与诗词文赋的读法就有许多的不同。所获得的感受自然也就大异其趣。《元曲选》的编订者臧晋叔在《元曲选序二》中谈到了曲与诗词的大不同,很有意味:“词本诗而亦取材于诗,大都妙在夺胎而止矣。曲本词而不尽取材焉,如六经语、子史语、二藏语、稗官野乘语,无所不供其采掇,而要归断章取意,雅俗兼收,串合无痕,乃悦人耳。”即是说,杂剧展现的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它无所不包,故须兼收并蓄,雅俗共赏,便是所谓“情词稳称之难”。这里所说的“难”不仅是指剧作家创作之难,也隐含着欣赏者体味之难,。王国维激赏《窦娥冤》第二折的[斗虾蟆]等曲,说:“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宋元戏曲考》)又在列举郑德辉《倩女离魂》第三折[醉春风]曲后云:“此种词如弹丸脱手,后人无能为役。”(同上)王国维是真正读懂读透了元曲,读出了韵味,他不仅将其当作戏剧的文学剧本来读,且当成美文来读:“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其写景抒情述事之美,所负于此者,正不少也。”(《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写于1912年,是中国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之作,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合起来,被称为戏曲小说研究的双璧。即使今天,它仍然是我们探讨研究元明杂剧的案头必备之作。明清人虽有不少的曲论和评点类的著作,但真正系统深入地研究元明杂剧,实始于王国维此著。王氏论元曲,强调元曲的自然之美,他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在同一著作中,他又指出“元剧最佳之处……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足见王氏的“自然”与“意境”是互用的,至少是密切相关的,这显然与他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境界”说有着某种息息相通之处。中国艺术,特别重视意境。元剧广泛汲取其他各门类艺术的滋养,其重意境则是当然的。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它的“自然”与“有意境”又与诗词文赋不同,极饶独特性,这就是它总体风格上的恣纵、奔放、朴野、犷悍,即本质上的自然之美,本色之趣。这个特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其艺术语言方面。清人徐大椿谓元人作剧,“因人而施,口吻极似,正所谓本色之至也。此元人作曲之家门也。知此,则元曲用笔之法晓然矣”(《乐府传声》)。例如郑廷玉的《看钱奴》第二折,写周荣祖风雪中卖子的曲词,十分动人。青木正儿称其为“极别致的杰作”,“在大风大雪中出卖儿子的那一场,写得特别好”(《元人杂剧概说》)。元明杂剧中写風雪而富特色的剧本还有一些,如《破窑记》《冻苏秦》等。值得一提的是,明初无名氏的《贫富兴衰》(有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据脉望馆本校印),亦见特色,颇值得我们重视。第一折[点绛唇]以下三曲,起手不凡,先声夺人:
四野云迷,雪花飘坠;长空内、柳絮纷飞,裁剪的鹅毛碎。([点绛唇])
以下二曲与首曲一气呵成,将雪景描写与人物内心活动溶成一片,用语精炼,比喻恰切,写得气象开阔,画面感极强,真可与《水浒传》中“风雪山神庙”的描写相媲美。这一类的曲词读得多了,才能真正感受到王国维“千古独绝文字”的评价是有的放矢,绝非溢美。
倘若细味王国维的“自然”观和“意境”说,我们不难悟出其所指绝非仅仅是在语言艺术方面,“自然”之誉当然包括剧作家深刻敏锐的思想感情,“意境”说也与戏剧情境、人物命运以及矛盾冲突相联系,语言文字自然是情感与思想自然的外化,而深层的东西当然是思想感情和内容。因此,以“自然”和“意境”评价元剧,是王氏对传统曲论的一个突破性贡献。
为什么元剧对社会的黑暗、政治的窳败所作的揭露与抨击不遗余力?何以反抗精神、抒发与宣泄牢骚愤懑成了元剧的主旋律?这正应了《陈州粜米》中的一句曲词:“温柔不过溪间水,到了不平地上也高声。”即不平则鸣,不吐不快。元曲家不择题材,信手拈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至文人轶事、神仙道化,都可以用作不平则鸣、一吐为快的载体。严格说来,元明杂剧很少有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但又几乎所有的剧作都曲折地映照着现实社会。《窦娥冤》《陈州粜米》自不必说,《王粲登楼》《荐福碑》且不去论。就说神仙道化戏吧,细究深味,元人为之恐怕意不在企望羽化登仙,亦不在把玩神异和奇幻,而分明是在品味人生,寄情于讽世。度脱与点化,不过是个外壳,内里却是别有追求的。这就是不与元蒙统治阶级合作,消极反抗,在内心世界里求得人格的自由与重塑。我们不能苛求元代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只有一个模式的生活态度,个性的发展、人格的独立,必然是有差异的。如马致远的创作,在总体风格上与关汉卿形成鲜明对比,他是消极反抗的典型作家,可是在《荐福碑》中他也流露出不少的牢骚愤懑。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美主义的作家。他关心现实的方式与关汉卿不同,对其杂剧作品未可笼统厚非。他如范康的《竹叶舟》,也是一本神仙道化剧,其中的浩浩的人生慨叹,否定现实社会的不遗余力和愤世嫉俗的激昂情绪,都是掩抑不住的,很难以空幻、消极等说法简单加以论定。读元明杂剧,不注意到这一点,即使不是一个失误也是一种缺憾。一般说来思想倾向比较显豁的作品相对容易读一些,前人的研究探讨也多一些,难点正在那些曲折隐晦的作品,这一点不可不察。“显豁”的说法,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此类作品也不是说泛泛读过即可明了,如公案戏、水浒戏,同样包含着曲折性和隐喻性。所谓“梁山泊东路,开封府南衙”,企望清明和公道,揭露黑暗和腐败,表达人们的理想和愿望,往往借助于人们所熟悉的故事,便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头之垒块”。在剧作家,是借宋代故事指擿和批判元明间社会现实,在观众,则是到勾栏瓦舍中去求得心理上的抚慰和平衡,企望有包拯、张鼎一类清官出来,株锄奸恶,或冀希梁山泊好汉们再世,铲除不平。郑振铎先生说得好:“平民们去观听公案剧,不仅仅是去求得故事的怡悦,实在也是去求得快意,去舞台上求法律的公平与清白的!”(《中国文学研究》)今天的读者或研究者,必须对这种特殊的心态烛微洞幽,细细品味。如《窦娥冤》这个戏,可以看作中国古典悲剧典范性的作品,它从总体上、根本上否定了黑暗的元代社会,同时也具有某种对整个封建社会加以否定的精神,这从第三折开始的三只名曲中透露出来。[滚绣球]中有两句:“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王季思先生认为日月是隐喻君临天下的皇帝,鬼神则暗指各级官吏(见《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之《窦娥冤》眉批)。这个批语值得再三体味。在无名氏的《陈州粜米》中,官府与平民之间的冲突可谓怵目惊心,那象征着特权和压迫的紫金锤贯穿全剧,用意极深。最后包拯让小撇古用紫金锤击杀小衙内,带着浓重的平民们的理想色彩。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其看作是一个时代反抗精神的折射。剧作家们种种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都自觉不自觉地宣泄着平民们的心声。即使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一类的作品中,往往也带有强烈的理想色彩。这正是元明杂剧的主流精神。
阅读欣赏元明杂剧,不仅要把它看作是文学作品,还必须注意到它作为戏剧的一些特点,或者说它是特殊的文学作品,要兼顾案头和场上。这就需要一些专门化的知识,如关目处理、排场布置、角色行当、科诨穿插等等,都必须在读赏中注意到。清人黄振曾说过:“词曲譬画家之颜色,科白则勾染处也。勾染不清,不几将花之瓣、鸟之翎混而为一乎?故折中如彼此应答,前后线索转弯承接处,必挑剔得如,须眉毕露,不敢稍有模棱,致多沉晦。”(《石榴记·凡例》)黄氏所谈是曲词与科白之间的关系,他设喻揭出,颇得心会。元明杂剧中有许多曲白相生、互为映带的好例子。我们这里以马致远《岳阳楼》第一折中的曲白为例。吕洞宾扮作卖墨的先生来到酒楼,要以一块墨换酒喝,酒保不换,正末扮吕洞宾唱[后庭花]:
这墨瘦身躯无四两,你可便消磨他有几场,万事皆如此。(带云)酒保也,则你那浮生空自忙。他一片黑心肠,在这功名之上。(酒保云)我不要你这墨,你则与我钱。(正末云)墨换酒,你也不要?(唱)敢糊涂了纸半张。
墨在这里分明是追逐功名的读书人的象征性替代物,语语双关,句句讽喻。酒保的不识货,似也暗指元代知识分子不被识用,志不得伸。你看吕洞宾与酒保一来一去,倘若在舞台上演出,一定煞是好看。假若这只曲子中间不夹宾白,韵味不是要大减了吗!又如科诨的穿插,关汉卿每剧必用,且都极饶情趣,非是漫作和敷衍。孔尚任深明此中奥妙,《桃花扇》中的科诨就运用得恰到好处,深得元人精神。他说:“设科之嬉笑怒骂,如白描人物,须眉毕现,引人入胜者,全借乎此。”(《桃花扇·凡例》)要之,立足于中国戏曲综合性特点以及以抒情写意为主要手段的基点上,多看多琢磨,自会读出兴味来。董每戡先生说:“戏曲不光是曲子,它是戏,铁定为舞台上演出用的戏……我们必须跟历来的曲论家们不同,不能不设想着它活在舞台上那个当口的灵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长生殿论》)虽说这是泛指读古典戏曲,然与读元明杂剧同样适用。这里附带说到,一向有一种误解,以为元明杂剧是近古的东西,读起来仿佛比读中古和上古的东西容易得多。事实上元明杂剧中的特殊用语范围极广,俗语方言,市井谣谚,甚至勾栏切口、帮会行话,应有俱有,连蒙语也间或出现,文字上的障碍也不在少数。有时要借助于一些工具书,过去徐嘉瑞、陆淡安等先生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王季思先生也在校注《西厢记》时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则以顾学颉、王学奇合编的《元曲释词》较为全备。此外,要真正读懂元明杂剧,还必须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文人心态、典章制度以及职官吏制、风俗民情有所涉猎,具备多方面的修养。又因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多数是“世代积累型”作品(徐朔方先生说),故读元明杂剧又必须涉猎一些小说作品和其他姊妹艺术的作品,在比较分析中求得有所创获。
黄宗羲说:“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又一尽。”(《明夷待访录·原法》)揣摸其意,似在说秦一统后,在思想上是对上三代的一个反拨;而元代异族入主,传统文化出现断裂,是对汉以来所谓正统思想的一个大冲击。读元明杂剧,确有不少“离经叛道”的东西,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过去我们强调元代政治黑暗的一面,原本无可非议,然过犹不及,我们同样要注意到问题的另一面。如元代究意是“文网密、禁语多”,还是文禁少,较宽容?近年来在这方面的探讨有所深入。其实很简单,要视具体时间、场合而论,不可笼统言之。李约瑟曾谈到中国十三世纪是科技史上最辉煌的时代,颇能启发我们深入思考一些问题。许多材料都能说明元代并非黑暗到一塌糊涂的地步。不少前贤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郑振铎、刘大杰等先生,还有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都有不谋而合的论述。如刘大杰就认为元代的新政治使得旧精神、旧信仰崩溃了,“文学得到了新的发展的机运和自由”,它“从旧的圈套和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商务版《中国文学发达史》216页)。吉川氏则说:“元初的社会是人们的生活脱离传统,而弥漫着清新与活泼的社会……这种促成杂剧勃兴的社会力量,充实了作者的精神,也在作品里洋溢着无限的活力。”(《元杂剧研究》下编二章)这样的看法,是否与我们所说的元代社会黑暗相矛盾呢?不是的。元代社会政治上黑暗,思想上却相对比较解放,这与少数民族统治以及传统文化发展链条上的断裂有关。大转折的时代造就了相应的天才。没有“书会才人”的出现,元杂剧的繁荣是不可设想的。这种宏观上的总体认识,对我们深入研究元明杂剧,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关于元明杂剧的独特性以及阅读、研究中的问题,尚有多端,限于篇幅,本文只是举其大略而已。
(选自《古典文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