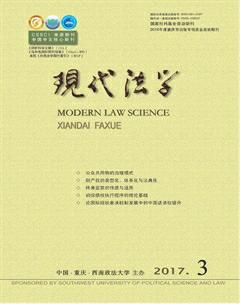宋例新探
吕志兴 曾友林
摘要:在中国古代,例的基本含义有二:一指判例或先例,此乃本源之义;一指法律原则或规定,多用于法典、制敕中。宋代以例为构词元素的法律术语多从第一义项,除条例、则例外,大多指判例、先例和惯例。宋例与制定法的关系是“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是制定法的辅法,在法律体系中位阶最低。但惟常例(判例、先例)和惯例性质的例才是制定法的辅法,是法律渊源,而优例则否。宋例虽备受批评,但因其具有补制定法之不足的功能及简便、风险小等优点,在实践中被大量援用,其实际地位比较高。
关键词:宋例;判例;先例;惯例;法律渊源
宋代的例是个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复杂之因有二:一是缺乏能够说明其性质及内容的文本资料;二是涉及例的史料极多,容易混淆,难以把握。学界对宋例已有一定的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尚未弄清楚,比如以例为构词元素的法律术语很多,如条例、则例、断例、旧例、近例、定例、常例、优例、乡原体例等,它们的含义分别是什么?宋例是否是判例或者仅仅是判例?宋例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实际地位如何?鉴于此,本文拟在学界同仁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前揭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例之基本含义
关于例之含义,《说文解字》解释曰:“例,比也,从人。”例与“比”密切相关,比,比照、参照的意思,原为动词,指比照、参照某人的某件事以处理类似的事情。后“比”字名词化,被比照、参照之事称为“比”,又称“决事比”。对于决事比,汉、唐学者做有解释,东汉经学家郑众为《周礼·大司寇》中“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作注曰:“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弊之,断其狱讼也。”唐代经学家贾公彦对郑注疏解日:“先郑云:‘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者,此八者,皆是旧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断事,皆依舊事断之,其无条,取比类以决之,故云决事比也。”决事比即被比照以决断类似事情的案件或事件。汉以后,古人将被比照、参照之事称为“例”,并且“比”和“例”互称。比如,对于宋神宗时官员张仲宣犯受财枉法罪,法官比照李希辅案从轻处理一事,《宋史·刑法三》记载为“法官坐(张)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而《宋史·苏颂传》的记载是“法官援李希辅例,杖脊、黥配海岛。”前者的“前比”和后者的“李希辅例”指的是同一事情。所以,例亦是被比照、参照来处理类似问题的事件,此义项为例的本源之义。例用于法律领域,其基本含义则指被比照、参照来处理类似法律问题的案例和事例。如宋代人所指出的“夫例者,出格法之所不该。故即其近似者而仿行之,如断罪无正条,则有比附定刑之文。法所不载,则有比类施行指挥,虽名日‘例,实不离于法也。”被比照、参照来处理类似法律问题的案例和事例,借用现代法律术语,可分别称为“判例”和“先例”。
例作为法律术语,其基本含义不限于判例和先例,用于法典及皇帝的制、敕中,则有法律原则或法律规定之意,如《唐律疏议》中对“名例”的解释是:“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名例”中之“例”即为“法例”,“法例”之“例”是五刑适用的主要规定,亦即刑法原则和制度。《唐律疏议》和《宋刑统》的律文和疏议中都有很多的“例”字,如《宋刑统》卷六《名例律》“断罪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条规定:“诸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同者,依本条。即当条虽有罪名,所为重者,自从重。其本应重而犯时不知者,依凡论;本应轻者,听从本”。疏议日:“例云:‘共犯罪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斗讼律》:‘同谋殴伤人,各以下手重者为重罪,元谋减一等,从者又减一等。又例云:‘九品以上犯流以下,听赎。又《断狱律》:‘品官任流外及杂任(释日:杂任,解在《杂令》),于本司及监临犯杖罪以下,依决罚例。如此之类,并是与例不同,各依本条科断。”引文中几处“例”都是法律原则之意,特别是“疏议”中两处“例云”后面的内容,本身就是《宋刑统》中的刑法原则。
南宋编纂的法典《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赦降·名例敕》规定:“诸犯罪会降,称死罪降从流者,流三千里(注:本条罪不至死,有编配法者,依不至死编配例)。”敕条“注”中所说的“编配例”之“例”,显然是对应于上文的“编配法”的,指“不至死编配法”的具体规定。又如卷七十六《罚赎·名例敕》规定:“诸犯罪情轻,杖以下听以赎论。即公人有罪而朝省或按察官司令勘决者,不用此例。”该条中“不用此例”之“例”,即指敕文关于“诸犯罪情轻,杖以下听以赎论”的规定。而卷七十三《检断·名例敕》的规定更能说明问题:“诸敕、令无例者从律(注:谓如见血为伤,强者加二等,加者不加人死之类),律无例及例不同者从敕、令。”这里的“例”则是法律规定之意,因为律、敕、令都是制定法,其中没有案例或事例。
宋代有几部“编敕”中有“总例”,如《嘉祐编敕》《熙宁新修审官东院编敕》《熙宁五路义勇保甲敕》皆附有“总例”1卷。有学者认为“总例”是指“编敕”的修撰凡例而言,并非断例之“例”。笔者以为,“总例”是法律原则或原则性规定,类似于《庆元条法事类》中的“总法”。《庆元条法事类》卷五十“释道门”、卷七十六“当赎门”、卷七十九“畜产门”中都有“总法”一目,卷十四“选举门”有“荐举总法”一目,卷二十八“榷货门”有“榷货总法”一目,其所编录的虽仍是敕、令、格、式,但从内容看都是对各该门类有关问题的原则性规定。
在皇帝的制、敕中,例也作法律规定解,如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七月诏:“群臣举官,例皆连坐,宜有区别。自今朝官、使臣、幕职、州县官,须显有边功,及自立规划,特著劳绩者,仍以名闻。如考覆之际,与元奏不同,当行朝典。或改官后犯赃,举主更不连坐。如循常课绩历任奏举者,改官犯罪,并依条连坐。其止举差遣,本人在所举任中犯赃,即用连坐之制。其改官他任,纵犯赃罪,亦不须问。”其中“群臣举官,例皆连坐”之“例”,与后面“连坐之制”的“制”对应,其意即指法律规定。
在上述例的两个义项中,由于“被比照、参照来处理类似问题的事例或案例”为例的本源之义,宋代史料中大多数以例为构词元素的法律术语即从此义。
二、宋例各术语之含义及其分类
(一)宋例各术语之含义
宋代史料中以例为构词元素的法律术语较多,如条例、则例、断例、旧例、近例、定例、常例、优例、乡原体例等,其含义分别是什么,学界至今语焉不详。下面以史料為据对这些法律术语之词义作解释、辨析。
1.条例
现代法律术语中有“条例”一词,指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或最高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明清时期也有“条例”一词,指由事例、案例等提炼而成的、经皇帝批准后公布实施的法律,是当时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实际上该术语在我国中古时期即已存在,如在宋代,条例作为一个法律术语已被频繁使用,有不少法律文件即以“条例”命名,如“诸司库务岁计条例”“人吏功过条例”“国信条例”“六曹寺监条例”“客省条例”“四方馆条例”;宋代的史料中也多处提到“条例”,如真宗“令礼部贡院取前后诏敕经久可行者,编为条例”。神宗命“著作佐郎俞充、大理寺丞李承之编修中书条例”。又命“光禄寺丞杜纯为枢密院宣敕库检用条例官”。崇宁年间,徽宗“下诏追复元丰法制,凡元祐条例悉毁之”。
宋代的条例是什么?从现有文献资料中未看到对宋代条例的解释或说明,现根据史料中关于条例的记载加以分析。
仁宗时,纠察刑狱刘敞指出:“朝廷旧法,不许用例破法,今顾于刑狱极谨,人命至重之际,而废条用例,此臣所不喻也。”神宗时,侍御史张汝贤奏:“按法之文而折中于理,谓有司之事。无条有例,或虽有条而文意未明,应用例以补之,皆在所司。可以常行,与法未碍,则为不应奏请可否之事,若陈乞差遣,自有定法。……又官制申明逐处例册,候册定条目不用,即知有司所用之例,自可修条。未知特旨碍法之事,能如此否?”钦宗时,尚书右丞徐处仁“乞诏自今尚书、侍郎不得辄以事诿上,有条以条决之,有例以例决之”。
上述三段引文中,均将条例之“条“和”例“分开称说,可见条例不是一物,而是两物。根据引文内容分析,条指的是制定法条文,即法条;例指的是判例、先例等在制定法之外的可以对制定法进行补充的法律渊源。可见,宋代的条例是法条和例的合称,而不是例的一种。
2.则例
关于“则例”,我们较熟悉的是清代的则例,指的是非刑事的、制度性的法律规范,是清代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宋代已有则例的概念,它是例还是制定法呢?现举涉及则例的两则史料加以说明。
仁宗嘉祐四年(1059)正月,“三司使张方平上所编《驿券则例》,赐名曰《嘉祐驿令》。初,内外文武官,下至吏卒,所给券皆未定,又或多少不同。遂下枢密院,取旧例下三司掌券司,会萃多少而纂集之,并取宣敕、令文专为驿券立文者,附益删改凡七十四条,上、中、下三卷,以颁行天下”。
哲宗元祐八年(1093)正月,户部言:“元祐元年二月五日敕:‘官员差出所带人吏,如合支期券,从本部契勘职名,依令内则例,不许陈乞别等则例,如违许劾奏。自降朝旨,差官出外所带人吏,多乞优厚券俸,申请特旨。虽依上条劾奏,而朝廷特依已降指挥,不惟紊烦朝廷,而近降朝旨遂成空文。欲今后人吏、公人差出,虽有特旨不依常制,或特依已降指挥,别支破驿券之人,并从本部只依本职名则例支给。从之。”
从上引两则史料看,则例与令关系密切,则例是令的内容。又从第一则史料看,张方平所编的法律文件原定名为《驿券则例》,后皇帝赐名为《嘉祐驿令》,则例与令可以等同,可见则例是制定法,是法律规则或规定,而不是例的一种。
3.断例
宋代的史料中关于“断例”的记载较多,除《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崇宁断例》《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淳熙新编特旨断例》外,还有涉及断例的修订过程的,如:
仁宗庆历三年(1043)三月,“诏刑部、大理寺集断狱编为例”。
哲宗元符二年(1099)四月,左司员外郎兼提举编修“刑房断例”曾旼等奏:“准尚书省札子编修‘刑房断例,取索到元丰四年至八年、绍圣元年二年断草,并刑部举驳诸路所断差错刑名文字共一万余件,并旧编成刑部大理寺断例,将所犯情款看详,除情法分明,不须立例外,其情法可疑,法所不能该者,共编到四百九件。许依元丰指挥,将诸色人断例内可以令内外通知,非临时移情就法之事,及诸处引用差互,曾被刑部等处举驳者,编为刑名断例共一百四十一件,颁之天下,刑部雕印颁行。其命官将校依条须合奏案,不须颁降天下,并诸色人断例内不可颁降者,并编为刑名断例共二百六十八件,颁降刑部大理寺检用施行。勘会申明,颁降断例系以款案编修刑名行下检断,其罪人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有荫人情不可赎之类,大辟情理可悯并疑虑,及依法应奏裁者自合引用奏裁,虑恐诸外疑惑,欲乞候颁降日令刑部具此因依申明,遍牒施行。从之。”
高宗绍兴四年(1134)七月,“初命大理寺丞评刊定见行断例。刑部言:国朝以来断例皆散失,今所用多是建炎以来近例,乞将见行断例并臣僚缴进《元符断例》衷集为一,若特旨断例则别为一书。二十六年闰十月一日刑寺具崇宁、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三百二十条,二十七年吏部尚书详定敕令王师心编修以‘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为名”。
从上引史料看,断例系已经审判的疑难刑事案件编类而成的案例选编,可分为“刑名断例”“特旨断例”。刑名断例是“其情法可疑,法所不能该者”及“非临时移情就法之事,及诸处引用差互,曾被刑部等处举驳者”之类无法可依的刑事案例的选编。“特旨断例”是皇帝特旨断狱案例的选编,关于特旨断狱,请见下文。
4.旧例、近例、常例、优例、久例、定例
宋代史料中时常出现这几个法律术语,为便于分析,试各举一例。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七月,诏:“自今应差文武臣僚充安抚使副、巡检、都监及提点刑狱之类,但系同差带职名者,并令一班辞见,合重行异位,即依常例。”
仁宗嘉祐三年(1058)十二月,閤门言:“近例,上殿班除三司、开封府、台谏官遇进辰牌不隔外,其余并次日上殿,或更有三司、开封府并高官者臣僚,亦于辰牌隔下,臣僚后引,于理未便。欲乞今后未进辰牌依旧例外,其辰牌隔下者,如至三次,得旨许令特上者,即于自来不隔之后引。从之。”
神宗元丰六年(1083)三月,学士院言:“本院久例,亲王、使相、公主、妃并节度使等除授并加恩,并送润笔钱物。自官制既行,已增请俸,其润笔请寝罢。……从之。”
哲宗元祐五年(1090)三月,右谏议大夫刘安世与朱光庭言:“……其先修例册,如有轻重过当,仍逐事参酌增损,立为定例,遵守施行。”
徽宗崇宁元年(1102)六月尚书省奏:“准条,引例破法及择用优例者,徒三年。从之。”
据上述引文并结合相关史料分析,上列六个法律术语系从例的不同特点而言的。旧例与近例均从例的形成时间着眼,旧例指从很久前甚至是宋初即形成并沿续下来的例,又称本朝旧例,因时过境迁,其与待处理案件或事件的相似度往往不高。近例指最近才形成的新例,因时隔不久,其与待处理案件或事件的相似度较高;常例和特例、优例均从例是否在正常情况下形成,其内容是否符合常理、常法的角度着眼,常例指正常情况下(如大臣依法定程序奏请)形成的,内容符合常理、常法的例。特例、优例指非正常情况下(如亲信大臣或近侍人员恃宠而索求)形成的,内容违反常理、常法,如皇帝给予某人特权或优待的例;久例从例适用时间着眼,指某例已经长久适用,被认同度较高,有的已成为惯例;定例指经过编修成册,被确定为合法有效的例。
5.乡例
对于乡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载,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殿中侍御史张廓言:“奉诏京东安抚,民有储蓄粮斛者,欲诱劝举放,以济民贫,俟秋成依乡例偿之,如有欠负,官为受理。从之。”南宋判词集《名公书判清明集》更是多处提及,如“都例:产钱至一贯者,合当充役。”“本乡则例:中等每顷四十五文。”“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乡原体例:各有时价,前后不同。”“建阳体例:交易往往多批凿元分支书。”“湖湘体例:(利息)成贯三分,成百四分,极少亦不下二分。”
从上引史料看,乡例指宋朝政府认可的,可在行政执法和司法审判中引作依据的乡里税役习惯或民间民商事习惯。
(二)宋例的分类
上文对宋代以例为构词元素的法律术语之含义进行了解释、辨析,为便于读者对宋例有进一步的认识,有必要对其加以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性质及地位进行分析。宋例虽名目繁多,但按不同的标准,可将其分为具有对应关系的几大类别。
1.判例、先例与惯例
判例、先例即已经处理过的,其精神原则可作为以后类似问题处理依据或标准的典型案例、事例;惯例指对某类事务的长期处理中自然形成的、人们自觉遵守的习惯。判例、先例和惯例都是不成文法,其区别是某例是否具有普遍性效力和规则性内容。判例、先例只具有个别性效力,即对类似的案件或事件有参照适用的效力,其精神也未形成规则性、条文化的内容;惯例则具有普遍效力,是某例长期适用并形成一定的规则性内容的习惯。在表述上,以具体某人命名的例都是判例、先例,刑名断例是判例;以某官府、某事命名的例,及久例、乡例则是惯例。
结合史料来说,判例、先例均提到具体的人或事,如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兵部尚书寇准为枢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荐之也。准未告谢,命向敏中权发遣枢密院公事。自是枢密使罢,即命宰臣权发遣如敏中例”。神宗元丰六年(1083)四月,“赠太尉刘从广妻普宁郡主赵氏乞依曹诵妻延安郡主例增俸”。这两则史料中所提及的例,均以具体某人命名,都是先例。前文提到的《元符刑名断例》等一般的“刑名断例”也都是判例。
惯例一般只笼统说例,或称久例,如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封婉仪杨氏为淑妃。……宰相言宫掖加恩,朝廷庆事,臣不可缺礼,望令客省依例受贡贺。上勉从之”。仁宗至和元年(1054)三月,“枢密使、彰德节度使、同平章事王贻永,数以疾求罢,己巳,罢为景灵宫使,加右仆射、兼侍中,仍诏特依宗室例,岁赐在京公使钱五千缗,其进奉听如两府例”。这两则史料中提到的例,均以某官府或某类人命名,都是惯例。前文提到的乡例也都是惯例。
2.常例与优例
按某例是否在正常情况下形成,其内容是否符合常理、常法,可将例分为常例和优例。常例指在正常情况下形成的,符合常理、常法的例;优例是皇帝特旨处分,给予某人特权或优待,或对有关罪犯减免刑罚,但违反常理、常法所形成的例。
在表述上,常例一般注明“后遂为例”,或皇帝在相关诏令中明确某件事“自今为例”或“著为例”,如真宗咸平元年(998)正月,“赐近臣岁节宴于宰相吕端第。自是遂以为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以高邮军民荀怀玉为本军助教,以其出米麦三千斛济饥民故也,仍诏自今为例”。仁宗天圣四年(1026)十月,诏“郎中以上致仕者,自今与一子官。时都官郎中熊同文请老,自言更不愿分司、监当,只乞录二子各末科出身。既许同文守本官致仕,仍特补其一子太庙斋郎,因著为例”。
而对优例,皇帝往往在作出特旨处分的当时即明确规定“不得为例”,如仁宗明道二年(1033)六月,“许著作佐郎张充于馆阁读书。前诏罢馆阁读书。充,宰相李迪婿,迪特为请之,仍诏不得为例”。“宣庆使、遂州观察使、入内都知麦允言卒,赠司徒、安武节度使。又诏允言有军功,特给卤簿,今后不得为例”。“诏中书检正官有兼局当给添支处,增给一处,余官毋得援例”。
3.散例与编例
以例是否被有关机构编修成册,经皇帝批准而公布,可将例分为散例和编例。宋例的来源,大致有:大理寺、刑部审断或举驳的刑事案件;皇帝以特旨处理的刑事案件;皇帝决定的或由大臣提出意见经皇帝批准而处理的行政或民事等方面的事例。例与制、敕一样,都是针对具体的案件或事件而形成的,是为散例。一段时间后,散例数量增多,前后或有矛盾,适用起来容易产生分歧,宋朝政府遂指派官员将例编修成册,经皇帝批准而公布,这就是编例。例经編修成册,一方面便于查阅和适用;另一方面,在编修的过程中,要对例进行筛选,并与制定法进行对照,将合乎常理常法的例人编,而将优例删除,宋朝皇帝要求编例的诏令对此均有明确要求,如神宗元丰(1080)三年七月诏:中书“以所编刑房并法寺断例,再送详定编敕所,令更取未经编修断例与条贯同看详。其有法已该载而有司引用差互者,止申明旧条。条未备者,重修正。或条所不该载,而可以为法者,创立新条;法不能载者,著为例。其不可用者,去之”。又如崇宁元年,“令各曹取前后所用例,以类偏修,与法妨者去之”。所以,编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立法的过程,被编修成册的例比散例地位更高,可优先适用。在宋代,一般称“例”的,都是散例;称“例册”,及以皇帝年号命名的“刑名断例”“特旨断例”都是编例。
三、宋例的性质及地位
(一)宋例的性质
宋例的性质所指有二:一是指其部门法属性,二是指其是否是一种法律渊源。
关于宋例的部门法属性,比较容易理解。宋例在部门法属性上大多属综合性的,其中有一部分是刑事方面的例,如上文中提及的《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名断例》《崇宁断例》《绍兴刑名疑难断例》《乾道新编特旨断例》《淳熙新编特旨断例》皆是。说它们都是刑事例,从名称上即能看出。另外,断例在编纂上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例、捕亡、断狱12门,与《宋刑统》篇目完全相同。散例中也有一些刑事例。乡例主要是民商事性的例。但无论是散例还是编例,绝大多数的例都是非刑事例,特别是与行政机关工作有关的例数量较多,其中与吏部工作有关的选举、任官等方面的例最多。
宋例是否是一种法律渊源,即是否可作为处理类似案件或事件的法律依据,学界对此分歧较大。传统的观点认为,宋例是判例,是法律形式,在司法审判方面“有高出于法律的效力”;戴建国认为宋代的“断例”是一种判例。王侃则对传统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宋例不是判例、先例,不是法律淵源,只有少数“例子”之例才是“成例”“事例”,才是法律渊源。
笔者以为,学界关于宋例是否是一种法律渊源的认识存在着不足。传统的观点缺乏分析、论证,过于简单,与史料中所反映的宋例的情况亦不相符;戴建国对宋代断例中的“特旨断例”关注不够,结论不够全面;王侃的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但过于强调和夸大“特旨断狱”和“特旨除授”在宋例中的比重,以致完全否认宋例的判例、先例性质,只承认少数例是“成例”“事例”,且未注意到宋例还包含惯例等内容,也有失偏颇。因此,学界关于宋例性质的观点需要补正。宋例是否是一种法律渊源,应作如下区分:
1.惯例性质的例是法律渊源。从本文第二部分的内容看,惯例性质的例在处理行政事务和司法审判中被引作依据或标准,影响着各该案件和事件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无疑是一种法律渊源。
2.常例,即符合法律精神的、可被援引处理类似行政事务之事例(先例)和类似司法问题之案例(判例),是法律渊源。从史料看,宋代很多行政和司法疑难问题都是援引例来处理。处理行政事务时,遇到法律无规定的情况,如果查询有类似的先例,均依先例而行,无须多议。如:神宗元丰六年(1083)四月,“赠太尉刘从广妻普宁郡主赵氏乞依曹诵妻延安郡主例增俸。诏:吴王元俨女,皇家尊亲,同行存者止此一人,可特给月俸百千,春冬衣各增十匹,生日增银五十两”。哲宗元祐七年(1092)十一月,“三省言,郊礼毕徐王加恩,赏赐剑履上殿,缘虚文,已删去,请岁增公使缗钱。太皇太后曰:‘尝有例耶?吕大防对曰:‘仁宗时荆王元俨增至五万贯,徐王昨亦增赐,今为三万缗。于是诏许增三千缗”。郡主与藩王都是皇室宗亲,从血缘至亲关系而言,为其增俸或加赐属理所当然,但因其涉及国家有关制度,统治阶层较为慎重,但该两例中,最高统治者见已有先例,未作过多讨论,便依例而行。在这种隋况下,先例均作为处理类似问题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渊源。
在司法审判中,遇法律没有规定的情节,司法机关则援引判例来定罪量刑。如《折狱龟鉴》载:“陈执方大卿通判江州时,民饥。有刈人之禾而伤其主,法当死者。执方以为:‘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尽矣,然尚缓刑,况于今哉!即奏贷其死。”关于陈执方奏请免除罪犯死刑的依据,《折狱龟鉴》之作者郑克在“按语”中作了补充说明:“李士衡观察权知天雄军。民有盗瓜伤主者,法当死,士衡以岁饥奏贷之,自是著为例。执方之奏,盖用此例也。”偷盗并伤人,属抢劫重罪,但案犯有法律未规定的“民饥”从轻情节,司法官员援引有关判例上奏,使案犯被“贷死”,即免死,其所援引的判例实际上是处理该案件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渊源。
具有法律渊源性质的常例(先例和判例)有一个特征,即都是被确定“自今以为例”或“著为例”的例,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五月,“以高邮军民荀怀玉为本军助教,以其出米麦三千斛济饥民故也,仍诏自今为例”。又如:“襄州饥,人或群人富家掠困粟。狱吏鞫以强盗。(马)寻曰:‘此脱死尔,其情与强盗异。奏得减死。论著为例”。
3.优例,即皇帝特旨除授之事例和特旨断狱之案例(特旨断例),不是法律渊源。宋代人对“特旨”的解释是:“特旨乃法令之外,出于人主之意,惟君上得专,非人臣所拟。”“特旨者,人君之利柄,以法令与罪人之情或不相当,则法轻情重者,特旨重之;法重情轻者,特旨轻之。”特旨即皇帝根据需要对有关问题于法外而作的变通处理,包括特旨除授和特旨断狱。特旨除授主要是皇帝对亲信大臣及近侍人员于法外以特旨的形式予以擢升或荫补其子孙或给予特权和好处的决定,这种情况在宋代很多,宋朝官员连篇累牍地上奏反对用例,针对的主要就是此类例。特旨断狱是皇帝对司法机关因“罪人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有荫人情不可赎之类,大辟情理可悯并疑虑”而上奏的案件,以特旨的形式于法外或予加重或予减轻处罚的决定。从现有资料看,宋朝皇帝特旨断狱中予以加重处罚的虽不乏其例,如哲宗元祐六年(1091)八月,开封府有一抢劫杀人案,“刑部侍郎彭汝砺引例,乞加贷配。执政不以汝砺所言为是,降特旨皆杀之”。但予以减轻处罚的则为绝大多数,如《宋会要辑稿·刑法·矜贷》收集了皇帝特旨断狱的案例约180个,其中172案中罪犯被减轻处罚,或免死,或减刑,或免罪。
皇帝特旨除授之事例和特旨断狱之案例即优例,因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精神,在行政和司法中禁止援引。禁止援引特旨断狱之例(特旨断例),宋初制定的基本法典《宋刑统》即有规定:“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人者,以故、失论。”制敕断罪与制敕不同,制敕是皇帝依法定程序发布的命令,是宋代重要的法律渊源,臣民必须遵守执行。制敕断罪即皇帝对有关犯罪以制、敕的形式于法外作出的变通裁决。制敕断罪就是特旨断狱。宋律对皇帝制敕断罪的案例禁止作为例而援引,否则造成不利后果,司法官吏要承担故意或过失出入人罪的法律责任。这里有一个问题,即:既然皇帝特旨断狱的案例禁止援引,那为什么宋朝政府还要将特旨断狱的案例编订成如《乾道新编特旨断例》《淳熙新编特旨断例》的断例汇编呢?合理的解释是:尽管皇帝特旨断狱可以超然法外,但宋朝统治阶层还是希望皇帝在特旨断狱时,能参考以前皇帝裁断的理由,不要太过随意。编订“特旨断例”即为皇帝提供这样的参照,是对皇帝特旨断狱随意性加以限制的一种努力。
特旨除授的事例,皇帝在相关诏令中即规定“毋以为例”“不得为例”,禁止援引。有关史料上文已有引证,又如: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月,因此前“诸王子初授官,即为诸卫将军,余以父官及族属亲疏差等。诏宗正卿赵安仁参议定制,安仁请以宣祖、太祖孙初蔭授诸卫将军,曾孙授右侍禁,玄孙授右班殿直,内父爵高听从高荫,其事缘特旨者,不以为例”。如有关人员妄行援引的,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徽宗崇宁元年(1102)六月尚书省的奏:“准条,引例破法及择用优例者,徒三年。从之。”
被禁止援引的例自然不是处理有关事务的法律依据,也自然不是法律渊源。
(二)宋例的地位
宋例与律、(编)敕、令、格、式、制、敕、宣、申明等制定法的关系是“有司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后用例”。有法而用例,是不允许的,如南宋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左正言李次膺奏:“近有废法而用例者,……且事或无条乃可用例,事既有条何名为例?一例既开,一法遂废。望今后凡有正条,不许用例。”若法有明文而引例决事断狱或有常例而援引优例决事断狱,徇私枉法的,要追究刑事责任,徽宗崇宁元年(1102)即规定:“引例破法及择用优例者,徒三年。”故例只是制定法的辅法,在法律体系中位阶最低。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制定法的辅法,适用“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原则的例仅是具有判例、先例、惯例性质的例,如常例、久例、定例、乡例等。优例被禁止援引,不是法律渊源,自然不是制定法的辅法。断例中只有“刑名断例”具有判例性质,是制定法的辅法,是法律渊源,而“特旨断例”则否。
宋例中因有数量不少的优例,一些官吏为其一己之私,往往舍常例而援引优例,宋代有“谚称吏部为‘例部”的说法,便是对吏部过多援引优例的讥讽。这种做法,使法制受到较大程度的破坏,因此宋例受到正直官员较多的批评,有官员甚至建议尽废例而不用。尽管如此,终宋之世,例被大量援引的局面并未改变,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援例决狱有制定法依据
宋代在司法中实行疑狱奏谳制度,要求地方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时,若遇有疑难,依常法不能决断的,必须申报朝廷,由大理寺审断,刑部复核后提出意见,奏请皇帝裁决。刑部提出的处理意见必须附上相关的断例,供皇帝参照,即所谓“贴例”。如宋代官制规定,刑部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若情可矜悯而法不中情者谳之,皆阅其案状,傅例拟进”。即规定刑部处理奏谳案件,必须附例上奏。元丰五年(1082)神宗又下诏:“刑部贴例拟公案,并用奏钞。其大理寺进呈公案,更不上殿,并断讫送刑部贴例。不可比用及罪不应法,轻重当取裁者,上中书省。”规定刑部上奏谳案件均需附相关的断例,无例可附,报中书省讨论后上奏。由于疑狱奏谳制度需断例配合实施,只要该制度不废止,断例亦不可能被废除。
2.例对制定法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
宋代虽然立法活动频繁,法律渊源种类繁多,其制定法内容丰富,体系完备,但制定法不可能规定所有的问题,遇法律未作规定的事项,则以例补其缺。以例补制定法之缺,宋朝法律有明文规定:“诸断罪无正条者,比附定刑,虑不中者,奏裁。”即在审理刑事案件时,如遇对危害国家和社会的行为如何定罪量刑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可以比附定罪量刑。被比附的可以是制定法,也可以是判例。那么例是如何补制定法之缺的呢?从现有资料看,主要在一些具体情节的认定上对制定法进行补充。比如,对某一犯罪的基本事实的认定及量刑,制定法一般都有规定,但同样的行为,其动机或后果、影响往往不同,这些情节对量刑有较大的影响。对这些影响量刑的具体情节的认定标准,往往由例来补充。哲宗时刑部一份关于案件处理的奏文对例的这种补充功能提供了较好的诠解。
哲宗元祐六年(1091)八月,开封府发生杨宗等共同抢劫杀人案,其中,案犯“刘俭旧不曾为强盗,后来受杨宗结架劫刘宝家财物,到本人家等人出来。刘俭为行得脚困,于本处地上睡著。财主刘谭开门出来,其杨宗刺伤刘谭,随入堂前行抢,刺伤刘清、刘宝。其杨宗把刘清等控缚,畴刘俭方睡觉入堂前,刘俭叫道:‘不要俦他人。”该案报经刑部复核后,刑部侍郎彭汝砺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指出:“刘俭虽有逐项罪犯,然有可悯情理。”认为刘俭系被人胁迫参与抢劫,到被害人家后,既未伤人亦未抢物,且有“不要伤他人”等悔戒之言,遂援引有关判例,请求对刘俭免死刺配。但宰相刘挚“不以汝砺所言为是,降特旨皆杀之。”彭汝砺坚持己见,遂向皇帝再上奏章,指出:“臣看详刑部自祖宗以来法与例兼行。强盗杀人不分首从,在法皆死。强盗一次及盗杀人,其非为首及元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或杀人不曾见、不曾闻、不曾知,或曾有悔戒之言,在例皆贷,前后甚多。”
宋律规定,犯强盗杀人罪,不分主犯从犯皆处死刑。但在强盗杀人犯罪中有从轻情节,如“强盗一次及盗杀人,非为首及元不曾商量杀人,后来徒中杀人,或杀人不曾见、不曾闻、不曾知,或曾有悔戒之言”的,如何认定和量刑,宋律无规定。宋例则对具有这些从轻情节的,“在例皆贷”,即全部从轻处罚。宋例的精神对宋律未作规定之处作了补充。
3.援例决事断狱,简便易行,风险较小
由于判例、先例是已经处理过的案件和事件,以后遇类似的案件或事件,无须费力去做案情分析和认定,照葫芦画瓢即可,较为简便。更为重要的是,既然以前对此类案件或事件是如此处理的,现在做同样的处理,一般没有风险,不会招致批评和责罚。这一便利,不仅官吏要考虑,即使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也不能不考虑,因为皇帝虽贵为至尊,但仍须遵守祖宗之法,否则会被责以不孝。因此,在决事断狱之时,只要有例可援,无论是官吏还是皇帝,都会援例。宋朝皇帝援例以决事的事例较多,除上文已列举者外,又如: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月,“中书欲支章悖见任料钱、添支并给驿券。上批:‘惇已请添支,又请驿券,恐碍条贯,检嘉祐以来至近岁例呈。冯京言:‘近来有此例。王安石曰:‘嘉祐、治平已有例,且陛下患人材难得,今无能之人享禄赐而安逸,有能者乃见选用,奔走劳费,而与无能者所享同,则人孰肯劝而为能?如悖以才选,令远使极边,岂可惜一驿券?纵有条贯,中书如臣等,亦当以道揆事,佐陛下以予夺驭群臣,不当守法,况有近例。上曰:‘有例须支与,兼其所得不过数百,不为多也”。引文中要决断的是大臣章悖请求支付添支并给予驿券的事。按宋代制度,大臣因公务所需请求支付添支是可以的,但支付添支后,能否再给驿券,法律没有规定。此事非大事,神宗本可以立即做出决定,但此时神宗正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改革,已招致保守派的反对,加之章悖乃神宗亲信,为了不授保守派以柄,神宗处理此事较为慎重,要求查询有无先例。当冯京和王安石都说有先例,并考虑到数额不大,神宗才同意支付添支并给予驿券。宋代官吏援例以决事断狱的事例更多,其做法有时甚至达到很极端的程度,如《宋史·刑法一》载,“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
综上,宋例虽然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最低,但因其对制定法有补充功能,且援例决事断狱有诸多便利,因而在实践中被大量引用,其实际地位比较高。
本文责任编辑:龙大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