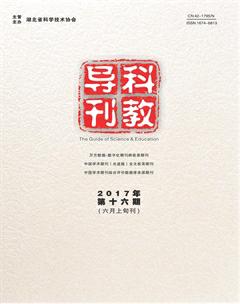《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演说辞真实性问题初探
沈芝
摘要 修昔底德《伯史》中大量运用演说辞的手法在将演说应用到历史作品的传统中是体现十分突出的。本文试图从《伯史》的原文、修昔底德求真治史风格、历史学家的大量引用中可以初步探析《伯史》演说辞的真实性。
关键词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演说辞 真实性
修昔底德《伯史》中的演说是书中精华,是作者著史时精心记录下来的。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演说既是我们研究古希腊的各方面的重要史料,又是文艺作品,应当受到重视。究竟依据何种演说分类来编列出《伯史》演说辞目录,鲁斯查纳特(Luschnat)提供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一个详尽的演说辞分类图表。鲁斯查纳特首先清楚明白地详述了41个演说辞目录,这是一种早期的看法。然后他提出自己看法,介绍了60多个这样的口头演说的单元,但鲁斯查纳特只打算把他的这种分类作为修昔底德若干不同演说辞的一种详细说明,而不是演说辞本身非常明确的目录。就目前国外史学界对修昔底德演说辞目录索引做了比较详细,相对准确介绍的学者应是斯达特(Stadter)。而斯达特本人承认,他的编目不可能是包罗万象的,有许多条目若按演说辞和叙述两者区别的客观条件来看,当不属演说辞名录下。但斯达特还是搜集整理所有这样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只要是人们所说的,则通通编入演说辞条目中,但排除了简短的叙述性陈述。结果,包括密提林对话在内,斯达特列出52个直接演说,85个间接演说,以及直接和间接演说相结合的三个演说,共141个演说。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中约占1/4篇幅,是其作品的特色。将演说应用到历史作品的传统中,修昔底德演说辞的运用体现十分突出。这种特色鲜明的写作方法引起了国外学者的争论和分歧。如理查德(Richard)、克来维尔豪斯·杰布(Claverhouse Jebb)、约翰·麦考姆·米切特(JohnMalcolmMitched)和吉格(Jeager)都认为,演说辞再现了公元前五世纪希腊社会的真实面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体现了修昔底德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和启示。持不同意见的学者罗吉(Rokeah)博士认为,演说辞只是修昔底德作品的点缀,是修昔底德杜撰编造的,以使其历史更易阅读或者显示历史事件中演说者的性格特征。他甚至认为修昔底德演说辞是色彩极浓的文学作品,以炫耀的词藻来吸引观众。
纵览修昔底德《伯史》演说辞目录,学者纷纷提出疑问的是,修昔底德为何在其著作中包括了如此之多的演说辞,至今并未达成一致。如汤普逊就认为:“修昔底德采用这些演說辞的目的何在,我们还理解不到。当他正在平静地叙述事件时,突然叫伯里克利发表讲话,我们不明白他实际上所说的是什么。也不清楚作者有意造成这样印象的意图是什么。修昔底德只是令其记述适合于人物和环境,此外并无其他。”(P45)汤普森的观点代表了一部分学者的看法,甚而至于有的学者认为《伯史》中演说辞是修昔底德著史的缺陷之所在,演说辞不仅割裂其陈述历史的连贯性和整体性,而且也戕害了修昔底德真实、精确、客观的治史风格。并认为这些演说辞涵盖的只是修昔底德自己的言词,是一种高度的修昔底德的个人风格,没有一个古代希腊演讲者利用其中任何一个演说辞在论坛上演讲过。因此,演说辞虚构特性与修昔底德客观治史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而其他很多学者,尤其近年来国外研究成果表明,认为修昔底德演说辞是虚构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伯史》中大量演说辞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也是恰当合理的。
在分析演说辞存在的原因之前,我们首先探讨演说辞是否具有真实性、史实性的问题,这事实上也关涉到了修昔底德整部著作真实客观的基础。试想如果141个演说辞都不具备一定程度的可信性,那么修昔底德整部著作的真实性也就荡然无存了。由于条件所限,我们不可能通过原始考古资料一一核实,每个演说的真实性、精确性,但是经过分析推理,修昔底德著作中的演说辞还是有一定的真实性的。
首先从《伯史》的原文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力求演说辞准确真实。在《伯史》第一卷第一章有这样两段原文:“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利用了一些现成的演说辞,有些是在战争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中发表的。我亲自听到的演说辞中的原词原句,我很难记得了,从各种渠道告诉我的人也有同样的困难。所以我的方法是这样的:一方面尽量保持讲话人的实际所讲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每个场合所要求他说出的话语来。”二是关于战争事件的叙述,我确定了一个原则: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事件,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的,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就是这样,真理还是不容易发现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说法,由于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或者由于记忆的不完全。我们这部历史著作很可能读起来不引人入胜,因为书中缺少虚构的故事。修昔底德有关演说辞及记述事件原则两段话,尤其是第一段有关演说辞的引文必须与随后正文有关实际行动的言词一同来注解,至少字面上二者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然而阐述上述原文的问题仍旧集中在如何理解。“每个场合所要求说出的话”与“实际上所讲话的大意”的意思。若按修昔底德时代(公元前五世纪)对修辞的理解,“每个场合所要求说出的话”的意义一定是说出每个场合所必需的对事件具有相当说服力的话,即每个场合辩论所要求的言词,必须确信使听众采纳演说者的建议。事实上,学者们对此句话的解释曾引来对修昔底德演说辞众多分歧。既然是说出每个场合所要求的话来,那么修昔底德就可以按照不同历史场景虚构演说辞;而另有一些人则认为,“说出每个场合要求话”,正是作者坚持求真、求实写作原则,来回忆记录演说辞。笔者认为,不能单纯强调一方面,毕竟我们知之甚少《伯史》中发表演说的实际情况,以致不能裁定修昔底德任何一个演说辞是真实还是不真实,因而演说辞有修昔底德虚构的成份,但是这种虚构不是无原则的,一要符合真实客观的历史背景,二要符合每个具体历史场合。而修昔底德强调了记录演说者“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同样也证实了这点。对此句话理解。一些学者认为它的意思应是“演说辞”的总的主旨,而不是“大意”。修昔底德记录演说辞时就是尽可能不断接近其“总的主旨”。所以演说者在最起码紧急必需的事情争论和修昔底德使用的全部相关联的辩论之间,一个演说者所要达到的主要意图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而人们不应该忽视“实际上所讲话的大意”本身所包含的丰富的意义。毕竟演说是一种以口头表达为主的形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作者不可能完全精确地记载演说辞的每段话,每个字,而修昔底德对演说辞所持的观点,尤其是“尽可能接近实际所说的”表明,在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中,演说辞已经最大可能地接近了事件的真实性。
虽然笔者能从修昔底德字里行间的记述中推理演说辞的真实性,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这种优势作用是有限的。修昔底德总是建议一个一贯要遵照的方法,却没有写出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这个方法是怎样被使用的。因为修昔底德告诉读者他已全面考虑冲突双方的解释。尽管如此,我们仍不知道在每个演说场合中,修昔底德怎样达到其最终的结果。因此后世学者总在推测修昔底德演说辞在创作方面的一些灵活性,即当作者既不在现场,又没有对演说者所说的可靠性进行验证时,这就不得不允许作者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再加工。总之,笔者认为相信《伯史》中演说辞具有一定真实性基础上,也不否认修昔底德虚构演说辞的另一面,但这种虚构也是依据具体环境所要必须说的话,并经过仔细考核。
虽然判定修昔底德演说辞真实性与否困难重重,即使从修昔底德原文中对演说辞的态度中推断其史实性也有一定困难,但从修昔底德求真求实治史风格的角度看。也能从一个侧面证实其演说辞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千百年来后世学者公认,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接近于真实,记载态度也比较慎重认真。对远古的传说进行了批判,对诗人的话表示怀疑,对同时代的事件他采取了极具慎重而科学的态度。他尽量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他不轻信传闻,只是把他亲身经过的和调查研究过的事实,全面而翔实地记载下来。对修昔底德这部著作整体的评价同样适用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演说辞。很难想象一部基本客观精确的历史著作中含有将近1/4篇幅的演说辞完全是作者杜撰虚构的。所以我们在承认部分演说者为了达到说服听众,实现自己所想达到目标,而沾染上诡辩学派浮夸词风,有不实之词,以及为了符合修昔底德写作要求,其演说辞有再创作的痕迹外(即使如此,作者也尽可能接近事实),总体上来说,《伯史》中的演说辞基本上可以作为真实的史料而存在。这在后世经典历史著作中多次转引修昔底德演说辞作为论据,也可看出众多史学大家是基本认可演说辞可靠性的,例如,在《剑桥古代史》中,李维斯(Lewis)等学者的曾多次摘引修昔底德演说辞作为史料证据,证明其所要阐明的论点。至于说,如哈蒙德、布尔瑞的《希腊史》等其他国外史学通史及国内大部分专著和论文也都直接引自演说辞证明作者的观点。从这个角度,也同样证实《伯史》演说辞是基本可信的、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