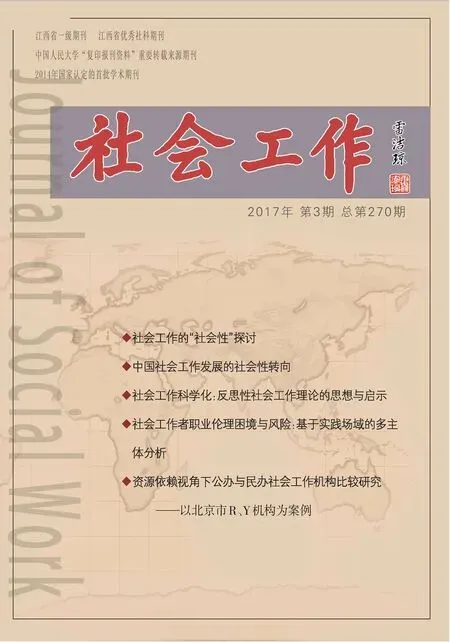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①
李侨明
社会工作者职业伦理困境与风险:基于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①
李侨明
随着中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职业伦理困境和风险产生于社会工作实践当中。然而,关于我国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研究却多以伦理理论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以哲学思辨为方法,缺乏实践案例与实证分析;与伦理困境相伴而生的职业风险也基本上被学界所忽略。因此,本研究采用多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透过“案主—社工—机构—职业”的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讨论我国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职业风险。研究发现,以深圳、广州社工为代表的中国内地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困境,例如案主自决还是限制、隐私保密还是公开、专业服务中的私人关系等问题,多由社会工作者缺乏实践经验、专业伦理规范的模糊与缺失、案主在伦理中的主体性被忽略,以及社会工作者对伦理原则的认知误区等因素所导致。社会工作伦理困境又进一步产生出职业风险,如身心安全、行业处罚、被起诉等。社会工作者可以采用避免单独上门服务、规范服务流程、熟识相关法律政策、向资深从业者学习等策略去防范职业风险。另外行业协会与政府也需要借鉴欧美、港台先进经验,结合本土文化传统,搭建本土的伦理体系,并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法制化。
社工伦理困境 职业风险 多主体 实践场域
李侨明,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博士生,社会工作师、兼职社工督导(广州510275)。
自2006年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建设规模宏大的社工人才队伍”以来,中国社会工作事业通过制度建设、高等教育、人才队伍培养、社会工作机构培育、“政府购买服务”(郭伟和,2016)、“三社联动”(徐永祥、曹国慧,2016)以及“社工+义工”(李迎生、方舒,2010)等,在各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构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步框架(张丽霞、李芳,2016)。社会工作发展的总体性框架建构,主要是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的场域中进行的(Payne,1999),即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政治决策、法律法规和社会政策,为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工作机构、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民生议题做出了一系列的动员,提供了丰富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另外两个重要的社会工作建构场域是“案主—社工—机构”以及“机构—职业”,前者指的是案主与社会工作者及机构的互动,后者则是社会工作者如何通过机构、社会工作行业协会(工会)等组织将实践具体化、制度化。“政治—社会—意识形态”、“案主—社工—机构”和“机构—职业”这三个职业建构的场域是相互影响的,每个场域的变化都将深刻地影响另外两个场域的变化(Payne,1999)。总的来说,实践场域的多主体分析,主要是通过场域建构的视角审视场域内各个要素之间的互动及其相互影响。
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工作研究,例如,社会工作嵌入论和服务型治理(王思斌,2011、2014),“三社联动”(徐永祥、曹国慧,2016;顾东辉,2016),社会组织边界生产(黄晓星、杨杰,2015),“从规训走向社会建设”(郭伟和,2016),行政权力对专业的吸纳(朱健刚、陈安娜,2013),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张和清,2011、2016),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错叠现象”(王思斌,2013)等等,基本上都是在上述的三个场域中进行建构的。美国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发布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也强调“专业伦理在社会工作中占据核心位置”。因此,关于社会工作伦理实践的议题也应该如“嵌入论”、“整合社会工作”、“三社联动”等等议题一样,在三大建构场域中获得重要的位置。但是,中国内地除了少量集中在医务、养老、婚姻暴力以及残障服务等领域的实务伦理研究之外(定光莉,2011;沈颖,2011;袁芮,2016;冯浩,2015),为数不多的伦理研究停留在以理论本身为研究对象,以宏观的哲学思辨为方法,以社工的伦理困境(ethical dilemma)和伦理抉择(ethicaldecisionmaking)为主要议题的起步阶段(沈黎、吕静淑,2014)。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绝大多数来自于康德式的普世性伦理,即“绝对主义”伦理规定与历史的、现实的冲突(Hugman,2003)。而社会工作伦理抉择是社会工作者的“两难”,而非案主的“两难”,“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而非以案主为主体”(冯浩,2015)。“缺乏案主”的参与暗含着对社会工作者伦理建构缺乏案主参与的批评。甚至,国内的社会工作伦理规范一般由官方(民政部)或者行业协会(原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单方制订,从事直接服务的“一线社工”很难有机会参与其中。有些地方行业协会也会做出一些相应的规定,但也仅仅是“聊胜于无”,很难发挥实质性的指引作用。因此,国内的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实践需要一种多元主体参与的场域建构视角。
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本土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伦理问题受到关注,其复杂性和迫切性需要得到更多本土伦理研究的支援。例如,国内第一例因违反社会工作职业伦理而受到行业协会处罚的事件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深圳市一线社会工作者“郭社工”因“违反职业伦理规范”而被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深社协”)以“注销注册资格”处置。①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关于“郭社工违反社会工作职业伦理规范”的处理决定》,2017年4月10日。http://www. szswa.org/index/association/detail.jsp?id=30329这实际上是与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相伴的职业风险问题。此事件也标志着国内关于社会工作伦理的争议进入实践层面。因此,相关的研究也应转向以社会工作实践内容本身为研究对象(沈黎,2012;江娅,2007),以更多的实务案例分析去总结中国本土的伦理实践经验和智慧。
目前来说,国内的社会工作研究对职业伦理与风险的关系几乎没有涉及。“职业风险”可以理解为由于外部环境或者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从业人员面临政治、经济、法律以及身心安全方面受损可能性(冯雅,2013)。有学者将司法系统内法官所面临的职业风险分为内部职业体系产生的职业风险和外部社会环境带来的职业风险(李霞等,2011)。借鉴职业风险的上述定义及分类,本文中的社会工作职业风险,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助人的过程中面临违反专业伦理或政策、法律而遭受惩罚,以及在助人过程中遭受身心损害的可能性。笔者在CNKI分别以“社工职业风险”、“社会工作职业风险”和“职业风险”作为搜索的关键词,发现国内只有两篇的文章涉及社会工作职业风险的论文,而涉及护士、医生、律师、法官、警察、会计等职业风险研究则有15650篇(截至2017年5月16日)。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工作职业化时间较短,社会工作在中国是否作为一个职业或专业都尚且存在争议;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界对社会工作职业风险敏感度不足。
与职业风险相关的两篇文章,其一为“社会工作者保护保障机制”,主要探讨社会工作者在职业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在侵害的保护机制(徐翀,2012),其二为“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风险及应对策略”,主要研究社会工作者在职业中所面临的身体安全和心理伤害,并提出干预对策(冯雅,2013)。徐翀(2012)将社会工作者职业保护的现状总结为法律、聘用单位和社会工作者的自我保护意识等三个方面的缺失,而将职业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职业保护法律不足、雇佣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保护意识不强和社会宣传不足等视为主要原因。徐翀在成都调研发现,83.5%的社会工作者都表示所在单位没有建立社会工作应急制度,82%的社会工作者表示所在单位不能提供有安全保障的服务环境和条件,72.5%的社会工作者表示所在单位没有购买特殊的人身保险。

注:引自徐翀,2012,《社会工作者保护保障机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冯雅(2013)将职业风险的成因归结为社会工作职业的特殊性、社会工作者自身的意识以及低认知度三种因素,认为“各国社工职业守则中,都是以案主利益为主,要求社会工作者如何做,却没有一条是维护社会工作者权益的……当社会工作者遭遇风险攻击时,在不违背职业守则的前提下,他们很难保障自身权益”,并提出要“改进就业劳动条件、加强专业教育和改进社工职业守则”等三种策略应对职业风险。国内2012由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指引》缺乏关于职业伦理执行的保障条款,也导致了职业伦理面临丧失执行效力的风险(沈黎、吕静淑,2014)。
由此可见,社会工作伦理的实践困境与社会工作职业风险之间关系紧密却被国内学界普遍忽视。上述的研究和事件启发了笔者借鉴Payne的场域建构论,将社会工作伦理实践研究放诸“案主—社工—机构—职业”多主体的实践场域中,通过案例分析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伦理困境及所带来的抉择难题和职业风险。笔者主要关注,在实践场域当中,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伦理困境是什么,伦理抉择难题会给社会工作者带来什么职业风险,以及如何预防这样的职业风险。
一、社会工作职业伦理、困境及解决原则
“伦理”(ethic)一词源于希腊语ethos,指的是一套获得公认,特别是以道德为基础,以控制行为的信念体系。①剑桥英语词典http://dictionary.cambridge.org/zhs/%E8%AF%8D%E5%85%B8/%E8%8B%B1%E8%AF%AD/ethic“职业”(professional)则是一个现代的词汇,源于德文Beruf,对应的英文为calling,原意为“奉神之召”,在天主教占优势的民族里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汇,在基督新教占优势的民族里则相反(韦伯,2010)。在韦伯(2010)看来,Beruf的现代意义源自圣经的翻译,尤其是译者路德的思想。Beruf的现代意涵在路德所翻译的《西拉书》首次出现,其字义连同其思想都是“宗教改革的产物”。Beruf被路德赋予的全新意涵是,“将世俗的职业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就摈弃了天主教将出世禁欲作为唯一的侍奉神的方式,转而着眼于俗世的岗位的职业义务,并将其描绘为个人的“天职”。韦伯(2010)进一步指出,路德最初依循的理念,完全是中古主流的传统,即将世俗的劳动视为如同饮食的自然基础,与道德无关。后来随着“因信称义”思想的形成,他认为世俗职业劳动是“邻人爱”的外在表现,愈来愈强调世俗的义务是侍奉神的唯一之道,“任何正当的职业在神面前具有绝对同等的价值”。可见,“Beruf”经历了“道德无涉”到与新教的“宗教道德”融为一体的重大变化。沿着这一关于“职业”(professional)的“考古”,我们便可知道现代职业为何跟道德与伦理密不可分。从“职业”的词汇起源看,基督新教的宗教道德深深地嵌入了现代“职业伦理”。从这一点来看,社会工作作为一种现代职业与其他的职业都带有类似的基督新教的道德伦理,社会工作伦理本身并不能单独地成为区别自身与其他专业的核心。也就是说,一套看起来“标准化”的伦理及守则并不能让社会工作成为一门独特的职业或者专业。
现代意涵的职业伦理源于现代医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803年的英格兰。到了1847年,美国医学会也发展出了首个专业医学守则,而当时的医生社会名声并不好(多戈夫等,2010)。类似,由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受到质疑,美国在Mary Richmond的推动下于1920出台了首个个案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草案。而在世界上最广为流传的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协会(NASW)于1996年制定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2008年最新修订)(沈黎、吕静淑,2014)。社会工作伦理指的是在专业的价值观体系之下发展出若干伦理原则,再演绎为专业实践中的专业行为守则,界定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和活动范围,为社会工作者的助人行为提供指引或限制(多戈夫等,2010;沈黎、吕静淑,2014)。专业伦理与专业实践之间并非一一对应,这也带来了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它指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助人行动中陷入了“两难”甚至“多难”的价值选择情景当中。
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成因主要是由同个原则内部或者不同的伦理原则之间于实践中发生的冲突造成。常见的冲突包括案主隐私保密与公开;案主自决与限制;专业关系中的双重关系,等等(多戈夫等,2010)。这些冲突在具体的情景中都非常复杂,给社会工作者带来极大的挑战。拉尔夫·多戈夫等(2010)提出了专业伦理原则的金字塔以缓解冲突问题。伦理金字塔从塔尖到塔底的排列顺序依次是:保护生命;平等与差别平等;自由和自主;最少伤害;生命质量;隐私和保密;真诚和毫无保留地公开信息。这一原则的次序排列出了其优先程度的“一般”(非绝对)的次序。当有两个以上的专业伦理原则相冲突时,可以寻求在金字塔框架内解决。
伦理抉择难题隐藏着社会工作伦理原则的价值观矛盾。学界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伦理取向划分为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前者拒绝固定的道德法则,它判断伦理决定的合理性以具体的背景或者产生的后果为依据,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为代表。边沁秉持“大多数人最大的善”这一原则,究其本质则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伦理取向由“案主利益最大化”及“最小伤害”的社会工作伦理原则充分体现。后者则强调固定的道德原则有绝对的重要性,不管这一道德原则会造成多少损失,都应该不分场所的实施,以康德的道德哲学为代表。康德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内在价值,无论他(她)的行为是否有利于他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理性的存在物,能够根据他(她)的选择或愿望来决定该如何行动,因此,一个社会工作者最好的策略就是尊重案主的选择,把案主当作有能力选择且能对选择的后果负责任的个体(江娅,2007)。
笔者认为,难以简单地区分伦理相对主义与伦理绝对主义孰优孰劣、孰对孰错,社会工作者应当考虑到在实际的工作情境需要而进行调和。一方面,以边沁功利主义为代表的伦理相对主义,没有固定的道德观或者说道德倾向,“以多数人的善”作为其出发点,注重了人性与社会复杂性,并带来了社会工作灵活多变的助人模式。但是,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否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比“个体的利益”更加重要?谁又能证明多数人的“善”比个体的“善”更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单单秉持这种伦理相对主义思想的社会工作者容易掉入功利分析的陷阱,从而忽略了案主作为个体存在的价值,也就是说案主自决原则很容易在这种伦理哲学取向中被忽视。
另一方面,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绝对主义承认了人的理性与自决权,强调了人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从这一层面讲,康德哲学是有利于案主的自我成长和自我充权。但是从社会工作实践层面去理解的话,过分强调固化的道德观而对具体的情境不加考虑,会导致助人行为过于僵化而损害案主的利益。另外,过于强调“尊重”和“自决权”,而不考虑自决权的适当限制,也容易造成社会工作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推脱自身的伦理责任(冯浩,2015)。也就是说,在实践中采用绝对主义的伦理哲学取向可能会造成社会工作者违背以案主利益为中心的原则。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两种伦理取向都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同样亦有其自身无法避免的缺陷。
上述伦理取向与伦理原则提供的是一套专业人员在实践当中的“指南”,供社会工作者依情境作判别,以及进一步的反思与研究,而并非是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和步骤。尽管这些伦理原则可作为社会工作者在一般实践的情景下的操作指引,但是它们仍然难以解决实践中的很多“两难问题”。“两难问题”的出现往往结合了“当时当地”的特殊情景因素,缺乏经验的社会工作者容易倾向于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解决问题,因而也可能产生更复杂的伦理困境。因此,社会工作者要在“两难困境”的伦理冲突中做出“适当”的伦理抉择,非常考验个人的实务经验和智慧。
二、实践场域中的社会工作伦理困境与抉择
实践场域中的伦理抉择,是在Payne(1999)所述的“三个场域”之中建构出来的。在实务中,社会工作者常常遇到“自决还是限制”、“保密还是公开”、“专业服务里能不能有私人关系”等主要的伦理冲突。伦理抉择也就多是围绕这些冲突进行。鉴于实务场域的伦理冲突较多地集中在微观(社工—案主)和中观(机构——行业协会)的场域,因此以下的案例分析,主要围绕着“社工—案主—机构—行业协会”的多方建构场域进行。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分析并非说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这种宏观的场域对于伦理抉择的影响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完全避开宏观层次的分析;而是在宏观的场域中过多地分析伦理,容易再次走向伦理研究的“哲学思辨”,更容易滑入专业伦理研究的“政治正确”,坚守于“结构功能主义”的专业取向。因此,宏观层次的分析将作为辅助的伦理抉择分析层次。
(一)自决还是限制?
社会工作者经常面对伦理困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做出伦理抉择。“案主自决”原则就常常遭遇伦理原则内部或外部“两难”的冲突。“自决”原则的价值哲学来自美国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自决是美国社会的第一位原则”,受到美国宪法第九及第十四修正案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影响,众多的社会工作从业人员都主张这是一项绝对的权利(戈多夫等,2010)。尽管社会工作行业在对自决作为重要的专业伦理上有共识,但也有学者质疑自决原则在日常实践中的真实性(Perlman,1965),自决的含义和应用含混不清(clouded)(Rothman,1989),并成为“社会工作者最常遇到、令人困惑的难题”(Abramson,1985)。Freedberg(1989)通过对自决原则的历史发展回顾发现,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带有实践色彩的“自决”概念存在着固有的,无法解决的矛盾,反应了“社工在民主社会里的矛盾立场”(Freedberg,1989)。上述这些自决原则的实践困境也是国内的社会工作者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国内的案主自决伦理困境中还混合了与美国等国家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差异。在“案主自决”背后是美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经常与之发生冲突的是蕴含在社会工作服务过程当中的社会控制(Freedberg,1989)。在国内,自决原则背后的个人主义假设与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和整体(集体)观相冲突(定光莉,2011;冯浩,2015)。
例如,某案主的家属因交通意外成为“植物人”,医生诊断为“无医学上的医疗价值”,虽然家里一贫如洗,根本承担不了医药费,但案主却不愿意放弃治疗。①该个案为笔者在深圳从业期间跟进三年的案例,对案主的个人隐私信息已做匿名处理。这时,社会工作者是应当站在伦理绝对主义的立场,坚持“案主自决”,尊重他的决定;还是站在伦理相对主义的立场去跟他分析现实——倾向于“案主利益最大化”,以现实利弊分析,让他少做几乎看不到希望的努力呢?②Freedberg(1989)通过历史分析发现,美国的中产比较支持“案主自决”,将服务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群体则相反,他们更希望社会工作者能替他们做决定。该个案的案主是外来劳务工,在服务过程中也常常表现出类似的想法。在笔者看来,前者罔顾案主的现实条件;而后者则忽略了案主对亲情眷恋不舍的感受和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因此,社会工作者首先肯定了案主对亲人的眷恋之情,并作为“同行者”的角色,在政策和自身能力的范围内,支持其从家庭获得情感支持,从社会寻求救助资源。其次,社会工作者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协同案主向社会寻求救助后,再根据情况与案主分析,最大程度上维护其“自决”能力。再次,案主的家庭伦理负担减轻后,慢慢地采用了医生建议的“消极治疗”方案。在案主看来,即便未能达到理想地治疗“植物人”的效果,但社会工作者与他都一起尽力了,尽管他在亲情上还是不舍,但是减少了遗憾;而在社会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者已经在伦理责任和案主的利益上尽可能地实现了平衡,既让案主“自决”,也陪他一起面对“自决”的后果。
然而不可否认,不论社会工作者坚持哪种伦理取向,案主自决原则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伦理难题之一。其中的关键是,案主的自决权在什么情形下应当受到适当的限制?Biestek(1957)提出四种情形常被用来作为限制案主自决的参考依据,它们分别是:案主具做出积极而有建设性决策的能力;民法产生的限制;道德产生的限制;以及机构功能产生的限制。
在实践中,案主的个人权利常常让位于家庭伦理和本土情境。以家庭暴力个案为例:某案主为75岁的女性长者,长期忍受儿媳言语上的辱骂,偶尔还遭受她儿媳的殴打。③该个案笔者跟进了三次,与街道办司法所伙伴协作处理,对案主的个人信息已做匿名处理。社会工作者看到女性长者身上的一些伤痕后,认为其身心权利受损,建议报警处理。然而此时,女性长者坚持不让社会工作者报警,原因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报警的话她儿子也会“没面子”,她只是希望社会工作者警告其儿媳不要再有类似的行为。参考Biestek的四项限制条件,我们进一步分析:首先该长者神智清醒,可以从言行判断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希望借助社会工作者阻止儿媳的“家暴”行为,也就是说她具有能力借助外部力量阻止儿媳侵害行为的决策能力。①当时《反家庭暴力法》尚未出台,长者也不认为儿媳的辱骂属于“家庭暴力”。其次,虽然儿媳对该长者身心有所伤害,但民法上并未明确规定“家暴”是一种必须以报警处理的不法侵害。就算《反家庭暴力法》出台,规定了社会工作机构承担了对“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的家暴个案承担“应当报警”的义务,长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并不符合“应当报警”的规定要件。再次,最重要的是,长者受到“家丑不可外扬”的家庭道德伦理观念影响很深,很担心儿子受到邻里、社会的非议,也就是说违背传统观念而报警对她来说反而是“不道德”的。最后,根据社会工作者家访的情况判断,该长者并没有面临急迫的危险。因此,如果此时社会工作者限制案主的自决权,贸然报警,将有可能给该长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社会工作者从案主的述说中得知在其家族中的“三叔公”极有威望,于是社会工作者与该长者一起借力“三叔公”,较好地缓解了“家暴”问题②因工作岗位调动,笔者当时并不能做结案后的跟进工作。而根据“家暴”的反复性特征,笔者并不能确定一次就“解决”了家暴问题。。
由此可见,“案主自决”在中国的意涵要丰富得多,既有情景的复杂性,也有本土道德伦理和文化传统的深层影响。因此,很多时候,社会工作者不能够把“案主自决”理解为案主“个人自决”,更多的情况下要考虑到案主的家庭、家族以及邻里等“利益持份者”(stakeholder)对案主的影响力,才可能从根本上与案主一起解决问题。
(二)保密还是公开?
由于工作的特性,社会工作者经常会接触到案主的隐私信息。于是,“保密”就成了案主对社会工作者“神圣的信任”(Biestek,1957)。对案主来说,隐私权是自然法赋予的基本人权之一,“保密权不是目标但却是保护他们其他权利的方式”(Biestek,1957)。Biestek(1957)如此定义“保密”:“保密是保存关于案主在专业关系里公开的秘密信息。保密建立在案主的基本人权的基础上,它是个案工作员进行有效服务的一项伦理义务。尽管如此,案主的权利不是绝对的。更多时候,案主的秘密被同一机构或者不同机构的其他专业人士所分享,该义务平等地约束(他们)”。
“保密”对社会工作者来说,既是作为一项职业伦理要求,也是一项法律的要求。美国就有在司法程序上对“特许保密通讯”(privileged communication)的保护。没有得到“最初信息提供者”(在社会服务中指“案主”)的同意之前,司法机构不能强迫处于受到“特许保密通讯”保护的人披露信息。这些信息会被作为司法程序上的强制排除证据,认定目击者“没有能力”为特定的事件作证。如历史上就规定了丈夫和妻子、律师和当事人、牧师和和忏悔者、医生和病人等四种类型的“特许保密通讯”,而关于社工与案主之间的保密规定,美国各个州都有不同的规定(多戈夫等,2010)。1965年,一名叫“塔雷索夫”的女孩被前男友杀害后,其家人起诉心理治疗师。法院认定其前男友的心理治疗师未对她尽“警告”的义务。判决所确立的“塔雷斯夫原则”使得很多美国的社会工作者很谨慎地对待保密原则。
在中国内地,虽然保密原则没有受到类似于“特许保密通讯”保护,但是,公民的隐私权也是民法所保护的重要权利之一。因此,社会工作者必须做好案主的隐私保护工作。同时,“塔雷斯夫原则”提醒我们必须关注“保密”的例外情况。遗憾的是,国内的社会工作伦理研究对于诸如“什么条件下可以打破保密原则”等问题没有进行有效的讨论,而恰好是这个问题在实践中给社会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困扰和职业风险。
例如,广州社会工作协会(以下简称“广社协”)在2017年4月28日对广州各个社会工作机构发出了《关于若干家综接到居民“王某”求助的情况通报》。①消息来自于微信“好友圈”。笔者搜索了网络,并没有发现网站相关信息。随后通过同行得到信息来源确认,并访谈了其中广州家综的一位亲历事件的社工。根据该通报,隐匿个人信息的“王某”在广州6个区共18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就“儿子青春期问题”求助,并指定青少年领域的女社会工作者跟进,但一概拒绝进一步面谈。广社协要求社会工作者“及时报备”并“报送市社协备案”;谨慎处理;注意安全。同时也呼吁该居民“速与属地家综社工或其他专业机构联系”②广社协与深社协在行业内“通报”中做出对“王某/王女士”的回应,遭到一线社工的批评。她们认为,“王女士”可能无法获得行业信息。笔者认为,以“王女士”对社工行业的掌握情况,极有可能在网络上获取了信息。在深社协发布了“通报”后,受访的社工表示有深圳的社工陆在5月19、21日,接到情况类似于“王女士”的“王先生求助孩子青春期问题”(受访社工z)。。无独有偶,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深社协”)在2017年5月18日也发出《关于我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工密集接到“未成年人性教育问题”求助电话的情况通报》。该《通报》指出“王女士”在深圳6个区60家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就孩子的青春期教育问题求助。深社协要求社会工作者接触到类似情况要向督导和机构“报备”;要“注重个人隐私保护”;“必要时寻求督导、机构和协会的支持”。同时也呼吁居民与“属地社工或者其他专业机构联系”。可以发现,广社协与深社协几乎以一样的方式处理了该事件,要求社会工作机构:报备、隐私保护、注意安全、呼吁“王某/王女士”合理求助。
5月21日,深圳市社会工作者谢某作为事件的亲身经历者,在微信公众号“社工观察”上发布了《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反思与社工执业安全——从“12岁青春期儿子性教育电话求助”案例谈起》的文章。③谢洁翎,个案工作中的专业反思与社工执业安全——从“12岁青春期儿子性教育电话求助”案例谈起,2017年5月21日。https://view.inews.qq.com/a/20170521G05FSE00?refer=share_recomnews该文章首先指出,虽无法判别求助者的真实性,但基于“服务对象利益优先”和“接纳”的伦理原则,“该事件中接案的六十多家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做出了在该情境下唯一可以做的正确的事”;其次社会工作者应该兼顾“个人安全”和“坚守专业伦理”;再次,该事件波及深圳全市10%左右的服务中心后才被通报,跟社会工作者的“保密”伦理原则有很大的关系;最后,强调社会工作者的执业安全需要更多的保障,深圳社协的回应“回避了其(王某)涉嫌违法犯罪的事实”,也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保障一线社会工作者的人身安全。
综合广社协和深社协的通报信息,笔者发现,“王某/王女士”在两市的求助范围都是分布于“六个区”,涉及的服务中心分别约占两市的10%。尽管动机不明,但笔者认为这类似于概率抽样,可能对两地的社会工作者执业安全极为不利。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笔者用微信在线个别访谈和焦点小组的形式,对深圳的一线社工Z、S、D、P、社工督导J,以及广州的社工G等亲历者,退休警察Y,中山大学性与社会工作专家裴谕新副教授,北京大学应用心理学博士X等人进行访谈或咨询,希望探索社会工作者在此次事件中经历了怎样的伦理困境,以期识别伦理困境带来的职业风险。
访谈发现,首先,“王女士”颇为熟悉社会工作行业。她一般要求“青少年领域”或者“家庭领域”的女性社会工作者,“有婚姻或者性经历”,并要求“保密”。④“王女士”的性别无法判断,原因是首先是现在很多的手机应用软件,一用就可以变身;其次,深社协发布通报后,有些社工继续接到“王先生”类似的“求助”。其次,“王女士”的“求助动机”不明确(甚至并不具有“求助动机”)。“她”述说的内容无法判断真假,是亲历者基本的共识。再次,描述很多是露骨的,她与自己孩子的“母子”性行为细节,并探听询问社会工作者的个人性经验。①深圳社工Z认为“王女士”描述现象很“专注仔细”,但对自身的情绪描述则“迟钝”。Z说,“当我主动去确认她的情绪的时候,她的回应都是‘对啊’,也带给我一些不真实的感觉”。但是,描述儿子行为的时候就很详细,例如:“你知道他射精在什么地方吗?就是我的那个内裤的那个地方,那个裤裆的位置”;“在我练习瑜伽的时候,我儿子会从背后抱住我,用他那个地方顶住我,而且他又是穿睡裤,没有穿内裤,下面都露出来了”。Z想继续探寻她感受的时候,她还是继续描述,例如:“Z姑娘,你能告诉我,他拿我的内裤进房间是怎么手淫的吗?”。受访者多感到“不适”、“特别不舒服”、“被侮辱”或“性骚扰”。有社会工作者提出“王女士”似乎是在“享受快感”,在于别人“分享”,感受不到“王女士”的焦虑或者受困扰的情绪。最后,社会工作者在此事件中面临的伦理困境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有社会工作者将社会工作的“助人”性质、“非评判”、“接纳”与“不能拒绝”、“不敢拒绝”对等起来;也有社会工作者因觉得需要“保密”而没有与督导、同行及时沟通,担心泄露案主隐私;也有社会工作者承认“缺乏会话技巧”而受到困扰。
笔者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工作者在本次事件中两个相关联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会拒绝为案主提供服务”,以及“什么条件下可以打破保密原则”。在微信在线焦点小组中,几位亲历者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不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或者服务辖区范围内;感到危险;不明求助动机或(社工与案主的)价值观不匹配;案主信息不实,存在欺骗行为,对专业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和否定。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总结为:案主可能严重伤害别人或者自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如伤人、自杀、家暴、虐待);涉及司法刑事案件;专业关系没建立(或被案主的不良动机摧毁)。②社工B与其他社工不同,认为只要没确定“王女士”是性骚扰,就必须保密。
根据上文Biestek(1957)对保密原则的定义,笔者认为他强调了三点:第一,强调在“专业关系”中才存在保密的信息;第二,强调同意社工行业信息可以共享,并需要承担同样的保密义务;第三,强调案主的隐私并非绝对的,是可以带义务和附加条件的。对照这个定义,首先,社会工作者对专业关系何时建立的理解并不一致。比如Z社工的理解是:“我严重质疑她求助的动机不在于求助。专业关系都毁了,就不用保密了”,也就是说,“求助者”虽然已经来电咨询,但若“动机不明”就意味着并没有有效地建立专业关系,真诚的专业关系应该是“双向的”,社会工作者要真诚,案主也要真诚。与Z不同,对督导J来说,她认为从接电话开始就建立了“专业关系”,也就是说,保密义务从社工与“服务对象”的“咨询”就开始建立。③社工督导J认为,“服务对象可以包含所有的服务内容,(而)案主觉得同意接受一对一辅导或者接受开案为他解决问题时,为案主”。
其次,同机构或者同行业内专业人员之间没有实现信息共享,缺乏工作信息交流,是本次事件不断发酵的关键。受访者多数基于“保密原则”,并不会第一时间跟督导或者机构内其他同事说明详细情况(除非非常明确自己处理不了),更不用说在同行业内讨论。而社会工作者这种对“保密原则”的持守,恰恰被“王女士”所有意或者无意利用,直到事件造成较大影响才被广、深社协发现并通告。
再次,社会工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非评判(接纳)原则”和“保密原则”理解上的误区,这种误解也带来了笔者所认为的“虚假的伦理困境”。例如,保密原则的打破,受访社会工作者的理解总体上是与“主流”的认识一致的,如严重触犯法律,危及他人或自身安全的时候可以打破。但是,社会工作者对“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拒绝服务以及打破保密原则”,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及反应。例如,社会工作助理B在第一接电话时就被“王女士”的性描述吓到挂电话。她在感到“恐惧”和被“侮辱”的情况下,被“助人理念”所“绑架”(对她来说似乎意味着不能拒绝),在超出自己的工作能力,以及感受到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几次拨通“王女士”的电话。她的上级,“组长”也没能察觉到她的困难以及提供援助(微信在线焦点小组)。社工Z虽然有所警惕,但也在犹豫是否“不保密”,对督导坦诚实情,直到Z的督导收集到其他亲历社会工作者的求援后,Z才完全打破保密义务(微信在线焦点小组)。社会工作者对“非评判”(接纳)及“保密”伦理原则的“绝对化”认识所产生的处理困境,笔者认为是“虚假的伦理困境”。这可能导致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案主非合理要求时未能做出清晰而坚决的“拒绝”,并在感受到“危险”、被“侮辱”或者被“性骚扰”的时候,不能报警寻求协助。①笔者也咨询了中山大学知名的性与社会工作专家,裴谕新副教授。笔者提出的问题是,社工如何判断在来访电话中是否受到性骚扰?裴教授的答复是:“如果是自己觉得不舒服,并且口头表达出来(需要明确地拒绝),这种不想让对方继续的意愿,当对方明确了解你的意图,仍然不停止,就构成性骚扰”。如果按照这种定义,受访的社工几乎都可以定性为“受到性骚扰”,原因是其细节描述非常“露骨”,且受到社工拒绝,要求换一种描述方式后,仍然要求用“直白的方式”。例如:“王女士”说,“我的儿子的鸡鸡遗传了我老公的,很粗大。我儿子不像我老公,直接跟我做,我儿子,更懂调情”,社工引导她用“性器官”替代“鸡鸡”的说明,她拒绝,且会说“跟我说(话),不要说的那么不清楚,我听不懂,你就直白一点”。“王女士”说,“我做瑜伽的时候,我儿子会从后面抱住我然后把鸡鸡拿出来在我屁股边摩擦”。社工跟她确认“有跟儿子真正发生性关系吗?”,“王女士”回答“有插进去,好爽”。会话过程中并没有围绕求助的‘愧疚’、‘困扰’、‘想结束(跟儿子的性关系)’话题进行(深圳社工J提供记录)。
最后,尽管社会工作者都认为案主隐私权并非绝对的,但在现实处理上,绝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对打破保密原则顾虑重重。甚至在发生了牵涉广州、深圳两地的“王女士”事件后,只有深圳社会工作者谢某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行业协会也并未在公告中体现出会进一步寻求警方等的外部协助。个别机构做出了进一步保护一线社工的反应,如深圳YG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笔者访谈中所了解到的唯一的一家机构。在该机构内部正式发文,将“王女士”事件定性为“语言性骚扰”,并提出社会工作者遇到类似情况可以拒绝。由此可见,不管是社会工作者个人、机构还是行业协会,都没有寻求警方协助。笔者通过访谈发现了社会工作者在“王女士”事件当中的伦理困境。但是,对于机构、行业协会为何也放弃寻求外部援助,原因还尚未可知,这也是笔者将进一步研究的工作。
另外,为了进一步了解公安对于“性骚扰”的处理,笔者也咨询了侦查经验丰富的退休警察Y。他告诉笔者,这种类型的事件,就算报警也未必能够在“性骚扰”的角度立案处理。“性骚扰”在中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处理,公安处理一些诸如“偷盗女性内衣”的相应的措施基本都是以一般的行政拘留和训诫为手段。Y强调,“王女士”可能有“变态心理”特征,②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X也同意“王女士”的反常“求助”行为,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行为表现。建议从保障公众安全的角度,由地方社协寻求警方协助,找出“王女士”,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
笔者认为,“保障公众安全”与“伦理金字塔”中最高层的“保护生命”原则最为接近,是很符合社会工作伦理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在考虑是否拒绝服务,或者报警立案时,或许可以从更合理的角度,从“寻找警方协助保障民众安全”③保护民众安全包括保护“王女士”的孩子在内。如果“王女士”对所有社工的描述真实的话,她可能实施了涉嫌“猥亵儿童”的犯罪行为。开始,而不是在立案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要求警方“立案”。这种做法在没有完全确定“王女士”真实情况之前,不失为较妥当的处理方法。既以较高的“保护生命”原则去有限度地公开其所谓的“隐私”,打破“保密”原则;也在法律上规避了直接“报警”处理,直接侵犯其隐私权的可能。
(三)专业服务里能不能有私人关系?
根据现有主流的社会工作伦理守则,一般都是限制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建立专业关系以外的私人关系(被认为是有损案主利益),这种公私关系并存的情况,一般被称为“双重关系”。双重关系一般被禁止,美国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守则》与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都很明确地禁止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发生“性关系”。
上文提及的,“郭社工”因与“服务对象”“恋爱”而被深社协“注销注册资格”,是国内第一例社工因“双重关系”而被处罚的事件。深社协的处罚公告指出,“郭社工”在家访过程中经王女士介绍而与其女李小姐认识,并“确定恋爱关系”。事情发生之后,郭社工没有“报备”机构和督导。因此,郭社工被投诉后,深社协依照《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守则》及《深圳市社会工作者登记与注册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做出了“注销郭社工注册资格”的决定;“郭社工”的任职机构因“管理视察”,也被按照《2016年度深圳市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绩效评估》的相关规定处理(未说明如何处理)。此事件迅速引起了学界与实务工作者的讨论。
例如,《中国社会工作》杂志组织了三次“讨论会”形式的文章发布,集结了高校学者、一线社工、社工督导、机构负责人等各方,从学理和实务的不同角度去讨论这一事件。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伦理的“意义”、“作用”、“本土化”(颜小钗、高晓敏,2017);“社会工作者如何处理伦理困境”;“如何保障社工伦理发挥作用”;“社会工作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如何加强社会工作伦理教育”等等问题(汪昊,2017)。在这些讨论中,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某些“共识”:首先是讨论者都认同“社工伦理是社会工作的基石”,社会工作伦理需要达成共识;其次是坚持社会工作的基本伦理原则,如保护生命、保障隐私、保护案主利益等基本原则需要得到遵守;再次,社会工作伦理规范需要对专业(行业)、社工、案主、机构等各方利益负责,在处理伦理困境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利益的平衡;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需要对西方普世性价值为主导的伦理规范做出部分而具体的调整。
另一方面,这些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差别。首先,在本土化的伦理修订上面,梁建雄强调了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即“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本土化修订问题需要很详细的讨论,参与者应当包括国际及本地学者、机构运营者、富有经验的社工、法律界人士及政府官员”(汪昊,2017),而陈涛则强调文化和情景特性,“应当结合我国甚至不同地方的文化与社会情境,更充分地探讨各种选择及其可能的含义,再定出更恰当合理的具体标准”(汪昊,2017);其次,尽管业内人士都在认同“伦理底线”,但陈涛认为抽象的价值伦理导致了“人人都有底线,但这些底线并不相同”(汪昊,2017);再次,学者们更强调专业伦理的意义,而业内的机构负责人、督导和社会工作者则更强调专业伦理对提升行业社会地位的重要性。总的来说,尽管上述观点有差异,但并不存在着对“郭社工”事件根本性的观点矛盾。
有趣的是,随着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的出现,一些在“民间”的行业声音也得到了传播。其中有代表性观点来自“反压迫社会工作”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郭社工”背的三口锅:社工伦理的尴尬中国面孔》。该文“就事论事”从事件本身的细节和行业协会的权力本身入手分析,认为深社协的处理方式存在几个方面的疑问。第一,“郭社工”违反伦理守则的事实不清晰;第二,深社协的处理程序不合理、不透明;第三,深社协作为行业协会,其权力“合法性”模糊;最后强调了社会工作伦理的发展性和建构性。①锅社工,“郭社工”背的三口锅:社工伦理的尴尬中国面孔,反压迫社会工作,2017年4月14日。http://mp.weixin.qq. com/s/-9vKoQP2GNDOijc3vOlx8Q面对热烈的行业讨论,《中国社会工作》杂志再次回应,强调了社会工作行业协会肩负守护社会工作伦理的重任。②行业协会应该肩负守护社会工作伦理之重任,中国公益新闻网,2017年4月24日。http://www.cpwnews.com/content-24-4994-1.htm l深社协秘书长在文中强调了深社协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成立与职能、处理“郭社工”事件的合法程序、处置方式的合理性以及强调对事件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从讨论的针对性和明确程度去看,笔者认为“民间”的声音,也就是“锅社工”的几个疑问更具有“就事论事”地讨论“双重关系”的针对性。尤其是“郭社工”事件中关于其“违规事实”的部分并不清晰,脱离“事实”的细节和过程很难断定其违反专业伦理的程度。笔者认为“讳言违规事实”是当前地方社协处理社会工作伦理违规案例的通病,一方面是跟缺乏处理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处理程序存在规范化的问题。更关键的一点是,地方社协既要通过行业内部惩处违规从业者,向外界展示行业自律的能力,以提升行业的专业形象和专业地位(锅社工,2017);又要通过违规事实和惩处手段的模糊化以保护行业声誉。在处理程序上,若要使得当事人和社会各界信服,也可借鉴香港的做法。香港社会工作注册局接受投诉的处理程序流程十分明确,例如,仅就处理涉及社会工作者投诉的“纪律事宜”而言,就有五个相关规定,它们分别是,纪律程序说明指南、投诉人指引——聆讯前程序、纪律聆讯前程序规则、纪律程序规则、纪律委员会备选委员小组等。这些投诉的“纪律”规定,对涉事各方主体的权利和责任都有相当细致的说明和程序上的交代。①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http://www.sw rb.org.hk/tc/Content.asp?Uid=3
对于我国内地的社会工作者而言,大多希望有较详尽的社会工作伦理指南和守则,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社会工作者守则》②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会工作者守则,中国社会工作协会,1994年。中未能找到明确的专业指引。这个守则包括四章十七条,包括总则、职业道德、专业修养、工作规范。工作规范也只是泛泛提及社会工作者对各类案主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而没有操作方面的细化,没有实际的操作性。而2012年由民政部出台的《社会工作道德指引》虽然做出了一些改进,并将其拓展为七章二十四条,从内容上讲基本涉及到了社会工作者对案主、同事、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作为专业人员自身,以及社会的伦理责任,但是与台湾、香港等其他华人地区的法定伦理守则相比,还是显现出缺乏实际操作价值。不过,也为地方的行业规定留出了具体操作的空间(沈黎、吕静淑,2014)。
上述案例的发生地都涉及深圳市,我们可以《深圳社会工作者守则》(以下简称“深则”)为例对社会工作者的地方伦理规范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深则》共有六部分、28款条文,分别为:个人素质及操守,工作守则。内容方面以简要条文要求社会工作者与案主、同事、机构、用人单位③对“用人单位”的伦理责任是深圳社会工作者守则最特别的地方。在其他的国家和地区尚没有找到这种称谓,及规定条款。、社会以及自身专业之间的责任。其中,与上述伦理困境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保密原则”、“自决原则”以及“禁止双重关系原则”,分别是:“遵守保密原则。对在服务过程中获得的资料,在与公共利益不矛盾的前提下应予保密,如因工作、法律等需要必须公开案主的资料时,应尽可能事先取得案主或其法定代理人以及社会工作者机构的同意,并对可能识别案主身份的信息进行必要的技术处理”,“尊重案主的自决权,培养案主的自决能力;当案主的行为会伤害自己或他人时,社会工作者可以对其自决权进行适当限制”,以及“不得滥用与服务对象的关系,藉以谋取私人的利益”。④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社会工作者守则,2009年。它们分别对应了我们在上文讨论的三种伦理困境。我们将在下文逐条进行讨论。
首先,《深则》的“保密原则”条文强调了“公共利益”优先于“案主隐私”,如因司法需要也可公开。“应尽可能”取得案主等相关方同意是一个补充的说明,也就是说,就算案主不同意,在有些情况下,如案主犯罪也可以公开。这种对保密原则模糊的规定,与我国缺乏像美国那样的规定有关,给予某些职业,如律师、心理咨询师、医生、社会工作者(某些州)等“特别通讯保护权”,以排除案主的信息被作为司法证据。相比而言,美国社会工作人员协会(NASW)订的《全国社会工作者伦理守则》明确规定“在司法程序中,社会工作者应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保护当事人的隐私权。当法庭或者有法律授权的单位指令社会工作者在未经当事人授权的情况下披露隐私资料,而披露资料会给当事人造成伤害时,社会工作者应请求法庭撤销指令,或者让指令要求披露的资料尽可能缩小范围,或者封存记录,让公众不可以查看”。①深圳社会工作者协会,深圳市社会工作行业投诉处理规范(暂行),2010年12月10日通过。这对于社会工作者的保密原则是一个很细致的补充和说明。当然,就算美国的NASW对于打破保密原则的规定是:“除非是迫不得已的专业上的理由,社会工作者应保护好在提供专业服务过程中获得的所有机密资料。一般来说,当披露资料可以避免当事人或其他可以确定的人造成严重的、可以预见的、近在咫尺的伤害时,社会工作者可以打破保密原则”,但也仍然不清楚什么样的威胁会造成这种伤害。
《深则》保密原则条文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界定“公共利益”在概念和操作化上都是难题。例如,“王女士”的“求助”动机不明,就本次“王女士”对社工们所影响的广泛程度而言,难以排除她对他人可能产生的威胁。因此根据该条文,“王女士”涉嫌“性骚扰”,深社协可以保护“公共利益”的名义打破保密原则。这也是其中一种合理的,对社工实行职业安全保护的操作化选择。
其次,《深则》的“自决原则”强调在案主可能自伤或者伤及他人的时候,可以限制案主自决。但是,该条文并没有对案主的“自决权”在什么时候必须受限制,限制到什么程度没有做出细分,这也留给了社会工作者较为模糊的判断空间。与NASW的规定相比,强调保护人身安全,用于打破保密原则的条件也被用于《深则》的“自决”原则当中。这一原则的运用,在上述的工伤植物人个案以及长者虐待个案中,“自决”背后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明显与中国的整体(集体)主义、儒家文化、家庭伦常传统有着深刻的区别。“自决”在很多时候并不意味着案主一个人的决定,而与整个家庭甚至是家族密切相关(冯浩,2015)。而这种价值观的差异,如果根据欧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价值观进行绝对化的处理,也可能令这种“自决”原则很难在社工做伦理抉择时起实质性的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工作者处理案主家庭问题的时候。
再次,《深则》的“禁止双重关系”原则,其出发点是,社会工作要以维护案主利益为中心。因此,禁止社会工作者在工作岗位上获取“私人利益”是合理的。在美国和香港,社会工作者被行业协会所禁止的是与案主发生“性关系”,结案之后社会工作者也不能再与案主联系等。“郭社工”事件中,虽然当事人“郭社工”因与案主“谈恋爱”而被严厉地处罚,但是因为深社协没有公布更多的信息,这导致外界难以用事实去推断“禁止双重”关系的适用程度,以及对“郭社工”处以“注销注册资格”的决定是否得当。也就是说,为什么“郭社工”不被深社协处以“警告”、“记过”、“通报批评”或是“暂停执业”等等惩罚?②请参看《深圳市社会工作行业投诉处理规范(暂行)》,深圳社会工作者协会,2010年12月10日通过。http://www. szswa.org/index/association/detail.jsp?id=1130至少在深社协公布的文件上,我们不能发现足以证明处罚措施与“郭社工”犯错程度相匹配的过程或者细节交代。这些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外界热议“郭社工”事件的主要原因。
在此,进一步若以场域建构的视角去分析,案主理应可以参与到与社会工作者保持何种关系的协商当中来。“案主——社工”的专业关系是社会工作伦理的核心基础,如果只是社会工作者单方面去决定要与案主保持在什么范围、何种程度的关系,那么社会工作伦理势必也会继续把社工强化为专业关系当中的“主体”,而案主则继续为伦理的“客体”。尤其是在中国这种注重人情和私人关系的场域,公私分明、“一刀切”的职业伦理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工作实践场域。例如,从事农村社会工作的社会工作者不跟村民一起坐上饭桌、不与村民一起劳动、不主动了解村民的生活困难,根本不可能与村民建构良好的“专业关系”。当然,这种允许社会工作者与案主的关系维持适当的弹性空间并不意味着专业关系与私人关系不需要边界。相反,这种私人关系的弹性空间,恰好是为了促进专业关系的建立、稳固和发展。
上述几点对《深则》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内地的社会工作在伦理守则具体化、可操作化实践等方面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实际上,在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当中,从业者平常说的“伦理困境”中的“伦理”指的是以欧美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尤其是康德“绝对主义”的伦理取向)为中心的“伦理”,而“困境”则在很大程度上,是欧美社会工作价值观与我国本土的情境结合而成的“困境”,其中包括社会工作者对伦理守则绝对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我国的社会工作实践实际上并没有一套自己的伦理框架。伦理的背后是多元复杂的价值观体系,这些价值观之间甚至常常存在冲突,伦理困境实质上是社会工作助人价值观体系相互矛盾的具体化。伦理守则和相关的指引条文,在很多情况下也只能做一般情况的参考,不能将之奉为圭臬,应在具体的情境中做出适当的调整。在此情况下,社会工作者可能先从欧美的社会工作伦理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再结合本土文化和社会情景做出伦理抉择。这种伦理困境的抉择案例积累到一定程度,我们可能从中总结出某些一般化的规律,从而构建出中国内地本土化的伦理框架体系和伦理操作守则。
三、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风险
在上述的社会工作实践中,尽管社会工作者已经做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极其谨慎地在“案主自决原则还是限制”、“保密原则还是公开隐私”之间做平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郭社工”因违反“双重关系”的限制而被案主的亲友投诉、被深社协处罚;深圳、广州两地的社会工作者恪守助人理念、坚持“绝对化”地为“王女士”的隐私“保密”,服务过程中“非批判、接纳”,疑似集体遭受“性骚扰”,甚至有些亲历社会工作者产生严重的身心不适反应。有趣的是,如果对比深社协对“郭社工”和“王女士”事件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尽管深社协对待社会工作的“双重关系”的伦理问题看似严厉,但是对于一线社会工作者疑似被集体“性骚扰”的事件却以行业“通报”的形式处理,并未采取进一步的保障社会工作者执业安全的措施,如寻求警察协助等(广州社协的处理方式也与深圳社协类似)。可见,地方社协在处理行业伦理规范问题时,似乎更倾向于运用伦理规范“严惩”一线社工,以保护案主权益,维护行业的社会声誉;但是一线社工面临外部职业风险时,则可能因“保密”等专业伦理而弱化对社会工作者本身权益的保护。这一方面与专业伦理的约束力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社会工作的职业保护缺乏正式的规范。因此,社会工作在职业保护规范未出台之前,都将长期面临职业风险,有必要做好自我保护与行业保护。我们可以根据现有的经验总结出社会工作者可能面临的职业风险:
第一,身心安全风险。首先,社会工作者工作方式和内容决定了人身安全风险存在的可能性。社会工作者经常去社区进行调研、家访、在办公室或上门会谈,需要与各类案主接触;尤其是社会工作者单独向家庭(校园)暴力、性侵、社区矫正、医疗纠纷、(灾害)应急干预等案主提供服务时将面临更多的身心安全风险。其次,在移动互联与人工智能时代,外部风险更是被无限放大,社会工作者作为“普通人”的身心脆弱性暴露得更加明显。如本文所分析的“王女士”的涉嫌电话“性骚扰”事件并非发生于传统的面对面情景,而是通过移动电话及其他可能的工具(微信、qq),波及了广州与深圳约1/6的服务中心,比起传统的职业风险涉及面更广,传播速度更加迅速。
第二,缺乏职业保护规定,面临被投诉、被处罚的风险。首次,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大规模职业化发展刚刚过去十年,发展较快的广州、深圳、上海等东部地区已经开始建立了地方性的社会工作伦理规范制度。这一方面意味着,随着规范的完善,社会工作者在执业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的约束;但另一方面这些伦理规范很少通过“社工—案主—机构—行业协会”的多方实践经验共同建构,而是模仿欧美、港台地区的规定居多。这样带来的问题是,伦理规范很难受到社会工作服务的利益相关方共同认可,在实践中也很难具有指引性、可操作性以及保障执行力度。这种情况下,本来应该具有保护和约束社会工作者职业行为双重功能的专业伦理规范,就沦为是行业协会(绝大部分情况下代表官方主管部门)单方面约束与惩罚违规社会工作者的工具。其次,港澳台及中国内地等华人地区的社会工作伦理大都缺乏保障伦理规范顺利实施的规定(沈黎、吕静淑,2014),甚至连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社会工作伦理也缺乏关于职业保护的条款。这就意味着,我们构建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伦理的时候,不仅需要纵向地借鉴欧美、港台地区的先进经验,尤其是港台的社会工作伦理规范是建立在正式立法之上的进一步细化指引;也需要横向地借鉴如律师、医生等的伦理规定和立法,确立与职业特质紧密相关的职业权利和职业保护。例如,我国的《律师法》就规定了律师在司法程序上如“会见权”等独有的职业权利。现有与社会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虽然“涉及”社会工作的某些工作内容,但是这些规定基本都是“一笔带过”,对社会工作者的工作职责与义务并没有详细说明或有进一步的法律或政策上的具体补充,例如《反家暴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基本都只是“鼓励”社会工作“参与”相关工作的态度。再次,社会工作者面临行业处罚而缺乏相应的救济渠道和程序。以内地第一例因“双重关系”而被深社协处罚的“郭社工”事件为例,深社协虽然有《深则》等一些业内规定作为处罚依据,但是却并没有建立完整的伦理处理的“正式程序”,使得“郭社工”被强硬“注销注册资格”却缺乏行业内的救助渠道。①司法程序上的救济具有一般性,对于社工处理有一定的使用性,但并没有职业针对性,内地也暂时没有这种因行业处理而出现司法救济的情况。因此,不能断言在民法上的救济程序能否有助于社工寻求救助。因此,社会工作者如没能做好隐私保护、避免双重关系等等工作,有可能会案主遭受投诉,并面临行业处罚而缺乏规范的救济途径。
第三,遭受案主起诉的风险。例如,隐私权是我国的《民法典总则》、《侵权责任法》所保护的民事权利,而社会工作的行业性质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案主或多或少的隐私。社会工作者若侵犯案主的隐私权则意味着可能既要受到行业处罚,也会被案主起诉的双重风险。虽然现时还未出现社会工作者因侵犯案主的隐私权力而被起诉的案例,但是从业人员做好预防侵权的防范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在刑事责任方面,《刑法》第三百一十条更是规定:“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该罪包括两种行为:一是为犯罪人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的行为。这是指将自己的住处、管理的房屋提供给犯罪人或者给予犯罪人钱、物,包括食品、衣被等,帮助犯罪人隐藏或者逃跑,逃避法律追究。二是作假证明包庇犯罪的人。这是指向司法机关提供假的证明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法律追究。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工作性质可能使社会工作者对案主产生“反移情”效应,从而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盾牌”下做出窝藏、包庇案主的极端行为。另外,在我国的刑法中规定了几种类型的特定职业犯罪,如常见的公职犯罪: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医生(医疗)犯罪: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律师犯罪:妨害作证罪等等。可见我国刑法对涉及重要的人身财产权利的职业犯罪监管较为严格。随着社会工作行业的发展,或许与社会工作者相关的职务犯罪也可能进入刑法。
四、结论与讨论
简而言之,社会工作作为我国新兴的职业,与律师、会计师、医生、警察等等职业一样,都面临着类似和迥异的伦理困境和职业风险。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在很多时候是由于实践经验和从业伦理规范的双重缺失所致。社会工作者对专业伦理原则的认识误区也可能加剧伦理困境,使得伦理冲突更加复杂化,笔者将这种类型的困境称之为“虚假的伦理困境”。之所以为“虚假的”,是因为这种“困境”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工作者对专业伦理的认知偏差、扭曲所致,当这种认知误区与具体的实践场域、情景相结合时,便表现出复杂化的伦理冲突,而这种冲突有时又会演变为职业风险,危及社会工作者身心安全和执业安全。如上文所分析的“王女士”事件,某些社会工作者便对“保密”、“接纳”、“不评判”等等原则表现出僵化的理解和误解。例如把“保密”理解为“对所有人保密”,把“接纳”案主理解为“不能拒绝求助者”,把“不评判”案主的个人价值观和态度理解为“不批判”案主的行为和社会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在现实中非常常见的情况。一旦遇到类似于“王女士”这样的“职业案主”(professionalclient),便演变成为非常复杂的伦理困境,甚至陷入被语言“性骚扰”的险境当中。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陷入伦理困境及抉择冲突当中,很多时候没有意识到产生困境的原因在于专业伦理规范上的“唯我独尊”,即忽略了案主的主体性,排除了案主对于伦理建构的参与,误把自身的困境当做双方的共同困境。例如,把“禁止双重关系”伦理原则“移植”到中国内地时,便会在实践中发现社会工作者单方面强调与案主的“专业关系”,而排斥“私人关系”,十分容易引起案主反感,导致双方的“专业关系”难以建立和维系。上文所述的“郭社工”事件,也是一个触动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双重关系”的契机。另外,“案主自决”原则也不是为社会工作者“甩锅”(推卸责任),而是应该意识到其原则背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在做伦理抉择时除了尊重案主自决外,更需要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一起面对抉择后的局面,共同承担决定带来的后果。
因此,在我国社会工作行业职业规范缺乏具体的可操作化规范和相关立法,而在地方省、市、区(县)的相关规定又不一致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工作从业人员更有必要有意识地去处理伦理难题,防范与社会工作实践相伴而生的职业风险。
首先,外出服务时尽量避免单独行动,将身心安全风险降到最低。1)社会工作者进行社区调查、上门家庭探访等服务时最好有同伴同行,没有同伴同行的情况下,也有必要告知机构的同事自己的工作去向,做好规范的外展记录,防范伦理与职业风险。2)社会工作者在从事高风险领域服务时(如家庭暴力,禁毒等等),需要积极联动警察等资源,主动寻求协助,保障执业安全。3)移动互联时代、人工智能时代接踵而来,更是将社会工作者所面临的身心安全风险无限放大,社会工作者需要继续学习网络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咨询及会谈技巧,总结服务经验,避免陷入新的职业风险,如被“王女士”等“职业案主”(professional client)骚扰等等。
其次,规范服务流程,签订书面/口头的服务协议,做好服务记录。借鉴社会工作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的从业者守则,如美国的《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守则》,香港的《社会工作者工作守则》等,规范自身的服务流程,签订书面/口头的服务协议,做好全程的服务记录,以防范被投诉、被处罚、被起诉等等的职业风险。
再次,社会工作者要熟悉与服务相关的法律、社会政策,以免在服务的过程中触犯法律或者违反政策。在服务地缺失相关从业规定的情况下,要主动援引较受国际认可的行为守则作为自己的工作指南,如美国的《全国社会工作人员守则》、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等等。当然,这些规范也并非十全十美,仍然需要从业者在实践中根据情景而批判性地使用。
最后,向资深从业人员请教、学习。资深从业者在社会服务的过程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多向他们请教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和抵御职业风险。学习与汲取资深从业者的经验,并不意味着将他们的经验当做唯一的权威。现实中,业界“崇港”、“媚美”的现象并不少见,这一方面是因为本土的社会工作职业体系尚未发育成熟,另一方面则充分地表现了内地从业者的“专业不自信”。
总之,随着我国社会工作职业化的纵深发展,加强社会工作伦理建设、完善伦理规范,防范社会工作职业风险的必要性将势必随着社会工作实践的推进而逐步显现。首先,我们应当总结过往的实务经验,并合理地看待中国的“精英式的传统道德文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政府的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殷妙仲,2011),提炼出有中国本土的社会工作伦理理念。例如,在家庭暴力个案中,传统观念认同“家丑不可外扬”,十分重视保护家庭的亲情伦理。那么社会工作者在处理此类个案时,就既要考虑案主的生命安全与隐私保护,也要充分考虑与案主相关家庭的亲情伦理。其次,在构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伦理体系的同时,借鉴欧美、港台地区构建社会工作伦理体系的经验,使“本土”与“国际”接轨,搭建与中国内地实务的场域相符合的伦理框架。再次,制定操作性较强的社会工作伦理规范(守则)以便社会工作者更好地处理伦理困境。最后,参考香港的《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与台湾的《社工师法》等华人地区较为先进的社工立法方式,推动与社会工作相关的立法工作,使社会工作在法律层面上获得认可,从而更好地保护与约束社会工作从业人员,将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的职业风险降至最低。
[1]定光莉,2011,《案主自决原则在临终关怀中的应用及伦理冲突》,《中国医学伦理学》第2期。
[2]冯浩,2015,《案主自决原则在华人社会中的实践困境》,《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3]冯雅,2013,《社会工作者的职业风险及应对策略》,郑州大学。
[4]郭伟和,2016,《从一种规训技术走向一种社会建设——社会工作参与现代国家治理的作用转变》,《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第4期。
[5]顾东辉,2016,《“三社联动”的内涵解构与逻辑演绎》,《学海》第3期。
[6]黄晓星、杨杰,2014,《社区治理体系重构与社区工作的行动策略——以广州C街道社区建设为研究对象》,《学术研究》第7期。
[7]江娅,2007,《社会工作中的伦理困境和价值冲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8]李霞、尚玉钒、高伟,2011,《职业风险、组织公平对离职倾向的影响作用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5期。
[9]李迎生、方舒,2010,《现代社工、义工事业兴盛的条件与机制——基于西方及中国港台地区的经验》,《河北学刊》第5期。
[10]拉尔多夫·多戈夫、弗兰克·M洛温伯格、唐纳·哈林顿著,2005,《社会工作伦理:实务工作指南(第七版)》,隋玉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1]马克斯.韦伯,2010,《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版)》,康乐、简惠美译,广西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2]沈颖,2011,《案主自决与价值中立原则下的老年社会工作服务》,《社会工作(实务版)》第9期。.
[13]沈黎,2012,《本土社会工作实务的伦理困境与伦理抉择——基于上海青少年社会工作实践的质性研究》,《社会工作》第2期。
[14]沈黎、吕静淑,2014,《华人社会工作伦理守则的比较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5]王思斌,2011,《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
[16]王思斌,2014,《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社会工作》第1期。
[17]王思斌,2013,《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叠错现象分析》,《广东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18]汪昊,2017,《“郭社工”事件与社会工作职业伦理之问》,《中国社会报》,4月21日第005版。
[19]徐永祥、曹国慧,2016,《“三社联动”的历史实践与概念辨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20]徐翀,2012,《社会工作者保护保障机制探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6期。
[21]袁芮,2016,《社会工作介入婚姻暴力中的伦理议题——以案主自决和保密原则为例》,《伦理学研究》第3期。
[22]殷妙仲,2011,《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第1期。
[23]颜小钗、高小敏,2017,《社会工作伦理在社会工作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中国社会工作》,http://theory.swchina.org/exchange/2017/0410/28719.shtm l
[24]张丽霞、李芳,2016,《中国社会工作发展高端论坛在武汉召开》,《中国社会工作》08月25日。
[25]张和清,2011,《社会转型与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思想战线》第4期。
[26]张和清,2016,《中国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议题与实务模式探索——社区为本的整合社会工作实践》,《东南学术》第6期。
[27]朱健刚、陈安娜,2013,《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第1期。
[28]Abramson,M.1984,Theautonomy-paternalism dilemma in socialwork practice.SocialCasework,66,387-393.
[29]Biestek,F.P.1957.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Chicago,Illinois:Loyola University Press.
[30]Freedberg,S.1989 Self-Dtermination:Historical Perspectivesand Effectson CurrentPractice,SocialWork,34,33-38.
[31]Hugman,R.2003.Professional Values and Ethics in socialwork:Reconsidering Postmodernism?The British JournalofSocialWork,33(8),1025-1041.
[32]Perlman,H.H.1965.Self-deternination:Reality or illusion?Social Service Review,39,410-422.
[33]Payne,M.1999.“Social construction in socialwork and social action”in Jokinen,A.Juhila,K.and Poso,T. (eds)Construcing SocialWork Practices(A ldershot:Ashgate):25-65.
[34]Reamer FG.1998.Ethicalstandards in socialwork,Washington,DC:NASW Press,.
[35]Rothman,J.1989.ClientSelf-determ ination:Untangling the knot.Social Service Review,63,598-612.
编辑/程激清
C916
A
1672-4828(2017)03-0048-18
10.3969/j.issn.1672-4828.2017.03.004
①感谢深圳、广州两地的社工同仁为了推动行业持续改善、发展而接受笔者在线访谈;感谢中山大学裴谕新副教授、伊利诺伊大学犯罪学蒋博士、北京大学心理学谢博士、钟警官接受我咨询。另外,笔者已经对受访者个人信息做尽可能地隐匿处理,笔者自负一切文责。
——认知行为治疗介入精神障碍康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