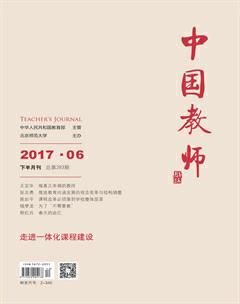平凡的教师,不凡的历史
柴净净
郑书廷
女,1945年10月生,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宋夏庄人,初中学历。1963—1972年于宋夏庄小学任教,1972—2000年于小章村任教。1986年以前为小学民办教师,1986年转为国办教师。1993年被评为“小学高级教师”,2000年退休。
历史的拥有不应仅局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伟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故事。追忆往事,那些不经意间走过的漫漫长路或许会成为后人永远珍藏的精神食粮。用一篇文章来讲述我作为一名乡村女教师近四十年的历史故事,恐怕不能完全概括。但是基于对教师生活整体上的认识,我会将最值得分享的教师故事展示给大家。回顾这一生,我认为可以用这样两个具有对比意蕴的词汇来概括我的经历:物质匮乏和精神饱满。
一、物质匮乏的一生
物质匮乏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是当时整个社会的主色调。我出生的时候,抗日战争刚刚结束;我的成长经历解放战争、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等时期。可以说,我成长的那个年代,社会正处于尤为困顿的状态,无论是生活条件还是教学条件都极其恶劣。我相信任何一个与我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以及任何一个真正走进我的生活世界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触。
1.生活上由朝不保夕到节衣缩食
(1)求学时代的朝不保夕
在那个穷的一无所有的年代,我人生的前四十年几乎都生活在食不果腹的环境中,尤其是上学的那些年,生活的艰辛更是令人难以想象。
在艾村小学上高小的那两年,我们家连过年都吃不上馒头,平日里都是吃糠、野菜和草籽儿之类的东西,拉肚子便是经常的事情。一到春天,好多男孩都上树去摘榆钱儿吃,我不会爬树,只能吃榆树皮和他们扔下来的榆树叶。条件那么艰苦,我们也要坚持上学。
在平乡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日子更加艰苦。家里的人都是在大队里吃大锅饭。他们吃的也不好,都是菜窝窝、野菜汤,见不到半点油水。而且,只有下地干活儿的人才能在大队分到饭吃,我是学生,队里不管饭,都是家人们把自己的饭匀给我一些。有的时候,姐姐会从大队食堂里带回来一些洗刷完之后、比较稠一点的汤水给我喝,除了这些,没啥可以吃的。
那时候从来没想到会过上现在这样不缺吃不缺穿的日子,更不会想到几十年后的人们会这样严重浪费。现在铺张浪费的人,大都是没挨过饿的,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反而不懂得珍惜。
(2)任教之后的节衣缩食
196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辍学在家的我与教育结缘。我先后在宋夏庄和小章村两所农村小学任教,但是无论在哪里教学,我的生活依旧一贫如洗,尤其是在小章村当民办教师的那二十多年,生活条件更是艰苦。
生活条件艰苦,最主要的原因是民办教师的工资待遇极低。在宋夏庄小学任教期间,我的工资是一个月4元钱,外加一天9工分。在小章村任教期间,除了1984年①,我的工资一直都是一个月6元钱,外加一天9工分。每年积攒的工分到了夏天可以换半桶麦子(20多斤),秋天的时候大队还会分四五十斤玉米和十来斤大豆。那时候的教师也没有医疗保险,生病了连药都买不起。感冒了,就用家里的土方法,用茅草根熬水喝,然后钻到被窝里捂汗。
除了工资待遇低,“农民”的身份也加重了我们的生活负担。由于丈夫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的四五亩农田便只能靠我一人打理。无论多累,我也要抽时间下地,遇到浇地的时候,就只能晚上自己去浇。我经常中午去锄地,有一次实在累得撑不住了,竟躺在坷垃窝儿(农田洼处)里睡着了,醒来的时候看看太阳觉得到点儿了,就赶紧起来去学校上课。那些年,我早晨去学校的时候带上午饭,中午把带的冷窝窝头什么的吃了,喝点儿水,然后不是备课就是下地干活,那些年(1972—1986年),我中午几乎没有回过家。
艰苦朴素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或许这就是时代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留下的印记:因为苦过,更知甜之不易。
2.教学上由一无所有到独当一面
(1)任教之初的一无所有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任教之初实际上是在创办耕读小学。村支书请我去当老师的时候,宋夏庄小学已不存在了。我答应邀请,便开始街邻四舍地寻找生源。我们找到了十几个五六岁的孩子,宋家庄小学又建起来了。然而,除了学生,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没有教室。最初,我们在一户乡亲家的大门底下上课,后来因为学生们太过吵闹,被迫离开,搬到另外一个乡亲的破屋子里上课。不到一年,我们又因为同样的原因被迫离开。最终,我们固定在村里的一间破庙里上课。有了教室,还没有桌椅。我就带着铁锹在破庙里挖坑,隔一段挖一个坑,学生们就坐在土坑里,把地面当桌子。桌椅的问题解决了,我们又开始上课了。
(2)教学路上的踽踽独行
由于资源有限,宋夏庄小学和小章村小学(1966年以前)都是只有两个老师、两个班级、班级里各个年级的孩子都有。老师们都是全科教师,我主要负责三、四、五年级的课程。为了能够教出好成绩,我做的最多的就是给孩子们加课,其他班和村里的其他学校都是上午和下午上课,而我跟我的孩子们,每天五更(清晨3時至5时)上课,晚上也上课。每天早上起来之后,我会在我家门口点上油灯,孩子们看见我家门口的油灯亮了,就知道该上学了。晚上上课学校没有照明设备,我就把自己家的花籽油拿到学校给学生点上照明。因为没有钟表,只能自己看天色或者凭感觉。那时候,下课也没有具体的时间,从早上上课一直上到晚上,已经无法按照正常的课时来衡量工作量,只希望能够教会
学生。
二、精神饱满的一世
虽然物质上拮据了一些,但我依然热爱生活和我的学生们,而且我坚信丰富的精神世界完全可以超越甚至掩盖匮乏的物质世界。
1.钟爱学习的可贵品质
我从小就喜欢学习,这种品质伴随我走过了六七十个春秋。我在上学期间,学业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那时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班上的女生寥寥无几,父母也并不支持我上学,经常让我旷课在家帮忙,我随时面临辍学的危险。因此,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家里没电,我就用胶泥捏成蜡碗,晒干,然后往里边放点儿油,再把棉花搓成捻儿放进去,晚上点着这样的油灯学习。
業精于勤荒于嬉。任教之后,我依旧保持着谦虚好学的态度。我珍惜每一次去县城进修学习的机会,并经常写教学日记以帮助自己反思、改进教学。20世纪90年代新课改之后,我面临一些教学上的困难,但我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为了解决困难,我经常一个人在办公室研读各种教材、资料。实在无法解决,我便骑着自行车去向四五里之外的侄子求教。我的儿子和侄子比我的学历高、懂得多,所以我便时不时地向他们请教。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从未懈怠过。
2.乐此不疲的教学生涯
(1)选择孩子就是选择快乐
我喜欢教师这个职业,而且在我的熏陶下,儿子师范毕业以后也做了教师,儿媳妇也是小学教师,我们都是从内心认可自己的职业,觉得当老师是个良心活儿,心里踏实。在小章村小学任教的时候流行样板戏,我便自编自演教孩子们说样板戏,这曾经一度成为了我们音乐课的内容。全校的体育课也由我一人担任,我参加过体育课的培训,学过广播体操,体育课上,我跟孩子们一起做操、做游戏、编顺口溜。比如,在孩子们上体育课站队的时候,我就自己编一些类似这样的顺口溜儿:“一二一、一二三四,挺起来脯儿,扬起来脸儿,嬉皮笑脸儿多难看儿。”孩子们很喜欢我的课,而我也乐在其中。虽然经济条件落后,但是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
创造!
(2)付出实乃优秀教师之王道
虽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但是跟村里的人关系非常融洽,大家也都很尊敬我。究其原因,我认为这跟我多年来的付出分不开。学生生病了没去上学,我会在当天就去家访,而且往往会带上几颗苹果;学生想吃蔬菜却没钱买,我会伸出援助之手;学生在学校受伤了,我会送他去看医生;偶尔会有经常旷课甚至几欲辍学的学生,我苦口婆心地劝导他重新回到学校……因为经常给感冒的学生买药打针,所以村里的人都知道我会打针。有一次爆发流感,村里的赤脚医生不在,大家都找我打针,我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打,从放学一直打到吃晚饭的时候,最后累得腰都直不起来。还有许多类似的事情,我勤勤恳恳地付出,乡亲们都看在眼里,怎么可能得不到学生及家长的尊重呢?
我这一辈子虽然没迈出过学校的大门,但却跟打仗一样,一直在跟他们斗智斗勇,只是他们不是我的敌人,而是我的亲人和战友。
访谈后记
从一个十六七岁的初中毕业生到投入了二十多年心血的民办教师,再到名正言顺的公办教师,直到以小学高级教师的职称退休,可能很多人无法想象在那样恶劣的条件下,在如此繁重的工作量面前,郑老师是如何泰然处之的,又是如何化物质悲剧为精神动力的。郑老师对往事记忆犹新,面对访谈毫无保留,侃侃而谈。从她声情并茂的话语中,可以看到一名普通的乡村女教师对农村教育事业的默默耕耘与执着付出。在我看来,“苦”是郑老师教学时代的主旋律,而“坚忍”则是生长在她内心深处的常青藤。未曾经历过便很难真切地体会经历者的情感世界,作为一个研究者,我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将最真实、最原始的状态呈献给读者,至于体会和感悟大概也会因人而
异吧!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口述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胡玉敏
huym@zgjsz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