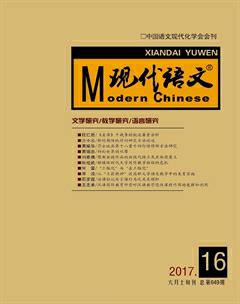论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 要:聚焦于苏童笔下的女性形象是当下苏童女性研究中的重点。文章试图通过分析苏童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类型及特征,进而探究红粉女性形象特征的原因。最后通过联系作者之前和之后的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引出苏童塑造的红粉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苏童 红粉系列 女性形象
引言
“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比如《妻妾成群》中的颂莲,比如《红粉》中的小萼,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或者我觉得女性身上凝结了更多的小说因素。”[1]“女性形象”是苏童小说中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在其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占据了大量的篇幅,无论是《妻妾成群》中陈佐千的四房太太,还是《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亦或是《妇女生活》中的娴、芝、萧,《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的简氏姐妹和三个店员,她们都极具特色,在苏童的笔下顾盼生姿。苏童以其独特的女性观和历史观,充分探讨女性身上形成的性格特征,深刻关切女性的命运。
目前对于苏童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红粉”系列上,主要针对其中具体的女性形象和女性悲剧的成因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对于之前的“枫杨树”系列和之后的“香椿树”系列中对女性形象的研究较少,进而得出苏童塑造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的研究少之又少。本论文将以苏童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为切入点,细致全面的展示苏童对于女性形象的认识,进而梳理苏童关于女性形象特征的女性觀和历史观,最后引出苏童塑造的红粉系列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一、“红粉”女性形象类型及特征分析
(一)争宠夺爱的妻妾们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女人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明争暗斗,她们既可以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不可开交,也可以无事生非,上演着勾心斗角的戏码。《妻妾成群》中以毓如、卓云和颂莲等为代表。大太太毓如是以一个信佛老太太的形象出场的。当陈佐千带着颂莲去见她时,她在佛堂里念珠诵经,口中念念有词,罪过,罪过,始终没抬眼看颂莲一眼,就连颂莲想要替她捡佛珠,都被她轻轻推开。由此可见,妾的地位在明媒正娶的太太眼里是非常低贱的,是得不到认可的。后来焚烧枯叶的事件中毓如表现出对颂莲强烈的不满,拉开了两人的斗争帷幕。可以说颂莲与毓如的斗争是《妻妾成群》中最隐晦的,没有硝烟弥漫的战场。颂莲对毓如的攻击不过表现为在陈佐千面前的几句调笑,而毓如对颂莲的攻击则被披上维护家族颜面的外衣。在颂莲醉酒事件中,毓如有这样一句话:你们都动手呀,给这个疯货点厉害。这里变很有一些歇斯底里的疯狂,毓如封建家长的外衣也就被沉底粉碎。颂莲在年龄、外貌上对毓如的嘲笑,毓如自恃身份对颂莲的蔑视,这构成了两人的基本矛盾,其本质是对自己在陈府中地位的维护与争夺。在二太太卓云身上,显现出女性人性中最为阴暗、丑陋的一面。卓云的最大悲哀在于一生中都沉浸在做奴隶和帮凶的角色中不可自拔。她把自己的不幸和痛苦都报复在与她同样不幸的女人身上,她表面慈眉善目,看似善解人意,实则工于心计,在妻妾斗争中最为阴险歹毒。她为了自己在陈家的地位不受动摇,偷偷给三太太梅珊下堕胎药,唆使丫鬟雁儿对四太太颂莲下咒。她在参与杀害三太太时表现出的种种行为,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一个人性尽失、毫不自知的女性形象。小说中,颂莲因为人性未泯致使在妻妾斗争中陷入弱势,一次偶然的机会让颂莲发现卓云指使雁儿对自己下咒,竟残忍的用剪子剪下卓云的一只耳朵,甚至花园里的人也听见了卓云那声可怕的尖叫,梅珊房里的人都跑过来看个究竟。她们看见卓云捂住右耳直冒虚汗,颂莲拿着把剪刀站在一边,她的脸也发白了,唯有地板上是几缕黑色的头发。颂莲终究在这场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斗争中变得越来越恐怖,她把陈家大院中的女人都视为自己最大的敌人,用一切残忍的手段来宣泄自己内心中的仇恨。当颂莲发现比她地位更为低下的丫环雁儿也做着太太的梦,并且与老爷之间关系暧昧时,立即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下,雁儿最终死在了颂莲的手里,此时的颂莲丝毫没有悲悯之心,她始终都觉得雁儿这样的女人就该死,她却不知道雁儿的结局也预兆着她自己的结局。颂莲对雁儿非人的虐待,已充分展示出颂莲病态的内心,这种病态的内心尤为让人觉得可悲。
(二)孤苦不幸的风尘女子
社会的日新月异,可以改变一个人生活的外部环境,但却改变不了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历史残留,这样的女性在苏童的小说《红粉》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红粉》中的秋仪和小萼都是孤苦无依的女性。秋仪的父亲是个瞎子,没办法给秋仪起到保护作用;小萼的父亲死了,母亲也改嫁了。两个人十六岁就都进了妓院,由于长期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使她们养成了好逸恶劳、贪图享乐、自甘堕落的恶习。
秋仪是一个性格刚烈、爱憎分明、反叛意识很强的女子。她拒绝政府对她的改造和安排,在去往劳动集中营的途中她跳下卡车逃跑了,去投奔她所钟情的男人老浦。她原本想嫁给老浦,但是老浦的母亲根本不接受她。在投奔无果的情况下,她去尼姑庵做了尼姑。在尼姑庵里她的妓女身份暴露后,她最终被赶了出来。秋仪有着强大的韧性,生活中的不幸她都承受得起,她与命运做着顽强地抗争,她希望自己能开始新的生活,但是希望却一次次的破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回到家中打算过安分的过日子,但是却遭到了亲人蔑视与抛弃,她心如死灰,终于明白即使时代变了,自己也永远无法摆脱妓女身份,只有投靠男人才是唯一的出路。最终她选择了嫁人,嫁给了一个鸡胸驼背的男人。
小说的另一个女主人公小萼的身上有着更多人性的弱点。她懒惰麻木、贪图享受、好逸恶劳,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全然找不到踪迹。她被迫接受了政府对她的劳动改造,但是一天缝三十条麻袋的劳动任务并没有改变小萼好逸恶劳的恶习,也没有让她树立起独立自主的自强意识。劳动改造的结束对于她来说只是代表苦难日子的结束。从麻场出来后,她与纨绔子弟老浦百般周旋,并如愿以偿嫁给了老浦,却又因为贪图享乐把老浦送上了不归路。老浦死后,她不肯艰辛度日,贪图一时安逸与房东私通。她甚至为了与另一男人北上而将自己的儿子留给了秋仪。秋仪和小萼两个人的个性完全不同。秋仪有主见,也有远见。小萼却是一个只喜欢依靠别人生活的寄生虫一样的女性。表面上看起来她们对生活道路的选择是完全不同的,但结局却惊人的相似,都选择依附了男人。依附于男人是她们最终的命运归宿。
(三)形形色色的市井红颜
苏童的《妇女生活》中展示了一家三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小说由三个独立的故事组成,每一个故事叙述了一代人成长的故事。苏童用最平淡的语气讲述了母女三代之间令人心悸的故事,三代人同样都是自私、乖决、冷漠的,在她们的身上我们读不到人情温暖,有的只是相互的抱怨与仇恨。一家三代女人都将自己不幸的人生归结在彼此的存在上,亲情在仇恨之中完全泯灭。虽然三代女人都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但是她们有着惊人的相同的生存方式和思维轨迹,她们都把自己的命运和男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女人不一定非要结婚,可她们离不开男人。她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男人的身上,但是她们所寄托着希望的男人都无一例外的背叛了她们。
《另一种妇女生活》中讲述的故事仍然是一群女人之间相互猜忌、相互仇恨的故事。地点是坐落在阴暗潮湿的江南小镇上的酱园。酱园的楼上住着深居简出的简家两姐妹,姐姐简少贞和妹妹简少芬。楼下店堂是以卖酱油为主的副食店,里面有三个女店员,粟美仙、杭素玉、顾雅仙。这三个女店员相互猜忌、尔虞我诈、拉帮结派、相互谩骂。粟美仙和杭素玉的不合,使她们经常指桑骂槐,相互斗嘴。粟美仙因怀疑杭素玉头拿店里的钱对杭素玉搜身时,被杭素玉用月经带打的满脸是血。杭素玉则带着自己的老公拿着菜刀去店里割粟美仙的舌头,一场场闹剧无休无止地上演着。最终因为粟美仙对杭素玉的造谣,以及后来的一场捉奸行动,让杭素玉惨死在了自己的丈夫的刀下。一場女人之间疯狂的战争,以一个女人的惨死匆匆收场了。
纵观简少贞的一生,她就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她漠视外面的一切,没有一丝一毫的热情投入到外面的世界,在她身上有着一条与社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她无法容忍妹妹的叛离,选择了用绣花针扎破了自己的动脉血管。在无法回避的现实面前,妹妹简少芬虽然内心充满了恐惧,但她还是愿意去看看小屋外面的世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融入社会。而姐姐简少贞却拒绝和任何除了妹妹以外的人打交道。当周围的环境要逼迫她去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她宁可选择自杀也不愿意迁就。她内心的孤独与冷漠是没有人能体会的。
二、“红粉”女性形象特征的原因探究
(一)苏童的女性观
苏童认为: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贱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逢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2]。苏童的小说中有这么一个情节:美是特别容易被摧毁的,本来就不多,很容易受伤害,或者说变质。将这两个观点融合理解,可以看出苏童对女性群体的认识,即女性是美而弱的。因为美而招惹是非,因为弱所以注定要遭遇不幸。而且在苏童看来女性所遭遇的不幸部分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缺陷:性格的缺陷。在红粉系列中,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拥有美丽的外貌,成长于不健全的家庭环境,《妻妾成群》中颂莲漂亮洁净,父亲经营茶庄,最后因破产而自杀,对其生母只字未提;《红粉》中秋仪丰满妩媚,父亲却是个瞎子,小萼十六岁死了父亲,母亲改嫁;《妇女生活》中娴十八岁无父,芝是一个私生子,而萧则是抱养的;《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氏姐妹亦是父母双亡。这种不健全的家庭环境养成了其偏执的性格,这种偏执又进一步使其敏感而空虚。秋仪可以说是整个红粉系列里最具抗争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女性,然而在其命运中依然缺乏自主选择权。面对政府对妓女的改造,她选择逃避;面对老浦母亲的羞辱,她选择逃避;面对尼姑们的为难,她还是只能逃。接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只是默然接受后母的安排嫁给陈佐千做妾,对陈佐千也表现出一种邀宠的意味,并为之与毓如、卓云等争风吃醋,互相斗争。陈佐千是她的“合法”丈夫,她对他既有受伦理支配的归属感也有一丝源于少女天性的情感幻想与依赖。陈佐千被颂莲寄予了感情依赖,在某种意义上,他填补了颂莲的空虚。娴给孟老板做情妇,她明知对方有妻室,也知道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却只忙于与其他明星争夺角色,而无暇顾及。小萼只顾自己享受而逼迫老浦挪用公款。这些人性的负面因素构成女性所代表的美的弱点,并最终成为其悲剧的根源。
“苏童的这些关于女人的故事引领我们审视的正是这种一定文化下的女性生存意识和生存状态,这就是说,作者关注的焦点不是男权文化中的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等如何为女性设计了种种深渊绝境,而是这些女性身陷深渊绝境之中而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3]这些故事并没有展现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与压迫,男权社会只是作为女性置身其中的基础背景,男性形象也在小说中被淡化,作者只是尽力剖析女性自身的特点和相互之间复杂的关系。
红粉系列中的女性形象,或清纯,或丰满,或苗条,无一不有诱人的外貌,其本性里又隐藏着人性的自私、贪婪与情欲,同时不健全的家庭成长环境养成其偏执的性格。她们是美,却有着摧毁自身的先天不足;她们是弱者,是被压迫者却无反抗的意识,只知一味地去依附。她们是时代主题的承受者而不自知,甚至游离在时代之外。
女性是美好的,在这里苏童将女性与美统一起来,其对女性形象的构建也就直观地展示出了他的审美情趣,而这种审美情趣的主体来自于他的“江南”。江南——美——女性,这三者在苏童的红粉系列里交织,彼此映衬。而苏童的江南是由少时的记忆与想象构建起来的,少时得肾炎的经历自然为此蒙上死亡与沉闷的气息,记忆与想象则延伸出唯美与朦胧。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的美,也就显得纯、脆弱,作为这种美的代表,“红粉”里的女性呈现出柔美与偏执,其本身没有信念支撑,显得弱,同时又包藏摧毁自我的因素。
(二)苏童的历史观
作为一名先锋派作家,在“先锋小说”风起云涌的鼎盛阶段,苏童的写作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转为“古典叙述”,接连写出了《妻妾成群》和《红粉》这两部充溢着古典性和抒情性的中篇小说。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文本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感慨苏童的才情和丰富的想象力,沉浸在作品所蕴含的历史中。
《妻妾成群》故事背景发生在二三十年代,这是一个刚刚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特殊时期。接受过新思想的女学生颂莲,本可以被塑造成冲破封建枷锁,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以此来形象地再现那段历史发展的“本质”。然而,苏童笔下的颂莲却退去了那身“白衣黑裙”的学生装,换上了“粉绸旗袍”和“绣花拖鞋”,返回到深深的庭院之中。在妻妾争宠这种类似于自然界的优胜劣汰的斗争中,让女性本然的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任由欲望膨胀,人性中的“恶之花”自由的绽放,最终掩盖了历史的锋芒。
同样,《红粉》也被安排在风云变幻的历史变革期,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小说中的秋仪和小萼这两个昔日的妓女,在新社会到来之际面临着必须接受改造的命运,然而,改造妓女可以说是符合当时“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类的政治历史背景的主流话语,但是秋仪和小萼似乎成为永远也改造不好的对象,她们坚守着自己的价值观念,游弋于历史的潮流之外。苏童偏偏绕过了这一主题,在对历史的反讽中完成了探究人性的命题。“在这些小说中,个人与历史的关系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个人不再是历史忠实的奴婢,而以自身的生命律动与节奏,同历史意义及价值分离,并最终摒弃了历史参照系,以自在自足的全新姿态,宣告了个人从历史规范中破壳而出。”[4]苏童试图摆脱一种常用的写作惯性,小心地把人从时代标签下剥离开来,更多的讲述人的故事。苏童曾说:“我并不觉得我有能力去从历史中接近真理。我不知道真理在什么地方。所有的历史因素在我那个时期的小说中都是一个符号而已。我真正有能力关注的,还是人的问题。”[5]苏童从来都是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作家。他在穿越历史中讲述苦难,思考人性,无不出于他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照。
三、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
苏童是以先锋小说作家的姿态进入文坛的,然而引起文坛轰动的不是他犀利的先锋叙事,而是对于女性的成功刻画。他对于女性身心的细腻把握,极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语境,彰显了苏童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体现了他对人的命运、归宿特别是女性的深入思考。
苏童是以他的“枫杨树”系列进入我们视野的。在那个朦胧未开化的年代,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承载着太多血泪、太多辛酸,苏童所构建中枫杨树中女性已完全沦为男人的附庸、生育的工具。像《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祖母蒋氏活脱脱就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在她的生命中好像孩子是永远生不完的,蒋氏怀孕了八次,忍受痛苦生下了几个孩子,自己在物资条件极度匮乏的环境中拼命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然而女人生育的本能并没有因为生活条件的恶劣而有所改善。祖母蒋氏在枫杨树村除了生孩子就是永不停歇的劳作,但是她从不抱怨生活的不公,也从不责备丈夫的胡作非为。蒋氏身上集中着中国传统女性的优良品质,勤劳、朴实、任劳任怨,把所有生命的不公化作沉默和无息的劳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从四德的紧箍咒紧紧套在她的头上,不会有脱下的那一天。在《罂粟之家》中的刘素子和崔花花同样是苏童先锋模式的探索。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更加娴熟地把先锋意识发挥到极致,荒诞的想象,畸形的生存状态,死亡和生存交织的枫杨树村到处充斥着血腥和暴力。作品中的女性完全沒有独立意识,懵懂无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同情,没有人怜悯,自生自灭的她们任凭男人的摆布,她们懵懂的独立意识和自觉意识很快湮没在贫困的生活状态和以男性为主导的滔滔洪流之中。
然而让苏童被广大读者熟知的不是他的先锋叙事,而是苏童的“红粉系列”,是苏童对女性真实、细腻的刻画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可以说苏童的“红粉”系列是苏童较为系统的对女性的生活进行全面的、多角度的、立体式的刻画,全方位地展现了女性在不同的时代环境所展现的相同的命运。
徘徊在社会边缘的妓女,游离在丈夫和姐妹之间的小妾,永远也摆脱不了男人的祖孙三代,远离社会侵蚀、却被社会无情唾弃的简氏姐妹,林林总总的女性在苏童笔下或是个性张扬或是含蓄默默,又或者是蛇血心肠、善良可亲,命运就好像事先安排好的一样,都对她们有一定的惩罚。《红粉》的秋仪和小萼不论怎么想和社会靠拢,但社会总是板起面孔,就是不接受她们,把她们拒之门外。小萼和秋仪为代表的妓女这一特殊群体在社会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社会在这中间充当了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一方面想尽办法改变这些女人的生存环境,让她们走向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但另一方面却又伪装得高尚无比,拒绝接受这些低贱的人群,她们就这样被社会骗来骗去,谋取生存的唯一的资本也被社会剥夺,零乱孤寂的心灵就这样随风飘荡,无处安放。《妻妾成群》是苏童从传统社会和家庭伦理对女性深入思考的小说,小说可分为明线和暗线,一明一暗构成了四位姨太太的悲剧命运,明线就是封建传统社会的一夫多妻的社会现状,男性作为社会和家庭的主导,是女性的生活的中心,暗线就是男尊女卑的家庭伦理观念,不但深深扎根在男人的骨子里,在女性的心中同样也默认这样一种安排。四位姨太太就这样在陈府大院中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只不过她们的争斗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的,输掉了战争,就失去了生命,所以她们谁也输不起。
苏童借助陈家大院这个小环境来折射大社会的真实处境,小家庭其实就是大社会的浓缩,大社会也就是小家庭的扩大延伸。苏童通过书写陈府的女性,表达了作者对于女性别样的理解,他已经从先锋文学的叙事角度脱离出来,女性不在完全是男性的附庸和工具,不在丝毫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她们开始有了独立生存意识,并逐渐加以延伸,这是苏童对女性角度的审视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开始的俯视逐渐转变为平视,观察角度的不断上移展现出作者的女性意识不断增强,是作者的女性观不断完善,不断丰富的表现。
在苏童作品系列中,“香椿树街”是怎么也绕不开的,香椿树街是苏童童年生活的缩影。在苏童的“香椿树”系列中女性俨然已经脱离了枫杨树故乡和“红粉”系列中依附于男人的困境,女性开始以独立的个体参与社会生活,这种变化一方面得益于新中国的成立、封建旧思想的瓦解,另一方面是女性自己独立意识的觉醒。然而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大环境依然没有退去,仍然在女性和男性的观念中发挥着作用,女性的悲剧还在香椿树街上一幕一幕上演着。《城北地带》中的这些女性不在局限于大院中和阁楼上,空间范围的扩大,生活环境从封闭到开放,女性的性格也不再阴险毒辣,反而增添了几分开朗、几分泼辣。被父亲卖掉,失去丈夫和儿子的腾凤,被丈夫和儿子欺骗的素梅,锦红的惨死,美琪的落水(《城北地带》)。遭亲生父亲多次强暴的红菱姑娘(《南方的堕落》)。被丈夫毒打的蒋碧丽(《训子记》)。为了哥哥的孩子一生忙碌,最后累死的华金枝(《菩萨蛮》)。苏童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的同时,也开拓了自己的女性观意识,对女性的塑造也由单一封闭的环境中转变成为开放热闹的弄堂里,生活环境的变化促使作者女性观的变化。在纷乱复杂的“香椿树街”上,女性不在单纯地面对自己的男人,自己的家庭,而是多了很多,像父母、孩子、同事、邻里等,致使她们不能把全部的精力完全放在自己的男人身上。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丈夫的背叛,儿子的不驯,周围环境的不断打压,让这些生活在香椿树街上的女人们的视线不得不从向内转到向外转,转身之间她们承载了太多的辛酸和委屈,但是就在她们转身的一瞬,却无人顾及她们内心的感受和痛苦。
苏童就是这样深深抓住了这些女性的内心孤寂,深刻地剖析了女性生活的艰难。在“香椿树街”系列中,苏童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女性的另外一种世俗的生存状态,更加全面地刻画出女性不同的生活面,丰富了作者的女性观。在这些女性身上他倾入最多的是同情,是怜悯,在描绘这些形形色色的女性背后,支配这些人物形象活动的是作者对于女性理解的女性观。在苏童看来,女性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她们是整个社会伦理的悲剧,女性只不过是整个社会运行的牺牲品。在她们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屈辱和伤痕,整个历史的变迁,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变迁,女性在某些地方起到了陪衬的作用,我们忽略了她们的功绩,甚至污蔑了她们的功绩。然而苏童却让这些被历史埋没的女性又鲜活了起来,让她们又一次站在历史的舞台上,并且以不同的面貌示人,在男权社会极度严酷的情况下开辟出了一块新的天地。
结语
本文以苏童的“红粉”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苏童独特的女性观及历史的分析、探究,了解了紅粉女性形象的特征,进而通过联系苏童之前的“枫杨树”系列小说和之后的“香椿树街”系列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最后得出苏童塑造的红粉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作者让这些被历史埋没的女性重新站上历史的舞台,由对作品中小环境的分析引出作者对于社会问题的分析,丰富了现当代中关于女性形象的研究。
苏童对于女性的深切关注,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对人的生存、人的发展和人的终身的深刻思考,在强调女性这个弱势群体中,表现出作者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对人性归宿的思考和探索。苏童用别样的笔法伸向历史和现实相互交映的女性身上,在这些女性身上找到了人的价值。
在本文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从同时期的先锋作家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上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探究苏童塑造的红粉女性形象的文学史意义。我们还要思考的是这些女性形象对我们当代女性的启示。
注释:
[1]苏童:《寻找灯绳》,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2]白华:《你是一条河》,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3]吴秀明:《江南文化与跨世纪当代文学思潮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208页。
[4]汪政:《苏童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490页。
[5]苏童:《妇女生活》,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王一丹 山东青岛 第五十八中学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