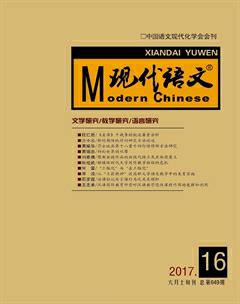从青葱时代到“青铜时代”
摘 要: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内心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亦具有稳定性态势,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约着作家的艺术选择。王小波创作于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作品虽然离成熟文本的标准尚有一定的差距,但已显示出别具一格的写作素质。这些早期作品不仅昭示了王小波最初的写作野心,同时其中积淀的美学精神和文体探索的自觉意识对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三部曲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王小波 早期小说 《青铜时代》 艺术嬗变
作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特立独行”的作家,王小波因小说和杂文受到读者热烈追捧,在文坛上掀起“王小波热”,实际上王小波的文学活动起步较早,甚至可以追溯到70年代的云南插队时期。王小波早期文学创作并不算特别丰富,目前可以见到的仅为收录在《黑铁时代》中的9部中短篇小说。当然就客观而言,这些早期作品在艺术上远未称得上圆熟,除《猫》等个别篇什外,大部分小说显得粗糙青涩,尤其是和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青铜时代”相比更是显得局促和简单。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作家的创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内心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亦具有稳定性态势,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制约和决定着作家的艺术选择,使之保持相对固定的风格。虽然王小波前后期小说创作的整体风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其艺术探索早期所秉持的文学精神和叙事特质并没有被作家刻意遗忘,而是沉淀于其文化意识之中,以新的方式继续参与作家的艺术创造活动。
一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可能很少有作家能像王小波这样,终其一生都将“新奇”和“有趣”作为文学创作最主要的美学追求。王小波创作起步的青年时代,恰恰是中国社会最保守、沉闷和封闭的文革时期,插队时的王小波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无休止且异常繁重的生产劳动,而当时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实行的半军事化管理,又使知青面临严重的精神禁锢和思想贫乏。时代造成了无智、无趣的世界,给作为“觉醒者”的王小波带来强烈的精神折磨和痛苦。正是基于对平庸无趣现实的反抗,王小波用文字和想象力构筑了一个新的“有趣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可以在大海中自由遨游并建立高度发达的海底文明(《绿毛水怪》),凶残丑恶的公社书记变为了一头驴(《这是真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自由交换性别(《变形记》),刘三姐也失去了美丽的容颜变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丑小鸭” (《歌仙》),在王小波早期小说中,真实和虚构的界限十分模糊,生活中种种现实规则被不断突破,异想天开的想象、奇诡怪诞的情景和新鲜有趣的构思随处可见,有力地反衬了现实生活的苍白和压抑。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小波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生活于行政体制之内,让王小波对社会中刻板无趣的一面有了更加清醒和直观的认识,也更加坚定了其利用写作构筑另一个诗意世界的决心。在王小波后来的写作中,发挥想象才能,追求“有趣叙述”成为其始终遵循的小说创作原则,甚至成为一个自觉的写作目标,使其小说文本带有某种“狂欢化”色彩。他努力尝试以大胆神奇的想象、夸张的变形和隐喻为主要艺术手段,再结合“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为20世纪末的中国小说创作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在留美期间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唐人故事》里,王小波对《昆仑奴》《红线》《僧侠》《潘将军》等古代传奇小说进行改写和戏仿,在同一个文本之中撮合了古人和今人两种不同截然不同的生存际遇,或者赋予古人某种现代色彩的情感特征,从而产生令人绝倒的阅读效果。借助奇谲的想象力,王小波虚构了一个个富有生趣的古代历史情境,却倾注了现代人在无趣沉闷的现实中的人性体验,让读者在捧腹之余不禁反思自我的生存状态。在另外的描写里,王小波则是纯粹向读者呈现一种精神和想象的奇观,天马行空,异彩纷呈,使读者获得一种阅读的满足和乐趣。在一向推崇现实主义的中国文坛,王小波的带有独特想象标签的“青铜时代”具有非同寻常的文学价值和意义。
经历了反复摸索和写作实践,特别是经受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思想洗礼后,王小波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局限有了深入反思,认为只有依赖想象和虚构,作家才有可能触及文学的真正本质。正因如此,在 “青铜时代”里王小波尽情挥洒着“澎湃的想象力”,将特立独行的人物、荒诞离奇的情节和趣味盎然的叙述结合起来,使小说文本树立了一种奇异的浪漫风格。
二
一个作家的某种“写作情结”的形成往往源于其自身成长历程中刻骨铭心的经历或情感体验,时过境迁后以潜隐的方式沉淀于作者内心,而在创作中又以各种方式“复活”,成为文本中的一个经典符号。在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中,各种死亡和刑罚场面层出不穷,或怪诞,或诗意,或夸张,完全颠覆了传统文学中沉重压抑的死亡印记,以另类的角度传达出对历史上粗暴践踏人类生命和尊严的暴行的强烈反讽。从死亡中洞观现实,以死亡(或者幻想中的死亡场面)超越无趣、无智的世界,成为王小波精心选择的一种文学表达方式。
王小波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天真烂漫的年纪却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沿街揪斗、大院教师被迫害致死、知识分子跳楼自杀、文革中红卫兵“武斗”殴伤人命等惨痛的场面,在其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特殊的人生阅历使王小波显得比同龄人更加早熟和沉稳,其早期创作也频繁地触及到死亡意识和死亡场面,包含了诸多死亡叙事的因子,对生死这个哲学命题的深入思考使其早期小说远远超越一般青春文学或者文革结束后社会上较为流行的知青写作模式。在《猫》这部气质独特的短篇小说中,王小波创作出具有象征意义的“死亡”符号,使其超越肉体消灭本身,昭示着残酷事件背后的社会学及文化学意义。王小波从一只只野猫被疯狂迫害后的惨状出发,联想到人类历史上一切在“文不对题”的借口下暴力、活埋、割喉等人类暴行,弱小者被剥夺反抗的权利,始终无法摆脱被宰割的命运。被挖掉眼睛后默默死去的猫,成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类中弱势群体和弱小民族的象征。显然,王小波通过对触目惊心的非正常死亡的描述,体现了一种清醒的国民性批判和对整部人类文明史的深刻反思。
在王小波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青铜时代”中,死亡叙事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重视,已经不再是作为交代小说人物结局的简单处理,而是另辟蹊径,将死亡视为人物的重要“生存体验”。在小说中,充满戏谑和游戏意味的死亡场面层出不穷,王小波又令人惊异地将死亡和性欲联系在一起,赋予了死亡摆脱无趣、释放生命的独特意义。王小波对死亡场面的处理则要复杂得多,基本剔除了和死亡相伴的血腥、残忍,再渗透诸多情感因素,将人物死亡的过程处理成一场夸张的“行为艺术”。典型的例子有《万寿寺》中薛嵩和红线在森林里杀死女刺客的情景:“那个亮丽的女人被反拴着双手,立在院子里,肩上笼罩着白色的雾气。此时马蜂在身边飞舞,嗡嗡声就如尖厉的针,在洁白的皮肤上一次次划过。后来,她就被带出去杀掉。在被杀的时候,薛嵩握住了那一大把丝一样的头发往前引,她自己则往后坐,红线居中砍去。按照红线的想象,这女人的血应该是淡紫色的,散发着藤萝花的香气。”在这些如诗般华丽的文字里,死亡不再仅是承担着叙事功能的符号,它甚至就是文学审美的对象本身。王小波充分调动类比、隐喻甚至通感等艺术手段,向读者描绘出奇特而另类的“死亡之美”。如果死亡使屈辱和痛苦得到解脱,那么诗意又是对死亡的超越。而通过各种死亡“仪式”的展现,特别是借助行刑者——被杀者——观众三者之間的张力关系,使王小波笔下的主人公实现了某种精神突围,尽情嘲讽和颠覆了僵化刻板的体制和意识形态,也使作品中的“死亡”具有了多方面的复杂意蕴。
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探索最为活跃的时期,在西方后现代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一些青年作家如刘震云、苏童、李冯、徐坤等热衷于对存在的经典文本进行重写和戏仿,对人物、情节、结构进行大的添加和改动,使读者突破对前文本的固定印象,最大限度地解构了前文本提供的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表现出对现代小说叙事艺术的自觉追求。而王小波早在70年代就率先实验了重写与戏仿的创作手法,展现了王小波创作过程中的逆向思维特征和建立在追求有趣的创作旨趣基础上强大的艺术想象能力,更显示了他在文体探索上一种可贵的探索意识。
王小波的第一部重写和戏仿之作是《歌仙》。《歌仙》中的人物原型刘三姐的故事流传甚广,而王小波对这个凄美忧伤的故事进行了大胆的重构,使之焕发出新的文学意义。这部短篇小说里,王小波一方面保留了经典文本的主要元素,又加以大胆的改动和突破,使新文本与前文本之间产生大的错位,同时创造出一个与原文本迥异的结局,借此传达出对社会人生新的认识和感悟。从小说的整体创作倾向来看,王小波并非是对原有文本添枝加叶式的扩充,而是将之前的人物设定和故事内核进行重大调整,以匪夷所思的人物和情节强烈冲击着读者的神经,造成什克洛夫斯基所谓的“陌生化”的独特美学效果。
在中后期的小说创作里,王小波对“重构历史”仍然倾注了巨大的文学热情,重写和戏仿甚至成为王小波最重要的艺术创作手法。早在留学美国期间,王小波就以《虬髯客传》《昆仑奴》等唐传奇为蓝本,创作了全新的《红线盗盒》《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舅舅情人》等五部短篇小说(后结集为《唐人秘传故事》出版),在这些小说中,王小波借用唐传奇中的人物和部分情节,运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虚构出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历史场景,同时又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反观历史,在“古今一般同”的叙述中,使历史与现实完成了奇妙的对接,也彻底解构了原文本营造的充满神异色彩的氛围。而在由《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万寿寺》等三部长篇小说组成的“青铜时代”系列中,王小波继续延续了重写与戏仿的手法,将小说视为个人化的历史虚构和想象,用相同的故事元素探索一个故事的多种发展可能性,只是文本结构更加宏大复杂,篇幅比唐传奇本身拓充了数十倍,共同叙述者“王二”生活的现代社会和小说中描绘的隋唐时代在小说中交织互渗,使文本具有了某种“复调”结构,极大扩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王小波的写作重点显然不是简单重述遥远时代的古老故事,在写到古人的某类生存遭际时,王小波常常运用联想和类比的方法,自然地插入现代人相似的心理体验,从而建立起两者之间异质同构的关系。借助古人和今人两条叙事线索,在历史和现实两个时空中不断闪回,以古喻今,借古今类比来反衬无智、无趣的庸常现实,成为王小波“青铜时代”的重要写作主题。
严格说来,上文分析提及的《绿毛水怪》《战福》《歌仙》等作品离成熟文本的标准尚有一定的差距,但王小波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写作能够最大限度地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和刻板的文学观念的束缚,使这些初试啼声之作带有鲜明的个性色彩。尽管王小波并没有因这批作品成名,但早期的摸索和准备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王小波的文學气质,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中后期的写作。如果说王小波早期小说创作经验是一粒种子,最终它在“青铜时代”中长成了参天大树。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王小波全集(第一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2]王小波.文明与反讽[A].沉默的大多数——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C].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张伯存.躯体 刑罚 权力 性——王小波小说一解[J].北京文学,1998,(9).
[5]南帆.小说艺术模式的革命[M].上海:三联书店,1987.
(杨开浪 云南芒市 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 678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