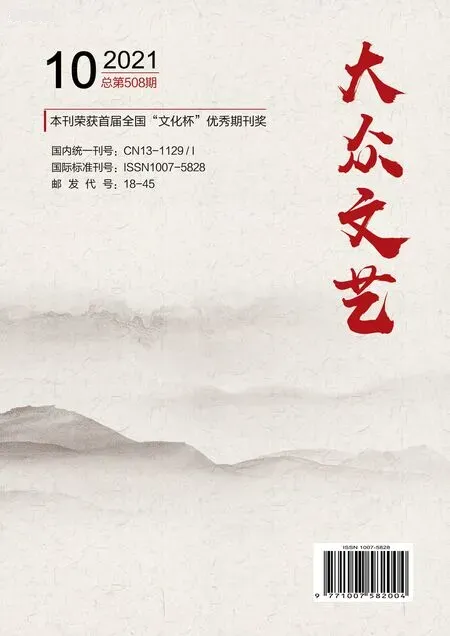精神生态批评:席勒《强盗》的再阐释
王自强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0024)
精神生态批评:席勒《强盗》的再阐释
王自强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30024)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席勒的剧作《强盗》关注不多,而且对其阐释也通常局限于“狂飙突进”运动 “抗暴”主题的话语范畴之内。不过《审美教育书简》蕴含了很多席勒对人类精神领域的思考,尤其是“完整的人”的概念的提出,为人类精神荒芜与碎片化的病症提供了一种解决的办法。精神生态批评在国内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理论本身还有很多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将席勒的“完整的人”的概念与精神生态批评相结合,借助对《强盗》的再阐释,是丰富理论和重读经典的有效方式。
精神生态批评;席勒;完整的人;《强盗》
国内对精神生态的关注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对人们精神荒芜的一种文化批判。首先,“生态”的概念只是借用附加在自然生态中的平衡和协调的象征意义;其次,“精神”的概念是与物质相对应的,而不是自然。而紧随其后的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是针对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等文化领域的精神之病。因此,这种“精神生态”的文化概念并不是一种批评方法,只是呼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的平衡和批判物质至上的风气。在新世纪之交,美国的生态批评传入中国。本文的精神生态批评便是基于生态批评的视野,并且认为,精神生态批评是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这一时期的精神生态中的精神的对应物不再是物质,而是自然与社会。精神生态批评就是要紧紧盯住人类的精神界,关注人类的精神污染、精神失落、异化、抑郁、疯癫等一系列的现代精神疾病,并寻求一种走向精神和谐与平衡的方法。
一、精神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和内涵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发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是其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动因。1978年美国生态批评家鲁克尔特首次提出了“生态批评”(ecocriticism)的概念。文学的生态批评的方法在美国逐渐形成一种成熟的、有体系的批评潮流,并且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生态批评最初是作为一种关注自然界的批评方法,指责人类的不合理行为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生态批评的批评范畴也在不断扩大。综合来看,美国的生态批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其诞生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是为第一阶段,即生态中心主义阶段。这一时期的生态批评是一种典型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尽管这种批评模式看到了人类对自然的无休止的掠夺所带来的全球生态危机。但是这种对自然与环境的过分强调显然走向了极端,同时生态中心主义式的文化批评对人类生态文化的危机根源的阐释也面临着一些学者的质疑。人类应该也必须要保护环境,这样做的原因是更好地利用环境,使得大自然能够可持续地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为此,九十年代末期以来,一些美国生态批评家如T.V.里德提出了“环境公正”的生态批评术语。这可视为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第二阶段。“环境公正”的批评模式主要呼吁生态批评要从“荒野”中回到人与自然交汇的中间地带。这一阶段的生态批评对“环境”一词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环境不再指纯粹的自然环境,人类生活的社会环境也被纳入到生态批评的视野。
生态批评从单纯的关注自然环境到关注社会环境,是批评的一次深化。但是,对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区分背后,依然是“人”与其外界生存环境的对立。虽然“环境公正”的批评模式在先前的“生态中心主义”批评模式中的“自然”范畴中加入了“社会环境”的批评视野,但是生态批评的两个发展阶段都没有摆脱长久以来的“人/环境”的二元对立模式。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生态批评自诞生以来的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使得人被割裂、被分离,最终被对立。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被认为是人类欲望高涨,对大自然无限征服与掠夺的思想毒瘤,并且这一思维方式被上溯至人类早期的神话时代。
在创世神话中,中国的盘古和女娲,《圣经·旧约》中的上帝,印度的梵天,以及日本的伊邪那岐命和伊邪那美命,虽为神灵却皆为人样。不是神按照自己的样子造人,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样子造神。这可以视为早期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萌芽。仅从西方来看,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文艺复兴,此间经历了两千年,人类的主体性或主体意识在不断地觉醒、完善,但还没有到膨胀的临界点。而且这种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并没有引发对自然占有的欲望,以人类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模式只是为了解放人自身,因此不应受到生态批评的批判。反之,人类主体性的觉醒为非人类生命体的主体性的发现提供了一个切口。对此,国内有学者认为:“自然科学已经证明人和动物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承认非人类生物的主体性已无逻辑上的障碍。”1只是,自15世纪末期的航海大革命以来,新大陆的发现,伴随着殖民扩张,人类在欲望的驱使下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与掠夺。随后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在整个欧洲普遍兴起,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主体性的意义空间被工业文明所诱发的利益欲望所排挤,与自然的对立成为这一思维模式的最为直接的显现。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中心主义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此间,其内涵不断发生流变。不可否认的是,在15世纪殖民扩张之前的人类中心主义,更多的是作为对自我主体性建构的积极意义而存在。生态批评所批判的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是以欲望主导下的对自然的掠夺与破坏的发展阶段。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流变的,也是复杂的,单纯地站在生态批评的视角对与自然对立的“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提出批评是武断的。因此,在生态批评的范畴之内不断加入社会环境因素,甚至加入精神环境的因素也解决不了这种困境。因为在“人/自然”二元对立的批评思维模式下,生态批评无法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做出区别的对待。
在二元模式下,“人”是作为自然的对立面而受到审视的,只有摆脱这种二元模式,生态批评才能获得更精准的批判力和更强的生命力。这也是精神生态批评产生的理论前提。人类中心主义之所以会发生意义的流变,是因为“人”这一内涵本身是复杂的。精神生态批评只有切实地关注“人”本身,考察人的复杂性,人的精神的多层次性,才能发现和谐的人格。在这个问题上,生态美学家曾繁仁先生曾认为:“生态美学的对象首先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审美关系,这是基础性的,然后才涉及人与社会及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2可以说,人自身的生态审美体系的建立对当前生态批评的完善与深化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精神生态批评从多层次、多角度关注处于完整的生态系统中的“人”,阐释人的精神生态的发展状况,才能更好的找出应对人类精神疾病的方法。同时,精神生态批评对人的精神生态的关注,也从一个侧面瓦解了“人/自然”的二元对立模式。人不再是自然或环境的对立面,人本身就是一个生态环境。所以,将精神生态批评从生态批评中分离出来是必要的,将精神生态批评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理论分支也是合理的。这就是精神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方法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
人的精神生态的完整与和谐,才能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人的精神生态的关注就是对欲望以及碎片化生存状态的改善,因此人的精神生态也和自然生态一样成为生态批评关注与呵护的对象,人不再是单纯的施害者。精神生态批评的应着重关注人类精神界的完整性与协调性,只有这样人才能是一个精神健全的人,也只有这样一种健全的人格才能更好地促进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思想界,对人的精神的完整性的关注最早应始于席勒,他在《审美教育书简》和《强盗》剧作中均做了十分深刻的阐述。
二、《强盗》与精神生态的完整性
从青年时代起,席勒(1759-1805)就开始构思戏剧《强盗》,1781年发表,1782年于曼海姆国家剧院上演,大获成功。《强盗》有两条主线,一条是以生活在世俗世界的弟弟弗朗茨为线索的“弑父”主题和霸占哥哥未婚妻的“乱伦”主题;另一条是以生活在丛林世界的哥哥莫尔为线索的为追求自由的“反抗”主题。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以下简称《书简》)中提出“完整的人”的概念,而其早年笔下的主人公一个强盗头子莫尔成为了“完整的人”的文学形象的对应。
在《书简》的第十二封信中,席勒认为人自身存在两种冲动,一种是感性冲动,一种是形式冲动。感性冲动来自人的肉体,是感性本身,它要求变化。这种来自肉体的感性冲动常常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断地扩展与膨胀,最终发展为人类的欲望。与之相对应的形式冲动,属于人的理性本性,它提供法则,要求不变,也追求自由。形式冲动中所包含的来自启蒙运动极力张扬的理性意图是不言自明的,它在承接文艺复兴对人的主体性呼唤的同时,也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加以复制,并用理性的外衣加以包裹。无论是来自肉体的需要与欲望还是人类不可摧毁的理性,最终这两种力量都将指向自然界,于是占有与掠夺以及奢侈的浪费便不可避免。“理性要求统一,可是自然却要求多样性,而人就被这两个立法机构同时要求着。”3席勒认为人类要调和这两种力量的规束就必须走向游戏的冲动,并且认为:“在其中两种冲动结合起来发生作用的游戏冲动……它扬弃一切强制……只有这样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4这种完整的人就是要节制感性冲动里的欲望,同时也要小心形式冲动下的强大的理性,从而达到人的“自然状态”。席勒受到卢梭的影响,都赞扬古希腊文明的素朴,主张返回自然。卢梭欣赏野蛮人的生存状态,认为那是绝对的自然,没有等级和压迫,没有私有制,人类才能实现完全的自由。但是和卢梭不同,席勒的返回自然,是为了寻找人的精神的完整性,是为了塑造一个精神强盛的人。
《强盗》中的流亡在森林里的强盗头子莫尔最终杀死弟弟,救出父亲和未婚妻。可是身为首领的莫尔已无法从原始的丛林生活中返回到现实社会,在面对作为首领的丛林责任时,他亲手杀死了自己仍然爱恋着的未婚妻。为了自由的追寻席勒让莫尔实现自己的丛林诺言,而且他敢于担负自己犯下的罪过,向法庭自首。戏剧中,莫尔为了救一个同伴却失手炸死了无辜的平民,这也是莫尔自首的原因之一。在席勒看来莫尔就是典型的“完整的人”,完整的人不是道德上的没有瑕疵的人,而是其精神生态是完整的,没有被分割的,摆脱了碎片化的人。席勒曾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写道:“现在,国家与教会,法律与习俗都分裂开来……人永远被束缚在孤零零的小碎片上,人自己也就把自己培养成了碎片……”5工具理性带来了人的碎片化,人的精神生态被破坏。由于人的内部精神生态的碎片化与失衡,人类在处理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便出现了裂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神生态批评应该关注人的精神生态的发展和存在状况。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主义思想认为,保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物种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的整体利益为最终目的。6整体性原则是精神生态批评的重要原则之一,那么精神生态批评对人的精神界的关注,也应奉行整体主义的原则。只有将人类自身内在的整体性建立起来,人在处理关于自然或环境的问题时,才能像古希腊人一样实现一种“自然状态”,和自然和谐共生。
对人的精神整体性的缺失的批判,席勒可谓是第一人。随后这种对人的精神和谐的探讨,被一种“异化”批判所取代,如黑格尔的 “精神异化”,随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说”,以及进入20世纪卡夫卡通过小说的形式对现代异化进行了阐释。而今当下社会正处于信息化工业时代,工具理性对人的精神的分割尚未消除,而人类本身对智能手机、互联网的极度依赖,以及充斥在我们周围的大量的垃圾信息和真假难辨的大数据,都使得人的精神状态被分割,甚至被奴役。我们不仅要看到人们改造并利用自然所带来的负面的乃至于极度恶劣的影响,也应该看到人也在无形之中受到人本身所改造的外在环境的影响。精神生态批评就是要在时代的洪流中,为人的精神的异化与碎片化敲响警钟。此外,透过具体的文本,精神生态批评也将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寻找摆脱人类精神困境的方法。
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哲学领域通常被追溯到古希腊的智者学派,然而对人类“自然状态”的怀恋也要回溯到古希腊。古希腊的诸多思想是后世很多应该受到批判的思想的源头,同时也是针对这些思想批判寻找解决办法的思想宝库。席勒认为古希腊人的生存状态从未脱离自然,并且借着对诗歌的分析,提出了“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素朴的诗是未脱离自然状态的诗,代表着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并且他把素朴分为“惊异的素朴”和“信念的素朴”。“在惊异的素朴那儿我们总是尊敬自然,因为我们必须尊敬真实;然而在信念的素朴那儿我们尊敬个性”7,在席勒看来素朴是统合了自然与个人的最好方式,它就像孩童时代的游戏。成人应该返回到自然中去,在游戏冲动里获得人性中自然本性和道德本性的调和。
《强盗》是席勒早年的作品,也是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作,因此它常被解读为反抗封建压迫和欢呼自由解放。这种阶级分析的批评方法固然可以看出作品的社会学意义,但是却忽略了对人本身的精神批判的维度。哈贝马斯在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反思中将席勒视为现代哲学建立的纲领性人物,是连接康德和黑格尔的重要桥梁,并在德国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当今时代,席勒对文化批评的建构依然有独特的启示意义,他的在游戏冲动中塑造完整的人的观念,正是我们解决精神生态危机的一种尝试。
三、结语
作为生态批评的一个分支,以实现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区别对待,这是精神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同时,关注人的精神的完整性与协调性,祛除人的精神荒芜、碎片化与异化问题是精神生态批评的理论内涵。通过第一部分的理论准备,阐释了精神生态批评的必要性,并为在席勒的哲学思想和文本对应中找到一个突破口,那就是“完整的人”的概念的提出。《强盗》为我们塑造了这样的人,通过精神生态批评的视角,在精神生态的完整性方面,《强盗》提供了一个新的阐释空间。
注释:
1.王晓华.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3.
2.党圣元、刘瑞弘选编.生态批评与生态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4.
3.席勒,张玉能译.审美教育书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8.
4.同上,43-44页.
5.同上,14页.
6.罗尔斯顿,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48.
7.席勒,张玉能译.审美教育书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55.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曹卫东.从全能的神到完整的人——席勒的审美现代性批判[J].文学评论.2003(06)
王自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文学,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