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独立于政治之外还是深陷政治泥潭
李丹
美国最高法院向来是个神秘的地方,在这里,九位“老人”白发苍苍,身披黑色法袍,他们非民选,且“一朝为官,终身任职”。多年来,美国宪法学者和新闻记者都致力于揭开最高法院的神秘面纱,还司法神殿以平常,给大法官祛魅。前有美国政治学家戴维·M·奥布莱恩。早在其1986年出版,荣获“银槌奖”(Silver Gavel Award)的《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一书中,他就表述了最高法院是一个政治部门的观点。后有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以及杰弗里·图宾。在第一本揭秘最高法院“内幕”的著作《最高法院的兄弟们》一书中,新闻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毫不留情地披露了伯格法院中大法官之间的矛盾以及首席大法官伯格的领导无方。2007年,追随其前辈的脚步,《纽约客》专栏作家杰弗里·图宾再次以编年史来给最高法院作传,讲述1980年至2007年间最高法院的故事。《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一书大获好评,连登《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之榜。《九人》的成功,再加上他在《纽约客》杂志长期从事报道罗伯茨、布雷耶、托马斯和史蒂文斯等大法官,鼓舞了他再次为最高法院作传。
2012年,在影响深远的奥巴马“医保案”判决三个月后,杰弗里·图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版了《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以下简称《誓言》)。时隔不到一年,中文版便出版。有趣的是,该书一出版便引起中国法学界人士的关注,并在上海引起了一场“法律与政治”的研讨,图宾本人为此专门到上海宣传其著作。
与奥巴马总统和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一样,图宾也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高材生,并担任过《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这样的学术背景使得他能够更深入地报道最高法院。
图宾在《誓言》中想要表述的主题是,最高法院所践行的美国宪法正是美国政治。“在最高法院所发生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与在国会或白宫发生的没什么两样”。仅时隔五年,图宾在《誓言》中表达了与《九人》不一样的观点,对法官和政治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九人》中,图宾对法官和政治的看法还比较温和。他不赞成一些人认为大法官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象,也不赞成另一些人认为大法官是披着“黑袍的政客”。他认为政治的确在司法领域起着巨大作用,但并不总是如此,政治总是包裹着法律的外衣,必须以法律的言辞来表达。但是《誓言》一书中,图宾却抛弃了最初的看法,认为现在的法院践行着党派政治,尤其是2005年上任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他是一位“身穿法袍、代表变革的候选人”。
《誓言》讲述了2006至2012年这六年间发生在最高法院的故事,以奥巴马总统与罗伯茨为主角,阐明了最高法院里的意识形态斗争,回应了为什么近几年最高法院内5:4判决意见如此之多的现象,同时也展示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与奥巴马总统之间的斗争。
2005年,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终老于任上。次年,51岁的罗伯茨接替其职,成为自约翰·马歇尔以来最年轻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来自芝加哥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在联邦司法部任职,后重返律师界,被人誉为“律师中的律师”。他在最高法院出庭39次,赢得了25次。在罗伯茨的提名听证会上,时任国会民主党参议员的奥巴马,投下了一张反对票,这也是他们暗地斗争的第一个回合。2008年,奥巴马获选为总统,在接下来的就职宣誓中,奥巴马与罗伯茨第一次正面交锋,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总统进行两次宣誓的场景。《誓言》一书便以宣誓为开始,讲述了奥巴马与罗伯茨的分歧。罗伯茨任职时,受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们的喜爱,奥康纳大法官忍不住对他的喜爱,盛赞其“除了不是位女性,其他样样都很出色”。史蒂文斯大法官赞扬其 “条理清晰,擅长说理,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出色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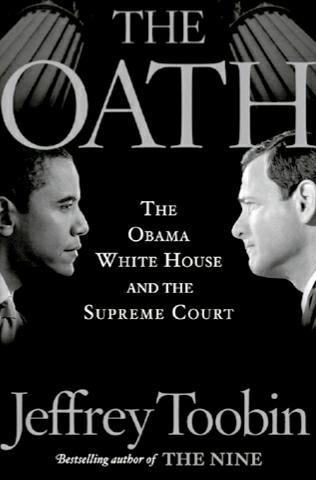
接下来,图宾定下了本书的基调,那就是罗伯茨与奥巴马:“一个相信改变,另一个信仰稳定性;一个向前看,另一个向后看;一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梦想家,另一个在谈到法律时则是保守主义者。”让人感到吃惊的是,相信改变的激进主义者是罗伯茨,保守主义者则是奥巴马总统。于是,人们会忍不住發问,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怎么会是保守主义者呢?图宾认为:“罗伯茨决心运用自己首席大法官的职位来倡导变革……奥巴马则决心捍卫有关宪法含义的旧有观点。”在奥巴马看来,“法院在保护基本权利方面是(或者应该是)静止的,他并不打算督促法官和大法官们去创设新的基本权利。”事实上,图宾说奥巴马相信法院在保护基本权利方面是静止的,似乎有点不太准确。众所周知,从其参加总统竞选时,奥巴马就表示相信同性恋权利和支持同性恋婚姻,任职总统后,他也一直在这样做。在涉及军队同性恋问题时,时任联邦司法部长的埃琳娜·卡根坚持认为第九巡回法院做出的判决,即支持同性恋者——空军少校维特的权利是不合宪的,奥巴马则承认了第九巡回法院判决,不再上诉。
同时,图宾也指出,在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信奉宪法能动主义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推翻法律,现在则是共和党在这样做。”这一观点也不太恰当。近年来,民主党也促使法院推翻了很多法律,从捍卫传统婚姻的联邦法律、到禁止局部分娩堕胎和展示“十诫”的一些州法律。所以很难说民主党就是司法克制主义者,至少目前来看,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履行司法克制,他们都希望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
在界定了罗伯茨与奥巴马不同的宪法观之后,接下来,通过“联合公民案”、“医保案”等一系列里程碑案例的细致剖析,图宾再次凸显了他要表达的主题,即最高法院的政治性,当然主要是罗伯茨的司法能动性。图宾认为,“联合公民案”界定了罗伯茨法院的公众形象,如同“布什诉戈尔案”是伦奎斯特法院的标志,两案都深陷党派政治的泥沼。
2009年的“联合公民案”涉及1989年通过的《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该法禁止企业和工会在初选前30日,或普选前60日发布任何涉及候选人的广告。早在2003年,伦奎斯特法院做出判决,支持了该法的大多数内容,而肯尼迪、斯卡利亚和托马斯三位大法官则持反对意见。2006年,有关该法的“联合公民案”再次上诉到最高法院。同年6月的投票中,“摇摆大法官”肯尼迪加入了罗伯茨、斯卡利亚、托马斯、阿利托一方,反对《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按照最高法院的惯例,首席大法官在多数一方时,由他指派大法官撰写法院意见书。最初,罗伯茨把这一案例分配给自己。在多数意见书的初稿中,一开始他并未明确地表示要推翻《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只是就事论事,认为该法不适用于联合公民组织,这也是自由派大法官们所希望的。然而,不久肯尼迪发表了一份协同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该再前进一步,宣布《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无效。于是,罗伯茨撤回了自己的意见,让肯尼迪撰写多数意见。这一举动惹怒了苏特,他在异议中外扬了最高法院的家丑,认为罗伯茨此举违背了最高法院的程序,是为了拉拢肯尼迪而达到自己希望的结果,又不至于承担责任。为了挽救最高法院的公信力,罗伯茨撤回了“联合公民案”,宣布9月份再辩论,这在最高法院的程序中是非常罕见的。

同年9月,苏特大法官宣布退休,奥巴马总统得到了第一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这也是15年来民主党总统的唯一一次机会。很快,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拉美裔女大法官索托马约尔走马上任。同时,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再辩论。肯尼迪的意见得到了斯卡利亚、托马斯和阿利托的支持,罗伯茨转而指派肯尼迪撰写多数意见书,最终肯尼迪的协同意见变成了法院意见书,最高法院宣布《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无效。图宾声称:“‘联合公民案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次斗争。首席大法官选择修改资助竞选的法律时,真正的问题等于,他希望多大程度上帮助共和党。罗伯茨的选择是:帮它个大忙。”
事实上,罗伯茨也是迫于多数的压力,而不是遵从自己的意愿,将意见分配给肯尼迪。如果是他本人写的最初意见,可能得不到多数的5票。相比起自身的党派意见,罗伯茨觉得法院的权威更为重要。当然,在自由派看来,这无疑有拉拢肯尼迪之嫌。将这个任务交给肯尼迪,罗伯茨不但可以回避这些攻击,还依然可以得到想要的结果。“联合公民案”后,九十多岁的史蒂文斯大法官决定离开这个让他感到陌生的地方。然而,失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早在2005年离职时,奥康纳大法官就讲到,“我所属的政党正在损害这个国家。”奥康纳退休后,保守的阿利托取代了她,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大法官第一次在最高法院获得了稳定的5票。
大法官深陷政治泥沼,不仅是在涉及竞选基金的“联合公民案”中,在2012年的“医保案”中也是如此。然而,在“医保案”中,罗伯茨却急流勇退,选择支持奥巴马任期内的最重要法律——《患者保护及可负担医疗法案》(简称《医保法》),与图宾一开始所设定的形象大不相同,不是司法能动主义者,而是做到了司法克制,维护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2010年,国会投票通过了奥巴马任期内中最重要的法律——《医保法》,对该法争议最大的一点是其中强制公民购买医疗保险的部分(个人强制令条款)。民主党人尚未能举杯欢庆,共和党人就在地方法院就该法的合宪性提出了质疑。2011年11月,最高法院受审“佛罗里达诉联邦卫生和公众服务部案”(简称 “医保案”),来审查《医保法》。在该案最初的言词辩论中,罗伯茨认为个人强制令超越了国会商事条款下的权力范围,这一点与斯卡利亚、托马斯、阿利托的看法一致。然而在最终的投票中,罗伯茨却转而支持整个《医保法》包括个人强制条款的合宪性。

罗伯茨在“医保案”的做法受到了已退休的奥康纳大法官的支持和赞扬。但是,其临阵倒戈却让共和党人痛心疾首,使得他们失去了挫败奥巴马的一个重要机会。那么罗伯茨为什么出现这一转变呢?图宾指出,在“医保案”中,罗伯茨临阵倒戈,转而支持奥巴马的医改法,不过是为了挽救法院的荣誉,免于置最高法院于2012年大选的中心。但是,这并不代表罗伯茨开始转向支持民主党,“即使是在医保案之后,罗伯茨依然是实行共和党议程方面强有力的倡导者。他依然是一个身穿法袍的代表变革的候选人。”在这里,图宾对罗伯茨的指责如保守的媒体人马克·李文一样,大法官是“披着黑袍的激進分子”。
图宾在书中毫不掩饰对奥巴马的喜爱和对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的攻击。在笔者看来,图宾过分夸大了奥巴马与罗伯茨宪法观的分歧。在他的笔下,罗伯茨成了抵制变革,崇尚司法能动的代表,这或许跟图宾本人的自由主义倾向有关系。事实上,奥巴马和罗伯茨在宪法观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致力于摆脱党派的界限,缓和两党的分歧,尽管最终都没能取得成功。罗伯茨也并非图宾书中描述的那样,是位宪法激进主义者。在初任首席大法官时,罗伯茨曾劝说他的同事,不要从自身党派倾向来判决案件,要避免出现过多5:4的案例判决。显然,在上任第一年,罗伯茨取得了一些成效,大法官们在45%的案件中做出了一致的判决。第二年,该比例就下降到25%,显然罗伯茨的努力失败了。
罗伯茨一直将最伟大的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视为偶像,希望尽可能维护最高法院的内部团结及权威。同时,他也熟悉这一点:约翰·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做出了超越党派的判决,间接地支持了他不喜欢的杰斐逊总统,维护了最高法院的独立和权威。考虑到这些,我们再思考罗伯茨在“医保案”中的转变,就不足以感到奇怪了。
毫无疑问,大法官的政治立场在司法裁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今天深陷党派政治泥潭的美国。但是,宪法先例的限制,公众舆论的反应,司法裁决的可行性,这些现实的制约有时比政治立场更能制约大法官的裁决,罗伯茨在“医保案”中的转变就受多种因素影响,而非仅仅出于他自身的政治立场。
———“人民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