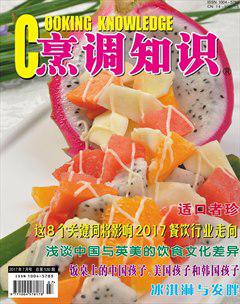适口者珍
刘翠红
汪曾祺在《宋朝人的吃喝》一文中,列举了众多事例来阐述宋人的吃喝,最终的结论是:宋朝人不很讲究大吃大喝。确然如此。尽管《水浒传》中屡屡提到“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事,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江湖侠气,不具有普遍意义。对于大部分民众乃至于官员来说,宋人的吃,似乎并不重在食物的肥美,而在于吃出一种“情味”。
有一次,宋太宗问苏易简:“食品称珍,何物为最?”苏易简答曰:“臣闻,物无定味,适口者珍,臣只知齑汁为美。”继之,苏易简就为宋太宗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经历。一天晚上,天气寒冷,苏易简围炉饮酒,大醉。四鼓醒来后,复拥衾而坐,但觉口干舌燥。“时中庭月明,残雪中覆一齑盎,不暇呼童,披衣掬雪以盥手,亟引数缶,连沃浊肺,咀齑数茎,灿若金脆。臣此时自谓上界仙厨鸾脯凤腊,殆恐不及也。”“齑汁”,何物也?不过是用葱、姜等碎末做成的汤汁,但苏易简却说胜过“上界仙厨鸾脯凤腊”,何也?只因彼时,有一种特定的情境,于是,就吃出了特有的情味。
不同的食物,味道自然不同;同一种食物,在不同的情境下吃到,感受也不一样。只要适合了自己的口味,那就可以视为“珍”。
故尔,“物无定味,适口者珍”!
抗战期间,梁实秋避居内地七八年。胜利返乡后,回到北京,他第一想吃的竟然是北京的“烤羊头”。他说:“一个冬夜,听得深巷卖羊头肉小贩的唱喝声,立即从被窝里爬出来,把小贩唤进门洞,我坐在懒凳上看着他于暗淡的油灯照明之下,抽出一把雪亮的薄刀,横着刀刃片羊脸子,片得飞薄,然后取出一只蒙着纱布的羊角,撒上一些椒盐。我托着一盘羊头肉,重复钻进被窝,在枕上一片一片地把羊头肉放进嘴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十分满足地解了馋瘾。”
一盘羊头肉,吃得如此香美,其“味美之意”恐怕就不在肉了,而在于这份羊头肉慰藉了梁实秋的乡思乡情。此时的这盘羊头肉,可谓其“珍”无比。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日三餐,不可能顿顿大鱼大肉,就是清朝达官贵人们的“满汉全席”,吃的,到底还是一份讲究,一份奢侈的炫耀。寻常百姓,大多素衣简食,于简单中,吃出味道,吃出情味,即可为“珍”。
丰子恺在《吃酒》一文中,记述了一位在西湖湖畔吃酒的“中年人”。“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边,向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饭米,挂下去钓。钓得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于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那么,这个人又是如何吃酒的呢?“他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蝦,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
这真是一个无比风雅的人,他不贪,他更懂得为自己营造一份吃酒的氛围,在特定的氛围下,三四只虾,就是无上美味了。
我的一位乡下亲戚特别喜欢饮酒,一日三餐,每餐必饮。但饮酒酒肴,只有一品:花生。油炸花生、盐浸花生、生花生,均可。而且,他还尤其喜欢带壳的花生,常常是,剥一颗花生,饮一口小酒,剥花生时,两眼望着前方,仿佛在望那不尽的田园风情,神情悠然,情态安详。
他要的就是此种情味,情味存焉,花生,即是“珍”味。
“适口者珍”,真乃解得食味者言。自己喜欢的,就好。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