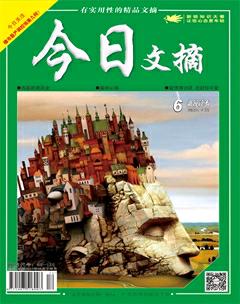王八的甲壳
程应峰
在很多人眼里,忍耐是一种崇高的德行。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可见忍耐是有目的性的。
在一个大家庭中,亲人间的谦让容忍是最为显见的。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因事登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睦之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之流涕,赐缣帛而去。
于是便有了“百忍成金”这样的成语。人不是独立的个体,只要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就会明了忍耐为什么是一种崇高的德行。
人的忍耐力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取决于一个人后天处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一位英国母亲临终时对儿子说:“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但就我国而言,儿女出门,长辈总是千叮万嘱地告诫:“少管闲事,切莫往人多的地方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叮嘱?因为在这些长辈看来,只有模棱两可、冷淡消极的态度最为稳妥安全。两种嘱托,两样人生,不言而明。
林语堂说:“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于是,相当一部分人在忍耐后的冷淡中变得圆熟,变得看似聪明乖巧,有很强的适应性了。
忍耐后的冷淡成为个人“适生”的甲壳,魏晋时期的人文状况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那个时期,智识阶层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消沉,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抱膝清谈,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追求不死之藥。有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佯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竹林七贤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群体,诗人之一刘伶,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荒淫,或则极端超俗。另一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至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大抵就是这样的人。大众以他们为偶像,犹如小王八以大王八之厚甲壳为崇拜对象。
一个人,经历了许多人生况味,最有可能变得实际、冷淡。一如寒山曾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云:“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这正如“三十六计,走为上”“乖人不吃眼前亏”“退一步着想”“负一子而胜全局”的态度。这种态度,说明执着追求的精神消磨殆尽,剩下的,自然是所谓的圆熟。用林语堂的话说,是“老猾俏皮”。正是这种圆熟,阻遏了思想和行动的活跃性。
这忍耐后的冷淡,冷淡后的圆熟,这王八的甲壳,时深日久,让人失去的,是思维的敏锐性与行动的推进力。■
(江意荐自《思维与智慧》)
责编:我不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