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种方式
[英]罗伯特·麦克法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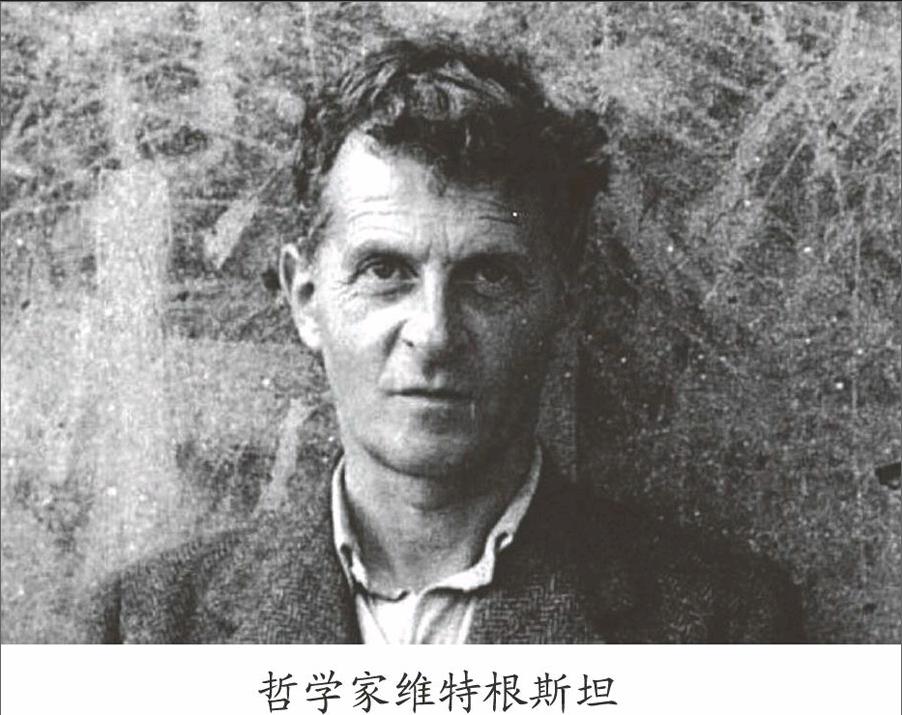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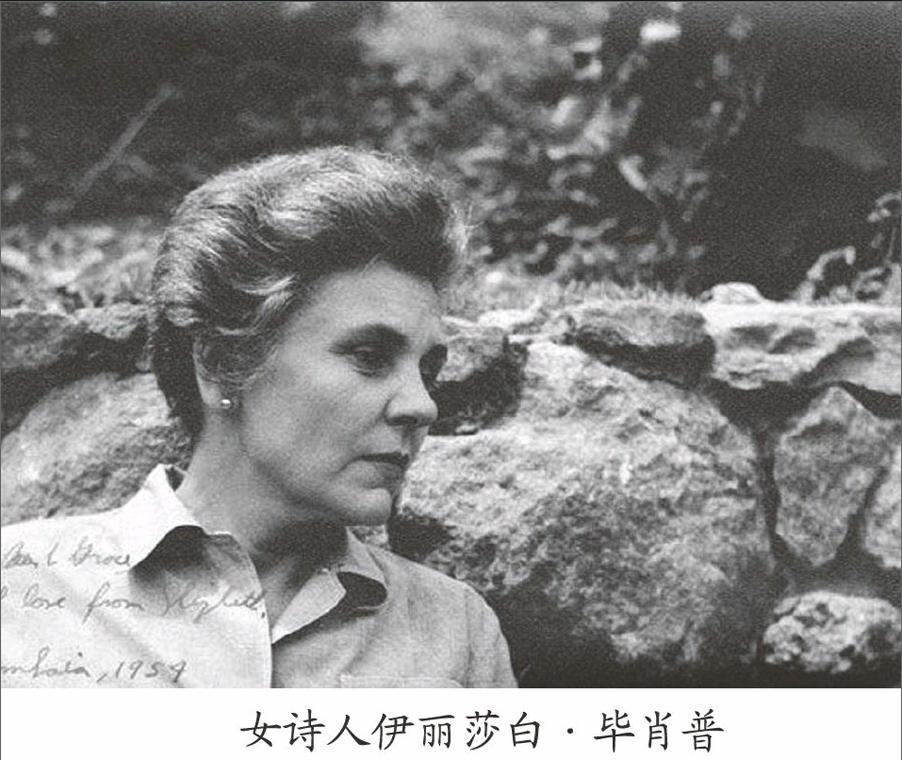
从我的脚跟到脚尖是二十九点七厘米,折合十一点七英寸。这是我步伐的单位,也是我思想的单位。“我只能边走边思考”,让一雅克-卢梭在《忏悔录》第四卷中写道,“当我停下时,我的思想也停了下来。我的大脑只和我的腿脚一起工作。”索伦·克尔凯郭尔推断,心灵应该按照每小时三英里的步速运行才发挥最佳效能,他在一则日记中记录了自己一次漫游,并发现自己“被各种想法吞没了”,以至于他“几乎迈不动脚步”。克里斯托弗-莫利在论及华兹华斯时说,他“将自己的双脚当作哲思的工具”,而华兹华斯谈及自己时则谓之自己的“感官领悟力”。在这个问题上,尼采是一贯的绝对——“只有那些来自徒步行走的思想才算有价值”——而华莱士-斯蒂文斯的观点一贯是试探性的:“或许/真相依赖于一次环湖漫步。”在所有这些描述中,步行不是一种你可以通过它抵达知识的行动:它是我们认知的手段。
提出认识既是行动敏感型的,也是地点特定型的,在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出现,但是真正令它广为人知的还是卢梭。这在今天是众所周知的提法,但要把它定位一项规则,我们表示怀疑是合理的。有时,步行是心灵亲密的伙伴,有时却是残忍的敌人。如果你曾经日复一日地长距离步行,你就会知道,途中的极度疲惫会消灭除了最基本的功能外的大脑所有功能。走上二十英里,你就会头晕目眩,傻呆呆地看着约翰-希拉比所称的“脑在非西方文化中,足跡作为知识,步行作为思维方式的想法广为人知,特别是作为回忆的一种隐喻——历史是人返身走人的一个地区。基思·巴索写过,西贝丘阿帕奇印第安人是如何将过去比喻成一条小径或一行脚印,祖先们踏过,但是对于生者却大部分都不可见,必须要通过激活某些记忆中的道路间接地重温。这些道路——包括地名、故事、歌曲以及遗存——有时被阿帕奇人称为——“脚印”“行踪”。对加拿大西北部的科林;中人来说,步行与知识是几乎无法分别的:他们用于指称“知识”和“脚印”的名词可以互换使用。一部大约六百年前的西藏佛经用shul表示“一种当初留下印迹的东西已经消失后所残存的印迹”:脚印是shul,小径是shul,这些印迹引得人回头,通晓过去的事情。
乍一眼看上去,“步行就是思想”或者“脚可以知道”这些想法很陌生,令人困惑。我们并不将脚想象成一种表情达意或感官的附属器官。脚缺少手那样多才多艺的本领。大脚趾转动不灵:它抓握方面的最大的本事,不过是和二脚趾一起做出剪刀一样的笨拙动作。脚感觉上更像是假肢,带着我们四处走,但不能为我们阐释或组织世界。手肯定比脚更灵巧——我们说掌控,但从不说脚控。然而理查德·朗——他曾经每天步行三十三英里,连续走了三十三天,从康沃尔的利泽德走到苏格兰北部的达尼特角——写信时爱用一个红图章,上面是一双脚的轮廓,脚底板上有双眼睛,盯着你看。脚步是看待大地的一种方式;触觉相当于视觉——这就是我的所持的观点。
对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而言,用脚和用脑子进行探寻在他的哲学里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期间,他会在罗素的房间里大踏步地来回,躁动不安、缄默不语,有时能走上好几个钟头,在不过几码大小的房间里走上数英里。有一次,罗素半开玩笑地问这个在房间里踱着大步的学生:“你是在思考逻辑问题还是你身上的罪恶?”“两个都是!”维特根斯坦不假思索地答道。1913年,维特根斯坦回到挪威一个偏远峡湾里的小村庄肖伦,在那里度过一个漆黑、漫长的冬季,一边探索逻辑问题,一边沿着村庄或通往山间的小径散步。那土地贫瘠而坚定,与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非常般配,也就在那个冬季,他解决了关于象征主义探索真理作用的关键哲学问题。“我想象不出,我在别的地方也能像在这里一样专心工作,”他在后来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在我看来,我已经产下了自己体内的新思想。”维特根斯坦用来表示思想的词Denkbewgungen是生造的,大体可以译作“思想行动”“思想路径”或“思想之路”:思想,经由沿着一条路而来人间。
在托马斯·克拉克一首默默无闻的诗作中,一位行人沿着一段海滨来到一个地方,这里的石级“在岩石上雕刻而成/一直伸人水中”,旁边是一片沼泽。诗歌接受了石级的邀请,那位行人想象着“下到海里/进入另一种知识/荒凉而寒冷”。这里影射的是伊丽莎白·毕肖普的伟大诗作《在鱼庄》。鱼庄的房子慢慢探人纽芬兰的某个港口那“灰暗、清澈、冰冷的水中”:那水“像我们想象中知识的模样:/黑暗、咸涩、清澈、流动,完全自由自在”。而我想,毕肖普也是在模仿,模仿的是华兹华斯1815年那句人如何能接近“理性的深渊”:一个深奥的国度“心灵不可能自然而然地下沉到那儿——而是必须踩着思想的阶梯一步步下到那里”。这三首诗彼此互为应和——是它们自己的一行脚印或一连串阶梯。脚步、知识和记忆三者问最广为人知的联系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歌行观。根据这种宇宙发生学观点,世界是在一个叫梦幻时间纪里创造出来的。那时,先祖们发现地球是个黑暗、平坦、毫无生机的地方。他们开始走出这个非地。他们一边走,一边开挖地球表面的硬壳,释放地下沉睡的生命,于是大地随着他们的步子开始焕发生机。布鲁斯·查特文在他有瑕疵但影响很广的描述中解释道:“每个如图腾般的祖先,在走过大地时,都认为沿自己的脚步撒下一串文字与音符。”依据它们落脚的地方,这些步调就与特定大地的特征联系起来。因而,世界就被“梦幻小路”覆盖了,它们“覆盖在大地上,成为交流的‘途径”,每条小路有相应的歌。澳洲大陆,照查特温的说法,因此可以被视为“集合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如意大利通心面般扭动,每个‘篇章都是可以用地质学术语读懂的”。因此,唱出歌谣——到今天依然是让它们勉强留存下来的方式,虽然每一代歌谣都在遗失——于是唱出歌谣也就是找到自己的路,讲故事和步行是不可分割的。思想与步行的关系在语言史中浸染很深,也许演示了就我所知的最宏大的词源学。这条轨迹从动词to learn(学习)开始,意为“获取知识”。从语言史角度上溯,我们发现了古英语中的leornian,意为“获得知识,教化”。从leornian开始,这条路径进一步向过去延伸,进入原始日耳曼语满是摩擦音的盘根错节中,指向liznojan,该词有个基本义项是“跟随或找到一个痕迹”。因此,“学习”究其根本而言——究其发展路线而言——意思是“沿着一条路径”。谁想得到呢?反正我之前不知道。要感谢那些词源探究者,是他们揭示了那些消失了的路径,将“学习”与“沿路径而行”之意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