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是一场意外事件
思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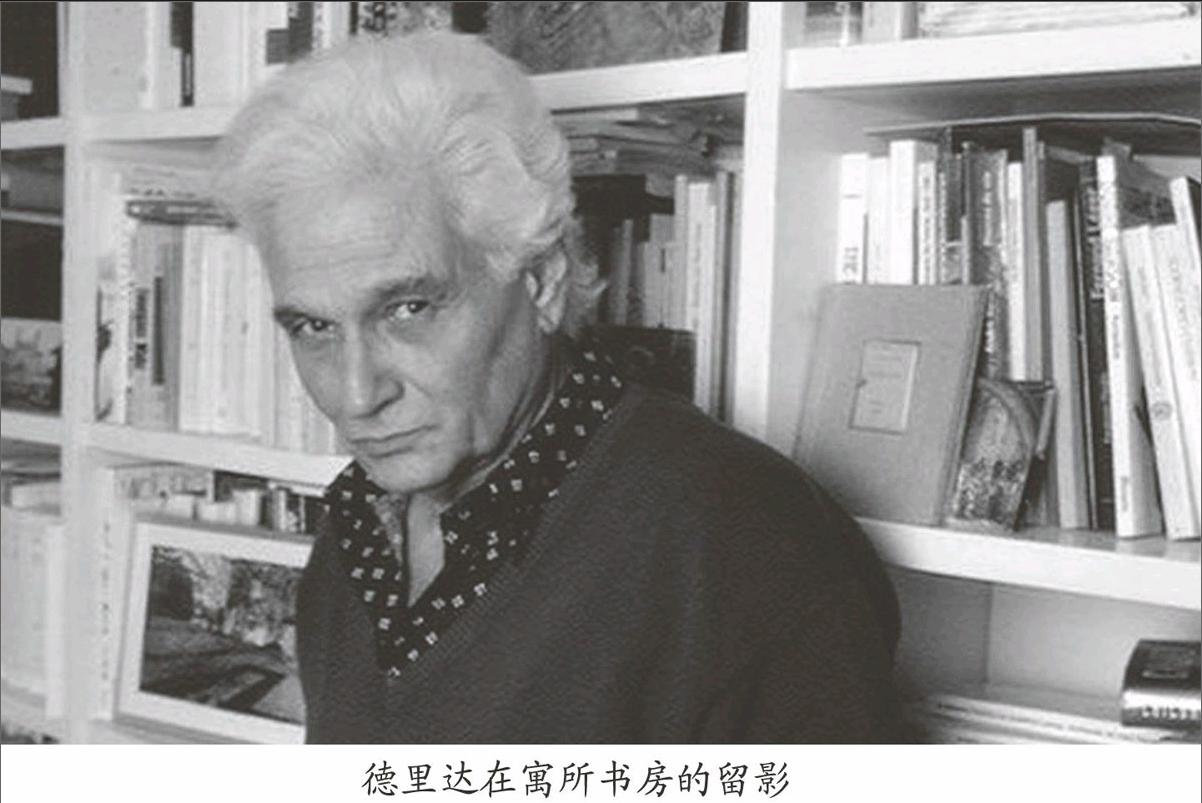
1
1831年,刚从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的达尔文,在老师的推荐下,登上了英国海军“小猎犬号”,开始他环游世界的科学考察。那一年,他22岁。
这次“小猎犬号”的航程一直持续到达尔文27岁,带着他从普利茅斯到了蒙德维得亚,穿过了麦哲伦海峡,北上加拉帕格斯群岛,横跨南太平洋到达塔希提岛,前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跨过印度洋到达毛里求斯,绕过好望角,又一次回到南美洲。在后人们的普遍想象中,这次科学考察的旅程通常被视为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发现之旅,他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奇怪的动物,包括巨大的陆龟、海生的蜥蜴、在自己的声囊中养育小蝌蚪的蛙类等等。在智利进行探索时,有次正在远足之中的达尔文停下来休息,突然脚下的地面开始晃动,就像柔软的果冻一样,“那一秒钟时间带给你的心灵上的强烈不安感,是几个小时的思考也无法重现的。”他如此写道。地震几天后,他发现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没有剩下任何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屋,一点也不夸张。”这场景是他目睹过的“最可怕却又令人感兴趣的宏大景象”。
这次长达6年的航行,彻底改变了一个神学院学生的生活。他父亲本来希望他从剑桥大学毕业后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但在航行中看到过世界众多变化的达尔文再也无法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上帝在一周之内创造出来的。在他看来,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故事根本就是神话——在那个神学还主宰我们思维和心灵的时代,能够从一次航行中得出这个结论,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冒险,更何况,他还将这次航行的经验上升到了生物进化的高度。從历史意义上看,说达尔文的航行改变了我们的现代生活也并不过为。当然,从现代意义上看,达尔文的这次航行可能是一次巨大的浪费。试想一下,我们很少花费六年的时间去进行一次未知的探险,因为我们不知道航行的下一站到哪里,发现什么。对达尔文而言,未知的神秘和恐惧一直都主宰着他的心灵,就如同他第一次见识到地震的破坏性的威力之后说的那句话:这种亲身体验到大自然威力的恐惧感,是几个小时的思考也无法重现的。现代人在开始旅行之前,已经制定了足够安全和稳妥的计划,我们知道要去哪里,去欣赏什么,享受什么样的美食和美景,甚至早已想好了遇到什么样的人。这样旅行的意义在于享受计划之中的乐趣,计划之外的未知完全排除——这是一种不用浪费任何思考就可以执行的旅行计划,仿佛暗示着,外面巨大的空间也尽在我们掌握之中,我们是世界的主人。
2
达尔文的旅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时间长,他对外面的那个陌生世界几乎一无所知。我一直在想,在那个漫长的旅途当中,他一定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用在沉思上。帕斯卡尔有句名言说,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不想安心待在房间里。其实换个说法,我们也可以说,现代人最大的不幸就是不想、不会或者没有时间去沉淀自己的思考。沉思产生的智慧,已经让位于不断地旅行产生一种肤浅、刺激、满足的意识。
现如今,我们几乎想去哪里都可以,我们可以像鸟一样飞翔,穿越大海,去访问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我们足不出户,借用媒体和网络,我们也能把千里之外的信息带到我们身边。这也是现代与前现代生活之间最大的区别: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到达任何地方,即时信息已经成为了现实。在美国哲学家卡普托的《真理》一书中,他说现代这种高速的没有终点的旅行给我们的真理带来了一场危机。因为拥有这种现代的交通体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还有现代信息系统,通过它任何东西都到我们眼前,现代生活比过去更加多元,我们会更多地受到他人的影响,他人也会更多受到我们的影响。这样的生活带来了一种观念的变化:文化不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更多选择,更加五彩缤纷。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越来越说不清目的是什么,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我们都疯狂地四处奔忙,但是我们说不清我们要去何方。每个人都很忙,没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就像那个的笑话,当船长对乘客们说,好消息是我们正在飞速前进,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
3
现代科技和交通工具的便利,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去旅行,而不用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都听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康德,他一生从未去过离出生地四十英里之外的地方,打了一辈子光棍。他成年后的生活只是日复一日地讲学、研究学术、写作。他的生活如此严格,如此规律,以至于他的邻居都根据他出门散步的时间来调整时钟。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从未旅行过的哲学家,却也认为旅行是了解我们人类的最佳途径。因为真正的旅行可以让我们深入接触另一种文化,强化我们对共性与差异的认识。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提醒,提醒我们,外面有个不一样的世界。
要知道,我们的世界观受限于我们的视野和心灵的开阔程度。为什么年轻人总是梦想着离开家乡,闯荡世界。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家乡的小镇上,心灵只会日渐萎缩,我们的生活没有选择,只要很少的可能性,未来几乎一眼都能望到头。但是外面的世界,意味着无数可能性和无数的未来,用一句俗烂的话说,这个时候,你的心有多大,未来就有多宽广。
加缪写过一则关于旅行的札记,他说,旅行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恐惧。就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因为和自己的家乡、语言距离得那么遥远,我们会被一种模糊的恐惧攫住,会本能性地渴望能够再度受到积习的庇护。这就是旅行最明显的收获。他说旅行并不能带来任何乐趣。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不如说是一种苦修。一个人之所以会踏上旅途,是为了自我养成,如果所谓的养成即是去锻炼我们那最内在的、对永恒的感受。乐趣会让我们迷失自我,就像帕斯卡尔认为消遣唯有令人和上帝更加疏远。旅行,好比一门最庞大也是最沉重的学问,让我们得以踏上归途。
其实这是最朴素的认知。试着想一下,如果你人生大半辈子从未离开过你生活的乡村或者小镇,突然有一天有笔意外之财,让你有机会走出家乡,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当你踏上旅途的一刹那,心中升起的一定是一种忐忑不安的恐惧感,这种恐惧让我们警醒和退缩,惊讶和沉默。我们从熟悉的地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会有格格不入的感觉。如果我们像加缪所说的,如果旅行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踏上归途,那么旅行就丧失了真正的意义。
当代哲学家中,热爱旅行的人并不少,但很少有哲学家能把旅行变成沉思哲学的方式,除了德里达。哲学史上从未有哪个哲学家像德里达那样旅行过。他是一个哲学的旅客,在全球奔跑,他的大多数著作都写在路上,酒店里和飞机上。在他不停地周游世界时,德里达总是喜欢在抵达一个陌生的城市时,独自漫游,让他自己迷失在附近街区的迷宫中,最后找到回酒店的路,中间不打探方向。这是他自己的一种“事件”理论。“事件”是德里达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那种“正在到来”的某物,或者“将要到来”的某物。作为一种未来的东西,事件“是某种我们看不到它的到来、让我们感到意外地侵袭我们的东西,就像一封意外地抵达邮箱的信,带来了一个改变了你一生的消息,不管是好还是坏的改变。事件会造成两种影响:要么带来巨大的欢庆,要么带来巨大的惊恐”。就是在这里,“事件”的这种不可预料性与我们人生的旅行联系在了一起,人生是一次旅行,它的终点被彻底遮盖了,在这场冒险中我们看不到会发生什么。而对德里达来说,他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漫游,就是对一场“事件”保持一种开放性的心态,无论是危险还是希望,他都拥抱这种结果的到来。因为对德里达来说,一个事物的真正真理,就在于它能给我们带来意外。
如果旅行的意义在于加缪所说的恐惧,我也要说,正是这种恐惧让旅行变得有价值。你每天都会在新的地方对世界有新的发现,你会感到孩子般的好奇心,你会发现很多故事,感受到陌生人的温情或者恶意。这些都是你人生独一无二的经验和收获。每个人都会有与世界独特相处的方式:你可以选择待在房间里阅读,你也可以选择走出房间,买上一张机票,选择一个陌生之地,迎接一个意外事件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