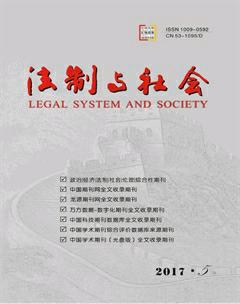李斯在法家人性观下的实践
季善威 刘雨婷
摘 要 人性观一直是政治法律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之一,在法家思想家看来,所有人都受利益驱动,趋利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这是法家人性观的主体部分。本文意在通过分析李斯的政治实践,理顺其中蕴含的理论基础,深化人们对中国古代法制思想的认知。
关键词 李斯 法家 人性观 书谏逐客 定制颁法
作者简介:季善威,长沙学院外国语学院;刘雨婷,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5.287
一、人性观是什么
关于人性,如今人们日常实际上大致有以下两种基本用法。一种是传统哲学的用法,强调的是概念上人同其他事物或物种的根本区别 (“本质”或英文的 “essense”),因此隐含了较强的规范意义。我们批评他人“禽兽不如”,就是这种用法。另一种更多是伴随着社会科学发展起来的,是对人生来就有、稳定不变的自然特性或潜质的经验描述或概括,英文的说法是 nature,一般不带有道德意味。儒家的荀子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主张人性自然生成,就是这个意思。而本文所说的人性观是第二种基本用法中的人性观。
二、法家人性观概述
(一)法家人性观是主张“性恶论”的吗
战国晚期儒家集大成者荀子主张“性恶论”。而理所当然的,李斯和他的同门师兄弟韩非的思想必然深受其師影响。但是我们也并不能因此就说,李斯和韩非的人性论就是等同于荀子的“性恶论”的。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是儒家学派中少有的持人性恶的人,明确主张性恶的人性观。“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指出,人自出生开始就有喜欢,财利之心,若纵容它不管,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违法乱纪等社会败徳现象。荀子又针对人的性恶的情况阐明了如何引人向善的见解,“故必将有师法之道,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他认为生活当中的礼仪教化是不符合人性的,但通过后天的教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性恶”的本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向善。我们之所以将荀子归为儒家代表,也是由于他强调了人会受到礼仪的教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荀子的“性恶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孔孟儒家的“隆礼重法”的社会管理思想,讲究理治法治共举。
但无论是管子、商鞅、慎到等这些荀子之前的法家代表人物,还是法家理论集大成者韩非或是深受荀子影响的当时法家理论最完全的实践者李斯,都没有单纯对人性从道德上做出善恶的评价。“他们只谈人性,不讲善恶,只讲人的基本生理、心理需要,不论后天的伦理、道德教化及其评价”。可以这样说,在法家看来,人们其实不能也不具有对自然人性进行善恶道德评价的资格,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皆共有的自然而然的现象,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给其冠之以善或者恶而加以扭曲。由此可见,他们并没有对于人性有“善”或者“恶”的道德层面的评价。
(二)法家“趋利避害”的人性观
法家的人性观是一直围绕着"好利"来进行的,法家思想家秉持这样一种观点——人生来就有"好利"的本性,趋利避害,这是人的本能。人喜欢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法家思想家看出了人性"好利"的本性。
韩非在《六反》中指出:“人主挟大利以听治,故其任官者当能,其赏罚无私。使士民明焉:尽力致死,则功伐可立而爵禄可致,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矣。”当君主认识到了人的这种“好利”本性之后,就可以去利用它,因为人都是追求“利”|的。《商君书·去强》当中的“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在一定程度上阐明了当时治理国家的艺术。
法家主张按照法令做事,依法治国,同时利用人对“利”的追求,设立嘉奖,制定刑罚,结合现实,推行法治。早在管子的时候,法家就已经开始承认人的“自利”性并强调要礼法并重来对这种人的天性加以规制;战国时候的商鞅,深知人“违害就利”之本性,以恩威并施、赏罚分明的方法谋求秦国的强兵富国;随后,慎到“揭露了道德教化的虚伪性,将赏罚二柄作为驾驭臣子与民众的利器”;最终,韩非则完全地将人当成了一种具有“自利”功能工具。“奉法为教,以吏为师”,法家以法律作为衡量利益以及社关系的准则,无不体现着法家对于人性的认知。
三、李斯在法家人性观下的实践
(一)书谏逐客,妒杀韩非
韩国担心日渐强大的秦国会对本国造成巨大威胁,想方设法牵制秦的东进。因为修筑沟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韩国便遣水工郑国到秦鼓动秦王去修建水渠。但不久,郑国的意图被暴露了。这时,其余各诸侯国也效仿韩国,派人来到秦国做宾客。秦国的大臣对于外来的这些宾客议论纷纷,对秦王说:“这些人到秦国来根本就不是为了秦国而是别有居心的,请大王把宾客们遣散吧。”因此,秦王下达逐客令,驱逐从各国来的客卿,李斯不是秦国人,也被列入其内。李斯向秦王进献了一封劝诫其不要逐客的信——即历史上著名的《谏逐客书》。
任谁都不能说,李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写这篇《谏逐客书》的,而我们在《谏逐客书》中看不到一点李斯为自己辩解的痕迹,相反,李斯反对逐客的理由都很高大上,很有“大局观”。他从历史的高度,列举了穆公、孝公、惠王、昭王重用客卿之功,认为假如这四位国君对客卿闭门不纳,疏远外来之士而不用的话,就不会使秦国富强,秦也不会有强大的威名。同时,李斯还认为秦王本身并不拒绝来自别国的色乐珠玉,却单单在用人方面“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而这绝非“跨海内、制诸侯”之术。这种“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问,裹足不入秦”的做法,只会增加敌国的实力,最终使秦国陷于危境。此时的秦王还不是刚愎自用、乾纲独断的帝王,还能闻过则喜、从谏如流,他采纳了李斯的谏议,收回了驱逐客卿的成命,恢复李斯官职,不仅没有诛杀水工郑国,反而让他继续主持修建关中水利,使千里沃野遂成良田,成就了“秦万世之功”。嗣后,秦王嬴政任用大批“客卿”,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为灭六国、开帝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李斯这篇言辞恳切、有理有据的《谏逐客书》,使秦王放弃了那个为了预防少数间谍渗透就彻底闭关锁国的政策,而正是这种开放和包容,成就了秦国的强大,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另一种走向。就李斯写的这篇《谏逐客书》来说,其文采如何自然不用多说,鲁迅先生说了“秦之文章 ,李斯一人而已”。只是光靠文采自然不可能打动秦王,归根结底还是法家岁推崇的一个“利”字。李斯看准了秦王想要一统天下的心,那么所有的出发点,都站在了为了帮助秦王一统天下的立场上,李斯陈述厉害,自然顺利地打动了秦王,也使得自己在仕途上又迈进了一步。这种对秦王进行“利诱”的艺术,是李斯对于法家人性观完美运用的体现。
(二)定制颁法
法家的不懈努力均是为追求“以法治国”。他们从人性论入手,通过对人性的认识和分析,提出了“因人情”而“治天下”的法治思想。就李斯而言,他所倡导的政治体制同别的法家代表人物一样,是“法治”。他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属,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秦朝的“学法令”便是除了专职的狱吏外,所有的官员都需要学习的,并以此作为一项政绩考核的内容。法家以“以法治国”为本原,进一步将法律、君主二者的权威视为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并认为立法权和最高决策权应该牢牢地掌握在君主手中,君主通过成文法来管制子民与百官,并实现统治稳定与国家繁盛。但是法家内部法律能否约束君主的权力问题,却存在一定分歧,在商鞅看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崇尚法律,所以君主也该当义不容辞地尊崇法律,“垂法而治”不应因一己之私而打破。而李斯认为君主應该“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即统治者就是最高法律,超脱于法律之外,只有这样,官吏和百姓才不敢反抗,统治者才能独擅天下。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李斯在他的政治实践中,对于文字、车轨、货币、度量衡等方面皆采取了相关措施以限定。秦始皇三十七年,李斯向嬴政请奏了一封举足轻重的奏帖:撤废秦币外的其他六国货币,举国上下只允许使用一种货币。即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不容置喙,秦统一货币的举措不仅对秦的经济发展、巩固集权起到一定作用,更是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发展。秦国一统天下后多方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但惟独货币体系一成不变。市面上使用的货币样式十分繁杂,使用起来十分不方便且不利于管理。鉴于此,李斯对于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标准做出了严格规定。后世将李斯这一举措认作经济史上的首创。因此而锻造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也因其圆形方孔的造型可随身携带,使用便利,一直使用到清朝晚间。
从某方面看,几千年泱泱中华代有才人出,名将功臣比比皆然,但大多功在当朝,曾引领了某一时代,但沧海桑田,他们也就随之消逝在了历史长河中。而在李斯的政治生涯中,可以说每一项重大举措的影响都绵延千年,荫及后人。《史记》对这位褒贬不一的法家实践者的评价是这样的:“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四、对法家人性观的批判、反思
李斯将人性彻底看成利益命题,纯粹利用严刑酷法遏抑人的本性,从未重视伦理道德的教化、感化力量。”秦将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置若罔闻,这很大程度上加速了秦短命而亡的进程。司马迁曾就这一点批驳道:“法家不别亲梳,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曰:‘严而少恩。”
法家否认了人性的多维性,只看重奖惩,这在理论上要求有一个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根本无法支撑的强大政府;仅此一点就注定了它政治实践的失败。
五、结语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传统,但法家对人性的深刻、细致的理解和尊重,甚至于我们对法家人性观的反思对于今日中国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和社会转型,我们更应该不断的去追求,依据现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去吸纳中国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在一定层面上,这对于平衡转型中国的各种潜在冲突的社会利益,保持社会的多元一体和长期稳定,还是想要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战略,都非常必要,也相当紧迫。在另一层面上,它也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
韩非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吕不韦总结了百家,他们的影响都只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然而,李斯用鲜血和实践创设的制度影响了千百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可以算一部史诗的话,那么这一点,李斯做到了。
参考文献:
[1]苏力.早期儒家的人性观. 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5).
[2]刘红卫.从李斯的功利观看秦朝的灭亡. 惠州学院学报.2002(22).
[3]杨宏潮.法家的人性观与法治. 法制与社会.20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