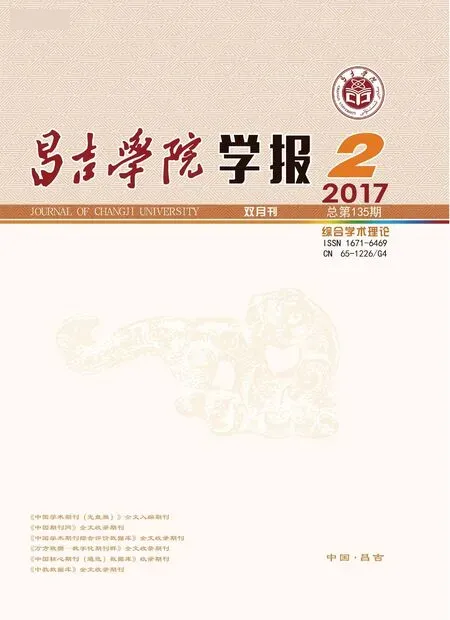中国学生对英语“NA空间表量构式”习得的实证研究
孟彩娟 罗思明
(1.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2)
中国学生对英语“NA空间表量构式”习得的实证研究
孟彩娟1罗思明2⋆
(1.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2.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2)
文章从“NA空间表量构式”习得假设出发,探讨中国学生对此英语构式的习得情况。实验结果发现:低水平组的得分最高,高水平组其次,中水平组最低;并且三个水平组的平均得分几乎都低于0.5分(每题1分)。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语言的正迁移对低水平组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而高水平组对此构式的形式和意义有一定的把握,加工能力较高,相比之下,中水平组受英汉差异敏感度的负面影响最为严重,但随着知识的增加,会超过低水平组。另外,总体水平较低说明此构式的教学存在严重不足,需要改善教师教学方法和技巧。
“NA空间估量构式”;二语习得;语言迁移;外语教学
引言
根据Goldberg(1995)[1]的构式理论,本课题所指的“名形表量构式”是一类表量“名饰形”形式—意义—功能匹配体,其结构可为短语或复合词。汉英都存在“NA空间表量构式”来表达物体性状的相对量度(relative measurement),其构成成分通常包含一个名词、名词性短语或数量短语(N)和一个空间维度形容词(A空间),两者在名词选择上存在不同制约(主要是词汇语义制约)和选择,如(*表示不合法,全文同):
(1)a.小村中竟有胳膊粗的大蜡。b.一根约五个手指粗的钢索支承客车重量。
*a’an arm thick candle b’Robertson broke a finger-thick stick.
国内外对“名形式”从语音、语义、句法、功能及其生成机制等角度进行了此构式本体或类型学研究,然而针对该构式的实证性研究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将通过问卷测试的方法,考察中国学习者对英语“NA空间表量构式”的习得情况与英语水平的相关性问题,并做出阐释。
一、文献回顾及理论背景
Schwarzschild[2](2005)和Kennedy[3](2007)从词汇语义出发,认为“NA空间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制约的语内和语际差异存在词义和语言独特性:英语中“tall/wide/deep/thick/old/long/high”等形容词可见于此构式是“同形异义规则”作用的结果,无法根据词义做出语内或语际预测;同时,作者提出一条蕴含制约规则:凡可用于“NA空间表量构式”均可用于比较构式的形容词。佟慧君(1992)认为“N”所代表的物须具有实物性、具有某种特征(如“笔”取其形状,“蜜”取其味道)、可感知性、与所修饰的形容词素的语义须具有联系性[4];董晓敏(2005)对其进行了补充,提出“NA空间表量构式”中的名词具有熟知性、典型性且语用上的无指性[5]。张菲菲、张黎(2009)得出结构中的名词主要包括器具、生物构件、消费物、创造物、植物、动物等语义类别,且进入该结构的频率不等[6]。罗思明(2014)研究得出,英汉“NA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存在语间差异(具体见下表):汉语中形容词的语义范围大于英语,如含“重量维度形容词”;英语形容词制约为强制约,常不容许“负向语义”和“零向语义”违反,汉语则为弱制约,可违反,如“负向空间维度形容词”和“反义AA”[7]。见表1

表1 英汉短语类“NA表量构成”形容词制约对比
本文仅研究空间维度形容词,由上表可见,英汉都具有这种构式,区别在于英语的空间维度形容词都具有正向义,如“tall/wide/deep/thick/old/ long/high”,汉语既可以是正向,也可以是零向和负向义,如:长、短、宽、窄、高、矮、粗、细、厚、薄、深、浅、远、近、大、小。
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总是在发挥着重要作用。Odlin[8]在1989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语言迁移:语言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将“语言迁移”定义为“迁移是目标语和任何一种已经习得的语言(也许是没有很好地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Transfer is the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any other language that has been previously acquired(and perhaps imperfectly acquired))”。人们研究发现,母语中有“对应词”的二语词语或结构,学习者学起来比较容易,准确度也比较高。针对英汉共有的“NA空间表量构式”,二语学习者的习得情况如何,下文将进行初步探究。
二、实验过程
(一)假设
英语水平与“NA空间估量构式”习得水平成正比,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高,对此构式习得水平越高,相反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低,其对此构式习得水平越低。
(二)受试
受试为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三年制英语大专一年级学生27人,都通过了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宁波大学英语专业本科二年级学生26人,都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另外是宁波大学英语专业研究生23人,都通过了英语专业八级考试。分别代表低、中、高三个水平组。
(三)实验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以句子翻译和语法判断为测试工具。为避免语法判断中的“NA空间表量构式”影响受试者的翻译构思,本人将句子翻译放在语法判断之前。共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为句子翻译题(汉译英),含有“NA空间表量构式”的8个汉语句子,每题1分。要求被试写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所有英文翻译表达。译文即使语义正确,可以翻译为对应的英文“NA空间表量构式”却没有译出不得分;译文中含有“NA空间表量构式”,存在拼写、介词等其他错误不扣分。不可以翻译为英文“NA空间估量构式”却翻译成了此构式,不得分。如:最小的金属管只有铅笔粗。
甲:The smallest metal tune is only pencilthick.(得1分。)
乙:The smallest metal tune is as thick as a pencil.(不得分。)
第二部分为语法判断题,含有20个英语“NA空间估量构式”,其中有13个是被英语本族语者使用,有7个是汉语中存在直译过来的,而英语本族语者未曾使用。要求被试认为英语中有这种表达的“打勾”,相反,没有的“打叉”。如:
()1.head large()2.thimble long()3.cat big()4.eyelid thin
被试每答对一题得1分,答错得0分。随机排列,不具有规则性,以排除因被试发现合法句的排列规则“猜测得分”,而非英语真实水平的反应,从而影响实验结果的真实性。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学习者的英语“NA空间表量构式”二语习得水平问题,因此,用于测试的全部句子均为简单句,均来自真实材料,8个汉语合法句来自北京大学语料库,13个英语词组或复合词均来自美国古代语料库(COHA)、美国当代语料库(COCA)或英语国家语料库(BNC),7个不合法的英语词组或复合词是根据汉语临时造的,所涉及字词大都为全体受试所熟悉,必要时提供相应的词语,对于个别较生疏词汇,予以提示,从而确保被试不受句子复杂程度、生词等因素干扰而影响实验结果。低水平组测试在正常上课时间举行,中水平组利用课前时间举行,不单独组织正规考试形式进行检测,高水平组在课堂完成,目的是为了保证被试都能够不借助翻译工具或抄袭他人,从而确保实验信度和效度。整个实验时间持续近半小时,即句子翻译和各15分钟,答题完毕,立即收回试卷。
(四)实验数据的处理
关于句子翻译题,大部分为空白的,或语法判断题明显可以看出是随意判断的(如:全部打勾或全部打叉)试卷予以剔除。最后,选取低、中、高水平组分别22份、21份、20份试卷进行数据统计。实验结果借助SPSS20.0软件包进行分析。
三、实验结果
根据评分标准,在完成句子翻译和语法判断后,对各类数据进行分析、归纳和整理,低、中、高三个水平组的得分情况如下:

表2 句子翻译和语法判断每小题(1分)分别平均得分情况

表3 “NA空间表量构式”习得情况实验综合数据(满分28分)
表2中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反映了低、中、高二语水平组受试完成问卷主观题和客观题的平均得分情况。首先,就组内差异而言,各组受试在语法判断的平均得分都高于句子翻译。其次,从组间差异而言,不管是句子翻译还是语法判断,均为低水平组的平均得分最高,高水平组其次,中水平组最低。
表3显示综合考虑句子翻译和语法判断,二语水平与“NA空间表量构式”习得水平不成正比,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高,并不代表其对此构式习得水平越高,相反,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越低,也不能代表其对此构式习得水平越低。另外低水平组的标准差最大,说明成绩的离散度高,总体趋势分值差异较大,而中水平组标准差最小,表明离散度低,分值差距较小。最后,我们可以看出,高水平组的得分明显高于中水平组,而低水平组却高于高水平组,这一结果的获得受一定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的影响。
五、分析与讨论
从上文的分析结果可看到:第一,本实验的结果与假设不一致,英语高水平组对此构式的掌握并非最好;第二,受试的三个水平组每题的平均得分几乎都低于0.5;第三,低水平组的标准差最大,分值最高。究竟是什么造成的?
首先,本实验结果的高低层次的成绩分布,符合外语学习的认知心理。由于英语和汉语都存在此构式,低水平组受汉语此构式的影响最大,母语的正迁移对他们产生了促进作用,而高水平组利用较为完备的外语知识来判断,中等水平组知识不完备,并且具有对英汉差异的敏感度,生怕出错,却偏偏出错。因此,就造成了低水平组成绩最高,高水平组其次,中水平组最低的成绩分布结果。
其次,我们认为“三个受试组的平均成绩都较低”是由英汉“NA空间表量构式”的不对等性造成的。通过本人的前期研究发现,汉语“NA空间表量构式”的使用明显多于英语,而且“N”的语义类别差异巨大。如:当“A”为空间维度义“粗(thick)”时,汉语中“N”多为“餐饮器具(如:碗口)”和“生活用具(如:水桶)”等,而英语却无一例;相反,英语中“N”可以为“cell(细胞)/module(分子)/atom(原子)/particle(粒子)”等,而汉语却无一例。英汉“NA空间估量构式”的共性在于“N”通常都为具体名词,而非抽象名词,且名词越具体,其所表达的空间量越显著[9](王文斌,2013)。这种差异和共性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我们认为英汉民族存在不同生活习惯、科技水平和文化习俗造就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英语重理性,汉语重悟性[10](潘文国1997);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进程先于我国;中国的文化历史底蕴深厚、历史悠久,而西方只有几百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不同。以上三方面在英汉“NA空间表量构式”都得到了体现。洪堡特(1963)曾说过,“语言从精神出发,再反作用精神,这是我要考察的全部过程。”[11]该研究给对外语教学有如下启示:
(1)外语教师应该立足学术前沿,密切关注对比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等专业学科的最新发展动态,掌握学术新知,不断积累,并把这些知识用到自己的教学当中去。
(2)外语教师对于此构式的低掌握度要进行反思,改进教学方法和模式,特别要关注中西方的文化和认知异同,从而深入有效地促进中国学生对此构式的习得。
[1]Goldberg,A.E.Constructions: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Schwarzschild,R.Measure Phrases as Modifiers of Adjectives[J].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2005, (34):207-226.
[3]Kennedy,C.Vagueness and Grammar: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J].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2007,(30):1-45.
[4]佟慧君.“名+形”结构偏正式形容词之特点[J].世界汉语教学,1992,(2):103-106.
[5]董晓敏.“名词+形容词”估量短语[J].世界汉语教学,2005,(3):76-82.
[6]张菲霏,张黎.“名词+量度形容词”结构研究[J].文教资料,2009,(18):209-211.
[7]罗思明,查如荣,江晶晶.英汉“NA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制约的语料库与类型学研究[J].外语研究,2014,(3): 31-37.
[8]Odlin T.Language Transfer: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M].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9]王文斌.从“形动结构”看行为动作在汉语中的空间化表征[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6).
[10]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
[11]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H03
A
1671-6469(2017)-02-0098-04
2016-12-12
国家社科规划课题“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13BYY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孟彩娟(1990-),女,河南洛阳人,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
罗思明(1970-),男,安徽太湖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英汉对比、语言类型学与词典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