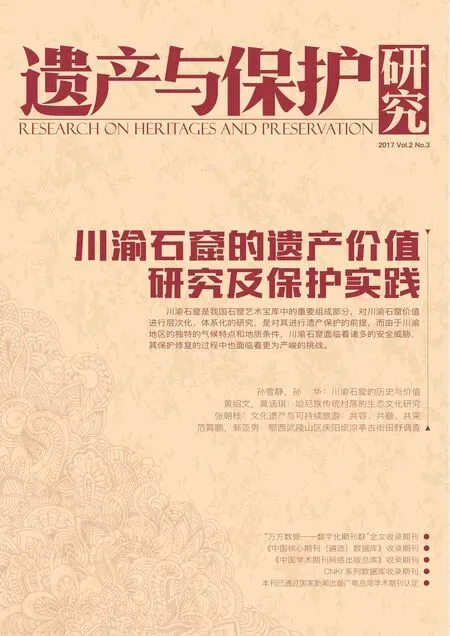川渝石窟的历史与价值
孙雪静,孙 华
(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 100054;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川渝石窟的历史与价值
孙雪静1,孙 华2
(1.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 100054;2.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文章在简单梳理川渝地区石窟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川渝石窟及造像的价值,并尝试探讨其价值研究的不足和重要性。川渝地区开窟造像发轫于南北朝时期的川北地区,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中,历经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至两宋达到鼎盛。川渝石窟具有突出的价值:是中国晚期石窟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集大成者;在众多领域开创了佛教艺术的新风格和新题材;拥有中国最为系统的密教造像,是中国道教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儒释道三教并流在石窟艺术领域的重要见证;对宗教史研究意义重大。在遗产价值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川渝石窟价值进行层次化、体系化的研究,是川渝石窟遗产保护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川渝石窟;唐宋石窟;遗产价值;艺术价值
四川盆地群山环绕,气候宜人,土地肥沃,先秦以来就号为“是农耕文明的天府之国”。由于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民相对殷实,思想和文化艺术也向来活跃。早在夏商的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就形成了“东有扶桑,西有若木,十日序行,皆托于鸟”的宇宙观念,出现了人首鸟身的太阳大神和三神配置的神像系统。正是由这样的社会基础,东汉末期这里也出现了早期的道教组织,川渝及其邻近地区成为道教早期传布的重要区域之一。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胡商的入蜀经商,佛教及其造像也传入的四川,以后一直是佛教和道教传教的重要区域。当中原地区在先后经历了汉末动荡、五胡乱华、天宝之乱、唐末混战等多次社会战乱后,佛教赖以发展的经济基础受到摧残,民众的宗教热忱也明显消退,而社会经济长期稳定、文化传统一直延续、宗教热诚依然如故的川渝地区,便逐渐成为佛教高僧、道家名流和文人画师的心仪之地。到了唐宋之际,川渝高僧之集中,佛寺规模之宏大,经典写刻之精美,寺观画塑之驰名,已在全国首屈一指。由于四川盆地多丘陵和山地,石质又松软细腻,易于开凿岩洞和雕刻图像。生活在川渝地区的民众长久以来就在这些山丘边缘挖凿岩洞,营建墓穴,垒筑石阙。数量众多的汉代崖墓和石阙,为后来劈崖建寺和开龛造像奠定了技术和传统基础。在此背景下,从南北朝时代佛教流行开始,川渝丘陵山区适宜于开凿龛像的地方就成为建立石窟的理想地点,遗留下了大量的佛教和道教石窟寺观和造像。川渝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情感价值和利用价值,开展川渝石窟的价值研究应该具有意义。
1 川渝石窟的历史与现状
四川及其邻近地区是中国较早出现佛像形象的区域。早在20世纪50年代,四川乐山市麻浩1号崖墓、柿子湾1号崖墓中发现了带头光的汉代坐佛雕像,四川早期佛像的问题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2]。以后,在四川、云南和贵州东汉晚期至蜀汉的墓葬中都发现了铜或陶的近似佛像的形象,这些佛像大都与摇钱树有关,铜铸的摇钱树干上不时可见佛像混迹于仙人之间,陶制的摇钱树座上偶尔也会做出类似佛的形象。早期佛像的这种存在形式,说明在佛教造像传入四川时,是与本地宗教传统和神仙形象混杂在一起,普罗大众对佛教还缺乏真正的认识[3-4]。川渝地区成熟的佛教造像的出现是在南北朝时期,重要的代表为多批带有明确南朝纪年的佛造像,最早的例子如成都万佛寺出土的南朝宋元嘉二年(公元425年)净土变石刻及宋、梁时期佛造像[5],以及成都北原茂汶羌族自治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佛造像等[6]。这些造像都是佛寺殿堂内摆放的雕像,川渝地区石窟寺的开凿则略晚于地面寺庙建筑(如上述早期佛造像的供奉场所),开始于南北朝晚期萧梁/北魏晚期。我们知道,北朝的河西和中原地区都进入了佛教石窟寺建造的高峰时期,著名的天水麦积山石窟就是这时期佛教石窟的代表。与天水邻近的四川北部广元地区,由于位于连接中原北方和四川盆地的交通要道上,自然也就成为佛教在川渝地区传播的最早区域之一。广元旧城出土的北魏石雕释迦文佛造像,背屏刻有“延昌三年,太岁在甲午,四月廿日,梁秦显明寺比丘惠楞与平都寺比丘僧政等,觉世非常敬造释迦文佛石像一丘”等文字,铭文中的“梁秦”指梁州和秦州,包括了四川北部、陕西南部和甘肃南部一带。四川广元千佛崖(图1)、皇泽寺的南北朝晚期龛像,就成为川渝地区目前所见最早的佛教石窟寺的遗存。

图1 四川广元千佛崖(北魏至唐)
广元千佛崖和皇泽寺都位于嘉陵江边、川陕主要官道附近。石刻始凿于北朝晚期,兴盛于唐,以后很少开凿。千佛崖现存窟龛848座(不含窟龛内补凿的雕像),皇泽寺现存窟龛57座。开凿于北朝时期的早期窟龛有:千佛崖第726号窟(“大佛洞”),约开凿于北魏晚期;千佛崖第226号窟(“三圣堂”)、皇泽寺第15、38、45号窟和大佛楼侧小龛,这些窟龛的开凿年代略晚于大佛洞,其中第45窟是四川罕见的中心柱窟。这些早期石窟的造像组合有一佛二菩萨/弟子、一佛二弟子二菩;造像题材有释迦佛、三世佛等[7-8]。无论是洞窟形制、造像组合、造像题材、还是造像风格,都与同时期中原北方石窟相近,可见川渝早期的石窟造像受北朝中原地区石窟造像系统的影响较大。
隋统一全国后,奉佛教为国教,蜀地佛法日益兴盛。隋末之际北方战乱,川渝地区偏安一隅,愈发带动了佛教石窟造像的发展,佛教石窟造像从川北的广元地区向南延伸至巴中、绵阳等地,道教石窟造像也随之而起。入唐以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两京地区与川渝佛教文化的交往日益频繁,为川渝石窟造像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安史之乱后,川渝地区成为唐王朝赖以生存的政治后方和重要的经济中心,成都还一度升格为与两京齐名的“南京”,成为大量来自北方僧侣、文人、信徒、工匠集聚的文化中心。中晚唐至五代,北方地区连续遭受灭佛与战乱,中原石窟造像愈加衰颓。与中原石窟逐渐衰落形成对比,川渝地区石窟在此时期异军突起,成为唐代中期以后中国石窟造像最盛行的区域。石窟造像由川北扩大到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盆地腹地,尤其是绵阳、乐山、内江、资阳、大足等地。这时期的川渝石窟明显地形成了地域性的特点,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的佛教石窟划分为广元石窟(包括绵阳)、巴中石窟、西蜀石窟(成都周边),就反映了这种认识[9]。隋唐五代的代表性石窟寺除了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外,还有广元观音崖,巴中西龛、南龛、水宁寺[10],梓潼卧龙山[11],安岳卧佛湾(图2)、圆觉洞、千佛寨,大足北山,仁寿牛角寨、乐山大佛、夹江千佛崖[12](图3)、浦江飞仙阁、丹棱郑山/刘嘴等。这个时期的窟龛开凿数量众多,造像内容丰富多彩,川渝地方特色已经展现。隋至唐初的造像组合出现了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五尊式,造像身后凿出浮雕双树,双树与窟顶相连构成背屏,并在造像身后表现出人形化的天龙八部护法形象。盛唐时期释迦、弥勒说法图、西方净土变题材最为流行,其后释迦佛、阿弥陀佛为主导的释迦三圣、西方三圣、观无量寿经变,千手观音经变、药师变、地藏与观音、毗沙门天王等题材常见。密宗题材的造像在初唐后就少量出现,盛唐开始广为流行,并极大影响到以后的川渝石窟造像。

图2 四川安岳卧佛湾卧佛及经窟(唐)

图3 四川夹江千佛崖(唐)
两宋时期,北方地区石窟造像进一步衰落,川渝地区却一枝独秀,进入极盛。北宋初年至南宋末年,川东地区石窟造像艺术最为兴盛,异彩纷呈,以安岳、大足两地为代表。大足石刻地点众多,约40余处,遗存造像5万余躯,是唐宋时期重要的摩崖石刻造像群。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有北山、宝顶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和南山等处,其中北山和宝顶山摩崖造像最为集中,规模宏大、雕刻精美。大足北山造像开凿于晚唐,经五代至宋达到极盛,造像题材丰富而复杂,以密宗题材最多,如降三世明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如意轮观音、数珠手观音、如意王菩萨、欢喜王菩萨等。宋代还出现有弥勒下生经变、地狱变、观无量寿变等经变题材。大足宝顶山造像集中在大小佛湾两区,均为摩崖造像,两区造像应经过统一规划设计,以大型连续性的雕刻和庞大群像为代表,场面恢弘。造像题材以密宗和经变题材为主,如华严三圣、广大宝楼阁、六道轮回图、毗卢道场、孔雀明王经变、千手千眼观音、地狱变、观无量寿变、父母恩重经变、十大明王等。造像题材糅杂了密宗、禅宗和儒家等思想。大足南山石刻造像主要为道教题材,石门山、石篆山造像则常见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内容。
安岳石窟及摩崖造像多达200余处,遗存窟龛1 000余座,造像2万余躯,是川渝地区除大足之外石窟及造像最多的地区。较为重要的地点有卧佛院、圆觉洞、毗卢洞、华严洞、玄妙观等。其中卧佛院开凿于盛唐至五代时期,主要造像有释迦说法、涅槃经变、三身佛、弥勒佛和千手观音等。1982年于卧佛院新发现有巨型卧佛和15座刻经洞窟,其中第66、71~73窟为经文和造像的合造窟,石经为唐开元年间刊刻,有《涅槃经》《法华经》《维摩经》《大方便佛报恩经》等10余部,约40余万字,体量恢宏。圆觉洞开凿于盛唐至宋,主要为佛教造像,也有道家窟龛及佛、道合开窟龛。造像题材有释迦、西方三圣、三佛、七佛、地狱变、千手观音、明王、毗沙门天王和天尊像等。此外,毗卢洞(图4)华严洞(图5)、玄妙观、千佛斋等地也开凿有许多佛教和道教龛像,主要题材有华严三圣、西方三圣、弥勒佛、药师经变、天尊像等。
川渝地区是道教发源和形成的重要地区,道教信仰传统深厚,川渝地区现存最早的道教造像见于隋代,川西绵阳、潼南等地有较为集中的道教造像。其中绵阳西山道观道教摩崖造像,由隋延续入唐,玉女泉老君龛、玉女真人龛为其中保存较完整者。唐中期之后,川渝地区出现一批规模较大的道教石窟造像群,广泛分布于安岳玄妙观、丹棱龙鹄山、仁寿牛角寨、剑阁鹤鸣山等地,其道教造像多与同时期佛教造像风格一致,并出现了佛、道合一造像,如安岳玄妙观的唐代佛道合龛像。宋代与唐代一样尊崇道教,又倡导儒学,重庆大足石门山石窟、南山石窟等是这一时期道教造像的代表。这时期不仅有佛、道像同龛,更出现儒、释、道三教合流的造像,如大足妙高山第2窟,主尊释迦两侧分列孔子和老君。也有三教在石刻地点分别开窟造像的情况,如大足石篆山既有孔子及门徒像窟,也有老君像窟,还有文殊、普贤、地藏十王像窟(图6)。

图4 四川安岳毗卢洞柳本尊十炼龛(南宋)

图5 四川安岳华严洞右壁圆觉菩萨像(南宋)

图6 重庆大足宝顶山地藏十王像局部(南宋)
综上,川渝地区石窟寺分布广泛,地点数以千计,造像数量巨大。早期石窟寺建造发轫于与北朝交流密切的川北地区,广元和巴中地区的早期石窟受中原北方石窟的影响较大。随后石窟寺建造深入到四川腹地,在得天独厚的自然及人文环境中,历经隋、唐、五代的蓬勃发展,至两宋达到鼎盛,川渝地区遂成为全国晚期石窟寺艺术的中心。在此过程中,不仅逐渐独立于北方造像系统的影响,更发展出极富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造像题材和风格。不仅有题材丰富的佛教、道教造像,还有自成体系的密宗题材,以及数量众多的儒释道合一的题材。南宋之后,川渝石窟的修建由盛转衰。元明及至民国,川渝地区多遭战乱,但仍在多个地点延续有造像活动,并多次对原有龛像进行过修缮维护。就其整体而言,两宋之后的川渝石窟已是盛况不再,逐渐显现出衰落的景象。
2 川渝石窟的价值研究
对川渝石窟寺价值的研究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法国学者色伽兰(Victor Segalen)、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水野清一已经对当时四川中北部的石窟寺有过评议。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川渝石窟寺价值的认识较为感性,一些石窟寺考古专家和佛教艺术专家通过比较认识,指出川渝石窟寺有其独到的价值,对其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川渝地区石窟在晚唐时期方兴未艾,在两宋时期走上顶峰,其晚期窟像填补了中国晚期石窟寺研究的空白;二是川渝佛教造像兼有南北佛教造像的影响,并发展出自己的地域特色,尤其大足、安岳一带的密教造像,在中国佛教史研究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三是川渝石窟遗留下不少道教石刻龛像,基本反映了道教造像的发展全过程,并且是道教、佛教、儒教相互渗透的历史见证。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川渝石窟寺的资料不断公布,关于川渝石窟寺的地位和价值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①"以下参看罗炤.四川石窟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巴中石刻内容总录.成都:巴蜀书社,2006。
(1)四川造像样式对中原造像的影响。四川以成都地区为中心,出土有多批南朝石刻造像。这些造像与中国同期造像风格大不相同,并且出现了中国现知最早的双领下垂汉式袈裟样式。从南北朝后期开始,中国绝大多数佛教造像均以这种袈裟样式为主,如四川茂汶县出土的南齐永明造像碑有迄今发现的纪年最早的双领下垂式袈裟造像,今藏四川省博物馆[13],是早期佛教汉化最明显的标致。此外,洛阳龙门唐代石窟中有带高浮雕莲茎的莲花座,一般认为源于长安地区,但在四川西安路、万佛寺和汶川的南朝梁代佛造像中已经出现此类样式的莲座。不仅如此,隋唐时期,中国佛像开始出现丰满健壮形象,武周时期中原北方流行丰腰肥臀的菩萨形象,这一隋唐时期丰满的风格在四川南朝后期造像中已经开始显现,这在汶川北朝后期的双观音立像以及四川省博物馆藏的南梁造像碑上已初见端倪,并继续保持在四川地区北周至唐初的造像中。西魏时期,四川并归长安政权所有,西安地区此时出现的健壮的佛像造型、满饰璎珞的菩萨像以及丰满扭腰的形式,很可能来源于四川地区。洛阳在北朝后期多次沦为战场,龙门石窟的再次兴起是在唐高宗和武周时期,而这时期所流行的健壮丰满的造像风格,应主要来自西京长安。因此,以目前发现造像的情况看,唐代流行的丰满健壮的造像风格,与褒衣博带式的袈裟样式一样,最早应出现在四川地区,继而通过当时的首都影响到全国。
(2)四川佛教造像题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唐代天宝之后,中原丧乱,有大量高僧从中原入蜀,佛教中心的转移,使以成都大慈寺为中心的佛教影响范围极大,在这里创作或改造的佛造像题材成了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和喜闻乐见的内容。例如水陆忏法题材的流行,宋代东川有杨谔水陆仪、蜀中有杨推官仪文盛行于世;宋元祐八年(1093年),四川眉山人苏轼绘水陆法像,作赞16篇,被称为“眉山水陆”②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四十六,《大正藏》第49册,第418页。;当两宋时期,水陆大法非常盛行,这与蜀地的水陆法仪文和图像有很大的关系,也是大足宋代石刻的重要内容之一,有些石窟完全按照水陆道场的仪轨开凿。又如地狱与十王题材,佛教流通中国不久,因果报应的思想就流行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人死后要据其在生业行得不同果报,唐代发展为由十王审定在生业行,南宋志磐著《佛祖统纪》时尚言十王的名字“藏典可考者六,阎罗、五官、泰山、初江、秦广”③宋 .志磐:《佛祖统纪》卷三十三,《大正藏》第49册,第322页。,然而在四川的安岳有完整的唐末五代时期的十王形象,南宋大足石刻也有同样完整的内容,并配有地狱诸像。此外,唐后期,出自成都的千手千眼观音图样传到中原,竟相模仿;唐后期川渝地区的毗沙门天王像,是目前中国最多、最系统的毗沙门天王造像。
(3)四川佛教龛像对云南和河西等地的影响。1990年在云南巍山垅圩图城出土了200多件佛像,是目前云南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佛教造像。发表的资料中有多件与四川隋唐造像组合及风格相同,如大耳戴环的佛像,戴大璎珞、胸饰玲铛形饰物的菩萨像等与四川隋代和唐初的造像类似,属于同一系统之造像。而且出土处是一座寺院遗址,同出的还有莲花纹铺地砖瓦当等,与汉地佛寺同类构件相同④巍山出土这批佛像现在大部分藏巍山县文物管理所,参见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编《巍山文物荟萃》,其中图版157为南朝梁代造像,159-165为同出的铺地砖、瓦当等建筑构件。。巍山垅圩图是南诏的发源地,这意味着南诏佛教传播之初即是汉传系统,至唐代仍然如此。后来其佛教中出现的最为特殊的阿嵯耶观音也是他们根据汉地佛教中圣僧(如僧伽)等的形象创造的[14]。汉地系统对南诏、大理施加的影响,四川是一个最重要的地区。唐时就有南诏子弟在成都大慈寺学习,唐与南诏有时还因此发生战争,南诏后来改称大礼也与唐使减少其在成都学习子弟的数量有关⑤宋 .司马光著,元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 .唐纪 .宣宗》卷二百五十载:“初,韦皐在西川,开清溪关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以慰悦羁縻之。业成则去,复以它子继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稟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予,所从傔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其贺冬使者留表付嶲州而还,又索习学子弟,移牒不逊,自是入贡不时,颇拢边境。……子酋龙立,……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国号大礼,改元建极,遣兵陷播州。”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21页。。四川佛教和图像对敦煌的影响很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敦煌发现的《报父母恩重经》,其署名即为成都大慈寺沙门藏川,这是四川僧人创造的对中国影响最大经典。敦煌壁画中的西方净土变画,与四川石窟晚唐至宋代净土雕刻几乎相同,文献中记载晚唐五代成都唐慈寺最多的壁画之一就是净土变画,可见晚唐五代四川与河西也有很密切的联系[15]。
(4)川渝道教石窟寺的重要性逐渐显露。仁寿县千佛寨的道教石窟题记中保存有关于道教经典最早而且完整的记录,不仅比权威的《开元道藏》还要早,而且与《开元道藏》的记录有很大的差异。这一记录在20世纪末期曾经引起国际道教学界的关注,结合道教经像进行研究,已经成为川渝道教造像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结而言,川渝石窟在东亚石窟艺术史和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其价值的认识还在不断地刷新。依据现有的认识,本文暂将其价值归纳表述为以下5个方面。
第一,是中国晚期石窟发展的历史见证者和集大成者。唐天宝年间之后,长期战乱使得中国中原北方地区大规模开窟造像转盛而衰,川渝地区的石窟则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在此时异军突起、独领风骚。其开窟造像活动历经中、晚唐和五代时期仍方兴未艾,于两宋时期达到高潮,将中国大规模开窟造像的时间向后延续了500年,是中国晚期石窟发展历史的重要见证。作为晚期石窟艺术的中心,川渝地区的石窟寺地点数以千计,遗存下的佛、道、儒三教造像数不计其数,是中国晚期石窟寺及造像艺术发展的集大成者。
第二,在众多领域开创了佛教艺术的新风格和新题材,对东亚佛教艺术史影响深远。在佛教艺术造型上,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艺术风格,例如双领下垂汉式袈裟样式、带高浮雕莲茎的莲花座、扭腰丰臀一腿微屈的菩萨形象以及隋唐时期流行的丰满健壮的造像风格等,都在南北朝时期的川渝地区首先形成,继而影响到云南、陕西等周边地区,并通过当时的首都影响到更大范围。
在佛教艺术题材上,诸多在晚期流行甚广的形式和主题,例如水陆法仪、地狱十王、千手千眼观音、毗沙门天王、报父母恩等,皆产生或成熟于川渝地区,在川渝石窟和造像中有着丰富的反映,很多题材不仅影响到全国,也传播到朝韩、日本、越南等地,显示出川渝石窟艺术对东亚佛教艺术的强大影响力。
第三,拥有中国最为系统的密教造像,是密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四川安岳、大足一带的密教造像,是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而自成系统的密宗造像,以南宋后期的大型密宗石窟寺道场大足宝顶石刻为代表,经由严密的规划而成。川渝密教石窟及造像,作为密教艺术的杰出代表,在世界佛教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第四,是中国道教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儒释道三教并流在石窟艺术领域的重要见证。川渝地区作为道教发源、形成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拥有规模庞大的道教石窟造像群,基本反映了道教造像艺术发展的全过程。此外,川渝地区还广泛分布有数量众多的佛道合龛以及儒释道三教造像,是中国唐宋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历史在石窟艺术领域的生动反映。
第五,拥有规模很大的佛教石经,并有对道教经典最早的记录,对宗教史研究意义重大。川渝地区的佛教石窟寺中遗存有中国现知数量最多的佛教石经,散布在多处石窟寺中,其中安岳卧佛院石窟寺拥有中国南方年代最早、面积最大、数量最多的石经,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此外,仁寿县千佛寨的道教石窟题记中保存有关于道教经典最早且完整的记录,对道教史研究也有重要意义。
3 川渝石窟价值研究展望
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使得专门针对川渝石窟寺的价值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为我们未来的价值研究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应成为我们发现薄弱环节和进行弥补改善的动力。可以看到,现阶段的研究整体还较为缺乏理论性、系统性和层次性。
一方面,遗产价值具有多样性。正如遗产保护学界分析过的那样,遗产价值有本体的与衍生的、核心的与附加的、经典的与稀缺的、上层的与草根的、文化的与经济的,不一而足。而在现阶段的遗产价值学研究中,对这些多样性的价值界定和研究并没有完全构架起理论体系。理论的薄弱直接影响到了价值研究的深入。具体而论,川渝石窟寺的价值应包括石窟寺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情感价值和衍生的其他价值等,但在实际讨论中,并没有真正做到准确区分。我们所阐述的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大都与历史价值混为一谈,而对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这所谓“三大价值”之外的价值,例如川渝石窟寺的精神情感价值等,更是缺乏关注和阐述。因此,要对川渝石窟寺价值进行深入研究,首先要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这些基本问题进行逻辑层面和理论层面的体系化探讨。
另一方面,遗产价值具有主观性。就主体对遗产价值的认知来说,遗产是否具有价值、遗产价值的结构要素以及不同价值重要性的排序等,都需要 “人”这个主体来进行认知、判断和评估。不同的人除了个体认知的差异外,还分属于不同的时代、社群、族群、国家和阶层,因而对“自我”的或“他者”的遗产,不同的人们价值认知都会有所不同。
以川渝石窟寺的艺术价值为例,不同的学者对其艺术价值就抱有不同的看法。大足石刻号称中国“五大石窟”之一,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大足石刻的评价是:“大足地区的险峻山崖上保存着绝无仅有的系列石刻,时间跨度从9世纪到13世纪。这些石刻以其艺术品质极高、题材丰富多变而闻名遐迩,从世俗到宗教,鲜明地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的日常社会生活,并充分证明了这一时期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和谐相处局面。”但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20世纪40年代前往西南地区进行古建考察时,在肯定了大足石窟的整体价值的同时,也提出大足的宋代佛教石刻已经庸俗化,艺术价值不及秀骨清像的北魏石刻[16]。诚然,川渝地区开窟造像的高潮在唐宋时期,与早期北朝石窟及造像相比,其题材和风格确实产生了较大的转变。但是这意味着当时人们的文化需求和审美趣味已经与北朝时期的不同,进而主动选择了新的、更符合他们自身需求和审美的风格。正如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断本土化、世俗化,佛教石窟及造像也相应地,在晚期显示出了更为本土化的审美趣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之后的艺术取向直到今天仍然在中国本土的民众中有着广泛的审美共鸣。因此,如果我们以某个人的,即便是某个权威学者的,审美判断为依据,简单地认为北魏时期石窟寺更有艺术价值,或认为本土化之后的川渝宋代石刻艺术价值更高,都会显得有失偏颇。
因此,在承认主体对遗产价值的评判具有主观性的基础上,如何对川渝石窟寺的艺术价值进行科学的研究?首先面临的还是遗产价值的基本问题,即,需要首先在逻辑层面对“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本身进行理论体系的探讨和界定,这是我们正确认识川渝石窟寺艺术价值的基础。
除以上两个基本问题外,川渝石窟的价值研究还要求我们对川渝石窟寺及造像进行更为细致地分期、分区和个案研究工作。川渝地区拥有全国数量最多的石窟造像地点,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而我们目前对川渝石窟的分期和分区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一般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只对个别石窟寺和区域进行了初步的价值研究。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将39组55处石窟寺列入“川渝石窟寺保护展示工程”规划,这些被列入规划的展示保护工程的典型石窟寺的价值是否能够涵盖川渝石窟寺的整体价值?拟开展的保护、修复和展示工程何以能够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展现川渝石窟寺的价值?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更为细致的分期、分区以及针对个案的价值研究工作,才能妥善解决。由此可见,在遗产价值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川渝石窟价值进行层次化、体系化的研究,是川渝石窟遗产保护的前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川渝石窟寺目前只有大足石刻(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和乐山大佛被列入了世界遗产,还有一些石窟寺也具有世界遗产的潜质,如广元石窟、安岳石窟等。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大足石刻中南宋时期的代表宝顶山石窟,与邻近的四川安岳石刻中的多处石窟寺同属一个体系,可能都属于柳本尊教团的遗迹。毫无疑问,大足与安岳的这些相关的同类石窟寺遗存,如果集合成系列遗产,其价值肯定会高于每个单个石窟寺的价值,也高于这些石窟寺简单相加后的集合价值。然而,在大足和安岳石窟中哪些石窟寺属于安岳-大足柳本尊教团的遗留?大足宝顶山石窟早还是安岳相关石窟早?这些石窟寺如果是赵智凤统一营建的整体,各个石窟的题材关联性及其寓意又是什么?凡此等等,都是川渝石窟柳本尊教团遗迹价值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应该有助于这些石窟今后的保护、管理和展示工作。
[1]李复华,曹丹.乐山汉代崖墓石刻[J].文物,1956(5):61-63.
[2]俞伟超.东汉佛教图像考[J].文物,1980(5):68-77.
[3]吴焯.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与传播途径的考察[J].文物,1992(11):40-50.
[4]宿白.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扎记[J].文物,2004(10):61-71.
[5]刘志远.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M].成都: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8.
[6]袁曙光.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J].文物,1992(2):67-69.
[7]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广元市文物管理所.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M].成都:巴蜀书社,2008.
[8]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广元千佛崖石刻艺术博物馆.广元石窟内容总录.皇泽寺卷[M].成都:巴蜀书社,2014.
[9]胡文和,胡文成.巴蜀佛教雕刻艺术史(中)[M].成都:巴蜀书社,2015.
[10]四川省文物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巴州区文物管理所.巴中石窟内容总录[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绵阳市文物局.绵阳龛窟[C]//四川绵阳古代造像调查研究报告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安美术学院.夹江千佛崖:四川夹江千佛崖古代摩崖造像考古调查报告[R].北京:文物出版社,2012.
[13]雷玉华.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C]//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14]罗炤.隋唐“神僧”与<南诏图传>的梵僧:再谈<南诏图传>对历史的伪造与篡改[M]//艺术史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15]王卫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唐、五代、宋时期西蜀佛教美术发展探源[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150-158,180-191.
[16]梁思成著.西南建筑图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History and Value of Cave Temples and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SUN Xuejing1,SUN Hua2
(1. Chongqing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Chongqing 100054, China; 2.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ic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With briefly summarizing the history of cave temples and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significant values of them, and tries to discuss the importance and deficiency of the heritage value. Building cave temples were start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flourished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nd reached the peak in the Song Dynasty. Caves and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bear a unique and exceptional testimony to the Cave Temple history in China; they initiate a various of new types and motifs in Buddhist art; they bear the most systematic carvings of the Chinese Tantric art; they are outstanding examples of the Chinese Taoist art and exceptional testimonies to the interchange of the "three teachings"; they provide significant information to the world religion study. To systematically and hierarchically explore the values of Cave Temples and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are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basic theory study of Heritage Values, which is of major and immediate significance and lays the groundwork for the heritage conservation.
cave temples and carving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cave temple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y;heritage value;artistic value
K825.4
A
孙雪静(1990-),女,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考古学及艺术史。E- mail:verysx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