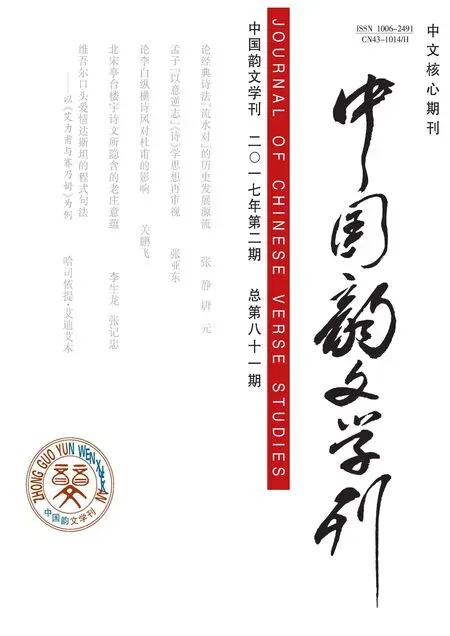北宋亭台楼宇诗文所隐含的老庄意蕴
李生龙 张记忠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北宋亭台楼宇诗文所隐含的老庄意蕴
李生龙 张记忠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北宋时期亭台楼宇诗文很有特色,不少诗文隐含着老庄的理念、情愫与意识。它们或借亭台楼宇寄托道家之政治理想,或借亭台楼宇抒发自己的适性态度,或借亭台楼宇来表达自己的超越意识。适万物之性而适己之性以超越物欲、是非,以此而入人间世,亭台楼宇诗文乃为一个很好的载体。
亭台楼宇;道家;适性;超越
北宋初社会日渐安定,公私都开始大量建造亭台楼宇,大量亭台楼宇的诗文也随之涌现,它们或记叙其筹措缘起,介绍其设施格局,或描绘其风光人文,纪录其交游晏乐,或抒发其览物之情,阐释其人生妙悟。在北宋老庄之学兴盛的文化语境下,不少诗文都彰显出老庄的浸润与沾濡,亭台楼宇之作也是如此,它们或借亭台楼宇寄托道家之政治理想,或借亭台楼宇抒发自己的适性态度,或借亭台楼宇来表达自己的超越意识。分析这类作品,对我们理解北宋老庄之学的渗透之广泛、深刻,亭台楼宇诗文文化内蕴之丰富、复杂有一定意义。
一、借亭台楼宇诗文寄寓道家政治理想
“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孔子和老子有相通之处。不管是儒家的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都是统治者的美好政治理想,王朝建立之初,统治者更多急于成功。这从北宋初的赋作就可见一斑。田锡有《人文化成天下赋》《德合天地赋》,范仲淹有《用天下心为心赋》《圣人之大宝曰位赋》《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君以民为体赋》,王禹偁有《君者以百姓为天赋》《圣人无名赋》等等,这些赋虽多应试之作,却并非一味应景颂圣,而是往往于理想有所寄托,于君主有所厚望。田锡《人文化成天下赋》结云:“今我后功格昊穹,泽流区夏。复风俗于淳古,播咏歌于大雅”,这是以回归风俗淳朴的理想期待当今君主。范仲淹《圣人抱一为天下式赋》开头云:“巍巍圣人,其教如神。抑一而万机无事,抱一而庶汇有伦”,这是以老子的抱一无为对君主有所启发。王禹偁《圣人无名赋》末云:“今我后尚黄老以君临,阐清静以化下,仰徽号于睿圣,扇玄风于华夏。有以见圣无名兮神无功,信大人之造也”,这个“我后”可能是宋太宗。虽然宋太宗并未宣称自己以黄老君临天下,但文人把这种理想“强加”给他,他应该为之窃喜而不会反对。
北宋士人往往融合儒道二者为一,并于描写悠游山水亭台游宴之中寄寓这一理想。曾巩于庆历七年所作的《醒心亭记》,“群山之相环,云烟之相滋,旷野之无穷,草树众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闻,则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也。故即其所以然,而为名取韩子退之《北湖》之诗云。噫,其可谓善取乐于山泉之间,而名之以见其实又善者矣。虽然,公之乐吾能言之,吾君优游而无为于上,吾民给足而无憾于下,天下学者皆为才且良,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乐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曾巩旨在颂扬欧阳修之所以师法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之《北湖》一诗,“闻说游湖棹,寻常到此回。应留醒心处,准拟醉时来”,取名“醒心亭”,实寓“其心洒然而醒,更欲久而忘归”之意;而欧阳之所以能如此久游忘归,实是因为其时君上效法古人无为而治,以致天下太平,人民富足,夷狄鸟兽草木皆得其生养之宜。所谓古人的“无为而治”,既可理解为儒家式的用贤者以致无为,也可理解道家式的与民休息以示无为。前者如何晏注《论语集解·卫灵公》注“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无为而治”,意为通过恭正己身招揽和合理使用人才使政事顺遂,民生安乐,君主无事可做,清闲养寿,实现“无为而治”。曾巩说“天下学者皆为才且良”,就暗寓人才充足之意。儒家还有“以佚道使民”之说,意为为政应得而不害,宽缓不苛,使百姓得以休息。宋人林希作有《佚道使民赋》,程颢也有《南庙试以佚道使民赋》。林赋开头说“古者善政,陶乎庶民。上安行于佚道,下无惮于劳身”,讲的就是这种“无为而治”。后者如《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足,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之“无为”也是使万物生之育之,亭之毒之之道,自然也可以使“夷狄鸟兽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故儒道两者之“无为”并不矛盾,可以相互为用。曾巩说“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意为欧阳修并不只是简单地优游山水,而是在优游的同时也寄寓有对“无为而治”理想的肯定与向往。曾氏以推测的语气言说,但联系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所描绘的山水清和、百姓丰足、官吏无事、太守宴安的景象,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儒道都推崇的“无为而治”理想政治境界。欧阳修有《藏珠于渊赋》,其中说到庄子的“无为而治”理想:“得外篇之《寓言》,述临民之至理。将革纷华于媮俗,复芚愚于赤子。谓非欲以自化,则争心之不起”,对庄子的返朴还淳、无为而治作了精警的揭橥。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创作出《醉翁亭记》这样的名文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如果说欧阳修、曾巩所推崇的“无为而治”理想主要还是以儒家式的得人任贤为主,苏轼则更倾向于道家的“与民休息”的政治理想。其《盖公堂记》云:“吾观夫秦自孝公以来,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镌磨锻炼其民,可谓极矣。萧何、曹参亲见其斫丧之祸,而收其民于百战之余,知其厌苦憔悴无聊,而不可与有为也,是以一切与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参为齐相,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而齐故诸儒以百数,言人人殊,参未知所定。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使人请之。盖公为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推此类具言之,参于是避正堂而舍盖公,用其言而齐大治。其后以其所以治齐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称贤焉。”盖公事迹见《史记·曹相国世家》。《史记·乐毅列传》说黄老派之初祖为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暇公,乐暇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为曹相国师。高密也就是密州。盖公教曹参以“清静”之道治理秦汉动乱的凋敝天下,成就了文景之治,在历史上传为美谈。《盖公堂记》即作于苏氏知密州(神宗熙宁七至九年,1074—1076)时。其时王安石一党(新党)正推行新法,目的在于改良宋代弊政。然新政名目繁多,方田、青苗诸法实际上加重了人民负担,反而变成了扰民病民之举。苏氏多有诗文抨击新法。此文也是针对新政有感而发。他从医病求良药入手,实际上暗示“新政”的扰民病民,引入盖公、曹参等以老子“贵清净而民自定”的理念,要求为政少苛繁之扰攘,使民生得以休息,也是对症下药之意。苏轼平生深受老庄浸润,儒家情结也相当深厚。他也曾力图把老庄同儒学会通起来。其在元丰元年(1078)所作的《庄子祠堂记》中说庄子对孔子“阳挤而阴助之”,就是这一会通理念的结果。对这一理念,后人赞同的、反对的都有,但就苏氏本人的衷曲而言,借记叙庄子祠堂而“回护”评论庄子,力图调和庄子与儒学的矛盾,却是其一贯的思想学术追求。
二、亭台楼宇诗文中所流露的老庄适性情愫

“适性”常常借助非世俗的事物来展示,亭台楼宇自然是最能使人“适性”的事物之一。早在南唐时,徐铉的《游卫氏林亭序》就借游金陵卫氏的林亭表达自己的适性理念:“陶陶孟夏,杲杲初日,虚幌始辟,清风飒然,班荆荫松,琴奕诗酒,登降靡迆,窥临骀荡,熙熙然不知世之与我之为异矣。嗟夫天生万物,贵适其性。君子有屈身以利物,后己而先人,或行道以致时交,或効智以济世用,斯有贵乎自适者也。朝市丘壑,君得中道焉。下官道污智劣,无益于事。山资弗给,归计未从,每寻幽选胜,何远不届,一践兹境,杳然忘归。”北宋初,王禹偁之作《李氏园亭记》,张咏之《春日宴李氏林亭记》也都表达了此种心态,后者云:“人生无贤愚,孰不欲快身于显贵,休思于荣赏。二者,天下之通美。小不适宜,则儒者黜其非道矣。李公之林亭,适宜矣。”张咏感觉李公“适宜” 于显贵和荣赏之中,“外作关劳,内适性情”,乐于林亭草木之宴游。陈尧佐《涵碧桥记》云:“寒山鳞鳞,屏焉四合,澄波瑟瑟,鑑焉中照。倒万象之影,而曲直可见;湛千流之注,而毫发不隐。岂清和所毓之翠,不可以言筌耶?……或曰:‘启塞之说,实有古之训,山水之乐,未达子之志。’曰:‘朝廷有道,区宇无事,能敏其政,又适其性,则斯人也,庶几乎不妄乎?’”此言实为陈公内心真实所感,比徐铉、张咏借他人之事抒己之怀显得更加亲近。在亭台之上往往可以使身心达到清净,张俞《望泯亭记》云:“君子望之则目益加明,形益加静,心益加清”,清净之中乃可造平淡。
政治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从政者往往容易陷入政见分歧、人事矛盾、派系斗争、君臣龃龉,故在官场一帆风顺者少,而遭受打击、迁谪的事情屡见不鲜。这时受挫者往往需要调整心态,安顿心灵。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往往也成了他们心灵的避风港,或借题发挥的话头。例如王禹偁为人正直,遇事敢言,喜欢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颇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弃。晚年贬谪黄州,曾作《三黜赋》以见志,此时之心境应该是很黯淡的。可是其《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却说“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显出一派非常洒落的神态。王氏平生以儒术立身,但于道家也深受濡染。所作《卮言日出赋》《天道如张弓赋》《圣人无名赋》皆能于老庄有所发挥。如《卮言日出赋》云:“故曰不言则齐,同形相禅,巧如簧兮非偶,卒若环兮无变。得之者,毁誉两忘;失之者,是非交战。”对庄子的毁誉两忘有所体会。正因为有此种体会,其作品中所展现的心态才显得那般平和与超脱。
宋庠《诸公留题王氏中隐堂诗序》亦有此意:“每车骑休休,牛酒过家,则必释朝绶而袭野巾,却赤舃以御山履。沔柯阴樾,举觞啸咏,踌躇四顾,为之满志,回睨印绶,若桁杨缰锁之遗,而朝贪其能,愿卒弗果。于时钜公名卿及世之贤者,闻其风而悦之。”虽未必真的归隐,然而心向往之。再如胡宿《高斋记》云:“南中江山,类多托赏之美。……安辑江介,政尚凝简,日多休闲,寄意琴酒之适,留好风泉之赏。……反照正性,保御太和,人境相得,其乐如何哉?……君子根本于道德,拯垫于性命,利用于安身,有余于治人,不役志以营己,常虑心以待物。其有为也,精义致用,以经世务之蕴;及其无事也,恬熙相养,以济天均之和。”以隐士之心入仕,在北宋并非个例。张界《水乐亭记》云:“惟至人全士,淡然有忘情自得之怀,则知以山水之乐为乐也。”“忘情自得”乃不以人之好恶内伤其身,并非真的无情。
北宋士人多有归隐之心,“其中包括对个人物欲、外志的损削”。刘述《题竹阁》云:“闲身方外去,幽意静中来。”在此竹阁之中有利于体悟得世间纷纷物欲之困扰,向上一层,为摆脱物欲提供了条件。穆修《静胜亭记》云:“吾职甚逸,吾性加疏。思得洒然空旷一宇寄适之地,尽粪除耳目俗哗,而休吾心焉。”穆氏在此“洒然空旷”之亭中,得以内视“吾心”。邵雍《秋阁吟》云:“淡泊霜前月,萧疏雨后天。”可见其淡泊寡欲之心态。刘敞《新作石林亭》云:“朝廷入忘返,山林往不还。念无高世姿,聊处可否间。……邱壑成弱丧,簿书常自环。及尔灭闻见,旷如远尘寰。岂敢同避世,庶几善闭关。”在入世之中“灭闻见”“善闭关”,把一己之私欲减至最低,不束缚于物欲,把目光放在天地之道之上。
北宋士人在面对困苦蹉跎之时多能乐观面对之,并对困苦之源有所体悟。李复《登夔州城楼》云:“夔州城高楼崔嵬,浮空绕槛云徘徊。百川东会大江出,群山中断三峡开。关塞最与荆楚近,舟帆远自吴越来。雄心乘险争割据,功业俯仰归尘埃。”名利非可持久之物,其得与失不可长挂胸中,亦不可为此徒增烦恼,这并非是消极无所作为的表现,而是庄子“天地与我并生”思想的引发。北宋一部分士人的名利观往往表现出一种人生进程的演变,少年之时往往极具建功立业之思,中年以后则视名利为畏途,洒然而乐;或者仕途上稍有坎坷即具隐逸之思;或者秉承老庄之思,自幼年即心归于隐逸。这在亭台楼阁诗文之中有一定的反映。范仲淹早年以建功立名为人生之目标。其《近名论》甚至批判老庄:“《老子》曰:‘名与身孰亲’,《庄子》曰‘为善无近名’,此皆道家之训,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斯人之徒,非爵禄可加,赏罚可动,岂为国家之用哉!”从政治学的角度说,名是刺激士人进取的兴奋剂,不受名利诱惑的人往往也不受政治牢笼。然而,范氏认为不受名利诱惑的人有时也可能是大有益于天下的人。其《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称赞不受汉光武帝羁络的隐士严光说:“唯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是有大功于名教也”。主持新政失败之时所作之《岳阳楼记》却对名利更有所淡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政治失意而悲慨,也并不由此而忘记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氏这种人生态度表面上禀承儒家,实则兼老庄而为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一种老庄式的超越境界,唯有此境界的人,才能物我兼忘,进入到老子所说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的境界。故范氏《用天下心为心赋》说:“赜老氏之旨,无欲者观道妙于域中;稽夫子(孔子)之文,虚受者感人和于天下。若然,则其化也广,其智也深。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达彼群情,侔天地之化育;洞无民隐,配日月之照临。”其道儒结合之迹,昭然可见。
三、亭台楼宇诗文中所昭显的老庄超越意识
亭台楼阁诗文中最能体现超越感的莫过于围绕超然台所作的一批作品。细绎这些作品,可以看到老庄的超越意识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
据苏辙《超然台赋序》说,此亭建于苏轼知密州时(熙宁七至九年),其命名出于《老子》:“顾居处隐陋,无以自放,乃因其城上之废台而增葺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辙曰:‘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老子》曰:‘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尝试以‘超然’命之,可乎?”故所谓“超然”,实是取超越世俗之是非、名利、荣辱,而求其内心之闲晏平和、超脱洒落。苏辙是《老子》专家,苏轼是《庄子》专家,兄弟俩意趣相投,苏轼自然同意了弟弟的建议,将此台取名“超然”,并作《超然台记》以阐发“超然”的内蕴。
在苏轼看来,人的心态如何,与自己的观物角度有莫大关系。如果从事物的内部甚至低处观察事物,就会使自己产生压抑、窘迫之感,产生眩乱反复、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的可悲后果。所以要想超然,就必须站在高处、外面来静观事物,使自己产生超越感,从而获得愉悦、获得美的享受。这就像他的《题西林壁》所说的那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站在庐山内看庐山,就只能眩乱反复;如果跳出庐山来反观庐山,就能欣赏那“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姿多态的美景了。苏轼的这种感悟,既从庄子中得来而又独有所悟。《庄子·则阳》载戴晋人嘲笑魏齐之争如蛮触二国之厮杀,就是站在“上下四方有穷乎”这样的高视角来立论的;在《逍遥游》中,大鹏抟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高空,回视人间,什么斥鷃啦、学鸠啦,各种讥讽嘲笑,它都不予理会。苏轼的观物方法深得庄子神髓。就现实而言,苏轼来知密州本来就是政治上受新党排挤的结果,其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苏轼自己生活也颇艰苦,“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这种状况,其内心不说是苦,至少应该是“不乐”的。但由于苏氏有这么一套观物方法,竟体验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餔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的快乐心经。苏轼的这一套,不独用于密州,也用于一生,他一生遭受打击不断,却直到哪里乐到哪里。他总能从当地、从生活中发现美的事物,找到美感,从而形成自己“无往而不乐”的独特审美体验。有了这种审美体验,就很容易转化成诗。苏氏有《望江南·超然台作》曰:“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正因为超然,所以触目皆春,与物无忤,诗酒新茶亦可以趁年华,度日月。解脱于是非之场,超越于荣辱之境,则何处不可安歇,何处不可为乐,“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在《记游松风亭》有云:“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正是“超然”注脚。
苏辙的《超然台赋》把老子的超然、庄子的达观和儒者的乐易以及楚辞的忧愤镕铸一体,虽然不像其兄那样具有个人之独特体验,却也是有思而发,有感而作,有病而吟:“嗟人生之漂摇兮,寄流枿于海壖。苟所遇而皆得兮,遑既择而后安。彼世俗之私已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诚达观之无不可兮,又何有于忧患。顾游宦之迫隘兮,常勤苦以终年。盍求乐于一醉兮,灭膏火之焚煎。……惟所往而乐易兮,此其所以为超然者邪。”乐牛说苏辙命台为“超然”,“以《超然台赋》劝诫其兄不要转入纷争,要超然于纷争;不要因三年不得代而忧愁,而要超然于自我”,后一种意思容或有之,但劝其兄不要转入纷争的意思却很难看出。苏辙名台为“超然”,显然有以“超然”兄弟共勉之意,而兄弟之“超然”,正是为了有异于世俗之辈的争竞与自私,故赋中有“彼世俗之私己兮,每自予于曲全,中变溃而失故兮,有惊悼而汍澜”等语。对苏辙的这篇赋,苏轼十分称道:“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气体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万为可贵也。”说弟弟之作精确高妙,并非勉词,而是合乎实际的评议。
除苏辙外,文同、鲜于侁、张耒、李清臣都有《超然台赋》,可能都是苏轼邀约他们所作。文同是个颇具艺术气质的人,其赋作也想落天外、高蹈出尘,不仅有老庄脱俗之玄想,还有《远游》《大人》出世之仙心。其末曰:“使余脱乱天之罔兮,解逆物之韁。已而释然兮,出有累之场。余复仙仙兮,来归故乡。”苏轼评论说:“吾友文与可,非今世之人也,古之人也;其文非今之文也,古之文也。其为《超然》辞,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其《远游》《大人》之流乎?”就是将此赋比作屈原《远游》和司马相如《大人赋》,肯定超然物外、高迈洒落之人生品格。鲜于侁赋多用庄子、楚骚语,如:“蜉蝣之生兮,蟪蛄之年,朝菌晔煜兮,舜华鲜鲜。蛮触之角兮,醢鸡之天。佳人兮奈何,道不可流人兮,时不再来。聊逍遥兮自得,与日月兮同存。”表达一种人生短暂、时不可再的人生慨叹和追求超然的必然。
张耒赋采用对问方式,假设“或有疑乎超然”者对苏氏兄弟以“超然”命名其台提出质疑,以反驳名超然者未必真超然为主旨,指出“彼方自以为超然而乐之,则是其心未免夫有累也”。意思是说,自称“超然”的人未必真的就超然,其实他们的内心牵累众多,说自己“超然”只是掩饰其不超然。“客”(即作者自己)反驳说:“子知至乐之无名兮,是未知世之所可恶。世方奔走于物外兮,盖或致死而不顾。眇如醯鸡之舞瓮兮,又似乎青蝇之集污。众皆旁视而笑兮,彼独守而不能去。较此乐超然兮,谓孰贤而孰愚?何善恶之足较兮,固天渊之异区。道不可以直至兮,终冥合乎自然。子又安知夫名超然者,果不能造至乐之渊乎?”这是说,“超然”是相对的,相对于那些如醯鸡舞瓮,如青蝇集臭的卑污小人,追求超然的人与他们何啻天壤之别。追求超然虽暂时未必真已超然无累,但怎知他们最终不能达到真正超然的最高境界呢?这似乎是在为苏氏兄弟辩护,通过维护“超然”来肯定超然的可贵。
李清臣是一个比较有独立精神的人。他为人宽洪,跟苏氏兄弟交好,对旧党有所同情,执政时对新党的一些举措也颇多施行。在五篇《超然台赋》中,李清臣虽然也以老庄理念为主轴,如云“余宏望而独得,思浩渺而难传。轶昊气而与之游,遗事物之羁缠。嗤荣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烦煎。万有不接吾之心术兮,味《逍遥》之陈篇”,即是以庄子之逍遥相砥励。但下文“蛾眉弗以为侍兮”至“斥醪醴而不御,尘芳茶以漱泉”云云,是说苏氏为了体现自己的“超然”,对世俗的一切都予以否定,似乎是为了超然而超然。结尾“系曰:世处甘处,我以为患兮。物皆谓危,己所安兮。非彼所争,为乐不愆兮。佩玉袭绶,得《考槃》兮”,末句《考槃》为《诗经·卫风》中篇名。毛序:“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退而穷处。”可知此篇乃隐士之作。李清臣说苏氏“佩玉袭绶”而得《考槃》,实有微讽其为了反对世俗而否定世俗的一切,就像做着官却吟唱着隐士的诗篇一样,不说是假隐,至少也是朝隐、吏隐之类。对此,苏轼有跋为自己和弟弟辩护:“世之所乐,吾亦乐之,子由其独能免乎?以为彻弦而听鸣琴,却酒而御芳茶,犹未离乎声,味也。是故即世之所乐,而得超然,此古之达者所难,吾与子由其敢谓能尔矣乎?邦直之言,可谓善自持者矣。”这是说,从世俗之乐中达到超然,即使古之哲人也难以做到。自己和弟弟又怎敢说自己就能做到呢?李清臣的说法,可算是善于坚持自己的看法了。
[1] 曾枣庄,等.全宋文[M].成都:巴蜀书社,1988.
[2] 〔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M].李勇先,王蓉贵,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3]〔宋〕王禹偁.王黄州小畜集[M].宋绍兴刻本.
[4]〔宋〕曾巩.曾巩集[M].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5] 〔唐〕韩愈.韩昌黎诗系年集释[M].钱仲联,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6] 程树德.论语集释[M].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楼宇烈.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 〔宋〕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9] 〔宋〕苏轼.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郭象.南华真经注疏[M].成玄英,疏.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陈伯君.阮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2]俞绍初,张亚新,校注.江淹集校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13]傅璇琮,等.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4]〔宋〕苏辙.栾城集[M].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5]邹同庆,王宗堂,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6] 乐牛.苏辙《超然台赋》赏析[J].名作欣赏,1989(3).
[17]〔宋〕张耒.张耒集[M].李逸安,孙通海,傅信,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
责任编辑 李剑波
2016-09-28
李生龙(1954— )男,湖南祁东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张记忠(1977— ),男,河南中牟人,博士生。
I207.2
A
1006-2491(2017)02-00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