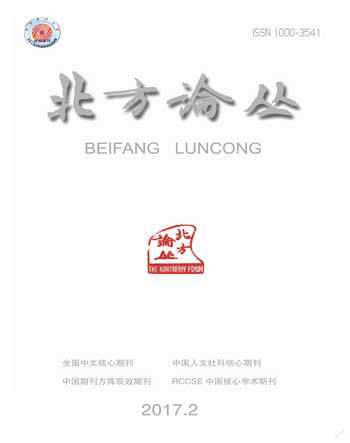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嬗变
肖海薇


[摘要]清末民初的演说意识受益于福泽谕吉倡导的“著书立说”主张影响,与英文Speech语义翻译有直接关系。此种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引进,而是词义的辨析。演说意识的嬗变对中国近代白话文学倾向和报章“新文体”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演说
[中图分类号]K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39-05
演说是清末民初的一个热点词,在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态中频繁现身,其频繁使用程度和人们的重视程度,此前没有,此后恐怕也不会再有了。演说的勃兴和引起的热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特定文化倾向的标记。在有关当时的戏剧、小说研究中,常有学者以演说为切入口进行专门探讨,多有创见[1];但对演说意识的嬗变和现代语义生成等进行具体研究,还显得有些薄弱。本文拟以此为出发点,对演说在清末民初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上怎样从古今中外的意识碰撞中逐渐被人识别、体认,以及接纳和影响等做一些具体辨析。
一
演说一词,中国古代早已存在,一般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引申阐述”,二是指“讲说”。比如,“下文更将此九类而演说之”,其中的“演说”就是“引申阐述”之意;而 “随汝所问,我当为汝一一演说”,指的则是“讲说”[2]。但就总体而言,古代汉语中的演说,还不是一个意义凝固的词,它的语义来自“演”与“说”两个词意义的叠加。《汉语大字典》解释:“演,长流也。一曰水名。从水,寅声。”段玉裁注:“演之言,引也,故为长远之流。”《说文》上称:“说,释也,从言,兑声。一曰谈说。”段注云:“说释者,开解之意。”由此可见,“通过语流进行引申、铺陈、解说”是演说词义的基本由来[3]。
“演”与“说”的“引申阐说”之意,在两汉佛教传入中土时,意向显得更为切实,结构也更加稳固。佛家说经“必须说理明达有据,辞义清晰易辨,必要时须用手势或姿态加以辅助说明”,此亦被称为演说[4]。自从演说披上袈裟,作为梵语nirdes/a和巴利语niddesa的汉译后,就成为中古时期一个常用词。对此,赵朴初有较为具体的说明:
高僧说法,也称“演说”。如《晋书·姚兴载记上》记载:后秦国主姚兴曾率众沙门至逍遥园澄玄堂去恭听当时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演说佛经”。僧人讲经蔚然成风,逐渐面向社会大众,又形成了一种通俗的讲经方式——“俗讲”。后演化成就某一个专门问题向广大听众发表见解,阐明事理,称为“演说”。[5]
那么,中国近代演说意识的崛起,是不是对“阐述”“解说”和“说法”“俗讲”理路的直接承袭呢?恐怕并不这样简单。因为从“演”与“说”的古义,到俗讲意识的形成,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演说意念始终与“解释”“说明”联系更紧密,意义更侧重于“说”。比如近代民间艺人表演说唱时,亦可称为演说。《老残游记》第二回:“这说鼓书本是山东乡下的土调,用一面鼓,两片梨花简,名叫‘梨花大鼓,演说些前人的故事。”[5]说鼓书就是说书,“演说”用在这里,本意在于说明说鼓书是一种什么样的艺术形式。这样的演说意念与清末民初崛起并被普遍接受的那种为推进某种社会意图而采取的宣教手段还有一些差别,也与我们要研究的演说意识有一定距离。问题不在于演说“前人的故事”,还是演说“现实的故事”,而在于“演说”是否可以独立存在,用“演说”做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演说意识的崛起是与外来影响有关系的,特别是与近代日本演说意识的介绍有直接关联。
明治维新时期,演说在日本风行一时。那么,日本是如何理解演说的词义的?《大汉和辞典》做出如下解释:
演説,①道理や意見等をのべておくこと。《書·洪範九夀·疏》更将此九类而演説(周書熊安生传)一一演説。(古杭夢遊録)说话有四家:说经,谓演説佛書。②公衆の前に立って意見を述べること。主義、主張等を吐露して衆人に聞かせること。演舌。[6]
显然,《大汉和辞典》演说词条的第一个义项,照抄照搬《词源》中的引例。“《大汉和》所收的汉字,以我国《康熙字典》为主要依据,并参照了《说文解字》《玉篇》《广韵》《集韵》《字汇》《正字通》《中华大字典》等字数和韵书”,“所收词目主要是作者直接从我国的经史子集中收录的,同时也参考了我国的《辞源》《辞通》《辞海》《国语辞典》等著名辞书”[7]。毫无疑问,在“以中国为师”的古代日本,“演说”的“能指”(词形)是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问题是作为它的“所指”(意义)究竟什么时候传入日本?又是否如《大汉和辞典》解释的那样完全照抄照搬中国古代演说的意涵呢?据沈国威(2008年)研究,在中日两国文化交往中,“日译汉”最活跃时期是16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二百多年间,又可以细分为两期:第一期是耶稣会创制的新词、译词,它们主要通过他们的译述和同时代的中国士子的著述(即前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为日语所吸收。第二期可以从1807年新传教士马礼逊登陆广州算起,新教传教士创制的新词、译词,主要通过汉译西书、英华辞典等(即后期汉译西书)传入日本”[8]。虽然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演说”的“能指”具体以何种文本形式传入日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早在江户时代(1600—1867年),“演说”这个词语就已为日本汉学家所使用了。尽管近代之初,日语流行的演说词义与中国古代演说词义区别不大,但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特别是在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下,演说的社会价值却被重新发现,或者说是被赋予新意涵。这也就是说,在中日两国文化语境中,尽管演说的“能指”差别不大,但“所指”却大有不同。学界一般认为,日本文化背景中的“演说”新意获取“与福泽谕吉有关”。日本学者杉本っとむ认为:“因福泽谕吉而有名的词语有‘演说以及‘接吻、‘裁判所。这些词全部都是江户兰学者和长崎翻译家们苦心创造的新词。”[9]之所以称“演说”为新词,不仅因为它特殊的“汉语词”身份,還在于福泽谕吉对它的语义做出新的诠释。在1872年(明治五年)发表的《劝学篇》第十二篇《论提倡演说》中,他这样说:
演说一语,英文叫作“Speech”,就是集合许多人讲话,即席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他们听的一种方法。[10]
在文章中,他还进一步补充说:
我国自古没有听说有过这种方法,只有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在西洋各国,演说极为盛行,上自政府的议院、学者的集会、商人的公司、市民的集聚,下至冠婚丧祭、开店开业等琐细的事情,只要有十个人以上集合在一起,就一定有人说明集会的主旨,或发表个人生平的见解,或叙述当时的感想,养成当众发表意见的风气。这种方法的重要性,实已无待赘言。例如现在世界上有所谓议院之说,议院开会时,如不先有讲演的方法,则虽有议院,也不能起到什么作用。[10]
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福泽谕吉所说的“演说”,是英文Speech的翻译,“演说”只是借用汉语的字形而已。虽然“寺院里的说法和演说差不多”,但它已不是“说法”“讲经”“阐发”“解说”等所能概括的,它已成为日本明治时期集会、议事的重要手段,“说明主旨”“发表见解”“叙述感想”才是它现代的意向所在。福泽谕吉不仅用汉语词“演说”翻译英文 speech,还身体力行将这一新见解和新主张付诸实践。1858年,他在江户时代一所规模很小的传播西洋自然科学的“兰学塾”的基础上创建庆应义塾大学。1863年,他又把“兰学塾”变为用英语研究西洋文化的“英学塾”,1868年命名为庆应义塾大学。1875年,他创建“三田演说馆”,率先开启日本演说西方学术的新风气。在《劝学篇》中,他反复强调,学者“须博览群书,著书立说,与人交谈,或发表意见”,“借交谈交换知识,并以著书和演说为传播知识的方法”[10]。在福泽谕吉的倡导下,这种演说风气在日本骤然兴起,并在社会各个领域引起巨大反响。
很显然,清末民初在中国得到士绅首肯的演说风潮,受益于福泽谕吉的启示,是英文Speech的语义翻译和“著书立说”意识影响所致。此种演说意识挣脱以往街谈巷议意识的羁绊,一跃而成为时代意识的翘楚。
二
对于清末民初演说意识的崛起,陈平原认为得风气之先者是 “明治思想家福泽谕吉;而近代中国演说风气的形成,则康梁师徒大有贡献”[1]。确实如此,“演说”的“出口转内销”,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有直接关系。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曾与日本“宪政之神”犬养毅,以及“西学先锋”福泽谕吉私交甚密,并对他们的维新变革主张推崇有加,这对他日后形成的变革中国社会的思想多有影响。在《文明普及之法》中,梁启超直言不讳,几乎重述福泽谕吉的观点:
犬养木堂语余曰:“日本维新以来,文明普及之法有三:一曰学校,二曰报纸,三曰演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日本演说之风创于福泽谕吉氏。(按:福泽谕吉氏日本西学第一先锋也,为一时之泰斗。)在其所设庆应义塾开之当时自为怪物云。此后有嘤鸣社者,专以演说为事,风气既开。今日凡有聚会,无不演说者矣。虽至数人相集?饮,亦必有起演者。斯实助文明进化一大力也。[11]
对于“‘演说的新观念源于日本”,晚清新闻媒体亦多有评述。《申报》1903年9月17日《演说篇》认为:“演说盖取法东瀛也,盖欲法东瀛人士之演说以启迪我华人也。”《申报》1903年8月31日在《记客述浦左演说肇祸事》中说得似乎更加具体:“古无演说之名,自北周令熊安生至宾馆演说《周礼》,咸究根本,演说二字始见于史书。日本师之,凡举一事,必先当众演说,以发明其意旨。中国拳匪乱后,朝廷百度惟新,诏下各省有志少年,赴日本留学,归则凡事醉心日本,日以演说鼓动人心,其沪上之演说于张氏味莼园者为最著名,大抵科诨兼施无殊演剧,笑骂交作,有类说书。”[12]虽然“演说二字始见于史书”“日本师之”的说法,不排除是文人掉书袋、“老子曾经阔”的意识反应,但“演说”一词在清末逆输回国也是事实。怎样让古已有之的“演说”脱去旧时衣冠,换上时代新装,在中国比之于日本,不能不多一些周折。如果说在日本,新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经由新词语的译介而达成;那么在中国,新演说意识的形成,首先不是词语的译介,而是词义的辨析。
通过检索《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我们发现,“演说”一词最早出现在1896年《时务报》古城贞吉翻译的“东文报译”上,标题是《英前相虞翁演说(译日本新报西十月廿一日)》。古城贞吉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他曾“主持‘东文报译栏目56册(期),发表译文600多篇,共计34万余字”[13]。在“东文报译”和“英文报译”两个栏目上,古城贞吉共翻译10篇演说文。这些演说文基本上是世界政治情形和商业情形的介绍,演说者均是英、美、德、日等国的国王、首脑、大臣或名士。从演说文的标题上,我们看到“演说”有从动词向名词转化的趋向。如“英相演说筹画中国情形”(《时务报》1898年第58期),“新报主笔某君演说俄国情形”(《时务报》1898年第60期),“大隈伯演说于商业公所”(《时务报》1897年30期)等,这些“演说”都是被当作动词使用的,而且可以带宾语或补语。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演说”,不管是演说佛经还是演说故事,“演说”也从来都是被当作动词使用的,如果仅从这一点来分析,古代的“演说”与现代的“新演说”还真的难以区分。但在古城贞吉翻译的演说文中,我们还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演说”是被当作名词来使用的。如“英前相虞翁演说”“德皇演说”“理财学会演说”“美国总统演说”“英国殖民大臣演说”等。在这里,“演说”虽然还留有动词的意味,但却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名词化倾向,“演说”不再仅指代一种动作、一种行为,而且可以指代一种事物、一种现象。我们在前文已指出,当“新演说”从日本“出口转内销”时,尽管“能指”基本相同,但“所指”却不完全一样。当初人们主要想表达的是用“演说”做什么,后来人们意识到“演说”还可以是什么。当人们把“演说”做动词使用时,是一种社会行为;当人们把“演说”做名词使用时,则是一种新文体(有关问题在下文讨论),这种名词化的演说,在清末民初代表的是一种新事物,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时演说意念的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在中国古代没有,在中国当代也不多见,却是清末民初的一道独特风景。
1905年,一篇《论某省改宣讲为演说之宜仿行》的文章,还讲到圣谕宣讲与演说的关系问题:
吾国从来虽无演说之实,己非无演说之名。定律地方官,每逢朔望,尝有宣读圣谕、讲述律例者,至今虽早视为具文,而各地善堂之讲演善书,至今犹遵奉。若旧其意,无非补教育之不及。举乡愚、村民而尽引之使善,则犹演说之旨也。其所以裨益治化者,寗谓浅鲜。昔法自当效法之,而仿则之者也,而胡为不以彼易此,成斯莫大之美举。
今者某省绅士,禀请大吏,将宣讲改为演说。每当人登坛,环而观者数十百人。风气之开,吾知其有勃然者矣。夫自西国文化东渐我沿海各省,当其衡演说之功,人莫不心知而发挥之。[14]
“今者某省绅士,禀请大吏,将宣讲改为演说”,“胡为不以彼易此,成斯莫大之美举”,道出人们希望以演说代替宣讲的冀望。虽然宣讲和演说同为教化的手段,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古代宣讲的内容和方式都已经落伍。宣讲无非“讲圣谕”“讲律例”“讲善书”,内容乏陈;而演说则与时俱进,涉及许多新事物、新思想,是一种新风尚、新形式。“从宣讲到演说,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时代蜕变的痕迹,一方面可以看出新生事物、现象的根苗”[15]。
在中国近代社会,人们在使用“演说”这一概念时,还常常与“讲演”“演讲”混用。笔者分别以“演说”“讲演”“演讲”为关键词,对《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1833—1911)》,以及《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1911—1949)》进行检索,得出图1图2图3。
从图1图2图3我们得知,“演说”“演讲”“讲演”等三个词,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语境中有一个不断嬗变和筛选的过程。自“演说”在1896年现身《时务报》到1911年之前,是其使用频率最高时期,而后逐年下降,但“讲演”和“演讲”则逐年上升。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关于“演说”“讲演”“演讲”的词义辨析透露出原委:
演讲/演说辨析
同,都是动词,都有就某个问题发表讲话的意思。
异,词义范围大小不同。“演讲”还有对听众讲述、讲解某一事物的知识的意思。“演说”没有这种意思。
讲演/演讲辨析
都是动词,都表示讲述推演的意思。二者词义极为接近,常可换用。
异,对象。“讲演”可以用作讲述知识方面,也可用在推演见解方面;“演讲”多用于推演见解方面。[16]
“讲演”“演讲”的主旨在于“讲述知识”“推演见解”;而“演说”却“没有这种意思,它只在就某个问题发表讲话”。“讲述知识”“推演见解”与古代“演说”的含义颇为接近,“就某个问题发表讲话”却是清末民初新演说的身份象征。这些告诉我们:清末民初崛起的演说意识与古代的演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当这种新演说意识蜕蛹化蝶以后,原本与其相关的词义则被人改用“演讲”“讲演”去称谓了。1950—2014年的报刊索引显示,“演说”“演讲”“讲演”等三个词的使用量,“演讲”占压倒性多数的56%,“讲演”占19%,“演说”占25%,从中也可证明我们在前文中所说的“演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清末民初特定文化倾向标记之说不妄。
三
演说意识的崛起,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倾向的反应,给中国现代文化变革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利用演说“说明主旨”“发表见解”“叙述感想”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作为“著书立说”的手段,“演说名词化”给中国现代文化变迁带来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在进行启蒙主义宣传时,始终要面对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意见主张恰当准确地传递给普通民众的问题。所谓“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就是基于这一现实才提出来的。这也就是说演说意识的崛起,部分原因也与通俗宣教意识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说,演说意识有天然的白话倾向。1901年发行的《杭州白话报》在提到 “开通民智的办法”时强调,演说“如同《圣谕广训》一般,把中国外国古来的事,现在的事,到城里乡下,各处去讲,并且要学外国教会送书的法子,把孔夫子的书演成白话,钉成薄薄的小本子,不取分文,送把人看,是第二等妙法”[17]。这里不仅告诉人们什么是演说,还告诉人们怎样去演说,即“把孔夫子的书演成白话”。其实,它所说的“孔夫子的书”大半也是文言演成白话的意识反应,泛指“主旨”“见解”“感想”而已。正因为如此,当演说意识崛起时,白话文和白话报刊也风行一时。因为“白话报纸之在社会,得其一而失之九,遗憾尤多。济白话之穷,舍演说莫为力也。演说者,又白话之先锋也”[18]。于是,纷纷有人提倡“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日本文明开进之速度,半资报章,半资演说。上自朝廷内政……资生日用之微,无不由报纸握其枢,演说尽其力[18]。“从现有资料来看,我们知道早在1897年,就出现两份白话报,到1900年以后,数量开始急遽增加。根据统计,从1900到1911年间,共出版111种白话报”[19]。而我们知道,此时恰恰是演说意识崛起的井喷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演说与白话内在倾向的一致。二者可谓一体两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演说的风行同時带来白话文倾向的抬头。
当把在大庭广众面前的演说题旨,挪移到报纸杂志上发表时,还启动人们文章意识的蜕变。在清末民初的中国语境中,一方面这些“叙述、解释”总是要变成白话讲述;另一方面,这些“叙述、解释”总是要写成文字发表,所以一种新的“演义文体”逐渐走入人们的视线。创刊于1897年11月7日的《演义白话报》,是最早的一批以白话命名的报纸,且每期都刊载长篇连载白话演义体《通商原委演义》,用白话的方式讲述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归附清王朝以来,经鸦片战争乃至甲午战败割让台湾的整个历史过程。这种“演义体”的历史言说与后来的中国白话小说,特别是白话历史小说到底有什么文体上的联系,还需要进行专门研究;但它无疑是中国现代最早用白话讲述的故事。在中国近代,白话演义体叙事意识在文学中广有影响。“比如,在这个时期的白话文字上,我们时常看到‘给各位演说一段白话文字看看之类的句子,写这些白话文的人,显然是把白话和传统说书之类的通俗文字一体看待。白话文就好像演唱者的底本或唱本,可以做表演讲说的底稿”[15]。晚清白话小说在用语和文体意识上多有演说的痕迹,可谓渊源有自。
前文我们已指出,古城贞吉在《东文报譯》上发表的“译文”中,有大约半数的“演说”是名词化的。这种名词化的演说,在大庭广众面前实现出来是一种社会行为,在报纸杂志中呈现出来就可能是一种“新文体”。梁启超在鼓吹演说时不遗余力,他的新文体文章更是风靡一时。梁启超是《时务报》的主笔,它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平易畅达,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20]。而大凡这样的文章都有非常浓厚的演说痕迹,比如,为人们所熟知的那段《变法通议》: “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也。”[21]正统桐城派古文家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只有惯于演说者才不会感到这些文字有什么拖沓的毛病,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平易畅达”的目的,才能有一种感人的“魔力”。这样的文章“惊醒了许多人的迷梦”[22](p50),引领一批时代才俊接踵而起,文风为之一变。追根究底,这种新文体是与演说的倡导和演说意识的流行有关的,看一看陈天华的《狮子吼》:“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23](p59)这不是演说的口吻吗?反过来说不正是演说意识的崛起,才催促这样的新文体的诞生吗?
至于演说中“科诨兼施无殊演剧,笑骂交作,有类说书”的倾向[12],以及这种倾向给中国近现代小说、戏剧体式带来的影响,学界已多有探讨,兹不赘。本文只是进一步提示人们,演说意识在清末民初的崛起,已渗透到社会变革的不同领域,除了其明确的社会变革意识以外,还在多个层面影响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变革。探讨“演说”词义的嬗变和演说意识的崛起,可以让我们从多个视角去再次窥探近现代之交的中国文化转型。
[参考文献]
[1]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J].文学评论,2007(3)
[2]辞源:修订版[K]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汉语大字典[K]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10
[4]丁福保佛学大词典[K]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
[5]赵朴初俗语佛源[M]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6][日]诸桥辙次大汉和辞典·卷七[K]大修馆书店,1986
[7]于家齐,徐永真献身《大汉和辞典》的诸桥辙次[J]辞书研究,1982(4)
[8]沈国威汉语的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兼论现代汉语词汇体系的形成[J]南开语言学刊,2008(1)
[9][日]杉本っとむことばの文化史 ——日本語の起源から現代語まで[M]桜榥社,1985
[10][日]福泽谕吉劝学篇:第十二篇·论提倡演说[M]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梁启超文明普及之法[C]//清议报全编:第二十卷
[12]记客述浦左演说肇祸事[N]申报,1903-08-31
[13]陈一容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论略[J]历史研究,2010(1)
[14]论某省改宣讲为演说之宜仿行[N]广益丛报,1905(83)
[15]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16]周行健,于慧邦,杨兴发现代汉语规范用法大词典[K]北京:学苑出版社,1995
[17]杭州白话报:序[N]北京新闻汇报,1901-05
[18]论政府宜利用报馆并推广白话演说[J].东方杂志,1905(8)
[19]蔡乐苏清末民初的一百七十余种白话报刊[C]//丁守和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2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21]梁启超变法通议·论不变法之害[N]时务报:第2册,1896
[22]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23]陈天华警世钟·猛回头[M]罗炳良主编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讲师,博士研究生)[责任编辑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