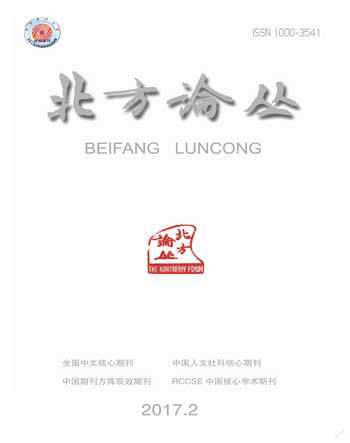冯其庸先生与《北方论丛》的“红楼梦研究”专栏
曹立波
[摘要]1981年春,冯其庸先生在《北方论丛》发表了《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长文,围绕这篇文章的撰写、投稿和几番修订,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4月,冯其庸先生亲笔草书给《北方论丛》责编夏麟书写去9封书信。本文真实再现了信函原文,书信往来之间,反映出冯其庸先生作为一位中国红学会的负责人,对红学事业的执着;作为一位专家,对著书立说的严谨;作为一名编辑,对业内同行的体贴。9封书信的字里行间,传达出新时期红学的历史风貌,记录了《北方论丛》的“红楼梦专栏”在当时的影响。
[关键词] 冯其庸;红学;信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7)02-0022-07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伊始,红学研究基地除了《红楼梦学刊》等专门性的刊物,还有以《北方论丛》为代表的高校学报。1979年《北方论丛》刚一开设《红楼梦》研究专栏,就连续发表了戴不凡先生的《揭开红楼梦作者之谜》《石兄和曹雪芹》两篇文章,在红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著作权问题的热烈讨论。可以说,《北方论丛》的“红楼梦研究”专栏,是当时京城之外最有影响的红学论坛①。这个栏目的负责人是夏麟书先生,他曾主持将相关论文编辑成《红楼梦著作权论证集》。夏先生已于2001年9月仙逝,作为他的亲属,在整理遗稿时,笔者发现在其保留的书信中,有一些冯其庸先生的亲笔信,辑录并研读书信的内容,能够切实感受到在80年代初期,冯先生对《红楼梦》事业的投入和支持。
1981年春,冯其庸先生在《北方论丛》发表一篇论文,题为《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②,围绕这篇文章的撰写、投稿和几番修订,从1980年11月到1981年4月,冯先生给《北方论丛》的夏麟书责编写去9封书信。以下是这些信函的电子文本③:
第一封信:1980年11月8日
麟书、文源同志:
来信收到,我的文章刚写了一部分,就被一连串的会议打断了。现在离十五号只有几天了,眼看会议还不断,怕耽误刊物的出版,请速安排别的文章,我这篇文章写完后一定交您们处理,估计第二期用是不会有问题的。出版社那面如来不及,只好不用这篇文章了,免得耽误您们的出书。
又复印《红楼梦》的事,价钱已问到,大约复印下来要二千多元,其他装订费用都还不算在内。所以我觉得太不合算了。我们当时复印是因为要校书,无此工作不能进行。将来影印本和汇校本陆续出来,这种复印本就无意义了。所以我也觉得还是不印好。当然如果有必要印的话是一定会代办的,只要您们来信好了。
请问国良。“良”应为“梁”,指李国梁,曾任黑龙江省红楼梦学会会长、哈尔滨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北方论丛》编辑部主编,冯其庸先生每封信都向李国梁问好。及其他同志好。匆致
敬礼!
冯其庸
十一月八日
这封信所用信笺的抬头写有红色的“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字样。信的内容交代了投稿的缘起,即《北方论丛》的约稿,得到了冯先生的积极支持。从“一连串的会议”不断的工作状态可见,他在百忙中积极支持《北方论丛》的红学专栏。书信里还传达了一个历史信息,即红楼梦研究所的《红楼梦》校订本1981年的时候尚在进行中。针对《红楼梦》古本的复印问题,冯先生对待红学同好的坦诚和热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第二封信:1981年1月10日
麟书同志、编辑部其他同志:
您们好。前属写稿,直到今日才脱稿,已去复印,共五部分,约三万余字,简目另附。不知能发否?如有困难(篇幅太大),我就不寄来了,如不增加您们负担,则当遵属寄来。匆致
敬礼!
冯其庸
一月十日
信纸上眉批:麟书同志请告知出版社是否要将此文收进去,如要,我当另寄稿去。又及。
待复:
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冯其庸
目录
引言
一、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
二、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的一些意见
三、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分工问题
四、关于考证
五、关于思想和艺术研究
结语
这封信所用信笺的红色抬头写着“中国人民大学”,不久前冯其庸先生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主持《红楼梦》研究工作。联系上一封信可知,冯先生信守承诺,“遵嘱”迅速完稿,并在投稿之前写了一封信,寄上长文的写作提纲。
第三封信:1981年1月17日
麟书同志:
来信收到。原拟打印出清稿后再寄去,现在只好把复印的原稿寄上了,如实在不好排,就算了。因要请人抄一遍,说起码要十天,还要自己校对,时间耽误太久。所以,实在无法,竟将这样乱糟糟的稿子寄去,心理有所不安。我这里已发去打印,将来打印出清稿后,再寄去你校对用,大概能来得及。这篇文章原是去年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要我写的,因问题太多,写得过长,所以没有送给《人民日报》。头二节的内容,就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写的,现在似乎正合适,因此希望能赶在第二期发,太晚了,就不大好。排出后请能寄我校一次,以免出错。增加您们不少麻烦,谢谢。
我在本月廿一日可能要到长春,23日离长春回京。可惜没有时间到您们那里去了,请问同志们好。致
敬礼!问国良、伯英、锦池同志好!
冯其庸
一月十七日
出版社那邊请告诉他们一下,如他们想收进去,请与您联系。拜托,又及。
这封信所用信笺的页脚写着绿色小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稿纸”,全文草体书于稿纸的背面。从信的内容可知,冯先生把复印的原稿寄到了地处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北方论丛》,并一再解释因时间仓促,来不及誊抄、打印,为如此“乱糟糟”的初稿给编辑带去的麻烦,表示体谅和感激。这里也记录了一些历史信息,这篇长文的写作背景,“原是去年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要我写的”。信中所言“头二节的内容”指“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和“如何看待毛泽东同志对《红楼梦》的一些意见”。问候语中的“国良、伯英、锦池”分别指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党委副书记李国梁、红学专家王伯英和张锦池教授。冯先生诚挚的话语,体现出他的谦和、认真,以及对编辑同行的理解和尊重。
第四封信: 1981年1月21日
麟书同志:
稿已寄上,想已收到,因时间紧迫,未能细改,现有几处,恳为改正:
一、 第9页第一行第一句末改为句号,下面“因为新红学派的理论和欣赏趣味里,还混杂着若干封建性的东西。”这句删去。
二、 第14页倒数第4行末三字“甚而至于……”到最末一行全删去。
第15页第1行开头“对的”两字改为:“这种情况”,下接原文“是不利……精神的”以下“对于这种歪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共同来予以清除。”全部删去,改为:“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避免。”
三、 第52页第二行“红楼梦探源 吴世昌著”以下空白语填写“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英文本”。
第五行:“11,红楼梦论稿”,下面一行请添“12,论凤姐 王朝闻著 1980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下面“漫说红楼”改为“13”,以下顺次改,到“17,曹雪芹家世新考”下一行再添“18,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 蔡义江著 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以下次序顺次改为19、20、21、22、23。
四、 第55页第6行第二句“应该贯彻百花齐放”请改为“应该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百花齐放”下接原文。
五、 第55页第8行第一句“定别人的劳动。”下面增加以下一段文字:“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但也欢迎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探讨,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的竞赛和发展,决不搞‘一言堂,要认真贯彻学术民主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应该好学深思,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甚至帮助不同意见发表和自己讨论的气度和胸襟。应该认识到学术的是非任何人是专断不了的,只有历史才是真正的权威!因此我们应该真诚地欢迎各种不同的意见,欢迎各种不同方面的研究。”以下接原文“只要对红学有所……”。
以上各点,恳托麟书同志代为改正。文章太长,如换掉别的文章不方便,就不一定发,不要造成您们的困难。我22号去长春讲学,就是讲这个问题,顺便也听听意见,但文章不给他们发表,已经给您们了,我不会再交别处。北京已请了一部分同行看了,大家觉得适时,增加的这一段就是大家讨论的意见。
清样排出后,请让我校一遍。匆致
敬礼!
冯其庸
一月廿一日晨
出版社王敬文同志处请告知他,此文已在您处。又及。
这封信所用信笺的页脚写着绿色小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稿纸”,全文按格写在稿纸上。冯先生对初稿进行仔细修改,并及时寄去校订文字。书信落款时嘱咐编辑部“清样排出后,请让我校一遍”,足见他的严谨认真。这封信对自己的论文列了五条教改意见,逐一体味,颇有启发意义。第一条,冯先生斟酌,删去了这样一句:“因为新红学派的理论和欣赏趣味里,还混杂着若干封建性的东西。”第二条,将“对于这种歪风,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共同来予以清除”全部删去,改为:“这种情况我们应该避免。”修改后的文字,语气更有分寸感。第三条,对注释的顺序等细节问题的处理,一丝不苟。第四条,增加了词语“坚定不移地”,对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加以的强调。第五条所示,增加的文字较多:“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但也欢迎各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相互探讨,欢迎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的竞赛和发展,决不搞‘一言堂,要认真贯彻学术民主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因此我们应该真诚地欢迎各种不同的意见,欢迎各种不同方面的研究。”信中坦言:“增加的这一段是大家讨论的意见”,可见冯先生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第五封信:1981年1月26日
麟书同志:
日前寄去一信,请为改正数处文字,想蒙收录。关于拙文(小字,自谦款式)过分冗长,弟(小字,自谦款式)寄出时,只是一时完成此稿,未曾仔细计算,现在看来,您们处理此稿,实在为您造成了困难,心里很觉不安,我们都是自己人(朱笔右侧圈点),我自己也在编刊物,这类难题是常遇到的,我深怪自己太鲁莽,请您理解我诚恳的心情,并不是有别的任何想法,只是觉得不应该(朱笔右侧圈点,“不应该”三个字朱笔双圈。)给您们送去这么一个难题,向您们表示真诚的、深深的歉意(朱笔右侧圈点)。为了使您们不致不好办,我提出几点处理意见:一、不发表此稿,如王敬文处出版编入,则可以写信与我商量。二、分两期发,第一期发前三节,即发完红学的分工问题,其余二个问题放在下期发,因下两个问题时间性不太强,下期发还无关系。如一次全部发完,篇幅实在太长,会造成许多矛盾(朱笔右侧圈点),即使分两次发,第一次发完三节,也已经有二万多字了,已经够长的了。所以千万请您们理解我的诚意,不要为难,如不好发,完全可以不发,决不会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决不会影响我们的亲密关系,请千万放心(朱笔右侧圈点)。并请一定将我的意思转达到国良同志,我们大家都在办事,都只能从工作出发,事业出发,不能违背原则。可能由于我想到这点太晚了,已经造成你们的许多困难,因我于23日匆匆被长春强邀去,稿件寄出后,根本无暇思考这个问题,今天开完我们的编委会,心理安静一点了,坐下来一想,觉得我处理此事,实在欠妥,务请理解我的心情。同样的意思我也给锦池写了一信,请他转述我的意思。另外,您及其他同志讀完拙稿(小写,自谦的款式)后,感到有什么不妥之处,务恳告诉我,以便修改,这是最重要的(朱笔右侧圈点),此点务请帮助。致恳了。匆匆不一一,顺问
好!
其庸
一月廿六日夜深
冯其庸先生信中有些字词的书写方式传达出感情色彩。信中称呼自己时的“弟”,称呼自己文章时的“拙文”或“拙稿”等字写成小字,以表自谦。这封信中冯先生加了多处圈点,用朱笔圈于竖写的文字的右侧。笔者以下划线标出。这些圈点处的句子语气诚挚、恳切,传达出他善于换位思考,严于律己,对编辑同行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也表现出自己的敬业精神。信上提到的“王敬文”为黑龙江出版社编辑,当时欲编辑出版《红楼梦》论集。
第六封信,1981年2月2日
麟书同志:
来信收到。知道拙稿(小字,自谦款式)现在的处理办法,心里很过意不去,只好特向您及其他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了。今天下午,中宣部贺敬之副部长约我去谈工作,又问起了我写的这篇文章,因原是他要我写的。我向他汇报了这篇文章的五个部分的基本内容,他听了表示同意,并问在哪里发表。我告知他在《北方论丛》第二期发表,他也表示同意。并要我把我的打印稿印出来后就给他送去。还谈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并要我仍旧为《人民日报》补写一到二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本是应该在《人民日报》发表)。我的打印稿已打好,在校对过程中,又有几处小的增改,现将增改的文字另纸录来,恳请代为改入(六个字用朱笔在右侧加圈点)。我的打印稿大约十来天内可以印出装订好,到时当即寄上。以便校对。经这次改定后,不会再有什么改动了,决不会再动版面了。请您代我向排字的老师傅致以深切的谢意,请问候国良同志。王敬文同志处等打印稿出来后,当即寄去。匆致
敬礼!
冯其庸
二月二日夜深
另纸所录增改的文字:
一、 原稿第五页第一行:“这时又大肆泛滥”句加一注号①,并请将下面这段注文增排。注①:当然,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与后来“四人帮”的“影射红学”、“阴谋红学”,无论是在政治上或是在运动的形式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它们各自有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的,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这里仅僅是就两者都具有主观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这一点(三个字加朱笔圈点)而说的。
二、 原稿第5页第八行(此行空白行不算)“又有了新的繁荣发展的气象”:下增以下一句:“一九八○年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下接原文“一九八○年六月美国……”
三、 原稿第41页右面边上增加文字倒数第六行“《废艺斋集稿》的真伪问题”下请增加以下三句:“书箱问题,香山正白旗39号老屋的问题,白家疃的问题”,下接原文“等等,对于这些……”
四、 原稿第51页第一行:“一,影印《石头记》原著”,“原著”两字请改为“抄本”。
五、 原稿第53页第八行下,第9行起,另增以下一小段重要文字,务请增入(四个字加朱笔圈点):
(行侧朱批:低两格另起段)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红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秀,他们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刻苦钻研“红学”,发表了一批很有见解的文章和专著,在“红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还有一种新的情况,就是在全国出现了几个“红学”较为发达的地区。例如:哈尔滨、沈阳、南京(包括扬州)、上海、安徽等地,研究“红学”的空气颇为浓厚,当地的领导也很重视。还有散处在全国各地的“红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更是难以数计。这种情况,说明了“红学”已经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了一支全国性的“红学”队伍,说明了“红学”后继有人,它不再是少数几个人关在书房里作个人钻研的情景了。可以说,在文学史上,还找不到第二部作品或第二个作家,具有如此庞大的完全出于自发的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队伍,这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和兴奋的现象。
以下再接原来的段落“这里还要说明一点……”这一段文字,仍是低二格另起段。
冯先生的三万字的长文即将在《北方论丛》在1981年第2期上全文刊出。对“拙稿”当时的处理办法,冯先生心里很过意不去,诚恳地向夏麟书编辑致歉。同时,他精益求精地修订文稿,从1981年1月21日和2月2日两封书信中所附的10个修订条目清晰可见。这一封信中的修订内容除了正文的增订,一些写给编辑的提示语也令人瞩目。如第五条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红学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新秀”开头的一段增文,“特别”前面加了两个空格符号“√√”,并在左侧空白处朱批了“低两格另起段”。还在这一条的结尾写道:“这一段文字,仍是低二格另起段。”于细微处显现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第七封信:1981年2月26日
麟书同志:
您好。我寄去的校样想早收到并代为校改了,谢谢。今天检查我的手稿,发现第29页(全文第二部分谈爱情掩盖说的一段)倒四行,到30页开头二行“相反,如果硬要把曹雪芹所申明的‘真实隐去‘假语村言解释为相同到现代创作术语的从生活素材到艺术成品过程,把‘假语村言解释为‘一番典型化的工作,这样的理解,恐怕要离开曹雪芹的原意,未免有点吧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过分地现代化了。”这一段文字我是在原稿上删去了的(我手里留的原稿)。但我寄您的复印稿当时还未删去,后来看校样时,我记不起来是否已经删去了,很可能仍未删,我寄您那复印稿是最早的稿子,删去是复印稿寄出后,在我的手稿上删的,原想在看校样时删的,很可能当时看样稿过于匆促,忽略了此事没有删去。请为检查一下,如已删去,则甚好。如未删去,则这段话说得有不清楚不准确之处,是否来得及登一作者来信:
“编辑部负责同志:拙稿《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第二部分”相反,如果硬要把曹雪芹申明的‘真实隐去……未免有点吧曹雪芹的创作思想过分地现代化了。” 这一段文字是应该删去的,我在看校样时疏忽了,未曾删去。请为刊登此函,以向读者致歉。谢谢。
冯其庸
一九八一年二月廿六日
这一期估计是来不及登此信了,请在下期借贵刊一角,予以说明,并恳注明见本刊第几页到第几页,或见本刊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行。如已经删去了,则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原意是要说《红楼梦》里既非全是真事,也非全是虚构(典型化),是这两部分有的。片面地强调某一面,都不符合实际。我的那段话,并没有把这层意思说清楚,相反容易发生误解。
这篇文章,费了您不少精力,十分谢谢。我目前的工作太忙,常常发生差错和疏忽,真是没有办法。匆匆,即问好!
冯其庸
二月廿六日
冯先生将校样寄给《北方论丛》之后,又在手稿原件中发现可能出现疏漏,请编辑帮他再检查一下,如稿子已经刊出,希望能在下一期刊登自己的一封作者来信,以补上校订的文字。“这一期估计是来不及登此信了,请在下期借贵刊一角,予以说明,并恳注明见本刊第几页到第几页,或见本刊第几页第几行到第几行。”细致入微的叮嘱反映出冯先生在为自己的文字负责,为文章的社会影响负责。他对《红楼梦》研究的态度,可以说是富有示范意义的。1981年2月26日的信函中续写的一段话发人深省:“《红楼梦》里既非全是真事,也非全是虚构(典型化),是这两部分有的。片面地强调某一面,都不符合实际。”从今天的现实来看,依然有人把《红楼梦》看成“全是真事”的家传,进而牵强地进行“曹贾互证”,忽视了这部世情小说的文学性。我们重读冯其庸先生30年前的理论文章,依然不乏现实意义。
第八封信:1981年3月19日
麟书同志:
来书收到多日,因事忙未速复,甚歉。我前几回所说的那段文字,于内容无关紧要,只是上下文接不上,意思说得不清楚而已,我当时就估计来不及删了,所以不删也无妨。我已将打印稿送给了中宣部,也给耀邦同志送了一份,现在刊物大概已出来了罢,我23日趁飞机去南京,要兩周能回来,回京后又要接待日本的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估计五月份我是够忙的了。刊物出来后,请速寄我数份,如能在去南京前收到就好了,但可能来不及了。谢谢您的辛劳,谢谢编辑部的同志。又黑龙江出版社的事,毫无关系,因我以为此书是他们与您们大会一起编的,他们还数次来信催稿,我也告诉他我无法如期写出来,请他们不要打算在内,后来又听说此书一直未发稿,故我提一笔,如来得及可收入,现在既已来不及,自然毫无问题。
见国良同志请为问候,匆匆,不一一,顺问
好!
冯其庸
三月十九日
1981年春天,冯其庸先生从北京到长春、上海、南京等地频繁开会,同时与哈尔滨师大的《北方论丛》杂志紧锣密鼓地通信,又要接待日本红学家的来访。从天南地北到海外,为红学事业忙碌着。《红楼梦学刊》1981年3期记载:“日本著名红学家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应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于今年四月二十四日至五月十四日访问了我国。松枝先生现年七十六岁,是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冯先生1981年3月19日的信中提到“回京后又要接待日本的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结合下文4月23日信中所云“明天日本朋友来访,到五月十五才离开”,时间、人物、事件吻合,翔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信息。
第九封信:1981年4月23日
麟书同志:
您好,我出差了一个月,十六号在上海飞机场见到了《解放日报》您摘要的拙文(小写,表自谦),谢谢您的关注。回来后读到您的信,出作者问题讨论集,我是很赞成的。写长篇论文,实在没有时间了,因明天日本朋友来访,到五月十五才离开,我抽不出时间。如要写一个简短的叙言,则可以挤点时间出来。但可否在我送走日本朋友后再写,大约五月中旬定稿。如实在等不及,则就不要耽误出书,就不要我写了。请您酌定之。
拙文(小写,表自谦)在上海反映较好,昨天魏同贤来信又谈到此事,徐恭时也说文章说出了他们多年想说的话。来信照登与否,登也可以,因为我收到集子里去的文字已经删掉这一段了。现集子已付排。谢谢您们的大力支持。问同志们好,问
国梁同志好!
冯其庸
四月廿三日
关于写序言的补充:
若要写,能否给我一个目录及文章(主要文章也可),如无文章给目录也可,我可托人去找。
信中可见,冯先生当时的日程排得很满,但对《北方论丛》的红学事宜都是积极支持的。撰写并发表一篇长文后,《北方论丛》要编辑《红楼梦著作权论争集》,他答应“如要写一个简短的叙言,则可以挤点时间出来。”并在落款之后又补充说,如要写序言,需寄给他论文集的目录,足见其诚恳和热情。文中“您”的称呼,以及“拙文”的自谦写法,都体现出冯先生为人的谦逊。
这封信写于1981年4月23日,夏麟书编辑对冯先生发表在《北方论丛》上的长文加以概述,撰写了《红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冯其庸著文探讨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一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1981年4月16日。冯先生信中所言《解放日报》上的文章即指此文。全文如下:
红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冯其庸著文探讨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北方论丛》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冯其庸的《关于〈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提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见解。
关于研究《红楼梦》还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文章认为,建国三十年来,《红楼梦》的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四年,是新学派占主要地位。一九五四年的那场文艺思想的批判运动,虽有它的缺点和错误,却是红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分界线和转折点,使红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用马克思主义研究《红楼梦》阶段,红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十年浩劫”期间,一切文化遗产统统被打倒,以往的历史被纳入一个狭窄的农民起义的框框,唯框框以内是光明,框框以外,全是黑暗与罪恶。只有《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不在打倒之列。“四人帮”肆意曲解践踏《红楼梦》,通过他们的御用班子大搞影射红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人帮”的评红则是意在周公,给红学造成极大的混乱。
文章说,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红学,还是回到唯心论的老路上去?这是当前红学研究中不能不加以思考和认真解决的问题。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地解释《红楼梦》这部巨著,才能给红学注入新的富有生机的内容。
文章认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过去对《红楼梦》的一些看法,就公开发表的正式文件来说,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同志《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所提出的四点原则性意见,即批判唯心主义,提倡用马列主义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红楼梦》,提拔新生力量,团结知识分子,其基本精神是正确的,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不能因为这场运动的做法有不妥之处,起了些消极作用,因而忽略了它的积极的主要的方面。
其次,毛泽东同志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曹雪芹的时代是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萌芽,但还是封建社会的时代,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富有启发性。贾宝玉这个典型,实质上就是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典型,因而这个艺术典型成了时代的标志。另外,他还指出,贾宝玉是一个不满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这样也就明确地指出了贾宝玉这个典型形象的思想的主要方面。这些精辟见解对于我们研究《红楼梦》具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再次,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把《红楼梦》与我国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等并列起来,这是对《红楼梦》的空前的高度评价,是正确的。
文章从传抄的抄件中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文章认为,说《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是不妥当的。《红楼梦》不是描写历史上的政治斗争事件的小说,而是道道地地的描写当代现实的文学。但同一些优秀的小说一样,当作历史来读是完全可以的。文章又认為,关于第几回是纲问题最早提出来的要数脂砚斋,但是曹雪芹当年写《红楼梦》未必象今人一样先拟出写作提纲来,然后动笔,何来第几回的“纲”?如果是说我们今天读《红楼梦》应以第几回为“纲”,那就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完全没有必要去定于一尊。至于所谓“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问题,文章认为是作者交代他创作本书的基本态度和一些特殊手法,作品中确实有许多“假语村言”,即艺术的虚构和想象,但并非全是虚构。理解得过于刻板,以为真事都已隐去,容易被作者“瞒过”。关于所谓“爱情掩盖政治”,文章认为,这样说确切不确切,能否用来提示复杂的内容,是否容易引起简单化的理解,是可以商讨的。然而决不能因此而认为《红楼梦》是单纯地描写爱情的作品,没有政治内容,也不能认为《红楼梦》里的爱情描写和政治内容都一样写得很突出很明朗,不存在什么掩盖不掩盖的问题。文章还认为,《红楼梦》的内容是深广的,包含着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的内容的,只要我们不对它作不符客观实际的牵强附会的解释,从这方面去进行研究和探索,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分工问题,文章说,大体上“红学”似乎已可粗略地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曹学或外学,它似应包括曹雪芹的家世、传记、文物的研究等等;此外,似还可以包括曹雪芹的时代以及明清以来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建筑史、满族史等等各方面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关的部分在内。二、红学或内学,它似应包括《红楼梦》的版本学;《红楼梦》的思想内容、人物创造、艺术成就、成书过程;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红楼梦》八十回后的情况;脂批的研究;《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研究;《红楼梦》语言的研究;《红楼梦》与我国古典文学传统的关系;《红楼梦》给予后世的影响;《红楼梦》与清代社会,等等。文章认为,《红楼梦》确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不可能要求一个红学研究者去研究红学的一切,而应该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
关于考证问题,文章认为:三十年来,我们学术界对于考证,常常是左右摇摆,时而加以批判,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而当一旦考证出某些重要成果时,考证又成为一门时髦的学问。我们应该提倡充分掌握材料,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材料进行分析,从客观材料中经过科学分析得出科学结论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考证方法。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对资料工作包括资料的考订工作不够重视,尤其是十年浩劫期间,我们的党风、文风,在学术上大兴实事求是之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此来扫除“四人帮”的歪风邪气,在“红学”的领域里同样是如此。
关于思想和艺术的研究。文章认为,必须把重点放在对《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上,要通过分析,看清楚这些艺术形象所包含的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社会性质。从而更深刻地去认识这些栩栩如生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的思想内涵,更深刻而确切地去评价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的思想意义
文章在结语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十年的红学所达到的成就,可以说远远超过了过去二百年来红学成绩的总和。而且红学目前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问,海外学者在红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卓越成就。红学正面临着历史上的新时期,大发展的时期。(麟 书)
载《解放日报 》1981年4月16日
本文以1981年上半年冯其庸和夏麟书的通信为研究视点,通过9封书信的录入和研读,不难发现,这些书信主要围绕一篇论文《关于当前〈红楼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撰写、校订、刊出的过程,生动反映了冯其庸先生作为一位中国红学会的负责人,对红学事业的执着;作为一位专家,对著书立说的严谨;作为一名编辑,对业内同行的体贴。中国红楼梦学会诞生30年来中国红楼梦学会1980年于哈尔滨成立,2010年在北京召开三十周年纪念会。,之所以能够紧密地团结了海内外的红学同好,和我们有“事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带头人,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诚挚而勤勉的付出是分不开的。
2010年10月16日初稿
参加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国学前沿问题研究暨冯其庸先生从教六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1年3月31日增订稿
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编《国学的传承与创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4月
2017年1月22日冯其庸先生仙逝之日深情重校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责任编辑连秀丽]
发表说明:此文曾于2013年4月发表于论文集《国学的传承与创新——冯其庸先生从事教学与科研六十周年庆贺学术文集》,此次发表于《北方论丛》,因冯生生2017年1月22日仙逝,冯先生生前多关心《北方论丛》的《红楼梦》专栏,谨以此文纪念冯老先生,愿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