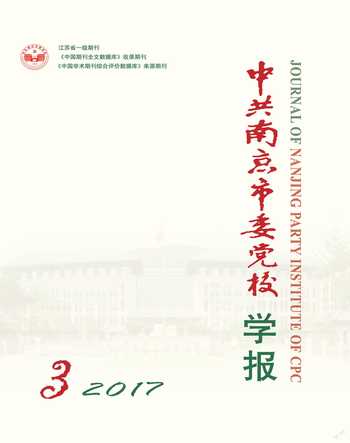论单一全球原初境况的合理性
向青山 戴芳
[摘 要]罗尔斯《正义论》和《万民法》的问世引起了广泛讨论,所讨论的热点之一,便是罗尔斯的正义原则能否运用到全球范围,尤其是作为两个正义原则之契约论基础的原初境况,能否同样作为全球正义原则的契约论基础而发挥作用?如果经过适当解释后的两个正义原则和契约论可以扩展到全球范围,那么作为一种代表机制的全球原初境况应该是何种情形,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需要分别采用原初境况,还是单一全球原初境况的解决办法更为合理?针对这些问题,罗尔斯及其批评者们给出了不同解答,引出了不少争议。
[关键词]全球原初境况;单一全球原初境况;全球正义;全球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 B82-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071(2017)03-0086-07
《正义论》中的原初境况能运用到全球范围吗?如果可以运用,那能否进行单一运用?这是《正义论》出版后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罗尔斯自己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全球范围内运用原初境况时,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将分别利用原初境况立约。以博格为代表的反对者则认为,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论要想保持一致性,就必须将两个正义原则运用到全球范围,而这就意味着首先要在全球背景下重新理解原初境况,原初境况在全球范围的运用只需要一次,而不需要多次。我将先讨论罗尔斯将原初境况运用到全球范围时的观点,然后讨论博格的“单一全球原初境况”,最后为博格的观点进行一种辩护。
一、羅尔斯的全球原初境况
罗尔斯的《万民法》以他早年《正义论》中的建构主义契约论方法为基础,提出了原初境况的第二次运用,即全球原初境况。罗尔斯早年的《正义论》坚持了近代以来的契约论传统,利用建构主义方法确立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以此作为社会制度与法律的评价标准。这种建构主义的新契约论假设了一种原初境况(original position),在这种原初境况中,立约各方作为代表,处于无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的条件限制之下,不知道自己的主观情况(社会地位、阶级出身、天赋、理智能力、善观念、合理生活计划以及心理特征等等),也不知道社会的客观情况(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明和文化水平等等),只知道影響正义原则选择的一般事实,包括知道自己的社会受正义环境的制约及其相关含义,知道一般性的社会理论(人类社会的一般事实、理解政治事务和经济理论原则、社会组织的基础和人类心理学法则)。[1]处于无知之幕中的各方代表对彼此的利益保持相互冷漠,在选择正义原则时遵循最大最小值规则(maximin rule)、反思平衡(reflective equilibrium)以及理性选择规则,最终选择了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原则是机会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
在《万民法》一书中,罗尔斯同样运用了原初境况的建构主义方法。在对原初境况进行第二次运用时,罗尔斯认为立约各方代表的是“人民”,而非“国家”或“个人”。[2]他把世界上不同的人民(社会)分为自由人民、合宜人民、法外国家、负担不利条件的社会以及仁慈专制主义。罗尔斯着重讨论的是前两种人民(社会)。自由人民(liberal peoples)的原型是当今欧美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建立了较为公平的社会正义制度,人民享有较为全面而广泛的自由民主权力,人权得到了较好保障。合宜人民(decent peoples)实施合宜的协商等级制度,虽然信奉某种广包理论(comprehensive doctrines),但对外尊重世界和平秩序,不具有侵略性,对内通过立法保障成员的基本人权(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形式平等的权利等等)。罗尔斯假想了一个“卡赞尼斯坦”(Kazanistan)作为合宜等级社会的模型。[3]这两种社会被罗尔斯称为“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ies),后面三种社会则是非良序社会。关于良序社会的万民法属于“理想理论”,关于万民法向非良序社会的扩展属于“非理想理论”。
在全球原初境况中,各方仍然处在无知之幕的限制条件之下,遵循理性选择原则和最大最小值规则,对恰当的主题和选项进行审慎思考,并且基于人民的根本利益选择万民法原则。[4]罗尔斯的全球原初境况事实上运用了两次,第一次是自由社会的代表在全球原初境况下立约,第二次是合宜等级社会的代表进行立约。虽然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是分别立约的,但罗尔斯认为自由社会应对合宜社会保持一定的宽容,因而这两种社会将选择同样的万民法原则。这八条万民法原则与传统国际法原则是相一致的:第一,人民是自由而独立的,其自由与独立要受到其他人民的尊重;第二,人民要遵守条约与承诺;第三,人民之间相互平等,都是约束他们的协议的制定方;第四,人民要遵守不干涉的义务;第五,人民有自卫的权利,但除了自卫之外,无权挑起战争;第六,人民要尊重人权;第七,人民在战争行为中要遵守某些特定限制;第八,人民有义务帮助其他生活于不利条件下的人民,这些条件妨碍了他们建立正义或合宜的政治与社会体制。[5]
以上便是罗尔斯全球原初境况的主要内容。罗尔斯把他的万民法称为“现实乌托邦”,认为他的理论在道德理想性与现实可行性之间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结合点,这样的结合最有利于实现康德意义上的永久和平。不过罗尔斯的这种结合却使他的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出现了理论上的不一致。首先,在全球正义中罗尔斯并没有坚持他的两个正义原则,而是令人费解地维护了传统国际法的原则;其次,自由社会与合宜社会分别处在全球原初境况中立约,而分别立约的情况下竟然神奇般地制定了同样的万民法原则,这不能仅仅依靠“宽容”进行辩护;最后,考虑到全球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全球化的日益加深,以国家作为边界区分出原初境况的国内国际两次运用,越来越不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正如学者所批评的,全球日益密切的社会合作呼吁在运用原初境况时,取消国内与国际的区别。
二、博格等人对罗尔斯全球原初境况的批评与发展
博格十分赞同罗尔斯将原初境况进行全球化运用,并且力图为这一全球化运用辩护。所不同者,博格认为罗尔斯的国内国际两个原则并不一致,原初境况的第二次运用以及基于此制定的万民法,与罗尔斯所坚守的个人主义和两个正义原则有冲突之处。博格认为,他自己对于罗尔斯原初境况的全球化解释和运用,更加符合罗尔斯正义论的本质要求。
为了论证自己的解释更具合理性,博格分析了全球背景下对原初境况的几种不同解读:第一种解读把全球背景下的立约各方视为“个人的代言人”,各方受“无知之幕”的条件限制,遵循理性思考和推理方法,依据最大最小值规则选择正义原则,这样的正义原则关注的是全球范围内的最不利者。第二种解读则把各方设想为“国家的代言人”,各方关注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国家利益则由本国已承认的正义原则来界定,主要包括维系和保障正义制度。依据这种解读,理想的正义世界便是由正义的国家构成的世界,而国内制度不足以正义的国家便成为关注的焦点。上述两种解读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赞同罗尔斯在国内和国际背景下分别运用原初境况的做法。第三种解读是博格力图捍卫的解读,反对国内和国际两次立约,而是设想一个“单一全球原初境况”(a single global original position)。[6]该解读把全球社会作为一个封闭的整体,主张通过一次性立约制定出正义原则,同时作为国内和国际两种境况下的共同约束规范。
罗尔斯认为全球会议将重新确证人们所熟悉的传统国际法原则,但上述解读一和解读二都会拒绝罗尔斯的做法。首先,罗尔斯的做法对全球分配正义问题太不敏感,他也明确表示拒绝接受全球再分配原则。[7]其次,传统国际法规约下的不平等的国际关系会导致“承诺的压力过大”,而过大的压力会使得承诺遵守条约面临严重困难。再次,罗尔斯维护的国际法没有提供有效的“裁决和执行机制”,这很难确保各方遵守国际法原则。[8]最后,罗尔斯主张原初境况的第二次运用时,自由社会和合宜等级社会是分别立约的,而罗尔斯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足以证明两种社会的分别立约会得出同样的万民法原则。在博格看来,罗尔斯的此一做法等于是牺牲了自由社会的更高要求而迎合了等级社会,两次立约得出相同的万民法不是出于幸运,而是出于设计。[9]
然而上述解读一和解读二也各自存在问题:解读二把各方视为国家的代言人,这与罗尔斯所坚持的个人主义立场是相违背的,因为与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一样,国籍只不过是另一种偶然性,而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以个人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正义观”,[10]个人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才是道德关怀的最终单位。解读一把各方视为个人的代言人,这些个人代表在第二次立约时,会后悔自己先前对于国内正义原则的选择,依据最大最小值规则,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这样的正义标准:所有制度都要根据全球最不利者的利益而被评价;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保持封闭状态,很难脱离国际环境来确定和维持国内正义,国内和国际的稳定性是相互依存的。[11]博格认为,他所做出的“单一全球原初境况”的解读,不仅优于罗尔斯维护传统国际法的做法,而且优于解读一和解读二,是最符合罗尔斯正义论全球化的解读。
除了博格以外,其他学者也对罗尔斯的国际正义原则提出了批评。例如有些学者认为,只要经过适当解释,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本身就可以运用到全球,而不是像罗尔斯那样仅仅再次肯定传统国际法原则。因为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社会合作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在此背景下的国家边界不再具有根本的道德意义,原初境况下的无知之幕应该屏蔽各方关于自身国籍的相关知识,由此选择的正义原则应该运用到全球范围。贝兹也赞成两个正义原则的全球化运用,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运用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而且他强调,当契约论运用到国际范围时,国际原初境况的代表应该是“个人”,而不是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设想的“国家”,无国籍限制的个人应该成为全球差别原则的主体。[12]还有观点认为,全球原初境况下制定的全球正义原则,除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还应该包括其它一些原则,例如还应该涉及到有关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原则。或者就像巴里所建议的那样,立约各方应该同意成立一些永久性的国际组织,以便承担咨询、外交甚至集体安全之类的功能。[13]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批评了罗尔斯的全球原初境况及其两种正义观的不一致。
我认为博格和其他学者对罗尔斯全球原初境況的批评是合理的。罗尔斯之所以不愿意把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扩展到全球范围,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正义原则是以封闭而自足的社会为出发点的。[14]但随着国际交往的越来越频繁,尤其是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增长,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起到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国际问题(例如环境问题、反恐问题、控制核武器问题等等)都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尔斯所假设的国家封闭和自足并不能成立,利用国家边界来限制正义原则适用的范围,越来越不具有合理性。随着社会合作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国际经济合作的日益加深必然使国际分配正义问题由此产生,而传统国际法原则虽然承认国家之间出于慈善的援助义务,却不承认基于国际分配原则的正义义务。因而传统国际法并不能适应(至少不能完全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新需要,罗尔斯的国际正义原则仅仅满足于重申传统国际法原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博格和其他学者通过重新解释和扩展全球原初境况,满足了国际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其论证较之罗尔斯更加合理。
三、为单一全球原初境况辩护
“单一全球原初境况”的解读,可能面临一些反对意思。这些反对意见有些来自现实主义观点,有些质疑罗尔斯正义论之全球化運用的可行性,有些则坚持多元文化视角,还有一些强调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差别。我将结合博格的相应观点,为罗尔斯正义论的全球化运用做辩护。
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权力和利益的较量和冲突,各国采取各种手段追求自身利益和目的是古今中外的现实,因而也是十分自然而合理的,在国际关系中没有道德存在的空间和必要,也不存在道德上可行的方案以实现更正义的全球体制。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满了压迫、饥荒与战争,一种更正义的全球基本结构对于我们来说是遥不可及的。即便从理论上说一种更正义的全球秩序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博格对现实主义的反驳诉求的是理想道德理论的性质。[15]现实主义理论之所以力量強大,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经验的事实加以佐证。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似乎都意在“证明”,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力量与利益的斗争与合作,其间几乎找不到任何道德的字眼。但问题是,一种“描述性”的理论本身能否足以否定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描述性理论对应的是现实的“是”,规范性理论对应的是理想的“应该”。休谟曾经在“是”与“应该”之间划了一条界线,这条界线不仅提醒后人不应简单地用“应该”来取代“是”,也不应简单地用“是”来否认“应该”。一种更正义的全球秩序可能会面临可行性方面的诸多问题,但它仍然可以提供评价全球秩序的标准,为全球制度秩序的改革提供一个目标和方向,让我们在“道德上允许”和“现实中可行”的诸多制度变革方案中做出选择,从而为我们的全球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事实上针对现实主义者所提出的“理想理论不可能”的反驳,我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就理想理论的可行性而言,存在着两种意义上的“不可能”:第一种是指就目前的现实条件而言的不可能,例如就目前的现实条件而言,我们不可能实现所有适龄青年都接受高校教育(因为现有的高校招生规模无法满足这一要求);第二种是指在任何社会条件下理想理论本身的不可能,例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人性都不可能是绝对利他的。如果现实主义者所强调的不可能是第二种情况,那我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如果现实主义者认为关于全球原初境况的理想理论是第一种情况下的不可能,那其反对的力量就大大弱化了。现在很难被国家和个人接受的原则,不代表将来不能被接受;这正如现在被广为接受的自由平等观念在人类曾经的等级社会中不可能被接受一样。我相信随着国际交往的越来越频繁,随着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道德规范向全球范围的扩展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个人的接受。事实上我们的社会现实已经证明了这种进步的可能性,例如关于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曾经被视为对他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现在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为出于保护人权的正当行为。
对罗尔斯正义论和原初境况的全球化运用问题可能存在至少三方面的反对意见:第一,罗尔斯的正义论适合封闭的社会体系,而当今的国际互动并不足以使全球变成封闭的社会体系;第二,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公平合作的“互利”观念为前提条件,而满足了罗尔斯正义原则的全球制度秩序中,富裕国家的处境会坏于不受国际合作约束状态下的处境,因而不满足“互利”的要求;[16]第三,罗尔斯正义论以良序社会为前提,但当前全球社会太乱,不符合良序社会的要求。
针对第一种反对意见,博格指出,虽然富裕国家受外来因素的影响不大,但穷国的命运受富国和国际组织的影响极大;而且借助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富国成为过去的罪恶和不正义的受益者,当前的国际贸易和外交制度又有利于富国继续巩固和扩大优势地位。国际互动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再加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足以将整个国际社会纳入封闭的社会体系。关于“互利”问题,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值规则以及差别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方案,在满足差别原则的前提下,富国仍然可以追求合理的利益。而且,任何社会合作都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一种伤害富国利益的国际社会合作是不可能全面实施的。关于“良序社会”问题,罗尔斯的良序社会观念是一种规范,而不是一种事实描述,各方以良序社会的身份选择正义原则,并不意味着他们选择的原则只在良序社会中才有效。[17]
文化多元主义的反驳意见认为,罗尔斯式的全球正义理想确实可以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及深思熟虑的判断相一致。但全世界除了欧美资本主义文化类型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文化,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差别很大,甚至是完全异质的。而罗尔斯式的全球正义理想意味着要把欧美文化强加给其它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这种强加完全是不道德的。
文化多元主义的反驳是一种强有力的反驳,甚至罗尔斯自己也对文化多元主义有所妥协,因而主張“我们并不试图寻求适用于所有社会的正义观”。[18]罗尔斯所顾虑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就不同文化社会的建构模式表达立场,以及如何评价不同文化社会的国内制度是否正义,民主社会的正义观是否适用于其它文化类型。一种观点会认为,可以借助罗尔斯的“反思平衡”观念来反驳文化多元主义。罗尔斯的反思平衡认为,在我们通过原初契约所订立的正义原则和我们深思熟虑的判断之间,要达成一种平衡,某些情况下要修改原则,某些情况下则要修改判断。而我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形成的深思熟虑的判断之中,有一些是道德判断,这些道德判断最终将诉诸我们的道德直觉。不过罗尔斯并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把道德直觉当作理性存在者先天共享的东西,而是认为道德直觉是在生活经验中形成的,道德意识中的那些核心和稳固的东西也不具有先天的起源。[19]因而文化多元主义可以进一步反驳说,因为文化的差异导致道德直觉的差异,深思熟虑的判断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多样性,从而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诉求共同的道德直觉。
博格认为,要走出文化多元主义的困境,需要借助罗尔斯“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的理念。不同文化在正义观上可能有很大差别,但我们仍然可以就某些领域努力达成共识。这些共识的范围可能很狭窄,而且很可能难以实现,但只要各方真诚对话,共识的领域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宽。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能仅仅因为其当前存在就拥有某种道德上的神圣性。如果我们凭借反思确信它们是不正义的,我们就应该以可行的改进为努力的目标——即使一些真正的道德分歧暂时无法解决。”[20]在面对文化多元主义反驳时,博格的观点和态度是十分积极而大胆的。在他看来,重叠共识的领域不应像罗尔斯那样局限于政治正义观念,而应该努力实现一种实质性的道德共识。在全球正义层面,博格把《世界人权宣言》中所包含的人权内容,当成各国应遵守的共同道德约束。[21]
还有一种反对意见诉诸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差别。这方面的反对意见至少可能有以下几种理由:第一,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由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经过长期共处已经形成了同胞情感,因而国内社会已经发展成了稳固而友爱的社会共同体。这样的社会纽带产生了一定的道德要求和负担,以及同胞和群体成员之间的责任和义务。但国际社会从整体上来看并不是统一而稳固的社会共同体,国际交往虽然越来越频繁,但并未形成类似于国内那么密切的社会纽带,相应的权利和负担也不是那么紧密。因而国内正义优先于全球正义,罗尔斯式的两个正义原则在国内的实现并不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同样实现。第二,国内正义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国内有统一而强制性的权力机构保障正义原则的实施,而且公民在国内环境中可以培养出罗尔斯式的正义感,维护和参与正义制度,改革不正义制度;但全球社会没有类似于国内这样的统一而强制性的权力机构,而且由于全球社会缺乏统一的共同体意识,不能培养出公民的全球正义感,因而即便制定了全球正义原则也很难保证实施,全球正义是不能实现的目标。第三,国内的强制性制度和正义感对于维护国内正义是有利的;但是,即便全球强制性制度和正义感可以经过努力而实现,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可欲的,因为这样的全球强制性制度在效果上可能是极端的或者压制性的。[22]另外,正义感不仅涉及对正义原则的履行,而且是人的认同感的来源。全球正义感的增强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国家或更小群体的认同,而在较小范围内的认同对于个人的人格同一性、身份以及归属感是非常重要的。[23]
第一种理由强调国内正义的标准应高于全球正义,这有其合理性。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同胞的情感要远远浓于对他国陌生人的情感,“世界公民”的理念尚且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能够感同身受的人则更少。但这一推理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全球正义不重要或者可有可无。就目前而言,全球正义还很难达到国内正义的要求和标准,但目前全球社会的问题是连基本的正义标准都没有满足。博格提出了制度是否正义的两个最低标准:其一,社会规则能否经由多数人和平变革;其二,对生活贫困的威胁能否避免。[24]而关于这两个最低标准,当前的全球制度秩序都没有达到。因而国内正义相对较高的要求并不能为当前全球制度秩序的不正义辩护。
第二种理由看到了实现全球正义的困难,但却不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困难。全球正义的实现的确较之国内正义更加困难,其所需要的条件现在未必完全满足;但全球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现在不能满足的条件可以通过努力在不久的将来得到满足。事实上民族国家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宪政民主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正义感也是近代以來逐渐形成的。全球社会的发展进程要晚于国内社会,相应地全球正义的实现条件也相对滞后。当前全球社会的确没有统一而强有力的权力机构,而且世界政府因其潜在的压迫性难以成为可欲的目标,但我们仍然可以在现有国际组织(联合国、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等)的基础上有所作为,而且现有国际组织仍然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经过合理改革后的国际组织可以更好地保障全球正义原则的实现。另外只要对于全球正义问题加以应有的关注,人类的全球正义感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逐步培养。
第三种理由看到了全球强制性制度的强迫性以及正义感对于个人的群体认同和人格统一的重要性,这固然是合理的。但对全球范围内强制性制度和正义感的要求,并不需要类似于国内那样严格的标准。为了现实全球正义,我们需要相关的制度和正义感作为保障机制,但并不需要类似于国内社会这样严格的保障机制。将全球正义与国内正义作密切的类比是一种错误的做法。就当前全球正义的目标而言,最紧迫的是要保障一些人类成员的基本人权得到满足,因而这并不会影响到公民的国内认同。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博格等人对罗尔斯原初境况的全球化运用进行了详细的批评,而且提出了自己更具“罗尔斯式”的替代方案。从整体上来说,博格等人对罗尔斯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他们提出的“单一全球原初境况”解读,虽然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特征而容易受人指责,但至少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旨更相符合。博格等人对罗尔斯正义论的全球化运用所做的辩护,批评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反对意见,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代表了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扩展路径。而且我也补充了强调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之间差别的反对意见,并且对这些反对意见进行了反驳。全球正义是一个复杂的大问题,其中有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讨论。但道德规范的扩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使全球正义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迫切。如果契约理论在当代政治哲学中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魅力,而罗尔斯式的正义理论能够被我们基本接受的话,那么原初境况的全球化扩展就应该是一种可欲的目标,这必将带来道德哲学的巨大进步。
注释
① 这方面的批评可见Brian Barry. 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128-132; Thomas Scanlon, “Rawls Theory of Justic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21, no. 5 (May 1973), PP. 1066-1067; Peter Danielson, “Theories, Intuitions and the Problem of World-Wide Distributive Justi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 no. 4 (December 1973), PP. 331-340.
② 这些批评观点可见 Darrel Moellendorf, “Rawlsian Constructivism and Cosmopolitan Justice,” in Cosmopolitan Justic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2; Andrew Kuper, “Rawlsian Global Justice: Beyond the Law of Peoples to a Cosmopolitan Law of Persons,” Political Theory, 28, 2000, PP. 640-74; Simon Caney, “Cosmopolitanism and the Law of Peopl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0/1, 2002, PP. 95-123.
③ 關于近几十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的历史,可参考尼古拉斯·惠勒:《拯救陌生人——国际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涉》,张德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10][14]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18-119, 233, 4.
[2][3][4][5][7] John Rawls.The Law of Peopl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23-30, 63-64, 32-33, 37, 115-119.
[6][8][11][15][17][20] Thomas Pogge,“Rawls and Global Justice.”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 18, No. 2(Jun., 1988), PP. 234-237, 236, 138-145, 146, 147-150, 253-254.
[9] Thomas Pogge, “An Egalitarian Law of People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Vol. 23, No. 3 (Summer, 1994), p. 218.
[12] Charles R. Beitz.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52.
[13] Brian Barry.The Liberal Theory of Jus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P. 132, 157.
[16] Robert Nozick.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PP. 184-185.
[18] John Rawls, “Kantian Constructivism in Moral Theory”, Journal of Philosophy 77, 1980, P. 518.
[19] John Rawls,“Justice as Fairness: Political not Metaphysical”,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4, 1985, P. 235.
[21][24] Thomas Pogge.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2, PP. 64-65, 96.
[22]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P. 228.
[23] Sigmund Freud.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P. 61.
(責任編辑:华 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