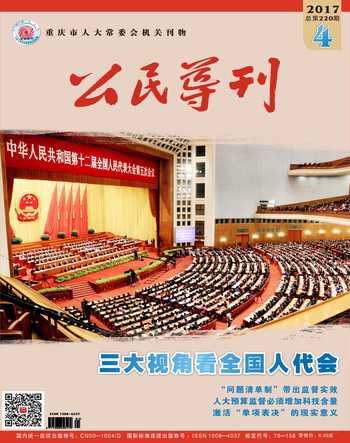民法总则,在争议声中是怎样炼成的?
帅恒
回望民法总则的立法过程,自2016年6月起,法律草案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代会的4次审议,始终争议不断、分歧难消,其激烈程度在中国立法史上实属罕见。而在激辩声中最终炼成的民法总则,也足以成为凝聚立法共识、破解立法难题的典型标本。
行为能力,年龄门槛的平衡
如何设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下限?是民法总则最大的立法焦点之一。
根据1986年出台的民法通则的规定,10周岁以上、18周岁以下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而在现实中,10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自行购买文具、零食等行为比比皆是。而法律所设定的“10周岁”门槛,却使这些交易在理论上均为“无效”,这既不合理也不现实。
学界普遍认为,经历三十多年的社会变迁,儿童的智力水平、辩识能力等等已远远超过民法通则当年立法时的预期,应当参照世界各国的普遍经验,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起点下降至6周岁。这一动议,最终体现在去年6月提交一审的民法总则草案中。
然而,这一立法方案却激起了一片反对声浪,以至演变成民法总则立法过程中最为激烈的立法争议。不少参与立法审议的人士指出:6周岁的儿童并不具有足够的认知和辩识能力,赋予其一定的民事行为能力,意味着儿童刚刚进入小学甚至尚在幼儿园阶段,就需承担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存在重大的制度风险,不仅不利于保护儿童及其家庭的合法权益,还可能给欺诈等行为提供空间。
民间舆论场的反弹更为汹涌,网络上更是犹如炸开了锅,弥漫着焦虑、质疑情绪。有人叹息今后将频频为孩子的任性交易买单,有人担忧孩子经受不住商家的引诱和欺诈,还有人预言,孩子拎得起“酱油瓶”,但拎不起民事责任……
尽管直到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法律草案依然维持了“6周岁”方案,但争议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加激烈。最终,草案在表决前夕作出了重大调整,既未退回“10周岁”,亦未一步突破至“6周岁”,而是设立了相对折衷的“8周歲”门槛。
根据新出炉的民法总则的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获得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后,“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但以何种标准判定是否“相适应”?恰恰是最大的难题所在。
破解难题的路径或许是,通过制订司法解释等方式,明确“相适应”的标准。比如学界通说认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的行为应当限定为,满足日常生活的、定型化的、标的不大的民事行为,纯获利益而不承担义务的民事行为,以及以某些人身权为基础的权利、发明权、著作权等等。但这些理论学说能否转化为实践标准,防止司法裁决陷入大量“模糊地带”,并非易事。
监护制度,现实难题的破解
如何定位居委会、村委会在监护制度中的职责?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二审稿均规定,在没有合格监护人的情况下,由居委会、村委会或民政部门承担监护责任。这一设计,意味着将“两委”的监护职责置于民政部门之前。但不少异议认为,随着社会转型,居委会、村委会的职能已明显弱化,经费、人员普遍不足,既不具备监护能力也缺乏监护意愿。因而,相关立法方案并不具有可行性,应当强调由民政部门等公权力机构更多地承担相应职责,而非将基层自治组织列为责任主体。
面对各方的批评意见,草案三审时作出了回应,明确在监护人缺位时,由民政部门承担监护职责,而“两委”作为补充主体。这一重大调整,不仅真正确立了民政部门的法定义务,更昭示了国家责任的时代高度。
更加令人注目的监护权恢复制度的不断改进。草案一审稿曾规定,“原监护人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指定的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但不少质疑者认为,这一制度设计存在极大的风险,其理由是,撤销监护权的情形均属严重损害被监护人利益,而所谓“确有悔改”极难通过证据认定。
但也应当看到,监护关系普遍由家庭纽带所维系,尤其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其血缘亲情更是难以割断。因而,全面否定监护资格恢复制度并不可取。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利弊得失,使制度设计更趋合理。草案二审稿为此作出的重大改变是,将“恢复监护权”的适用范围,大幅限缩至未成年人的父母,并且增设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限制条件。
及至三审,法律草案应各方意见再次作出“一放一限”的重大调整。所谓“放”,乃是基于现实需求,将“恢复监护权”的适用范围,放宽至“被监护人的父母或者子女”,虽然不再限定于“未成年人的父母”,但仍立足于家庭范畴。所谓“限”,乃是针对现实中存在的监护人严重虐待被监护人乃至性侵害未成年子女的恶性案例,进一步增设了监护权恢复的限制门槛,明确对监护人实施故意犯罪的监护人被撤销资格后,不得恢复。
从一审到三审,监护权恢复制度博采众议、不断调整,朝着最大程度保护弱者利益的方向渐行渐深,直至达成最大公约数的制度成果。
诉讼时效,弱者权益的关怀
如何改革诉讼时效制度?是制订民法总则时争议颇大的一大焦点。
多年以来,我国民事诉讼设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仅为2年,这与世界许多国家10年、20年乃至更长期限形成了强烈反差。然而随着交易方式与类型的不断创新,权利义务关系的更趋复杂,2年期限日益显现“过短”的窘迫。普遍认为,诉讼时效期间过短,不仅对权利人保护明显不足,抬高了权利救济的成本,而且助长了机会主义盛行,纵容老赖逃避债务,阻碍诚信社会的建立,与传统道德、公平正义抵触太甚。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民法总则的一个重大立法动议是,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2年延长至3年。但在草案討论过程中,不少批评认为这一调整方案过于保守,并主张应当提高至5年。不过也有观点认为,时效过短固然不利于保护权利人,但时效过长也会助长权利人的惰性,影响经济秩序和效率,延长至3年而非一下子大幅延长至5年,是更为合理的折中方案。
相比于普通诉讼时效期间调整幅度的争议,民法总则旨在保护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的诉讼时效制度突破,却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力挺。
有统计显示,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中,邻居、亲戚、朋友等熟人加害的占七八成左右,其中,监护人直接加害的又占20%左右。而受害者的权益保护却深陷困境,一方面,未成年人无力自我寻求法律救济。另一方面,传统观念和现行诉讼时效制度的束缚,又导致此类案件最终因时间的流逝而沉没。
不少人士因此呼吁:应当参考一些国家的立法经验,创设保护遭性侵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时效规则。这股强大的声浪,促成民法总则草案二审稿增设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进而为未成年的性侵受害者成年后寻求法律救济开辟了通途。这一被舆论形象地喻为“秋后算帐”的特别条款,在一片点赞声中最终载入正式出台的民法总则,并被视为最具人文关怀色彩的立法亮点。
回望民法总则的立法道路,诸多引发激烈争议的焦点议题,大多已找到了凝聚各方共识的理想答案,亦留下了一些尚待未来破解的立法悬念。但不管结果如何,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立法争议,既是立法所面临的挑战,也是推动立法前行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