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打架时,我们在打些什么?
午歌
昨天晚上姐姐约我下馆子,饭吃到一半电话响了,没讲几句话,老姐脸色都菜了。
“咋回事?”
“你外甥跟人打架了——”
“小男孩偶尔冲动一下,收拾个把人,不算啥。”
“事实上,是他被揍了,脸都肿了。”
“小男孩从小承受一点点挑战和打击,不算啥。”
“你倒是挺乐观。”
我夹起一只鸡翅,边啃边说。
“有个哲学家讲过,小孩子打架拼的是发育。”
“那你是怪姐姐没把他养好啦是吧?”
“当然不是。”
我夹过另一只鸡翅,放到眼前的盘子里。
“哪个哲学家说的?”
“罗永浩。”
“电视购物里卖锤子的那个?”
“额,是卖锤子手机。”
“看他的样子,也没见他发育得多好啊?”
“额……姐说的有道理。”
很快,第三只鸡翅也被我啃干净了。
“你甭吃啦,跟我回家。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外甥好好谈一谈。”姐说。
“好啊,服务员,剩下的鸡翅给我打包!”我是个爽快人。
一路麻溜地开回老姐家,外甥挺着个紫茄子脸瘫在沙发上。
“是谁先动手的?”我问。
“不管谁先动手都不对。”老姐抢话。
“是他。”茄子终于开口了。
“为啥呢?”我问。
“他借了我五毛钱很久都不还,还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推我。”茄子说。
“到底是因为五毛钱,还是因为他推你?”我问。
“这俩有啥不同?屁大点事。”老姐说。
“当然不一样,前者的话,你是暴力催债,后者叫誓死捍卫自个的人身自由。”我说。
“扯犊子吧,你!”
老姐说着,从包里掏出了鸡翅,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起来。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聊聊你自己的经历,比如小学、中学、大学你都是怎么过来的。”老姐说。
“我觉得可以。”我解开了塑料袋,掏出一个鸡翅,慢悠悠开启了我的故事。
那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光明小学读五年级一班,班上有两个女生特别让我在意,一个叫沈玉,一个叫马晓。沈玉是我的女神,是班花,坐在前排。沈玉有一张大月亮脸,笑起来明月出天山。马晓是我的同桌,是女生堆里的骆驼(俺们那旮沓,喜欢把个头高的同志,尊称为骆驼)。马晓有一张大雀斑脸,笑起来苍茫云海间。
那时候我是男生里个头最高的,但马晓发育得更好,足足比我高出半个头来。她是女生里的大姐大、扛把子,但凡女同学走个夜路、闹个感情纠纷或者掰饬个经济问题,一定找马晓来出頭。马晓学习并不好,有次考试的时候她还拿眼睛一直撩我,撩我和撩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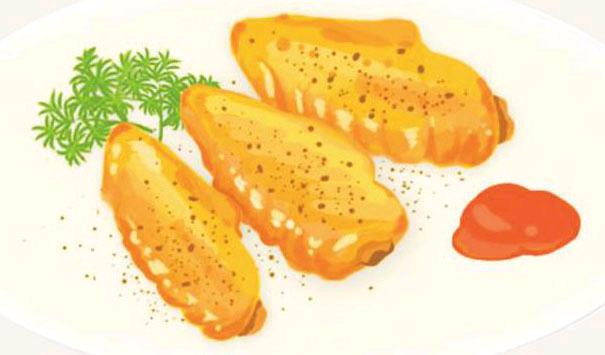
我说,你再偷看我试卷,我要告老师啦。然后我一不做二不休地举起手。马晓极淡定地抬起一条大长腿,慢条斯理地把我踹出两米开外(马晓在体育部主修标枪)。
我在心里默念着:好男儿不跟女同志较劲。所以我被踹飞的时候,并不觉得十分伤感。甚至我在从地上爬起的时候,我还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对监考老师小声说:“铅笔滚地上了,我去捡了一下。”
沈玉因为长得好看,长期受到高年级学长的骚扰。有次一个初中生把她叫到操场上表白,还企图动手动脚,我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担心发育得不如学长好。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心急火燎地冲了上去,对着他俩轻声说道:
“对不起,打扰一下。沈玉,数学老师让你现在马上过去一趟,赶紧的!”
初中学长瞪了我一眼,一脸不屑地走了。
没过两天,这家伙又来了,硬生生拉着沈玉去小操场。还好这次有马晓在,她很快跟学长干起来——确切地说是被那个初中生一胳膊肘子怼在胸口上,喘不过气来。这一次,我想打着语文老师召唤的旗号冲上去再试试,可一开口,却变成了:
“别打女生,有种冲我来!”
哪知那个学长对肘击如此执着,夸嚓一下,这次让我也喘不过气来。
我正迟疑着,马晓却捂着胸口去踹那个初中生。只见学长哐的一巴掌扇了过去,马晓应声倒地。我憋着一腔愤恨,准备冲上去咬他,结果学长只是骂了两句,便扬长而去了。马晓望着我,颤巍巍地笑了笑,苍茫云海间的雀斑脸煞是好看。
“小舅,你没再追上去打他?”
“并没有。”
“你这算是打架吗?”
“当然,只不过为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我控制了局面。”
“都说外甥随舅——原来怂是有基因的。”姐姐叹了口气,补充说:“我觉得你可以讲一些正能量的故事。”
好吧,那我继续。
当时我从光明小学毕业,我娘担心如果再不对儿子严加管教,上初中之后早晚要早恋。于是,她托人帮我转了学,送到了离家非常远的一所重点初中里。
有一天,我同桌新买的橡皮找不到了。他说,我怀疑是你拿了,我能不能翻翻你的书包?我回击,班里这么多人,凭啥怀疑我——要翻我书包,门都没有。他说,其他人都跟我是老同学啦,你不让翻,那就证明肯定是你拿了。
我本来初入中学部,人生地疏,一直活得小心翼翼。那天实在忍无可忍,我薅出书包,站在课桌旁,让同桌翻了个底朝天。
“没有哈。”末了,同桌云淡风轻地叹了一句,站起来将书包交还给我。
我缓缓接过书包,用眼睛撩了他,极为淡定地伸出胳膊,一拳凿在他青春无敌的面庞上。他的鼻子瞬时鲜血直流。
“小舅,就为这么点事?”
“你不懂,这关乎一个男人的节操和尊严。”我说。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小孩子都要被你带拐了。”老姐怒道。
我说,那次打架我被严重地处分了,还在全班同学面前念了检讨书,节操和尊严稀里哗啦地掉了一地。从此以后,我不断地反省自律,在高中、大学阶段阅览群书,终于变成了现在这样斯文软糯的谦谦君子。
老姐皮笑肉不笑地活动了活动脸颊。
上班之后,我以为已发育成暖男的我再也不会和人打架了。可事实上,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会我刚刚考出来国家起重机械检验师,被派到一个海島的小村子里检验一台“汽车吊”。要知道这些开汽车吊的小老板,个个土豪又龟毛,设备安全隐患再多,也完全不把国家法定检验放在眼里。
那天,我一大早就联系上一个吊机小老板,追着他跑了三个工地,他总找借口说设备在忙着吊重,不方便配合我的检验工作。末了,我把他堵在驾驶室里,好话说了一大车。他就是不肯下车,坐在驾驶室里优哉游哉抽着“中华”。
“看你这白净的样子,连香烟也不会抽吧?”小老板捏出一根烟,续上火,也不正眼瞧我,兀自吐着烟圈。我掸了掸烟灰,从驾驶室的倒车镜里看看自己的样子:这么多年的读书和教育,的确把自己收拾得很像个无公害的斯文书生——但是,做男人要有点血性不是?
我跳下汽车吊,跑回到自己的车上,摘下眼镜,脱掉电工鞋,换上后备箱里的一双“纽巴伦”,径直朝汽车吊蹿上去。彼时,那小老板正美滋滋地嘬着“中华”屁股。我一把扯开驾驶室门,攥住他的后衣领子,薅萝卜似的把他从驾驶室里连根拔起。
“别他妈的给你脸不要脸,我操,给我滚下来。”
那厮完全懵逼了,张口结舌差点把烟头给吃了。
“要么咱俩打一顿,要么你他妈的滚远点,让我把你的吊机验了!”
“哦,哦……”吐出烟头的小老板,望着比他足足高出两头的我,结结巴巴地陷入深思。
男人打架拼的是发育——他显然意识到这个哲学问题。
“别这么粗鲁呀,你。”
“滚开,去拉个三吨的配重来,我要做试验用。”
“哦,哦,你等着啊,你等着……”
开了土匪外挂的我,发现事情竟然顺利得出奇。大概这小老板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剽悍的工程师吧,他迈开小碎步,哆哆嗦嗦地跑远了。
“你胆儿真肥啊,你不怕他回村里叫一帮人过来揍你一顿吗?”老姐终于插话。
“开始真没害怕,过了好一阵小老板还没回来,我就开始担心了。”
我暗想:“哥们儿今天不会栽了吧——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的时候,同时还放出了一条狗。”
“舅舅,那后来呢?”
“我就站在吊机顶上往远处看,看到小老板开着一辆叉车回来的时候,心终于咽回到了肚子里。后来,小老板中午还请我吃了顿饭,点了老些个海鲜呢!”
“这人真是欠揍啊!”
“嗯,但我不是因为他欠揍才教育他的。我要依法检验他的设备,这是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
“舅舅你真厉害!”
“不!我不应该用打架来唬他。《教父》马里奥·普佐说过,最好的威胁是不采取行动,一旦行动了,人们就不再怕威胁了。”
“这……”茄子外甥摸摸脑袋,迷茫了。
“教父是谁?你这都什么知识储备?还有没有一些健康积极的正能量?”老姐发飙说。
我总结陈词道:说到底,打架是不对的。男人的胸襟是博大的,你应该学会宽容。屠格涅夫说,不会宽容别人的人,是不配受到别人宽容的。斯宾诺莎说,人心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爱和宽容征服。苏霍姆林斯基说,有时宽容引起的道德震动比惩罚更激烈。
姐姐的脸上终于绽出微薄的笑意:“听到没?舅舅读书多,跟舅舅好好学着点。”
“鸡翅凉了,姐,你去翻个热吧。”
姐姐转身离开,我趁机对眼前这个茄子脸男人厉声说道:
“上面这些人,有什么共同特点你知道吗?那就是,他们的名字都叫作——战——斗——民——族!”
我说:“你记着,男人不是不能打架,而是不要为了五毛钱就动手,不要为了别人推你一把、踢你一脚就还击。”
我说:“你看看小舅为什么打架?第一次是为了保护喜欢的女生,第二次是为了男人的节操和尊严,第三次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你懂了吗?”
连珠炮似的说了一大堆不要脸的话,我的脑袋涨得通红。微波炉在厨房“bi”的尖叫了一声,就在老姐回来前这电光石火的瞬间,我抓住茄子的手说:“你记住,在男人不得不打架的时候,一定要他妈的先动手。这是精髓。”
香喷喷、热腾腾的鸡翅被端了上来,气氛一下子就缓和了。
(刚好摘自“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