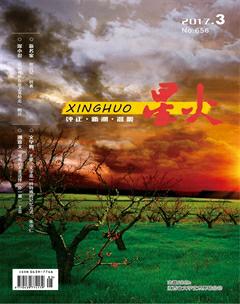最难的不是选择(外一篇)
王芸,中国作协会员。生于湖北,现为南昌市文学艺术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江风烈》,散文集《经历着异常美丽》《接近风的深情表达》《纯净与斑斓》《穿越历史的楚风》《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倾城张爱玲》。近200万字散文、小说刊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刊,有作品及被收入《21世纪年度小说选·2010短篇小说》《2010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10散文》等选本。
《妙笔生花》(《The words》)
[美]2012年版
导演:布赖恩·克卢格曼,李·施特恩塔尔
演员:奥利维亚·王尔德,佐伊·索尔达娜,布莱德利·库珀
妙笔可以生花,生出的却是虚妄之花。小说本质上就是无中生有,电影也是。
影片《妙笔生花》在一部小说中嵌套着另一部小说,一本书的作者身后隐藏着另一个作者,一个故事里环套有另一个故事,由此衍生出了最外层那个看似真实、实则虚构的故事。
作家克雷出版了他的新书《THE WORDS》。在新书朗诵会上,他朗读自己的作品,遇见了一个年轻女人。如果这是影片的现在时,那么影片还有两重过去时,在另外两个时间节点上链接有另外两个故事。影片结尾,年轻女人试图进入克雷的生活空间,探究小说是虚构还是真实,某一时刻她将扮演揭露者的角色,她能否揭开所谓的真相?
在抵达这一刻之前,影片需要先讲述两个环套在一起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一部作品如何和两个“作者”相遇。
罗瑞·詹森,一个一直做着作家梦却始终寂寂无名的写作者,终于因一部作品登上了领奖台。虽然不是一个多么大的奖项,但镁光灯聚焦在他身上,他成了纽约文学界冉冉升起的星星,被出版界、媒体、读者关注。看起来,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梦想,拥有了渴望拥有的一切。但,这部获奖作品并非出自他的灵感、他的笔端,他不过是将它誊抄了一遍,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作品的真正作者循迹而至,一个曾以自己的全部激情和生活经历铸造这部作品的不知名的写作者。他一度丢失了这部作品,却越过漫长的时光在别人的书中找到。
真相只有两个人知道。说,还是不说?罗瑞面临自我审视的关口,道德层面的危机,最终他做出了选择,并带着这选择继续生活。他,是否就是克雷的过去时?小说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多大程度上是虚构的?不管罗瑞与克雷有无重合,现实中的疑难是如此真实、具体、锐利,不容回避。
“罗瑞已经拥有了他曾经梦想拥有的一切,而那位老人却还在某地等待着,他的一举一动或许都会让现有的一切发生巨变……”作家克雷朗读着书中的情节,将我们带向另一个时间节点。
年轻的罗瑞大学毕业后,和未婚妻朵拉搬到一家旧工厂的阁楼上,带着他的写作梦想开始新生活。白天,他在纽约这座城市漫游;夜晚,他在寂静中勤奋地写作。没有工作的他,需得向父亲要钱用于支付日常生活费用,而他花费三年写出的作品一再被退稿或杳无音讯。尴尬的生活状态,不被肯定的写作状态,让他看到的是命运不肯青睐,而父亲看到的却是他自身的局限性——他适不适合那个梦想。年轻人急需证明自己,证明自己配得上文学梦,却在铁面无情的现实面前,不得不先为生计谋。他进入一家出版社工作,依然怀揣着自己的作品可能遇到伯乐的奢望,但一再碰壁的现实,让他不再在深夜勤奋地笔耕,他似乎开始满足于过平凡的日子。在去巴黎的新婚蜜月旅行中,他与一个老式文件夹不期而遇,它被塞在古董店不起眼的角落里,却被他一眼挑出,仿佛命运的安排。在这个旧文件包里,躺着一部不知尘封了多久的书稿。这不知来处的书稿,连作者的名字都没有,唯一明晰的线索是按在稿纸边缘的一枚墨印指纹。
“这些文字,让他看见了自己渴望得到的一切,也让他看清了自己永远无法成为卓越作家的现实。”克雷的朗读将两重时间联接在一起,使整部影片的节奏有张有弛。
这部并不厚重的书稿,以一种奇异的力量冲击着罗瑞,侵入他的生活,并轻易地撬动了他的生活,让他质疑自己的才能,自己的梦想,自己过往的生活,自己已有和将有的一切……文字就是具有这样的魔力,带来怀疑、颠覆、震动、恐惧,同时建设、改变、修复。
罗瑞仿佛被这部作品伸出的无形的手,紧紧地攫住。寂静的深夜,罗瑞终于抵挡不住内心的欲望,在打印机上敲下了第一个字母,和旧书稿上的,一模一样……
谜底慢慢呈现——并非罗瑞刻意将这部作品据为己有,而是妻子误会这是他的新作品。她无意中读到这些文字,一口气读完,溢出泪水的眼睛,看着他的激动表情,无法恰切表达的话语,让罗瑞渐渐放弃了否认,放弃了挣扎。他开始恍惚觉得这部书稿真的出自他的笔下,就应该出自他的笔下。他似乎别无选择,虽然他随时可以开口,告诉妻子:这是别人的作品!
“这些故事和你之前写的都不一样,感觉就像你不再回避自己内心的想法,它们更加饱满,更加真实,也更为诚恳,我从小说里看到了你自己的一部分,属于你但我从未见过的一部分。”朵拉被感动得流泪,激动不已。这段话,多么恰切地解释了误读的存在。读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将一个写作者的内心情感、图景移植给了另一个人,并声称从中捕捉到了另一个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
罗瑞没有勇气否定、纠正这一误读。他踏进自身局限的沼泽,不肯拔出腿来。“有了这个作品,罗瑞,你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在妻子无比信任的鼓励下,他将书稿交给了一位资深出版人。“你创作了一部非凡的文学作品。”权威给出的评语,让曾经梦想的一切,忽然间近在咫尺了。书,顺利出版,并且畅销。罗瑞没有料到盛大的荣誉,他切盼得那么辛苦的一切,如此轻易地到来了。
然而,旧书稿上的墨印指纹,那独属于某个人的物证,并不肯沉溺于时光深处。它浮现出时间的水面,带我们进入另一时间节点,也是这部书稿的真正起点。作品的真正作者,出现了。
1944年,另一時间节点,一个参军入伍却从未经历过战争的美国男孩,奔赴欧洲战场。战后,他随部队驻扎巴黎,一座远离家乡的城市。这个在部队里成长的青年,修过被德军破坏的地下道,搬运过踩上地雷的尸体,从战友递给他的书中看到了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那时,写作的梦想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青年与巴黎女孩西莉亚相恋,却面临退伍后的分离。已经领略了外面的广阔世界和书中的广阔世界,青年无法再适应家乡狭小的天地,也无法忘怀恋人。他重新回到巴黎,进入一家英文杂志社边学习边写作。很快,他和西莉亚结婚有了孩子,可是生活不肯按人的意愿发展,孩子得病死去,将他们的生活划开一道深邃的裂纹。
妻子整天以泪洗面,并选择离开他回到家乡。而他烂醉如泥,生活似乎难以继续。是写作,这一直难以被他抓握的漂浮之物,仿佛天使降临他的身边。痛不欲生的时刻,他拿起妻子留给他的信,在背面打出第一行文字,仿佛开启了情感与思绪的泉眼,水流狂泻而出。他的手指不停地敲动,在稿纸上显现出那些仿佛是上天恩赐于他的滔滔语流。
小说一气呵成。这不可复制的过程,将他救赎的过程,重新让他充满了力量。
生活难以完美。当妻子终于又回到他的身边,那部刚刚完成、靠激情驱动的小说,却被她不小心遗落在了火车上。“这个故事本来没有任何意义,但书写这个故事的过程却以某种方式将他救赎。”对书稿的看重,让他无法原谅和看淡妻子的无心之过。已经被撕裂的生活,进一步分裂,直到他离开巴黎,回到遥远的家乡。
他从没停止过思念她,却也从没想过去寻找她。一天,坐在火车上的他,意外地看见站台上分离很久的她,她在一个孩子和一个男人身边,她已是一个母亲、一个妻子。他们隔着车窗,火车缓缓启动,还未来得及挥手告别,便移出了对方的视线。
只有在失去了一切之后,他才意识到这样的失去对他意味着什么。但他没有去追问,这个巴黎女人为什么出现在美国,他的家乡。那是他的选择,他必须带着这选择继续生活下去。他的余生沉浸在悔恨中,冀望从平朴的生活中找回内心的安宁,他再未与曾经的激情相遇,再没有写出过让自己满意的文字,他放弃了文学梦,就仿佛他从未写出过那样一部杰出的作品。
写下这部书稿的年轻人,已身心颓萎,垂垂老矣,却在书店里与一本新书相遇。他吃惊地发现,书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熟悉,仿佛往事历历重现。在如此境遇下,与自己的旧作重晤,该喜还是该悲,该笑还是该叹?他一定为此辗转多时,感慨万端,最后决定出现在颁奖典礼的现场门外,在大雨中,目送罗瑞离去的背影。此时,沉浸在兴奋中的罗瑞,对即将到来的危境还一无所知。
老人与罗瑞在公园中的一场对话,是难度极高的桥段,一明一暗的对白,深藏内容的眼神,莫可名状的心情,尽在简洁干净的镜头语言中呈现,却又意味深长。
老人盯视着这个剽窃者,这个将自己的名字署在别人的作品上、似乎毫无愧疚的年轻人。后者已经从内心安然地将这部并不属于他的作品认领为了自己的,却不知危险正在逼近。老人的脸上带有隐隐的嘲讽的笑意。
“今天感觉如何?”
“挺好的,你呢?”
“你懂我的意思吗?”
“当然。”
在接下来一段精彩的对白中,奇妙的是,没有歇斯底里,没有咄咄逼人,“生活对你很仁慈。”老人仿佛一个关心此书的读者,不断给予作品赞美,并看着罗瑞不断以“谢谢”领受这赞美。他不疾不徐地将话题引向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个男人的故事,他写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丢失了,接着一个平凡的孩子找到了它。”老人说这话的表情,是曾经历过地震和海啸的生者,捱过漫长的时间、所有的绝望和伤痛都被时光层层掩埋之后的表情。他以极其平淡的语调说出的这句话,让罗瑞离开的身影定格。
转过身,罗瑞轻松的表情和心情发生了巨变,连同他的生活。
这一转身,成为罗瑞生活的一道分水岭,也让这部书稿的两个“作者”有了真正的交集。罗瑞重新坐下来,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听老人讲完了这部书稿背后的故事,一个男人的真实人生。漫长的故事抵达终点——“这是我的文字,我的故事。”老人望着罗瑞,清晰地说出这句话,然后起身离去。原来,他只是为了向这个剽窃者讲述这本书背后的故事,既然他占用了此书之名,那么就要承受关于此书的一切。做完这些,他的心才能获得平静,回过身去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原来,老人并不打算向全世界揭露罗瑞。
罗瑞被留在原地,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审判和内心的磨折,没有人逼迫他,没有人威胁他,但他过不了内心的那道关口。他不想后半生被道德的枷锁锁住,他不想继续承受被撕裂成两半的痛苦,他宁可说出真相将自己从这折磨中解脱出来。他将自己灌得烂醉,借着酒力壮胆向妻子坦陈了作品的实情。仿佛昔日裂纹的重现,虽然原因不尽相同,却情形相似,在一个丈夫和一个妻子之间,横亘着一部书稿,横亘着一个人关于文学的梦想和野心,横亘着破裂的信任,横亘着无法挽回的既成事实。分离,成为他们共同的宿命。
罗瑞也向资深出版人道出了实情,但所有人都阻止他将这一事实公开,甚至连老人也拒绝接受罗瑞带着愧疚的偿还,物质的和精神的,他都不要。
“你拿走了这些文字,就要承担相应的痛苦。”这才是老人讨要的公正。这位在花圃侍弄着花草的老人,已无法责怪任何人,包括命运,哪怕真的是命运安排了人世间的这场错失。罗瑞的偿还对于去日无多的他,没有任何意义。他要的只是告诉罗瑞关于这部作品真实的一切,因为时光不可再来,他为这些文字支付的欢乐与痛苦,他曾遭遇的一切,都不会重来,但他要将自己的人生,那沉甸甸的结满了痛楚的花果的人生,讲述给一个人,交付给一个人,一个从命运之手中接过了那部书稿的人。
或许,老人尚存的奢望,是有一天自己的故事也能变成文字,继续在世间流传。
“我们在人生中都会做出许多选择,带着这些选择继续生活,才是人生中最难的一课。这件事没有人能帮你。”这是老人说给罗瑞的一段话。他就是带着自己的选择,平凡却又艰难地度过了自己的后半生。罗瑞在文字建造的虛拟世界中,也将带着自己的选择继续生活,与妻子分开,在老人死去后将旧书稿放进他的墓地。老人的死,让罗瑞解脱,也让老人充满痛楚的一生解脱。一个秘密随之被时光掩埋。
似乎,一切尘埃落定,曾经的煎熬、曾经的挣扎、曾经的纠结、曾经的审判都已被时光抛掷到了身后、远方。
但真的可以掩埋吗?在寂静无人的深夜,那些往事的沉渣会否重新泛起。在某些无法逃避的时刻,悔恨和泪水会否将罗瑞吞没。又或者,他将一切掩饰得很好,弥合得很好,他生活得非常体面,将成功一再扩张,仿佛从来没有过裂痕的存在,没有过老人和旧书稿的传奇。一切都是梦幻般的虚构。又或者,他真的将这真实的故事放进了小说虚构的形式中。这就是年轻女人和作家克雷最后那场对话的焦点。
当读者恍惚以为这是发生在作家克雷身上的真实故事时,克雷为自己做出了辩护,他以“小说本就是无中生有的艺术”作为盾牌,挡住了年轻女人射来的箭矢。他说服了年轻女人,让她臣服,讓她顺从,让她心生爱慕。年轻女人发出质疑时,仿佛无数读者派出的一个代表,但作家克雷让她放下了质疑。
影片颠覆了我们的判断,或者说解构了我们的认知。这让先前发生的故事重新坠入现实与虚构之间的迷雾地带,难辨真伪。
影片的最后一幕,克雷脑海里晃过罗瑞和妻子朵拉拥抱的一幕。他在回忆的恍惚中望向镜头,望向我们,或者说时光深处。剧终。
终有一些过往是无法逾越的。任何一种选择,都需要付出代价。
“带着这些选择生活,才是人生最难的一刻。”
音犹在耳,余响不绝。
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完美
《完美的世界》(《A Perfect World》)
[美]1993年版
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
演员:凯文·科斯特纳,克林特·伊斯特伍德,T·J·劳瑟
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完美,我们还是迷恋着这个世界;尽管有那么多的不完美,逃犯海恩为男孩菲利浦营造的“完美世界”还是那么强烈地打动了我们。
一个成功逃狱的囚犯和一个不能参加万圣节游戏而心情失落的8岁男孩的相遇、同行,我愿意理解为是上天的慈悲,是命运使然,让两个可怜的人拥有一段短暂的“完美世界”,成为彼此缺憾人生中珍贵的慰藉。
因为同伴的冒失举动,海恩不得已将男孩菲利浦带上了逃亡之途。从头至尾,他都没有伤害过这个男孩,甚至为了菲利浦,他杀死了一起出逃的同伴。似乎,这是个杀人从不手软的家伙,内心凶残。可是直到影片最后,当海恩的一生像碎片一般被拼贴起来,我们才知道并非如此。没有人是天生的罪犯,只是走在命运的路途上,所遇到的一些人与事将他塑造成了这个样子——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坏人”。
关于好人与坏人,当我们年少尚未对世界建立起独立判断时,我们会被概念化的呆板教育系统灌输“非好即坏”的观念,好与坏是彼此对立的阵营,是将所有人划分为两大类的分界线。阅世渐深,当我们开始用审视的目光看待这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来真正思考这世界,拥有更多的宽容面对这世界时,我们才知道在好与坏之间,存在着十分广阔的地域,如同在黑与白之间存在灰色地带,且是深浅层次非常之丰富的不同色度的灰。世界不是绝对性而是相对性的,不是可以简单归类和定义的,复杂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方式与本质。善与恶可以在瞬息转换。而一个好人可能因情势所逼生出恶念,做出恶举;一个看起来十恶不赦的人,也有他值得被同情、被怜惜、被原谅的地方。
片中有两段对话。一是海恩用枪对准黑人农夫时,他的黑人妻子抱着孩子对他说:
“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个好人。”
“我不是个好人,也不是最坏的人,只是与其他人不一样。”
后来我们知道,那一刻海恩并没起真正的杀念,他只是完成着潜意识里对父亲的惩罚,一个从他六岁开始就离场的父亲。还有一段对话发生在片尾,孩子带着无尽的懊悔表情问海恩。
“你不是坏人吧,布奇?”
“我不是。”
布奇,是熟悉的人对海恩的称呼。这回答,是海恩对自己的认定。的确,他从来就不是“坏人”。
在逃亡的路途上,也许一开始,海恩是想以男孩为人质逃离险境,以男孩为掩护便于逃亡,但是,海恩对待男孩的方式,更像是一个父亲在对待自己的孩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仿佛是上天安排的一场慰藉之旅,已经成长到拥有足够力量的海恩,在八岁男孩菲利浦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而他所做的,是弥补当年父亲未曾给予小海恩的情感与帮助、关爱与赞美。
他在路途上为菲利浦营造了一个游戏世界。他们乘坐的汽车变成“二十世纪的时光机”,而他和孩子化身为船长和领航员,“前面就是未来,后面就是过去”。劫持人质的逃亡之途,就这样被转换成了游戏之旅。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海恩一下子就抓住了菲利浦的心。慢慢的,他了解到这是一个在父爱缺失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与他一样。因为母亲的宗教信仰,菲利浦没有去游乐场尽情玩耍过,没有尝过棉花糖的甜蜜滋味,没有享受过生日PARTY的欢乐,没有在万圣节扮演小精灵的权利……听到这些,海恩一定暗暗下定决心帮男孩弥补这些遗憾。他让菲利浦在纸上列出所有想做而不被允许去做的事情,承诺帮他一一实现。可是后来,当他知道自己无法帮菲利浦做到这些时,便以“释放菲利浦”为条件让他的母亲允诺菲利浦。多么不合逻辑的谈判条件,这一刻,海恩已经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一心想的是菲利浦的快乐,菲利浦的未来。
海恩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有着人性的诸多弱点,有时会残忍,有时会欺骗,有时会暴躁,有时会狂怒。可是海恩在面对菲利浦时,却像一个幽默、宽容、温情、尊重孩子的完美的父亲。在一连串的路途遭遇中,菲利浦渐渐对他生出了信任和喜爱。怀着依赖之情,他一再地伸出手去,想牵住那个从小到大都不习惯被人牵绊的人的手。当他们牵手走向田野时,那背影看起来真像一对走在回家路上的父子。
与此同时,一个以警察局长瑞德、州长派来的德州监狱犯罪专家莎莉、联邦调查局警员组成的追逃班子迅速组成。他们乘坐一辆崭新的拖车房,开始了追逃之路。他们与逃犯形成对立的阵营,他们似乎是公正的象征、正义的代表,可是在他们的看待和对待世界的方式中,却存在着那么多自以为是的偏见、误解。那是不可避免的人性的局限。
影片《完美世界》渗透着美国式的幽默,让人感觉不到通常追逐逃犯戏的紧张激烈,而仿佛这真的是一场无关生死的游戏,尽可以轻松对待,轻松观看。
同样堪称完美的“游戏”,在我看过的影片中还有一部,《美丽人生》。那是一个父亲出于爱为孩子营造的一个游戏世界,将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疯狂成功隔绝在外,让痛苦而艰难的战争时光成了欢快的游戏时光。只是到了最后,这创造和维护游戏世界的人,不约而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追逐一波三折。警察的反應总是比海恩慢半拍。这使得海恩和菲利浦可以轻松自如地进行他们的游戏。在游戏中,男孩扮演“印第安人”充当了海恩偷车的帮手,与他一起劫持了郊游一家人的新车,讨要食物变成了“糖果或捣蛋”的游戏。海恩非常细心地呵护着八岁男孩敏感而脆弱的内心,他尽可能地给予他鼓励,让他变得勇敢,将各种行为中的罪恶因素过滤掉,告诉孩子“永远别低估一般人的善心”,“偷窃是不对的,懂吗?但如果你真的需要,又没有钱,你可以暂时借用一下,这叫做例外”。一路上,菲利浦有过可以离开他的机会,却选择了跟随他。
他们在黑人农夫家里受到了善意的对待。可黑人农夫对自己孩子暴力的举动,触动了海恩内隐的神经,那里牵扯着陈年的伤痛。突然之间,他变得暴虐、冷酷、怪异,他逼迫农夫对孩子认真地说“我爱你”,用绳索和胶布将黑人农夫和他的妻子、孩子捆绑起来,用手枪对准农夫颤抖的脖颈……在这一连串行为背后,满满的都是属于他自己的伤痛——是他不曾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我爱你“,是他不曾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关爱,留下的遗憾。他只是在潜意识里惩罚着他永远不可能审判与惩罚的父亲。
原来海恩六岁时父亲便离开了他和母亲。八岁那年,他在妓院用手枪射杀了一个欺负他母亲的人。十二岁时,他母亲在妓院浴室上吊自杀。无人管束的海恩私开一辆路边的福特汽车去兜风,被法官送到最恶劣的感化院度过了四年。而执意将他送进感化院的,正是追逃的警察局长瑞德,他这么做的理由是,对于年少的海恩,进感化院好过将他送到偷盗成性、经常暴打他的父亲身边。殊不知,他的“好意”成就的依然是一个职业罪犯。当我们选择了一条路,就再无法得知如果走上另一条路是怎样的结果,那是我们的命途,独此一趟的路程,不能回头,无法改写,一切命定。就这样,海恩被自己无法抗拒的命运送上了与菲利浦同行的旅途,他生命的最后一程。
八岁的男孩还不能完全明白世事,但对事物具有了基本的判断力,他痛苦地看着海恩暴烈地对待黑人农夫一家,显然无法明白海恩举动的真实含义,无法洞悉海恩的内心,他看到的是表面的无情、威胁、伤害,闻到的是空气中越来越浓烈的死亡的恐怖气息。出于本能,他捡起了地上的枪,将子弹射向了海恩。
其实,海恩并不是一个随意杀人的恶魔,他的异常举动不过是因为愤怒,因为隐痛。在跟随跑向田野的男孩时,他手捂着涌出鲜血的伤口,对男孩说:“我这辈子只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伤害我妈的人,一个是伤害你的人。”他没有责怪男孩一句,他只想唤回他的信任。
原本,海恩打算和菲利浦一起去阿拉斯加,去赴他父亲多年前写在明信片上的一个约定。坐在树下,鲜血已在他的腹部漫漶成片,他大概知道了自己已难成行。他不想男孩继续怀着对他的误解,对他的恐惧,他拿出了父亲写给他的明信片,“亲爱的布奇,只是要告诉你,我的离开与你无关,阿拉斯加是个美丽的地方,常常冷得要死,将来有一天,你可以来这里,我们彼此也许可以更了解一些。”这封短短的信,海恩的评价是“很有感情”。他一直相信父亲对他是怀有感情的,这感情大概是他生存于世的一缕希望。
此时,警车正从四面包围而来,圆圈的中心是一棵树和树下的逃犯与男孩。还有狙击手,已经将枪口瞄准了树下的海恩。
男孩已经平静下来,恐惧的潮汐退尽,他从树上下来,伏在了海恩的身上,流着泪对他说“对不起”。这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再也止不住,一直汹涌到结局——菲利浦紧紧地抱住了海恩。
其实,这并非结局,但我希望这是。所有的追击到此为止,所有的伤害到此为止,所有的遗憾到此为止,所有的不公到此为止,还海恩一个“完美世界”。可是,那只是我作为一个观众的美好愿望。
影片的最后,本来有可能与菲利浦手牵着手走向新生的海恩,还是被射杀在广袤的田野上,手里拿着多年前父亲寄给他的那张明信片。那里装载着他只对菲利浦诉说过的,他对父亲的深情。其实,他一直记着自己的父亲,他喜欢福特汽车是因为记忆中的父亲一直开福特,他保留着这张明信片,因为这是唯一能证明父亲对他情感的物证。
男孩从他僵硬的手指间抽出了明信片,这段发生在他八岁生命时段的短暂旅程,想来会镶嵌在他的记忆中,终生不泯。而海恩的心魂,会否在他生命的底板上留下消退不掉的印痕?多年后,长大的菲利浦会否践行海恩未了的心愿,赶在大雪之前去到阿拉斯加?
作为观众,我们拥有近乎全能的视角,我们知道之中的那些误会、偏差、缺憾和不公,知道一个人被这世界和命运所强加的不完美的一生。那么的,让人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