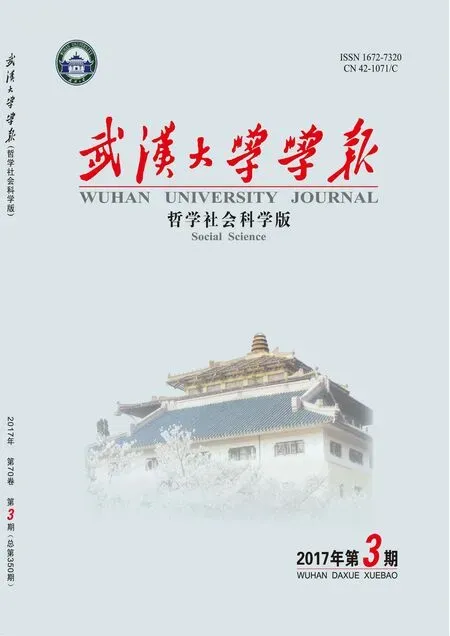从机关思维到程序思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探索
秦前红 底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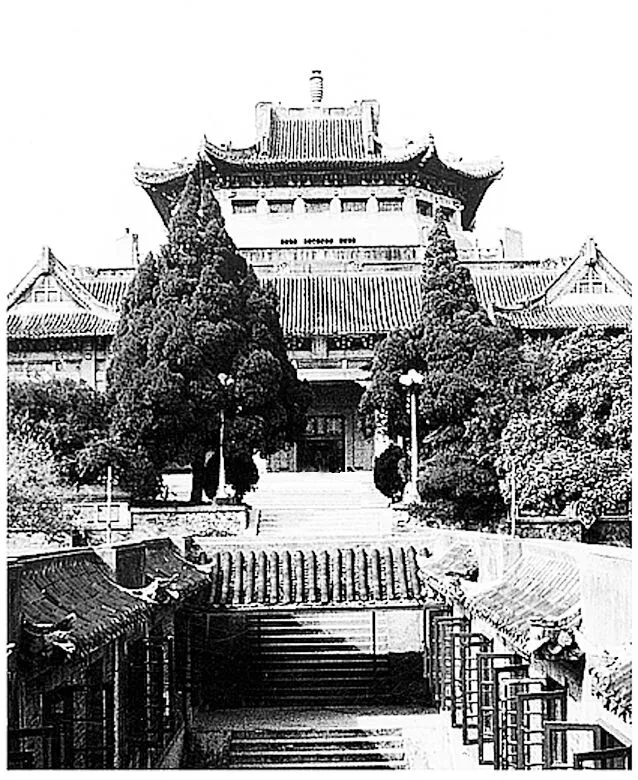
从机关思维到程序思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探索
秦前红 底高扬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当前的相关试点方案倾向于机关思维方法,机关思维以机关主体为中心,是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有违权力制约原则、民主原则等,需要对其予以批判。而程序思维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对权力设置、运作、监督等各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指引的方法,其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且两者的运用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序列问题。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应当统筹运用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和理性场域中获得秩序认同和现代宪法价值共识。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机关思维; 程序思维; 方法论
为了建立执政党领导下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参见《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党中央作出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政治决断。如果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视为我国实施改革的起点,那么近40年的改革实践让我们深深认识到改革的成功与否离不开正确的方法论(赵义,2014:10-11)。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方法论问题是极为重要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可以推动改革的蓬勃发展;错误的思维方法,则会把改革引入困境(艾丰,1993:1)。在我国由注重经济体制改革向“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改革变迁过程中,改革方法论也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转变为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更加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一点可以从重要官方文件中得到佐证。从所搜集的重要官方文件发布时间来看,其最先出现在2010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其他的包括《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试点方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等。。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言,其采取了“顶层设计+试点实践”*《试点方案》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此外,其选定了北京、山西、浙江3省市为试点单位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的方法,这符合现代化治理体系建立的一般程式*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建立是顶层设计与实践经验的综合体。参见蓝志勇、魏明:《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载《公共管理学报》2014年第1期,第1页。国家监察体系是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自然也应遵循这一方法论。。但进一步追问,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之内涵为何?
欲理解之,我们首先从“改革的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本身谈起。通说认为,其内涵在于就深化“改革”的目标模式、框架结构、重点领域、方式方法、运行机制和成本收益等方面的问题,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主导下,作出战略性和系统化的总体安排与部署(王建民、狄增如,2013:140-141)。除此之外,还有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说、制度总体设计说、科学决策和战略管理说等。我们认为,上述界定方案各有侧重,勾勒了“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基本框架。然而,其也存在诸多弊端,比如,顶层设计者的认识有局限性,这种列举式的界定方法可能出现“挂一漏万”的失误;我国幅员辽阔,地方差异悬殊,对重点领域的界定、方式方法的选择等作出统一安排,可能会犯“一刀切”的错误等。实际上,改革的顶层设计是难以用具体的要素和维度来界定的,而且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前,对其具体内涵进行界定无异于“盲人摸象”、“管中窥豹”,反而背离了顶层设计的初衷。
政治现代性是围绕主体性与理性展开的现代宪法价值取向和秩序认同(刘红燕、宋惠敏,2013:208)。基于这样的论断,本文以权力改革为对象,发现以往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以机关主体为切入视角,并以其为中心设计职权关系、组织体系、实施程序等,这种顶层设计方法有利于整合权力主体、推动主体性和秩序层面认同的进程,但它简单粗暴,缺乏理性和现代宪法价值*现代宪法价值不是指宪法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是现代宪法所追求的价值。关于其具体探讨可参见王崇英:《现代中国宪法价值初探》,载《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21~23页。指引,是一种形式权力改革观。在此,我们提倡一种实质改革观,即顶层设计以“权力”为视角切入,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在尊重权力客观运作规律的基础上,检视权力程序中各个环节,找寻其间可能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并予以弥补或防范,从而实现现代权力在宪法视域下的价值统合和体系建构的目标。我们把前者的设计方法称之为“机关思维”,把后者称之为“程序*这里的程序并非教义学意义上的法律程序,而是权力各环节反映的客观规律及其所蕴含的价值。程序思维目的是基于全面把握权力运作规律和特点,识别和防范权力各个环节异化的价值风险点,从而保证权力改革符合现代宪法价值。思维”。从学理上来看:第一,何谓机关思维?其何以成为我国传统改革具有优位性的方法选择?第二,什么是程序思维?其与机关思维是什么关系?其在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过程如何定位?第三,就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而言,如何对这两者作出评价?如何在程序思维视域下对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出完善之策等。以上问题构成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笔者希冀抛砖引玉,引起国家监察体制顶层设计者和学界的关注。
一、机关思维: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
由于我国过去计划思维的持续固化、国家权力的中央高度集中、社会组织力量长期疲软、民主机制不健全等影响,中共在执政过程中,形成了对国家、社会和公民等各层面的行政化治理范式。而治理的思想与等级化的权力、垂直和自上而下的指挥关系以及以整齐划一的方式推行的意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让·皮埃尔·戈丹,2010:14),由此形成了政党政治*在中国,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表现出了自己独特的历史景观,即体制上,政党与政府形成了高度的整合状态;而在功能上,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社会革新、民主法治建设等,都有赖于政党结构。参见:程竹汝、任军锋:《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30页。背景下执政党及其代理者在治理场域中的行政逻辑*本文中所称行政逻辑的主体为执政党,即执政党的执政逻辑表现为行政化治理逻辑。但是,在政治与行政各自独立,(参见James H.Svara,“The Politics-Administration Dichotomy Model as Aber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58,No.1(1998),pp.51~58)的视域下,执政逻辑应区别于单纯的行政逻辑。尽管这种认识与我国政党政治体制存在一定张力,然而在执政党实现依宪执政转型的变迁历程中,应当基于更高的宪法逻辑对这种行政逻辑进行修正,其核心在于将现代宪法价值镶嵌于执政党的执政逻辑中。。
(一) 行政逻辑的解构
行政逻辑是与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主导体制相联系的,强调的是权力上层的意志和行为。行政本质上是执行执政党意志的功能(弗兰克·J·古德诺,1987:41),其实现至少依赖以下几个条件:第一,雄厚的资源优势,这是行政逻辑的基础。这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政治资源等。行政是一个消耗的过程,离不开资源尤其是物质资源的投入和支撑。一方面,管理者为追求资源来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求,才有动力去执行国家意志;另一方面,被管理者只有服从国家意志才能获取其所需资源。第二,强大的制度约束,这是行政逻辑的关键。无规矩不成方圆强调了规矩或制度对秩序形成和维持的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强调了制度对人的限制和约束功能。制度存在于很多形式,包括法律、道德、纪律、命令等。从内容来看,制度包括动员、组织、实施、监督、奖惩等,这些制度预设了行政逻辑从形成到实现的展开过程。第三,坚固的暴力基础,这是行政逻辑的保障。行政是资源整合与调整的手段,利益主导者和利益既得者在利益一致的情境中表现为同盟关系,此时有利于行政的实现;但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两者表现为对抗关系,此时利益既得者构成行政推进的阻力,进而触发行政的防护清理机制,而这离不开暴力(军队、监狱、司法机关等)威慑与实施。
行政逻辑的主要特征可总结为:首先,强调权力主体的整体单一性。权力是行政的逻辑起点,决定着行政逻辑的形成、展开和实现,为了保证行政逻辑的一致性,必然要求权力主体是一个整体而不能分散,是单一的而防止出现多头逻辑,造成指挥系统的冲突和混乱。其次,强调意志与行为的统一性。意志的统一性是行政逻辑的前提,若意志多元化,轻则造成统治资源的内部折耗,重则导致统治系统的失灵,引发政治危机。行为的统一性是行政逻辑的典型表现,它既是意志统一后的外在效果,也是权力主体集中精力,以最小资源投入实现预设目标的不二选择(B·盖伊·彼得斯,2015:230)。再次,通过官僚组织贯彻国家意志。行政逻辑是一种单向度思维,在它看来,互动沟通是对权力主体权威地位的威胁与弱化。此外,官僚组织是行政逻辑展开的载体,其通过运作空间封闭化、权力关系层级化以及部门碎片化来建构统治者强大的控制体系。此外,其边际效应倾向于排斥社会。行政逻辑的外在追求效果在于降低官僚体系运作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将一切可以确定化的不确定性吸纳到系统内部,将一切不可确定化的不确定性拒之门外(周军,2015:21),从而压缩社会的自主参与空间,减少社会对官僚体系的冲击和挑战。最后,追求效率和秩序价值。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是行政逻辑的哲学基础,而效率是检验行政逻辑是否功利最大化的重要标志,加之执政党占有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速战速决”而非“持久战”是行政逻辑胜出的优势所在。当然,行政逻辑终究不是在真空中演绎,其顺利实现需要稳定的秩序支持,基于此,维稳常常是与行政逻辑相伴随的。
(二) 机关思维的形成及其比较优势
行政逻辑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最终选择,而是一定时期内统治者管理国家、控制社会的阶段性方法论。随着议会获得更多权力、多党制出现、公民权的崛起和民主法治环境的转变等(王敬尧、贾鹏举,2000:40),行政逻辑被逐步得到修正。但是执政党仍然将控制重心和着眼点放在承载权力的机关本身,通过控制机关来达到继续维系其统治秩序的目的。在政党主治体制下,执政党的行政逻辑就从政治领域自然延伸到了国家权力领域,形成以“权力机关”为中心的机关思维。
从实证的角度而言,机关思维在我国以往权力改革领域占主导,其受制于被改革权力自身所预设的组织、价值空间,无法在更具超越性的宪法预设的权力价值指引下实现各权力改革的融贯性、有机化,导致权力改革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以被广为诟病的行政权力改革为例,我国自1982年到2008年先后进行了六次较大的以机关为切入点、以“机构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刘厚金,2015:45), 但仅注重机关导向的行政权力改革缺乏权力制约、民主参与和监督、适度经济自由等现代宪法价值指引,并未按照行政权设置、运作各环节的客观规律对行政体制进行宪法化价值审视,遵循的仍是一套管控的行政化逻辑,导致行政干预过多、行政机构臃肿和职责交叉、行政权力腐败等问题不能从深层次得到纾解。再比如,我国司法权力改革领域的指导性案例制度,其本应是最高人民法院遵循司法权的运作逻辑,在进行司法活动过程中充分运用法律技术而形成,但遗憾的是,中国指导性案例的发现和确定机制,指导效力的约束机制都流露着极强的行政权运作逻辑的色彩*郑智航博士从最高人民法院垄断了指导性案例的遴选权、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的目的在于限制法院和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非规范法院和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体现了行政权的“高位推动”色彩、中国指导性案例控制机制的行政化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逻辑”,并从合法性、制度成本、缺乏竞争性、弱化法官自主性等对之进行了批判。参见郑智航:《中国指导性案例生成的行政化逻辑》,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118~128页。,体现着明显的机关思维特点。最后,再以以往的监察权力改革为例进行佐证。建国初期,我国设立人民监察委员会,隶属于中央政务院。之后改为国务院监察部,到了1986年,国家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从1993年至今,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办公,分别承担党的纪律检查和行政监督两项职能。可以看出,以往我国监察权本质上隶属于国家行政权,历年的监察体制改革均围绕机构和职责两个要素展开,没有明确监察权自身的属性和客观运作规律,更未跳出监察体制的自我封闭空间,导致将监察权仅局限于行政监察而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宪法功能的后果。以上权力改革实践和制度设计均不同程度反映了执政党在权力改革中的机关思维,形成了以机关整合为中心的权力改革改革路径和方法论。
机关思维具有以下主要特征:第一,以机关本身为中心。机关是权力的象征与载体,机关的设置与改革实质是权力内部或不同权力之间的较量与调配。在出现权力腐败甚至斗争时,权力高层往往从机关切入,通过设立、重组、合并、嫁接等方式对所涉机关予以调整,从而完成对权力的整合、调控。第二,体现集权思想。机关思维下的权力架构往往呈现出传统权力分配的“金字塔状”,各级权力能量随着层级的降低而减小,“权力在横向层级上向某个个人集中,在纵向关系上,下级向上级集中”(陈国权、黄振威,2011:103)。第三,唯上级论。从个体权力的产生来源看,权力个体依附于某一机关职位,而这一机关主要是上级决定产生的,尽管人民主权思想深入人心,但在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大背景下,其追溯到底是执政党高层的决定。由此在机关思维下,所产生的权力个体评价标准便是唯上标准。
机关思维作为一种权力控制方法论而言,在国家存在一种绝对强势力量的情境下容易成为该力量的优位选择,其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方法有利于及时抓住时机,促使预设目标能够快速实现。现代权力结构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一个整体联动的系统,在某一权力维度出现问题时,如果仅仅对其局部进行诊治,势必会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错误,不仅整治效果难以达到,而且可能会在调整其他权力系统过程中耗费时间、贻误解决良机。机关思维是一种直接的、深刻的、大刀阔斧的解决方法,在强力推动和坚实保障的情况下,此方法可以快速配置权力,完成权力结构的快速调整,短时间内实现所追求的价值和目标,而这对于执政党而言,无疑是提升其政治绩效、证成执政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绝佳机会。
(三) 对机关思维的批判
从功利的角度而言,机关思维有利于执政党的治理,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宪法价值相悖逆,不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应当对其予以批判。
第一,机关思维违背权力制约原则,易导致权力的封闭空间,滋生新的腐败。例如,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我国将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和公诉权配置给检察机关,就反腐而言,由检察机关同时拥有前后承继的两项权力有利于提高打击腐败的效度。但这种权力配置方法易形成侦查权与公诉权间的封闭空间,可能给检察机关该作起诉决定却不起诉创造机会,导致检察机关“灯下黑”问题的产生。
第二,机关思维有违权力运行的客观规律性,容易阉割权力自主修复功能。权力本身是一种具有自身逻辑和功能边界的自主结构,其有效运行既包括外在环境下的互动,还包括自运动。机关思维往往注意到了外在环境下该权力与其他事物的联系,容易忽略权力本身在设立、运行、实现等过程中的自有矛盾和自主修复功能。比如,此次国家监察体制欲融合行政监察、国家审计、预防腐败等权力机制,但后三者并非功能意义上的反腐权力。《行政监察法》第18条规定监察机关针对监察对象的“执法、廉政、效能”履行监察职责,可以说反腐只是行政监察权能的三分之一。再看国家审计权,我国《审计法》第2条规定审计机关对审计对象所列财政收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依法进行审计监督,这是审计权的真实功能,即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国家资金的正常使用。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只看到机关本身,忽视了机关背后权力各自的真实功能和运行规律,径直地将机关整合不仅破坏了权力自主体,而且这种颠覆性的改革方法无法为权力功能受损提供修复或救济途径,除非用相同的方法推倒重来。
第三,机关思维有违现代民主原则,公民、社会对权力改革的参与度低。这个问题体现在:一方面,机关思维强调权力高层的主观能动性,着眼点在于机关本身,这客观上导致公民个人与权力改革事项的区隔;另一方面,机关思维制造了逼仄的权力研讨空间,抑制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使社会组织游离于权力改革外围,无法激发和发挥社会组织在实现预设权力改革目标中的作用。
第四,机关思维可能违反人权保障原则,使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机关思维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对简单权力事项进行改革可能起到“短平快”的效果,但对于像国家监察体制顶层设计这样的复杂系统,若缺乏精细的制度设计和技术操作,加之机关原有的救济功能失效,很可能导致相关对象的合法权益受到制度侵犯而无法依法获得救济。
第五,机关思维是一种内耗式的改革方法,不符合宪法经济观。机关思维方法的实现依赖于权力高层的权威以及制度自身所形成的公信力,而这一过程大量消耗权力高层控制的人、财、物、制度等有形、无形资源。此外,改革走到今天,各项制度和权力已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内在有机联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推动下,机关思维在某一权力改革的运用可能直接导致其他改革机制的错位或熔断,造成诸多权力改革领域的龃龉、碎片化。机关思维可能将制造执政党内部权力分支间的“经济鸿沟”(查尔斯·A·比尔德,2012:1-11),进而发生马克思主义宪法的基础解构风险,引发上层建筑之价值冲突与失序。
二、 程序思维: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逻辑选择
方法具有时代局限性,机关思维是计划经济体制、政党政治不成熟、公民社会力量薄弱、民主机制不健全等旧时代条件下的改革方法,上文论述的诸多弊端凸显了机关思维方法的不适应性和方法改革的迫切性。现代民主政治呼吁新的改革方法论,我们认为程序思维方法正顺应了时代要求、改革趋势、发展特征,成为权力改革领域必将崛起的新的方法论。
(一) 程序思维的描述
从语义上判断,本文中程序的反义词并不是实体或实质,可接近“恣意”;其近义词并非过程或顺序,可接近“规律”,即程序是指事物各自的运动规律(赵振宇,2001:36-37)。基于此,本文把“程序思维”方法描述为按照权力产生、发展、衰弱、消亡的客观运动规律,识别这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破坏民主、侵犯人权、违背法治、消减制约等价值漏洞或风险点,并采取相应的制度措施予以引导和修正,从而保证该权力的发生与变迁符合现代宪法价值的方法。理想的宪法是符合价值诉求目标的权力组织法(程洁,2015:2),而程序思维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带有价值审视的方法,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
程序思维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第一,以权力为切入点,对其进行全面动态的审视。程序思维与机关思维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切入改革的视角,后者切入点为机关本身,以机关为中心设置程序;而前者以被改革的权力为切入点,审视权力设置、运作等各阶段是否符合现代宪法预设价值,并对之进行相应价值指引与修正。第二,体现分权思想。程序思维并没有像机关思维那样预先将权力集中于某一机关,再主观设置权力运行程序,而是在遵循权力之客观运动规律基础上,为其营造了一个比较开放的运作空间,吸引社会组织、公民等其他主体参与到权力运作中来,再按照现代宪法原则和功能最适当原则*功能最适当原则是对三权分立和民主集中制思想的整合,有助于实现权力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具体参见朱应平:《功能最适当原则是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基础(会议论文)》,上海: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的会议论文。对权力配置作出适当安排。第三,追求现代宪法价值。从功能来说,程序思维最主要是对权力运作的各个环节作出价值判断,弥补机关思维带来的现代宪法价值创伤和漏洞。从程式上讲,程序思维在具体情境中所采用的价值系统不是随机的,它可以在某一类情境中积累固定的特殊程式,从而防止在运用程序思维时遗漏某一价值。从内容上看,现代宪法价值不仅包括民主、法治、基本人权、权力制约、秩序、自由等一般人类文明共识,还包括宪法对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等各种具体权力形态的特殊价值要求。这些价值可能同时存在于某一权力整体或具体环节,且彼此之间存在张力,这时则需要按照公权力上的比例原则对价值进行取舍,作出实质上的更优设计。如果价值冲突无法调和,通过价值层面的整合或重组可能会催生出新的独立权力形态,这或许是我国国家监察权脱离行政权而取得独立宪法地位背后所隐含的发生原动力和发展机制所在。基于此,我们也可以称程序思维是一种充满价值博弈的方法。
(二) 程序思维与机关思维的辩证关系
程序思维与机关思维是权力改革的两种方法论,尽管两者存在诸多差异,但都具有一定的方法优势,在同一权力改革中,两者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配合,辩证统一的关系,具体来说:
首先,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本质上是按照权力之客观运作规律对权力的发生和变迁环节作出的价值判断,其形式是抽象的,必须依赖于权力主体才能在现实中发挥作用。机关思维尽管存在诸多弊端,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理顺相关机关的主体关系,最起码提供了权力运作的基本载体,这为程序思维对权力运作环节进行价值供给奠定了基础。
其次,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机关思维以具体机关为视角切入权力运作过程,其更多地带有整合性政治的倾向,即通过改革机关本身,整合机关优势,优化机关的政治序列,达到更好的政治效果。可以看出,这种改革方法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是这种方法比较简单粗暴,容易为了执意达到整合性政治效果而丢了现代民主社会推崇的宪法价值和基本精神。而程序思维从宏观上把握权力的客观运作规律,再以现代宪法价值为参考系来识别权力运作环节可能存在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再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弥补。可以看出,程序思维带有预防性政治倾向,具有更强的价值指引性,而这恰好可以补强机关思维在这方面的短板。
再次,程序思维和机关思维的应用不存在谁先谁后的序列问题。尽管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但这不意味着在诸如权力改革中先应用机关思维,再应用程序思维,更不意味着完全否定机关思维而选择程序思维,而是批判性地统筹运用两种方法,不可偏颇任何一方。否则要么权力改革由于缺乏现实制度承担载体而无法推进,要么因缺失宪法价值指引而引发新的宪法法律问题,甚至宪法危机。
(三) 程序思维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
程序思维是现代宪法价值实现的重要方法,其对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促进作用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有助于扩展权力运行空间,吸收社会组织、公民的民主参与。就权力改革而言,某种权力关系的重组会影响整个社会结构(理查德·拉克曼,2013:36),但这一论断是建立在程序思维基础上的。机关思维容易形成权力运行在机关内部型构的封闭空间,阻隔社会组织、公民对权力改革的参与,这与现代民主政治所提倡的公民参与政治的思想相违背。而程序思维尊重权力产生、发展、衰弱和消亡的动态过程之客观规律,按照现代宪法价值和功能最适当原则配置权力及其各环节对应的参与主体,从而使权力运作空间立体化、开放化,有利于扩大政治改革的民主参与度。
第二,进一步强化民主政治的实质性,推动民主政治精细化、宪法价值化发展。程序思维更加注重权力运作各个环节的价值性思考,其在尊重权力自身运作客观规律基础上,对权力的设置、发展以及与其他权力系统的协调衔接作出价值指引。尽管这增加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复杂性,但程序思维的应用有助于缓解权力改革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减少现实环节的直接对抗,更大限度地凝聚在权力改革领域的价值共识,增加各方面对权力改革方案的认同感和可接受度。
三、 程序思维视域下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完善建议
检视《试点方案》和当前正在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工作*这里我们列举浙江省在试点阶段的国家监察体制之顶层设计所覆盖的主要内容: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机构;依法有序推进改革;实现机构、职能和人员的全融合;探索形成监察权有效运行机制;建立监察委员会与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协调衔接机制;强化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制约。以上是浙江省监察委员会主任任泽民对浙江省相关试点工作做的归纳。参见闫鸣:《扎实推进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http://www.ccdi.gov.cn/yw/201701/t20170107_92451.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7年2月17日。,我们发现,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是由执政党以设立监察委员会为中心展开,将行政监察机关、国家审计机关、检察院反贪反渎局等机关整合进同级监察委员会,“要求实施组织和制度创新,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面覆盖,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察体系”。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方法论更偏向机关思维,注重理顺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监察体系和追求其体系内部秩序,未对国家监察体制整体和各环节提出价值层面的要求,亟须应用程序思维重新检视相关顶层设计方案,从而使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更符合现代宪法价值*我国现行宪法尚未对监察权作出规定,宪法层面的监察权预设价值还无法对当前的国家监察体制顶层设计发挥判断和指引功能,本文仅从一般宪法价值认知运用程序思维对监察权设立、运作等各环节进行检视,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意见。。下面,我们在批判性地吸收机关思维下顶层设计方案的基础上, 结合监察权自身客观规律和特点,运用程序思维重新检视监察权的各环节*需要说明的是,运用程序思维对监察权成立、运行环节进行价值判断仅是一种程式的具体展现,在其他案例中,顶层设计者或改革者可根据客体实际情况,设置相应地环节,运用程序思维识别各环节可能出现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并相应地采取修正或防范制度措施。,并对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一) 监察权设立环节
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处于试点阶段,监察权在我国尚未设立。运用程序思维来检视这一环节,我们认为这里可能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有两个:监察权的设立是否体现法治价值;行政监察权、国家审计权等权能被整合后,原有权力场域中的秩序价值如何维持。
具体来说,第一,从《试点方案》和试点实践可知,监察委员会由同级人大选举产生,这意味着监察权将成为与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并列的独立权力形态。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体制,监察权的成立是没有宪法依据的。为了使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具有形式上的合宪性,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相应地试点授权决定,但这种做法是存在重大瑕疵甚至可以说是违宪的*有读者可能认为在类似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等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的意志突然出现且具有迫切性时,全国人大可能还不到定期开会的时间,由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作出授权决定具有相对正当性和合宪性。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就严重违反法治原则,是法治不成熟的表现。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经过谨慎论证和试点,但是这一过程不能从改革起始就在效率和法治的天平上失去平衡,改革即使具有紧迫性也要遵循法治原则,而这一点我国宪法第61条对此作出了安排,即召开全国人大临时会议。,因为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进行法教义学分析,并不能推出其设置监察权的权力。因此,我们建议由全国人大重新对试点工作作出授权,重拾试点阶段监察体制顶层设计丢失的法治价值。进一步讲,如果将来国家监察体制在全国铺开,那必须获得宪法和法律依据,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尽快对之修宪(童之伟,2016:3-13)。第二,如前所述,将行政监察、国家审计、检察院反贪反渎等整合进国家监察体制,希冀更大程度上发挥反腐作用的做法是不当的。行政监察等权能被国家监察权吸收后,行政监察权等原在的权力场域将发生秩序动荡,比如行政效能的监督将面临空缺,国家资金被高效利用将无法保障等,如果还是运用机关思维将这些边际权能安排给其他机关,那是严重的破坏权力自身的客观规律的。因此,我们建议,为了维持行政监察等在原有权力场域的秩序价值,保留行政监察、国家审计等职能部门,仅把反腐的权能与相应的机关力量整合到国家监察体制。
(二) 监察权实施环节
我们认为这一环节可能存在的价值漏洞或风险点有三个:如何体现对监察权的权力制约价值?如何避免选择性或运动性反腐,使监察权的运行体现民主价值?被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价值如何得到保障?
申言之,第一,根据试点方案和试点实践,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三项职责,从效度上讲,这三项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连续权力为惩治腐败人员扫清了障碍。但是这种职权设置有违权力制约原则,因为上述权力安排实质构建了监察权运行的封闭空间,尽管对于涉嫌职务犯罪的腐败,检察院可对之构成制约,但仍有反腐案件未进入司法程序,这种设计对于所有公职人员来讲无疑是头顶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可能会给权力秩序带来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建议在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和处置之间介入一道制约机制,可以增加一个由执政党成立的相对独立的“反腐咨询委员会”,由该委员会根据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情况作出是否处置和如何处置的决定,再由监察委员会实施该决定。第二,我国拥有庞大的公职人员群体,如此规模的反腐仅靠监察委员会是难以完成的,可以说反腐是一项需要全民参与的伟大政治事业。但观察目前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它实际上阻隔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和社会、公民在反腐语境中的互动,现代政治强调的民主价值并未得到体现。因此,我们建议监察权的顶层设计应拓展监察权能,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监察腐败中的作用。比如在现实反腐中,信访举报工作是反腐败斗争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获取问题线索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基本途径(何韬,2015:1),所以,建议将信访功能赋予监察权。第三,就保障被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价值而言,一方面,根据“监察委员会调查职务犯罪行为后,对涉嫌职务犯罪的,移送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可知,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在程序上与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相衔接的,相当于检察院对职务犯罪的自侦权,即其本质上具有了刑事侦查权的性质,此时,监察委员会已经作为司法机关介入刑事司法程序,被监察对象转变为犯罪嫌疑人,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3条*即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应当允许辩护律师的介入。关键从何时可以允许委托辩护律师呢?委托辩护律师并不会给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带来显著影响,但对于被监察对象而言,这个调查程序性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发生上述“突变”,从而损害其程序利益,因此,从维护被监察对象的基本权利角度而言,我们建议公职人员在接受监察委员会调查时就应当被允许辩护律师介入。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拥有如此强大的监察权,难免出现其自身的腐败,从而产生冤假错案,侵犯被监察对象的合法权益。而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无法依法纳入现行法治化救济框架,可能造成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牺牲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为代价,产生新的人权“赤字”,因此,我们建议国家监察体制应设计被监察对象的权益救济机制,通过修法或法律解释途径将其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
[1] 艾 丰(1993).中介论——改革方法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
[2] [美]B·盖伊·彼得斯(2015).比较公共行政导论:管理政治视角.聂露、李姿姿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 [美]查尔斯·A·比尔德(2012).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何希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4] 陈国权、黄振威(2011).论权力结构的转型:从集权到制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3.
[5] 程 洁(2015).治道与治权:中国宪法的制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
[6] 程竹汝、任军锋(2000).当代中国政党政治的功能性价值.政治学研究,4.
[7] [法]让·皮埃尔·戈丹(2010).何谓治理.钟震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8] [美]弗兰克·J·古德诺(1987).政治与行政.王元、杨百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9] 何 韬(2015).跑好反腐败的“头一棒”——2015年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展望.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03-20.
[10] [美]理查德·拉克曼(2013).国家与权力.郦菁、张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1] 蓝志勇、魏 明(2014).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经验与复杂性.公共管理学报,1.
[12] 刘红燕、宋惠敏(2013).现代民主的价值内涵探析:现代性与底线.人民论坛,6.
[13] 刘厚金主编(2015).行政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童之伟(2016).将监察体制改革全程纳入法治轨道之方略.法学,12.
[15] 王崇英(2003).现代中国宪法价值初探.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
[16] 王建民、狄增如(2013).“顶层设计”的内涵、逻辑与方法.改革,8.
[17] 王敬尧、贾鹏举(2000).西方官僚体系的权力扩张与民主政治的矛盾.社会主义研究,4.
[18] 赵 义(2014).改革需要方法论.能源评论,1.
[19] 赵振宇(2001).程序及程序的设置艺术.领导科学,1.
[20] 周 军(2015).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通过任务型组织的建构寻求出路.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3.
[21] 朱应平(2008).功能最适当原则是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基础.上海: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2008年年会,会议论文.
■责任编辑:李 媛
From Institutional Thinking to Procedural Thinking: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in China
QinQianhong&DiGaoyang
(Wuhan Universit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centralized, unified, authoritative and efficient supervision syste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ruling party, to improve the self-supervis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nd constantly to enhance the abilities of the self-purification, self-improvement, self-completion and self-innovation,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s made the great political decision to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is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power, and needs correct methodology.Therefore, this study mainly concerns what’s kind of method can be adopted by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Through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judicial and supervisory powers, we found tha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ower reform in the past took the power subjects as an angle of view, and designed the power relations,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nd implementary procedure.This method can be called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It’s helpful to integrate the subjects of the power, and to promote the process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order identity.But it is simple and crude, and enslaved to the space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the value designed by the reformed power. It cannot realize the coherenc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power reform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ower value provided by the more transcendent constitution, and this will greatly affect the overall effect of power reform.Actually, the idea of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 is a formal power reform view.Here, we advocate a concept of substantive power reform view; that is to say,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power reform takes the power as the angle of the view, centering on the reformed power.And based on respecting the objective operation rules of the power, the designers examine the various aspects of the power processes through this method,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ossible value loopholes or risks and to make up or to prevent them.Therefore, the goals of the value integration and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pow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itution can be achieved.We call the later method procedural thinking.From the academic view, firstly, what is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 How can it become a favorable way to the traditional reform in China?What’s more, what is procedural thinking?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cedural thinking and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What is the position in the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our country?Besides, how can the two methods be evaluated in terms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What can be done to improve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under the view of procedural thinking.These are the main problems that the article tries to study.The main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act that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should have an overall application on the two methods of the institutional thinking and procedural thinking.And the goal is to obtain order identity and value consensus in the field of the subjectivity and the reason.There are two innovations in this paper:the first one is that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search is novel.Most literature on the reform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focuses on the specific problems of itself, such as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and the legislative issues concerning the state supervision, and so on.While, based o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ethods of institutional thinking and procedural thinking in the field of power reform on a deeper and more abstract level, and provides the method guidance for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This study has strong theoretical inspiration and practical guidance significance.The other one is that the recommendations are novel.It has found a series of dilemmas brought by the method of institutional thinking and tries to put forward a new method-procedural thinking-of the power reform.On this basis, it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and innovative policies to improve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such as setting up relatively independent “Anti-Corruption Advisory Committee” by the ruling party.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petition function should be given the power of supervision and the rights relief of the objects by supervised should be monitored into the scope of the state compens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amending the laws or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the state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institutional thinking; procedural thinking; methodology
10.14086/j.cnki.wujss.2017.03.001
2017-02-20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2003)
D911;D912.1;D90
A
1672-7320(2017)03-0005-09
■作者地址: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13907150379@vip.163.com。 底高扬,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597867945@qq.com。
——中国古代监察体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