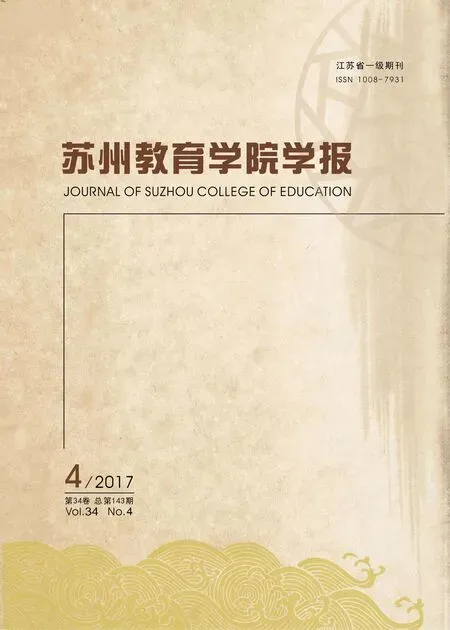陶渊明杂述五题
顾 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陶渊明杂述五题
顾 农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9)
陶渊明诗歌中偶用《周易》的卦名很得要领,前人或谓“陶诗用卦名不甚可解”,因前人所据之版本有误,所以议论不确。陶诗中不大涉及时政,对于那些一般认为是大事的军政时事,往往仅以碎屑视之。陶渊明对生死看得很淡,曾在《挽歌诗》直截了当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死亡引起的哀伤是早晚会淡化以至于终结的,此乃见道之言。陶诗中涉及大量历史人物,有些知名度并不甚高,但总是同他本人切身的经历和感慨联系在一起,值得逐一细加揣摩。陶渊明为孟嘉立传,大谈自己的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亲密关系,流露了他的某种政治态度。陶渊明对东晋王朝完全没有忠心耿耿、奉若神明的意思,当时这样的士大夫相当不少。
陶渊明;时事;生死;历史人物;政治态度
陶诗用卦名
陶渊明(365—427)“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1]217,早就把儒家经典读得很熟,于是后来在诗歌里常有引用或化用,尤以《论语》为多,有几十处,一般还算比较好懂;他偶用《周易》,理解起来也不算难。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陶渊明很讲究诗歌的可读性。
陶诗用卦名的情形,可以举他早年的作品《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为例来看—
自古叹行役,我今始知之。山川一何旷,巽坎难与期。
崩浪聒天响,长风无息时。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当年讵有几?纵心复何疑。[1]191-192
庚子岁当东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四年(400),三十六岁的陶渊明正在雄心勃勃的地方实力派桓玄手下任职,充当他的使者到首都建邺(今江苏南京)去办事,返回的途中遇到狂风激浪,只好在规林地方停下来暂避。这时他写诗大发牢骚说,老是出差东跑西颠实在辛苦而且无谓,呆在自家园林里过安稳日子多好!还是故乡好啊,我奔到这鬼地方来干什么!壮年时代(“当年”)还能剩下多少啊(“讵有几”)?还是过几天顺心的日子吧!
“巽”“坎”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分别代表风和水,这在古人是非常熟悉的。“巽坎难与期”是说行船途中有许多不确定性,风和浪的情况难以预料。那时没有天气预报,而就是现在也会有很突然的情况发生,仍然难以准确地预知(如龙卷风)。天有不测风云,呆在自己家里都好说,出门在外,行船走马,就有可能摊上麻烦甚至危险。陶渊明想到归隐了。
当然这时他还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顺便发点牢骚,他真的下决心归隐,还要在几年之后。
清朝人马星翼说:“陶诗用卦名不甚可解”(《东泉诗话》卷一)[2],其例句之一就是“巽坎难与期”,只不过他引作“巽坎相与期”—能够同风与水“相与期”,那很好啊,而下文又说风急浪崩情况很糟,这样的诗句前后矛盾,确实不好理解。马星翼读陶渊明用的本子不佳,以至影响了他对陶诗的观察和评价。
马星翼引来作为例子的另外一句陶诗也是文本有误,那里是把“瞻夕欲良䜩(宴)”(《于王抚军座送客》)[1]150错成“瞻夕欲良谦”了,原句只是说准备在一个美好的晚上举行宴会,同卦名完全无关;而“䜩”误作“谦”就麻烦了—六十四卦中是有“谦”这么一卦的,艮下坤上,《易传•谦》之《象》云:“君子裒多益寡,称物平施。”[3]这样一来就引起很大的困惑,这句诗也变得“不甚可解”了。
读书而不用校勘精良的本子,很容易将自己引入困境。再就此来发议论,肯定不能中肯。书非校不能读也。
陶诗与时事
建安以来的诗歌传统之一是喜欢直接地具体地歌咏时事,有些作品简直可以称为“诗史”,名作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曹植的《送应氏二首》等等。这样一种高度关注现实的传统,到晋代特别是东晋以后是衰歇了。抽象的清谈成为士人关注的中心,诗歌里充满了玄言,时髦的玄学让人们包括诗人看不起具体的事实,以为这些都碎屑不足道。
这种情形到陶渊明这里发生了若干变化。他也写玄言诗,如《形影神》等等,但比较少,而改为在诗歌的适当部分来几句带有玄理色彩的议论和感慨,这些议论和感慨不像先前那些玄言诗人似的照抄书本(特别是《老子》《庄子》《周易》),而是自己从生活里体悟而来的,因此可以增加诗歌的哲理性而仍然相当可读,并不像老派玄言诗那样干枯无味。
在如何面对重大现实题材的问题上,陶渊明远没有回到建安的传统上去。在他的一生中,政治上发生了许多大事,军事行动也非常频繁,有些就直接发生在他的家乡浔阳一带,但他基本上都不曾写到自己的诗里去。例如造反的卢循的部队同晋军官兵在浔阳一带的战事,陶渊明就完全没有写到;又如桓玄一度取代东晋,建立了自己的“楚”政权,同时把晋安帝司马德宗打发到浔阳安置,对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变化,陶渊明也竟至于只字不提。南宋以来有一批学者以“忠愤”论陶,影响很大,至今仍然有专家学者奉为典要。可是在我们看来,本朝皇帝被人赶下台了,而且恰好是被赶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陶渊明却连一句抗议或反感的话都没有,这哪里像是什么忠臣,离“诗史”的传统亦复极其遥远。
陶渊明关心的是他的家人、林园、琴书、酒樽、土地、庄稼、桑麻、邻居……,他有一种近乎老派农民的眼光和心胸。当然他也并非完全闭眼不看军政大局,更不是没有自己的观感,但他习惯于只是远远地点到那么一下,意思到了就作罢。
对于这样一种与现实若即若离的特色,昭明太子萧统曾经有过一个一笔带过的总结,他在《陶渊明文集序》中写道: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乎。[1]613-614
这里须特别关注的是“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这一句。关于涉及大局的“时事”,陶诗中只是指到为止,其余则全都交给读者去想。
试举两件同后来正式取代东晋的宋武帝刘裕有关的大事来看。刘裕在打垮桓玄并一度恢复了东晋的法统以后,致力于北伐,一直打到长安,收复了许多失地,极大地赢得了民心。这在他本人的雄图大略中只是收拾人心,为正式改朝换代作准备,而在老百姓和士人心目中则当然是了不起的丰功伟绩。陶渊明在《赠羊长史》诗里兴奋地写道:
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
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痾不获俱。[1]161
陶渊明迫不及待地要到中原去瞻仰圣贤遗迹,这就让读者想到刘裕北伐取得巨大成功这一历史大事。这就是所谓“语时事则指而可想”。
可惜刘裕没有能够真正统一九州,他很快就回到东晋的故地来,通过一套复杂而冠冕堂皇的手续,让原先由他安排上台的晋恭帝司马德文将政权“禅让”给他,顺利地实现了晋、宋的易代。据《晋书•恭帝纪》记载,司马德文非常配合刘裕,很痛快地在交权的文书上签字画押,并“谓左右曰:‘晋氏久已失之,今复何恨。’乃书赤纸为诏。”[4]171事情到这里都还是很完满的。但此后刘裕出了一着臭棋,派人用药酒毒死了司马德文。
有什么必要去毒死一个丝毫不构成威胁的下台皇帝呢。此举除了表现出政治上的不自信和手段的残忍之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呢。刘裕先前费了很大力气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人气资本,被这一步臭棋大大地折损了。
陶渊明对刘裕上台当皇帝可能不是太赞成,但也没有表示过反对,至于用残忍的手段害死前晋恭帝司马德文一事,他肯定是绝对不赞成的,但也只是在一首题为《述酒》的诗中借用典故顺便提到了一下,说是:
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1]290
山阳指山阳公刘协,也就是东汉末年那个献帝刘协。先前他在曹操挟持下当了多年傀儡,曹操死后曹丕不想继续挟天子以令诸侯,而要自己当皇帝,于是让刘协正式下台。刘协相当配合,很痛快地交出皇权,签字画押,行礼如仪,然后就跑到安排给他的山阳国(今河南修武)去,过他的退休生活,从此安享晚年,并且得以善终。他死后,当朝皇帝魏明帝曹叡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在这件事情上,三曹(武帝曹操、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和汉献帝/山阳公刘协都获得了正面的名声。
这是汉、魏易代时的故事,现在是晋、宋易代了,情形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仍然采用禅让的模式,不同的是司马德文的结局与刘协天差地远。陶渊明冷冷地作一今昔对比说,刘协虽因明智引退而得以善终,但名声还不够大,其言外之意大约是说,只有像当下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这样,虽已引退而仍然被毒死,才更为有名,才更能得到人们的同情。
这里又是陶渊明的“语时事”了,至于怎么思考和看待此事,他仍然完全交给读者。当然这样就对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应当是明白时事而且头脑清楚的。把《述酒》和《赠羊长史》等诗联系起来读,可以比较分明地看出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特色。
后代的读者要深刻理解他的这一类诗有一定的难度。当年的时事已成陈迹,人们的观念又可能有种种变化。理解并同情遂不免变得不容易。赵宋以来的一批学者由《述酒》一诗得出了陶渊明一生“忠愤”的结论,照我看就是不准确的,大有必要重新加以思考。
这样看来,魏晋诗歌中反映当代重大时事的路子有两条,一是正面涉及,具体描写;一是略一点到,由人去想。二法各有所长。后来杜甫兼用这两种办法。在言论不大自由的时代,后一种办法往往大行其道。但陶渊明惯用此法同言路的宽窄无关,他是在玄理的冷水里浸泡过久,又深爱园林生活,所以对于那些一般认为乃是大事的军政时事,往往仅以碎屑视之,觉得无甚可写,还不如多来谈谈饮酒和桑麻。
“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陶渊明写过三首《拟挽歌辞三首》,其第三首曾被选入《文选》(卷二十八,改题《挽歌诗》),最为著名,诗云: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嶢。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託体同山阿。[1]424-425
这一首写逝者下葬,丧事至此基本结束。陶渊明说,死了就是死了,送葬的都回家去了,家人和近亲有的还有些“馀悲”,其他人便完全恢复了他们的正常生活了—死者独自被埋葬在山坡里,如此而已。
“他人亦已歌”一句表示“他人”已经不再悲伤,甚至唱起歌来了。歌与哭在古代礼仪中都有明确而繁琐的规定,家有丧事,何人于何时何地必须哭,在《仪礼》以及《礼记》里有若干专篇作过详细的说明,总的原则是要看哭丧者同逝者关系的远近亲疏。关于吊丧者与送葬者如何表示哀伤,礼仪上也有许多规定,其标准同样要看他们同逝者关系的远近亲疏。儒家非常讲究这些,宗法社会,一切看血缘关系的远近,后来则渐渐衍变为主要看社会关系、情感关系的远近。
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生活总还要继续进行,不能无休止地哀伤下去。儒家经典里甚少谈论这个方面,而看破一切的大诗人陶渊明则直截了当地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哀伤是早晚会淡化以至于终结的。“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肯这样直说的人不多。一味说实话,才是陶渊明。
陶渊明诗中的历史人物
陶渊明曾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1]502,他用诗人的态度读书,借以丰富精神生活,尚友古人,提升自己的境界,帮助理解社会和人生,也有助于在诗中发表感慨和高见。他不是像学者那样刻意在做某一具体的学问或构筑某一体系。诗人读书如奶牛,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学者读书如食品加工机器,送进去的是奶油、面粉和鸡蛋,烤出来的是蛋糕。
陶渊明读书很杂,提起古人来,议论和感慨很多。
中国人看历史,固然关注种种事件,而尤为重视各路人物。中国的史学同文学一样,也是人学。陶渊明即“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1]206-207。他一再说:“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其二)[1]366“得知千载外,政赖古人书。”(《赠羊长史》)[1]161历史上的圣贤、君子以及其他风流人物都是他的榜样和朋友。他在为儿子们编撰的家庭教材《五孝传》《集圣贤群辅录》中提到大批历史人物,其中有些正可以同他的诗歌创作互相参证。①参见拙著《〈五孝传〉是陶渊明编的家庭教材吗?》,《中华读书报》2016年9月21日第15版。
陶诗中提到大量历史人物,除了作为典故偶尔提到一下的以外,他仰慕赞叹的人物有:箕子、伯夷、叔齐、管仲、鲍叔、程婴、公孙杵臼、黔娄、伯牙、锺子期、荷蓧丈人、长沮、桀溺、三良、於陵仲子、孔子、颜回、原宪、七十二弟子、庄周、韩非、鲁二儒、荣启期、屈原、荆轲、贾谊、商山四皓、疏广、疏受、张挚、杨伦、扬雄、张仲蔚、刘龚、袁安、黄子廉、丙曼容、邹次都、薛孟尝、周阳珪、田子泰……
这里有不少是人们耳熟能详、曾经得到反复赞叹的大名人,而更值得注意的则是那些知名度未必很高却为陶渊明特别关注的人物。例如关于汉朝人张挚(长公),陶渊明在《饮酒》其十二诗中充满感情地称颂他道:
长公曾一仕,壮节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仲理归大泽,高风始在兹。一往便当已,何为复狐疑?
去去当奚道,世俗久相欺。摆落悠悠谈,请从余所之。[1]263-264
张挚是张释之(汉文帝时曾作廷尉)之子,曾经当过大夫,后被免职。《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云:“(张挚)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5]说不干就不干,没有犹豫,不再反复。比较起来,在仕与隐之间反复多次的杨伦(仲理),虽然不失其高风,终不免落入第二义,折腾什么呀。
陶渊明很佩服张长公,又作四言诗称颂道:
远哉长公,萧然何事?世路多端,皆为我异。
敛辔朅来,独养其志。寝迹穷年,谁知斯意。
—《读史述九章》[1]527
张生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扇上画赞》[1]507-508
这样再三致意应当同陶渊明自己的身世大有关系,他本人也是先当官后退出的,只不过不如张长公那样决绝,曾反复折腾过好几个回合,误落于尘网中许多年—张长公特别值得钦佩啊。
张仲蔚是东汉的一位处士,皇甫谧《高士传》载曰:“(其)终身不仕。明天官博物,善属文,好诗赋。常居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性,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6]陶渊明非常佩服他,《咏贫士》其六是专门写他的:
仲蔚爱穷居,绕宅生蒿蓬。翳然绝交游,赋诗颇能工。
举世无知音,止有一刘龚。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
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1]375
此诗前半叙述其人其事,后半大发感慨,表明态度。这样来写诗,貌似咏史,而实为咏怀,此乃左思以来的新传统。钟嵘《诗品》说陶渊明“又协左思风力”[7],很能得其要领。
高人总是孤独的,而天下得一知己足矣。陶渊明又有《饮酒》其十六诗云: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1]271
这首诗本来是写他本人的,说自己如何坚持君子固穷的节操,而到最后忽然提到世界上没有一位孟公(即刘龚)能理解自己,却就匆匆结束了。此诗余味丰富。笔者在一篇旧作中说:“饥寒交迫长夜难眠固然痛苦,无人理解孤独寂寞则更加痛苦。《饮酒》其十六最深刻的悲哀在此,其动人之处也正在这里。”[8]陶渊明痛感自己的命运远不如张仲蔚,心中多有荒芜苍凉之悲。
陶渊明想起某位具体的古人并就此写诗,或涉笔成趣地提起某人,往往同他自己的世界观、历史观密切相关,有些则同他切身的经历、感慨联系在一起,如果逐一细加揣摩,那是非常有益有趣的事情。
陶渊明读过的书,有些现在已经失传。《咏贫士》其七云:“昔有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1]377一位叫惠孙的送他一笔厚礼,他不肯接受。黄子廉是东汉人,是赤壁之战名将黄盖的祖先,其姓名只在《三国志•吴书•黄盖传》里提到过一下,其他一无所知,惠孙的“腆赠”也不知其详。陶渊明晚年最穷困的时候,江州刺史檀道济来看他,送了不少礼品,陶渊明同样拒绝接收,他的做派正与黄子廉相视而笑。
要了解一个人,固然要看他做了什么以及怎么做,同时也可以看他怎样看待和评价别人,其中包括古人。
孟嘉其人
《晋书》为孟嘉立传,附于桓温传后,均在卷九十八。安排得如此靠后,是因为桓温其人虽然战功赫赫,却颇有不臣之迹,唐代的史官认他为反面人物,所以列于卷末,在《列女》《四夷》之后。卷九十八里还有一个人的传,那就东晋初年举兵进攻过朝廷的王敦。《晋书》卷九十九则是桓温之子桓玄的传,桓玄比他老子又进了一步,正式实行了改朝换代,他带兵攻入首都,自己当皇帝,以“楚”王朝取代东晋,但为时甚短,不久就垮了台—天下仍为东晋。卷一百记载的也是反朝廷的负面人物,他们是:王弥、张昌、陈敏、王如、杜曾、杜弢、王机、祖约、苏峻、孙恩、卢循、谯纵。
曾经当过桓温僚佐的官员相当之多,其中颇有名人,甚至也包括后来著名的宰相谢安(最后是他和王坦之合作,成功地抵制了桓温的篡权野心),而传记被附载于桓温其人之后者,只有孟嘉一人,他们间关系之密切不言自明。
孟嘉最有名的轶事自然也都与桓温有关,《晋书》本传写道:
孟嘉字万年……后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燕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叹。
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温问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问:“听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谓也?”嘉答曰:“渐近使之然。”一坐咨嗟。转从事中郎,迁长史。年五十三卒于家。[4]1723
桓温与孟嘉固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更像是不拘形迹的亲密老友。他们之间的问答都无关于政务公事,只是风雅得紧。
最早为孟嘉立传的是陶渊明,他写过一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其中说起“渊明先亲,君之第四女也”[1]492,原来他是孟嘉的外孙。这篇传内容丰富,行文潇洒,上述轶事这里已经写到,《晋书•孟嘉传》的其他内容也都不出于陶渊明此传的范围之外。
陶渊明为外祖父孟嘉写的这篇传,王瑶先生系于元兴元年(402)①见王瑶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2页。,逯钦立先生系于隆安五年(401)或元兴元年(402)②见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9页。,其他专家的系年与此基本相同,而这一写作时间值得高度重视。笔者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在陶渊明居丧的三年亦即恰恰是桓玄得志的那三年(隆安五年至元兴三年)中,他的作品往往有许多指向朝政的言外之意。例如《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一文为他的外祖父孟嘉立传,其中大写孟嘉与桓温的密切关系,并且特别提到:“光禄大夫刘耽昔与君同在温府,渊明从父太常夔尝问耽:‘君若在,当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人。’为时所重如此。”追叙往事,叹息孟嘉死得太早。陶渊明早不为孟嘉立传,晚不为孟嘉立传,恰恰在桓温之子桓玄继承父志夺取中央政权最为得意之时来写这份传,并且强调自己的外祖父与桓氏家族的密切关系,说一点言外之意都没有是不大可能的,其中很可能埋伏着深刻曲折的政治上的计算。
史载桓温早怀异志,多次试图夺取中央政权,都没有能够实现,到最后则要挟晋简文帝“临终禅位于己,不尔便为周公居摄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愤怨……寝疾不起,讽朝廷加己九锡,累相催促。谢安、王坦之闻其病笃,密缓其事,锡文未及成而薨”(《晋书•桓温传》)。桓玄做到了他老子想做而未能做到的事情。而就在桓玄一度代晋自立的前后,陶渊明忽然为孟嘉立传,大谈自己的家族与桓氏家族的历史渊源亲密关系,这显然绝不是偶然的无意的。[9]
陶渊明的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他对东晋王朝完全没有忠心耿耿、奉若神明的意思,当时持陶渊明这种态度的士大夫相当不少。
[1]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马星翼.东泉诗话:卷一[M]//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230.
[3]高亨.周易大传今注[M].济南:齐鲁书社,1979:179.
[4]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M].北京:中华书局,2006:595.
[6]皇甫谧.高士传[M]//四部备要:第四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15-16.
[7]周振甫.诗品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66.
[8]顾农.陶诗二首解读[J].古典文学知识,2005(5):24.
[9]顾农.从陶渊明《述酒》诗说到他的政治态度[J].文学遗产,2017(2):4-15.
(责任编辑:刘中文)
Five Miscellaneous Discussions over Tao Yuanming
GU No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9, China)
In Tao Yuanming’s poems, the occasional use of divinatory symbols from The Book of Changes is quite to the point. Therefore, the ancient comment that “the divinatory symbols used in Tao’s poems are unintelligible” is inaccurate because the critic based his remark on the wrong edition of Tao’s works. Tao’s poems rarely touched upon the affairs of the time, and usually made light of the major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ffairs considered by the general public. Tao Yuanming also took a light attitude to life and death, and stated straightforwardly in his poem Eulogy that the sorrow of death would diminish and disappear soon or later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which showed his deep understanding of life philosophy. Tao’s poems involved numerous historical fi gures, and some of these people were not quite famous, but they are worthy of careful study as they were related to Tao’s individual life experience and re fl ection. Tao Yuanming wrote a biography for Meng Jia, and talked a lot about the historical origin and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own family and the Huan Family, which revealed to some extent his political attitude. Tao Yuanming showed no loyalty to and worship of the East Jin Dynasty, and the practice was shared by quite a lot of scholars during the time.
Tao Yuanming; current affairs; life and death; historical fi gures; political attitudes
I206.2
:A
:1008-7931(2017)04-0054-07
10.16217/j.cnki.szxbsk.2017.04.004
2017-04-10
顾 农(1944—),男,江苏泰州人,教授,研究方向:中古文学、鲁迅学。
顾农.陶渊明杂述五题[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4):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