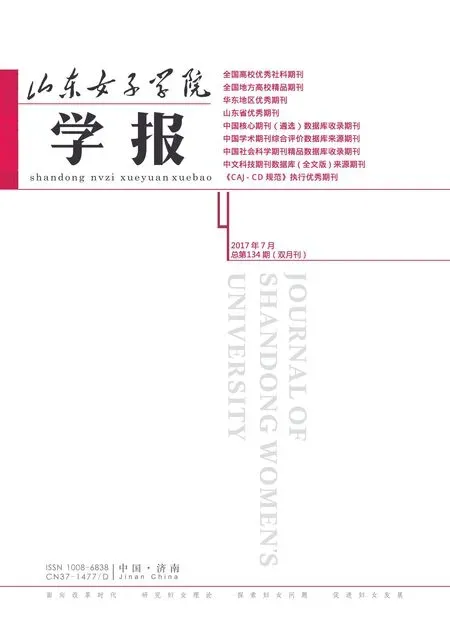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本解读为依据
李岁月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恩格斯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文本解读为依据
李岁月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的经典之作,尽管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但其理论仍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女性解放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因此,女性要转变传统观念,从历史维度正确认识自身社会地位的转变并积极改善;消解传统婚姻观念,树立正确的婚姻观;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妇女解放理论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为解决当代女性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对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女性解放;当代启示
女性解放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恩格斯并非女权主义者,其理论出发点和归宿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P276)。为了实现女性解放的共同目标,学者们较多以婚姻家庭为轴心,围绕家务劳动是否生产剩余价值、家务劳动是否应该社会化、有酬家务劳动以及社会性公共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它是一个涉及社会学、经济学、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交叉性问题,因此探讨并解决这一问题对于新的时代条件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真正实现女性解放乃至全人类解放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出版于1884年,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解放的经典之作,尽管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但其思想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试图以《起源》文本为依托,充分挖掘其思想内涵,结合现实探讨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对当代女性解放事业的启发意义。
一、转变传统思维,维护女性自身权利
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随着社会发展尤其是婚姻家庭形式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按照恩格斯在《起源》中的分析,其主要经历了从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再到文明时代的专偶制即现代所说的一夫一妻制,而与之相伴的便是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蒙昧时代,主要是基于群婚制的两种家庭形式,即血缘家庭和普那路亚家庭,后者是前者的高级形式,按照恩格斯的分析,即“凡血亲婚配因这一进步而受到限制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姊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2](P49)氏族的建立便是这一进步的最好证明,因为“它构成了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2](P49),这也是社会历史进步的助推剂。“在氏族制度内部,还没有权利和义务的分别;参与公共事务,实行血族复仇或为此接受赎罪,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这种问题”,“正如吃饭、睡觉、打猎究竟是权利还是义务的问题一样荒谬。同样,部落和氏族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不可能的”[2](P180)。“在包括许多夫妇和他们的子女的古代共产制家户经济中,由妇女料理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事业。”[2](P86)可见,在原始氏族部落时期和共产制家庭时期,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与人是平等的、各司其职的状态,男人和女人所从事的劳动无论是家务劳动还是外出猎取获得食物的劳动都是社会性的公共劳动,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劳动被“一视同仁”。而在群婚制下的社会结构与继承关系是一种母权制,但这并不意味着压迫与剥削,这些概念是不存在的,它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群婚家庭,无法确定孩子的父亲,只知其母,世系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所以恩格斯也沿用了巴霍芬定义的“母权制”这一名称,即指称“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2](P53)。
随着经济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氏族日益发达,它在巩固“习惯上的成对配偶制”和“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群婚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逐渐被对偶家庭所取代,由此便导致了“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不断缩小,直至“缩减到它的最后单位,仅由两个原子组成的分子,即一男和一女”[2](P65)。从群婚制到对偶制过渡的这种进步,妇女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古代遗传下来的两性间的关系”愈“失去素朴的原始的性质,就愈使妇女感到屈辱和难堪;妇女也就愈迫切地要求取得保持贞操、暂时地或长久地只同一个男子结婚的权利作为解救的办法”[2](P64)。但这种家庭形式的缺点在于逐渐不断排斥有血统关系和姻亲关系的通婚,使得“任何群婚形式终于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了”,直接的后果就是不稳定,容易“解体”,“不能使人需要有或者只是愿意有自己的家庭经济”,但这同时可能也与“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是多么没有关系”[2](P59)的现实有关。
相比较群婚制下的家庭形式,对偶制家庭的出现是一种历史进步,但是“它根本没有使早期传下来的共产制家庭经济解体”。共产制家庭经济的存在意味着妇女在家庭内的统治和对妇女即母亲的尊敬。因此,“在一切蒙昧人中”,甚至“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2](P60)正是对妇女地位追根溯源的历史性分析,恩格斯批判:“那种认为妇女在社会发展初期曾经是男子的奴隶的意见,是我们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所继承下来的最荒谬的观念之一”[2](P60)。
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游牧民族从其余的野蛮人群分离出来为标志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奴隶制,社会分裂为主人和奴隶两个阶级。随之而来的便是家庭的革命,按照之前的传统,“家庭内的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可是它现在却把迄今所存在的家庭关系完全颠倒了过来”[3](P181),即“谋取生活资料总是男子的事情,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是由男子制造的,并且是他们的财产。畜群是新的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最初对它们的驯养和以后对它们的照管都是男子的事情,因此,牲畜是属于他们的;用牲畜交换来的商品和奴隶,也是属于他们的。这时谋生所得的全部剩余都归了男子,妇女参加它的享用,但在财产中没有她们的份儿”[3](P181)。“料理家务失去了它的公共的性质,它与社会不再相干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服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3](P87)然而“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3](P181)家务劳动由社会性转向私人导致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即“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3](P181)。对待家务劳动地位的态度转变直接影响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男子“依恃自己的财富挤上了首位,把妇女挤到了第二位。”[3](P181)此阶段的家庭形式则是从母权制的对偶婚制发展而来的父权制下的专偶婚制,即所谓的一夫一妻制,但是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一夫一妻制。
由此可见,正是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导致了女性地位的变化:从“自由”和受到“高度尊敬”到父权制下的被压迫和被剥削,正如恩格斯所分析的:“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了”[3](P68)。这种剥削和压迫关系直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顶峰,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与此相适应,“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3](P87)。
通过对婚姻家庭形式的历史性溯源分析得知,女性的地位以及两性关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当代女性要从历史维度认识并确认自身的社会地位,而不是理所当然地全盘接纳历史遗留的“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旧思想观念,解放思想,打破束缚,跳出封建思想的藩篱,树立新的女性理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9月在全球妇女峰会上所指出的:“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4]女性应积极发挥自身在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同时积极争取并维护自身权利,这样才有利于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
二、消解传统婚姻观念,树立正确的婚姻观
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不仅是维护家庭和谐稳固的有效保障,也是女性真正自由解放和男女平等的表现。恩格斯在《起源》中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解读了爱情作为一种关系性范畴,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提出了即使在当代社会也被广泛认同并接受的真正意义上男女平等的婚姻观,这无疑对于女性摆脱建立在传统经济或者政治利益而非爱情基础上的资产阶级式的婚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起源》中关于家庭的历史发展分析表明了原始部落“婚姻共同体”范围的不断缩小,“结果,只剩下一对暂时松散地结合的配偶”,用恩格斯的话语即是“一旦解体整个婚姻就终止的分子”,可见,“个体婚制的发生同现代字面意义上的个人性爱是多么的不相干”[3](P59)。恩格斯以美洲印第安人为例,描述了原始婚姻包办的形式:“缔结婚姻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事情(而且往往不同他们商量),而是他们的母亲的事情”,甚至“订婚的往往是两个彼此完全不相识的人……婚礼之前,新郎赠送给新娘的同氏族亲属……这种礼物算是被出让的女儿的代价”,“出让”“代价”表明此时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一场等价交换,新娘被看作是“物”,“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而这与后来逐步发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婚姻本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到极致,以最赤裸裸的交易形式出现。之后,恩格斯通过分析南斯拉夫的扎德鲁加来说明“婚姻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它绝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它同个人性爱绝对没有关系”,它更多的“是一种必须履行的对神、对国家和对自己祖先的义务”,甚至“是一种负担”。最后,恩格斯得出结论,“个体婚制在历史上决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由此可见,随着家庭婚姻形式的发展,从原始部落群婚到“所谓文明时代标志之一”的专偶制,女性地位不仅没有相应得到提高,反而降低成为男性的附庸,被奴役的对象,无法真正实现女性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伴随着以赤裸裸的金钱商品关系为突出特征的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无论是身体还是感情都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3](P96)那么爱情是何时“出场”的呢?何时成为两性建立平等和稳固婚姻的主要考虑因素了呢?恩格斯理论阐释下的真正意义上“合乎道德”的婚姻是什么样子呢?
爱情在恩格斯看来是一个历史性的关系范畴,“在中世纪以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它“是从具有性爱的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前进的地方接着向前走的”[3](P91)。爱情的角色也经历了从“试图破坏婚姻”到“成为婚姻的基础”这一漫长的路程。恩格斯并不完全同意“现代的性爱作为夫妇相互的爱完全或主要是在‘专偶制’这一形式中发展起来的”,尽管它是“现代的性爱能在其中发展起来的唯一形式”,因为“在男子统治下的牢固的个体婚制的整个本质,是排斥这一点的”[3](P83)。并且分析认为在原始部落社会或者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爱情没有或者也不可能成为影响婚姻的核心要素,“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所以恩格斯历史地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官方社会以外才有”[3](P90)。只有到了消灭私有制、摆脱物质经济条件束缚的共产主义社会,女性才能真正在自身经济解放的条件下实现感情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也永远不会再处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而这才算真正实现了恩格斯语境下的婚姻自由,即如他所指出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3](P95)。恩格斯并不是女权主义者,他的妇女解放理论是服务于社会革命理论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的,所以这种婚姻自由与解放是对于男性和女性双方而言的,“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实现真正意义上两性自愿平等以爱情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彻底摆脱“因起源于财产关系而被烙上的全部特征……第一,男子的统治,第二,婚姻的不可解除性”[3](P96)。
婚姻自由并不仅仅体现在男女两性的结合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于离婚权利的尊重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婚姻解除的任意性与随意性,婚姻是神圣的,所以,必须明确恩格斯在《起源》中分析的婚姻的解除主要是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指出“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3](P96)。按照恩格斯在分析美洲印第安人以及同时期其他民族时指出的对偶制发生背景之下“婚姻可以根据夫妇任何一方的意愿而解除”,但是许多部落对于离婚却持否定态度的社会舆论,对于夫妇不和问题,双方氏族亲属首先出面调和,只有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才离婚,但“此时子女仍归妻方,以后双方都有重新结婚的自由”。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真正意义上结婚的自由,而依旧是一种束缚形式下不平等的“自由”,因为恩格斯曾明确指出过,妇女只有“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还有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时,才“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而这种自由和被尊重地位,随着从母权制向男权制社会的过渡,及对偶时期的到来也不断发生着转变。此后,恩格斯不仅批判地分析了阶级社会中把婚姻当作“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的作法,而且揭露了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契约基础上所谓“自由平等”婚姻的虚伪性,明确这种婚姻仍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状况也只有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得到根本性转变。
三、超越资本逻辑,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
自机器大工业时代以降,资本逻辑不仅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导逻辑,更是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统摄生产逻辑的主导逻辑。资本逻辑内在地蕴含着“自由和平等”的内在价值,然而资本逻辑下人类尤其是女性的生存境遇受到严重挑战的事实,给当下通过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这一扬弃资本逻辑的路径之一,逐步改善“强资本,弱劳动”的现状,摆脱资本逻辑的统治,最大限度地实现女性解放,提供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空间。
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结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而也对社会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恩格斯在《起源》中分析指出,由于普遍的贫困,完全不需要考虑财产继承问题,直接动摇了专偶制和维护男子统治地位的经济根基,这要归功于资本主义条件下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迫使妇女走出家庭,把她们变成了“家庭的供养者”,用现代话语讲,即妇女参与到社会性公共劳动之中,也成为家庭财富的制造者,实现了经济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地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依旧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因为资本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肯定资本在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5]。同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再次肯定资本对于劳动力解放的推动作用:“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6](P69)因此,资本的不断扩展在一定意义上为女性摆脱依附关系和被奴役被统治的境遇创造了条件,但资本增殖的本性,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不会变的,全球化是资本推动下的产物,资本重构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范围内蔓延的事实使女性解放事业“任重而道远”,尤其是“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6](P70)。
恩格斯在《起源》中进一步分析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披着伪善面具出现的“劳动契约”,指出,“这种契约的缔结之所以被认为出于自愿,只是因为法律在纸面上规定双方处于平等地位而已”[2](P86)。他认为:“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3](P87)尽管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工业发展“给妇女——只是给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但“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的服务的义务,那么她们就仍然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3](P87)这一点也是受到现代女权主义者批判的,女性履行家务劳动与参与社会性公共劳动是不兼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吗?现状是资本主义条件下,部分女性尽管参与到社会性劳动中,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家务私人劳动的束缚,然而却受到家庭和社会(包括丈夫)多重歧视和压迫,并未扭转女性的社会地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归根结蒂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地位,资本逻辑下的“强资本,弱劳动”状况并未得到改观,这也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所以,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3](P87)。恩格斯的“消灭家庭”主张的是消灭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奴役性异化家庭形式,实现未来自由人联合体条件下即共产主义社会基于自由平等尊重的和谐完美家庭,尽管没有明确表述未来家庭,历史植根于社会历史变迁之中,每一段历程都“包含了自我消灭的因素”,但社会生产的发展所带来的必然是“更高形式上的复活”,家庭的发展亦如此。
恩格斯通过剖析女性受压迫和剥削的根源,揭示了女性解放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他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3](P88)。“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3](P181)而这一切“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3](P181)随着资本的不断扩大再生产,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断转化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结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改善,女性的地位才能得到实质性提高,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而不仅仅只是法律纸面上的平等。“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更确切地说,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7]要将女性解放与人类解放事业相结合,超越资本逻辑,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压迫,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P276)。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小结
“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所以,尽管社会生产条件和劳动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起源》中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为我们研究人类尤其是女性解放史、解决当代女性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对于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强调妇女解放事业是无产阶级革命与全人类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恩格斯妇女解放理论也必将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发展和进步,为不断探索女性解放提供指引。我们应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为最终实现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作出积极贡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习近平在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EB/OL].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9/28/c_128272780.htm,2015-09-28.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89.
[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论述摘编[M].北京:学习出版社,2001.5.
(责任编辑 鲁玉玲)
On Friedrich Engel’s Female Liberation Theory and Its Present Application: Interpretation of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
LI Sui-yu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is acknowledged as a Marxist classic about female liberation. Although it has been created for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its theory still shows inspirational significance. Female Liberation is not only a historical problem, but also a realistic problem. Therefore, women should change their traditional viewpoint,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ir social status historically and try to improve actively. They should forsake traditional marriage concept and have a correct view of marriage. They should overcome the logic of capital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Up to now, the theory of Female Liberation in this book still maintains strong vitality, and provides a powerful theoretical tool for the new project of contemporary female development.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improve women’s social status and achieve the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Friedrich Engel;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 female liberation;the present application
2017-05-03
李岁月(1989—),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等研究。
C913.68
A
1008-6838(2017)04-0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