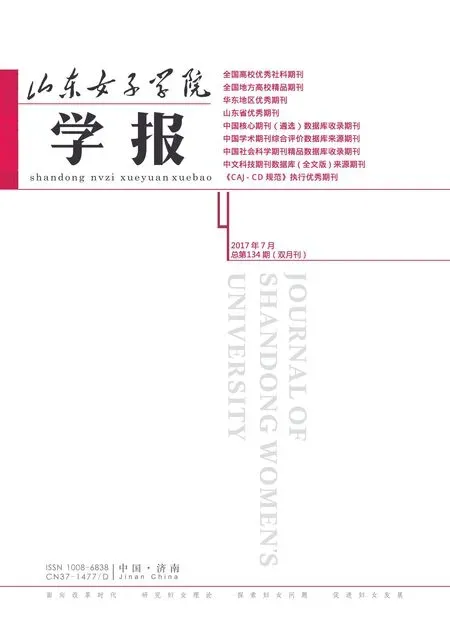男女不平等: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谈起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男女不平等: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
——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谈起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北京 100730)
私有制导致男女不平等在私人领域——家庭出现,进而产生基于生理性别的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市场隔离,并使男女不平等不断扩大和深入。直到机器大工业突破生理限制,逐渐打破男性在工业领域的霸权地位,使女性参与到社会各个领域,从家务劳动的束缚到工场手工业带来的家庭劳动工资收入的转变,再到家务劳动开始市场化、社会化,女性在私领域被压迫被剥削的根基逐渐动摇。但生育和性别角色定位对公私领域性别分工的强化在短期内难以改观,女性因生育以及养育等引起的劳动能力降低甚至劳动中断,使得男女在公共领域的平等尚难以彻底实现。需要通过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完善生育保障制度、消灭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构建平等的性别文化等,来最终打破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并实现男女平等。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男女平等;性别分工;生育价值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深刻阐述了男女不平等的起源是私有制,并指出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路径:生产资料公有,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妇女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溶化在公共事业中,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1](P128-152)。男女不平等和妇女受压迫是阶级社会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必然地、自然地产生,但也必将会被人类自觉地、必然地消灭。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的信条外,再没别的基础。平等是一种原则,一种信条。虽然不平等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平等是自然万物的萌芽,它出现在不平等之前,并终将会推翻不平等,取代不平等[2]。追求、实现男女平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一、私有制:男女不平等的起源
私有制是女权没落男权确立的根源。恩格斯认为,家庭的产生是人口繁殖——人类自身生产的结果,最初的繁殖是无意识的,完全是生理本能的结果,家庭结构以及性、婚姻等都是一种自然、混沌的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明确,确切地说是私有制的产生,催生了以奴隶为基础的最初意义的家庭,以及相伴而生的以性(压迫与对立)为基础的家庭,导致女性成为家庭的奴隶,男女不平等在家庭——私人领域正式出现。马克思后来也指出,私有财产的存在必然造成异化劳动,也是作为人口再生产主体的女性被压迫被剥削的根源。
(一)家务劳动由公共劳动变为私人事务
恩格斯在《起源》中,分析了家务劳动由公共劳动变为私领域的劳动,妇女被限制于私领域而缺乏公共权力,导致她们地位的丧失。
在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的劳动分工处于自然状态,尚未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没有剥削。两性基于生理和生活需求进行分工,男性打猎捕鱼,女性从事采集、家务劳动,两种劳动相互依赖,男女各自为政,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男子是森林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男女分别是自己所制造和所使用的工具的所有者[1](P149)。家庭经济是共产制的,男女在经济上是平等的。“委托妇女料理的家务,正如由男子获得食物一样,都是一种公共的、为社会所必需的劳动。”[1](P127)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人类进入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除于社会的公共生产之外,家务劳动(包括生育)变成了私人事务,失去了其公共性质。而私人性的无酬家务劳动,也正是妇女无法获得解放、依然是家庭奴隶的根本原因,因为“琐碎的家庭事务压迫她们,窒息她们,使她们愚钝卑贱,把她们放在做饭管小孩的事情上;极端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工作消耗着她们的精力”[3](P289)。
(二)公共劳动与私人劳动出现冲突
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三个方面,也就是后来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到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充足的物质资料为安全的人口再生产提供基本保障,而人口再生产为物质生产提供生产的基础——劳动力。妇女既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参加物质资料的生产,又作为生育主体为社会发展与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作出贡献。但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作为公私领域的两种主要劳动,在时间和精力上又是冲突的,“如果她们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私人事务的义务,那么她们仍然会被排除于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入了;如果她们愿意参加公共的事业而有独立的收入,那么就不能履行家庭中的义务”[1](P71)。家庭劳动不被社会承认的无酬性,使得妇女要想经济独立,就必须要参加公共的社会生产活动。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转变会影响家庭照顾能力,女性就业与家庭照顾冲突更加明显。为现实生活所迫,又囿于家庭照料义务的不可或缺,妇女选择了既承担家庭责任,又参与公共生产,双重负担导致妇女身心疲惫,又因为不能与男性平等参与公共事务,所以依然不能获得平等的权利。因此,只要存在公私领域而私领域劳动不被社会承认,只要人口再生产的生育依然由个体家庭中的女性承担主要责任,男女平等就无法真正实现。
(三)个体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存在
私有制最初的萌芽是在个体家庭,现代家庭在萌芽时,不仅包含着奴隶制,也包含着农奴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同田间耕作的劳役有关的。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发展起来的对立[1](P112)。男女之间的对立亦包含其中,现代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而现代社会则是纯粹的以个体家庭为分子而构成的一个总体”[1](P128)。所以,在恩格斯看来,个体婚制在历史上“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前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1](P119)。
妇女家庭奴隶的从属地位一直延续到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开始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资本主义的家庭劳动作为工厂手工业的附属物,是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对妇女来说看似是参与社会生产的一种解放——妇女从事有收入的劳动,但实际上是资本对妇女更大的剥削,因为妇女是最便宜的劳动力,家庭劳动工作环境极为恶劣,工人没有可能改变劳动条件,而资本没有动力去改善[4],导致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生产地位。
在家庭经济理论者看来,作为一个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个人都有比较优势,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确立自己在家庭中的分工,所以,家庭内的性别分工,男性更多的是参加公共领域的有酬劳动,女性更多的负责家庭照料和承担家务劳动,是家庭经济理性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家庭内的性别分工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与制度导致,所谓的个人比较优势是文化与制度建构的,不是劳动性别分工的原因,而是结果。
按照马克思的逻辑,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导致男女两性组成的稳定组织——也成了男女两性结构不平等的物质基础,妇女被限制于私领域而缺乏公共权力导致其地位丧失,“只有现代大工业,才又给妇女——只是无产阶级的妇女——开辟了一条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让妇女走向了公共领域,但家庭依然作为经济单位而存在,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20世纪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农业土地的使用权交由个体家庭,将家庭重构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内外的性别劳动空间及分工。
二、生育社会价值的轻视: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私有制也是因生育导致的分工而产生的不平等,归根到底因生育导致的劳动的性别分工,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历史上妇女没有进入关键的生产领域,不仅仅是在压迫关系中她们的体弱所致,还由于她们在生育中的作用,妇女生育后需要脱离工作休息一段时间,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妇女在生育中所起的作用[5]。妇女在生育中承担的大量抚养教育责任是妇女不能进入关键生产领域的关键因素,而这又源于家务劳动不被社会认同、没有纳入社会发展指标。
(一)人口再生产的异化
恩格斯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人类两个生产发展的结果。“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6]两种生产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
两种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延续,从这个意义来说,物质生产是为人口生产和发展服务的,或者说物质生产是以人口生产和发展为目的的。在母系社会,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和种族繁衍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制度起着支配作用,承担生育责任的女性地位相应较高。当男性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时,物质生产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衡量指标,成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第一个历史活动”[6](P531)。人口生产仅仅成为物质生产劳动力的来源,目的变成了手段,人类自身生产被追求发展的物质生产所异化。
(二)生育导致公私领域劳动的性别分工
性别分工已从最初的基于生理差异为提高劳动效率满足生活需要的自然分工,变化到家务劳动失去公共性和生产价值的固化的“男外女内”基于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工。“女主内”的家庭内分工决定了男女之间的财产分配,“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掉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在这里就已经表明,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1](P152)。即使在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家庭内劳动的性别分工,女性更多地从事没有交换价值的家务劳动,尤其是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潜在劳动力的人口再生产劳动,势必因为在公共劳动中投入较少而处于劣势地位。而内外的区分不仅仅是家庭与社会界限的区隔,更关键的是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的差异,女性因更多地从事不被社会承认的家务劳动,难以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尊重与较高的地位。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又是相互影响、相互加强的,公私领域的劳动性别分工导致女性无论在公共劳动还是在私人劳动中都处于劣势。人口再生产相对于社会物质生产和资本积累来说成为从属角色,以人口再生产为主的女性在劳动的性别分工中相对于以物质生产为主的男性来说也难逃从属地位的命运。“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7]二者互相“促进”,造成男女不平等以及女性在社会以及家庭中的地位低下,男女不平等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
(三)生育造成女性人力资本贬值
西方新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证明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支持,而生育会导致女性人力资本投资减少与贬值。
当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的价值是以收入来衡量,雇员的生产力取决于其以前的工作技能与经验时,任何非市场活动都可能导致人力资本存量的减少。雇主由于无法精确评估每个求职者的能力,通常认为男性的生产力比女性高,因为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女性劳动者容易因生育等家庭责任比男性容易退出工作,从而增加替换或培训成本[8]。因此,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招聘男性,岗位设置时也会把重要的职位更多地留给男性,将有限的资源以及人力资本投资向男性倾斜,给男性更多的培训与进修机会,女性也可能因为生育而主动放弃培训或进修机会,在科学技术飞快发展的当代,女性职业技能无法同步更新而进一步导致其原有人力资本贬值。生育尤其是抚养孩子有可能导致女性工作中的精力投入减少甚至是职业中断,人力资本部分或全部闲置,也直接影响女性人力资本存量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研究显示,35岁以下的劳动者,母亲与非母亲的收入差距大于两性之间的收入差距[9]。加里·贝克尔对生育成本理论分析认为,在发达国家过去100多年里,妇女挣钱能力的提高是已婚妇女劳动力参加率有较大增加和生育率有较大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说明,生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父母尤其是母亲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
三、劳动的性别分工: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内容和表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之所以受压迫是因为男性控制了社会生产,而物质生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人类自身生产被挤出社会生产的公共领域,生育变成私人领域的家庭事务,变成女人的事情,妇女被公共领域排斥并囿于家务劳动之中,为男女不平等提供了“合理性”。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相互作用,性别分工导致性别不平等。
(一)社会分工导致人类自身生产的重要性退居次要位置
“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6](P15)但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两种生产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劳动越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越受限制,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6](P16)。在人类早期,相比于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发展中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在无法确认生身父亲的条件下对母亲有着高度的尊敬。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为主的物质生产成为衡量社会发展与社会贡献的主要指标,女性为主的人类自身生产退居其次,并且成为男性压迫女性、男女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和方式,“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1](P119)。
导致女性在社会生产领域处于相对弱势的人口再生产,使她们不仅地位降低,在人类自身再生产领域也失去了主导权,女性在沦为家庭奴隶的同时,也成为家庭生育的工具。朱丽叶·米切尔在《女人的地位》中提出,繁衍后代的再生产是导致妇女从属地位的四个因素之一。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也指出,生育机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女性的生育功能导致了两性权力的不平等——在孕产期,女人的基本生活来源要依赖于男人,以及建立在生理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劳动分工。“性别之间差异的自然再生产,直接导致了在阶级产生之初的第一次劳动分工,并且提供了一种以生物特征为基础的社会等级的范例。”[10]性别差异导致的性别等级和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也是女性承担主要家庭责任、“主内”而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主要原因。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政治力量和再分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种性别分隔,大幅度削减了男性对女性的剥削,但亦不能完全排除。而以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通过对劳动力最大限度的使用和压榨,不断地强化这种性别分隔。
(二)劳动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的根源
家务劳动尤其是人口再生产的相关劳动基本由女性承担,却不在市场分工体系内,劳动价值不被市场机制承认,不计入社会发展,更难以得到有效的市场补偿,女性在市场分工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家务劳动社会化、自动化、现代化等为打破劳动的性别分工提供了一定条件,但与生育相关的家务劳动依然占据女性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大量无酬家务劳动尤其是家庭照料工作因占用女性大量时间和精力,成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有偿劳动的巨大障碍,使得她们在市场劳动中处于劣势地位,成为家庭经济的依附者,这不仅使她们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家庭地位的降低,也直接影响了她们社会地位的获得与提高。经济的依附性、家务劳动价值不被社会承认降低了她们社会价值的体现。
家庭内的性别分工,直接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传统社会男性在劳动力市场的优势使得女性从家庭利益考虑而更多地牺牲自我发展,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工经由家庭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社会分工使得各生产者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分工之间的联系以商品买卖为媒介,这种分工是以生产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商品生产者之间为前提的。”[11]市场分工,作为商品交换的社会分工,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配置方式,支配着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把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处于公共领域的市场分工的产生取代了基于生理差异的平等、互助的性别分工,家务劳动不被认同,不计入社会发展体系,市场分工和性别分工使得两性不能同步进入市场,导致女性社会地位降低。所以,承担着更多家庭责任的女性与男性“平等”参与劳动力市场竞争,而劳动力市场对女性要求更高,进一步凸显了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
(三)劳动力市场性别隔离:劳动性别分工的结果
市场经济和“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性别分工使得男女两性的收入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女性更多地集中于收入低、保障低、工作弹性大的非正规就业领域,在职业间收入差距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固化的职业性别隔离。职业性别隔离又加剧了市场中的性别歧视,进一步扩大了性别差距,导致女性化职业贬值,女性人力资本含量降低、投资减少,又进一步加大了性别隔离度,形成女性职业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女性更多地集中于与家庭角色关系比较密切或者社会经济领域延伸的“服务性工作领域”,而男性则更多地集中于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社会声望较高、收入较高的职业。
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使得职业的性别隔离从制度上得以确立并被文化所认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遭受歧视、劳动力市场存在性别隔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女性承担了生育尤其是养老育幼的照料责任和过多的家务劳动。现代化使得普通的家务劳动可以通过家政服务的发展得到解决,但生育和抚养则是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家庭无酬照料劳动的贡献通常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也没有进入对GDP的计算或是常规的劳动力调查。对于女性来说,家庭无酬照料劳动限制其劳动力参与和职业选择,这是导致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性别工资差距等的主要原因[12]。生育对女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身体的,即短期内体力劳动的弱势,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照顾孩子占用的时间和精力有可能减少女性投入工作的时间和精力,使得用人单位产生统计性性别歧视。
Polachek通过研究指出,男女劳动者都根据“理性化”原则选择其职业类型,女性之所以会集中在那些低收入的“女性化”职业中,是因为女性“理性地”选择了那些人力资本投资比较小且可以让她们兼顾家庭的职业[13]。长期以来,女性在劳动就业中受到不公平待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社会观念对生育性质认识上的性别盲点,将抚育责任单方面推给女性的结果[14]。而就业歧视贯穿女性求职、雇佣、工资评定、晋升机会与退休福利的全过程。所以,就业性别歧视和女性职业发展受限是所谓个人“理性选择”和用人单位“统计歧视”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管理角度来说,连续在业是对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女性因生育中断职业,职业稳定性减弱、职业积累减少,会减少她们进入管理层的机会,个人能力提升受到影响,会进一步影响到职业阶层和收入水平的向上流动。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男女不平等问题,首先要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
四、重建男女平等: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
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社会主义国家为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公共领域提供了机会与政治保障,妇女大规模地参加到社会生产中,在法律政策保障下公共领域的性别分工逐渐走向平等。但因生育造成的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依然存在,个体家庭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社会发展以物质资料生产为衡量指标;因生育而带来的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等家务劳动作为家庭私事由女性承担与社会对生育社会价值的轻视,以及历史形成的女性在资源和技术方面的劣势和因受教育程度、社会观念的影响女性潜力的开发还远远低于男性的状况在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等,都限制了女性平等权利的实现。因此,需要对生育的社会价值进行认同与补偿,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和男女责任共担等。套用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上的一句口号:“分一半权力给女人,分一半家务给男人。”
(一)生育社会价值的认同与补偿:完善生育保障制度
人口再生产对社会物质生产的附属性导致的男女不平等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根本原因,生育虽然是女性独特的生理机能,但也是一种社会职能,需要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在恩格斯看来,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这两种生产相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妇女在人类自身生产中的作用具有社会价值,“性和生育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部分”[15],养育孩子是“一件极其重要又极根本的社会事业”[16],人们通过生育创造新生命,为物质再生产提供劳动力资源。“生儿育女的妇女对国家作出的贡献决不小于用自己的生命抗击侵略成性的敌人来保卫家园的男子。”[17]罗素认为:“孩子是属于国家的利益,而不是父母的,他们的费用理应由国家支付,而不应让这沉重的担子落在父母身上。”国家应在生育中承担主要责任,包括建立足够的幼儿园和托儿所为已婚已育妇女提供托幼服务,使她们能够继续从事结婚前所做的工作;以及为愿意照看自己孩子的妇女发工资,当孩子长到一定年龄时保障妇女可以重操旧业[18],以体现家务劳动尤其是儿童照顾的社会价值。社会主义国家要重新确立生育的社会价值与意义,改变生育的“女性化”认识,由国家和父母共同承担抚育下一代的责任。在实践中,要建立健全生育保障制度,推行社会统筹的生育保障模式,由政府兜底来保障和补偿女职工因生育给个体、家庭以及所在单位带来的“性别亏损”,减轻个体与家庭在生育中的责任。
(二)打破劳动的性别分工:家务劳动社会化与市场化
家务劳动虽然在家庭内完成,但它是公共生产劳动在家庭的继续,是社会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的一部分,所以是一种社会劳动,不能作为私领域的劳动由妇女以无酬劳动的形式完成,因为“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妇女事实上仍然是受束缚的,因为全部的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19]。因此,一方面要推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只有在废除了资本对男女双方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生产部门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20]。“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开始了反对这种琐碎家务的普遍斗争,更确切地说,开始把琐碎家务普遍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那个地方和那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妇女解放。”[3](P289)实践也证明,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等公共服务和福利可以很好地解决妇女参加社会生活和料理家务的矛盾,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完善的针对家庭和育儿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家庭友好政策,更为宽松和平等的职业环境等都有助于消除就业歧视,推动女性就业和男女平等。另一方面要推动家务劳动市场化,将家务劳动作为社会生产劳动的一种,进入劳动力市场,从事家务劳动的劳动者(不再局限于女性)与其他社会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一样,享有各项劳动权利与保障。
(三)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提高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
公私领域的性别分工被打破,男女平等进入公共领域,但如果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与隔离未能消除,女性依然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不利地位。研究表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提高人力资本能有效提高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更好地打破职业的性别隔离,从而打破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一是要缩小男女在教育资源方面的差距,在国家财政加大教育投资基础上,提高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尤其需要提高女性在创造性学科中的比例,缩小不同学科的性别差异,提高女性进入高端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二是将教育投资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与就业密切相关的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尤其是中等职业教育中,能够快速提高职业技能,将资源惠及更多的女性,增强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三是在职业规划与培训中将资源适度向女性倾斜,尤其是高端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能培训。政府和企业都要将更多的培训资源给予女性,给女性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为更多的女性提供专业的职业规划指导等,保护和支持女性拥有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为女性参与物质生产提供充分保障,使女性平等获得就业权和职业发展机会。
(四)促进男女平等:重构平等的性别文化
社会主义革命扫除了旧观念、旧思想,法律上的平等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确立和实现,工业化尤其是高科技推动社会生产力不断进步,第三产业的兴起使得男女可以在真正意义上从事完全平等的工作,女性的社会参与程度和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和能力大幅增强,男女平等有了理论和实践的支撑。但男女不平等依然在各个领域广泛存在,主要是性别分工的方式大部分是传统习惯规定下来的,根深蒂固的性别角色观念对男女不平等进行了沿袭与强化,固化的“男外女内”的传统性别文化更多地期待女性扮演好家庭照料者的角色[21]。因此,要使男女共担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共享家庭权利与社会权利。一方面要从制度政策上保障两性在公私领域平等的权利与责任,“分一半权力给女人”;另一方面要宣传男性的家庭角色,推动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变革,动员男性从社会走向家庭,“分一半家务给男人”。家庭事务代表的不仅是责任,也是权利的实现,照料子女不仅是责任,也可以培养良好的亲子关系,更好地享受子女绕膝的幸福与快乐,为重新进入社会生产积蓄能量。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A].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法]皮埃尔·勒鲁.论平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5-20.
[3] 列宁.伟大的创举[A].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4] 列宁.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家庭劳动[A].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186-189.
[5] 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19.
[6]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C].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7] 海蒂.哈特曼:资本主义、家长制与性别分工[A].李银河.妇女:最漫长的革命[M].北京:三联书店,1997.74.
[8] Dennis J.Aigner, Glen C.Cain.StatisticalTheoriesofDis-criminationinLaborMarkets[J].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1977,(30):30.
[9] Crittenden A.ThePriceofMotherhood:WhytheMostImportantJobintheWorldisStilltheLeastValued[M].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2001.45.
[10] 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性的辩证法[A].[美]格伦斯基.社会分层[C].王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89.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89-394.
[12] Elson D.LaborMarketsasGenderedInstitutions:Equality,EfficiencyandEmpowermentIssu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9,27(3):611-627.
[13] Solomon Polachek.OccupationalSelfSelection:AHumanCapitalApproachtoSexDifferencesinOccupationStructure[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1981.58.
[14] 薛宁兰.社会性别与妇女权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8.
[15] [美]阿利森·贾格尔.女权主义政治与人的本质[M].孟鑫,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03.
[16] 费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73.
[17] [德]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299.
[18] [英]罗素.婚姻革命[M].靳建国,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139-140.
[19] 列宁.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A].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95-296.
[20] 恩格斯.恩格斯致盖吉约姆-沙克[A].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30.
[21] [美]R.H.罗维.初民社会[M].吕叔湘,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88-89.
(责任编辑 赵莉萍)
Gender Inequality: From Private Space to Public Areas
HUANG Gui-xia
(Women’s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Beijing 100730,China)
Private ownership leads to in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ir private space, which in turn gives rise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gender in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gender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the worsening of Gender inequality. Industrial production breaks through the physiological constraints, reduces men’s hegemonic status, and women participate in all areas of society, get freed from the shackles of domestic labor and become wage earners in handicrafts factories. From domestic labor to the public and social areas, women are no longer exploited for their depending position. However, gender segregation is difficult to change in the short term due to raising children and fixed gender roles. Moreover, the decreasing of labor capacity or disruption of labor caused by childbearing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en and women to achieve equality in the public sphere. Achieving gender equality requires the acknowledgement of reproduction’s social value and social protection for maternity, equal gender culture, and elimination of gender segregation in the labor market and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reas ultimately.
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PropertyandtheState; gender equality;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the value of reproduction
2017-05-02
201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类)“男女平等价值观研究与相关理论探讨”(项目编号:12&ZD035)
黄桂霞(1976—),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妇女就业与保障、性别平等研究。
C913.68
A
1008-6838(2017)04-0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