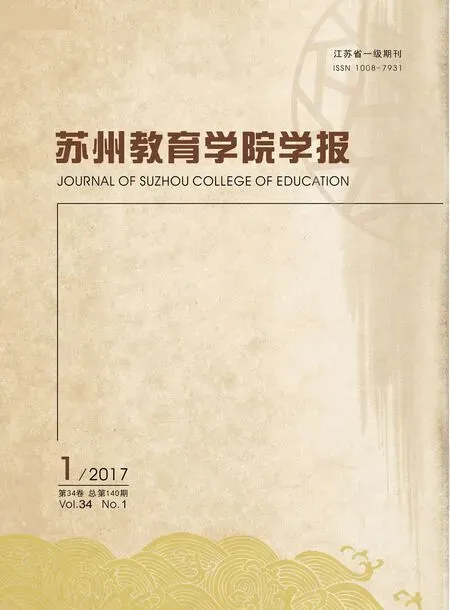刘云若诗歌论
张元卿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00)
刘云若诗歌论
张元卿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江苏 南京 210000)
民国通俗小说家刘云若本为京津地区有一定影响之诗人,惜其诗歌散见于当时报刊,生前从未结集,又为其小说之名所掩,以致时过境迁竟鲜为人知。通过探研其诗歌之来,认为刘云若诗歌主要是以竹枝体(打油体)来记录生活,讽刺现实,具有“诗史”品质,文献价值大于诗学价值,是研究民国诗歌和津沽文化的重要资料。
刘云若;诗歌;《待起楼诗稿》
析津刘云若①刘云若(1901—1950),原名兆熊,字渭贤,天津人。民国时期著名的小说家、报人和诗人。14岁随父客保定。18岁返津,入扶轮中学,其间所写话剧《结缡劫》曾在该校上演。中学毕业后曾做过列车乘务员。1926年前后,投稿《东方时报》,得编辑吴秋尘赏识,后经吴氏推荐,结识报界名人王小隐。时冯武越新创《北洋画报》,欲得一得力之编辑,经王小隐推荐,刘云若遂任《北洋画报》编辑。20世纪20年代后期,与冯氏发生龃龉,离开《北洋画报》,加盟《商报》,改副刊“杂货店”为“鲜花庄”,同时兼任《商报画刊》主撰,渐成沽上名编。1929年,小说处女作《燕蹴红英录》在天津《商报》连载,但未能完篇。1930年春,《商报》编辑沙大风筹办《天风报》,邀云若主编副刊“黑旋风”。在此期间,其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在《天风报》连载,一炮打响,欲罢不能,始致力于小说写作。20世纪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先后创作了《春风回梦记》《情海归帆》《红杏出墙记》《小扬州志》《旧巷斜阳》等五十多部社会言情小说,其中有五部小说被拍成影片,《春风回梦记》《红杏出墙记》等小说还被改编为话剧、评剧、大鼓、评弹等。1933年10月,刘氏自办《大报》,连载了《续春风回梦记》,并推出了郑证因的武侠小说处女作《风尘三杰》。后因转载《闲话皇帝》,《大报》于1935年6月被勒令停刊。1947年3月,刘云若开始主编《星期六画报》副刊“鲜花庄津号”。1948年2月,又主编《星期日画报》漫谈专版“小扬州”。抗战胜利后,开始创作以沦陷区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如《秋扇春风》《粉墨筝琶》等。1950年2月18日在天津去世。,世多目其为小说家,而罕有论其诗歌者,今欲论之,几不知话从何起?然民国文人多能诗,后世所谓通俗小说家如姚鹓雏、潘凫公、李寿民等,皆诗人而擅撰说部者,云若亦此中人也。奈何时世变易,世人为其说部之盛名所迷,竟鲜知此等人物本皆诗人也。
云若逝后,刘叶秋挽诗有句云:“世态都从腕底收,声名久溢小扬州。仅传说部宁初意,早识襟期异俗流。”②诗见刘叶秋:《旧体章回小说家剪影—忆刘云若》(载刘叶秋《古典小说笔记论丛》,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诗作于1950年春。此文后又刊于1989年2月18日天津《今晚报》。前两句乃就作品特色、流传区域来评说云若之小说成就。“仅传说部宁初意”,笔锋陡转,直言云若之“初意”非欲“仅传说部”,然则其“初意”何在?
1950年2月26日,天津《星报》刊登招司《悼刘云若先生》,竟招来一些非议,认为不必为刘云若这样一位旧文人树碑立传,云若就此声消迹灭三十余载。然非议横起之时,刘叶秋与吴小如竟在天津郊外探得云若之墓,木牌上书“诗人刘云若之墓”。此事甚奇,既已立牌,何不书“小说家刘云若之墓”,却称诗人之墓?余初亦不解。后辑校云若诗稿,忽觉诗人之牌殆障眼之法,实为随顺世议之举,因世人眼中说部写手自不敌诗人高名,以诗人之名书于木牌,正可暂避“旧文人”之嫌。今觉此举看似无奈,实有意为之,因立牌者久知云若之“初意”本欲为“诗人”,“仅传说部”非其所愿,说部固热闹于当下,诗歌必传之久远,天假以年,诗歌成就必更突出,“诗人刘云若”在其虽为盖棺之论,却深怀悯惜“初意”之心。
“初意”虽明,可毕竟乃推演所得,尚须寻绎云若实现“初意”之实绩,以相印证。
一、《津门鼓娘小选》之典范意义
1925年4月5日,上海《社会之花》第2卷第11期刊登了一篇《津门鼓娘小选》,作者刘云若。此文为目前所知刘云若最早发表之作品,文前小序写道:
曩与朋辈听雨近水楼中,灯下清谈,四壁幢幢摇人影,有击案节拍,小度清讴者,居近歌楼,风送鼓声,随雨脚入窗,来相和答。乃相与谈津门鼓娘色艺,拟其卢后王前,貌嫫母而调驴鸣者,皆不入选。朋辈各编其所爱,议论纷呶。幸余平章风月,素有能名,平停其间,终得金钗之数。虽持论未能尽平,而嗜好尚能殊俗。籍兹粉黛,遣我闲情,人系以一评一诗,附庸风雅,颜曰《津门鼓娘小选》,以示为私人所推,非出公意,且以别于令人齿冷之“大选”二字。拉杂而书,酸咸异致,雅人莞尔,俗客嗤之而已。[1]
可知此文乃云若“平章风月”之作,“人系以一评一诗”,其中列名第一者为“小月如”,文中写道:
(一)小月如
昔人语竹,谓不可一日无此君。月如亦人而竹者也。艳装素韵,不见人而见一树梨花,不闻歌而闻九天鹤唳。欢场繁灯,幻为明月,令人如坐碧山深处,听远岫鸣琴,作小山招隐之调,不知魂销几许。人固瘦削如六朝人书,然拟以飞燕,转嫌唐突西施。余听鼓三年,惟见一笑,清标可想。微论红尘十丈,即芦帘纸阁中,亦着此素心人不得。余友肇朋绝爱怜之,尝谓如此天人,当以晶玉作楼居之,风清月朗时,倩歌一曲,则明日十里内无俗人矣。古人金屋贮娇,徒使美人增龌龊气耳。歌《长坂坡》曲,至“夫人说,儿可是要乳吃么?”于悲郁中出慈爱之致,听之脊骨生寒意,戏为句曰:“倘使月儿成乳母,愿天变我作婴儿。古愁病骨轻于燕,愁煞阿侯入抱时。”可于此想见其人。歌《活捉三郎》曲,以幽怨之人,唱凄怆之调,妙固绝妙,人何以堪。“别样风流亭亭立,三郎不顾的害怕,才勾起他的旧相思。”声调凄恋,令人泥絮禅心,又动红尘一念。“劝君不结子的鲜花休着意,露水夫妻莫情痴。”此等言词,出之美人香口,真如我佛向众生宣上乘佛法。我为天公,当为雨花,我为顽石,当为点头。至师传之正,尤属难得。惜流水高山,赏音恨少,故数年津沽憔悴,无籍甚声华,可慨也。
碧玉休轻出小家,鲛丝细织泪年华。苍天何必生红豆,但祝东皇护落花。[1]
全文皆为“评”先“诗”后之结构,先读“评”,则“诗”似为余绪,然读“诗”之后反观“评”,则“评”反如“诗”之长注。前之研究者多看重此文之“评”,而将其归为散文小品,以为“刘云若的《津门鼓娘小选》在描写天津大鼓书演员时,在叙述中夹杂褒贬,便是运用中国古代史书写作的‘皮里阳秋’的笔法”①1997年《津门鼓娘小选》被袁进先生收入所编“鸳鸯蝴蝶派散文大系”之《永恒的微笑》(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社会之花》为当时鸳鸯蝴蝶派刊物,云若此文能被该刊看中,或亦因其能用皮里阳秋之法来写鼓娘色艺,然仅有皮里阳秋,并不符合鸳鸯蝴蝶派凄艳婉丽之美学追求。此文能为该刊所用,余以为首先在于“评”有凄艳婉丽之风,又含皮里阳秋之意,然“评”再好,若无艳诗压轴,终少余韵,而“一评一诗”,兼具二美,允称佳构,编者不求自得,怎不暗自欢欣?故余所属意者在“诗”,而不在“评”,且在余看来,“评”实为诗注也。如此,且略去“诗注”,先看“艳诗”:
(二)小玉香
若以诗心论眉史,鲍家俊逸庾清新。底事锋芒嫌太露,能添蕴藉更宜人。
(三)小月楼
月样双蛾故故颦,孤芳愁绪抱秋心。红儿亦有青衫感,误我文章误汝贫。
(四)小翠
风怀小勒似儿时,解听江南肠断词。谱罢霓裳一低首,教人恨煞小腰肢。
(五)刘问霞
胡姬竟似吴娃媚,塞笛能传玉树哀。底事六朝烟水气,也随名士过江来。
(六)花云仙
横波溜出小钟情,花里清弦有爱声。一种玉盘珠走意,梅花五月落江城。
(七)王瑞喜
肯与巡檐同索寞,故随春卉斗繁华。若教品入群芳谱,应是人间富贵花。
(八)高妙楼
如此丰华不自知,乱头粗服惹人思。销魂不为腰肢瘦,怜取莺喉半哑时。
(九)赵翠卿
霓裳法曲筵前谱,洛水明妆委绿鬟。若向天台逢汝笑,刘郎何事忆人间。
(十)富润卿
搴帷旧貌有秋容,稍恨容单逊彼清。一样颦颦黄瘦脸,何心月没替教星。
(十一)赵宝翠
往日繁华记尚真,鹍弦一拂一怆神。低徊商妇江船意,解赋琵琶是此人。
(十二)王鑫樵
格调清刚半似人,红纹界靥隐春痕。马樱花下侬家里,暮雨潇潇半掩门。[1]
此诗虽为云若处女作,遣词造句已极自然,情韵亦深挚,可知其娴于此道已非一日。云若何以能有此等手笔,向无人深究,其实他在评“小月楼”时已透露一些信息:
昔元稹诗曰:“第一莫嫌才地弱,些些缀缀最宜人。”能明此意,然后可以聆月楼之歌。樊山诗曰:“便逢薄怒犹堪爱,何况嫣然送盼时。”能体斯旨,然后可以瞻月楼之貌。[1]
云若为品评“月楼之歌”与“月楼之貌”所预设之标准,出自善写艳诗之元稹和樊增祥之诗句,显有以古例今之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云:“微之自编诗集,以悼亡诗与艳诗分归两类。其悼亡诗即为原配韦丛而作。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2]民国时诗坛有所谓中晚唐诗派,此派师法白居易、元稹、李商隐、温庭筠等中晚唐诗人,以才气相尚,不为义理所拘,一时蔚然成风,樊山即其中翘楚也。寅恪先生所谓“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证之民国诗歌,尤觉慧眼独具。云若以元稹、樊山之艳诗为理解鼓娘之标准,却不囿于诗句表面之情致,更希望观者能明了诗外之意旨。然则何为诗外之意旨?元稹、樊山之艳诗多为其情人所作,是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这便要求观者之于鼓娘,必先了解其隐于台上情感之后之情感,始能体会台上“嫣然送盼”之情韵。亦即观者必先有情于心,深谙古人叙写男女悲欢之至文,才可感知鼓娘唱凄怆之调,传悲欢之情时,是否能遥接古今哀怨悲欣,何处能传续到位,何处又有今人之新创,而令观者魂销。简言之,云若是以中晚唐艳诗之情韵来品评鼓娘之色艺,由此亦可窥知云若艳体诗之诗学渊源。
《津门鼓娘小选》中之诗歌虽为艳体诗,所写之鼓娘却率皆“无籍甚声华”之普通艺人,则其情不在某人,而有大爱于世间,其关怀现世之诗心并不为表面之艳体所掩,此云若艳诗与元稹、樊山艳诗不尽同之处。
此后云若亦时有艳诗问世,但多有诗注,内容渐从品评色艺扩至记录日常生活、风俗时尚,诗体也从杂体转为竹枝词体,诗以纪事之旨愈发明晰。然其纪事诗之格调与构型实肇端于《津门鼓娘小选》,其典范意义实不容忽视。
云若之纪事诗多属竹枝词,然其纪事非仅限于日常生活与风俗时尚,亦常批评时政,讽刺现实。此类诗歌已非艳诗,嬉笑怒骂,一随己意,诗体多转为打油,情韵亦背离《津门鼓娘小选》,然关怀现世之情怀终与其一脉相承。
二、诗以纪事
云若之诗,自《津门鼓娘小选》始,便有纪事之风,内容虽有人、地、事之别,实录世情之旨则一也。就诗体而言,以1934年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体式较杂,绝句、律诗、古风皆有,后期则多为竹枝词体。
前期诗歌主要有《陶园书所见》《歌场三不见》《戏咏特种捧角家》《饮冰室即景》《张园纪事》《天津小姐歌》等。题目中之“所见”“即景”“纪事”,在在表明其诗意在实录世情。试观下面两首:
陶园书所见
此处专收夜不收(“夜不收”,天津俗语,谓终夜浪游,若无家可归之人也),
游人宁止作清游(游客虽云来为乘凉,形如幽人之幽,而心似醉翁之醉)。
贴肤薄泅臀难掩(女子臀肥衣瘦,行路时于柳腰款摆中,将其臀部构造,完全表现无遗),
齐膝新妆腿善溷(妓女学时装,矫枉过正,长袍仅至膝上,腿上只着长袜,远望若揭水而来)。
小妇裙边鸡眼弄(缠足少妇,行步蹒跚,听其对女伴言,则足下鸡眼疼也),
美人肩上狗生头(时髦女人二,各于肩上掮一“羊皮狗”,狗头人面,对映甚美)。
妙哉结伴成公式,
一女双男嬲不休(最妙者,园游伴侣,多为两男一女,而行坐时,必将女子夹于中间,对对如此,似乎已成公式)。①刊于1928年8月8日《北洋画报》第210期。
张园纪事
门票三毛买(门票价,洋三毛),
冤家一笑逢(入门见一妇因其子哭喊回家,大骂冤家不止)。
猫头随处露(发蓬蓬若狮子毛之剪发女郎甚多),
鸡眼满园风(野鸡三五,大飞眼风)。
花影出深洞(假山下石洞中,时有妓客密谈),
莺声乱故宫(逊帝曾寓之楼,今改为饭庄,有人招花侑酒)。
黎明看活鬼(一夜汗蒸露侵,男女皆成活鬼),
万目尽矇眬(一夜无眠,人皆不像人样,美者亦变为丑,倦眼相看,殊觉有趣)。②刊于1930年7月13日《天津商报图画周刊》。此二诗之结构为一句一注,与《津门鼓娘小选》之“一诗一评”不同,然“注”与“评”并无本质之差异,皆意在实录世情,将诗句未能表达清晰者坐实,所异者无非篇幅之短长。再看《天津小姐歌》:
人言天津如沙漠,外见繁华内寂寞。环河背海好风光,不加点缀无颜色。中华画报独出群,立帜翻能张一军。欲探出谷寻兰蕙,故从人海选钗裙。妙哉此举非无意,多少须眉逊女子。若教湮没不得彰,秘德潜光谁之耻。比闻选事动津沽,盛况豪情前所无。恍将一幅新闻纸,幻作三津仕女图。璇闺雅望人难及,陈家小姐最称异。选票高标万有三,位号定于正月一。名媛本自出清门,交际场中众所尊。绝艳惊才追谢蕴,知音鼓瑟号湘君。一代红装山水秀,二分烟月女儿魂。芳名从此南金重,七十二沽同此盛。区区幸是里中人,原以一言辱清听。方今烽火正漫天,鼙鼓声声镇九边。还应领袖众闺阁,出为国家做盾援。或劝捐施劳口舌,或演义戏动管弦。激励津人齐振奋,即保吾津国亦全。行见一九三三年,花冠仍在小姐前。①刊于1933年1月13日《中华画报》第3卷第244期。
此即云若所谓自由韵长歌。此诗无注释,然其容量亦能大致包容注释所欲言者,况歌行之体少有注释,加注反添累赘,影响吟诵。可知此一时期,云若为诗,着意者在内容,而非诗体。
以上三首诗歌,所咏皆昔日天津“当下”之事,陶园、张园乃公园之写照,《天津小姐歌》直当日选美之通讯也。《张园纪事》中之“逊帝”指溥仪,张园即云若所游之逊帝“宫苑”,惜已成藏污纳垢之所。后世介绍张园之文章,皆言溥仪离张园后,此地竟成日军军部,而未有言及逊帝“宫苑”曾为公园之事实。《天津小姐歌》所咏为陈湘君,又名陈瑞章。陈氏被选为“天津小姐”后曾在天津荷莱坞餐厅举办加冕庆礼。此虽当日天津都市生活之一斑,可若无云若之诗为之记录,后世研究天津社会文化史或人文地理者,必无从想象当日都市生活之鲜活与变幻。而云若之社会小说亦以能真实反映此情状而为后世论者所称赞。这即表明实录“当下”,反映现实,乃云若一贯之文学主张,社会小说与纪事诗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此一时期,云若之纪事诗作,调侃多于批判,却不漠视时局,虽写天津小姐,亦有铿锵之声:“方今烽火正漫天,鼙鼓声声镇九边。还应领袖众闺阁,出为国家做盾援。或劝捐施劳口舌,或演义戏动管弦。激励津人齐振奋,即保吾津国亦全。”②同①。
1934年后,云若依旧诗以纪事,诗体却慢慢固定为竹枝词体,最后竹枝词体竟成为其诗歌之主要体式。这一时期的主要诗作有《新年幻想诗》《津门六不见诗》《春日怀人十不见》《消夏杂诗》《国大竹枝词》等。
1933年8月1日,云若曾在《中华画报》发表《津门消夏竹枝词》,表明前期他亦属意竹枝词,虽尚未将其作为主打体式,然自《津门鼓娘小选》,向竹枝词演进之趋势由此豁然明朗。试录《津门消夏竹枝词》第一首,以见转变之痕迹:
昨冬烽火六楼盛,今夏筝琶五夜繁。且乐承平忘离乱,笑携女伴上中原。
(日租界中原游艺场又重开矣,绣幕银灯,一时称盛。催吾人今日乘凉之楼,即去岁日军置炮之地。游侣皆欢喜无量,曾无憬然回忆者。区区不才,亦曾一往,哀莫大于心死,信然。)
此诗依然关心时事,依旧实录“当下”,自不待言,可注意者乃在竹枝词体之使用。王士禛《带经堂诗话》云:“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③王士禛著,张宗柟纂集:《带经堂诗话》,清同治癸酉(1873)广州藏修堂重刊本。后世论竹枝词者大多赞同王渔洋之观点,并以此为写作、辨别此体之主要标准。云若此诗以七绝状写都市风土人情,笔致琐细诙谐,复有注释补叙史实,正合乎王渔洋对竹枝词体之要求,亦符合竹枝词常体(七言四句体)之规范。
这一时期,云若诗以纪实,而多出之以竹枝词。《新年幻想诗》虽无小注,亦无竹枝之名,却是精彩之竹枝词:
年来鸡犬亦登仙,更有何人感岁阑。最是欢声腾父老,白头重睹太平年。
欃枪兵甲久销潜,不夜城中不戒严。除夕回更灯火彻,途人犹说拜新年。
一事真堪入画图,小春晴雪照庭除。儿童敲罢太平鼓,堆个雪人亦美腴。
火树银花夜欲低,屠苏酒美沁诗脾。何来入耳添年意,爆竹声喧画阁西。
垂髫小女着红衣,插朵梅花鬓上绯。含笑低言告女伴,阿爷买得锦灯归。
醅酒烹肴兴倍豪,家家欢乐庆良宵。丰年何事为凭证,门户都无债主敲。
祖母含饴向爱孙,压岁钱多且贮存。阿父今年心事好,归来任讨几多元。
结伴新年拜旧神,娘娘宫里夜香温。华严宝境今方见,殿上都无乞讨人。①刊于1934年2月23日天津《大报》,署名“若”。
《津门六不见诗》“忆其可忆者六人”,兼具艳体诗与竹枝词之风致(云若谓之“歪诗”),可见《津门鼓娘小选》之潜在影响,亦录一首:
宝扇华灯护玉人,随风咳唾散秾春。佳期十二红娘杳,不见多情马妲陈。
(津门数年前昆曲颇盛,同咏社为诸名士闺媛所立,专研昆曲,时或彩排。社中有陈女士者(不注其名,读者当亦能意料而知),美而多才艺,为交际名手,曾数登显者堂,后卒沦落不偶,退隐于津,入同咏社以习曲自娱,曾两登台演《惊梦》及《佳期》。余得瞻仰其《佳期》一剧,陈饰红娘,活泼玲珑,声清韵雅,殊为难能可贵,惟红娘所歌《十二红》一折,词颇淫艳,出诸香口,闻之令人春意满腔,不止作三日思。今陈南迁沪上,得人而事,惜已垂垂老矣。
注:第三句费解,“佳期十二红娘”六字,以白话译之,即《佳期》剧中歌十二红之红娘也。红字一材两用,嫌不合理,然亦经济办法,读者谅之。又马妲者,即法国语“夫人”之意。)②刊于1934年6月15日天津《大报》。
此一时期最有竹枝词风味,又能实录“当下”,而充盈悲悯者,为《消夏杂诗》与《国大竹枝词》。此二诗均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各录二首:
人间何事近修罗,粮贵煤荒八路多。火箭飞盘原子弹,嗟余不饮奈愁何。
(往岁暑中止酒,今岁则狂饮无度。处此人间地狱中,百物昂涨,四郊多垒,二次大战之后,又酝酿三次大战,原子弹成世界之争点,飞盘为满天之旅客,今又传火箭为毁灭人类之利器矣,当此乱世不饮何为?)
余生早欲老江村,其奈郊原战垒屯。消夏清凉寻火宅,白兰香里度黄昏。
(余久倦于都市生活,倘囊中有资,当买山而隐矣。“门外白莲三十顶”,“五月江城夏亦寒”之风味,宁不令红尘中人羡。惟然近日烽火弥天,更何处觅干净清凉境耶。只又醉生梦死于火宅中,醉卧美人膝耳。白兰花,女子所佩也。)③刊于1947年8月9日《星期六画报》第65期。
国大生儿万事足,欣看民主有萌芽。终身免票黄家子,不必摇头坐电车。
(无锡国大女代表黄卷云,于八日诞生一九磅宁馨儿,取名庆宪,报纸争传,称为国大之子。这位少爷,真会把持时机,寻最好的时候降世,不待说生产医药之费,是由国大招待处会账,而且还有许多位国大代表,要建议入会,赋予这位国大之子以白坐车船飞机的特权,可谓人世殊荣。社会上有一种特殊人物,坐电车以摇头为记,不必买票。此国大之子,必有终身免票,挂在襟头,坐车可无须摇头矣。)
梅兰芳与马连良,歌舞升平唱几场。宪政开张邦有庆,弥天烽火在何方?
(国大招待机关,特派飞机赴沪,装运第一流名伶梅兰芳、马连良等,赴京演剧,慰劳代表兼以庆祝国家元首之产生。宪政肇基,邦家有庆,升平歌舞,理固宜然,且国中烽火,远在北方,共匪宣传五月渡江,尚须有待,钟山之紫气犹新,秦淮之碧波未涸,春光正好,美援欲来,固宜及时行乐耳。)④刊于1948年4月24日《星期六画报》第102期。
竹枝词之重要特性在于广为纪事,以诗存史。不入正史之社会轶闻、生活花絮,经由竹枝词,始得以传之于世,成为修史、补史之难得资料。因此竹枝词不仅具有文学价值,亦具有社会历史价值。云若之竹枝词,兼具此两种价值,实为直录史实之诗史也。
民国时期文人写作竹枝词乃一时风尚,鸳鸯蝴蝶派文人最乐此道。旧体诗词在民初“鸳蝴”报刊多有专栏,后时势变迁才渐成补白要角。此即旧体诗词在民国之处境—即便与通俗小说同坚守传统之阵地,亦难改变其渐行落寞之运命,于同类繁华中暗自萧条。然此实“鸳蝴”诗词在公共平台之萎缩,在“鸳蝴”文人雅集之时诗词又恢复主人之尊荣,依旧“欣欣向荣”。个中原因甚多,最重要者在于众多“鸳蝴”小说家本身即为诗人,在写作通俗小说之前他们已是诗人,撰写通俗小说之际,并不曾丢掉言志抒情之旧体诗词,在私人交往中常互传诗作,以诗人自命者亦不乏人。因此,关注“鸳蝴”小说家,必要关注“鸳蝴”诗词,否则我们很难真正走进这些作家之内心,他们由诗人向通俗小说家之转型及诗化通俗小说形成等问题必难阐述清楚,故“鸳蝴”小说与“鸳蝴”诗词之研究必须要双翼齐飞。而要研究“鸳蝴”诗词,在搜罗已刊诗词专集之同时,便要在“鸳蝴”报海中打捞被时光深埋之“鸳蝴”诗词。云若诗词原亦深埋故纸,数年搜寻幸有所得,才可于今日论其得失。
昔李寿熙为刘豁公《上海竹枝词》作序云:“竹枝之歌,千余年来代有作者,多以妩谐遣兴视之。顾考其功用,往往可以补正史之阙。吾国史乘,偏重朝章国故,欲知社会风俗变迁得失,非征之歌谣杂著不为功。豁公此作,述沪蠕奢侈之习,以及人情诈伪,无不曲尽其状,视为上海社会史可也。唯诗歌之作,终不免于裁剪,则豁公所知必不尽于此。定庵诗云:‘他年青史如搜采,来叩空山夜雨门。’异日修社会史,其有叩豁公之门而索史料者乎?”[3]余以为云若之竹枝词,虽不可视为天津社会史,然异日修天津社会史,叩云门而索资料者,必不乏人。
三、时作不平鸣
明清以来,竹枝词渐以记述风土、微寓劝惩为指归。民国竹枝词亦顺承斯旨,只是内容更为丰富。云若之竹枝词亦庄亦谐,颇能刻画时代之面影,然多是微寓劝惩。如《津门消夏竹枝词》:
昨冬烽火六楼盛,今夏筝琶五夜繁。且乐承平忘离乱,笑携女伴上中原。
(日租界中原游艺场又重开矣,绣幕银灯,一时称盛。催吾人今日乘凉之楼,即去岁日军置炮之地。游侣皆欢喜无量,曾无憬然回忆者。区区不才,亦曾一往,哀莫大于心死,信然。)①刊于1932年8月1日《中华画报》第2卷第177期。
又如《国大竹枝词》:
劳民何事复伤财,盛世终逢盛会开。几万流民离市去,三千代表过江来。
(南京某报有大标题曰:“劳民伤财的国民大会”。据闻国大经费,约当美国援华贷款八分之一,可谓伤财。全国选代表以赴大会,可谓劳民。然最“劳”者乃南京下关之流“民”,因大会将开,国都为之外观瞻所系,更恐代表掇为议题,遂全部驱至外县。流民因当此励行民主之期,而国家剥削其居住之自由,不胜愤慨,又饥而无食,遂效奸人匪行为,共人之食矣。)
满江春水流民泪,一朵红妆国大花。代表沪杭多似鲫,嬉春谋国好生涯。
(国大会场中花絮纷披,美不胜收,有“国大之花”“国大之疤”“国大之子”等新兴妙词,不胜闲情逸致之至。而当此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杭州西湖,沪上龙华,皆不少代表芳踪。谋国嬉春,并行不悖,固人生乐事也。)②刊于1948年4月24日《星期六画报》第102期。
然云若所处之世,时事之变幻常有出乎其主观意愿与忍受限度之外者,竹枝词体之诗以纪事、微寓劝诫,不足以独自承载其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精神苦痛,“抑郁填胸臆,时作不平鸣”③刊于1927年8月16日天津《益世报》,署名“刘兆麟”。,云若之诗遂更为多样,情感亦由微讽渐化为悲愤,甚至痛骂。
1933年3月14日,云若于《商报》发表杂文《打死虎》,认为对于张宗昌、汤玉麟等人,“在他们凶势炽烈时,才是舆论发动真力的机会,早应该群起而攻,使之有所畏忌,或者笔尖儿横扫五千人,把他们赶走,替民众解除痛苦,但那时我们都正躲在阴影里打战,直到老虎自己害病死了,大家才‘走路捡鸡毛凑胆子’,同声相应的骂个剌剌不休,死虎有知,也当匿笑”。又写道:“如若打死虎是可怜可鄙的事,那么,算起总账,我便是个可怜可鄙的人,所以现在彻底明白,以前虽对失去一省的汤玉麟曾经攻击,但如今对负失去四省全责的张汉卿先生,却再不置一词,且进一步祝他飞机安稳,并受南方民众爱护。”①云若:《打死虎》,刊于1933年3月14日天津《商报》。斯时“凶势炽烈”,竹枝词之婉讽已难作为舆论“发动真力”,故云若常有嬉笑怒骂之杂文见诸报端。此一时期,杂文虽多有,诗作却不减少,竟常出现在杂文中。如《呜呼!老命》结尾,云若赋诗讽刺汤玉麟:
承德已随小鬼去,此地空将老命留。老命一逃不复死,热河从此算真丢。汽笛鸣鸣察哈尔,烟土销销□□②按,原文如此。楼。日本追兵何处躲,长城难入使人愁。
老命相拼载誓书,热河终不任沦胥。缘何上将飞神腿,先为家财抢汽车。崔董有兵偏不打,孙翁无助势随输。他年娱老津租界,铁像修成骂有余。③云若:《呜呼!老命》,刊于1933年3月8日天津《商报》。
此时,云若之情感虽甚悲愤,文字亦嬉笑怒骂,然还是微讽,情感犹能把控。抗战胜利后,金融崩溃,民生凋敝,云若身在其中,自有切肤之痛,其情感便难抑控,诗虽依旧嬉笑怒骂,意志却已迫近拍案痛骂之境矣。
1947年之《不想汉奸想什么?》写道:“近日物价高涨,一飞冲天,多谢大时代的提携,人们能吃到每斤三千元的玉米面,中国岂止个个富翁,而且个个贵人矣……即沦陷时期,棒子面亦未至三千元高价也,所以我主张把大汉奸们都赶快枪毙,斩绝根株,勿留迹象,若弄得汉奸都留了遗爱,那真太残了。”④《不想汉奸想什么?》,刊于1947年5月31日《星期六画报》第55期,未署名。此即云若必须面对之时代。1948年云若《妄谈改币》写道:“自从民国二十四年,中国用英国李滋罗斯的计划,脱离银本位,停止现银流通,民间存银交给政府,由政府发行法币以来,直到如今,已是十四年。这十四年中,我们一直过着纸上生活,到如今政府又用美援来改革币制,改为虚金本位,颁行金圆券,用这种金圆买东西,好像物价暴落,又可以数圆数角数分计价,每袋洋面由三千万落到八元,这真是个奇迹,几疑又恢复了三代唐虞之盛。但是仔细算算,我们才知道已变到穷得可怜的程度。就收入方面说,譬如一个中级公务员,每月薪水三百元,说来总不算少,依二十二日报纸上公务员待遇调整条例,以四十元为基数,三百元以下者,余数按百分之三十计,那么余数二百六十,变成七十八,再加四十,成为一百一十八元,折合法币是三亿五千四百万,美哉多乎,但若折成战前的银币,就只有五十九元,呜呼惨矣。”又写道:“我们在花用金圆以后,不免发生叹息,叹息我们都变穷了。”又道:“还有人主张以后最好大量的发行五角硬币,事为补救,只是又恐怕老百姓因久别情浓,竟而藏诸箱箧,传给子孙,不肯再拿出来,而市面飞舞仍是纸币。我们只有仰天祷祝,金圆券能如诸葛亮渡泸所入之地,永远不毛。”⑤刘云若:《妄谈改币》,刊于1948年8月28日《星期六画报》第120期。杂文常被喻为“匕首”,然能“发动真力”之诗歌实亦为“匕首”,其穿透作用抑或要甚于杂文。此时云若之诗即如“匕首”,《妄谈改币》中之七律实为此杂文之点睛笔,诗云:“金圆虽好惜为券,还得兼金抵一银。十四年来桑海变,方知举国尽穷人。新币颁来手艺高,民心终是爱泉刀。纸堆久已惊风鹤,敢向青天祝不毛。”⑥
此诗虽直刺时弊,然情韵流于驳议,已有打油意味。寓诗歌于杂文,诗歌必浸染杂文之腔调,此文体并置之必然结果也。至于打油味,则不尽是文体并置所能使然,云若情感由悲愤转为无奈,自会玩世不恭,而玩世不恭见之于文字,见之于诗歌,自不免打油复打油,亦不足怪也。
此外,云若本就不以打油体卑,反乐于“正经”诗歌中添抹打油味,以示不随流俗,故其打油之味,其来有自也。且看1932年之《烧饼歌》:
前者秋君撰《开滦观剧记》,涉及爱情问题,好事者公开研究,多所揣测,羽高君谓秋君发奋为雄,冰心六郎辩田君不甘人下,各执一词,未能两可。而缺德君竟代订互惠条约,勒令公平交易,必使扑朔迷离,雌雄莫辨,揖让进退,上下相孚,理或宜然,德实缺尽,且因羽高君有“羡煞吾侪”之言,因劝其另组一班,对台唱戏。岂将如《红楼梦》中所云,令各当事人“大家公公道道的贴一炉烧饼”乎?因录宋版古本刘伯温烧饼歌,为缺德君进一解。
劝君早把烧饼卖,卖了烧饼烧饼在。居家可以交朋友,出门省得带铺盖。外观只少菊花纹,内秀应加木耳菜。君今不卖也徒然,带进棺材枉朽坏。①刊于1932年1月17日《天风报•垃圾集(二十七)》。
此诗为论战之作,打油亦为战法,然细揣词意,云若实以此自喜。1935年《新年幻想诗》云:
似闻粥厂寿臣开,林总苍生喜出灾。乞丐有衣皆锦帛,窝棚无处不楼台。飞机再掷传单下,落地方知法币来。大众发财齐救国,“管他娘的”好枪排。②刊于1935年12月31日《北洋画报》第1342期。
诗末写道:“相声专家张寿臣,善说‘开粥厂’笑话,所述待遇贫民之优厚,足使富人垂涎。今当民困难苏之际,若延张君为粥厂总办,实行其政策,行见灾黎得救,鸡犬升天。尤有幻想者,则常时飞机之散放传单者,若改为投掷法币,使穷人尽成富翁,其乐何如?救死之后,势宜救国,倘再有声言‘国家事管他娘’者,枪毙无赦可也。”③同②。由诗注反观此诗,则可见此打油味之“不平鸣”,犹有竹枝词之韵味,以今语言之,是为“混搭”。
云若之诗由“不平鸣”竟成打油调,诗体亦由竹枝体变为打油体,终未能返璞归真,竟止于“混搭”,不止今人惋叹,时人亦早有规劝,奈何诗人薄命,终未及修成正果。
四、君是诗中霹雳手
云若之诗多为竹枝词,其他诗作或为艳体诗,或为打油体“杂诗”,“正经”诗作并不多,与诗人之名似不相称,却颇得时人赞许。马克吐冷《记刘云若》云:“云若以写小说得名,其实他的诗词骈体,尤见功力!不过,他因为写小说写的‘得以’了,所以索性搁下诗词了,但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依然佳什连篇,方地山、金息老、章一山都钦佩他的诗才。”④刊于1948年5月7日《一四七画报》第21卷第1期。云若自以写小说作为资生之计后,疲于应对报纸连载,未再专注于诗,故常是“兴之所至,偶一为之”。之所以“佳什连篇”,得前辈称赞,因云若确有“诗才”。
云若最早之诗自是《津门鼓娘小选》,然囿于“一评一诗”之结构,“诗”因“评”起,亦从属于“评”,即“评”主纪事,“诗”专言情,其任务实在补“评”之情韵之不足,故以艳体为之,以申余韵,然以独立之诗绳之,则内蕴尚不完足,未能独立于“评”而存在。即便如此,《津门鼓娘小选》艳体之功力已不寻常。此处所欲言者,乃在云若之诗才并非仅在艳体诗、打油体“杂诗”,其“正经”之诗,亦具诗才。
《次和梦天丁卯秋日集玉溪句金陵战事感怀二绝》刊于1927年9月5日天津《益世报》,诗云:
石头城下激风雷,苦战虫沙鼓角催。龙虎江山争霸地,眼明蜃幻几楼台。
西风残照又秋深,抚事诗人百感心。拈出义山凄婉句,江南是处足哀吟。①刊于1927年9月5日天津《益世报》,署名“丁丑生”。
此为云若早年之作,既不“打油”,亦不滥情,乃中规中矩之七绝。或有人曰:中规中矩亦可谓之有“诗才”乎?答曰:所谓诗才,非自以为是逞能之才,乃善依法度,能于规矩之中自用其才之才。云若之诗才,即能于规矩之中自用其才之才。能中规中矩,然后才有自家面目。云若此诗之长处,在中规中矩,然尚未有自家面目,此其不足。然亦不可遽然否定其诗才,须知古今有诗才者甚多,有自家面目者却稀如星凤,因诗才乃就能力而言,而面目所强调者乃在个性。云若写诗之才能世多首肯,然其诗歌之个性却少有人言,因晚清民国为传统诗歌最后之辉煌,能诗者大有其人,个性鲜明足与唐宋诗家比肩者,亦不乏人,云若之诗在其时代并不突出,既不足与陈三立等“同光体”诗人争胜,亦无法在樊樊山等中晚唐诗派中压倒时贤。云若之诗虽无鲜明之个性,然其追求个性之努力,既已实现其诗以纪事之初衷,复可见旧体诗在新时代求新求变之艰难足迹,亦不应忽视。
云若《陈散原先生诗》曾自道学诗心得:“先生之诗,积册累帙,愚读之殆遍。世谓其古体诸作,风格最高,近体七绝,则非所长,不似天琴老人(樊山)犹能以短兵取胜。其实,自愚观之,殊不尔。《散原精舍集》中,七绝俊品,随叶可见,读者自不察耳。偶发旧箧,得□敝纸,上录先生绝诗数首,盖愚早年□讽诵而成忆者,辄著于此,以见俊赏。”文中随录陈氏七绝八首,现录两首,略见云若早年之欣赏趣味。《楼望》云:“嫋嫋高云过雁残,满楼山色酒杯寒。墙西合抱数行树,剩倚斜阳带泪看。”②刊于1933年4月4日《大报》,署名“云”。《立春夕对月》云:“鸦衔缺月在檐端,丑石疏花负手看。漫向今宵数城柝,微风吹酒是春寒。”③同②。云若早年欣赏者,为此类“绝诗”,似乎不甚喜欢散原之古体诗,然散原古体诗乃其作为同光诗魁的代表性作品,由此可见云若并非“同光体”之赏音。云若之诗,以议论见长,嬉笑怒骂充盈其间,但不屑于锤炼字句,故作生新,意蕴亦不深隽,实为有诗才而无风格之诗。云若曾学散原,却不屑于锤炼字句,亦无力追步散原诗境,但有些诗竟有散原之味道,如《铙吹歌》:
胡天十月雪漫漫,一骑飞还夜叩关。接驿五更传捷火,前军进扼贺兰山。
将军知是霍骠駣,壮士神闲惨欲骄。千帐月明闻号令,齐追突厥向临洮。
战罢阵云冻不开,冰原洒血接轮台。将军斫得贼王首,双挂鞍鞯跃马回。
回乐峰前晚角哀,报闻虏骑拂晨来。月明先作沙□饮,拾得人头是酒杯。
冰为甲胄雪为裘,万士单衣卧战沟,夜梦何人呼杀贼,将军一笑扶吴钩。
白雪皑皑好墓田,葬身何必定青山。拼将十万男儿骨,扩作秦城第二关。④刊于1936年12月2日《天风报》。此亦可证云若确有诗才,亦有追求个性之心。然云若本是才子,非苦吟诗人,后又致力于通俗小说写作,有限之精力多耗于小说,其于诗歌,实无力“钻营”,有时亦袭用他人之诗味与词句,故难成自家之面目。
就袭用他人之诗味而言,云若似更愿从樊山处取经,因云若本亦乐为艳体也。其《暮春偶成》《过宝琴楼》《赠嫣然老七》等诗,皆有樊山风味。而其言情小说中之诗歌,亦多此调,如《春水红霞》开篇题诗:
一编何事细研摩,乱世文章涕泪多。天意江山方战伐,人情醉梦尚笙歌。
逃名宜咏闲居赋,笑口独开春梦婆。俯仰酒樽搔短发,堂堂白日此蹉跎。
天津桥上梦犹温,留得啼鹃几血痕。十里鱼盐水呜咽,一城箫鼓月黄昏。
楼中燕去空余恨,画里人归易断魂。回首前尘绮业在,凄凉玉树不堪闻。
绮梦沉沉未易醒,误人两字是聪明。事如后顾难啼笑,心到能平悟死生。
色界独来寻苦海,柔乡久住即愁城。缠绵不断恩兼怨,又惹相思笔上萦。
琴自无弦声自多,拟将心事托微波。调丝欲□中年感,取瑟疑闻子夜歌。
无可思量空咏叹,任教哀乐与销磨。春风乍白花前鬓,一笑凄然唤奈何。①此为《春水红霞》(刊于1933年3月6日天津《商报》)第一回开篇之诗。此类诗歌甚合言情小说之氛围,用于开篇则又常担负确立小说基调之作用。云若自言是以写诗之心写其小说,则其言情小说在其心中不啻为一艳体诗也。因此,言情小说与艳体诗,虽为两种笔墨,其用心则一也。此外,云若之艳体诗又有于樊山风味中透出散原“绝诗”意趣者。且看《惊遇》:
找寻旧院,遘小旋娟。文波印月,恍疑再世玉箫;瓜字含瓤,怅此华年锦瑟。一展再展,云已无心;上弦下弦,月还经眼。欲成捉搦,聊代丹青。以人喻物,同开箧之方花;以人喻人,亦入帘之魂魄。惟于思满颊,雏毕初眉,看人自看。类乎不类,可发一笑,因成四诗。
皓齿清歌宝炬明,偷声笑吐唾花馨。怓怓□写丁年影,隔雪疏棂暗一灯。
宿草红心任再芃,三年梦已不玲珑。香姜文瓦应同视,只喻开箧忆旧容。
佛作不成情可无,鬼怜相舍镜揶揄。总教天女维摩似,为报东坡戟样须。②刊于1934年《风月画报》第3卷第25期。
《春水红霞》开篇题诗,乃连载于报端给读众翻阅,故用语通俗,气韵通畅。《惊遇》则自写心曲,故遣词造句较为生涩,亦较有意境。生涩而有意境,正是散原“绝诗”之意趣,云若毕竟未能忘怀。他早年虽钟情散原“绝诗”,然于古风亦不生疏,偶作古风,多能得时贤赞许。《戏作晶社诸友歌》即此类诗作:
晶社泱泱大国风,济济多才盛此中。只以文章联气类,不将成败论英雄。连翩报道佳宾至,四壁花香饮微醉。朋欢笑语围一灯,韩贾推敲商五字。貌堂堂兮美髯张,墨守班供俱莫当。便看随手三元中,为有罗胸万卷藏。(张用陈兄美须髯,诗谜攻守俱擅长,因饱学也。)信乎可道非常道,居常有欲观其窍。大敌无怯小敌逃,胜固欣然败不笑。(陈鲁道博学多能,谋而后动,如妙手空空儿,一击不中,即翩然去。)俊人湖海有元龙,吾党夙推风雅宗。座中色变声声慢,心上花开朵朵红。(陈病树先生戏诗迷诗,每呼慢来慢来,即知将全盘要搬一下,主者惊而色变,因其每搬必胜也,朵朵红即次次胜之意。)陈侯嵚奇高华若,到处腾欢春有脚。吟哦口角动风雷,指挥笔底生丘壑。(诵洛兄推敲喜音节响亮者,昔袁子才谓用字响者必寿且贵,信然!)巍吾社长任使君,才狂心侠更温文。笑谐偶出康熙字,等闲难撼岳家军。(瑾存社长偶戏出僻字,众以为必查《康熙字典》始能识,然瑾存堂堂之阵,固长胜军也。)声威赫赫彭宫保,横挥大笔千军扫。善从勺水展江湖,更以高吟寄怀抱。(彭新穆先生人戏称为宫保,品高学粹,群流镜仰。)妻梅子鹤羡林逋,倚马高才故踟蹰。□是盲翁慵负鼓,手如道士乱书符。(节和兄风趣过人,于社中号为专家,又号盲翁,但未见其负鼓;书符者,谓其举棋不定之状也。唐突唐突。我这里给节和叩头了。)卓叟星槎称祭酒,一尘不惊辔在手。初看如碧却成朱,瞻之在前忽焉后。(卓星翁最善制谜,能使人惝恍莫辨。)华仁飞将吾所钦,设伏出奇敌莫侵。奇字杨雄应③按:应为扬雄,引文以原文为准。败北,空城诸葛定遭擒。(吴华仁兄最富韬略,遇有出奇字或以空城计尝试者,必为所败。)百忍张公目如电,不持寸铁能白战。文心转路复回峰,妙句千锤兼百炼。(张子培兄制谜极工,常获大胜。)
惟有云若称附庸,滥竽东郭追高踪。愿祝诗翁永高年,年年酒颊生春红。①刊于1936年12月2日《天风报》。
晶社为云若与其友人所组诗社,诗中歌咏了张用陈、陈鲁道、陈病树、陈诵洛、任瑾存、彭新穆、林节和、卓星槎、吴华仁、张子培等晶社诗友。云若不加入当时天津声名最著之城南诗社,却与友人结为晶社,许是因其更喜松散之小圈子,而不愿做“大组织”之附庸。此诗开篇写道:“晶社泱泱大国风,济济多才盛此中。只以文章联气类,不将成败论英雄。连翩报道佳宾至,四壁花香饮微醉。朋欢笑语围一灯,韩贾推敲商五字。”当日围灯联吟虽非绝唱,亦令后人浮慕不已。云若此诗发表后两日,天津著名诗人赵元礼在《天风报》发表和作《读云若先生戏作晶社诸友歌名章俊句逐绪纷来为之起舞乃破半夕之力步韵和之仓促成篇自嫌疏略尚乞笑正》,开篇即盛赞云若之诗:“云若放笔为古风,霍然崛起诗坛中。返虚用是能如浑,积健要自称为雄。诗肠得酒诗醇至,诗益清超酒益醉。模糊醉眼对寒灯,满纸惊鸾回凤字。”②刊于1936年12月4日《天风报》。诗中又云:“钓诗之钓却为酒,君是诗中霹雳手。”③同②。推许其诗才之意溢于言表。
元礼此诗不仅有推许,亦有批评:“登山须尚最高峰,铸句应加钢百炼。打油钉铰皆凡庸,愿君追逐前贤踪。”④同②。此语主要批评其“打油”倾向,可谓一言中的,正戳着云若痛处。云若亦自知其短,遂于元礼诗后附识云:“夙叨幼梅丈辱爱,几于逢人说项,誉为诗才,赐和鸿篇,尤见老辈爱人以德,对贱自属望深矣。惟若迫于生事,不得不弄墨舞文,脂韦媚世,思欲进修,甚苦力不从心,久自叹恧。兹当奋劢,求副所期。至此篇所论,足为学诗矩矱,谨书绅铭座,不敢偶忘也。”⑤同②。“此篇所论”,主要即指“登山须尚最高峰,铸句应加钢百炼。打油钉铰皆凡庸,愿君追逐前贤踪”而言,云若虽愿以此“书绅铭座”,然其“迫于生事”,终未能如元礼所期,追踪前贤,更上高峰。
赵元礼、章一山在题诗落款中均称云若为“云若社长”,云若既不曾加入城南诗社,自非城南诗社社长,而那时只有晶社与云若有关系,“社长”当指晶社社长。云若之为诗社社长,说明众诗友亦认可其为“诗中霹雳手”,此实云若诗人生涯极有光彩之一页,亦为其“思欲进修”诗艺之历史痕迹。
云若于《戏作晶社诸友歌》中坦言:“惟有云若称附庸,滥竽东郭追高踪。”⑥此虽谦辞,实亦有“思欲进修”却无力更上高峰之无奈。1947年3月15日,云若在《郭啸麓逝世》中称,与啸麓先生“深感知己,缘悭一面”,国都南迁后,先生退隐津门,“纵怀诗酒,为城南诗社中坚,余不能诗,岂敢附庸风雅,始终未加入诗社。津中寓耆宿,虽多知好,然迄无同社之雅,与啸麓先生尤从未一面也”⑦《郭啸麓逝世》,刊于1947年3月15日《星期六画报》,未署名。。啸麓为晚清民国著名文人,隐居津门后,常与友人在其寓所栩楼雅集,城南诗社因有郭氏加入,社事更为兴盛。城南诗社为天津著名之民间诗歌团体,自20世纪2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一直是天津旧体诗词创作之主力军,主要成员严修、赵元礼、王仁安、吴子通等皆为津门文坛耆宿,先后入社者约百余人。云若虽非城南诗社社员,但常参与诗社活动,以致后人一直认为他也是该社正式社员。虽非该社社员,然云若参与该社活动亦绝非“附庸风雅”,只是由于诗歌一途未有进境,又深恐与诗人为伍,“滥竽”其中辱没时贤,故自视为“附庸”,其谦抑如此。
2016年10月,余辑注之刘云若诗集《待起楼诗稿》已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如此,云若之诗稿亦将与其“说部”一同传世,其欲作诗人之“初意”必将因诗稿之流传而广为世人知晓,而其诗人之身份亦必将得到更为客观之认定。①云若诗作虽散见昔日之报刊,但从未结集出版,余友王振良兄有鉴于此,以为云若诗词数量可观,常促余整理,以展示诗人刘云若之风采。壬辰盛夏,余避暑乡间,某日振良兄来电,又促余整理,遂着手搜集,历时两年,初稿编竣。云若诗词向未结集,渠既以“待起楼”名其文稿(1948年刘云若曾在《星期五画报》发表《待起楼文稿•某夫人寿启》),故颜之曰《待起楼诗稿》。2013年7月,《待起楼诗稿》收入天津问津书院主编的《问津》杂志,作为其第7期印行。2016年10月,《待起楼诗稿》又被收入“问津文库”之《津沽名家诗文丛刊》,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总之,云若之诗主要是以竹枝体(打油体)来记录生活,讽刺现实,其诗具有“诗史”品质,文献价值大于诗学价值。随着《待起楼诗稿》之流布,研究津沽文化和民国诗歌者必会对其诗歌作更深入之探讨,本文只是略论,深入剖析,尚待来哲,余企望之。
末录云若《西沽展大方衣冠塚及寒云墓》,借以追悼云若,并结束此文:
各有幽怀忆可怜,曾回春梦吊婵娟。诗人死作桃花主,千树嫣红胜往年。②云若:《西沽展大方衣冠塚及寒云墓》,见1937年4月15日《天风报》。
[1] 刘云若.津门鼓娘小选[J].社会之花,1925,2(11):9-20.
[2]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81.
[3] 顾炳权.上海洋场竹枝词[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484.
[4] 刘云若.歌舞江山[M].天津:天津书局,1939.
(责任编辑:石 娟)
A Study of Liu Yunruo’s Poems
ZHANG Yuanq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Nanjing 210000, China)
Known as a popular novelis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u Yunruo used to be a famous poet across Beijing and Tianjin. However, Liu’s poems became oblivious with time passage and circumstance changes, because his poems scattered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 the time and had never been collected in an anthology, and his novelist fame surpassed the poet on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Liu’s poems shows that his poems are mainly of a Zhuzhi style (doggerel), with which he recorded life and mocked reality, and embodied the quality of a “poetic history”. Therefore, the documentation value of the poems overweighs the poetic value, and the works provide important literature for the study of the poetr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well as the culture of Tianjin.
Liu Yunruo; poems;A Poem Collection of Daiqi House
I206.6
A
1008-7931(2017)01-0013-13
10.16217/j.cnki.szxbsk.2017.01.002
2016-10-12
中国文艺原创精品出版工程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研究”;姑苏宣传文化人才重大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互文研究”
张元卿(1970—),男,山西原平人,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晚清民国诗歌。
张元卿.刘云若诗歌论[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1):1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