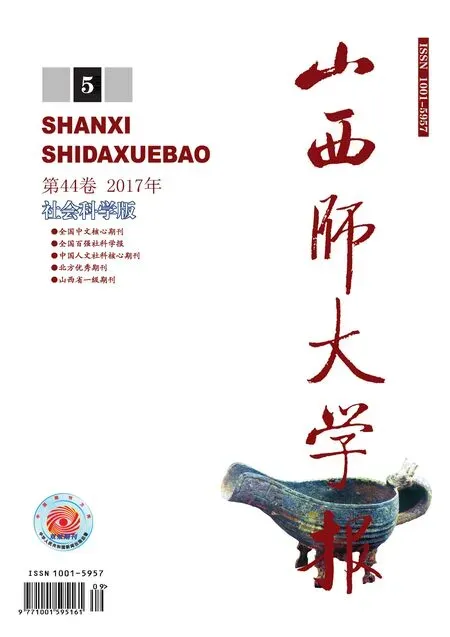从弹词《精卫石》看秋瑾的理想世界
魏 玉 莲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2000)
弹词《精卫石》是秋瑾创作的“带有自传体性质的作品”[1]67。现存完整的二十回目录和近二万字前六回较完整的内容,主要讲述以黄鞠瑞为代表的小姐群冲破封建礼教而走出闺门,与男性志士并肩担起爱国重任的故事。“作品中的主人翁黄鞠瑞(后来改名黄竟雄),就是以作者本人为模特儿来塑写的。”[2]562因此“从1875年诞生到庚子事变以前,秋瑾的思想感情充分表现在她的自传体评弹小说《精卫石》一至六回里”[3]28。人们比较关注秋瑾的诗词文,但通过这部弹词有利于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秋瑾在晚清社会巨变时代思想复杂变化的过程。
一
秋瑾丈夫王廷钧,字子芳。其家在湖南以经商发家,经营当铺,家资巨万。在这样经济富足的商人家庭里,王廷钧幼失学,缺少文学修养。而秋瑾出身官宦之家,才学出众。“婚姻是她父亲在湖南作州县官时所定的,迫于父母之命,而非她所心愿。”[4]88二人结合给秋瑾带来无穷痛苦,她早期诗歌《谢道韫》中就有“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的感叹。后王廷钧捐官到北京任职,秋瑾随行,但“伉俪之间,根本参商,益以到京以来,独立门户,家务琐琐,参商尤甚,迹不能掩”。[4]109参星与商星永不能同现于天,可见二人关系之对立。留学日本期间,秋瑾给哥哥秋誉章信中斥王廷钧“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5]35“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5]38,秋瑾对他愤恨到极点。不过直到秋瑾轩亭被斩杀,二人夫妻之名仍存。但从情感上而言,二人早已彻底破裂。
秋瑾将这段不幸婚姻放置到弹词《精卫石》女主人公黄鞠瑞身上。黄鞠瑞十四岁时,苟家提亲下聘。苟父“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人”。苟公子“刻待亲族如其父母样,只除是嫖赌便不惜金银。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改更。虽只年华十六岁,嫖游赌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恃豪华不理人”,这明显是王廷钧恶行的再现。黄鞠瑞出身仕宦之家,“满腹文才,罗衣锦绣,为人又英武又义侠”。苟公子与黄鞠瑞在家庭和品行方面差距甚大,是秋瑾自我婚姻的真实写照。弹词中言及古代江南才女谢道韫、朱淑真、袁机有此相似命运,谢道韫有天壤王郎之叹,朱淑真浓愁深恨,精神苦闷,袁机遭丈夫高氏非人的虐待。秋瑾以历史语境下才女真实婚姻经历为依托,提出典型才女俗子式的婚配。如果说才子佳人包孕男性幻想的圆满,那么才女俗子匹配则凸显女性面对客观残缺婚姻的愤怒。秋瑾作为封建婚姻的受害者,这一婚配方式的提出颠覆女性以夫为天的奴化思想,敢于以俯视姿态居于主动地位而贬男,隐藏着女性对丈夫志趣相投的理想化祈盼。谢道韫、朱淑真、袁机对婚姻不满却承受着,但秋瑾在晚清男女平等思想影响下以实际行动挣脱夫权压制与依附,求得学问而独立。
黄鞠瑞婚姻虽是秋瑾以自我经历为原型,但秋瑾对她的婚姻结局却略作改动。弹词中黄鞠瑞订婚而留学,男方的恶是旁观者鲍夫人以全知的视角道出。而秋瑾亲历了订婚、结婚、生子、留学的整个过程,丈夫的恶是以妻子的视角在生活中获得的。秋瑾将黄鞠瑞结婚及其婚后经历直接舍掉,与旧式婚姻隔离,带有婚姻理想化的色彩。因为结局这样处理后黄鞠瑞可以直接避免遭受婚后种种不幸。一则封建社会婚后的女性受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思想的吞噬,卑微如奴。秋瑾在给哥哥的信中说道:“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为人奴隶,何不自立?”[4]35可见其婚后生活极度不如意。弹词《精卫石》中也抨击封建婚姻关系中女性依附性的奴隶地位。“说甚夫为妻纲之谬语,妄自尊大便骄侈。”“三从更是荒唐话,把丈夫抬得恍如天帝尊。……般般须听夫之命,一事自为众口腾。”“一生女似为牛马,又似那买断奴才把主跟。”这是男尊女卑下不平等婚姻的真实写照。如果封建社会女性不结婚,可以直接避免封建社会夫权的迫害。二是封建社会妻妾制度也导致女性婚后面对冲突不断的家庭生活。秋瑾曾帮助陈范妾湘芬、信芳摆脱妾的身份而独立,陈范女儿陈撷芬本来许配给粤富商为妾,也因秋瑾干预而没成,可见秋瑾是反对妻妾制的。弹词《精卫石》也揭露了妻妾制的危害。善良的黄鞠瑞母亲遭妾欺,义结金兰姊妹梁小玉因妾所生而遭到嫡妻及其儿子的虐待。封建社会妻妾间尖锐矛盾必然导致一方受到伤害。黄鞠瑞不结婚,这种风险自然就剔除了。三是没有事实婚姻可避免孩子的牵绊。秋瑾因自己留学只好把女儿安置在北京好友家,后来女儿被女仆艰难地带回湖南。秋瑾将黄鞠瑞设置为逃离夫权压制的环境,没有子女的牵绊,妻与母角色的舍弃,这映射出觉醒的女性在家庭与社会天平上暂时的失衡状态,是女性从封建家庭出走到社会的必经阶段。因为她们无法将封建男权社会的礼教规定从贤妻良母角色上剥离,只能将贤妻良母固有角色一起丢掉,然后与男性一样在社会活动领域自由驰骋。
秋瑾不仅以更改黄鞠瑞婚姻结局来传递美好意愿,而且还在弹词中直接道出理想化的婚姻观。两家有情谊的陶在东认为秋瑾对“大抵李易安管夫人之际遇,最所心羡”[4]110。徐自华《秋瑾逸事》回忆与秋瑾日常生活打趣细节,提到孙夫人配刘备,徐淑配秦嘉。在秋瑾心目中男女婚姻注重的是精神契合。晚清随着男女平等思想深入人心,秋瑾理想婚姻在志同道合的基础上又契入了新的时代特点。弹词中黄鞠瑞言“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书说自由权,并言男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她通过书报获得了男女平等、天赋人权思想,因此理想婚姻中切入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弹词中黄鞠瑞云:“此生若是结婚姻,自由自主不因亲,男女无分堪作友,互相敬重不相轻。”掌控婚姻的是男女当事人,摒除尊卑等级观念,志同道合,相互敬重。不仅如此,黄鞠瑞还提出了学堂式婚姻,这是以女学堂逐渐兴起为基础的。“学堂知己结婚姻。一来是品行学问心皆晓,二来是情形志愿尽知闻,爱情深切方为偶,不比那一面无亲陌路人。”封建社会包办婚姻最大的弊端在于缺少男女间彼此了解,而学堂是增强了解的公共场所。据《日本留学生调查录》1901年12月记录,留学日本只有三位自费生,次年夏天,二十多名赴日求学,而到1907年,留学日本女性只有四百多名。秋瑾在《精卫石》序指出女同胞“虽有学堂而能来入校者、求学者,寥寥无几”,这可以说是实情。女性入学堂少的客观事实也意味着学堂式婚姻方式实践起来不易。而在国内封建顽固势力依然强大,1907年正月学部向清政府上奏《女学堂章程》,其中明确指出要彻底根除不谨男女之别和自行择偶之风,赞成父母择婿,女子以服从为主。由此可见晚清封建顽固势力仍然维护礼教。虽然学堂式自由婚姻提出有理想化色彩,在晚清社会付诸行动有一定难度,但它是以男女相互了解基础上的结合,因而具有合理性与前瞻性。
二
兴女学是秋瑾关注的重心,也是晚清社会关注的时代焦点。早在明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里,李贽认为女性在品德、学识方面胜过男子,而且还列举中国古代二十五位女性。随着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兴办女学,但带有文化侵略性质。维新派“以进化论,‘天赋人权’,民权平等思想为武器,积极宣传男女平等思想,为妇女解放大声疾呼”[6]69。兴女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早期改良主义的维新人士因参加洋务运动接触到西学,也有他国游历的经历,国外女学发达给他们强烈刺激。王韬《漫游随录》、李圭《环游地球新录》、郑观应《盛世危言》等提到了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日本等国的女学情况,他们在中外比对中积极主张兴女学。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把兴女学理论提升到新高度。梁启超从经济学角度强调教育能使女性自食其力,摆脱依附性强的奴隶地位。他还提出教育能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7]19的“贤妻良母”主张,同时他意识到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女性能够自立谋生,国家财富自然增加而变强。可以说梁启超的女学观将个体、家庭、国家较为合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还带有一定的封建局限性,但对中国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秋瑾与维新思想密切关联主要是在北京期间。她随夫入京,结识了邻居吴芝瑛,二人义结金兰。吴芝瑛丈夫廉泉,思想倾向维新,1895年著名公车上书,他把自己名字写入名单里。他又开设文明书局,出售新学书刊,因此秋瑾“在吴家经常阅读当时的新书新报”,[4]212吴芝瑛在《秋女士传》中云:“凡新书新报,靡不披览,以此深明中外之故,而受外潮之刺激亦渐深。”[4]68秋瑾以书报为媒介接触到维新思想,女学观明显受到梁启超的影响。吴芝瑛在《纪秋女士遗事》中概括秋瑾观点:“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事事仰给男子。”[4]71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中国女报发刊辞》《敬告姊妹们》等文中控诉女性没有丝毫自主性,生活如囚徒,指出女性挣脱被奴役地位最重要的是求学问而自食其力。
秋瑾在京期间不仅受维新思想深刻影响,而且还结识日本人服部繁子,坚定了留学日本的决心。服部繁子是由日本政府派遣到中国京师大学堂任教的服部宇之吉之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要求侄女吴芝瑛陪同初到北京的服部繁子,这样秋瑾因吴芝瑛得以结识服部繁子,从而加深了对日本女学的了解。正如王时泽《回忆秋瑾》云:“京师大学堂日籍教授服部博士之妻极力称道日本女学之发达,她就决计突破家庭阻力,东渡留学。”[4]199可见,秋瑾是在维新思想女学观和日本女学兴盛的双重影响下决定东渡的。
弹词《精卫石》中的黄鞠瑞深受维新思想影响而求独立。黄鞠瑞“妹的先生甚喜维新,近购得此种书报示妹,并为指点外间情形;若是家中,何能得有此种书看”。因以维新思想妹夫为桥梁,黄鞠瑞才能在封闭闺阁空间接触到新思想,这妹夫有廉泉的影子。弹词《精卫石》的女学观侧重女性求学问而独立。作品中指出男性“设出‘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话出来,欲使女子不读书,一无知识,男子便俱可自尊自大的起来,竟把女子看得如男子的奴隶、牛马一样”。封建社会男性为维持两性关系中的支配地位而弱化女性智力。因此女性“不思自立谋生计,反是低头过矮檐”。黄鞠瑞主张女性“有了学问,日后必可自立的”。
既然求学问而自立,日本女学的发达就成为留学的最佳去处。在弹词中,日本女子“学校皆同男子等”,男女有权进学堂学习。“不同我国但学经和史”而是“哲学理化学并然,工艺更加美术画,师范工科农业完”。专业多样,课程设置文理兼备。最重要的是女性受教育后可从事不同的社会职业。她们“出外经商女亦有,学堂教习更多人”。“电局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院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物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可见,日本女子受教育后能从事不同职业,自食其力。
秋瑾笔下的黄鞠瑞不仅自己留学,而且梁小玉、鲍爱群、左醒华、江振华四位女子与她一起成功东渡。秋瑾自身是启蒙思想的接受者,但弹词中黄鞠瑞成为启蒙他人的核心人物。为了突出其主导的身份,首先弹词《精卫石》对黄鞠瑞形象进行了美化。作品中反复渲染其外貌不凡,侠风烈烈,以彰显她出类拔萃。梁伯母眼中的黄鞠瑞“只见那黄女生来貌不低,容如美玉口如脂;淡淡春山含侠气,冷冷秋水显威仪;举目自如无俗态,谦和举措不骄侈;傲骨英风藏欲露,行为如不受拘羁”。丫鬟秀蓉眼中的黄鞠瑞:“只觉侠骨稜稜,英风拂拂,目虽美而有威,眉虽疎而含彩;精神豪快,身体端庄。”梁小玉眼中的黄鞠瑞“多豪爽,侠骨英风见面含。虽非国色天香艳,秀目修眉樱口鲜,面如鹅蛋红间白,姣妍终究带威严。行为好义和怜苦,装饰惟求朴素焉”。可见黄鞠瑞是古代传统女性温婉美貌和男性雄姿英发相融合的一个形象,“傲骨”“侠气”“侠骨”等词反复运用彰显出黄鞠瑞热心侠义的德行,这是她主动担当启蒙者与引导者不可或缺的内在精神。
其次,弹词中女性留学遇到的经济和家庭两大难题被轻易化解,留学顺利是秋瑾理想化的结果。弹词《精卫石》黄鞠瑞是偷拿了家里订婚筹的钱,而且无偿救助身无分文的梁小玉。在黄鞠瑞引导下,鲍爱群、左醒华、江振华也变卖首饰筹钱。另一方面,为解除留学时家庭阻挠,黄鞠瑞巧设一计。鲍夫人过寿时,女儿鲍爱群到寺庙为她祈福,在寺庙五位女子汇合一起成功留日,完成了走出闺门的第一次跨越。实际上,秋瑾借黄鞠瑞形象淡化了民间自费女子留学的困难,虽然母家成为女性夫家缺失的物质支撑者,但也不易。秋瑾赴日第一次是托人变卖首饰而得的。第二次归国筹学费,母亲“单夫人典卖衣物,筹措了几百银元给她回日读书”[4]215。为省钱,秋瑾云:“往返者数,搭船只三等舱,与苦力等杂处。长途触暑,一病几不起。”[4]72备尝留学艰辛。秋瑾之所以将留学难处遮掩,与弹词《精卫石》创作目的的教化意义有关。秋瑾创作《精卫石》“写以俗语,欲使人人能解,由黑暗而登文明”,其目的是想激励更多女子能自振,困难的淡化有利于减轻她们自振的阻力。
最后,弹词《精卫石》中把启蒙对象理想化。其一,留学女子群具有平民化倾向。弹词中鲍爱群、左醒华、江振华均为年龄相仿的闺中小姐,出身官宦之家,衣食无忧,才华横溢。但梁小玉是妾生,受到封建礼教与嫡母双重迫害,生活如奴。黄鞠瑞对刚认识的丫鬟也表明想救她跳出奴坑的意愿,这打破了封建社会的尊卑等级观念,渴求建立一种平等互助的关系。梁启超、经元善等创办上海女学堂,所招女生要求是闺秀,奴婢和娼妓被排除在外,带有明显的封建局限性。求学群体下移扩大,秋瑾前瞻性的眼光是正确的。其二,受启蒙者自身对所处境况有不满情绪,具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弹词中的她们不是匍匐封建礼教下的奴从者,而是介于愚昧服从者和完全觉醒女性之间的群体。她们处于封闭性强的宅院,但生活体验使得她们思想上自发产生叛逆情绪。梁小玉母亲是妾,对封建妻妾制愤恨不已。左醒华才学出众的“女儿无地谋生计,幽闭闺房了一生”。女子不能自由出入社会而谋职挣钱,因此“心中常愤世轻女,胸中壮志日飞腾”。江振华痛斥婚姻中“夫为妻纲”之苦,鲍爱群倾诉“绣花之苦”。这类群体经适当地引导很容易挣脱封建礼教禁锢而走向进步。
三
秋瑾留学日本,在学习的同时也接触到爱国志士,革命意识日益浓烈。在1905年春第一次归国期间,由徐锡麟介绍,她加入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冬,为挽救祖国危亡而组建的,地点在上海,发起人是蔡元培、龚宝铨、陶成章,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以推翻满清政府,收复河山为宗旨,因而光复会有反满的种族主义色彩。光复会“有浓厚的地域性,会员大抵是浙江人,多数又是绍兴府人”。[8]172蔡元培、陶成章、徐锡麟、龚宝铨、鲁迅、许寿裳、章太炎、秋瑾等都是浙江籍人。“光复会前期,由章炳麟、蔡元培、龚宝铨主持,总机关在上海。中期,由徐锡麟、秋瑾主持,总机关在绍兴。”[9]633归国后秋瑾由普通会员而成为光复会的核心人物,她到杭州新军界发展光复会会员。后主持大通学堂期间,以光复会会员为中心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同时,加入革命队伍,她已做好牺牲的准备。她在《致王时泽书》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而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5]47《鹧鸪天》:“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身。”《寄徐寄尘》中言:“恩宗轻富贵,为国作牺牲。”可见秋瑾暗地筹备反清革命时已做好献身的准备。这份无畏的大义根源有二:一则源于秋瑾炽热的爱国情怀。秋瑾喜欢读爱国情深的杜甫、辛弃疾的作品。在《敬告姊妹们》云自己“是个最热心去爱国、爱同胞的人”。[5]13给侄儿《致秋壬林书》云:“但凡爱国之心,人不可不有。”[5]46二则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女性应担救国大任,“把妇女运动紧紧地与反帝爱国和反清革命联系起来,号召妇女投身民主革命”[6]210。陈天华《警世钟》明确提出国之危亡妇女应救国,邹容《革命军》强调女性为国民一分子,应与男性一道救国、建国。秋瑾深受影响加入救国事业成为骨干力量。
弹词《精卫石》中五位女子留学日本期间由陆本秀和史竞欧的引导而加入光复会。光复会“唯以报祖宗的仇,光复祖宗的土地,为自己的汉人造幸福,不求虚名誉,不畏艰难,必要取所失的土地为目的,不愿为他族之奴隶”。光复会舍弃个体利益以实现崇高的政治目的,加入光复会实际意味着女性加入了救世救国的大业中。弹词以华胥国君臣昏昧来突出女性加入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弹词中的华胥国,皇帝喜欢睡觉,民间叫睡王。而臣子“一入了宦途,不知如何,就会生出糊涂病及近视眼来,曾有人批评过的;实因利欲熏心,污臭入目”。因此,“外人见他们自己这样糊涂,就人人来想他这个土地,这个这里割一块,那个那里分一处,各各霸占了去”。“矿山铁路和海口,一齐奉送与洋人。”“年年赔款如斯巨,亦是搜罗百姓身。”华胥国现状实际就是晚清时局的再现,清政府割地赔款媚洋人,对百姓进行残酷压榨。光复会虽以复汉去满为宗旨,带有狭隘的种族思想,但华胥国统治阶级太腐朽而实有推翻的必要性。
弹词不仅鼓励女性加入革命,而且把她们加入革命的深度提升到无畏生死的理想境界。秋瑾《精卫石》序中云:“余日顶香拜祝女子之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继罗兰、马尼他、苏菲亚、批茶、如安而兴起焉。余呕心滴血以拜求之,祈余二万万女同胞无负此国民责任也。”罗兰因法国革命而被送上断头台,俄国虚无党苏菲亚参与暗杀沙皇而被杀。作为国民一分子,她们义无反顾参与救国事务而牺牲。同时,秋瑾在弹词中举出两个真实人名,即邹容和史坚如。邹容创作了革命派号角的反清力作《革命军》,被捕死于狱中。而史坚如因暗杀清官失败被杀。秋瑾实际上给了挣脱封建压制的女性一个方向上的指导,女性摆脱了奴隶的身份,就扛起救国的责任而不怕牺牲。
弹词除了渲染女子救国外,还虚构了男女齐心成功推翻政府,实现共和的理想。弹词第一回里虚构了一个理想的仙宫,瑶池中王母娘娘见人间怨气弥漫,召集成仙的男女下凡到人间。这些女仙都是古代在才学、军事方面突出的女子,如左棻、谢道韫、秦良玉等。而男仙则是忠君爱国的英雄,如岳飞、宗泽、文天祥、史可法等。男女仙都是德行崇高之人,“男和女同心协力方为美,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焉。唤醒痴聋光睡国,和衷共济勿畏难。锦绣江山须整顿,休使那胡尘腥臊满中原”。弹词《精卫石》从第七回到第二十回完整目录,我们可大致看到黄鞠瑞回国后与爱国志士一起尽各种努力。第十二回“天足女习兵式体操 热心士扬独立旌旗”,第十六回“拔剑从军男儿遍义勇 投盾叱帅女子显英雄”,第十八回“姊妹散家资义助赤十字 弟兄冲炮火勇破白三旗”,第十九回“立汉帜胡人齐丧胆 复土地华国大扬眉”,第二十回“拍手凯歌中共欣光复 同心革弊政大建共和”。男女共同努力,不怕牺牲的,推翻胡人统治而最终建立共和,这是一个理想化的结局。
秋瑾借弹词《精卫石》寄托理想,这是弹词创作的一个固有传统。弹词这一文体女性化特征较为明显,其创作和阅读者多是女性。女作家往往借助女易男装的情节模式,实现自己的宏图美梦。《玉钏缘》中谢玉娟、《安邦志》中冯仙珠、《再生缘》中孟丽君、《榴花梦》中桂恒魁等都是女儿身,但她们易装为男,中状元、建军功、为宰相,达到古代男性事业的巅峰。女子隐匿自我性别而以男性面目出现,但最后真实身份暴露,又回归封建传统家庭,女性在封建社会出将入相的美梦化为虚无。弹词《精卫石》虽然也以女儿面目参与社会事务,但她们最终并没有回到贤妻良母的封建女性角色里,而是一直维持着身先士卒的女革命者形象。不仅如此,秋瑾在《精卫石》中所提出的社会理想最终都变成了现实。对于婚姻,维新人士很少全方位探讨过,后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尖锐地批判封建礼教:“‘五四’以后婚姻自由的观念在智识阶级里似乎已经普遍化了。大多数人已经觉得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10]3991931年《中华民国法》对婚姻方面加入了法律的干预,削弱了封建家长特权。在女子教育方面,辛亥革命后掀起热潮,1922年实行“壬戌学制”不仅是第一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而且制度上规定了男女受同等教育的权利,在女子教育史上有重大意义。而在共和理想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派号召女性积极投身反帝反清的民主革命当中。辛亥革命成功后于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它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和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诞生。弹词《精卫石》等文学作品在革命理想实现中显然是功不可没的。
[1] 郭延礼.秋瑾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3] 穆长青.秋瑾评传[M].兰州:甘肃教育学院,1982.
[4] 郭延礼.秋瑾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
[5] 秋瑾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上海:中华书局,1989.
[8]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 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M].沧州: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
[10]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